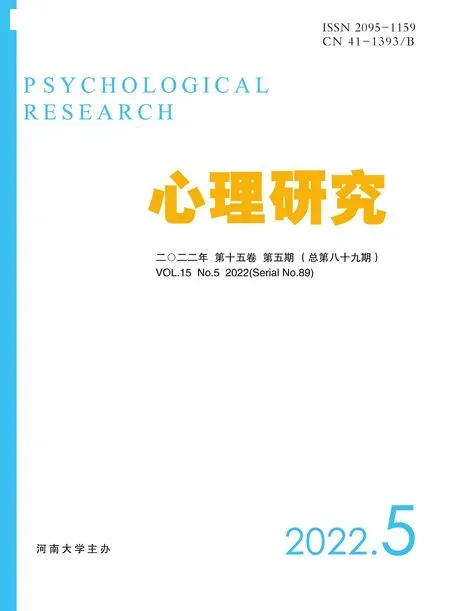数字迷信与消费行为:影响机制及边界
徐凯强 秦学者 侯佳雯 汪 玥 赵 娜
(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89)
1 引言
认知心理学认为, 个体对于外在刺激物的加工包含认知、存储、提取三个阶段,其中数字是个体进行决策时主要的外部线索之一。例如,个体可以通过商品的价格判断商品的吸引力,认为 4.44 比 8.88 的价格更加吸引人(Adaval, 2013)。
数字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人们每天都会面临与数字相关的决策。如购买几个甜甜圈,购买价格为多少的手机, 亦或是购买哪一单元或楼层的房屋。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些与数字相关的决策大都是在“理性人”的基础上做出的(Tversky & Kahneman, 1974)。 然而,一些心理学家指出,个体决策时也会受到数字迷信等非理性信念的影响(Bhattacharya et al., 2018)。 他们发现,个体在采用大脑表征系统解读量化刺激物属性时会受到数字迷信的影响, 进而对用不同数字表示的同一商品产生不同的需求,最终选择8.88 这一更为吉利的价格。 换言之,数字迷信迫使个体违反了效用最大化原则,最终趋于不理性。
数字迷信是指整个社会、 民族所共有的数字信仰, 即一个数字的发音与外界的客观事物之间存在偏离了科学概念的因果关系, 进而有了积极与消极的额外意义(Hirshleifer et al., 2018)。 当前有关数字迷信的研究集中探讨了数字迷信对房地产(Fortin et al., 2014)、股票(Bhattacharya et al., 2018)、车市 (Agarwal et al., 2014)、 通信行 业 (Chen &Tsung, 2016)等多个消费领域的影响,同时数字迷信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关于数字迷信综述研究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但当前综述研究对数字迷信与消费关系的讨论较少。 如陈永燕等人(2009)只是使用数字迷信以佐证迷信源于观察学习的结论,而郭昱琅等人(2016)只是单独讨论了非理性信念对消费的影响。 因此本文拟从数字迷信造成消费者消费行为改变的视角入手, 首先综述数字迷信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接着总结数字迷信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边界及研究方法,最终探讨数字迷信未来的研究方向, 以期能对消费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有所启发。
2 数字迷信对消费的影响
2.1 产品满意度
不同数字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研究发现,消费者普遍高估带有积极数字迷信商品的满意度, 这是因为积极数字增加了消费者的积极情绪;相反,与消极数字迷信相关的商品则会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排斥(Adaval, 2003)。 Block(2009)的研究则通过加入控制组的方式严格探讨了两者关系。研究表明,在产品品牌包装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相比于数量为10 的网球袋, 数量为8 的网球袋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满意度。 Fortin 等人(2014)则以更大规模的数据库验证两者关系的科学性。结果发现,消费者普遍愿意接受存在溢价但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房屋, 并且他们对于这类房屋的评价更高。同时,消费者普遍拒绝购买地址中带有消极数字迷信的房屋, 这是因为消极数字迷信降低了消费者购买体验的愉悦程度。
但消费者对产品的数字迷信存在 “失灵” 的情况。其一,数字迷信信念所引发的满意度变化这一现象伴随着消费者产品所有权或类别专业知识的增加而恶化(Homburg et al., 2006)。 其二,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消费者满意度存在“反噬”现象,致使产品失败等糟糕情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Chen &Tsung, 2016)。
2.2 品牌忠诚
品牌忠诚是指使顾客产生一种对企业有利的认知态度和重复购买行为, 其中数字是消费者感知品牌的重要线索(Siguaw et al., 2021)。语义加工理论指出, 品牌营销成功的关键在于激活消费者的积极内隐记忆, 其中积极数字迷信可以显著预测品牌标识敏感度, 而消极数字迷信则会增加消费者与品牌的心理距离(Yong et al., 2012)。 之后这一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有研究者发现,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品牌名称更受欢迎, 并且消费者进行二次回购、 积极评论与分享的概率更高 (Block &Kramer, 2009)。 相反,包含消极数字迷信的品牌则会遭受更多的警告与投诉(Ang, 1997)。 Wang 等人(2012)的研究则进一步在控制产品熟悉性的前提下验证了这一关系。他们发现,积极数字迷信可以增加消费者对于陌生公司品牌的识别。同时,这一关系在跨文化背景下依然成立。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于包含积极数字的外国品牌有着更高的忠诚度(Magnusson et al., 2011)。
2.3 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是指消费者出于谋求某种社会地位的动机而进行的消费活动, 其中数字迷信是常见的炫耀手段(杜伟宇, 许伟清, 2014)。 如 Agarwal 等人(2014)认为,诸如航空公司花大价钱购买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号码等现象均是炫耀心理的反映,这是因为购买者普遍认为积极数字会为其带来好运。但也有研究者认为, 消费者购买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商品只是想证明他们有能力购买, 并非是数字迷信 的 影 响 (Chen & Tsung, 2016)。 Fortin 等 人(2014)在控制经济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两者关系。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会影响中国消费者对于积极迷信数字的追求,这是因为包含“8”的房屋更吉利且具有更高的价值是中国人的共识。之后,这一关系在增加了控制组的前提下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研究发现,相比于中性及消极数字迷信,包含积极迷信且更昂贵的选择在“婚宴”场景中被选择最多,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体的炫耀心理(Rao et al., 2014)。
2.4 价格偏好
数字迷信会影响消费者的价格偏好, 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对于特定价格的接受。Yang(2011)通过寻找数据库中的价格变化规律以分析北京人的价格偏好。他们发现,北京的超市商品价格中8,9 等积极数字出现的比例远远大于4 等消极数字。 同时这一关系在其他文化背景中也得到了验证,研究发现,与7 相关的公寓楼层显著正向预测西方人的房屋需求,而与13 相关的楼层则受到了西方人的普遍排斥(Antipov et al., 2015)。Jeong 等人(2017)的研究则以更大规模的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以8 为价格结尾的方式在中国最为常用,其在音乐会、体育赛事、剧院、餐厅、酒店等出现的比例高达43%,而以4 为价格结尾的比例只有5%。
其二,数字迷信会增加锚定效应的程度。研究表明, 当商品广告将价格中最左边的数字改为6,8 等积极数字或是4,13 等消极数字,均会增强个体高估最初信息、低估或忽略之后信息的偏好(Westjohn et al., 2017)。 具体来说,当价格第一位数字为积极数字时,相比于不迷信的个体,具有数字迷信特质的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更高(Wong et al., 2017)。
3 数字迷信对于消费的影响机制
3.1 情绪认知加工视角
Risen 等人(2016)使用情绪认知加工模型阐释了数字迷信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积极数字迷信及消极数字迷信的思维系统存在差异。 具体来说, 积极数字迷信所引发的积极情绪容易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启发式的加工方式; 而消极数字迷信所引发的消极情绪则会产生算法式的加工方式。 基于加工方式的不同, 消费者对于商品信息的解读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启发式会增加消费者非理性消费的概率,而算法式则增加了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审查。这一模型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 他们认为,数字迷信所诱发的情绪存在特殊性,即无论是积极数字迷信还是消极数字迷信皆会启动个体的启发式思维(Bhattacharya et al., 2018; Hanks et al., 2016; Yang, 2011)。 这是因为消极数字迷信所引发的消极情绪常常象征着“死亡”,可能会增加个体的否认与逃避倾向(Arndt et al., 2007)。 之后的研究对这一模型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认为,消极数字迷信之所以引发启发式思维是启动了死亡焦虑的结果。 换言之,对于高迷信特质的个体,他们更倾向于将消极数字理解为死亡提醒而非健康引导,而低迷信特质的个体则会采用算法式(董娟 等, 2014)。 总之,这一模型对于数字迷信与消费行为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具体机制可能会随个体迷信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如图1 所示)。

图1 情绪认知加工模型
3.2 认知一致性视角
也有研究尝试使用认知一致性模型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前人的研究中,积极数字迷信普遍具有吉祥等积极寓意, 而消极数字迷信普遍具有死亡等消极寓意。 因而,带有积极数字和消极数字的产品均会使消费者产生一定的预期。 具体来说,消费者对于包含积极数字的产品预期较高, 而对于包含消极数字的商品预期普遍较低(Wheeler et al., 2008)。
产品的实际表现与预期是否一致会影响个体的消费行为。具体来说,当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价格与美好的用餐体验结合时, 商品价格中的积极数字可以增加消费者重复购买及推荐的概率;相反,当包含消极数字迷信的价格与糟糕的用餐体验结合时,消费者会减少对此类商品的购买(Parsa et al.,2010)。 与之相反,如果积极数字迷信与糟糕的购物体验结合时, 消费者的商品满意度存在反噬现象(Demarree et al., 2005)。 而当包含消极数字的股票号提供了积极的投资体验时, 消费者则会主动避免数字迷信的影响而趋于理性投资 (Ke et al., 2016)。之后,Master 等人(2018)尝试使用认知一致性模型解释迷信对邪恶商品及绿色商品等具有典型社会意义商品的影响, 研究结果进一步增加了认知一致性模型在数字迷信对消费影响中的解释力。 总之,如图2 所示,该模型是当前解释两者关系最为适切的模型, 这一模型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 认 可 (Master & Marsa, 2018; Naomí et al.,2019)。

图2 认知一致性模型
4 数字迷信影响消费行为的边界条件
数字迷信可以影响消费已经在不同领域得到了证明,但在一些条件下,数字迷信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不一致性。 为了进一步理清数字迷信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我们提炼归纳了数字迷信影响消费行为的个体特征和文化特征, 从而为数字迷信对消费影响的差异性提供解释。
4.1 文化边界
中西方数字迷信的来源客观上决定了中西方数字迷信偏好存在边界。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数字迷信普遍与发音相关,如4 的发音与“死”相同,9 的发音与“久”一致,8 则是“发”的体现(郭昱琅, 张攀,2016);其次,中国人对于偶数也有着同样的积极情感,这是“阴阳对立相生”及好事成双观念影响的结果(刘斌, 2018)。除此之外,数字顺序也会影响中国人的偏好, 其中复数形式的消极数字更为中国人所厌恶, 而积极数字的复数形式则得到了更多的推崇(董娟 等, 2014)。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对于数字的迷信多为传说及历史事件影响的结果。 如西方人偏爱7、厌恶13 的原因是上帝7 天创造世界及耶稣在13 日遇难, 亚当与夏娃在13 日被赶出伊甸园等(Greatbatch et al., 2018)。
基于世界各国数字迷信偏好的差异, 文化成为数字迷信影响消费行为的边界之一, 而这一边界在跨文化营销研究中较为普遍。有研究表明,达美乐等西方品牌在中国的推广可能会因定价、 数量问题与中国的消极数字迷信相关而遭到抵制;类似的,中国的出口产品采用6.66 等积极价格并不会达到预期营销效果,而更为昂贵的7.77 则受到了西方消费者的欢迎(Simmons & Schindler, 2003)。
4.2 个体边界
一些个体因素也可以改变数字迷信影响消费行为的方向。 首先,相比于高教育程度的个体,低教育程度的个体对数字更加迷信, 在选择结婚日期时会主动避开消极数字(Ruiu & Breschi, 2017)。 其次,除了教育因素, 性别也是影响个体数字迷信偏好的因素之一。 其中女性在消费决策时会更多地受到直觉思维的影响,在实际行为中也会更加迷信数字(常路, 严金海, 2019)。 但之后的研究表明,在年轻的性别群体中,男、女迷信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Andrew, 2011)。 再次,年龄也可以影响个体数字迷信的程度。 研究发现,数字迷信程度存在代际差异,其中老年人普遍比年轻人更迷信 (Johnson & Nye,2011)。 最后,社会经济地位在数字迷信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来说,富人多将数字迷信作为一种炫耀手段, 而穷人的数字迷信更为虔诚(Agarwal et al., 2014)。
5 数字迷信的研究方法
数字迷信与消费行为的关系可以通过纵向研究、测量、实验的方式进行验证。 其中纵向研究大多是基于数据库进行的。 而测量主要来源于迷信信念量表中有关于数字迷信的题目, 目前尚无研究直接使用这些题目测量被试的数字迷信。 也有研究者通过实验的方式探讨数字迷信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考虑到数字迷信的直接测量并不完善, 因此本文着重介绍纵向研究与实验研究这两种方法。
5.1 纵向研究
由于迷信观念具有长期性及不稳定性的特点,以往研究者多基于纵向视角考察数字迷信。 如Fortin 等人(2014)通过 2004~2006 年成都公寓交易记录的交易价格判断成都人的数字迷信程度。 他们发现,以“8”结尾的楼层三年内的平均价格(每平方米)比其它楼层高235 元,这与成都人的数字迷信程度相关。 Ke 等人(2016)的研究也使用了这类方法。他们收集了2016 年香港金融市场1 月到6 月50 只成分股的数据,对交易量、交易次数、交易码等股票信息进行了2600 万余次的分析,最终得出香港股民的数字迷信程度及学习效应。
西方关于数字迷信的研究也沿用了这一方法。有研究者收集了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的亚裔聚集区积极及消极住址十年间的价格变化数据集。 他们发现,2004 到2011 年间,亚裔聚集区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地址始终处于溢价状态, 这可能与亚裔居民的数字迷信相关。 但在2011~2014 年期间,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地址溢价及包含消极数字迷信的地址折扣现象均已消失, 这是因为文化融入减弱了本土数字迷信对亚裔消费行为的影响 (Rehm et al.,2018)。 Burakov 等人(2018)的研究使用莫斯科一级房地产市场的数据集以探寻数字迷信与房屋销售的关系。他们发现,俄国消费者喜爱购买编号为7 的房屋,厌恶编号为13 的房屋,但这种偏好会随着溢价及折扣的情形而产生变化。总之,纵向数据库具有反映数字迷信的发展趋势及跨代效应的优点, 但基于数据库的研究并不能完全排除市场风险和交易规模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得到准确的因果关系。
5.2 实验研究
当前关于数字迷信的实验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启动实验与情境实验两种。 启动实验是指通过阅读或者想象的方式, 让参与者暴露在与迷信相关的文化氛围中,进而激发个体的迷信心理,前人多将其分为外显与内隐两种方式。 其中外显方式多为直接呈现数字迷信。 在 Kramer 和 Block(2008)进行的消费行为与迷信关系的研究中, 研究者要求台湾参与者在阅读迷信与营销行为的文章之后,对数量为8、标价含有4 及中性标签的产品满意度进行打分。 研究发现, 消费者对于包含积极数字迷信产品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包含消极数字迷信的产品。Jiang 等人(2009)的研究也沿袭了这一方法。 在积极数字迷信启动条件下,参与者被给予数字“888”,而在消极数字迷信启动条件下,他们会得到数字“444”,参与者需要判断带有这些价格标签的书包成本高于还是低于这一数字。 结果表明,相比于素数组及消极数字迷信组,个体对于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书包估价更高。
内隐启动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启动个体的迷信心理。 如 Kramer 与 Block(2008)要求实验组的参与者回忆并书写13 号星期五发生的事件,而控制组参与者需写出19 号星期二发生的事件。 结果表明,参与者在13 号星期五列出的负面关联项目明显多于19 号星期二的情况,并且参与者普遍将这些消极事件归因于 13 号这个日期。 Jiang 等人(2009)则要求被试进行阈下启动任务及填充任务, 被试需要快速判断计算机页面中字母串的元音个数, 判断正确后页面中会出现单词或者数字 (积极数字和消极数字)。 在呈现掩蔽刺激后,被试需要对自身的积极程度进行判断。结果表明,积极数字迷信引导下个体的积极程度显著高于消极数字迷信。
情境实验是指通过编制具体情境, 让参与者对情境中的人或者行为进行判断。 如Block(2009)等人要求被试想象购买数量为8 或10 的网球袋的情景(不提供价格信息,包装完全一致),之后以量表的形式评估他们的购买意向。结果表明,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网球袋更受欢迎。Chen 等人(2016)也沿用了这一方法, 他们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四种不同的手机号码购买情境中。 其中包含消极数字迷信的号码可以为消费者带来150 元的折扣, 而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号码则包含480 元的溢价。实验结果发现,消费者普遍接受包含积极数字迷信的溢价号码, 而排斥包含消极数字迷信的折扣号码。除此以外,情境实验还可以设定包含中性属性的决策任务让被试做出相应选择。 如Rao 等人(2014)让被试选择自己的婚礼日期以及与朋友聚餐的日期。结果表明,婚礼的吉祥意义促进了被试对昂贵吉利日期的选择, 而与朋友聚餐则不会考虑这一点。
6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迷信的来源及其对消费的作用及机制,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数字迷信的积极作用、数字迷信与跨文化融入、 数字迷信的测量及数字迷信的生理机制等四个方面展开。
6.1 数字迷信的积极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 数字迷信会干扰个体的正常消费行为, 同时也是许多不良消费习惯的诱因之一(Bhattacharya et al., 2018;Fortin et al., 2014)。最近的研究则尝试使用数字迷信助推个体的健康消费行为。 如Master 等人(2018)使用恶魔等象征邪恶的标签以提示邪恶商品 (指那些能够在短期内满足个体需求,但长期来看对消费者身体有害的商品)的危险性, 研究结果验证了消极数字迷信对邪恶商品风险提示的有效性。 这一结果也在另一项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研究人员发现,积极数字迷信可以增加个体对健康食品的消费, 这是因为积极数字迷信增加了健康商品的趣味性 (Naomí Muoz-Vilches et al.,2019)。整体来看当前仍然缺乏对于数字迷信积极作用的研究,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在真实情境下操纵商品表面的数字类型, 以期增加消费者的积极消费行为。
6.2 数字迷信与跨文化融入
文化会影响个体对具体数字的偏好。 其中中国人普遍将6,8,9 视为积极数字,将4 视为消极数字;而西方人则将7 视为积极数字, 将13 视为消极数字。随着世界交往日渐增多,跨文化融入似乎已经演变为一种常态, 那么这种跨文化融入是否会影响移民本来的数字偏好呢? 有研究表明,2003~2006 年间,奥克兰亚裔移民的数字偏好没有发生改变。但这种迷信价格效应在2011 年的销售交易分析中已然消失 (Rehm et al., 2018)。 Fortin 等人 (2014)在2000~2005 年间温哥华移民数字偏好的研究中则否认了这一点, 他们发现华裔居住区的吉利房屋溢价效应在2010 年后仍然存在。
两者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居住区种族的混杂程度相关。其中奥克兰的研究对象是混合种族,而温哥华的研究则是在华裔聚集区进行的, 因而温哥华亚裔聚集区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可以最大程度上保持原有的迷信偏好。 但当前对于亚裔聚居区与亚裔分散区的数字迷信对比研究较为缺乏, 这也造成了研究者总是基于跨文化视角探讨数字迷信的偏好差异,常常将某一种族或国家的数字迷信偏好单一化(Shum et al., 2014)。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跨文化融入的背景, 于单一国家考察不同亚文化群体的迷信偏好,以期为具体的跨文化营销提供参考。
6.3 数字迷信的测量亟需开发
当前对于数字迷信的研究于个人层面的考察较少, 这是因为数字迷信缺乏科学完备的测量工具。Wiseman 和Watt(2004)的研究首次将数字迷信纳入到迷信信念的考察中, 但题目仅局限于消极迷信信念的分量表, 而积极迷信信念的测量则多以好运符等概念为主。之后Brad 等人(2009)在其开发的迷信信念量表中同时加入了部分测量积极与消极数字迷信的题目。 但他们普遍将消极数字迷信的测量归入消极迷信类型,且测量范围仅局限于数字13;而积极数字迷信的测量则被归入了好运魅力, 缺乏对数字迷信的单独测量。 因而这一量表在施测中的效度受到了质疑。例如,接触数字更为频繁的人可能不会受到数字迷信的影响, 但并不能否认他们拒绝相信其他消极迷信或好运魅力 (Bhattacharya et al.,2018)。总之,目前缺乏单独测量数字迷信的工具,未来研究应基于数字迷信的特殊性开发专门的量表予以施测,并在不同文化环境下验证其信效度。
6.4 数字迷信的生理机制
以往研究对于数字迷信生理机制的讨论多侧重于迷信的不确定性。 研究者认为数字迷信的产生是在外侧前额叶的主导下完成的, 这是因为外侧前额叶与不确定性归因相关(Volz et al., 2005)。最近的一些研究集中探讨了积极数字迷信的生理机制。 如有研究发现, 积极数字使右额中上回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激活(Rao et al., 2014)。 但当前对消极数字迷信关联脑区的研究并不充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 消极数字迷信所引发的消极情绪可能与颞叶相关(Dongju et al., 2013)。 其二,消极数字迷信可能与内侧前额叶相关。 这是因为个体对消极数字迷信的排斥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可能会使自我及家人面临灾祸, 而中国人的自我与亲密他人所激活的脑区是相同的;但对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消极数字迷信似乎并不能引起内侧前额叶发生变化 (Zhu et al., 2007)。未来研究可以针对消极数字迷信影响的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研究, 明确消极数字迷信的生理机制, 以期从生理层面对消费者的迷信行为做出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