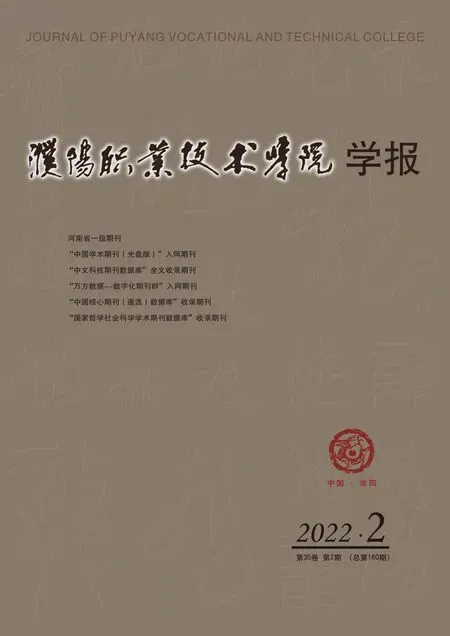诗歌:信仰与文明关怀
——昌耀、骆一禾、海子的诗歌思想
张定华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000)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奉持各种主义、分属各种流派的诗人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诗歌文本,各式富于启发性的诗歌思想、创作理念层出不穷,不断冲击旧有审美规范,给后来者以诗歌何为的认识及如何写诗的指导。尤其是1986年由徐敬亚等人发起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向公众推介了64个诗歌流派、100多位诗人的作品和宣言,使生气勃勃的“第三代”诗群集体亮相,营造出一派文学、文化繁荣的景观。然而,当人们对诗歌的热情逐渐减退,当诗人逐渐走向边缘化的位置,其写作行为趋于“常态”,我们再回过头去审视历次诗歌运动中产出的文本、理念时会发现,纵然它们确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但又大多存在着某些偏误,无法引导中国的诗歌乃至文化进入一种大气磅礴的境地。当下的诗歌写作片面强调反映个人化的真实,即将写作主体自己的生活细节、生命体验、其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独到领悟呈现纸上,于字里行间再寄予一点对中国人整体生存状态的观想,对现时代精神疾苦的揭示与关怀。这样的创作固然有其可感性,能够蕴含一定的诗意、提供一定的启示,但因其格局狭小、意境琐碎、构思平淡,很难使读者领略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得到思想和情感的升华。如果广大诗人照这样的路径创作下去,中国诗歌纵然不会流于空泛虚伪,但真正伟大的作品也难以诞生;而如此路径之所以流行,概因为当代以来,眼界开阔气骨峥嵘的经典诗作为数不多,萦系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诗歌思想亦属罕有,榜样的力量较为缺乏。虽然当代中国尚未产生如太阳般辉煌的巨匠型诗人,如星辰般璀璨的圣者型、天才型诗人,却幸而可见:始终徘徊于主流诗界的热闹之外、以诗歌为其信仰、以写出能够抬升中华民族文明高度的伟大之诗为其追求的昌耀、骆一禾、海子等,即属此列。这三位诗人的创作虽然内蕴迥异、风格不同,但都做到了既着眼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时时从现象的碎屑中提炼出照耀人心的精神符码,使读者被写作主体的深邃感悟、强力意志所震慑;既立足于小我日常而又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营构出广阔的诗意空间,关怀人类精神文明整体;既坦承人活于世体验到的荒诞与虚无,又坚定地表达对人世、人类的爱,对美善的无比信赖。诗歌在他们那里绝不只是寄托一己情思的载体,更非用来逞才炫技、博取关注的工具,而是一种文化、文明救赎之道,能够驱散现代性黑暗,使人类社会逼近“大同胜境”。本文将结合具体文本,对这三位诗人的诗歌思想再做推介,以期中国的诗歌创作更上一层楼。
一、越过现象的碎屑,提炼照耀人心的精神符码
昌耀、骆一禾与海子在生活中互有交集:骆一禾曾任《十月》杂志编辑,慧眼识珠地发现了久被埋没的昌耀的价值,两人通过书信往来,建立起伯牙子期式的友谊;海子与骆一禾相识于北大求学时期,两人过从甚密,后者作为前者的引路人、倾听者而存在;昌耀、海子因骆一禾的关系,相互有所了解,但由于性格都属内向,虽“彼此间是有感觉的”[1]187,却未能建立私交。这三位诗人绝难被划归到某一群体、某一流派,各自的创作都有其复杂性,但因他们都是识见超群、才力卓越的写作者,对中国当代以来的诗歌发展及文明状况都有深入的思考,创作出的诗歌还是会显现出某些共性。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他们的诗歌都抒情性较强,想象较为丰富,较少拾掇、编排零碎的生活现象、日常经验,较少就具体的人物事件展开叙述,而是擅于从大千世界森罗万象中提炼出一些别致的、富有象征性的意象进行观照和体悟,进而抒发一些深刻的、有关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心理状态、精神结构的感思。这样的创作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价值和思想性价值,但因为一眼望去,它们似乎是凌空蹈虚,烟火气不足,对人世的关怀不够,也容易遭受误解与轻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意象化的书写方式在后新诗潮的“语言论转向”中受到揶揄与批判,而心鹜八极神游万仞的抒情模式亦在诗歌的日常化运动中遭到质疑,上述这种古典色彩、浪漫气息浓重的创作自然就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意象入诗并不必然导致语词指涉的可能性受限、并不必然会使元气淋漓的生命意识受到阻滞;过度耽溺于抒情也许会令诗歌显得矫情和做作,片面地反抒情却也必将损害诗歌表情达意、沟通人心的基本功能。随着光阴荏苒,三位诗人运思和表达方式的高明之处逐渐显露出来。
首先,虽然昌耀、骆一禾与海子都不习惯将一地鸡毛式的生活景象直呈于诗歌,但这绝不代表他们的创作不是本于现实,缺乏在地性和及物性。他们所做的是将日常经验与时代现实、宇宙自然接通,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景象、生存实感画像。昌耀因其流寓青海高原二十余年,他的大多数诗作都含纳了高原的自然和人文风光,对一种独具魅力的“西部生活”有所袒露,甚而对特殊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有非同寻常的记录。譬如,其早期诗作《水色朦胧的黄河晨渡》,极为生动地描摹了雨雾迷蒙、橹声欸乃的黄河岸畔,活泼的少女呼唤情人,黄河铁工和黄河牧人热情劳作,伫立柳堤的老人怀想青春的情境[2]10。这样一幅风俗画有明显经过诗人想象加工的痕迹,近似于对乌托邦的描绘,但其中人物的情态是自然的、合理的,整幅画面将昌耀主动投身西部大开发时所具有的欣喜、豪迈的心态很好地托显出来,亦忠实体现出西部民间所普遍的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精神,以及建国初期万象更新,人民群众积极投入生产建设的真实景况。其《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一诗,虽副标题为“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笔记”,但总体还是切实描绘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某个恰逢一对青年恋人将要举办订婚酒宴的哈拉库图山庄,如何享受欢庆,又怎样遭逢挫折,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铁水顺利流出,酒宴也成功举办的图景。全篇绝无意识形态化表达,只能见到对真实生活情节所做的适当艺术加工,一种蓬动勃发的生命力显现于字里行间[2]17。骆一禾的诗歌虽然充满宗教意念和智性哲思,但他并未把诗歌变成宣传教义或推演哲学的工具,他在写诗时执着于观照美妙的自然风光、充满灵性的动物植物,首先去感知、领会客体的本质特征,接着再将主体积极的情感、思想投射过去,做到主客交融,彰显出世间的和谐与美善。例如在《野蜂》一诗中他写到:一只野蜂在“我”的面前悬停,在它的翅膀后面是一匹白马眨着大眼睛,旁边还有独角的牛在河水里看着自己的倒影,而“我在河岸上/吹着口琴/那声音又美又野……”[3]44自我的情思和意志并未遮蔽周围的生灵,野蜂、白马、独角牛并不是作为缺乏主体性的起兴之物出现在诗中,而是作为富有能动性的存在者出场,与诗人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品味这样的诗歌,读者能领受到一种物我融洽、天人合一的境界,感到体内人与自然相亲的原始本能被唤醒。海子的诗学观念曾被概括为“远方诗学”,即他视野所及、思维情感所系,都是一些邈远的事物,因此他屡被指责创作缺乏现实维度。但当我们深入了解他的作品,会发现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海子写过大量婉转动人的爱情诗,其中尤以有关初恋的篇目最为出彩,但因其初恋女友最终离他而去,诗中的感情色调大都偏于幽冷。这些诗作不仅记录下了海子“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真切体验,而且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并不少见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社会制度给‘乡下孩子’带去的命运、情感的不幸、苦难及其心理上的惨痛”[4]27。此外,“海子诗歌中反复出现的‘饥饿与胃’,同样不可仅作抽象高蹈的‘圣词’来解,它们同样具有当代中国并不遥远的社会历史维度与现实内容,但凡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国人应该大多数都不会陌生”[4]27。
其次,我们纵不能排除确有一部分诗人运用意象是出于取巧、省事的考虑,但也必须承认,有一些诗人将主观情思凝注于客体对象,是为了将某些难以直接陈说的、或隐晦或复杂的生命感悟传达出来,让读者心领神会。如此塑造出来的意象,往往具有原创性和非凡的感染力,能够成为照耀人心的精神符码。在昌耀、骆一禾、海子的诗歌中,这样的意象随处可见,最为典型的便是海子的“麦地”。海子直接以麦为题的诗有《熟了麦子》《麦地(吃麦子长大的)》《麦地(或遥远)》《麦地与诗人》等,这些诗作中的麦子灵气逼人,见证着苦难与希望,而麦地绝不只是生产粮食的处所,更象征着家乡的温情、诗意的栖居,以其光芒照亮人心的空缺。可以说,安土重迁的中华民族有关农业文明的说不完道不尽的温暖而又苍凉的记忆,被海子以其天才的笔触,融汇于一块具体的麦地之上,顷刻就变得具体生动起来,正由于此,海子身后才涌现出了大量的追随者——一大批缅怀乡土吟唱牧歌的“麦地诗人”。海子之找到麦地作为他的核心意象,依恃的并不是浓烈的情感、奇崛的想象,而是一种沉浸式的触摸体验。换言之,他并非是一厢情愿地赋予朴实无华之物以高格和深意,而是通过长久地置身和感触,发现了麦地蕴藏的奥秘。在经历过饥饿和贫穷的人看来,粮食极其珍贵,而麦浪滚滚的景象不仅象征着未来的希望,更标示着当下生活的根基,所以感恩“麦地和光芒的情义”[5]412理所当然;海子超于常人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到了麦地于人食物供给和精神安慰的双重价值,更对收割后麦地的荒凉深有体会,认为那喻指着丰收之后,乡土社会的贫穷和苦难依旧难以驱散[6]77。昌耀笔下类似的核心意象、精神符码有高车、雄牛、紫金冠等,而骆一禾诗中的“果树林”亦属此类,同时指涉具体的恋人和值得倾慕的大自然的美神。
诗歌如若完全脱离柴米油盐的日常,脱离对平凡人生的切身感受,则其真诚性就会丧失,通篇剩下的只是造作和虚伪;但如果诗人只书写日常所见的鸡毛蒜皮,只注重表达生物性的人的低级欲念,则诗歌品位又必将降得很低,将不再具有感动、净化人心灵的功能。据有学者研究,“骆一禾认为,诗的任务并不止于对日常经验状态的描摹和呈现,更重要的是揭示日常经验状态下人的精神内质和精神结构”[7]156。昌耀也说:“我所理解的诗是着眼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深沉思考”[2]377,意即光是反映一点生活情境、生活趣味,光是表达一些具体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写作还达不到诗的要求,真正的诗必须有所超越、有所担当。海子也有近似的观点,他说得更为详细:“写诗并不是简单的喝水,望月亮,谈情说爱,寻死觅活。重要的是意识到地层的断裂和移动,人的一致和隔离。”[5]1037或许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的那种只讲求凸显个人化真实的诗歌创作,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
二、营构广阔的诗意空间,关怀整体的人类文明
当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狂欢行将落幕,诗人们发现无论是朦胧诗还是“第三代”诗,其写作发表实际都未脱离建国十七年诗歌的那种群众化、运动化、意识形态化的思路,为求复苏诗中久已缺乏的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诗歌界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个人化写作”的命题,倡导诗人忠实地抒写自己的所见所历、所感所思。此后,这一提法因被一些写作者过度理解,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非历史化倾向,个人化逐渐走向了私人化。为了纠偏正误,中国诗界又援引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等诗学资源,开始倡导一种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原则,“指的是诗人在写作诗歌时,既在纵向上应该带着‘历史意识’把自己纳入已有诗歌传统中,也在横向上应使自己与同时代的诗人艺术家之间‘有一种不自觉的共同性’,即要努力做到‘一份共同的遗产和一项共同的事业把艺术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8]104。“个人化”强调的是感情流露、经验呈现,“非个人化”则专注于技巧和修辞,主张凭借运用复杂细节、戏剧化处理等方式,使诗歌表达走向客观与博大精深。但实际上,非个人化的主张并未使诗歌恢复应有的大格局和公共感染力,很多所谓实现了历史关怀、现实介入的文本,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个缺乏整合力的小我在搬弄着各种事件名称、知识符号,嗫嚅着一些貌似新奇、深刻,实则稀松平常的感悟心得。总而言之,缺乏一种广阔的文化视野,一种强有力的主体精神,诗歌的诗意空间必然逼仄,其影响文学发展乃至改造、提升精神文明的能力必定受限。
昌耀、骆一禾与海子之所以被诗歌界和读者大众公认为杰出的诗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其诗歌的眼光、思维、格局都呈现出难能可贵的大气象。先抛开长诗、组诗不论,这三位诗人都写了大量的抒情短诗,在这些诗中出场的,必然是一个具化的、切身感受平凡生活之悲欢的“我”,但如若仔细体察,我们会发现这一抒情主体并不以其感受的私密性、独特性彰显与众不同,不会囿于个人性感知的细枝末节,而是既咀嚼味尝独属于己的体验,又从中透视到某种普适的人生经历,某种“天涯共此时”的情感或心理。昌耀的《夜行在西部高原》是一首清新朴素的诗作,在一开头就直言到:“夜行在西部高原/我从来不曾觉得孤独。”按照惯常的思路,我们会以为诗人接下来要写的是某次独特的夜行经历,而他之所以不觉得孤独,大概是由于知心友人的陪伴或野生动物的喧呼使他得到了慰藉、感到了热闹。但接着往下读,我们会惊异于昌耀运思的巧妙、视野的开阔——他描绘的是一幅戈壁远景,一种西部山区普遍的、温馨的生活:傍晚时分,坐落山野的村庄有几缕炊烟升起,牧羊狗悠闲地伏卧着,看护着这炊烟。混杂着人间烟火气的“成熟的泥土的气味儿”扑面而来,使人感觉无比惬意。天色渐暗后,有间房屋的窗户被突然推开,灯光闪射出来,似乎是大山张开嘴想要对人诉说什么。但“蓦地又沉默不语了”,或许是“乳儿的母亲/点燃窗台上的油灯/过后又忽地吹灭了……”[2]29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认为,昌耀确实“打通了生命与‘地气’的联结,从而摆脱了当代诗歌体制的言说理路和想像陈规”[9]80,这得益于他的感知触角蔓延得极其广远,在写自我所见所感的同时,自然就写到了整个民间,写到一种遍在的人世的幸福。骆一禾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都以“爱”作为主题,但他绝不只停留于吟诵、赞美自己获得的爱情,“爱的母题在骆一禾的诗中经历了从个人情爱到绝对爱的跃迁和升华。骆一禾从个人情爱体验出发,经由对弱者的同情与关怀,最终发展出一个绝对爱的命题:无因之爱”[10]35。如果说其前期诗作如《守望爱情》《给我的姑娘》《爱的忧愁》《爱的河》等,所抒发的爱是具体的、特指的,那么到后期诗作如《我爱这急流》中,爱的对象简直扩大到了整块养育人类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有生无生的存在物。诗人别出心裁地想象自己倒毙在泥土上,自我生命与大地的生命合二为一,从而能够将一切美好都纳入自己的眼帘、囊括进自己的心胸。海子的很多诗歌都境界高远,尤以广受世人称道的《九月》为甚。这是一首有关“远方”的诗歌,但海子所执迷描画的,并不是浅层次的“异域风情”,不是自我置身远方美景、慵懒地享受生活的那种“小资情调”,他伫立于“众神死亡的草原”体悟到的是一种凄迷、一种虚无,一种空间的平旷和时间的无垠。“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5]205这一句,精准道出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对无限境地的向往,以及向往而不可抵达、无法触及的惆怅,可谓神来之笔。品读海子的这首诗,我们会感到诗中并不是只有诗人的那一个“我”在独白式地诉说,远方的本体、人迹罕至的遥远地域本身也在与人对话,主动回应着人类对它的向往与呼唤。
诚如骆一禾所说:“内心不是一个角落,而是一个世界。”[3]842每位诗人的创作无论其中“有我”还是“无我”,所书写的实际都是其自己的内心;唯有内心世界宽广、丰盈,创出的文本才有可能大气浑成,摆脱狭隘与靡弱。他深刻地指出,若是诗人的“内心锐变为一个角落”,必将导致创作诗歌时“引起意象的琐碎拼贴,缺少整体的律动,一种近乎‘博喻’的堆砌,把意象自身势能和光泽的弹性压得很低,沦为一种比喻。归根结底,这是由于内心的坍塌,从而使张力和吸力失去了流域,散置之物的收拾占据了组合的中心,而创造力也就为组合所代替而挣扎”[3]842。骆一禾与海子都是“大诗”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所谓“大诗”即印度人对史诗的称谓,他们之倾心于此,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现代史诗”写作热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虑极其广远,他们对人类、世界有很大很深的关怀,建构史诗几乎可算他们的一种本能需要。与这两位诗人共同被誉为“北大三剑客”的西川曾经这样的断言:“骆一禾对于世界的关怀特别大,他写《世界的血》,写特大的题目,包括他诗歌里的主题都特别巨大。”“海子一开始也有广阔性,但海子的这种广阔性是天生的,是带出来的。他从家乡来到北京,土地、田野、山林……像《东方山脉》等早期的诗歌,这种东西基本上是抒情性的。”[11]203-204骆一禾与海子各自依凭内心的广博,构造出广阔的诗意空间,前者的《世界的血》分为六章,向读者描绘了天地之间万物苏生、狂飙突进的景象,表明了世间纵有无尽的苦难和死亡,但宇宙永在运行,新生的希望永远不泯;后者的《太阳·七部书》“意象空间十分浩大,可以概括为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其中是以神话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12]4。诸如此类的史诗建构,是对人类生存繁衍、文明发展的一种统摄性审视和梳理,虽然如此的鸿篇巨制难免让一般读者望而生畏,但只要潜下心来沉浸其中,读者就能深受震撼,感到自己被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抬升而起,凌驾于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占据的全部时空,对生命的来路、文明的走向、大地上所有的劫数与荣光戚戚于心。而昌耀虽然未能写就类似的体量巨大的诗章,他的很多组诗、长诗却也营构了阔大的诗意空间,譬如声名赫赫的《慈航》,虽然叙写的是昌耀流落西部高原,备受磨难之后终于得到一户善良的土伯特家庭救赎的故事,但笔触所及绝不只是个人的悲欢痛痒,他通过这一组诗歌,简直叙述出了一部“荒原生命史”——“不朽的荒原”如何繁衍出各种极具灵性和野性的生物,如何繁衍出勇敢而善良、以心中的信仰对抗命运之狞厉的土伯特民族,又如何考验一个外来者,示予他蛮荒之地的贫瘠与生机,使他脱胎换骨,最终将他收容……所有这些,都被《慈航》的诗题下统领的12首诗娓娓道出,这样一组诗作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强烈的沧桑感,以及历尽沧桑后了悟生命真谛的快慰。
三、矢志重建价值理性:如堂吉诃德般悲壮进军
综观昌耀、骆一禾、海子的诗歌创作,我们不难领会到他们诗歌思想的真诚与严肃,以其真诚,必然不能容忍那种炫人耳目、哗众取宠的“创新”出现于笔端;以其严肃,必然难以容许一些轻浮的趣味、浅薄的机智见诸于文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商业化发展带来的浮躁氛围笼罩人心,各种纯粹提供快感的轻娱乐受到中国大众的青睐,人们浸淫于无需耗费脑力的各种娱乐项目,即便阅读所选择的也多是徒有情节的网络小说,长此以往,其整体审美品味难免下降,越来越难以接受那些苦心孤诣创作的纯文学纯艺术。昌耀和海子可被看作“文章憎命达”的典型:昌耀有大量诗作写于1957至1979年,这一时间段可算是他创作发轫和诗艺走向成熟的时期,然而在此时期内,他因特殊的政治身份,并无发表作品的权利,也就是说他的写作长期处于一种缺乏读者、无人关注和欣赏的状态。至1979年昌耀方始“回归”中国诗界,在燎原、邵燕翔、骆一禾等人的尽力推介下,其诗歌的价值渐渐得到公认,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真正否极泰来。然而在昌耀被诗歌界指认为大诗人的同时,诗在中国的命运却走向偃蹇,面对着物欲横流、工具理性高扬的市场社会,昌耀甚感悲愤,他致力于以自己的发声匡正世道人心,却终究难有实效。后来他又遭逢感情变故、罹患不治之症,最终在新世纪初带着诸多遗憾撒手人寰。海子的命运虽不似昌耀这般坎坷,但他在短短25年人生中也饱尝了知音稀少的苦恼和精神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海子实际创作的时间只有七年,他在七年时间里写下了大量优美动人的抒情短诗和卓异特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太阳·七部书》,但当他的这些作品出现于被誉为诗歌的黄金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却并未获得多少赏识者——诗篇中透出的浓郁的浪漫、古典色彩和强烈的建构精神文明的冲动被很多当红诗人认作是业已过时。知音尚且阙如,海子那天真的、想要联合中国诗人群体一起创造一部“伟大的集体的诗”的宏愿自然更不可能实现。海子卧轨自杀引起中国诗歌界乃至全社会对于“诗人之死”的热烈讨论,引起他自杀的主要因素固然是形而下的,但我们不能否认一些形而上的打击也是促成悲剧发生的重要推手。相较于上述两者,骆一禾的人生经历要平顺得多,但他也同海子一样殒命于青年时期,当他在世之时,他的创作主张和创作实践同样与当时的流行趋势有所龃龉,他注定不会伫立于诗坛的中心,成为春风得意的弄潮儿。总的来说,这三位诗人运气不佳,在他们的时代并未获得与其才华相称的关注与赞美,这一方面纵然可归结为造化弄人,另一方面却也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为了维护诗歌的严肃性与崇高性,为了坚持匡谬正俗的英雄主义式的理想,他们拒绝涉入哗众媚俗的写作道路,拒绝借助商业资本成名获利,自愿选择了沉寂与孤独。
昌耀对于自己的理想抱负曾有如此表述:“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亦是我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我一生羁勒于此,既不因向往的贬值而自愧怍,也不因俱往矣而懊悔。”[2]667海子则这样说道:“在一个衰竭实利的时代,我要为英雄主义作证。这是我的本分。”[5]1035仅凭这一句,一切指责他对社会现实缺少观照和介入、对烟火人间缺乏关怀的论调便不攻自破——为英雄主义作证,就是为了唤醒和激励读者大众,把他们从现时代所猖獗的消费主义、市侩主义中振拔出来。骆一禾也有类似的表白:“在中国进入新文化形态时,传统的价值理性有系统性的败落,价值的建设至今仍是举步维艰,所以诗歌的处境也是势所必然的。我和海子之写作长诗,对于价值理性建设的考虑也是其中之一,结构的力量在之它具有吸附能力,这可以从古代希腊的体系性神话,史诗及希伯来体系性神话的奠定对西方过程的影响,不断塑造和作为认识构架的例子得到证明。”[12]19经由上面这些话语我们懂得,三位诗人所热爱的不只是诗歌本身,更是一种与严肃之诗、真诚之诗有关的伦理文化背景,是人类应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当他们看到世俗现代性过度发展,人们凭着唯利是图的心理去面对人生、拥抱未来,从而有意无意造成很多荒诞悲哀的景象时,当他们意识到公共性的价值意义已经越来越不为人所关心,越来越多人漠视社会和历史,只知洋洋得意地沉浸于原子化的小市民生活中时,他们必然是痛心疾首的。他们意欲通过自己的创作、自己的发声,恢复一点价值理性,唤回人们对正误美丑的正确认知,但在诗人边缘化、诗歌浅俗化的时代语境下,这样的努力又能有多少成效呢?不过正如昌耀在《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中所写:“风萧萧兮易水寒。背后就是易水。/我们虔敬。我们追求。我们素餐。/我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累累若丧家之狗。”[2]535虽然悲愤、绝望,却仍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便是昌耀、海子、骆一禾三位诗人写作的姿态,这样的姿态理应引起世人敬畏。
行文至此我们也可明白,为何昌耀自西部荒原返归主流社会之后,仍对荒原的风物尤其是一些有强悍生命力的野生动物念念不忘,仍对一种农牧区的前现代生活方式充满着眷恋。他的真意并不在怀旧复古,而是想让神完气足的西部生灵与羸弱迷惘的现代人、朴素温馨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忙乱压抑的现代生活方式形成对比,指引读者对抗现代都市文明的“无物之阵”。海子之钟情于描摹一些远古时期洪水覆地、烈火焚天的景象,执着于在其大诗创作中塑造操剑戟舞干戚的“失败的英雄”,其目的也不在借古以自重,而是意图接引人类远古时代的那种以血与火为象征的文化精神,为当下感染“现代文明病”的社会换血。骆一禾对自然的亲近、钦慕也是同理,他并不是想仿效西方浪漫主义诗人,靠着寄情山水逃避现代社会的烦扰,他只想为读者揭示一点:人原本就是自然之子,拥有通灵大自然、感悟天地之灵气的能力,我们不该任现代生活的光怪陆离淆乱自己的内心,而是应当如老子所说的那样:抱朴见素,将活生命的力量,播释于人与人之间,发挥到它的极致。[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