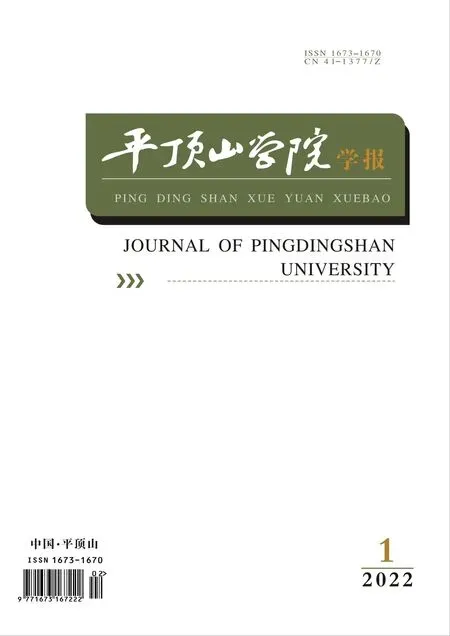论狄更斯小说中的学校空间
王欢欢,谭千秋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的两个重要维度影响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是相对于时间来说,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的背景常常处于被忽略的状态。20世纪末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空间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生产也和空间息息相关。文学是人类认知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文学描绘对象的世界具有空间性。文学作品试图透视、创造出来的精神世界,也是物质世界的折射,同样无法脱离空间。但文学和空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而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知识秩序。文本投射于空间之中,其本身成为丰富多元空间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空间是狄更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只是小说故事发生和情节开展的一个场景,也表现了作者的社会和生活信念。在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空间批评的方法对狄更斯小说中的学校空间展开研究,挖掘经典作家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促使文学创作和研究在传统中完成创新,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一、狄更斯的学校情愫
1812年狄更斯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海军职员家庭,由于父亲经济条件恶化,小狄更斯在11岁的时候就被迫中断学业。他被迫到泰晤士河河滨的黑鞋油作坊做工,每周领取6先令的工资补贴家用。1824年年底狄更斯的父亲得到了海军军需处发的年金,每年145镑,其家庭经济条件好转,狄更斯得以重回学校。狄更斯成了伦敦汉普斯特德路韦林顿寄宿学校的走读生,共在那里待了两年多。狄更斯在学校表现得特别不错,他在学校学习英文、舞蹈、拉丁文、数学,几次得到奖励,最后成为优等生。但这所寄宿学校的管理制度并不为人称道,校长有体罚学生的恶习,学校的差生经常承受皮肉之苦。“校长虽然如此苛刻,但他日后反倒比大多数的校长更幸运,他成了《大卫·考坡菲》中的克里克尔。”[1]1827年春,15岁的狄更斯离开了学校,走入了社会。狄更斯自身的求学经历就是当时英国学校教育现状的真实写照。英国在19世纪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和教育的普及。19世纪是英国现代教育制度确立和教育普及的世纪,教育运动持续高涨,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英国出现,学界有部分教育史学家甚至将19世纪称为“英国的教育世纪”。但教育繁荣、学校数量增多的背后,依然存在着许多危机和问题。狄更斯自身特殊的求学经历,使他对学校教育格外关心。他为改善贫困儿童的受教育环境奔走,自己出资兴办贫困儿童慈善学校,为适龄儿童编写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教材。狄更斯作为一名对社会现象敏感、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拿起笔记录了这一历史现象,表达了自己对这既是最好又是最坏年代的思考和忧虑。在19世纪的欧洲作家中,狄更斯是涉及学校描写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有关于学校的描写,有的小说如《大卫·考坡菲》《我们共同的朋友》等,人物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和学校息息相关。狄更斯小说中的学校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场所,而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表征空间。不同的作品及同一作品的不同部分,学校这一具体可感的空间所表征的意义都不同。可以这样说,我们以学校为切入点,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和解读狄更斯的小说。
二、狄更斯小说中学校空间的作用
狄更斯小说中的学校空间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教育不公
教育公平关乎社会成员的身心发展,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保障。19世纪是英国教育发展、学校普及的世纪,但教育不公在社会中依然存在。很多贫穷儿童依然被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女性未能同男性一样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不同阶级背景的孩子在学校受到不同的待遇,贫穷学校的基础设施与贵族公学有着天壤之别等。作为一名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狄更斯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教育不公十分不满。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出资兴办、资助贫困学校,在报纸、杂志上发文呼吁教育公平,还在小说中以学校为背景对各种教育不公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
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教育的不公首先表现在教育资源的不公。《远大前程》中的主人公皮普就读的乡村夜校,位于沃甫赛先生的姑婆租的一间小房子内。这是一所很小的房子,沃甫赛先生占据着楼上的房子,楼下的房子既是学生的教室也是一间小小的杂货铺。教师沃普赛先生的姑婆在给学生上课期间,总是处于沉沉酣睡的状态,学生每周付两个硬币,就是为了有机会观赏沃甫赛先生的姑婆睡觉。学生的文房宝贝就是一块破了的石板,一支半截头的石笔。《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查理·赫克萨姆所在的贫民免费学校,情况更为堪忧。这所学堂坐落在一个狼藉的庭院中的小阁楼里。这所学堂收学生不分年龄与性别,但管理学生却分年龄与性别。男女生分在两处坐,又按不同年龄间隔开来,平均分组而坐,十分拥挤、嘈杂、混乱。狄更斯甚至把这所贫民免费学校形容为高地市场。《董贝父子》中的小董贝所在的勃林勃尔贵族寄宿学校却是另一番景象。勃林勃尔学校是一所朝海的漂亮房子,保罗·董贝住在面临大海的房子里,床位靠窗,还有挂着白帐子的漂亮小床。勃林勃尔学校的餐厅环境很阔气,每个学生面前都有一把大的银叉、一块餐巾,饮食很丰富,餐桌上汤、烤肉、煮肉、蔬菜、馅饼和干酪应有尽有。因此,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学校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景,狄更斯通过对不同学校物质环境的对比描写,对教育不公发出抗议。
与教育资源的不公相比,学校内部不同学生待遇的不公平现象更严重,危害也更大。它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扭曲学生的性格。《大卫·考坡菲》中的主人公大卫·考坡菲是一个遗腹子,因母亲再嫁,他在家里受到继父枚得孙先生和继父姐姐枚得孙小姐的排挤,并在假期期间被送到寄宿学校撒伦学舍。在撒伦学舍,根据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出身,学生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学校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学生的活动区域,一部分是校长克里克的房子。学生住的房子和校长克里克住的房子有着天壤之别:
克里克先生住的那一部分房子,比我们住的那一部分房子舒服得多。他房外还有一个幽静的小花园儿。看惯了那个尘土飞扬的游戏场以后,再看到这个花园儿,真令人心旷神怡。那个游戏场,可以说是一片具体而微的沙漠,它老使我觉得,除了双峰驼或者单峰驼而外,其他的一切,到了那儿,都没有能觉得舒服自在的。[2]96
只有贵族出身、家庭富有的学生史朵夫和首席教师夏浦先生才能自由出入校长克里克的房子,和校长一起进餐,而其他的学生和助理教师麦尔先生满屋子安的都是松木桌子,在满屋里闻着都是油膻气味的餐厅就餐。体罚是校长克里克先生管理学生的主要手段,但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他从来不敢碰,那个学生就是史朵夫。相比之下,被叔叔收养的孤儿特莱得就是校长克里克手杖和尺子下的常客,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很少有不挨手杖的时候,只有一个星期一,碰上了放假,算是没有挨手杖,只是两只手挨了尺子。史朵夫煽动其他学生在课堂上公然嘲笑助理教师麦尔出身低下(麦尔的母亲住在布施安堂里,靠布施过日子),并和麦尔在课堂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克里克辞退了麦尔,并对史朵夫表示了感谢,因为他给撒伦学舍挣了面子,保留了体面。特莱得没有和其他学生一起欢呼麦尔的离开,反倒因为麦尔先生走了在那儿擦眼泪,被克里克用手杖暴揍了一顿。史朵夫在撒伦学校“特权”一样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其他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扭曲了其他学生的人格。一次,史朵夫在教堂中笑起来,教堂司仪以为是特莱得,于是他在公众的轻视下被押解出去,被拘留了好几个钟头,为了在史朵夫心中留下好的印象,获得他的赞赏,他永远不说出谁是真的“罪犯”。史朵夫赶走了撒伦学校的助理老师麦尔,周围的学生都附和着喝彩。对于麦尔老师的离开,大卫·考坡菲虽然心里很难过,但迫于史朵夫的威力,也热烈地参与了同学们的欢呼。不公平的学校环境抹杀了学生质疑权威的勇气,羁绊了他们对公平、自由的向往,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揭露学生管理制度弊端
19世纪现代教育制度在英国得到确立。学生管理制度是现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课堂教学、课外规范化管理、检查考试三部分构成。在这种管理制度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老师拥有绝对的主导权。老师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考试等管理手段,对学生进行规范化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提高了知识普及的效率,有利于社会平稳和正常运转。但在这种教育管理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存在着被社会权威规训的风险,不利于身心自由健康发展,这和学校教育的目的即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相背离。福柯在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弊端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理论化的总结[3]。早福柯一个世纪的狄更斯在现代教育制度确立之初,就敏感地捕捉到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弊端,并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个案例对其进行揭露,表达自己对维多利亚时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反思和质疑。
《董贝父子》中保罗·董贝就读的勃林勃尔学校是一所朝海的漂亮房子,房子里面却死气沉沉,毫无生机。颜色阴郁的窗帘,无精打采地躲在窗子后面。教室里的桌子椅子成排地放在一边,像书目里的几个数字。几间客厅很少生火,给人的感觉像井一样。餐厅最不像吃饭的地方。大钟的滴答声连在楼顶上都能听到。勃林勃尔博士坐在他奇特的书房里,每个膝盖上都有一只地球仪,四周都是书。在狄更斯笔下,学校仿佛也被勃林勃尔父女强制推行的规范化教育管理制度感染了。勃林勃尔博士把学生像做标本的小动物一样看待,至少给学生准备了100个人的学校资料。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为早7点到晚8点,以敲锣声为界,分五个时间段,早上预习,晚上复习,上午、下午学习新的内容,教学内容分五个等级,从A到E,从易到难,没有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禁止参加课间娱乐活动。学期结束学校会给学生的在校综合表现作出评价。学生评语会被邮寄给学生家长。学习任务之重,管理制度之严格,以致学生的头脑在睡梦中也同样受到功课的折磨,时不时会撂出一句半句希腊语和拉丁语。就这样,勃林勃尔博士以知识为工具,以自己为主导,以强制管理制度为手段,和学生建立了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狄更斯对此曾做出戏剧性的描述:
学生图茨在房门外无事儿可干,便炫耀似的检查他表里的齿轮,数他那几个半克朗。但这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勃林勃尔博士正好改变了一下他那两条裹得很紧的肥腿的位置,像要站起来似的,图茨一溜烟地逃走了,再也没有出现。[4]190
保罗·董贝是一个敏感且情感充沛的孩子,他经常无意识地反抗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他在学校时常想念姐姐弗洛伦丝和船工老格里布,替受罚的同窗求情。他的这一系列举动都触犯了勃林勃尔小姐的教育理念。在期末评定的时候,勃林勃尔小姐给保罗·董贝贴上了“古派”的标签。从此以后,“古派”像魔咒一样围绕着小董贝,他试图做一个文雅的、安静的孩子去获得别人的爱和感动,但是他的评语没法改写,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小董贝是“古派”的。他沉溺在“古派”的魔咒中不能自拔,甚至怀疑自己的骨头也是“古派”的,最终精神枯萎,走向萎靡不振。
《董贝父子》中罗布就读的磨工慈善学校也实行同样的教育管理制度。董贝为了“教育下层的人知道自己的地位,让他们安分守己”,推荐小董贝奶妈的大儿子罗布去磨工慈善学校接受教育。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无论身高体型都要穿统一的制服,每个学生都要有固定的编号。体罚是磨工慈善学校的老师管理学生最常用的手段,被老师威吓、打耳光、抽打是每位磨工的必修课,磨工在学校像鹦鹉一样接受老师强行塞给的“知识”。磨工罗布身材过于瘦小,穿着由蓝色台呢燕尾服、橘红色翻边帽子、红色羊毛袜、牛皮紧身裤组成的校服十分滑稽。罗布穿这身滑稽校服走在上学的路上,经常无缘无故被街边的流浪者打得眼眶青红,还会因此受到校长的惩罚。磨工慈善学校特殊的求学经历扭曲了罗布的人格,造成了罗布人生的悲剧。狄更斯在文中直抒胸臆地批评道:
磨工慈善学校从来不教孩子懂得什么叫荣誉,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制度倒是特别能造就伪君子。因为以前磨工们的许多赞助人和雇主都说,教育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还是别让他们懂得劳什子的荣誉为好。[4]590
成年后的罗布染上了捉鸟和竞走的恶习,过上了流浪汉的生活。后来,他以小董贝奶妈孩子的身份投靠董贝父子公司的卡克尔经理,为虎作伥,专做监听和打听情报的恶事儿。卡克尔派他到老所尔的海军仪器制造商店监听有关董贝先生和董贝女儿弗洛伦丝的消息。弗洛伦丝到海军仪器制造商店拜访老所尔,罗布堂而皇之地从屋顶上的天窗里往下张望、倾听。当卡克尔诱惑董贝的第二任妻子伊迪丝和其私奔的时候,罗布和卡克尔狼狈为奸。罗布负责护送伊迪丝到南安普顿和卡克尔会合。后罗布在布朗太太的唆使下背叛了卡克尔,将其行程泄露给了董贝,他的这一举动,导致董贝家族身败名裂,卡克尔在被董贝追赶的过程中被火车轧死。
同罗布一样,《奥立弗·退特斯》中的诺亚·克雷坡尔也是慈善学校出身。当他读书的时候,在学校受尽了欺侮,“皮短裤”“慈善学校的瘪三”等污秽不堪的绰号他照单全收。当历尽校园暴力的诺亚遇见一个可以给最卑微的人指着鼻子骂的孤儿奥立弗·退特斯的时候,他把自己所受的欺侮加倍施加到了奥立弗·退特斯的头上,致使奥立弗不堪忍受,逃离索厄伯里殡葬服务店,落到了盗贼团伙的手中。作为索厄伯里殡葬服务店的职员,他好高骛远,不安于本职工作,叛逃伦敦加入费根盗贼团伙,正是他的监听和告密行为导致了南茜的死。这样的悲剧发人深省,学校管理制度对学生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富有人文关怀的学校管理制度可以让人性的善之花绽放在学生的身上,反之,人性的恶之花就要在最无辜的儿童身上生根发芽。
(三)批判功利主义教育思想
功利主义哲学思想风行于19世纪的英国,建立在人类经验所认可的趋乐避苦进而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以保证个人利益为前提,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詹姆斯·密尔首次把功利主义带入了教育领域,他在《教育论》开篇即提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使个人获得幸福,先是为自己,然后推广到其他人。”[5]当时英国的学校教育侧重古典人文学科,神学、文法和古典名著是学校的主要课程。19世纪英国受功利主义影响的教育家对当时学校重视古典人文、轻视理性和实证的课程设置十分不满。他们推行实用主义的教育价值观,主张在学校广泛开展自然科学学科教育。这种提倡实用主义的教育推动了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升了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促进了教育的普及,提高了教育的效率。但它过分强调实用和效率,忽视了人文关怀,极易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作为一个有人文关怀的作家,狄更斯对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十分不满,并在小说中给予了批判。
比如,《艰难时世》以葛擂硬的贫民儿童学校拉开序幕。“事实”是这所学校的校训,这所学校的教育原则是:“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要连根拔掉。要训练有理性的动物头脑,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6]5葛擂硬儿童学校的教室是一间寒伧、没有什么设备、单调的拱形教室。教室里能让人记起来的就是一块黑板,旁边站着一个枯燥无味的“妖魔”用粉笔在上面画一些白色的鬼鬼怪怪的数字。校长汤玛士·葛擂硬穿着四四方方的外衣,长着四四方方的腿,四四方方的肩膀,有着四四方方像一墙壁般额头。他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诉你准确的重量和数量。“事实”弥漫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学校的教学内容就是教育学生只讲事实,使学生完全和“幻想”脱离关系。例如,马在葛擂硬学校的课堂上就是“四足动物。草食类。四十颗牙齿,其中二十四颗臼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春天换毛,在沼泽的地方还会换蹄子。蹄子很硬,但仍需要钉上铁掌”[6]7。学生西丝的父亲是位驯马师。她跟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马有整体、直观的认识,却不能给马下一个符合“事实”的定义。校长葛擂硬就认为西丝不能掌握事实,不能掌握关于一个最普通的动物的事实。
这种教育思想对课堂内容的影响还表现在老师强制给学生灌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概念。老师麦却孔掐孩在课堂上设计了三个问题问西丝,分别是:
一个国家里有五千万金镑。这是不是个繁荣的国家?一个都市里有一百万居民,而在一年之中,只有二十五个居民饿死在街上。西丝对这个比例的看法如何?在某段时期内,有十万人在海上作长途航行,只有五百人淹死了,或者被火烧死了。这个百分比是多少呢?[6]70
麦却孔掐孩希望西丝通过统计、计算国民平均财富、死亡率、生存率得出这三个例子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结论。西丝是一个情感充沛、自然活泼的女生,她关心的是国家的五千万金镑有没有她的一份。麦却孔掐孩对西丝的这种表现十分不满,他对西丝的学习评价是:“对于数目字,她一窍不通,她在学校的程度低的不能再低啦。”[6]68
倡导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学校会培养出来什么样的人呢?在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汤姆(葛擂硬的儿子)长大后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最终沦为银行的盗贼。葛擂硬的得意门生、学校的优等生毕周成了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在他的世界里利益大于一切,他不要婚姻,不重视情感,只在乎财富的积累。当汤姆盗窃被发现后,准备逃亡国外时,正是葛擂硬用“事实”原则培养起来的学生毕周断送了汤姆逃亡的路,而“坏学生”西丝却在为汤姆的状况失意落寞。“坏学生”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善,“好学生”却表现了人类情感的恶。狄更斯不动声色地给予了英国当时风行的功利主义教育制度无情的嘲讽。
三、小结
综上所述,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学校在其作品中不是作为一个场景存在,而是一个具体可感、有特征、有个性的空间,是揭露教育不公、揭露教育管理制度弊端、批判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场所。狄更斯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整体持否定态度。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狄更斯也没有忽视学校的积极作用。《大卫·考坡菲》里的大卫·考坡菲、《远大前程》中的匹普都出身寒门,是贫民学校所受的教育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获得了较好的薪酬。但狄更斯在小说中对学校的正面形象是用抽象、虚化的手段来表现的。例如《大卫·考坡菲》中的斯特朗博士学校就是作为撒伦学舍的对立面出现在文中的。“斯特朗博士学校办的非常好,它和撒伦学舍比起来就是善和恶的不同。教务安排严肃整齐,学校制度健全,无论什么全都诉之于每个学童的天良和尊荣心……与残暴的克里克相比,斯特朗博士是慈爱的,他以诚待人,以信接物,具有唯一无二的赤子之心。”[2]351-352正如国内狄更斯研究专家赵炎秋教授所说:“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但狄更斯又是一个有着强烈惩恶扬善倾向的作家,从不在作品中隐瞒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坚持全面反映生活的同时,通过虚化与突出生活的某些方面,以达到自己的创作目的,是狄更斯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7]同时,狄更斯在小说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去揭露学校教育的弊端,而没有积极地去歌颂学校教育的“丰功伟业”,也展示了其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这也是狄更斯小说的学校形象能够深入人心的主要原因。当“现代性”的拥护者从时间维度出发高扬现代教育制度的进步性的时候,具有人文关怀的狄更斯却从空间的角度关注现代教育制度的弊端和不足,这大概就是经典作家的魅力所在,他像一个矿藏丰富的宝藏,不同时代的“开采者”从不同的角度开掘都能发现“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