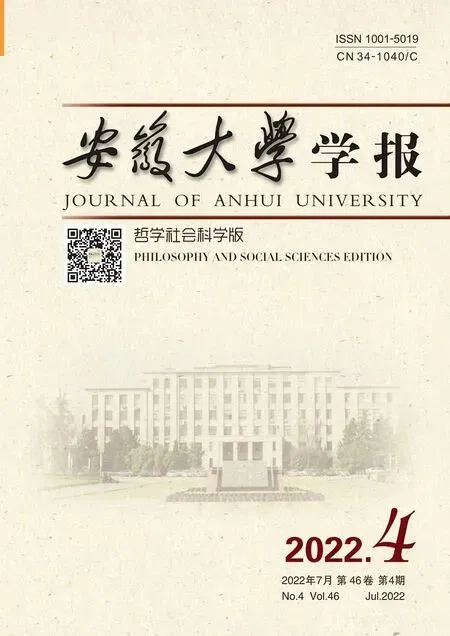论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
——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
方 芳,史玉民
20世纪以后,一些新的理论动向和现实问题的出现,使“关系”范畴的哲学价值日益凸显。分析哲学兴起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西方哲学开始更加坚定地抛弃“实体”而转向“关系”。罗素、摩尔等人意识到事物除了本质属性外,还具有关系属性。他们开始关注命题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由此使“关系”转变为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罗素甚至把关系问题看作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在罗素看来,其他的哲学问题,比如一元论与多元论,都取决于关系问题(1)参见黄敏 《布莱德雷、罗素与维特根斯坦论关系》,《现代哲学》2012年第2期。。20世纪初,布拉德雷(F.Bradley)和罗素展开了一场论辩,就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经验与实在等问题展开了争论。布拉德雷认为关系是内在于关系项的,否则关系就成了孤立的存在。罗素持“外在关系说”, 经过对摹状词和主谓命题性质的分析,他认为关系外在于关系项,不能归并于项的性质。此后,布拉德雷的责难促使罗素转向了命题概念,他借用弗雷格的命题函项理论讨论“关系”。两人的争论引发了哲学界关于“关系”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此争论提出了独特的观点。他在一种非常规的意义上讨论内在和外在关系问题。从前期的“图像论”到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从只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到考虑生活实践在认知世界中的作用。这种变化在维特根斯坦对关系的讨论中获得了深刻的揭示。他前后期的观点虽然迥异,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一、“对象”还是“概念”:维特根斯坦对“关系”的认知
在罗素、摩尔及布拉德雷等人围绕关系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的争论中,一个重要的论题是如何解决命题的统一性问题。如何确定一个命题(如“雨水在滴落”)不仅仅是构成要素(雨水、存在、落下)的集合而更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涉及解释命题的整体连贯性以保证整个命题的统一性的问题。如果用发生的事实来说明命题的统一性,会陷入一种逻辑上的循环论证,这里需要诉诸某种关系上的解释(2)J. Mácha, Wittgenstei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Tracing All the Connections,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 7.。外在关系似乎并不能胜任这项统一的工作,因为以外在的方式不能把关系与它的组成部分统一为一个整体。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论题是“命题”与“事实”的同一性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真理同一性”问题。所谓命题与事实是同一的,即命题所陈述的就是事实所呈现的,或者说命题的内容就是事实的真实状态,是事实的是其所是。罗素和摩尔后来意识到命题和使命题成立的事实之间关系性质问题的重要性。同样,外在关系并不能对命题和事实的关系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照此分析所有的事实只能是偶发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布拉德雷的回归论证。按照回归论证的解释,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似乎没有讨论关系的必要,因为现实就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即本体论一元论是对现实的终极解释。以上几个论题都把焦点指向了内在关系。内在关系或许能避免多元论的解释(3)J. Mácha, Wittgenstei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Tracing All the Connections, p. 8.,因为如果两个事项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那么就无须再寻求外在的东西把两者统一起来。而后,学界开始寻求对一些问题的内在关系解释。
有学者提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之间的区分具有误导性。首先,内、外在关系的意涵,尤其是对“内在关系”的界定和使用,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是有差异的,甚至在同一学派内部都无法达成一致。罗蒂认为,以往的内外在关系之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概念的不明确造成的。为了澄清这种混乱,他区分出弱意义(weak sense)和强意义(strong sense)上的内在关系。关于两者的区别他有如下陈述:
内在关系存在强和弱之分。弱意义上的内在关系是指,X与Y之间存在关系R,(如果可以将R归属于X)则认为R是X的内在关系,而这仅意味着“R与X存在某种真正的差异”。所谓强意义是指,在认识Y和R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逻辑上必然地推断出X具有某种确定的或相对确定的特性,而不是上述的那种特性(4)R. Rorty, Rela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nd edn, ed. by D. Borchert, Farmington Hills: Thomson Gale, 2006, pp. 335-345.。
因此,在讨论“内在关系”时要考虑的是,人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摩尔主要是在“内在关系”的弱意义上对此进行讨论。而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则是一个与逻辑必然性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摩尔曾经谈到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沿用了前人的表达方式,说维特根斯坦这样使用,只是因为别人这样用过,但他却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的确,20世纪30年代初,维特根斯坦表达过对内、外在关系划分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是两种不对等关系,“‘内在关系’具有误导性”,它们应当“归属于不同的类别”(5)L. 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s Lectures in 1930-33, Philosophical Occasion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3, p. 85, p. 87.。这种类别差异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6)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及其他》,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下引该书按学界通行方式以缩写TLP加码段形式随文夹注。中表明,这种差异源于我们是在什么层面讨论相关联的事物的性质。“内在关系”存在于概念(或属性、质、共相)之间,而外在关系存在于对象(或具体事物)之间。在早期著作中,由于他对“对象”“属性”和“关系”这几个词的交替使用,使“对象”与“概念”的区分被模糊化了。在后期思想中,这些不同的用法被相对固定在“语言游戏”的概念中,因而显得相对明确起来。他提到,一种语言游戏中的事实(外在)关系在另一种语言游戏中可能是语法(内在)关系。
维特根斯坦对内、外在关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逻辑哲学论》中他第一次提到了关系模糊性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对象和事态的形式特性,或事实的结构特性,而且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谈论形式关系和结构关系。
(也可以称“内在特性”而不称结构特性;也可以称“内在关系”而不称结构关系。我采用这些说法,是为了指出在哲学家中间非常流行的对内在关系和本义的(外在的)关系的混淆的根源。)(TLP 4.122)
维氏为什么说“内在关系”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如果某物具有X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特征属性,但仍然类似于X,那么它就是一个不恰当(improper)的X。换言之,说该物与X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系是不适宜的。恰当的关系应该是将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关系项联系起来,而这些关系项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不同的思想对象。因此,维氏提出是“对象”还是“概念”的“同一性”的问题,这可能是引起困惑和矛盾的根源。如果考虑的是“对象”的同一性,而不是“概念”的同一性,就会出现这些悖论。“同一显然不是对象间的关系”(TLP 5.5301)。说两个“对象”是相同的,或者说是不独立的,这种说法有些令人迷惑。因为人们可以追问,这两个对象到底是两个不同的事物还是同一个事物?而另一方面,说两个“概念”相同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可能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的意义,指代共同的事物,或者有某种相似之处(7)J. Mácha, Wittgenstei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Tracing All the Connections, p. 13.。“概念”和“对象”的区分始于弗雷格。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一书导言里提出了三条著名的原则,第三条原则为“绝不要忘记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区别”(8)G. Frege,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A Logico-mathema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 Number, New York: Harpter & Brothers, 1953, p. 22.。受此启发,维特根斯坦始终将其作为关系识别的基础。
维氏对“关系”的独特认知结束了以罗素为代表的外在关系说和以布拉德雷为代表的内在关系说之间的拉锯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关系之争”中的双方是在不同层面讨论关系,一方在“对象”层面,一方在“概念”层面。而维氏本人则专注于语词概念层面的讨论,不论是其前期的“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他对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在此层面展开。
二、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内在关系”内涵的转变
在澄清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别之后,维特根斯坦试图从关系角度来解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其前期的“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说当中。在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试图从关系的视角将对“概念”的讨论深入到命题和逻辑的深层,对“图像论”中的内、外在关系做出解释。维氏首先区分了三个层次的图像对应关系:(1)名称与对象;(2)基本命题与事态;(3)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世界的内在关系是最高层次的对应(9)J. Mácha, Wittgenstei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Tracing All the Connections, p. 69.,但语言与世界的对应相对宏观,名称与对象的对应则是一种形式上的对应,而基本命题与事态的对应是更为基本的。因此,维氏更多的是在讨论第二个层次的对应关系。
(一)“图像论”中“内在关系”的“显示”
维特根斯坦主要通过“说”(saying)与“显示”(showing)的区别来阐明图像论中涉及的内在和外在关系。语言是世界的图像,我们用语言来描摹世界。能够用命题“说”出来的,也即用逻辑符号表达的是一种外在关系。在一个命题中表达的所有关系都是外在的。而逻辑符号与世界的对应关系是内隐的,这种隐含的内在关系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被“显示”出来。也就是说,内在关系不能通过命题表达(说)出来,只能在相关的命题中显示出来(TLP 4.122—4.1251)。维氏把内在关系看成是语言逻辑符号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只能被“显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内在关系类似于“结构关系”。既然命题是事态的逻辑图像,那么,内在关系指向的是在命题与事态层面实现的一种逻辑结构上的对应。图像关系是通过“投影”(projection)的方式实现的。“我们利用可被感官感知的命题指号(语音的或文字的,等等)作为可能的事况的投影”(TLP 3.11)。“命题在其对世界的投影关系上就是命题指号”(TLP 3.12)。“投影”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是命题和事态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图像关系来自命题指号与可能的事态之间的投影关系。命题指号被投射到可能的事况上,通过一个事况描画另一个事况。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更像是一种“固有形式”(intrinsic property)。显然,他前期的观点没有脱离符合论的框架,其关系解释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展开。
此后,维特根斯坦声称他已经解决了关系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个争论(TLP 4.1251),开始了奥地利南部乡村的归隐生活。然而在此期间,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中,他开始质疑前期的“图像论”。维特根斯坦意识到语言不仅可以指称事物,它还与行动交织在一起。维氏开始回到日常语言中探索语词的不同用法。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开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哲学形式,提出了“语言是一种游戏”的观点。在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把前期的“说”与“显示”的区别转化为“语言所表达”与“语言所显示”的区别。因此,后期他一再提及“内在关系”是一种“语法关系”,也即从语言层面对关系做出解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对“内在关系”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到了后期,他关注的是一般的语法命题中的内在关系,而不是前期“图像论”中那种逻辑结构上的对应。
(二)“语言游戏”中“内在关系”的“概念构造”
维特根斯坦把对内、外在关系的争论从对象层面引向概念层面。而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对内在关系的讨论又跳出了前期符合论的框架,不再把内在关系看成是不可言说的、隐含在语言逻辑符号中的结构对应,而是把“内在关系”解释为一种语法关系,将内、外在关系看作是通过概念(语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如此一来,内、外在关系的界限就以某种方式消除了。
那么,转向“语言游戏说”之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概念有什么独特之处?哈尔克曾概括出维特根斯坦“内在关系”的三个主要特征:内在关系存在于两个事项而非多个事项中;内在关系无中介,它是一种语法关系;内在关系来自实践,而不是存在于某种抽象的心理中介物中(10)M. Hark, Beyond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Dordrecht: Kluwer, 1990, pp. 160-187.。在这三个特征中,后两个特征最为突出。我们以为,除这两个特征以外,内在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内在关系并无个体与共同体的区分。
(1)“内在关系”无中介,是一种语法关系
相比于外在关系,维特根斯坦更为关注的是内在关系。内在关系是一种语法关系。“内在关系除了语法中所描述的,并无其他”(11)L. Wittgenstein & F. Waismann, The Voice of Wittgenstein, ed. by G. Bak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237.。在对意向性、颜色、数学等问题的阐释中,他强调内在关系不存在于“对象”中,而是存在于“概念”中。内在关系不是对对象的描述,而是概念的构造。很多关系实际上是在语法中被建立的。维特根斯坦打破了内、外关系之间的绝对界限。一个句子可以同时表达内在和外在关系。比如,“桌上有 5本书”是一个经验命题,表达外在关系,其中5的意义来自| | | | |。可以写成“桌上有| | | | |本书”。由经验命题抽象出的数学表达式“2+3=5”表达的则是内在关系。等号两边的式子可以通过规则转换完成。维特根斯坦用概念(语词)把“内”“外”关系关联了起来。在一种语言游戏中的外在关系可能是另一种语言游戏中的内在关系,同一描述可以分属不同的语言游戏。而此前,布拉德雷在心理层面的讨论给两种关系划出了一条界线。维特根斯坦消解了这一界限。这是哲学观念上的重要转变,许多哲学难题因此得到了化解(12)张励耕:《感知、性质与关系——对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中“内在关系”概念的辨析》,《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内在关系来自实践
“内在关系”既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存在,也并非以心理为中介,而是来自人类实践。也正是在这点上,维特根斯坦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框架。抛开人的实践,在内在关系的解释中引入中介项会陷入解释的循环。任何一种寻求外在中介的解释都是不可靠的。维特根斯坦在对一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的讨论中,比如意向性、颜色、数学问题,都一再提及寻求中介项带来的困难。
以意向性为例。在《心的分析》一书中,罗素在心理层面寻求中介解释,用因果关系来说明意向性问题。在罗素看来,期待与满足之间必须有“愉悦感”(feeling of pleasure)作为中间要素,这是一个使期望成真的过程(13)B.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in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1, p. 270.。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罗素引入的这个中间要素并不可靠。因果关系的链条不总是纯粹的,可能有其他因素的介入,因此难以断定“愉悦感”是否是与初始的期待有关,是否是由期望的实现带来的满足。中间项的引入需要诉诸新的中间项来加以解释,从而引起解释上的无穷倒退。“言语与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而我们需要一种内在的关系”(14)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Remarks, ed. by R. Rhee, trans. by R. Hargreaves and R. White, Oxford: Blackwell, 1975, p. 64.。所有寻求心理中介的尝试,或者说在外在关系中寻求解释的努力都会归于失败。
维特根斯坦把“实践”引入意向性,最终化解了上述困难。“相信”“怀疑”这一类的表述,似乎是在描述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却是包含一种对预期行动的估算。当我说“我相信他会遵守诺言”时,这句话指向的并非是我的心理状态,而是依据对他以往的行为方式、人格品行的认知来对尚未出现的结果进行一种推断。“这些词或这些表象是一种估算的部分”(15)L. Wittgenstein & F. Waismann, The Voice of Wittgenstein, ed. by G. Baker, p. 416.。相信、希望、愿意这类动词具有像“切割”“咀嚼”“奔跑”一类的动词所具有的全部语法形式。类似的,“期待”与“实现”包含对行为结果的估算。从时间先后上看,先有期待,而后才有意向的实现。在期待的意向行为中已经包含了预期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期待等意向性行为不仅仅是发生在心理层面的内在意识过程。把握意向行为,要结合它出现的生活环境,在实践中进行解释。这样一来,期望与满足之间的那种不确定性就被克服了。
(3)“内在关系”无个体与共同体之分
“内在关系”的解释把个体认知和共同体统一在实践中,很好地解释了规则如何出现的问题。维特根斯坦以前的哲学,一方面对个体抽象规则的过程寻求心理解释,而后又对群体接受规则的过程提出另一种解释。在回答“共同体对规则的作用”这个问题时,一般的思维逻辑是:个体的实践还不能保证达成认知和行动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只能在共同体中达成。人们遵守着类似一种约定的“共同体一致性”(community agreement)。换言之,共同体完成了一种规则上的约定,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外在的标准,然后依此标准判断个体是否遵守了规则。对此,维特根斯坦并不认同。一旦设立外在标准,即便是在共同体层面,还是会出现解释悖论。一种解释之后总会引出更多的解释,没有一种解释能够实现自我圆融。这和个体层面的解释悖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维特根斯坦提出,我们之所以遵守规则并非是出于人们的约定,而是缘于人们的反应方式、行为方式的一致。“‘逻辑真理由意见的一致所决定’经常被当作一种论断。难道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跟意见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关于意见的问题。它们由行动的一致所决定:做同样的事情,以同种方式反应的一致。我们都以同样的方式行动,走在同一条道上,以同样的方式计算”(16)L. 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183-184.。通过同样的反应方式,共同体的规则遵守具有了一致性。一致性是重要的,它保证了运算规则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某次运算错误而改变。错误会得以纠正的原因并非在于权威的力量,而是在于:规则是一个系统,一条规则被改变,其他的规则就必须相应地发生改变。共同体无法为遵守共同的规则提供外在的解释和辩护。因此,从语言或规则本身,也就是内在视角来解释悖论,是更为合理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共同体的一致性是通过“训练”(training)完成的。“训练”是维特根斯坦在阐释规则遵守时反复提及的重要概念。训练不是一种外在的手段。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外在标准来让受训者遵从,而是通过“训练”人们才能在反应和行为方式上取得一致。他在《棕皮书和蓝皮书》中提到,这类似于训练动物去做某些事情(17)L. Wittgenstein, The Blue and Brown Book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p. 77.。只不过,人类的训练方式更为抽象,比如语言、数学活动中对规则的掌握即是一种训练。动物和人类的训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一再强调“训练”不需要心理中介(mental intermediary),不需要“通过形成对外物的意象来思考外物”(18)沈洁:《维特根斯坦论遵守规则的一个线索》,《学理论》2016年第5期。。
概言之,内、外在关系通过语词(概念)相联系,而“内在关系”作为一种概念构造其本身依存于实践,根据实践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此一来,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消除了此前内外在关系争论中的那条“关系界限”。他不但把“内”“外”关联为一个统一体,也把个体的认知和共同体的一致性统一起来。“内在关系”是维特根斯坦为了引出“内在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语法关系”的一个“梯子”。“维特根斯坦主要把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的区别作为一种启发性的工具,最终将其从形而上学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如果不是在《逻辑哲学论》中,那么肯定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19)J.Mácha, Wittgenstei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Tracing All the Connections, p. 8.。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讨论就如同“梯子”,使用之后,即可放置到一边(20)谢丽尔·米萨克:《拉姆齐、实用主义和维也纳学圈》,许振旭译,《哲学分析》2021年第4期。。当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之后,维氏就撤除了这个“梯子”,用“概念关系”替代“内在关系”,以“事实关系”替代“外在关系”。
三、“关系”的“语言”和“实践”根基
维特根斯坦的“关系”思想之所以有超越前人之处,首先在于他将对关系的讨论限定在“语言”层面,避免了此前形而上层面的讨论。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说在心理层面探讨关系,因而其讨论只能限于感知经验之内。罗素在语言层面对关系进行讨论,但罗素所说的“概念”是静态的命题概念,反映的仍是语言命题与外部世界的一种同构关系。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图像论”也是一种符合论。而在他的后期哲学中, 在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解释中,他找到了“实践”这个根基。主体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认识都离不开生活实践。他将内、外在关系统一于实践中,超越了前期图像符合论对关系那种割裂的解释。植根于生活实践的概念不再是罗素的那种静态的命题概念,而是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概念构造。
故此,维氏的关系思想找到了“语言”和“实践”这两个根基。通过整理其前后期哲学中有关“关系”的相关论述,可以梳理出以下一些重要观点:
(1)关系是一个系统;
(2)“语言游戏”是一种内、外在关系的勾连;
(3)语词充当了内、外在关系的黏合剂;
(4)内在关系可存在于复合物中;
(5)内在关系只在概念之间实现,是一种语法关系;
(6)内在关系来自实践;
(7)内在关系无中介;
(8)我们只能认识关系,而不能认识事物的属性。
这八个方面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1)—(4)是从“关系”视角对“语言游戏”的重述,强调的是“关系的关联性”。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内、外在关系相伴而生,同一描述可以“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21)L.Wittgenstein, Last Writ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 1, eds. by G. H. von Wright and H. Nyman, trans. by C. Luckhardt and M. Aue, Oxford: Blackwell, 1982, §761.。“内”“外”的分别是哲学思辨的产物。区别于布拉德雷从心理层面给内、外关系划出界线,维特根斯坦消除了这一界限。这是哲学观念上的重要转变,由此化解了一些哲学悖论或难题。其中(2)指出语言(语词)在语言游戏中的作用。语词把“内”“外”关系关联了起来,一旦涉及“内在关系”即进入了语言(概念)层面,就受到语法关系的制约。而(4)“内在关系可存在于复合物中”,强调内在关系不是纯粹的,而是可能与不同层次及属性的语言游戏相关联,从而分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
(5)至(7)聚焦于“语言游戏”中内在关系的特征。内在关系来自实践,且内在关系无中介。将此两者联系起来看,内在关系首先是根植于生活实践的。即便是那些抽象的、表达意向性的语词也要结合意向行为出现的情境,在实践中加以解释。换个视角来看,概念的构造方式并非唯一,不同的实践方式决定了语言游戏可以多种多样。至于(8)维特根斯坦想揭示的是:如果在事物表象的背后并不存在某种本质的、绝对的东西,那么,我们所能认知的是什么?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关系,而不能认识事物的属性,且认知的方式比认知事物本身更为重要。
概而言之,首先,维氏是在语言层面讨论关系,也就是他所说的概念关系。维氏从语言出发,以概念(语词)为媒介,探察到了语言与世界关系之“里”。在维氏看来,概念(语词)产生于内、外在关系的语言游戏中,并且植根于生活实践中。所有“关系”都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一旦用某种特定形式的语言表达,无论是经验描述的、逻辑的还是数学的,语法关系即被确立下来,或者说形成了一条规则。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在试图对对象进行描述时,规则就被相应地确定下来。规则是否成立,只能在关系内部进行验证。看似描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对世界的构造。
其次,语言并非是独立于世界的一种抽象,而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并不需要断定一个隐藏的本质或基础来解释外部世界。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具有共享背景的‘生活世界 ’中”(22)钟毓书:《海德格尔“在世”学说对解决环境危机的启示》,《江淮论坛》2022年第2期。,维氏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并且,在维氏看来,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或解释无时无刻离不开语言。在最初产生之时,语言是与人类其他形式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存在,也并非是以心理为中介,而是来自人类实践。“内在关系”被解释为依存于实践的、从属于概念的动态变化关系。不同的实践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关系表达方式。或者说,实践方式不同则概念构造的关系表达不同。既然认知的本质是一种相伴而生的内、外在关系的“语言游戏”,且在不同的“游戏”中概念(语词)表现出不同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语词或命题就并非是确定的,而是出于描述世界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选择。
四、结 语
综上,维特根斯坦首先把“关系之争”中关于“内在关系”的讨论从感觉转向了语言的层面,把此前基于“对象”的讨论引向了“概念”层面,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内、外在关系的争论。而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将对“内在关系”的讨论拉回到生活实践之中,拉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从而超出了前期图像符合论对内、外在关系割裂的解释。概言之,维氏“关系”是以“语言”和“实践”为根基的。
那么,维氏的“语言游戏”有怎样的深层蕴意?在关注到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之前,学界对于其后期的“语言游戏”的理解主要是对“游戏”的自然描述。而基于维氏对“关系”的解读,“语言游戏”的生成过程得以揭示。“语言游戏”可以被重述为:(一)语言是一种关系系统;语言游戏首先表现为关系的关联性,而语词是关系的黏合剂;(二)内、外在关系相伴而生,“语言游戏”表现为一种内、外在关系的勾连;(三)内在关系来自实践,一旦内在关系在实践中被赋予了概念形式,即会受到语言规则的制约,成为一种基于实践的“语言游戏”,概念的构造是一种关系的表达,实践方式不同则关系的表达不同;我们所认识的只能是事物的关系,而无法真正认识事物的属性或本质;(四)关系的表达或构造不是基于个体而是基于共同体,是在“训练”中达成一致的。
总体而言,维氏的“关系”思想从属于认识论的路向,其主要是从人对世界的认识的视角对关系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关系之争”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发展路向,其源于罗素对“关系”外在性的思考。在对关系问题的后续考察中,罗素不再纠缠于对象间的关系,而是转向了命题概念。他借用弗雷格的命题函项理论,用纯粹的关系的“勾联”来解释关系与项不可分割的性质。这促使罗素走向了对关系实在性的思考。在罗素的“外在关系说”的影响下,一些后继者提出“关系外在于关系项”和“关系先于关系项”,进而引出“关系实在”的思想,如此形成一种关系发展的本体论发展路向。两条发展路向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了“关系”思想的研究,使得“关系”成为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
致谢:在此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博士后叶斌致谢,衷心感谢在本文成文过程中提出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