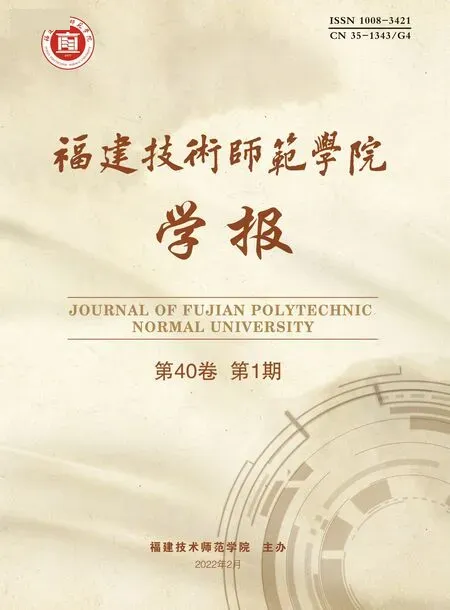网红城市打卡现象中身体与空间的互动性探究
黄林静
(福建商学院传媒与会展学院,福建福州 350012)
网红城市景观的打卡热潮作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吸引众多领域学者对之展开研究,从传播学角度看,借助社交平台展开的城市打卡行为,同样也是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日常媒介实践。那么,在这个网红行为中,人的身体、移动终端、城市空间、地理位置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跃升为“主体”的身体,是否真的成为可控的认知城市的主角?这种与城市主动相遇的具身性实践多大程度上建构可靠的人与城市的联结?与媒介高度融合的新型智能身体是如何展开对城市的认识?本文尝试以身体为基点思考人与媒介、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
一、打卡行为中身体的物理位移:真实空间中的个体与城市
“远程视觉(电视)再也不需要人身的可动性,而只需要他们的原地可动性……于是真实时间的这种城市化接替了真实空间的城市化,而真实时间的城市化最终就是市民自己身体的城市化”[1],维利里奥在《解放的速度中》如此表现他的悲观,认为过去那种人们只需端坐在沙发上就能看遍全世界的看似进步的体验事实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削弱性干预,降低了人们对现实的介入能力。这样的城市生活与“位置”无关,因为“位置”已经被抽离,人的身体感官同样被抽离,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的电视(或其它媒介)取景框提供的特定的城市影像,用非人的感官知觉视角看待城市,体现的是某种社会权力关系,当然也体现此类媒介所掌控的叙事法则。好比过去擅长宏大叙事的城市形象宣传片,由精心挑选的摩天大楼、城市交通干线、密集的人群等画面构成,仿佛唯有这些影像才能诠释一座城市,对现代性的过于重视造成对城市空间中具体人们生活场景描摹的淡漠,个体更是被这种精心组织的叙事内容所剔除,就如日常性被剔除一样。遮蔽了日常性的、剔除人们具身经验的“城市文本”被认为是“书写的城市”,与“表演的城市”构成城市研究中的“两极”,前者突出由媒介再现的城市,后者看重居民物质性的、空间性的体验行动。“表演的城市”可以看作是人们开放了全身的知觉感官,漫游在城市空间中,随着身体的物理位移产生关于城市的具体空间感知,这种对“都市空间和都市记忆的贡献”是“表演”性的、鲜活的,也是本雅明所倡导的身体与城市相遇的最佳方式。
而网红城市景观打卡行为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本人的物质肉身到达了具体某处,个体携带物质肉身完成了某一具体动作(例如品尝网红美食、参观网红建筑、住进网红酒店、摆出网红姿势等),继而将此类充满仪式感的体验过程记录下来,最重要的是标记出地理位置,发布在社交平台,等待社交圈的点赞、评论、转发。在这一整套熟练的动作中,代表身体进行了物理位移的“位置”元素是提升“人身可动性”的关键,无论是被刻意标注出的地理定位,还是影像中体现某一位置的标志物,都是身体在昭示自身摆脱了“书写的城市”的桎梏,展开了一场实在的活跃的“表演”,代表着物质肉身切实移动及其产生的身体与城市的感性相逢。对城市充满好奇的未知性探察,本身就是极具吸引力的,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城市影像虽然经过了滤镜、背景音乐、文字等多重编辑手段的叠加渲染,但每一个个体对城市的具身感知不尽相同,与其说是社交圈中他人发布的奇幻打卡影像刺激了观看者前往,不如说是对城市景观能带给自身怎样的感知体验的好奇驱使人们前赴后继。每一次的身体在场都有其独特性意义,由不同的具体肉身搭建起来的城市感知行走实践,得益于媒介技术的便利而为世人所知,因此从身体层面看,网红的是同一个城市景观,而不是人们行走于景观中的具身经验。
网红城市景观中的打卡行为强调空间的“到场”,象征着人们对城市感知对象的地理空间选取,既不同于纳入官方宏大叙事系统的景观体验,也不同于已“到场”人们的具身体验。身体的“到场”带来重大的变革意义,一改过去感官被传统媒介分割的缺席状况,得以回归在场,并使观看的城市成为体验的城市。
二、打卡行为中身体的媒介位移:双重空间中的个体与城市
探究城市中的网红景观打卡行为势必提及“一个为技术所捆绑、数据浸透的、连接虚实多重网络的智能身体”[2],拥有智能身体的人也被称为“赛博人”,乃“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3],海勒关于后人类的描述用来阐释“赛博人”也十分贴切——“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与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4],网红景观打卡行为恰恰产生一种“混合空间知觉”,具体肉身于物理空间中在场,虚拟身体于数字网络空间中在线,带来实体与虚拟空间的双重感知,构成新的城市认知维度。由于打卡行为所包含的具身到场与虚拟在场,它带来纯粹的现场感知之外,也产生一种工具性的数字化感知,承载于人们为了标示自身与城市关系所作出的数字记录中,当人们离开城市后,只要打开这记录,便能联想到具身在场时的切身感知,这数字记录便是打开感知记忆大门的符码。“媒介连接了打卡者的两个身体,新媒介创生的虚拟身体和自然的现实身体随着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重叠而融合”[5],更重要的是联通虚实之间的桥梁就是“赛博人”这一身体界面,借由发达的媒介技术,人们可以自如穿梭在不同属性的双重空间中。
不需经过专门培训,移动终端用户就能够迅速习得设备上有关定位的运用技能,只消打开设备中的定位功能,个体就成为地图上一个个活着的光标,不管是确认所处位置,还是前往目的地,打开相应程序,具体肉身与虚拟身体就同时产生位移,随着自然身体的移动,数字身体在终端界面的地图上画出轨迹。人所处的位置从未像当下充满新的意涵,若基于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元素考量媒介与身体的互嵌、共融,令人不得不想到麦奎尔提出的“地理媒介”,他认为像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这样的位置感知设备所传输的“位置化”信息“在城市空间中支持并实现了各种新的社会实践与商业逻辑”[6],同时阐述了地理媒介拥有的四个联系紧密的维度:融合,无处不在,位置感知,实时反馈。如此观之,只要终端持有者不关闭定位功能,他(她)作为光标在城市中的实时位置与行动轨迹将一直在线,成为后台海量数据的一分子,并将持续能够接收到设备发送的“位置化”信息,构建自身感知城市的又一维度。
从“地理媒介”与“位置”引申下去,还将找寻到一个重要的、体现打卡者作为新型身体与城市之间联结的标志物以及载体、地图。“作为重组空间的地理媒介”,地图跳脱过去单一制式视角,作为代表媒介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发明与移动终端设备天生捆绑在一起,是打卡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智能地图具开创性的意义在于呈现出身体看待城市空间的新视角。正如伊德所说,“技术影响了身体的空间知觉”。智能地图按照持有者不同需求在鸟瞰视角与平行视角间切换,集空间之上的“上帝”视角与空间之中的日常视角于一体,时而低空飞行,时而深入其中,身体也随着第一人称或是第三人称的视角转换联结与感知周遭城市空间。建筑学家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用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作为人们认知城市的五大要素,那么区域由节点框定、边界强化范围、道路穿行其中、沿途散落一些标志物,这不就是展开的一张城市认知地图吗?回到网红城市景观打卡这个过程性行为,打卡者借助智能地图工具,明确自身所处位置并在地图空间中作出标记,向社交圈宣布具体肉身已到场,且虚拟肉身以光标的形式在线,漫步在数字网络形式的城市空间中,借用地图这一载体宣告自身与城市的相遇。
三、身体所在的城市空间作为关系媒介:虚拟空间中的强社交联结
移动新媒体技术导致的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叠加与融合产生出新的空间,让人们再次审视媒介与空间的关系,使得人们对因尼斯所发现的空间偏向的媒介认知拓展出另外的意涵,相对于空间的媒介化,媒介的空间化问题有趣又应景的多。同样地,卡斯特说“空间就是社会”,关系将社会意义赋予空间,但在新的空间中时刻发生的、由技术加持的媒介实践又使这个观点的说服力略为逊色。显然,用空间作为一种媒介的切入点来看待时下的网红城市景观打卡行为更有助于看清技术赋权下的日常媒介实践带来的变革性意义。这种变革不仅止于人们通过打卡这一行为实现的关于城市空间故事的自主性书写,更在于虚拟空间以自身为媒介展开的意义再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再建构。
打卡行为本质是上一种交往行动,“人们通过观察他人虚拟空间的数据为自己的现实空间行为导航”[5]。当人们满怀期待地去一个新的城市时,势必会打开手机上的社交应用,输入“××城市旅行攻略”,并追随着他人的脚步去体验那些所谓“一定不能错过的景点”。这些攻略之所以会成为人们行走城市时的指引,在于他们与“攻略”一类内容的彼此间信任关系。攻略的发布者用笃定的口吻与字眼表达自己对某个城市景观的强烈认可,决定采用攻略的追随者同时也笃定自己的判断,这样相互信赖的过程是人们对个体化的城市体验的偏爱与亲近的体现,产生陌生人之间一种深切又疏远的联结。待人们追随着攻略完成网红景观的打卡行为后,在社交平台展示带有自身印记的体验文本,这一联结过程并未终结,而是继续引发新的信赖,产生新一轮的体验文本。某种意义上,这种联结关系比起人们借助网红景观的打卡行为来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社群的划分来说,更加稳固。打开智能手机中的视频应用,输入某个城市网红景观作为搜索标签,就能找到众多原创影像,这些产生于同一地点的大量打卡记录,是人们虚拟社交关系的体现,同时又加强了他们关于城市感知的联结,而这些是作为关系媒介的城市空间带来的。
“空间无不打着人的印记与社会的烙印,谈空间一定是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来说的”[7],具体肉身与虚拟身体共同所在的城市空间吸引具有相同目的人不断前来,并在他们之间产生稳固的社交关系。这一层稳固的关系并非依赖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而是依靠虚拟空间的互动行为得以展现,因此再一次验证了虚拟空间自身作为媒介的强大黏合作用。人们可以不用彼此认识,在实体空间中也不产生交汇,但他们彼此信赖,并于不同的时间仪式性地到达同一个空间并留下印记。借此,相同背景中的不同个体组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必须依赖个体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双重在场才得以生成。如此看来,打卡地作为媒介化的空间,集中体现为带来一种新型线上社交关系的强联结。
四、身体所在的城市空间作为认知媒介:真实空间中的城市弱“表演”体验
行文至此,虽然个体的网红景观打卡行为具有正面的象征意义,但继续深究,这一行为在建立个体与城市真正可靠联结上依然有明显的可诟病之处。2021 年国庆假期刚过,公众号“新周刊”在2021 年10 月9 日发布的《这个假期,我又被网红打卡点骗了》一文中写道,人们“逐渐把一切出行的目的变成了出片,放假休闲,逐渐被拍照打卡占据”,一开始代表着人们打破被“书写”的桎梏,跃升为自由主体的城市行走实践者的打卡行为,与其本身想要强调的意义渐行渐远,演变成一种纯粹志在被观赏的行为。“漫游是对一座城市的最大尊重”,人与城市的相遇本应是对原有城市空间秩序的重构,是一种“即兴的创作”,是一种优哉游哉的漫游体验。“如果将城市空间视作一张布满五线谱的白纸,那么行走就是使这张白纸变成终能奏出美妙乐章的音符”[8],漫游者的行走实践对城市空间展开了个体的、具象化的改造,并产生自我与城市的独特空间记忆,让空间真正成为被实践的地点,每一个个体参与书写的“表演的城市”生动而丰富,是一种偶得的行为实践。而看似展现人们对城市景观强大好奇心的网红景观打卡行为更像是一场不经思考的狂欢,经由一个个相同的背景、相同的拍照姿势、相似的体验文本逐渐消解了人们与城市空间的经验性独特联结,看起来就像是被社交平台宠坏的人们为充斥眼前的热闹景象蒙蔽了双眼,没有闲暇也没有信心去发现其它展现城市特质的不同景观。“在旅行尚未开始前,卷入到短视频消费和生产中的用户已经建立了被框架化的常识,已经拥有了结构性的关于所到之地的叙事”[9],城市与身体的互动性大大降低。对他们来说,跟着他人的脚步去打卡网红景点,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城市造访运动,只要留下印记并发布出去、得到圈友的点赞,这个运动就完成了,对城市的感知也仅止于此,看起来十分浅薄。也有学者从文化工业的视角,质疑打卡行为中身体的真正主体性的发挥,认为人们趋之若骛前往网红景观生产出的影像,事实上都是对一套“规范语言”的遵循,早已被纳入网站的内容生产机制中,用来创造以文化消费与生产为目的的认同。
与热闹的虚拟空间相比,真实的城市空间是寂寥的,空有表象的短暂热闹,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打卡者之后,并不给他们留下特别的印象。而是否能有表面的热闹景象还取决于是否有人发现“其物理空间之上附着的精神气质层面的事物”[[8],这种“修辞”式的言说造就只属于这个时代的媒介景观,“例如一家大众点评的网红餐厅一座难求,排队的人群蜿蜒成长龙,一墙之隔的另一家相似口味的餐厅却门可罗雀”[[8]。网红打卡点起初来源于人们的偶得,并不具备唯一性,但经过媒介技术的放大与美化,产生了排他性,而这又与其起初的偶得性相违背,可见网红景观打卡行为兼具开创性与局限性,体验文本在传播与发酵的过程中限制了人们对城市感知的多样化选择,陷入另一种被书写的境地,弱化了“表演的城市”的体验。
五、结语
“打卡本身是体验的过程,也是与环境互动以建立在世存有的过程”[[5],说是媒介技术赋能也好,是人们对身体感官经验的空前重视也罢,网红景观就在打卡——个体不断重复的媒介日常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中形成了。纷纷攘攘的网红景观前,人们鱼贯而上,留下在场的证明,影像可以带着地理位置的标记记录人们在场的情状,而个体在现场感受到的嗅觉、味觉、温觉、触觉、听觉、视觉却无法通过网络传达到屏幕另一端,但屏幕中的人依然起到了界面作用——“身体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去历史的、中性的客体,它是一个穿越历史、地理、文化经验,并且与感官所构成的经验互相交织而成的实体的界面”[[10],帮助屏幕外的人理解城市空间,最重要的是这个界面总能激发新的身体界面去创造属于自身的独特体验,寻找从自己的身体出发,与生活的土地连接而产生认同的可能。可见,剥开这纷攘的表象,检视打卡这一现象级行为的关键,是身体与空间的双向互动构筑起人们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或认同。但我们还应继续追问:技术究竟让人更自由抑或更不自由?在媒介高度参与身体对时空感知的时代背景下,究竟该如何看待技术激起的具身实践浪潮带来的变革意义,个体通过身体这个界面对世界展开的认知是否真的可靠?既然媒介极大便利了身体的日常化物理位移与技术位移,那么又该如何避免媒介技术特性本身带来的感知城市空间的桎梏?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假如抽离人的肉身,城市影像呈现的不过是无意义的物象世界,正是身体为城市影像赋予了灵魂”[[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