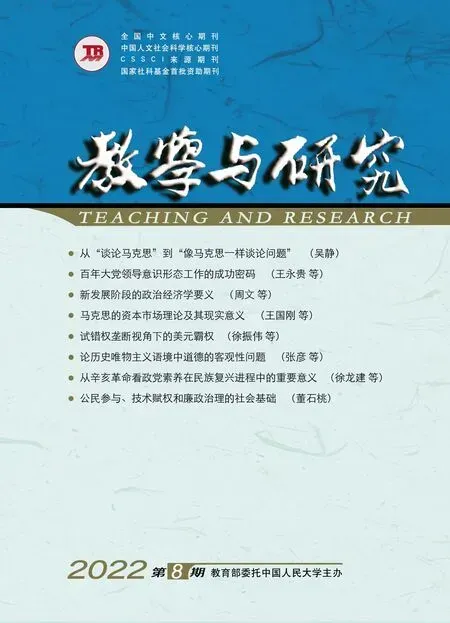论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道德的客观性问题*
张 彦,李家祥
道德的客观性指道德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属性。道德客观主义对此持肯定立场,认为道德价值具有客观性,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道德相对主义则相反,认为不同人、不同社会以及不同时代之间道德价值存在差异,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道德相对主义在文化多元的今天似乎显得非常具有说服力,甚至已被许多人接受,一些文化人类学和道德哲学理论更为其提供了支持性论证。但是,这却导致了一种困境,即在文化多元性和道德多样性已成为事实的境况下,人们进行道德判断越发亟需一种可通约的、客观的道德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对道德多样性和流变性的支持,使其同样面临着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其主要体现在,根据元伦理和规范性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从特定社会形态和阶级立场的角度出发,资产阶级道德与无产阶级道德都是正确的,即使二者存在冲突,人们也应当保持包容态度,这无疑会否定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理论合法性,进而弱化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要走出这一困境,则必须构建一种可通约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这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确证道德的客观性。具体地看,这至少要经历三个步骤的考察:一是剖析道德相对主义否认道德客观性的原因,由此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道德客观性的前提条件;二是回应历史唯物主义所遭受的道德相对主义质疑,说明其支持道德客观性的可能性;三是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为道德客观性奠定基础,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如何支持道德客观主义。
一、道德客观性的前提
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作为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暗含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判断标准的相对主义观点。这一观点曾遭到苏格拉底的批评,在他看来,这种观点会使得不同的人“对任何问题作出任何回答都同样正确”(1),因而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相应地,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观点,追求作为普遍知识的美德,虽然苏格拉底声称自己“不知道美德本身是什么”,却认为“尽管美德多种多样,但它们至少全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性质而使它们成为美德”(2)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202,p.873.,必然存在某种最高的善为美德提供普遍性的标准。要说明道德客观性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追溯西方道德哲学中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论争,从而辨明道德相对主义在当下流行的原因,这也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道德客观性进行辩护的前提性工作。
事实上,从古希腊乃至中世纪,道德客观主义一直是西方道德哲学的主流立场。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最高善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他提出永恒的、不变的“善的理念”,为美德提供普遍的、客观的标准。“善的理念”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终极实体,是所有事物、所有行动最后的原则,也成为所有伦理行动的依据。柏拉图的理论把道德的客观性建立在实体这一确定基础之上,奠定了古希腊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和目的论基调。此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同样以形而上学和目的论为基础,只是相比柏拉图,他试图为苏格拉底关于最高善的问题提供更为具体的回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的善在于其特定本性的实现,事物的目的就是显露其特定的本质,对人来说,这种本性的善所趋的目的即是“幸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依靠形而上学的实体确证道德的客观性,借助目的论的形式,道德原则与最高的善实现统一,是最早支持道德客观主义的理论体系,其重要意义在于奠定了道德客观主义的基本模式,即道德的客观性必须借由外在的客观基础进行确证。直至中世纪,这种道德客观主义体系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只不过在神学的笼罩下,上帝成为了最高善的代名词。奥古斯丁认为,对人来说最高的善存在于对上帝的爱之中,且人自身无法获得确定的知识,只能通过禁欲、节制和自制仿效基督,达到相对的完善。这意味着关于美德的知识必须借由上帝获得确证,在形而上学和目的论的意义层面,奥古斯丁仍然遵循古希腊的实体主义传统,支持道德客观主义,上帝作为超验实体,仍然发挥着提供绝对伦理标准的作用。而当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相融合以后,古希腊的伦理传统在中世纪伦理学中更加凸显。阿奎那认为,“每一件事物都是由于上帝的善才被称作善的,这上帝的善即为所有的善的第一原型的、动力的和终极的原则。”(3)[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卷,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5页。上帝在创造中显示了他的善,万物的本性都以其善为目的,并因其善而成为善的。
然而,道德客观主义在启蒙以后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当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方式确认“我思”的不可怀疑性之后,道德客观性的依据就已经从外在的实体转移至人的内心。不同于将外在实体视作宇宙秩序与道德原则原因的前现代传统,笛卡尔宣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完全拒绝这种目的论的思维模式,并抛弃了所有关于实体逻各斯的理论”(4)[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这也使得从人的内心出发为道德标准寻找新的合理性证明,以某种人性确证道德的客观性成为启蒙以后哲学家们面对的新任务。
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系统论述了启蒙以后哲学家们进行证明的尝试,并将其称为“启蒙筹划”,主要包括休谟、康德和克尔凯郭尔提供的三种类型的论证。其中休谟在“理性”和“道德感”之间选择了后者,将人的激情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而康德则与休谟恰恰相反,认为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理性规则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能够提供绝对客观的标准。克尔凯郭尔所面对的问题是对休谟和康德论证的继承和延续,不过他已意识到这种证明筹划将会失败,因而他同时摒弃休谟和康德的选择,将道德判断诉诸无确定标准的人的“选择”。麦金太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启蒙筹划是必然失败的。因为不管哲学家们选择何种人性概念作为道德的基础,作为全然事实性的人性概念都会与道德的或者评价性的结论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而“这条原则一旦被接受,就成了他们全部筹划的墓志铭”(5)[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随着传统道德权威的失落和人类主体理性的崛起,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道德的客观性失去了确定依据,启蒙以后的道德哲学在对人类社会道德多样性进行解释时也往往走向道德相对主义。那么,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否能够实现统一?只有顺利解决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为道德的客观性提供证明,这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确立道德客观性的前提条件。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道德相对主义的深层原因正是在于,它同启蒙以后的道德哲学一样,对通过外在实体确证某种“永恒道德”的做法表示拒斥。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在他们看来,以往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充斥着意识形态,且只会助长存在“永恒真理”的错觉。而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道德只是“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中的一种,必须从作为其物质基础的“市民社会”来解释,即不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虽然马克思在说明其历史观时所批判的对象是费尔巴哈的“类”、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以及施蒂纳的“唯一者”,但在他看来,这些词句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乃是思辨的前提,其出发点并非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这样的历史观反映在道德哲学中意味着两种倾向:反形而上学与反先验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拒斥将外在实体作为道德客观性的依据,而力求以“纯粹经验的方法”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接受任何思辨的先验设定。
但是,这并不代表历史唯物主义同启蒙以后道德哲学一样,无法解决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人的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性活动,可以成为沟通事实与价值的桥梁。
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像传统哲学一样“解释世界”,而且更强调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合理地“改变世界”。从这一角度,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拒斥的是实体主义本体论解释世界的思辨方式,这表明其与启蒙以后道德哲学也存在根本不同,因为就从追求普遍道德标准的方式而言,从特定人性出发和从外在实体出发,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脱离实践的解释世界,把道德归因于观念的运动。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客观世界,认为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的“客观存在”。把一切现实的与人有关的存在都“当作实践去理解”,首要的意义在于实现了由思辨前提向现实前提的转换,找到了“改变世界”的现实主体力量,即“现实的个人”,认为人是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参与并影响现存世界。
另一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人的实践同时遵循两种尺度,即作为客体世界发展规律的外在尺度和作为主体自身目的与需要的内在尺度。从这一角度,人的具体的实践过程既受到事实因素的约束作用,也包含着价值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实践结果既是对认识的事实性检验,也包含人自身主观需要与价值诉求的实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哲学的主要缺点在于没有把实践活动看作是“对象性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要么缺少对对象从主体方面的理解(旧唯物主义),要么“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唯心主义)。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是道德哲学中事实与价值之间产生裂隙的深层原因。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则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结构,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客体的外部世界与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在实践活动中是统一的。正因此,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道德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人作为价值主体的能动作用,忽略人的道德实践本身是客观的活动,受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乃是处于统一样态,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歧只是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历史的分歧,而不是抽象思辨的永恒的分歧,二者只是历史的不同环节,并最终会在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得以解决,实际上并不存在二者相分离的现实状况。因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确证道德客观性的前提性问题就能够得以解决。
二、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客观性的标准
进一步深入历史唯物主义语境考察道德的客观性问题,就会发现,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由来已久。早在1906年,卡尔·考茨基就在《伦理与唯物史观》中提出人类社会在道德方面不断变化的观点,他认为,“一切道德都是相对的,所以所谓的不道德,只不过是一种偏离的道德”,而且“就道德标准而言,绝对道德和绝对不道德一样稀少。甚至不道德在这方面也只是相对的”(9)Karl Kautsky, 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918, pp.192-193.。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如艾伦·伍德提出,“对马克思来说,交易或制度的正义与否,将依赖于它们与它们所隶属的那个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某个生产方式中的正义制度,可能在另一生产方式中是不正义的。”(10)Allen W. Wood,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72, 1(3):244-282.理查德·米勒也在其著作中表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中缺少在所有社会中都有效的普遍准则,因而无法解决不同社会形态对道德价值认知上的冲突,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11)参见[美]R.W.米勒:《分析马克思——道德、权力和历史》,张伟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41页。
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道德相对主义的直接原因在于,其主张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为道德多样性和流变性提供了依据。这一点确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有迹可循。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道德作为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因而是动态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迁,这必然导致人类历史领域中的道德多样性现象。从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看,同一时代内发挥规范作用的绝不只一种道德,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各种道德观念在历史中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同道德标准间的冲突就显得似乎难以解决。恩格斯曾谈及这一现象:“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13)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同时存在“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现代资产阶级道德”以及“无产阶级道德”,但他拒绝将任何一种道德论作为永恒的道德真理的做法,认为道德世界没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99页。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恩格斯鲜明地支持了道德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这在追寻普遍道德标准的道德哲学家眼中,必然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同道德相对主义一样支持道德多样性和流变性,却不意味着二者在内在观点上具有一致性。根据黄百锐的解释,道德相对主义实际上包含三种论题:(1)描述性相对主义,即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和不同个人的道德判断存在广泛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涉及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2)元伦理相对主义,即不存在一个能被证明是普遍正确的道德标准;(3)规范性相对主义,拥有不同道德规范的社会、群体之间不应当相互评价或干涉。(15)David B. Wong,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ersion 1.0, Volume 6, Routledge, 1998, pp.539-541.从这三种论题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多样性和流变性的观点只是符合了描述性相对主义的部分特征,即经验地看,人们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在不同社会中存在差别,人类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道德规范也往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
描述性相对主义只是肯定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道德多样性现象,并不蕴含关于道德对错的看法。同样地,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对道德观念如何产生、发挥影响乃至维系进行解释,得出各种道德观念在历史中都存在合理性的结论,这种解释也并不意味着判断其正确与否。正如历史唯物主义会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一条道德观念符合特定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并被其接纳,该道德观念就有可能在该社会中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支持这一观点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会主张:该道德观念对于该社会的被统治阶级而言可能并不正确,即使他们已经接受了它。因此,即使历史唯物主义支持了道德的多样性和流变性,并不意味着其作出了关于特定道德观念对错的判断,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不会因此缺少效力。
然而,一旦描述性相对主义加上另一个限制性论题,就会导致元伦理和规范性的相对主义,从而产生损害无产阶级道德批判效力的结果。这个限制性论题是:“一个行为是对是错,取决于用哪一个特定社会的道德标准来判断。”(16)程炼:《伦理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这个论题将特定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一个特定群体或社会中。实际上,伍德正是基于此种论题认为,马克思不会以正义或不正义的道德词句评价资本主义,虽然他在其文章中承认马克思的理论并不会直接导致元伦理道德相对主义,但当谈到资本主义是否正义的问题时,他却毫不犹豫地为马克思加上了限制性论题。他说:“一个制度的正义,取决于这个特定的制度以及它所构成的那个特定的生产方式。因此,正义的一切法权形式和原则,如果没有被应用于特定生产方式,便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们的内容及其所应用的特定行为是自然地出自这种生产方式,并与这种生产方式具体地相适应,它们才能保持其合理有效性。”(17)Allen W. Wood,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72, 1(3):244-282.同时,米勒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即根据马克思的道德理论,“用来指导现在或指导将来的准则不适合用来判断过去”(18)[美]R.W.米勒:《分析马克思——道德、权力和历史》,张伟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0页。。这样的限制性论题实际上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多样性的观点引申为元伦理和规范性的相对主义,也剥夺了无产阶级基于自身立场对资本主义道德进行批判的权利。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会接受这样的限制性论题。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显而易见,如在论述剩余价值生产时,马克思写到:“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3-744页。这种跨阶级的道德批判潜在地表明了,即使马克思认为道德具有多样性,也依然存在能成为普遍尺度的道德准则;而且,这种准则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其并不诉诸平等、正义等基于法权的道德,而是诉诸人类解放进程的尺度。
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确实认为诸如平等、正义等基于法权的道德原则不具有跨阶级的普适性。因为历史地看,人类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对平等的要求往往不同,如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所说:“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100、100页。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平等的诉求也充满矛盾。在阶级对立仍然存在的社会中,法权道德往往依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制定,将阶级利益充当社会全体利益,通过扭曲化、神秘化的手段蒙蔽被统治阶级,以固化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因此,恩格斯强调,“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100、100页。,实际意指法权道德不能成为跨阶级的普遍准则。
但在另一方面,在消灭阶级对立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以人类解放进程为尺度,进行跨历史阶段、跨阶级的道德判断。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更包含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追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理想。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阶级社会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王国,利己主义是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因而“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22)[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32页。。在这种情况下,法权道德往往带有意识形态的欺骗,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即使具有补救性的作用,也只是有限的。因此,在阶级社会,由于“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人的自由与解放无法得到真正实现。而为了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消灭阶级对立(这是法权道德赖以生存的环境),认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100、100页。。这种“真正人的道德”以人类解放进程为尺度,追求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追求“真正人的道德”,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了囊括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视野,能够进行跨历史阶段和跨阶级的道德判断。
因此,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符合描述性相对主义的部分特征,却不会接受特定道德规范适用特定群体或社会这样的限制性论题,并不会导致元伦理或规范性的相对主义,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也不会因此失去效力。
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道德的客观性证明
基于以上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与元伦理和规范性的道德相对主义划清界限;但这并不足以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确证道德的客观性,与构建一种可通约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更是相去甚远,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能够并以何种方式支持道德客观主义,这主要可以从道德的客观基础和道德进步论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道德提供确定的客观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道德哲学史的角度看,道德客观主义有其特定证成模式,即“道德价值的客观化观点实际上有外在的来源”(25)J. L. Mackie, 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Penguin Books, 1977, p.43.。无论什么形式的道德客观主义,道德的客观性都是通过特定客观基础进行确证,由事实存在推出道德应当。那么,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提供类似的客观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此做出肯定回答:“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异化的扬弃视作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那么,以人类解放进程为尺度,通过将道德与生产力发展趋势是否一致、与先进生产方式是否适应进行判断,历史唯物主义便能够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推出道德应当。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同描述性相对主义的区别。虽然二者同样都为人类社会中道德的多样性现象提供了支持,但依据并不相同,描述性相对主义对道德多样性的解释基于人类文化的差异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前者只看到了人类社会中的多元文化现象,将道德差异归因于社会风俗的差异,对发现多样性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持消极态度;后者则坚信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受到客观规律的的支配,并主张应该“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302页。。这也导致二者对待道德多样性态度的差异,前者认为人类社会中道德规范的差异是广泛的、深刻的,无法真正调和,只能寄希望于异文化间的人们持相互包容的态度;后者则坚信道德现象受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即使人们的许多道德行为看似受到情感、欲望的驱使,但“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302页。。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据此对道德的变迁做出了合规律性的解释。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规范体系所呈现的样态,以往人类社会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时期:一种是特定社会形态稳定发展时期,另一种是社会形态交替时期。处于第一种时期,人类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相对固定,道德规范体系也相应呈现较为稳定的样态。虽然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只是整个人类历史存在的暂时形式,但如同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特定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释放生产力的过程通常是漫长的,当人类历史长期停留于某一阶段时,与特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便具有稳定的客观现实基础;而且,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稳定的道德体系往往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制定,呈现意识形态的特征。处于第二种时期,人类社会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不同阶级的道德观念往往处于激烈冲突的状态。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不同道德规范体系中仍然能够找出共同的因素,这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共同的现实因素,能够成为特定道德规范长期存在的客观基础。借用恩格斯的举例,如“切勿偷盗”这样的道德戒律,在不同形态的私有制社会中必然一致,因为它代表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共同诉求。
其次,在主张道德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基础之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相对应,人类社会中道德也会随之发生进步,支持道德进步论。历史唯物主义支持道德进步论的原因在于,对道德与其客观现实基础之间关系的解释基于一种依随性的视角,而非还原式的。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道德根源于经济基础这一客观实在,却又不是单纯将道德还原为自然物质现象,而是同时肯定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如恩格斯在阐明人类社会发展受到一般规律支配的同时,也认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302页。,即“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302页。。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类作为社会实践的行动主体具有能动性,能够通过设定实践的目的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说明,人类历史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而自由王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9、928页。,“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9、928页。。当人类历史表现为由“外在目的”到“目的本身人类能力的发展”这一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过程时,道德作为人自身主观需要与价值诉求的实现的集中体现,必然表现为一个不断发生变迁,由初级诉求不断实现到高级诉求不断产生的过程。
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随性不是同步发生的,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具有独立性,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但正是这种“或快或慢”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不同道德观念在发生冲突时,辨别其进步与否具有了重大意义,因为更为先进的道德往往意味着人类摆脱物质生产“外在目的”进程中的更高层次诉求。关于这一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虽然人类历史上道德领域散播下的真理是最稀少的,但是“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98-99、113页。。因而,在面对“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现代资产阶级道德”以及“无产阶级道德”三种道德观时,恩格斯做出断言:“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98-99、113页。也正是根据这样的看法,恩格斯在进一步论述“平等”这一道德规范时认为,“平等”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98-99、113页。。因此,即使人类历史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是多种道德观念、道德标准共存的状况,却只有其中最能反映社会变革诉求的那种道德观念,才更加进步、更能满足人类解放自身的目的性追求。
综上,历史唯物主义虽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道德的多样性与流变性现象,但并不会因此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可通过说明道德变迁的客观规律,将道德的客观性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基础上,以道德进步论的方式支持道德客观主义。
至此,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道德的客观性便得到了初步证明。这意味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今天,依然具有历久弥新的效力。因而,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树立具有阶级意识的价值形态,激发世界无产阶级进行自发政治运动的积极性,仍然具有时代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构建一种可通约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可能性。在文化多元的今天,一种具有可通约性、科学的道德理论不仅能为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赖以维系的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更能为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明形态突破意识形态硬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道德共识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