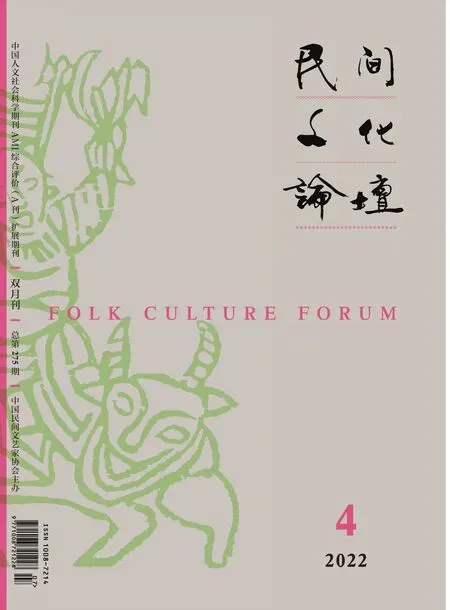论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
—— 兼谈接受历程中的“形式主义误解”
周毅恒 黄卫星
弗·雅·普罗普(В.Я. Пропп)是20世纪世界民间文艺学的大师级学者,其研究涉及民间文艺理论、民间故事、叙事诗等多领域,被誉为“结构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①С. Ю.Неклюдов ,“В.Я. Пропп и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No. 3 (1995), С.30.此文涉及到的俄文文献为笔者自译。普罗普的扛鼎之作是其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态学》。②本书原名《神奇故事形态学》(Морфология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为赋予该书以更大的意义,编辑出版时删去了“神奇”一词。经过欧美学界的积极推介,该书与所提出的功能结构诗学不仅直接推动了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发展,还构成一种故事机制,进入多个学科的集体记忆,成为广为人知的理论。但与普罗普的身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其功能结构诗学的基础性问题一直关注不足——特别是对诗学思想渊源的阐释上。其中,属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最为不清。今天我们对普罗普的身份认知大多源自西方结构主义叙事著述:西方结构主义把普罗普定义为俄国形式主义一员,在民间文艺领域挥舞着形式美学的大旗。之后又随着结构主义文论的经典化,“俄国形式主义”便成为普罗普深入人心且广为人知的经典印象。但实际上,如若重新回到普罗普功能结构诗学发生的起点,去考究两者在不同层次上的关联性,会发现其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关系是复杂而错位的。普罗普既非俄国形式主义阵营一员,其功能结构诗学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俄国形式主义”的直接成果。所以不能将普罗普简单等同于“俄国形式主义”。本文将深入历史语境并结合“俄国形式主义”的多重义项,分类讨论两者间亲缘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辨析西方接受的种种误解的同时,重新厘清普罗普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解立场与接受景观。
20世纪早期的俄国文艺学,最亮眼的莫过于“俄国形式主义”。事实上,“俄国形式主义”本身就是个结构性概念,具有复数性、多义性特征。从语义学看,笔者以为“俄国形式主义”至少有以下三种义项:
第一,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与风尚,俄国形式主义祛魅并动摇了外部因素的种种真理性,将权力的重心请回了语言本身,强调文学的自主性问题。该风尚针对庸俗社会学诗学的庸俗化倾向,具有本体性上的突围意义。
第二,作为一种文艺流派,当时文艺学界产生了所谓的形式主义阵营。阵营内部在初期比较统一,中期之后则开始分化,产生了多元复杂的理论倾向与立场。
第三,作为一种文艺研究方法论,俄国形式主义将研究视角从以外部条件为重心转为以文本为中心,由此产生了一条研究诸如“文学性”“语词制作的技巧”等实证要素的科学主义研究路数。尽管与后期相对严谨且逻辑化的论述笔调不同,其前期研究总体以抒情、洒脱的笔调为主,但其核心是一脉相承且稳定的,即始终以语言的能指形式为旨归。
三种意义内外契合,共同构成了意蕴复杂的结构性“俄国形式主义”。以下笔者将分类讨论,逐一考察这三重义项与普罗普的互动关系,发现普罗普对“俄国形式主义”并非是一种整体性的等价接受:对于不同义项,他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并时刻保持着批判性眼光。
一、与“俄国形式主义风尚”:基于“形构-历史”框架的故事识别-阐释实践
对于强调文本内部自主性的“俄国形式主义风尚”,普罗普实际上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外部因素依然具有无法被动摇的真理性。他上承俄国历史主义诗学传统,把“根源与历史”作为民间故事最具分量的外部因素。他在《论民间文艺学的特殊性》(1946)和《论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历史主义及其研究方法》(1964)等论文里反复强调了民间文艺中历史维度的重要性。而在《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中,普罗普这一立场展露得更为明晰,他把第一点的“俄国形式主义风尚”界定为:
1.“所谓‘形式的方法’主要的缺陷在于它往往将研究者引向将文学看作手法之和、看作机械混合体的观点。”(引自洛特曼语)
2.对形式主义者们来说,形式具有其独立自生的规律和不以社会历史为转移的内在发展规律。
3.文学创作领域的发展便是为形式规律所规定的一种自我发展。①[俄]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5—186页。
在普罗普看来,“俄国形式主义风尚”倡导一种内在的自我发展观,从彼形式到此形式,形式自身的演变趋向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发展逻辑。但这种发展观与庸俗社会学的教条主义发展观一样,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在《论民间文艺学的特殊性》中对此有过详论。
普罗普认为,民间文艺无疑具有自身特定的结构规律,所以研究内部结构是民间文艺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研究作品的内在结构对于民间文艺学而言是重要而又艰巨的。民间故事、叙事诗、谜语、歌谣、咒语等民间文艺现象的结构之规律,人们至今知之甚少。”②В. Я.Пропп ,Фольклор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76, С.20.如何研究呢?普罗普认为应当采用文本分析——这显然就是“俄国形式主义风尚”倡导的自我发展观,将发展全局自限于文本之中。但问题是,文本分析不仅具有缺陷,还只能描绘并揭示这些内部结构现象的存在,而无法解释它们。民间文艺研究恰恰需要进行进一步解释,“真正的历史科学要求不仅是确定发展过程这一事实本身,还需对其进行解释。诗学的创作是上层建筑性质的现象。解释意味着把这些现象抬升于造成现象的原因之上,而这些原因便在于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之中。”③同上,第25页。在普罗普看来,对民间文艺的民族志主义起源学研究正是“解释”的途径。所以“发展”不能仅局限于“内”,还应融入“外”的历史维度,构成“从内向外”的双线叙事:内部的形构发展逻辑能证实、揭示现象之存在;而外部的历史起源学逻辑则进一步解释其存在,将其回溯至历史往昔,探寻现象得以发生的根源。所以普罗普这里的“发展观”,既非“俄国形式主义风尚”倡导的内在自限性道路;也非庸俗社会学诗学倡导的教条主义道路,而是一种由内到外、由描述性到解释性的形构-历史道路,强调内部结构与得以形成内部结构的某种历史秩序相统一。
普罗普这一“第三种发展观”是将俄国两条重要文论遗产——历史诗学与形式美学相互补的成果;而这番“形构-历史”框架,也正是《故事形态学》与《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所共同承载的问题意识。“我不是与形态分析断绝往来,而是开始寻找在神奇故事情节比较研究中揭示出的那个系统的历史根基”①[俄]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第184页。,他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民族志材料的归纳主义研究,追寻了神奇故事各种母题的历史源头。本书还印证了普罗普曾提出的民间文艺学与民族志学的互动关系,“民族志学对于我们从事民间文艺现象的起源学研究尤为重要。民族志学是民间文艺研究的基础,若无这个基础,民间文艺问题便会悬而不决。”②В. Я.Пропп, Фольклор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С.27-28.最终,作为形构-历史路线的优秀成果,“功能结构诗学”与“历史民族志诗学”一体两面,共同构成普罗普民间故事研究的终极旨归。
值得关注的是,从普罗普自身的故事研究脉络看,这一始于对故事识别机制的思考、终于历史维度阐释的“形构-历史”框架,实质是“故事识别”与“故事阐释”相互动的文艺研究实践。诗学“功能观”的提出建立于对故事识别既有理论的反拨,“功能”如同维谢洛夫斯基的“母题”、沃尔科夫的“情节”一样,都是故事识别的基本识别单元。在《论民间故事收集索引的编纂》(1927)一文中,普罗普曾尝试建构一种基于非稳定要素与“功能”相联袂的故事识别机制;但在一年后的《故事形态学》里,普罗普则专事“功能”,将其作为故事识别的唯一尺度。而正如其在书中所言,“在阐释‘故事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前,必须要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③[俄]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第3页。。在其理论构想中,“故事识别”是“故事阐释”的前提;识别的目的,是为进一步的阐释奠基。只有确立了故事本体的形态结构,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阐释研究。因此形构研究的实质是识别实践,历史研究则是阐释实践,形构与历史的一体两面,本质是意图寓识别与阐释于一体。所以功能结构诗学并非纯粹的形式文论,其问题意识可规约为:进行科学的描述性故事识别工作;为解释性的故事阐释奠基。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正是由其奠基的阐释性著作。普罗普在晚年的民俗学专著《俄罗斯农事节日》(1963)中,又一次使用了“形构-历史”框架,对俄罗斯的农假节日民俗进行了识别-阐释研究。
日后列维-斯特劳斯曾提出困惑:既然两者一体两面,又为何其形态研究(1928)要比历史研究(1946)早问世近二十年呢?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在普罗普70岁寿辰纪念会(1965)上,时任《故事形态学》编辑的日尔蒙斯基曾专门就此向全世界澄清:《故事形态学》书稿共十章,最后原有“历史根源”一章,是他提议能否先出版前面重点讨论的形态研究部分,最后的起源学部分待成熟后另行出版。普罗普接受了,于是前九章以《故事形态学》为名问世。④Путилов Б. Н., “Владимиру Яковлевичу Проппу —100 лет,”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No. 6 (1995), С.147.最后一章普罗普一方面花了十年扩容,一方面又不断发表其中部分母题的起源学考述,如《论神奇故事的起源问题(兼论母题“坟墓上的魔树”)》(1934)、《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男性公房”》(1939)、《论奇异诞生之母题》(1941)等等。1938年书稿完成,普罗普凭其晋升教授;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该书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所以从历史事实看,尽管普罗普在一开始就提出并践行“形构-历史”思路,但其早期对于历史维度的起源学考察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因此也难怪西方会“望文生义”,仅凭时间差便提出所谓抛弃形态的“历史转向”误解。①Чистов К. В., “В.Я. Пропп: легенды и факты,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No. 6 (1981), С.59.1998年,俄罗斯迷宫出版社再版了普罗普著述,两书合二为一,构成完整的研究神奇故事体裁的民俗识别-阐释著作。
普罗普晚年曾就此回应列维-斯特劳斯,“这些话包含了在将来进行这种历史研究的许诺。它们是一张特殊的期票,对这张期票,尽管过去了很多年,我依然要守信偿清它”②[俄]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第184页。。可见,将形构与历史相结合,是普罗普一开始就立下的研究思路。因此对于作为社会思潮与风尚的“俄国形式主义”,普罗普与之的联系似乎更多是一种批判性的承继,他将其之文学自足性许可与历史诗学的历史维度相融合,在两条发展路线之外,走出了“形构与历史”一体两面的第三条发展路线。
二、与“俄国形式主义阵营”:观看与欣赏
关于第二点,不少西方学者把普罗普看作是“俄国形式主义阵营”的一员,如比尔·科娃-雅各布森认为普罗普是“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杰出成员”③Svatava Pirkova-Jakobson,“Preface,”in V. Propp,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trans. by Laurence Scot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58, p.vi.;罗兰·巴特把普罗普与托马舍夫斯基都归为“俄国形式主义派”人物④[法]罗兰·巴特:《叙述学研究》,张寅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等等。但从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普罗普实际上从未投身过形式主义阵营,他与形式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零距离的“认同并参与”,不如说是保有一定距离的“观看与欣赏”。
在《故事形态学》出版前,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阵营之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直接联系,他既没有参与过流派内部的任何论争,也没有作为其中一员,成为争鸣与被争鸣的对象。在形式主义阵营兴盛的十余年里,他先是在彼得堡大学斯拉夫语文专业学习,后在几所中学和高校潜心教书(以语言课程为主),与形式主义流派的学术圈并无交集。按照普罗普自己的说法,他在读大学期间发现当时(沙皇时代的学院教育)对语文学科的文学训练非常薄弱,民间文学更是不受重视。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他自1918年大学毕业就开始研究阿法纳西耶夫民间故事,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假日里写书;期间他一直独自思考撰写,既未咨询过任何人,也未受过任何指导。普罗普于1926年在奥尔登堡的《故事委员会年刊》上发表了一篇民间故事角色类型的简短论文,这是日后广为传颂的功能角色理论的前身;1927年,他在《故事委员会年刊》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故事分类的论文,其中将“功能”作为了一个分类项。其民间故事研究最终书稿的形态研究部分在1928年以《故事形态学》为名问世。⑤А. Н. Мартынова,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В. Я.Неизвестный Пропп, Сос. А. Н. Мартыно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02, С.10-11.如果以形式主义流派从发轫到兴盛再到式微的十余年历程来看,普罗普与形式主义阵营的交集主要体现在与阵营中个别人物的私人交往上。所以客观的说,这一时期的普罗普应算是一位独立学者,我们不能断定其属于形式主义阵营还是反形式主义阵营还是其他,因为他并未向学界直接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当然这或许和他的性格有关,从普罗普学生的回忆看,普罗普的性格小心谨慎、低调谦卑,与外界沟通不多,是位书斋型学者。①И. П. Лупанова, “Учитель и Друг,”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В. Я. Пропп, С.396-397.
尽管依照事实和普罗普的自叙,可以认为其与形式主义阵营并不存在直接联系。但通过一些细节和事实,可以断定,普罗普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来自形式主义阵营的间接影响。他就如同一位看戏者,虽未置身戏中,却一直在驻足观看,且心怀欣赏。
普罗普除了因列宁格勒战役被迫疏散到萨拉托夫三年,其余时间都生活在列宁格勒。从出生到求学再到工作,普罗普与这座发达的工业城市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1916年,由什克洛夫斯基发起的文学团体“奥波亚兹”在彼得堡大学成立,与莫斯科语言小组遥相呼应,共同掀起了形式美学的研究热潮。而这时的普罗普正与巴赫金等同学在彼得堡大学文史系读书。当时还是学生的普罗普曾参加过文学家谢·苗·范格罗夫(С. А. Венгеров)组织的普希金研讨会,在那里,他与学长尤·尼·蒂尼亚诺夫(Ю.Н. Тынянов)等日后的形式主义先锋们有过交集。所以尽管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形式主义阵营渐起之时,他就已具备近距离观看的条件。
普罗普对形式主义阵营的欣赏体现在书稿写就后的一系列行为上。他在自己70岁寿辰时的讲话中提到:1928年书稿完成后,他先后拜访了鲍·米·艾亨鲍姆、德·康·泽列宁和日尔蒙斯基。②[俄]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第200—201页。艾亨鲍姆是著名文艺学家、形式主义阵营的中流砥柱;泽列宁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俗学家;而日尔蒙斯基也曾是形式主义阵营的重要人物,所主持的艺术史所是形式主义研究的一大阵地。所以就如贾放所言,“尽管没有组织联系,但作为一种气氛,其(形式主义阵营)影响渗透在普罗普的精神之中”③贾放:《普罗普的故事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4页。。形式主义阵营带来的精神与思维上的熏陶,无疑成为普罗普日后多元思维方式中的重要一支。
因此从史实看,西方为普罗普勾勒的“形式主义者”形象只是一种带有主观意味的幻觉与误读。尽管他与形式主义阵营有过一些私下交际,但也只是在大时代下任何人都逃脱不开的时代留痕。况且从始至终,普罗普对形式主义阵营的态度都只是“观看与欣赏”,他了解他们的诉求与主张,也欣赏他们肇开新声的勇气与心血,但若以此就断定他是个“形式主义者”,甚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也委实冤枉。笔者认为,在形式主义阵营面前,普罗普只是对其提供的各种全新文艺思维感兴趣而选择驻足观看的诸多年轻文艺学者之一——这样的定位,可能更为真实。
三、与“俄国形式方法论”:一种可借鉴的实证工具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功能结构诗学在方法论上同源于俄国形式美学,如V.厄利希认为功能结构诗学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战略”④[美]V.厄利希:《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张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77页。;比尔·科娃-雅各布森也认为《故事形态学》是“正统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典范”等。尽管这些评价本身就值得商榷,但如他们所言,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具有应用维度上的沟通与互动,其功能结构诗学受惠并具有俄国形式方法论的理论特征。
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多次表现出对“形式方法论”赞赏与认同的态度。他在第一章“问题的历史”中提出了整体的问题意识,即先进行形态研究,再在此之上进行历史研究。但为何要将形态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石呢?普罗普的回答充满着实证色彩,“不曾尝试过形态学问题的历史学家,在类同实际存在的地方就会对它视而不见;他会漏过那些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然而却未被他发现的吻合之处。相反,在形态学专家看到类同的地方,他会指出,他所比较的现象是全然不同的”①[俄]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第15页。。他这里预设的大前提是,所有现象都存在类同性。这显然承继自歌德形态学的问题意识。
如何研究类同性呢?普罗普秉承“形构-历史框架”,将故事现象分为内部/外部两个整体,即形态整体与历史整体。前者确定“是什么”,后者再在此之上追寻其“从何而来”。对于前一个整体——形态整体,普罗普明确指出,肇开时代新声的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值得参照:“很多东西有赖于形式研究。我们不惮去做沉重的、分析性的、需要点耐心的工作,这项工作由于是从抽象形式问题的角度着手而更显复杂。类似沉重‘乏味’的工作,正是通往概括有意味的结构的途径。”②同上,第15页。普罗普上承歌德形态学与德国形态诗学,认为在自然界林林总总的具体现象中可能存在某种“类同性”,既然形式与内容无法分割,那么通过形式研究,概括出“有意味的结构”(即形态类同),就可以从实证角度确定类同性现象的本体性。有了这些,就可进一步引入历史维度的起源学考察,思考“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更大领域”(即历史类同)。很明显,普罗普之所以在方法论上认为形式研究值得借鉴,其一为,形式主义反对将内容和形式相割裂的态度无疑简化了实证“内容类同”的难度,只需实证形式并对形式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勾勒出“内容类同”;其二为形式主义方法论能更有效的判定“故事相似现象的性质问题”,“形态本体”的建构能取代过去的“内容本体”,“从组合或结构的观点出发对故事进行比较,那样的话,故事的相似将会从新的角度呈现出来”。③同上,第152—153页。所以普罗普对形式方法论的借鉴,更多是出于实证“类同的性质问题”的需要。而作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故事形态学》,也因此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形式主义方法论。
由此带来的,便是功能结构诗学具有“形式主义特征”。对于这些特征,过去的叙事学著述已充分言及,本文不再老生常谈。但有两点,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说明:
第一,正如美国普罗普研究专家沃纳所言,普罗普形态研究的“形式主义特征”仅存在部分,绝不适用于整本书。④Э. Э.Уорнер,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 и русская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ПбГУ,2005, С.20.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在问题意识、最终旨归与实践上都有本质不同,他只是在形态研究的具体过程中部分融入了形式方法论,而非将形式方法论完全移植过来。其民间故事研究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以形构与历史的“一体两面”框架进行的,此处的“形构”并不像割裂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论”。
第二,其形态研究与现代语言学思想还是存有一定距离的。从学理看,俄国形式主义无疑深受索绪尔语言学启发,普罗普形态研究重文本、重整体等特征也可与索绪尔语言论产生对位;但若以此就断定其形态研究完全受惠于索绪尔语言学,难免以偏概全。首先,从表面看,普罗普的形态研究是共时性研究,但从其编排功能的顺序、构建功能间组织关系的方案看,给出的却是历时性成果。因为其对于所指单位的编排原则与构成方式借鉴的是传统语言论框架下的德国形态诗学研究;其次,普罗普的文本分析也同样局限于传统语言学视野。他并未像索绪尔甚至是俄国形式主义者那样,意识到“能指”和“所指”间的约定俗成关系,而是秉持传统语言学思路,认为语词秩序必然代表行动秩序,每个词背后都是代表一个行动——而非是创造一个行动。按经典叙事理论的话来说,就是未能意识到“叙述”与“故事”间的界限,而是将二者看作是一个整体,前者代表后者。结构主义理论家正是看到了普罗普这一问题,日后用结构语言学思维进行了更具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
可见,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融贯性。但部分西方学者给出的类似“正统形式主义法”之类的评价,则充满着“距离误读”与“主观想象”。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普罗普形态研究的最终目的并非停留在语言/文本本身,而是想借此回溯历史往昔,探寻那埋藏其中的深层根源与奥秘。
四、与“形式主义指控”:三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主义”
通过考察以上三重关系,不难发现,普罗普只在方法论上部分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研究法,将其当作整个形构-历史研究框架中的一种研究工具,而非完全与整个“俄国形式主义”同步。他在历史诗学与形式美学基础上所创制的形构-历史诗学,与当年意气风发的形式主义青年们有着本质区别,并最终表现在问题意识、研究旨归与学术立场的迥异上。但可惜的是,两者间的差异不仅未被学界留意,反而却因此招致横祸。《故事形态学》出版后,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数十年后的西方学界,都遭到了“形式主义指控”:他们把普罗普的形态研究简单理解为“俄国形式主义”著作,并为其扣上饱含政治寓意的“形式主义帽子”。对此我们应当意识到,普罗普形态研究的“形式主义方法论”、俄国形式美学的“形式主义”、与所谓的“形式主义指控”,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具有本质差异的“形式主义”。
俄国形式美学的“形式观”之所以能肇开新声,根本原因在于,它摆脱了长期以来由“形式”与“内容”相对立而形成的二元论“旧形式观”,而将两者融合起来,提出两者不可分割的一元论“新形式观”。所以无论是所谓的“文学性”,还是“制作的技巧”,所承载的都不仅仅是纯粹的空洞形式本身,而是形式-内容一体化的“新形式”。但这一立足于反对“内容”与“形式”相分离而建立起来的“新形式”却并未得到学界以充分理解,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西方,都还是将“新形式”混同于“旧形式”。在苏联,政治上的“反形式主义运动”赋予了“形式主义”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导致“新形式”被刻意替换为政治上的“形式主义”,而被官方限制。1934年,作家沙·基尔沙诺夫在全苏作协一次会议上就曾公开为“新形式”的艰难处境鸣不平:
只要一接触到诗歌的形式问题,隐喻、诗韵或者形容语,就会立即引起反驳:让形式主义者们住口!人人都冒着被扣上形式主义罪名的危险。形式主义这个词变成了批评家们练习二头肌的拳击袋。一提到“声音的图形”或是“语义学”,马上就遭到无礼的对待:向形式主义者冲啊!有些残酷的批评家把这个口号当作战斗口号,来掩饰他们在诗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无知,来惩罚胆敢扰乱他们的蒙昧主义老巢的人。①[美]罗曼·雅各布森:《序言:诗学科学的探索》,[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页。
沙·基尔沙诺夫的这番激昂陈词显然充满隐喻性,普罗普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数场“反形式主义运动”中被看作是俄国形式美学在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倡导者,并因此被扣上政治性的“形式主义帽子”,频繁受到来源于体制的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指控”。在那个特定年代,不仅在本体性上与“旧形式”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形式”,被规训为寓意教条政治的“形式主义”;普罗普那别具一格的形构-历史研究路线也因此被埋没,不免令人唏嘘。特别是从今天看,这条将“内部”与“外部”相融贯的研究路线是20世纪俄苏文论至今仍待发掘的矿藏,普罗普的功能结构诗学与历史民族志诗学、巴赫金的体裁诗学与历史诗学、洛特曼的文本诗学与非文本诗学等都是结构与历史互补路线的优秀成果。①程正民:《俄罗斯文艺学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3期。
而与此相伴的,便是来自西方学者的进一步误解。
1958年,在罗曼·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和托马斯·西比奥克等结构主义者的积极推介下,《故事形态学》英译本出版,由此拉开了长达20年的结构主义接受浪潮。在这20年中,普罗普与《故事形态学》被深深联系在一起,如同沃纳所言,“在英语国家,如同在整个西方世界,人们是在不算很久以前才听说只是作为《故事形态学》作者的普罗普”。②Э. Э.Уорнер,“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о переводах «Морфологии сказки» В.Я. Проппа на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С.23.至于和它一体两面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虽然1948年即出版意大利译本,却未造成明显反响。所以西方学界自一开始,就是把功能结构诗学与历史民族志诗学割裂开来接受的。
关于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亲缘关系,首先进行诠释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在《结构与形式》(1960)中认定普罗普是形式主义者,其研究是割裂内容的形式研究、走的还是传统二元论“旧形式观”的路子。显然,该立场与俄苏“反形式主义运动”之立场并无二致。此番评价令普罗普十分不满,他撰写了一篇名为《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的长文予以回击,直接驳斥并澄清了所有“形式主义误解”。完成后,普罗普在日记中写道:“这篇文章我很满意,我肯定比那个法国人列维-斯特劳斯更强大,他是如此轻蔑地议论我。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工作,我也无法达到欧美都真正了解我的水平。”③В. Я.Пропп , “Дневник старости. 1962-196...,”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В. Я. Пропп, С.298.
这篇文章后收录于《故事形态学》意大利语译本,但却未能有效扭转西方学界对其“形式主义误解”。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后,西方普遍还是对普罗普展开了基于“形式主义指控”的不同程度的理解:普罗普是“形式主义者”,其研究是“正统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典范”,代表了“形式主义极端趋势之一”④Tzvetan Todorov, “L'héritageMéthodologique du Formalism,”L'Homme, No.1 (1965), p.65.。他们所言及的“形式主义”,往往游走于“俄国形式美学”与“二元论旧形式”之间,或将其视同俄国形式主义阵营,或将其理解为割裂内容的旧形式研究。显然,这些完全无视其历史研究的主观评价与真正的普罗普相距甚远:他那寓“形构”与“历史”于一体的发展观取向,以及与“俄国形式主义阵营”存有的距离,全都被“形式主义指控”所遮蔽,噤声于西方接受狂潮的人声鼎沸中。
所以从总体看,无论是国内,还是西方结构主义,对普罗普及功能结构诗学的接受历程都是“理解”与“误解”并置的双线叙事。功能结构诗学正是在此过程中与历史民族志诗学脱钩,成为一种具有自足性的文本理论;其与“俄国形式主义”真正的亲缘关系也被“形式主义指控”所取代,并完全无缘于两者的经典化过程。最终,“误解”替代“真实”,形成了今天普罗普广为人知的“俄国形式主义”印象。
关于误解形成的原因,笔者以为有四:其一,对普罗普的学术生涯与研究思想缺乏了解;其二,将出版时间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建立起想当然的联系;其三,把《故事形态学》深邃的问题意识简化为寻找形式“可重复性”的“一般规律”;其四,冷战地缘所致。
结 语
以上分别考察了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三重义项的各自互动关系。由这三重互动关系所构建起的复合关系体系,构成了普罗普功能结构诗学发生的“俄国形式主义”思想渊源。普罗普在外部历史诗学与内部形式美学之外,走出了寓两者于一体的第三条路线——形构-历史发展观。在此基础上,他对民间故事展开实证的类同性问题研究:在其研究的第一步——实证“故事类同”的本体性时有意识地借鉴了形式主义方法论,从形式美学的角度建立了“故事类同”的图式与结构,以更好的为历史起源学研究奠基。因此普罗普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亲缘关系,更多的体现在研究方法论的参照与借鉴上。从总体看,其形态研究并不完全属于形式主义研究,与历史民族志诗学一体两面的功能结构诗学也非完全是形式主义理论,普罗普本人更不属于形式主义阵营。结构主义在接受时造成了有别于“形式主义特征”的“形式主义误解”,这些误解具有巨大影响,是日后“功能结构诗学”与“普罗普形象”产生巨大文化偏移的重要动因。
但就像沃纳所说,无论普罗普被曲解的程度有多深,我们一定不能忘却,他的故事形态研究并非出于对文学创作抽象本质的兴趣和对民间文学叙事的分析欲望,而是由发现神奇故事中的“可重复性”现象,并试图揭示其深层(历史起源学)归因所致。①Э. Э.Уорнер,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 и русская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 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