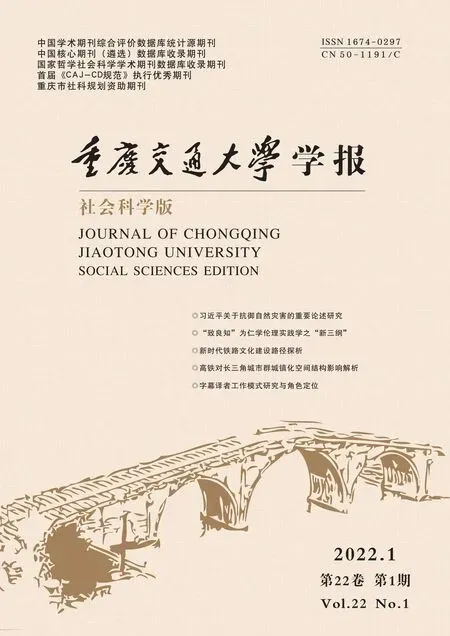高译《狄公案》的文化意象翻译及创造性叛逆
刘 黎, 王以涛
(1.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2.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一、引言
高罗佩(1910—1967)是著名的荷兰外交官、汉学家,他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狄公案》[1]的翻译(以下简称“高译本”[2])和基于中国公案素材自主创作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使其享誉盛名,笔下的“狄公”形象深入人心(1)狄公案中文原本小说作者为佚名。由于作者信息的缺失,无法对小说的原本书名进行考究。目前,该小说多以《狄公案》《狄梁公四大奇案》《武则天四大奇案》等出版和流传。本文所提及的《狄公案》以及参考文献中的《绘图武则天奇案》都指的是同一本小说,即高罗佩翻译所用的狄公案中文原本小说。。狄公案系列小说不仅通过文字译介和再创作的方式传播,“狄公”形象也搬到了大银幕上。如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3]80-81,又如美国拍摄的《庙崇案》[4]36,或译为《朝云观》(HauntedMonastery)。在倡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对优秀外译作品的学习和借鉴必不可少。目前,学界对高译本的研究大多集中讨论高罗佩译介的背景和缘由,讨论高译本中翻译方法和策略的使用[3-7]。也有学者以译介的题材和内容为落脚点进行研究,对比研究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叙事视角的基本差异[8],讨论高译本中的鬼神文化和超自然现象[9-10],以及关于司法和刑事内容的翻译[7]117-122。总体来看,学界对高译本的研究多停留在字词层面的文字转换和翻译技巧的探讨上,鲜有人谈及这一翻译活动背后的文化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象是民族文化的高度浓缩和智慧结晶。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手段,是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冲击,文学作品的译介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译介。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性和不对等性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翻译无法实现完全对等,带有浓厚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更是翻译的难点。本文拟从译介学创造性叛逆的角度,研究高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翻译,以管窥因不同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意象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文化信息的丢失、扭曲和添加,以不同视角丰富对翻译活动的认识。
二、文化意象的创造性叛逆
译文对原文忠实度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翻译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早期的翻译家认为译文应该完全忠实于原文,并试图从翻译实践中提出翻译理论,指导和规范翻译行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的翻译研究仍然是一种以文字转换和翻译技术为主导的模仿论研究模式”[11]。随着学界对翻译认识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任何翻译都没有办法绝对忠实于原文。相较于其他翻译语言类型,文学翻译更是难以实现对原文的忠实。文学作品作为两国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准确的文学翻译对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传递一国文化形象都起到关键作用。但是由于不同文化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不对等性,使得译者在翻译实践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减译、误译和创造性叛逆等现象。
(一)创造性叛逆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创造性叛逆的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12][13]5。这一概念引起了谢天振的强烈共鸣,他将此概念引入比较文学译介学,并作为译介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他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是指译者通过主观努力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魅力,叛逆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意愿而对译作造成的客观背离[14]137。“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译语的客观背离也应属于叛逆的范畴,也就是说译作可以是对原作的叛逆,也可以是对译语的叛逆。”[15]47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往往是无法分开的。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不少学者认同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描述和解释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董明结合描述翻译学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并谈及创造性叛逆对译语文化的积极影响[15]46-49。成滢通过文学翻译中常见的文化意象的翻译,讨论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化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等[16]。也有学者以译介学创造性叛逆作为研究角度切入,分析文学作品英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17]。理论的发展不仅仅需要认同的声音,反对或不支持的声音往往更能引起人们对该理论内涵的思考,不断推动理论向前发展。译介学创造性叛逆同样会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18],通过不断探讨和思想沟通,丰富和完善其理论内涵。
翻译行为往往是跨文化、跨民族的一种实践活动,译者在翻译时不得不面临和处理不同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信息的丢失、扭曲,甚至是添加。无论译者如何靠近和忠实于原文,原文和译文之间都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对等,创造性叛逆客观存在于任何一个翻译活动中。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主要概括为两种,即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14]146。有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个性化翻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等,大都是译者出于某一翻译目的而对原文内容的创造和叛逆;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多表现为误译和漏译,主要原因是译者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14]153。译介学谈论误译和漏译带来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意味着译介学倡导人们为了创造性叛逆而误译和漏译。创造性叛逆只是一个英文术语“creative treason”的移译,属于中性词,是对译文和原文之间必然存在的某种“背离”“偏离”现象的一个客观描述[13]6[19]。同时,也不是一种指导翻译实践的方法。因此,不能用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来评价译作的好坏。
(二)文化意象与创造性叛逆
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翻译,因为文学作品本身所使用的语言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将语言意思准确表达出来,同时还要将原作的艺术意境和审美传达到位,使目标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得到同样的艺术感受。文化意象作为一国文化的高度浓缩和剪影,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象对译者的要求更高。文化意象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他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14]180。文化意象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植物、动物、成语或谚语中某一喻体,甚至还可以是一个数字[14]181。文化意象的形成和每个民族的文化及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一文化意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含义可能一致,也可能大相径庭。如“龙”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截然不同。拥有图腾文化和祖先崇拜的中国将龙视为一种吉祥且尊贵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一种邪恶的怪兽、神的敌人,被视为不祥之兆。又如,数字“4”的发音因与汉语中“死”的发音接近,被认为不吉祥,人们常常会避开使用数字4,而在西方文化中,4则没有这一层含义。
文化意象一般有两层意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好的文化意象的翻译是既可以保留文化意象的外在表层意义,同时又能准确表达意象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但事实上,译者在翻译文化意象的过程中,往往很难兼顾两层含义的表达。有时保留了表层意义,却没有办法表达出意象背后的深层含义;有时表达了意象的深层意义,但丢失了该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形象。这其实就是学界常说的翻译中的形式与意义的问题。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文学作品或文化意象时,往往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解决翻译中面临的问题。不同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同、翻译目的不同、预设的目标读者群体不同等,都会导致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原作产生创造性叛逆。同时,文化间的差异也决定了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文化意象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浓缩,研究文化意象的翻译及其创造性叛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好更充分地理解译语文化内涵和文化形象。
三、高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及创造性叛逆
《狄公案》的翻译作为高罗佩翻译和创作狄仁杰系列小说的第一个环节,该英译本的成果为其后续创作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也帮助他收获了荣誉。《狄公案》作为一本典型的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无论是作品体裁还是内容都带有强烈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高罗佩通过翻译使得该作品在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获得第二次生命,赋予作品全新的面貌。这和埃斯卡皮及谢天振对翻译和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十分吻合。“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5
笔者对比阅读《狄公案》原本和高译本,发现作为传统章回体裁小说的原作中到处可见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这些文化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文化意象、人物意象、时间意象三大类。传统文化意象包括传统的宗教文化、文化习俗和节日、成语和惯用习语;人物意象主要和传统的历史典故与民族历史文化有关,多以人物名称来指代其背后的寓意或典故;时间意象是指古代中国计时法中的十二时辰,古人根据太阳升起的时间,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约等于现在二十四小时计时法中的两个小时。人物意象和时间意象实际上也属于传统文化组成的一部分,但由于小说中人物意象和时间意象出现的频率较多,因此将这两种意象独立分类和讨论。笔者拟从这三大类型的意象选取几例,分析高罗佩对原作文化意象的处理和其中的创造性叛逆。小说共有三十个章回,前十五章回高罗佩尽量靠近原作翻译,后十五章回则仅保留主体大意而进行编译。由于后十五章回中的文化意象无法进行文本平行对比分析,所举例均从前十五章回中选取。
例1原文。狄公道:“你抬起头来,此地可是鬼门关了么?你看一看,可认得本县?”
译文。Judge Dee said: “Look up at me, and see whether you recognize your magistrate.”
例2原文:可知这一开棺,那尸骸骨就百般苦恼,你是他结发的夫妻,无论谋杀怎样,此时也该拜祭一番,以尽生前的情意。
译文:This exhumation, however, is cruel to the remains of your husband. You are his wedded wife, and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or not you killed him, it is your duty now, before the work starts, to offer a prayer to his soul.
例3原文。此时陆长波见他们各道真言,知狄公是地方上的“父母官”,真是意想不到,赶忙过来叩头,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虎威,统求恕罪。”
译文:The manager, who by now had gradually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started on a long apology to the judge, saying that he had not known that such a famous and high official had honored him with a visit and so on.
例1中,原文“鬼门关”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阴曹地府的一个关隘,是阴阳交界的关口。高译本直接将“此地可是鬼门关了么?”删减不译。宗教文化和信仰不同,在目标语文化中没有“鬼门关”的宗教文化意象,由于文化差异,无法再现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例2中,原文“结发的夫妻”是指具有夫妻关系的两人,但是“结发”还有一个表象含义。古代男子束发而冠,女子束发而笄。“结发”是指婚礼上的一个习俗,即三拜堂和喝交杯酒后男左女右共髻束发,故称“结发夫妻”。虽然译文中的“wedded wife”表达了结发夫妻的深层文化含义,但“结发”这一文化表象却丢失了。例3中,“有眼不识泰山”是一个汉语成语,意为虽有眼睛却认不出泰山来,一般用来比喻某人见识狭隘,认不出本领大或地位高的人。高罗佩将这一成语译成“he had not known that such a famous and high official had honored him with a visit and so on”,虽然根据文中语境将这一成语的深层含义表达出来,但却无法兼顾在译文中保留“泰山”的文化意象。
例4原文:在下姓仁,名下杰,山西太原人氏。自幼博采奇书,精通医理。虽非华佗转世,也有扁鹊遗风。
译文:I humbly announce my surname as Jen, and my personal name as Djieh, and I am from Shanxi Province. Since my youth I have been engrossed in the study of rare books on medicine, and fully mastered the secrets of the art of healing. Although I would not dare to rank myself with the celebrated physicians of remote antiquity, I yet dare to say that I know the tradition of later famous doctors.
例4中,原文“华佗”和“扁鹊”都是古代中国著名的医学家,谈到“华佗”和“扁鹊”,人们总能第一时间想到他们高超的医术和渊博的医学知识。原作者想通过对比狄仁杰和这两大医学人物的意象,侧面凸显狄仁杰高超的医学水平。高译本虽然表达了深层意义,但没有保留“华佗”和“扁鹊”两大人物意象,导致意象表象丢失。
例5原文:到了辰牌时分,忽然地甲前来胡德前来报信。
译文:Then, unexpectedly this morning the village warden Pang Deh at nine o’clock, came to see me.
例6原文:说着,令人将他带下,传令明早辰时前往,未时登场。
译文:He ordered her to led away, and fixed the exhumation for the following day. He would leave the tribunal at eight o’clock, and the exhumation would be started at two o’clock.
上述两例中,原文都是指在什么时间段发生了什么事情,“辰牌时分”“辰时”“未时”都是古代中国特有的用来计时和表达时间的意象。不同时辰代表了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辰时指的是早上七点至九点,未时指的是下午一点至三点。高罗佩翻译时,将辰时译为八点和九点,未时译为两点。总体来看,高罗佩翻译的时间都在对应的时间区间内,时间意象的含义得以准确表达,但是中国文化中有关十二时辰的文化意象却未能保留。
例7原文:想着,走到前面,取来一看,谁知并不是书卷,乃是群庙内一本求签的签本。
译文:Thus he picked up the book, and opened it at random. This book, however, was only the collection of answers, used when consulting the divination slips.
例7中,原文“求签”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民间习俗,是占卜的一种方式。人们到庙宇,跪拜在佛像面前掷签来占卜凶吉。每一根签都有各自的编号,翻“签本”找到对应的签号和签文,通过对应签文来判断所掷的签是凶是吉,并就签文的具体内容来解读求签时所问之事。高译本中,高罗佩保留了这两个文化意象,分别译为“collection of answers”和“divination slips”,并添加文内副文本以解释这两个文化意象的深层含义。这一处理方法在保留文化意象表象和表达意象深层含义的同时,向译语国家传播了新的文化意象,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文化信息的添加。
例8原文:只因有个原故,要前来问你。我看这座坟地,地运颇佳,不过十年,子孙必然大发。
译文:My coming here has a definite reason. In my opinion this graveyard is situated very favorably from a geomantic point of view.
例8中,原文“地运”是传统文化风水学中的一个术语。在古代,人们将世界分为阴阳两界,阴阳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影响。无论是房子或墓地选址,选址的好与坏都会影响整个家族的运势。译文中将“地运”改译为“this graveyard is situated very favorably from a geomantic point of view”,将这一文化意象改为陈述句表达,同时又添加文内副文本来解释这一传统文化和意象。高罗佩通过改译和添加文内副文本的方法,表达了文化意象的深层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文化意象的表象。译者发挥创造性,以不同方式靠近原作,表达原作的内涵,但其具体表现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原作。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像高罗佩汉学基础较好的译者,也很难把握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即使表达了文化意象的深层含义,却没有办法保留和传递文化意象的表象特征,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对原文产生创造性叛逆。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一种基于文学的艺术创造,而叛逆是译者在综合考量之后不得已做出的对原作的主观背离。高译本产生这种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语言和文化上的客观差异,以及译者个体化翻译;二是不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不一样,形成的语言表达习惯、宗教文化、审美标准、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大相径庭。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象很有可能在另一个民族中找不到相匹配的表达,即意象概念的缺失。如例1中的“鬼门关”文化意象。“鬼门关”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象,即使强行保留这一文化意象,不熟悉中华文化的读者对这一文化意象背后所蕴涵的意义和意象象征也没有办法实现文化共鸣。又或是因为不同民族表达习惯不同,同一个意思可能需要通过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象表达。如例4中对同一时间段的不同表达形式。由于中西方计时方式不同,虽然想表达的是同一个时间点,却只能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和意象表达。还有一个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在于高罗佩的译者个性化翻译。译介学中创造性叛逆个性化翻译的表现指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的时候有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并且有其独特的追求目标,为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做出的叛逆[14]146。每位译者生活、学习、工作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形成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审美不一样,决定不同译者对翻译作品的思考和翻译实践有差异。高罗佩在译者后记中明确指出,该译本的目标读者群是广大的普通读者而非汉学家[2]227。他曾说,翻译这一公案小说是为了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的公案小说,让他们了解并领略公案小说的魅力,并努力赢得读者对中国公案小说的认同[7]118。高罗佩预设的受众群体和翻译目的决定了他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调整,这样的调整或多或少都会背离或偏离原作,从而产生创造性叛逆。受众群体为广大的普通读者,高罗佩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译作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高罗佩翻译《狄公案》的时间跨度在1943—1946年,译作首版于1949年在东京出版。这一时期,大部分译语读者对中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说极少接触中华文化。因此,翻译文化意象时需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首先要确保文化意象内涵的准确表达,不造成读者的误读或误解。在准确表达意思的前提下,再尝试保留意象表象。原作中出现的文化意象如此之多,假设每一个文化意象的翻译都要兼顾表象和内涵,译作恐怕会变得冗长且影响读者对主要情节的把握,从而影响译作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这也是高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多先顾及意义而非形式,高罗佩有意漏译、减译所产生的创造性叛逆的原因。
创造性叛逆可以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和叛逆,也可以是译者对译语的创造和叛逆。“对原作叛逆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是译作必须使读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必须像原作一样易懂;对译语的叛逆常常是因为译作肩负着用新的内容和形式来丰富译语的使命,而且译语文化也呼唤新的内容和形式诞生,尽管这样的译作读起来比读本族语的作品要难以领会。”[15]47如例7,高罗佩翻译“求签”和“签本”两个中国传统文化意象时,保留其表象意义,又通过添加副文本的方式表达其深层含义。这一翻译处理既准确表达原作的意思,又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将该文化意象译介至译语国家。如例8,高罗佩将“地运”的文化意象通过陈述句解释表达,又通过添加副文本的方式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学,为译文增添可读性和科学性,同时向译语国家和读者输出新的文化知识。创造性叛逆对译语文化带来积极影响的例子不仅存在于高译本中,也客观存在于其他文化或文学作品中。高罗佩以《狄公案》的翻译为基础,模仿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文学模式,自主创作狄公案系列小说,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公案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引介至世界文学。创造性叛逆带来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对我们的词语或日常用语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英语中人称代词“she”的翻译最初给国内译学界带来一大难题,经过时间和实践的选择,“她”成为“she”的对应翻译。汉语开始并无特指性别的人称代词,用“她”翻译“she”的创造性叛逆丰富了汉语词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汉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沙发”“传真”“可乐”等词汇,都是通过对外来语的翻译和对译语的创造性叛逆逐渐形成的。总的来说,创造性叛逆对译语的影响客观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语文化的形成,推动译语文化的发展,丰富译语文化词汇。
四、结语
高罗佩翻译的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狄公案》引起中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成功将这一小说题材译介到西方世界。作为中国传统小说题材,在小说的译介过程中,译者难免会遇到不同文化引起的翻译问题。面临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或者是误解的西方读者,如何准确表达小说的文化内涵成为关键问题之一。本研究从译介学创造性叛逆的角度切入,分析高译本中富含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的翻译情况,发现译者在翻译文化意象时,难免会对原作产生创造性叛逆。出现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即语言与文化的客观差异和译者个体化翻译。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高译本在文化意象翻译中的得与失值得人们关注与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