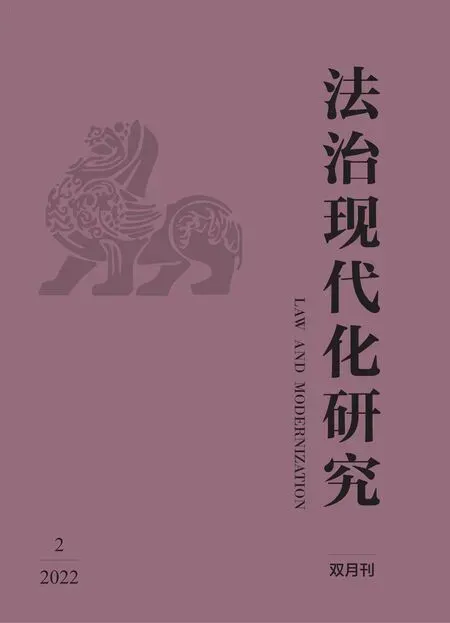宪法审查正当性论证的逻辑
[法]米歇尔·托贝 著 王建学 译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实证主义的宪法学中没有正当性理论的位置。正当性理论应当限于描述吗,或者说,它应当避免作出价值判断或解释吗? 它应当集中于一个能够被描述的目的,即一个完全由实在法律规范所构成的目标吗?
然而,宪法学不具有能够与一般国家理论相分离的科学方法,这一点在诸如皮埃尔·帕克泰(Pierre Pactet)的那本《政治制度与宪法》①参见Pierre Pactet.Institutions Politique,Droit Constitutionnel,Masson/Armand Colin,2001.或任何一本好的入门书中都得到了证明。“国家”,或政府,作为一般国家理论的对象,不是一个经验性事实,而是一套原则和概念,由此学者们能够进行实在规范内容的说明和正当性论证。对国家的描述因此是对原则、概念和正当性的描述。
此类描述无论如何也不能偏离实在法科学的理想标准。像宪法科学一样,具有科学要求的一般国家理论并不试图产生新的原则或正当性,而只是尝试着通过对其持续原则和正当性的分析来描述国家。正当性的分析不仅描述和分类,而且试图揭示某一套正当性论证压倒另一套正当性论证的原因,以及正当性论证与它所论证的那种规范或制度之间的特定关联。下文的分析将检视宪法审查的正当性论证。本文的论点并非论证宪法审查是正当的或是不正当的,而是检视其最常见的正当性论证,目的在于考察它们所根植的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描述它们的形式,评价它们的内部结构,并理解它们所必须采取的内容。
本文只关注宪法审查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的正当性论证,而不去涉及审查的特定技术或模式,例如事后审查是否比事前审查,抽象审查是否比具体审查,以及集中审查是否比分散审查更具正当性。本文也不考虑法院的类型或程序规则,更不用说司法方法论或司法原则的内容。必然会有读者认为事前审查优于或劣于事后审查,同时会有读者认为集中审查优于或劣于分散审查,也必然会有读者认为只有通过一个特别的法院进行宪法审查才是正当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终的问题都会归结为宪法审查本身是否正当。当然也可以认为审查只有在某一个特定模式中才是正当的,但这只是次要正当性,次要正当性必然要以根本正当性为前提。如果制度本身是不正当的,如何构建这一制度就变得无关紧要。而如果一项制度大体上是可接受的,那么本文的论述就跟宪法审查的特定模式是否正当没有关系。本文将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来看待宪法审查制度,易言之,只有制度本身才是本文的关注点。
通常用以论证宪法审查正当性的理由不仅数量繁多,并且各不相同,必须从一开始就把一些理由抛在一边。如果我们所谓的正当性论证只是寻找证据证明一项制度、规则或行为,因为与包含该制度适当性的特定原则或价值相符从而是有效的,那么这些理由就不能被认为具有真正的正当性。
因此,援引宪法规定更不能提供充分的正当性理由。②“法律商谈不能在既存规范的密闭体系内部来自足地完成,而是必须对来自他处的争论开放。”Jürgen Har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230(William Rehgtrans.,MIT Press 1996)(1992).在美国的术语体系中曾经争论,文字上的争论,若是脱离了宪法的规定,必须被放在一旁,以利于那些基于宪法建立的权力结构的非文字争论。参见John H.Garvey&T.Alexander Aleinikoff,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A Reader 219 62(West Group 4th ed.1999).例如,不能仅仅援引设立意大利宪法法庭的意大利宪法的特定条文来论证意大利宪法法庭的正当性,因为人们必须要明确论证的是,制宪权作出的设立该法庭的决定是正当的。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实质性的正当性论证:假设主权就是作出任意决定的权力,那么它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决定而不是那一决定,其正当性在哪里?
进一步讲,解释本身也不能构成正当性论证。可能有人认为一个特定的决定是妥协的结果,但这一决定只有与特定价值相符才能被视为一个好的决定。例如,不管法国1946年宪法第3条(“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是国民主权论者和人民主权论者妥协的结果这一点是多么清晰,这一条款只有在下列两个条件满足之后才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构想:第一,其含义是业已确定的;第二,这一含义与一个更一般的原则相关联。同样地,可能有人接受这样的解释,即宪法法院的创立源于制宪者限制多数权力的意图,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一意图本身是正当的。
我们同样也必须把这一理论置之一旁,即,一项制度只有在它本身或建立它的决定被接受为正当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是因为正当性信仰在本质上是偶然的和不可预知的。任何一个制度或政策都可能在特定国家和特定时间被认为是正当的,但在另一个时空却可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因此,必须论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制度“被认为”是正当的,也就是说,何种价值要求这一制度被采纳和维持。
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检视内部正当性,或者检视宪法审查由现行法所建立或许可这一主张。我们只对那些与超司法或外司法的原则——也就是那些政治的、道德的或司法—政治的原则——相关的外部正当性感兴趣。③关于内部正当性与外部正当性的区别,参见Jerzy Wroblewski.“Legal Decision and its Justification”,14 Logique et Analyse 409(1971);参见Justification,in 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de Théorie et de Sociologie du Droit 332 44(André-Jean Arnaud ed.,LGDJ 2nd ed.1933).如果宪法审查客观存在,那么它在定义上就被实在法所许可——正如审查机构所解释的那样,因此,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这一制度按照特定的道德或政治理论是否是好的。④在外部正当性中,一个特别的事例是宪法在若干机关之间分配立法权时的正当性问题。这既存在于法律同时制定于联邦层面和州层面的联邦制,也存在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均有权制定规则的非联邦制(如法国)。所有这些体制都有一系列的事务领域来界定每一权力的管辖范围。由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存在一种建立特定的机制解决冲突的技术上的必要性,设立一个宪法法院的想法就应运而生了。事实上,这是法国1958年宪法建立宪法委员会的主要原因。当行政部门认为议会制定的法律超越了其权限时,就可以以法律违宪为由而提交宪法委员会。然而,这只是审查的一种非常有限的类型,因为宪法委员会只审核法律的内容是否处于宪法赋予议会的管辖权范围内,并不关心可能发生对宪法其他部分的违反。本文关注的是宪法审查的广泛类型的正当性。
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事实,与作为正当性基础的原则和价值相符的一致性可能或多或少是严谨的。在特定情况下,人们可以主张一项制度是特定价值所必需的,因此,坚持这些价值的人必然也必须接受这一规则或创建这一制度。这种情形可以称为“强的正当性论证”。正是这种正当性论证经常被援引来支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因为男女平等原则来源于平等的一般原则。在其他情况下,人们的主张则限于一项制度或规则并没有违反价值或原则,例如,主张免除女性服兵役义务并不违反平等原则。这种情形可以称为“弱的正当性论证”。弱的正当性论证也可以是这种情形的主张,即特定的制度对于一个并不必需而单只是可欲的目的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手段。然而,不管正当性论证是强还是弱,它都不能实现其确保同意的功能,除非其倡导者和反对者都坚持相关的原则和价值,且都相信制度或决定因为符合这些原则所以是好的。
话说回来,也应当指出,人们在支持立法的宪法审查时只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援用外部正当性。例如主张,宪法法院进行的审查之所以是好的,乃是因为它使宪法法院行使立法权,而法院成员的公正性和技能使他们能够认识社会的真正需求和自然法的原则。也就是说,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法律将比单纯由立法机关产生的法律具有更好的质量。同样地,也可以做这样的主张,法院应当拥有真正的立法权以便与民主选举的多数相抗衡。然而,类似的想法在欧洲却很少提出,因为它们与这些制度的本质假定以及西方法律传统——也就是法院不能援引或适用自然法,不能基于政策作出判决,也没有保障社会组织和改革的责任——不能协调。相反,法院限于将宪法作为实在法加以适用。相应地,法律或宪法的司法适用并非行使一项单独的权力,宪法一直是民主的,人民是主权的,新法的创立被授权给民选机构。⑤因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59年明确拒绝基于自然法原则进行司法审查。参见Ernst Wolfgang Böckenpörde,Le Droit,L'état et la Constitution Démocratique:Essais de Théorie Juridique,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 220(O.Jouanjean trans.,LGDJ 2000).
类似地,也可以做这样的争论,根据政府形式的传统分类,法院是一个贵族气的发明,因为它由精英所构成。因此,如果一个政体允许法院限制民选议院的权力,那么这一政体应当被看作是混合体制。⑥参见Pasquale Pasquino.“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and Democracy,Comparative Perspectives:USA,France,Italy”11(1)Ratio Juris 38(1998).就像这种理论看似有道理一样,它本身与制宪者通过创立宪法法院来实现的民主的宣言是不相协调的。
上述所有正当性论证的理论必须证明法院执行政治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是权力分立以及相继地宪法作为实在法的至上性;另一方面是民主。
一、 通过宪法至上性的正当性论证
这种论证看上去采取了两种形式:宪法的至上性使审查成为必要(强的正当性论证),或者宪法并不总是至上的,但如果想要这种至上性,审查就是实现它的唯一方式(弱的正当性论证)。
(一) 强的正当性论证:宪法审查源于宪法至上
这种论证是简单的,并曾由许多不同的作者以类似的方式表述过。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首席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曾勾画过这一理论,但这一理论实际上比马伯里案判决更早产生。⑦参见Marbury v.Madison,5 U.S.(1 Cranch)137(1803).旧制度时的法院(parlements)在拒绝登记与王国的基本法律相冲突的法案时曾援引这一理论来作为正当性依据。西耶斯(AbbéSieyès)亦曾使用过这种理论,在1795年提出宪法要么是有约束力的,要么是无效的。⑧参见Convention Nationale,18 Thermidor year III(August 5 1795),reprinted in 25 Monteur Universel 442.同样的想法后来由玛尔贝格(Carréde Malberg)提出过,他在审查的可能性与制宪权和宪制权的分立之间建立了关联。⑨参见Raymond Carréde Malberg,La Loi,Expression de la VolontéGénéral 126(Economica 1984)(1931).根据马歇尔大法官的看法,“宪法要么是最高法,不能以普通方式加以改变,要么与普通立法处在同一等级,与其它立法一样可以由立法机关随意修改。如果前者是真的,那么与宪法相冲突的立法就不是法律;而如果后者是真的,那么成文宪法就成了人民限制那些本质上无法限制的权力的荒谬企图”。[10]参见5 U.S.at 177.
第一点对马歇尔来说是决定性的,因为“所有拟定成文宪法的人当然都把宪法视为形成国家的根本法与最高法,相应地每个这样的政府的原则必然是,立法机关的法案与宪法相冲突就是无效的”。[11]参见5 U.S.at 177.既然不仅立法机关而且法官都受宪法的约束,它们二者就都要宣布这类立法法案是无效的。[12]参见5 U.S.at 177 178.
这一理由引起了若干批判,我们只关心其中那些最重要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即宪法的创造者将宪法视为建立根本法是无关紧要的。戒命的创立者可能宣布其戒命为根本,但却没有任何赋予其至上性的意图或能力。例如,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一项普通法律要求未来的立法者按照特定程序行动或在其他法律中规定特定的内容,这一法律明显不会具有强制性,并且会很容易被置之不理,理由是“后法优先”(lex posterior priori derogat)。不会有任何一条规范只因为其创立者认为它是最高的所以就是最高的。除非是一个处在第三方的更高规范规定在甲规范与乙规范冲突时甲规范应优先,否则甲规范就不会比乙规范更高(例如,法国宪法第55条关于条约的规定)。但是因为没有规范比宪法更高,所以宪法永远也不可能具有这种相对于普通法律的至上性。
指出并强调马歇尔理论中的错误是非常关键的。在某一规范至上与否这一问题之外,人们必须要决定这种至上性所指为何。“至上性”这个词,就像“更高性”一样,在涉及规范的时候拥有很多含义。它可以指两个规范之间的下列几种关系:①一个规范决定另一规范的适用条件;②一个规范可以被另一个规范所修改;③一个规范如果与另一个规范相冲突则可以由法官撤销。显然,这三种含义并不同时发生,因为理论上非常可能而且事实上也经常发生的情形是,宪法只有按照特定的程序才能修改,而没有法官有权取消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马歇尔显然是在第三个意义上使用了“至上性”一词,且这里的第三个含义对马歇尔来说是与第一个含义相关联的:如果宪法不能由普通法律所修改,那么一个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在本质上是无效的。但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假定宪法的至上性,马歇尔的论断,即法院必须能够使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无效,也只是在重复大前提,而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同义反复。事实上,马歇尔只是确认了:
第一,只有在违宪的法律能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宪法才是至上的(或有约束力的)。
第二,因此,违宪的法律应予宣告无效。
为了脱离这个同义反复,人们必须表明,一个特定的修正程序的存在必然要求违宪的法律归于无效,也就是宪法在第三个意义上真正是至上的。但这是不可能证明的。我们无法从“宪法只能按照修宪程序加以修改”这一规范中逻辑地推导出“违宪的法律应归于无效”这一规范,因为后者不是前者的一种特定情形。同样不可能证明的是,宪法的创立者意图通过特定修改程序来建立“违宪的法律应归于无效”这一规范,并且这一假设是反事实的。而且,即使它是可能的,那么结论不仅对美国宪法,而且对任何其他宪法,包括那些没有宪法审查的宪法,也应当是真实的。
(二) 弱的正当性论证:宪法审查是实现宪法至上性的唯一手段
与前述第一点明显不同,第二点论述已经被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以不同形式详细阐释过。凯尔森的论述与马歇尔一样是以宪法的至上性为基础的,但与马歇尔不同,凯尔森并不主张这种至上性总是意味着合宪性审查,即使制宪权没有明确欲想或建立这种审查。
凯尔森将自己的主张限于,宪法若缺少了宪法审查就将不是最高的。凯尔森没有假定宪法已经生效,并将宪法解释为已经默示在授权宪法审查,而是把自己定位在宪法的制定时刻:如果不将宪法审查的权力包含在内——而这只有在明确决定时才会发生——那么宪法就不能真正成为最高的。换言之,宪法审查被表述为一个为实现特定目的——宪法的至上性——的手段。[13]参见Hans Kelsen.Preface to Charles Eisenmann,La Justice Constitutionnelle et la Haute Cour Constitutionnelle d'Autriche(Economica 1986)(1928).
尽管这一理由与马歇尔的不同,但它仍然没有逃离被批评的命运。凯尔森的论证并不完全协调一致。除了这一理论以外,他还维持了一个与第一点不相符且与马歇尔类似的观点,也就是,至上性是宪法的本质特征。根据凯尔森的《法的纯粹理论》[14]参见Hans Kelsen.Théorie Pure du Droit(Charles Eisenman trans.,Dalloz 1962).(注:凯尔森的这本书有英译本和法译本,英译本与德文原版存在语言差别,而法文译本由于更接近德文原版因此得到凯尔森本人的认可,本文援引使用法文译本),每一个规范的有效性基础是一个更高级的规范,法规的效力基础是法律,法律的效力基础是宪法。因此,即使缺少宪法审查,宪法也比法律更高。一项法律的有效性源于其与宪法相符,不仅是动态地,即它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而制定,而且是静态地,即它的内容与宪法的内容相符。静态的至上性使凯尔森推导出著名的可选择性规定的理论:如果一项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正处在实施中并且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那么它仍然被认为是有效的,因为一个无效的规范是不能构想的——这就是凯尔森所说的规范冲突——并且如果一项规范是有效的,那么必然是它符合了宪法。在回答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能否仍然符合宪法这一问题时,凯尔森的回答是,宪法无疑规定了立法机关制定或不得制定具有特定内容的法律,但是,如果宪法没有规定审核或批准,那也就意味着立法机关仍然被授权去制定具有不同内容的法律。这里不想花篇幅去讨论这一奇怪的理论,[15]关于这一讨论,参见Michel Troper.“Kelsen et la contrôle de constitutionnalité”,in Le Droit,le Politique:Autour de Max Weber,Hans Kelsen,Carl Schmidt(Carlos-Miguel Herrera ed.,L'Harmattan 1995).只需要指出,这些论述取决于如下一点,即宪法无论是否伴有宪法审查都始终是至上的。
凯尔森的主要思想是,除非伴有审查,否则宪法的至上性无法真实可靠。根据凯尔森的观点,宪法若缺少审查就不具有真正的约束力。这一想法会遇到若干重大难题。
首先,它只涉及宪法与法律之间的静态等级而没有考虑其动态等级。目前,后者是绝对游离在合宪性审查之外的,并且宪法不论是否伴有审查都具有真正的约束力。因此,一项只获得议会少数票的法案,在宪法要求多数票时在动态的观念来看,就不会是一项有效的法案。不管是否有审查,都不能认为它已经被通过了。相反,在宪法审查存在的情况下,当程序性规则被违反时,审查机构仍然可能没有进行审核。因此,在法国,宪法规定“议会议员之投票权,应由个人行使”。(第27条)其含义是议员必须亲自行使投票权,而不得委托。然而,委托却经常发生。但宪法委员会并没有因为法律的制定方式——表决过程没有符合个人投票的要求——而使法律无效。法国宪法委员会却曾宣布在审议进行中被加入法案的那些与法案主要内容无关的规定无效,但也有其他国家的宪法法院并未如此。因此,审查既不是使宪法等级得到遵守的唯一手段,也不能保障这种遵守。
其次,在如下两种思想之间存在一个矛盾,即一个是未生效的宪法不是规范,另一个是凯尔森在《纯粹法原理》中精心设计的有效性理论。根据凯尔森的理论,法律体系展现出一种主要的动态特征,即一个规范一旦按照更高级规范所规定的程序付诸实施,那么它就被认为是有效的。它的有效性被认为是基于这一高级规范。有效性由此不过是从属于某法律体系这一事实。结果是,宪法只要从属于某个法律体系就是有效的,而不管是否伴有宪法审查制度;它之所以从属于制度,是因为它给这一制度的法律提供了有效性基础。
无疑,肯定会有人反对有效性不只是从属于制度的事实,但这种有效性也意味着——尤其是对凯尔森而言——其拘束性。[16]参见Alf Ross.“Validit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Legal Positivism and Natural Law”,4 Revista Juridica de Buenos-Aires(1961);Alf Ross.Introduction a L'empirisme Juridique(Eric Millard&E.Matzner trans.,LGDJ 2002);Michel Troper,“Ross,Kelsen et la notion de validité”,in Michel Troper,La Théorie du Droit,Le Droit,l'État(PUF,2001).这一主张是微妙的。如果它的含义是,一个规范由于与另一个高级规范相关所以是有约束力的,理由是后者在制定一个较低的规范时同时也规定了较低规范必须被遵守,那么它就是准确的。宪法授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也以同样的姿态规定了那些应当作为法律加以适用的规则。一项法律必须被遵守是因为宪法必须被遵守。但这绝不意味着法律或宪法具有绝对的拘束力。绝对的遵守义务只能通过一个道德规范来建立。[17]“法律上的当为(Sollen)建立了一个绝对的道德价值这一主张中……并不存在故弄玄虚(牵涉到把指导他人以特定方式行为的特定人意志宣布为约束性规范)。恰恰相反,当出现在描述法律的法律提议中的当为只是被赋予一个特定的功能连接意义时,它不可能是一个意识形态故弄玄虚的问题。” 前引[14],Kelsen文,第143 144页。相继的结论是,法律因为与宪法相关而被视为具有拘束力,而宪法本身却也从来不具有约束力,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因为没有法律规范比它更高。
在这些条件之下,宪法审查对于宪法的至上性或法律的相对拘束性绝不是必需的。法律只要被鉴别为法律,也就是说,只要它是由宪法授权的机关按照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制定,那么它就是有效的或有拘束力的。任何实施中的法律的有效性因此来源于宪法,即使其内容看上去与宪法相冲突。宪法,即使没有约束力,也是最高的。即使在缺少合宪性审查的条件下,宪法也仍然是法律有效性的基础。
再次,审查的技术必要性的理论与凯尔森的撤销理论是不相容的。对于凯尔森而言,不存在无效的规范,只存在可以撤销的规范。这一理论是非常正确的。有效性不是规范的品质,而是其存在形式本身。因此,如果一项规范存在,它就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不是无效的,且关于一项违背高级规范的规范,人们唯一可以说的就是,这一规范可以由一个法院撤销。然而,这绝不要求审查以便保证宪法的至上性;相反,除非法院使法律无效,不可能确认法律的内容违宪。生效中的法律违宪这一主张,如果不是来自有权法院,那它只是表达了一个简单的主观意见,仅此而已。所有的法律不论其内容都必须被认为是合宪的。只要任何未被撤销的法律被通过宪法认定为必须有效,那么宪法审查似乎对于确保规范的等级性就不再必需了。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凯尔森的理论,正如一般意义上的强的正当性论证一样,假定了审查机构只是简单地适用宪法,即一个客观的规定,而客观中立的法官将自己限于宣布宪法的内容。然而,宪法不是一个规范,而是一组必须解释的陈述,而宪法规范是此类解释的产物。解释是一种意志性功能,一种创造性行为,以至于法院在依宪法规范审查法律时只是在依他自己产生的规范来审查法律。[18]参见Michel Troper,“Le problème de l'interprétation et la théorie de la supralégalitéconstitutionnelle”,in Pour une Théorie Juridique de L'État 315(PUF 1994);Michel Troper,“Une théorie réaliste de l'interprétation”,in The Theory of Law,前引[16],第69页。
相应地,如果说宪法审查是实现宪法至上性的手段,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宪法审查确实是一种“手段”,但它实现的是审查机构生产的宪法规范的至上性。
即使假设这是真实的,正当性论证仍然是不完整的,除非它解释为什么必须要追求的目标——宪法的至上性——是好的。对这一问题只有两个可能的回应。第一个是,宪法设置了某些基本法和必不可少的价值,宪法的至上性就意味着这些价值的至上性。第二个是,宪法代表主权人民的意志,而审查可以保证民主。由此,我们就要进入论证宪法审查正当性的第二项原则。
上述两个回应可以以相互支撑的方式,也可以单独地提出,但它们无论如何不是决定性的。事实上,一方面,如果宪法乃是因为保障着基本价值而弥足珍贵,而这些基本价值如果在本质上就是绝对的,那么它们在缺少宪法的情况下也仍然应当加以保障。因此,这只论证了审查法律的正当性,而不是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价值本身是应加保障的,那么也必须保护它们免受人民意志的侵害,这就是一种必然会遭遇到民主问题的主张了。
二、 民 主
与宪法的至上性不同,民主不能为宪法审查提供强的正当性论证,因为民主原则并不蕴含宪法审查。因此,这里只存在弱的正当性论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提出了与通过宪法至上性进行正当性论证相同的结构,即审查是一种服务于民主的工具;第二种是,宪法审查对于民主并非必要,但对取得与民主相协调的其他目标是必要的。
(一) 宪法审查加强了民主
这一论证较为简单。根据凯尔森提出的最完善的民主理论,民主是自由作为自治的实现,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每个人都只服从于他自己建立或至少是同意的规范。然而,完善的自治是不可能获得的,因为所有的普遍规范都必须以全体一致的方式通过,而那些与普遍规范最接近的制度,即多数决制度本身,也必须被通过。多数决制度通过一个功利性的主张得到正当性:它把绝大多数人放在了自治而不是他律的位置上。一个少数人可以被多数人取代或多数人阻碍少数人成为多数的制度将偏离自治的体制。因此,必须存在特定的程序确保多数的适当决定。宪法审查正是构建这些程序所必需的。
这一正当性论证如果没有遭遇三个重要的难题才是充分的,但事实正相反。首先,它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正当性论证。它通过将这一类型的选举法或政治少数的地位纳入审查,从而论证了对程序规则进行宪法审查的正当性,但仅此而已,因为它并不能论证这一审查在涉及基本价值或基本权利时的正当性。众所周知,凯尔森认为有能力审查法律与权利宣言相符与否的法院将行使绝对权力,因为权利宣言必然以抽象的条款书写,这使法院可以任意解释这些条款。因此,如果以这种方式获得正当性的宪法审查付诸实施,将无法保障少数免于多数派的长期侵害,后者可以轻易地压制少数,例如在尊重程序规则的前提下制定歧视性法律。同时,这一正当性论证必须证明宪法审查并不简单地是保证遵守游戏规则的可能工具,而是证明它是唯一工具并且是有效的。显然,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要观察当今的民主体制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例如,英国的政体并没有宪法审查,但却遵守民主游戏的规则,而与此同时,在设置了宪法审查的国家中,民主游戏的规则却经常不被遵守。最后,宪法审查的既有形式不能通过这一方式正当化,因为多数的既存法院本身大多都依靠实质性规则,尤其是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
凯尔森的民主理论并不依赖人民主权。但其他的理论则将民主定义为主权人民的权力。根据这些理论,假设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人民就委派代表来以人民之名行使权力。宪法规定了这些代表的委派方式、授予给他们的权力以及对这些权力的限制。如果代表逾越了这些限制,他们就不再被看作是以人民之名行使权力了,他们也不再是代表了。宪法审查因此具有确保人民的主权的功能。这一理论以不同的说法出现,有的集中在法律的制定者,有的则集中在法律本身。集中在代表的功能就是主张,宪法审查确保了法律在事实上由有权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因此,法律在事实上来自有效的代表。宪法审查因此是强化了有权机关的代表性。同时,也可以集中在法律本身,即认为由代表在其权限范围外制定的法律不能被认为是以人民之名制定的。这种方法被法国宪法委员会采用过,它宣布法律只有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才是普遍意志的表达。两种情况都假定代表制民主不是一个经验性的政治形式,而是宪法所界定的法律范畴。代表不是依照宪法所委派的人,而是在宪法权限范围内活动的人。没有依照宪法所制定的均不是法律。
但这一点导致了相当的困难。宪法法院决定代表的行为属于超越权限,并不是一种经验评估,而是解释。因此,它是一种意志的行为,而法院在决定某一法律是否表达普遍意志以及决定其制定者是否是代表时所使用的是其自由裁量。因此,法院参与了法律的制定。也因此,有人进一步提出这一命题就丝毫也不奇怪了,即宪法法院参与了普遍意志的表达,并且尽管宪法法官不经选举,但他们仍然充当了代表人的角色。[19]有学者偶尔错误地认为笔者支持这一理论,即宪法委员会实际上应当被看作是人民的代表。参见Patrick Waschman.“Volontédu juge contre volontédu constituent?Sur un débat Américan”,in Le Rôle de la Volontédans les Acts Juridiques:Etudes àla Mémoire du Professure Alfred Rieg 855(Bruylant 2000).事实上,笔者并没有企图为法国的司法审查提供正当性论证,而只是分析法国宪法第1条的表达(“法兰西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所具有的意义,以便把它与审查相协调。笔者通过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人们想把审查正当化,那就必须主张宪法法官参与了法律制定并因此在表达普遍意志,也因此是人民的代表。参见Dominique Rousseau.Droit du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Montchrestien 5th ed.1999);Dominique Rousseau,“La Jurisprudence constitutionnel;quelle nécessitédémocratique”in La LéÉgitimitéde la Jurisprudence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363 376(G.Drgao,B.Francsois,N.Molfessis eds.,Economica 1999).(我的评议和多米尼克·卢梭的回应,at 377 382).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捍卫了同一理论,他写道:“人民的代表首先和最主要是人民选举的代表,但选举代表不是人民之代表的全部。其他‘以人民之名’而言说、行动和决定的也可以被视为代表。法官,不管是司法法官还是宪法法官,就是这种情形。扩而言之,其他无数的管理机构也都具有这种性质。”Pierre Rosanvallon.La Démocratie Inachevée Histoire de la Souverainetédu Peuple en France 407(Gallimard 2000).
因此,很明显这种正当性论证的模式包括了民主定义的简单变化,民主不再是一个自治体制。民主也不再是人民的权力通过民选官员来行使,而只是权力由代表们以人民之名行使,而代表只有部分是民选的。
这种类型的正当性论证很少使用,一种不同类型的正当性论证曾以这样的方式使用过:宪法审查不是一项必然民主的制度,但它与民主相互协调。在法国,这种正当性论证表现为“扳道工理论”的形式。
这一理论由凯尔森和夏尔·艾森曼(Charles Eisenmann)非常敏锐地创立,但它经常被称为“扳道工”是因为路易·法沃赫(Louis Favoreu)所发明并由乔治·沃戴勒(Georges Vedel)所采纳的隐喻。[20]参见Louis Favoreu.“L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ans l'affaire des nationalisations”,98 Revue du Droit Public 419(1982).根据这一理论,法院实际上并没有表达关于法律内容的意见,而只是裁判其所制定的过程。因此,当法院推翻了一项法律,它其实是告诉议会,普通立法程序已经不足以采纳这一规则,而是需要宪法修改程序。宪法法院因此可以比喻为一个铁路扳道工,它只是根据性质或目的把列车从一个轨道导入另一个轨道。
法院在这一理论中远不是一个反民主的机构,而是以民主体制的必备要素而出现。在这一理论之下,宪法只能在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之后才能制定,它最经常地要求一个比普通法律更大的多数。任何给定时期的政治多数在没有少数支持的情况下都不可能集合成这一多数。这样一来,不仅法院以少数保护者的身份出现,而人们可以进一步主张,如果民主被定义为“自治”,那么,按照这种程序制定法律的体制比其他体制都更民主,因为绝大多数比例的公民要同意他们所服从的法律。
然而,这一理论有三个主要的弱点。
首先,它假定绝大多数作出的决定比一般多数作出的决定更民主。因此,理想的民主体制应当总是以全体一致的方式来作出决定。多数原则应当仅是最后手段:取得公民全体一致的同意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必须满足于对那些不太重要的决定采取简单多数的方式,但对于那些较重要的决定,如果达不到全体一致也必须绝大多数。
这种多数原则的观念是大有问题的。凯尔森本人就提出过有力的理论来反对它,他认为全体一致的体制并不是民主。事实上,全体一致是自治的反面,因为它使一个人能够反对其他所有人想要的法律。同样地,一个要求压倒多数的规则也会使少数有能力阻碍多数想要的决定。唯一能够保证最多数成员自治的民主体制,只能是简单多数。
其次,“扳道工理论”的第二个弱点存在于另一个假设中:法院指示的轨迹能够被实际地遵守。特定的宪法修正案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是由于事实的原因。例如,宪法可以要求影响到特定团体或特定公共机构的修正案必须取得该团体或机构的同意。而且,它可以要求在采纳新的宪法规定之前的特定条件。例如,1958年法国宪法非经参议院的同意不得修改,所以任何限制参议院权力的修正案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地,一项法律如果因为侵害基本权利而被宣布无效,那么这项法律就不太可能再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提出。但这些限制同样可以在性质上是合法的,如宪法禁止修正某个特定的核心原则,例如很多国家禁止通过修宪变动共和政体的形式。但同样可能的是,在意大利、德意志和印度,法院宣布自己有权审查那些被认为难以捉摸的特定超宪法原则的合宪性,例如,与宪法法官权力有关的原则。[21]印度最高法院曾两次取消宪法修正案:在1975年使选举生效的修正案(Smt.Indira Nehru Gandhi v.Raj Narain AIR 1975 SC 2299,review denied AIR 1977 SC 69)和1980年一项去除对修宪权的一切限制,从而使宪法基本结构的修改成为可能的宪法修正案(Minerva Mills v.Union of India AIR 1980 SC 1789),参见M.Hidayatullah ed.Constitutional Law of India,Volumes 1,2 AND 3,The Bar Council of India Trust 1984 1989.
最后,“扳道工理论”假设法院将自己限于确定法律的合宪性或违宪性。合宪性或违宪性看上去像是客观的:结果,法院不会具有解释性的自由裁量。但这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是明显错误的,因为法院必须也必然解释宪法的规定,而这种解释的任务涉及意志的行为。
尤其是,这一理论是难以与特定体制(如法国)中流行的代表制观念相互协调的。凯尔森的理论,即制宪权由于只能通过议员绝大多数妥协的方式来行使,因而更具民主性,假定这些议员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投票者。然而,根据法国的观念,议员并不代表投票者,而是代表人民或国家,以至于无论在民选议会中出现怎样的多数,人民都是被平等代表的,他们被表达普遍意志的立法权平等地代表,并被制宪权代表。主权并不存在程度之别。从这一点来看,在普通法律和宪法之间并不存在区别。[22]参见Frank Michelman.“Can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be Legal Positivists?or Why C onstitutionalism”,in Consteliations,Volume 2,293(1996).二者都是主权意志的表达。
这一理论的变种由沃戴勒提出,他同样试图证明宪法审查加强了民主。但沃戴勒的证明不慎地导致了相反的结论:宪法审查限制了民主。
按照沃戴勒的观点,宪法修正可以比为“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23]御临法院,直译为“出现在高等法院中的国王宝座”,是指有国王出席并主持的高等法院会议。高等法院可以通过注册和谏诤来抵制国王的法令,但国王可以出席高等法院会议并强制性地通过法令。——译者注的体制。在旧制度的这一体制中,主权者本人行动起来,以便推翻反对它的法院(parlements)的意志。
“法律在宪法中所遭遇到的阻碍可以由主权人民或其代表来移除,即他们求助于最高表达方式:宪法修改。如果说法官并不统治一切,那是因为,在任何时候,主权者,在以制宪者这种最完全形式出现的条件下,都可以用一种御临法院的形式来推翻法官的判决。”[24]参见Georges Vedel.“Schengen et Maastricht(A propos de la décision no.91 224 DC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u 25 juillet 1991)”,8 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Administratif 173(1992).
因此,宪法委员会无论如何不会是一个反民主的机构,原因是主权人民总是握有最终决定。如果法官反对立法者,他的判决总是可以通过制宪来推翻。
御临法院的隐喻显然比扳道工更高级,因为它可以与法律是最高意志的表达这一理论,即一个以相对假定的方式出现的理论,相互协调。如果法律与宪法相符合,它就表达普遍意志。当宪法法官宣布它与宪法相冲突时,法官的判决乃是基于这一假定,即它并不是真正地表达了这一意志。然而,如果主权表现为宣布其真实意志的人,那么这一假定就是颠倒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权者不是国王,而是通过制宪权以宪法修正来推翻宪法法院判决的人。
这一隐喻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并且它还产生了一个双重的不自觉承认。
一方面,它不自觉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宪法法院行使的不是司法,而是立法功能。尽管凯尔森会承认这一点,但法兰西的准则却相反,它严格确认宪法法官的司法性质并竭力否认法官涉足法律的制定。现在,旧的法院(parlements)拒绝登记敕令的行为不可否认地行使着立法功能。而且,当国王介入以推翻法院不是关于法律而是关于司法问题的反对时,相比于召开御临法院,国王更愿意召开御前会议(royal session)。御前会议的程序使国王看上去不像是立法者而是最高法官。[25]参见François Olivier-Martin.Histoire du Droit Français des Originesàla Révolution 543(Domat Montchrestien 1948);Dennis Richet.La France Moderne: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32 and 157(Flammarion 1973);F.Di Donato Un costituzionalismo di antico regime?Prospettivo socioistitutzionali di storia giuridica comparato,Introduction to Dennis Richet,La France Moderne:L'esprit des Institutions(Roma-Bari-Laterza 1998);Sarah Hanley.The Lit de Justice of the Kings of France:Constitutional Ideology in Legend,Ritual,and Discours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它不自觉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宪法委员会阻碍了主权。相对于扳道工根据这一正当性论证拥有评估性功能——决定某一措施是立法性的还是宪法性的,旧制度的御临法院,尽管收到国王精心考虑的要求,却通过拒绝登记法律来表达其意志。当御临法院反对国王的意志,只有国王的更高级的意志以御临法院的完全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推翻法院的反对。现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宪法委员会竭尽全力否认这一事实:反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等于是反对主权意志。但如果御临法院的正当性可以接受,那么也必须承认反对立法机关在事实上就等于是反对主权,且主权必须以完全的形式,即制宪权出现,以便推翻这一反对。在这里,人们在御临法院的两种解释之间犹豫不决:或者立法机关和制宪权都是主权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二者都以主权之名,那么就很难清楚地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高;或者立法机关和制宪权代表两种不同程度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解释主权怎么可以被看作是绝对的权力,以及怎么可以承认主权有不同的程度。
这种理论远没有证明宪法审查是民主的一种工具,而只是表明,宪法审查作为对民主的限制而存在。
(二) 宪法审查限制了民主
这里的理论是,宪法试图限制立法权,因为立法权总是存在于多数的手里并可能产生压制性。尤其是,多数能够完全地界定其本身以实现其利益,由此侵害少数的利益,尤其是权利。宪法因此陈明多数不得损害的基本权利,并设置宪法审查来加以保障。
这一理论在清晰明确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它既不主张宪法审查是民主的最高形式,也不认为宪法审查与民主相协调,而是坦率地提出,民主必须让位于其他更重要的价值。然而,这一理论只能在不完备的意义上实现其目标。
第一,它没有证明多数原则的弱点。如果人们认为多数在事实上不能尊重少数的权利,那么怎么能得出结论说宪法这一其本身就是由多数制定的文件能够建立在尊重基本价值和权利的基础上,并致力于保护少数? 毫无疑问可以做这样的主张,制宪会议的多数是一个更明智的多数,因为它生活在一个历史性时刻并想要携手共对未来,[26]参见Jon Elster.Imperfect Rationality,Ulysses and the Sirens in Ulysses and the Sirens: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或者它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是否仍处于多数,因此需要在自己成为少数时保护自己的权利。但只要承认这一多数能够具有这样的智慧,为什么还有必要在总体上对多数保持不信任? 如果开始质疑多数原则,那么制宪过程的根本正当性也必然存在疑问。[27]参见W.Sadurski.“Judicial Review,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Democracy:The Problem of Activist Tribunal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3 Studi Politici 93(1999).
第二,这一理论没有证明为什么宪法法院比议会更可能将这些价值纳入考虑的范围。根据传统的理解,立法多数在政策考虑方面具有排他性地位,而法院则考虑权利问题。但是,立法辩论过程也会涉及基本权利和原则。很难认为这只是旨在掩饰其他利益的门面,因为这一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宪法法院。关于多数与少数的辩论不仅是对立利益的表现,也是公共利益的不同观念的表现。[28]参见Jeremy Waldron.The Dignity of Legisl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Victor Ferreres.Justicia Constitutional Y Democracia(Centro de estudios politicos y constitutionals 1997).
第三,宪法法院是否真正在维护宪法的诸多价值,这根本就是无法确定的。即使认为立法多数只考虑政策问题,也不能就此认为这些政策考虑在宪法法官的头脑里是缺失的并且宪法法院将自己限于适用客观原则和捍卫基本价值。即使是那些不接受现实主义理论——每一文本都必须被解释——的人也承认,至少模糊的文本是必须被解释的。宣布基本权利的文本由于其普遍性必然是模糊的,同样因为它们是制宪会议中的妥协的结果,因此它们反映的权力关系与价值一样多。解释的过程本身表达了法官的价值论偏好,这些偏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必然与制宪会议中的多数偏好相吻合。它同样反映宪法法院中的权力关系,因为在宪法法院中仍然存在多数和少数,而多数本身亦是妥协的产物。
除了这些解释以外,一项法律的审查通常还涉及若干必须相互协调的原则,并且这种协调与立法议会中进行的协调并没有区别,也就是说,是政治性的。因此,在实现协调相互冲突的原则这一任务时,根本无法保证法官比立法议会的议员更少激情和偏见。正如维克多·费雷雷(Victor Ferreres)指出的那样,法院在回答宪法提出的解释性问题时所考虑的理由与反理由(reasons and counterreasons),与公民及其代表在介入权利问题时所考虑的理由与反理由,其实是非常接近的。[29]参见前引[28],Ferreres书,第99页。
简而言之,没有什么论据能够支持这种陈述,即宪法审查对于确保少数权利的保护是必要和充分的。在各种民主体制中,总是存在特定的少数,例如亿万富翁、红头发的人、集邮者、诺奖得主等等,他们根本不需要宪法法院的保护以对抗议会多数。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应当加以保护的少数是最脆弱的。但只有在得到宪法承认的范围内,他们的权利才能得到保护,并且制宪权未必会建立一个法院以图保护亿万富翁以对抗多数人民的意志或保障最少数的权利。
宪法审查因限制民主和保护基本价值免受多数侵害乃为必要的想法,只是一个更一般的想法——法律应当取代政治——的变种。在现实中,这一想法完全是虚幻的。法律不过是人民所建构和欲想的一套规范。当这些人是法官时,法律中的构想不会更少,其内容也不会更缺乏政治性。
在多数国家,这一观念遭遇到另一个相当大的困难。绝大多数宪法将政体定性为民主制。如果宪法法院主张适用宪法,他们不能将宪法所建立的民主制削减为一个宪法没有规定的、受尊重基本原则限制的体制。这一困难的唯一出路是,主张保障这些价值的政治体制不是一个受限的民主制,而是相反,是一个完全实现的民主制。易言之,人们被引导去修改民主的定义。
(三) 宪法审查修正了民主
这种正当性论证乃是回应宪法审查反民主的观点,因为在一个民主体制中,公共决定是由人民或其代表的多数作出的,而法院是由非民选的法官组成并有权反对民选官员通过的决定。这一理由可以回应为,通过修改民主的定义从而将基本价值的保障或慎议过程包含为民主的本质要素,或通过主张人民除了通过制宪权并不真正行使其主权。
民主可以被重新定义或削减为“法治国”(l'État de droit),也就是说,受法律——自然法——所限制的国家,或者说,通过法律行使其权力的国家。首先,民主被消化吸收为这种合法构成的国家,且不是被定义为多数的权力,而是一个通过宪法审查保障基本权利的体制。然而,这种观念可能与宪法至上的正当性论证发生冲突,基本权利之所以应当得到保障,是因为其固有价值,而不是因为它们被宪法文本所明确规定。根据这种观念,尽管特定的权利可能没有被宪法所确认,但保护它们的义务并不因此而减少。
这种论证方法提出了相当的困难,因为它不允许合宪性审查采取审查是否与宪法相符的形式。或者宪法法院在这种扩展的定义中保障民主——也就是说,因为所有的权利都被认为是根本的——然而它并不必然确保宪法的至上性;或者它确保宪法至上性而不保障民主,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不确保为民主体制所必需的所有基本权利。这一弱点可以说明为什么这种原理很少被使用。只有在特定的极端情况下,它才是有益的,用以主张以正确程序性模式通过的宪法修正依然与基本民主价值相冲突。
人们因此可能会将合法构成的国家想象为以法律形式行使其权力的国家,也就是每个决定都以符合更高级规则的方式作出。只有其宪法确保基本权利,这一合法构成的国家才会被定义为是民主的,而且因此可以认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对于如此理解的民主是必要的。然而,这一定义是不可能得到支撑的,因为它会要求把开明专制视为民主的,只要其尊重基本宪章中所规定的权利。因此,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不能完全把多数主义原则从其定义中排除出去。但因此,或者民主是一个多数有义务尊重基本价值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到了受宪法审查限制的民主制这一观念);或者,不把多数主义原则与基本权利作为对立物,而是将前者描述为使后者得到保障的手段。在这方面,丽贝卡·布朗(Rebecca Brown)写道:“我们对政府的一种更好的理解是,多数主义的政府以支持权利法案为目的而存在。”[30]参见前引②,Garvey&Aleinikoff书,第246页。那些具有第一个观念的人必须解释这一制度与受限制的民主制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区别,而第二个观念的支持者必须表明,一个体制在其多数人民的权力只是实现一个更高级目标的手段时,可以在什么意义上仍然被称为民主制。特定的学者,包括丽贝卡·布朗本人,是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并认为,美国宪法所试图建立的体制不是民主制而是自由制。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正当性论证都不是有效的,除非宪法审查真正确保基本价值并且没有给宪法法官以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如果这种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存在,那么以这种方式界定的民主将只是一个带着法官、政府面具的高雅名词。
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学者,包括美国和法国的学者,已经在为依赖于人民权力这一旧标准的民主寻求一个新定义。但正是后一个观念必须修正。朝着这一方向已经存在不少努力,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主权并不是通过立法职能排他地行使,而是通过制宪权行使,易言之,存在不同程度的主权。
对于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来说,民主是二元论的。[31]参见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Volumes 1 AND 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d 1998).主要观点概括在Bruce Ackerman.“La démocratie dualiste”,in Michel Troper&Lucien Jaume eds.,1789 et l'Invention de la Constitution,LGDJ 1994.它由一个双轨过程构成:第一个是规范的立法任务,通常由人民的代表承担;第二个是“宪法的陡峭之路”。宪法法院似乎不再阻碍人民的意志,而是确保表达在宪法文本中的人民的最高意志不受政府部门的侵犯。只有在非常时刻,人民才能够收回权力,并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正式地修改宪法,或者通过使新的宪法平衡正当化(正如新政时期所发生的那样)来非正式地修改宪法。民主在事实上之所以是二元论的,是因为人民的意志本身要求通过法院来实现权力的日常行使,并在非常时刻诉之于宪法修正。
这一理论无疑为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论证,但却具有高昂的代价。首先,表达在日常立法中的意志是低于宪法中镌刻的人民意志的,并且它本身不是人民的意志。二元论民主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其中法律可以与人民的意志相符合,但却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因此,在那些法律应当是普遍意志的表达的国家,这种观念对宪法审查完全是一个不充分的正当性论证。而且,为了承认法院确保宪法中镌刻的人民意志得到尊重,人们必须假设法院限于毫无自由裁量权地适用宪法,因为解释只能是一种评估性功能,或者因为人民能纠正对其意志的解释。第三个难题与统治权行使者的地位有关:如果他们被视为代表——用法国的术语,那些表达最高人民意志的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意志可以低于宪法中镌刻的意志,因为后者也是最高人民的意志,并且人民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意志。如果相反,他们被视为民选官员,并不参与代表(受制于法院从而服从人民的宪法意志)的功能,那么相继的结论是,人民不再被视为参与正式的立法。人民没有行使制宪权,意味着这一民主无论如何不是二元论的,并且它明显地与民主的通常含义不同。哈贝马斯(Habermas)把这种政治体制与另一种体制,即摄政者行使权力直到主权能够或愿意收回宝座,相比较。[32]参见前引②,Harbemas书,第278页。这种民主制是这样一种政府体制,人民是权力的核心持有者,但他们只能明确恢复权力却不能行使权力,甚至通过他们的代表也不行。
这一困难只能通过一个更复杂的解释才能避免。在这里,二元主义所影响的并不是民主,而是人民本身。不得不认为,通过代表行使立法权的人民与行使制宪权的人民是不同的。这种观点由马尔塞勒·郭舍(Marcel Gauchet)提出,后继者如多米尼克·卢梭(Dominique Rousseau)。[33]参见Marcel Gauchet.La Révolution des Pouvoirs:La Souveraineté,Le Peuple et la Représentation 1789 1799(Gallimard 1995);前引[19],Rousseau书,第469 70页.这些学者主张,宪法法官确保“至高无上的”或“永恒的”人民——唯一的真正主权者——的意志优于当下人民的意志。郭舍写道,当下的人民,“那些选举与投票的人民,其本身只是永恒人民的权力的暂时代表,而永恒的人民则通过代代传承而持续着自我认同,并且是主权的真正的持有者”。[34]前引[33],Gauchet书,第45页。
这种理解明显与阿克曼的认识不同,因为永恒人民的意志显然永远不可能直接地表达。它甚至不能由宪法法院来代表,宪法法官只限于唤起当下人民的意志。[35]郭舍写道:“宪法法官并没有被赋予代表人民之主权的职能……他只是负责把他们应当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事实表现出来。”前引[33],Gauchet书,第44页。按照同一思路,卢梭写道:“宪法法官通过一面镜子——权利的裁判性宪章——使人民看到自己是最高的,这面镜子把人民的主权反射回人民自己,对于代表,则把他们的从属性反射到主权上。这样,宪法司法就让人们看到了代表制通过从代表到代表经常忘记的内容。”前引[19],Rousseau书,第470页。按这种方式分裂出了关于人民的神秘理论,只有人民中的一部分是最高的,但却不能行使其主权,甚至不能被代表,这种理论除了产生了大量问题以外,还隐藏了一个内部矛盾。主权不是一种可以从人民的性质中被探知的品质。它只是一种宪法分配给人民的权力,而并没有在当下人民与永恒人民之间作出任何区别。因此,不能同时认为宪法法官适用宪法,且宪法法官的权力并不能只因为当下人民并不是真正的主权持有者而得到正当化。无疑可以反对说,如果宪法把主权分配给人民,并决定了这一权力的行使方式,那它必须源自另一存在,而这将是等级存在的无可争辩的标志。人们可能会进一步指出,最高人民的行为只能通过这一事实得到承认,即他们以符合宪法的方式来完成,如宪法委员会在“法律只有在遵守宪法的前提才是普遍意志的表达”这一公式中所表明的那样。然而,宪法的这些规定只是定义,绝不是一个更高存在对人民的授权。而且,这一理由导致了一个无穷的退化,即如果当下人民之所以是最高的,只是因为永恒人民的授权,那么就会出现后者的主权从何而来的难题。
三、 结 语
尽管这些正当性论证都非常精巧,并且别出心裁,但它们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们主张把所有可能的理由都考虑在内,即在规范的等级性、宪法文本、法官的自由裁量或代表制理论与民主等方面,认为宪法审查制度是正当的。
但这种失败是学说的失败,并不是制度本身的失败。如果人们承认学说(它提供正当性论证)与法的理论(它拒绝正当化)之间的区别,那么,后者必须承担分析实在法的任务和阐释学说必须呈现的正当性论证的任务。最后,实在法的分析导致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宪法法院行使重要的自由裁量权,并与民选机构一道参与立法权的行使。一个其立法权由民选的民主机构与非民选的贵族气官员共同行使的政府,其实是一个混合制政府。[36]参见前引⑥,Pasquino文。这一观察立足于它本身,没有必要为选择混合制政府找到正当性论证,正如主张宪法审查是一个民主机制并不必要从民主制本身寻求正当性论证一样。然而,学说避免作出这一观察,因为宪法法院应当适用宪法,而宪法应当宣布其本身为民主的。学说因此必须尝试着协调宪法审查制度与民主原则,并且无法从接踵而至的迷宫中脱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