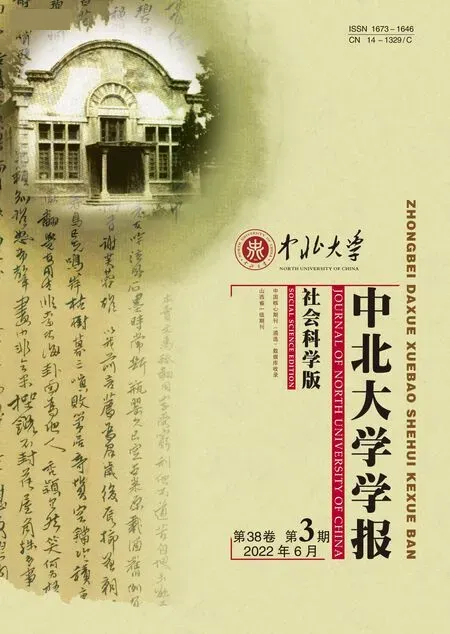帕穆克《红发女人》的柔性流散美学:女性视角、文化融合与政治书写
林国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帕慕克(Orhan Pamuk 1956-)被视为土耳其文学的代言人,长期关注文化融合、身份认同、族群关系等议题,燃起东西方对土耳其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作为一名流散作家,其作品常涉及土耳其的政治时事与文化政策,因而屡屡引起争议,无法获得本国读者的广泛认同。[1]3-9此种争议与土耳其国内社会分裂、宗教观念差异等现实有关,虽有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意味,但帕慕克的性别视角和文化认同也是重要原因,毕竟在地扼亚欧、多种文化并存的土耳其,任何关于特定文化的书写都可能引来厚此薄彼的指责。近年来,敏感且自省的帕慕克常关注女性议题,其风格更为中道和柔和。《雪》(Snow, 2004年)中妇女头巾之殇、《伊斯坦布尔》(Istanbul:MemoriesandCity, 2005年)中母亲的观点、《纯真博物馆》(TheMuseumofInnocence, 2010年)的爱情与女主人公的红颜薄命都令人印象深刻。在父权传统深厚的土耳其,帕慕克的这种转向有其相应的文化意义。
2017年面世的《红发女人》同样是一部充满女性意识的作品,讲述了伊斯坦布尔少年杰姆一家三代与一名神秘的红发女子长达20年的恩怨纠葛。小说虽然围绕父子关系展开,但故事的真正主角却是与祖孙三人都有交集的红发女人,她集叛逆、宽容和坚定的矛盾性格于一身,堪称土耳其当今文化的隐喻,同时也引起关于如何化解土耳其的不同文化、宗教、政治之间对立与冲突的思考。小说通过红发女人的形象和意识的探究,展现柔性文化的多重功能,协调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识,与政治书写相互映衬,是兼具女性情怀、文化融合和政治责任的流散文学作品。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解读红发女人多重身份的文化和政治意涵,探讨父权体制中柔性文化的存在空间,分析柔性流散美学的根源、形成过程以及帕慕克政治书写回归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及意义。
1 父权体系中的柔性书写
《红发女人》没有惊险刺激、跌宕起伏的情节,大量的篇幅花在父亲角色和父子关系的探讨上。小说对父亲的态度是消极的,不管是西方的弑父还是东方故事中的杀子都未能逃脱被奚落的命运。与此相对,帕慕克以较为隐秘的方式刻画了几位女性,或温柔善良,或叛逆果敢,或忍辱负重,她们努力维系父子关系,默默地承受家庭变故带来的后果,成为父权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矛盾日益加剧的父子关系最终都以破裂的遗憾告终,女性情怀反而成为弥合伤痛、化解恩怨的良药,反衬出父权制度的无情。
父子关系是该小说的显性话题,正如小说开宗明义提到,故事与“为人父与为人子的隐秘”有关。[2]3小说围绕着三对父子,杰姆和革命者父亲,杰姆和挖井师傅马哈茂德(准父子),杰姆与儿子恩维尔,展开对土耳其现状和未来的思考。三对父子关系十分紧张,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错位,如同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俄狄浦斯王》与《列王纪》传说中,在命定的必然中绝望地重复弑父或杀子的情节。这些父子关系逃不过破裂的结局,最终没有机会补救,造成了彼此人生的缺憾或损失,导致家庭的悲剧。帕慕克透过父子关系的讨论呈现了一个现实存在的土耳其父权体制。在土耳其的社会中,父权无所不在,正如红发女人观察的:“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很多父亲。国家父亲,真主父亲,帕夏父亲,黑手党父亲……在这里没有父亲无法生存。”[2]99杰姆成长的每一步都无法摆脱无所不在的父亲,这种强势的姿态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父子关系的极强隐喻性联动引出关于土耳其传统、文明、未来等一系列严肃问题的探究。
尽管小说大篇幅描写父子关系,但这是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父子文化仅是母子文化的背景色。在帕慕克的多叙述者风格中,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具有“飘移性和不确定性”,难以简单地确定,只能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人物的功能。[3]109小说对女性人物虽着墨不多,却不可或缺,甚至耐人寻味,如书名那样引人瞩目且值得深思。与吉姆紧密相关的三个女人,红发女人、杰姆的母亲和妻子艾谢都体现出光辉的母性,既是不屈不饶的抗争者,也是温和、宽容的协调者,充当了家庭守护者的角色。与父亲们的冷漠无情相反,三位母亲都温柔体贴,照顾着不幸福和不完美的家庭。在俄狄浦斯王和普斯塔姆的神话中,母亲的角色也具有分量,只不过在演绎的过程中,被有意地掩盖。通过红发女人扮演的俄狄浦斯王母亲的角色即可以窥见这一事实。无论古今,每个弑父故事中都有一个牺牲品母亲,而哭泣的母亲恰恰被忽视了。父亲的严厉也抵不过母亲的眼泪,母性的复杂特质才是帕慕克真正想要凸显的主题。红发女人在暮年的顿悟极其深刻:“宇宙的逻辑建立于母亲的哭泣之上。现在我便因此而哭。哭有好处,因为我察觉到哭泣时能够思考别的东西,我为一切而哭。”[2]293在母亲的眼泪中,饱含了同情、委屈与关爱。《红发女人》中的男性在女性面前,显得缺乏理智和爱心,如同偏执、丑陋和机械的木偶。
红发女人谜一样的特质中也夹杂着浓厚的女性解放意识。红发女人具有母亲与情人的双重身份。她是吉姆父亲的情人,与吉姆本人也有情感纠葛,其魅力足以让无论是毛头小子,还是世故投机者、年迈者看到生命的冲动。她具有性感的外貌,她的出现能震颤周围人的精神和肉体。只要她出现在舞台上,老中青观众都愿意去剧场消遣。红发女人并不被动成为受人欣赏的景观,反而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正如小说中提到的:“红发女人在西方意味着愤怒、好斗、暴躁的女人。”[2]283尽管在土耳其红头发的女人被视为对丈夫不忠,但她并不在意被视为异类,敢于挑战世俗,如同这个鲜明代称一样,她的头发从头红到尾。父权体制崩塌之后,女性也将迎来自由的空间。她对男性的种种行为嗤之以鼻:“还不到三十五岁,我就了解了男人的骄傲、脆弱和他们血液里的个人主义。我知道他们会杀死自己的父亲,也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不论父亲杀死儿子,还是儿子杀死父亲,对于男人来说是成就英雄,而留给我的只有哭泣。”[2]282对男权体制的蔑视和绝望是最无声的反抗。
小说隐含了宽容和解的文化态度。小说从头到尾笼罩在紧张和压抑的气氛之中,多种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然而在红发女人等人的努力下,各种冲突都迎来了最终的和解。杰姆一度怀揣着作家梦,但他没有成功,而是成了地质工程师和承包商。多年以后,与他针锋相对的儿子却最终继承了他的遗志,写起了小说。传统的马哈茂德最蔑视红发女人及剧场,但恰恰是红发女人救了他的性命,最终两人成了好朋友。作为土耳其现代青年,恩维尔反而喜欢马哈茂德的传统文化。红发女人身上的母性和情人特质也最终得到很好的协调,她既有西方女人追求事业、自由奔放、果敢的一面,同时也散发着东方女性重视家庭和子女教育,为孩子随时牺牲自我的精神。吉姆的妻子艾谢始终是一个光辉的贤内助形象,在事业和生活中都洋溢着最佳伴侣的形象。两人在事业开拓中共同出谋划策,在不孕这个痛楚中相互理解和开导。难能可贵的是,她在处理丈夫的私生子及其它善后事宜时表现得异常冷静和超脱,且谅解了红发女人的行为。以上例证足以说明,只要做到足够的宽容与隐忍,任何冲突和恩怨都是有机会化解的。
小说凸显了对自然环境的关怀。小说不缺乏对伊斯坦布尔土地美和自然美的展示:“云散日出,就连我们这片半贫瘠的土地都变得丰富多彩……我们挖井的这块平地,整个世界,远处暗淡的房屋,颤杨,弯曲的铁道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美。”[2]27帕慕克对比了工业化前后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工业化前,尽管城市经济相对落后,却有美好的环境和充沛的自然资源。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加强,古老的土耳其气息瞬间消失,环境的破坏令人痛心疾首。现代土耳其繁忙的都市生活与先前的古老故事场景形成巨大的落差,西化进程中的土耳其,“到处是小得多的厂房,生产中间产品的不知名的公司,以及没有粉的潦草建筑……每次新的旅途中看到城市伸展的手臂插入最偏远的地方,逐渐拓宽的道路上成百上千的汽车像无数耐心的蚂蚁般坚定地前行”[2]151。资源缺乏伴随现代化而来,地下水已经降到地面下七八十米深处,在城镇居民院子里挖井找水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伊斯坦布尔和覆盖在这里的土地失去了它的自然和纯真”[2]152。大地母亲是如此的美丽,但其遭遇与女性人物的命运又是何其的相似。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与女性都是父权体制压迫和剥削的对象,而对二者的关怀是建立新生态伦理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有助于现代环境危机的解决。[4]28-29
“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相互影响,构成社会的一般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在土耳其尤是如此,通过结婚生子、养儿育女等家庭和社会联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5]239小说在批判土耳其男权体制对女性压榨的同时,也呈现了土耳其的柔性文化,包括母性关怀、宽容情怀、族群和解、环境保护等内容,这种柔性书写成为帕慕克小说的独特风格。
2 柔性文化的流散属性
《红发女人》中的柔性文化并非帕慕克的创作想象,而是一直存在于土耳其社会之中,具有深刻的社会人文色彩,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是多种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果,并时刻催发新的化学反应。土耳其这个跨越东西方的国度,自古以来面临多种文明的碰撞和交融,现今仍然以独立的姿态周旋于各个强国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文化中柔性因素与跨文化特质。
小说的柔性文化跨越了时间维度,是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产物。“传统可以包容现代,现代可以改进传统。它们都分别合理地存在着,其形式可以是矛盾的也可以是交融的,但其内核是趋同的,因为人类的大体走向是共通的。而帕慕克及其作品就掩映在这光芒之下,不断地探索着文明冲突和对话的无限可能。”[6]261显然,柔性文化并非无根之木或无源之水,而是深植于土耳其传统文化之中,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下才形成的。作为老一辈的土耳其人,马哈茂德师傅身上除了沉淀先辈们的挖井技艺,也传承着古老的传统文化。更可贵的是,他并不排斥现代科技。最令人惊叹之处在于,他“既能在浇灌水泥、给电视机安装电池、画轱辘草图时如工程师般考虑,又能把传说和神话讲得如同亲身经历”[2]39。另外,作为新生代土耳其人,恩维尔身上也兼容传统与现代的特征。生活在现代化的伊斯坦布尔,西化力量把他培养成世俗的土耳其新青年,与此同时,因为从小和挖井师傅关系密切,受到了潜移默化的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他身上散发出坚毅和传统的土耳其人文色彩。新生代的他比父亲杰姆有着更为强烈的回归传统的欲望,并且坚信现代与传统能够兼容。如果说马哈茂德代表着土耳其厚重自信的过去,恩维尔和红发女人等人代表着土耳其经济振兴前后的承前启后一代,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完美演绎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柔性文化是跨区域沟通的结果。土耳其处在东西方交会之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接受两个世界的文化滋养。帕慕克曾提到:“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国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之间的悬置状态,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风貌。”[7]88土耳其一直以来积极实行西化的系列改革,试图让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认可其作为成员之一。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作出牺牲,所以土耳其的西化常遭受国人诟病。小说流露出对土耳其长期以来夹在东西方之间举棋不定的不安和焦虑。古老的挖井故事记录了东方手工技艺承载的文化智慧,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种文化正在消失殆尽,与土耳其在西化问题上面临的难题如出一辙。促进东西方的融通是帕慕克的一贯主张,《红发女人》犹如一幅画卷,既有东方传统韵味,又有西方文明的影子。2008年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中,帕慕克提到:“我是西方和东方幸福的共同体……我并不完全属于这两个世界。我的土耳其性多多少少就意味着我既不是纯粹欧洲的,也不纯粹是传统的,而是两者的结合。”[8]125小说对东西方文明的对立问题,始终采用兼容并蓄的态度,并精心探讨并存的方式。据学者哈全安观察,帕慕克关心的是“复杂性、混杂性和事物的丰富性”,他写作的目的就是消除东西方之间的隔阂,促进二者的沟通。[9]352
柔性文化沿袭多元文化的传统。古希腊罗马、波斯、拜占庭、伊斯兰等文化的融合成就了土耳其文明,多元文化并存是其特质和策略。帕慕克的创作基于土耳其的流散文化,“揭示一种文明追随另一种文明,但一个文明总也无法取代另一个文明,无论是伊斯兰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没有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虽然相近混杂在一起,但他们也各有其特色,两个人相近就像是两种文明混杂,帕慕克没有给出某一种文明比另外一种文明更加优越的答案,以后也不会给出这样的答案”[6]260。对帕慕克而言,土耳其文化既不会是欧洲文化的仿效版,也不是亚洲文化的衍生版,应该是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小说中,恩格然的流动剧场就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流动剧院里上演着观众喜欢的古老神话故事,期间也穿插着叫卖物品的广告台词,无论是卫兵还是普通群众在这里都可以畅然喝酒、玩乐。在红发女人的剧场中能够看到法国的《大鼻子情圣》、英国的《哈姆雷特》、伊斯兰的《先知易卜拉欣》、希腊的《俄狄浦斯》、波斯的《列王记》,可见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非同一般。此外,马拉茂德用朴素的《古兰经》故事传递着人生的教诲,告诫晚辈一定要践行这些准则,否则就可能遭受不可逆的损失。瑞典文学院的专家洛多恩曾指出:“通过帕慕克作品中平缓的故事情节与高超的讲述技巧,人们能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文化。这对于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相互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10]201-202对帕穆克而言,土耳其的文化不可能单一化,无需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样板,而是万花筒似的杂糅和开放。
柔性文化具有世界主义的意识。帕慕克的创作和生活轨迹基本盘旋在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他曾说:“我的小说是对伊斯坦布尔社会生活的记录,但其中有许多反讽、创新和想象。”[11]与大多数旅居异国他乡的作家不同,帕慕克身上散发的乡愁不仅仅是社会个体的,也是关于土耳其整体,属于这个国家特有的忧愁。[12]137他不仅需要呈现给全世界的读者他的故乡,而且还要把自己的思考和困惑巧妙地编织在其中。因此,他的作品也不能仅停留在民族意识,而是在内容和精神上汲取土耳其资源,但在文学形式和风格上借鉴西方现代或后现代作品。从民族出发,尽力去拥抱世界,形成了帕慕克流散美学的路径。身处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和迁徙已成常态,即使是居住在同一地方,也无法避免异质的渗入,因此文化流散与身份重构已成为常态。[13]12小说中的环境意识、传统继承及女性解放等议题,绝不仅存在于土耳其的国别文化中,而是具有世界性,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文化之中。正是这种开放的世界意识成就了帕慕克的柔性流散美学。
帕慕克是一位吃着“百家饭,穿着百衲衣,博采众长,成为文学‘行者’,他的创作失去了纯粹,而获得了混杂性和混合性”[14]56。在《红发女人》中,帕慕克以高超的技巧将不同时空的意识糅合起来,表现出明显的世界性和跨文化特征。杂糅是土耳其的特性,也是帕慕克作品的特质,多种文化的冲突融合才能够激发优秀作家和作品的诞生。
3 安身立命的政治书写
《红发女人》触及土耳其历史和现状面临的难题——西化、宗教、文化冲突,这些问题与政治紧密相关。虽然小说中包含了众多政治讨论,如派别分歧、专制批判、政教关系、社会主义等,但帕慕克柔性流散反对直接介入政治,避免明显的政治倾向和诉求,小说反而流露出对民生的关注,倡导回归安身立命的生活理想。
帕慕克没有忽视现实问题,其柔性流散书写不缺乏政治责任感。他曾说过:“我关心政治,或者在土耳其发表政治观点是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普通公民。但我关心政治更因为我是一名小说家。”[15]基于对土耳其的热爱,作家由衷地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改变国家的现状,让更多的人了解土耳其。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分析《雪》时感叹道:“帕慕克是兼有勇敢和被经验锤炼而成的慎重的政治小说写作者,他有必要明示缩写的是已经过去的情况。”[16]138在土耳其存在已久的政治体制,与父权体系、家庭伦理及社会文化紧密结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与普通个体都息息相关,令人窒息。《红发女人》充满了对政治现状的思考。父亲就是国家政权的隐喻。父亲无所不在,父亲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无论是弑父还是杀子,都指向残忍的政治游戏,无法摆脱政治的阴影。尽管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之下,政治体制无法再保持其强大的影响力,然而个体也无法完全游离在政治之外。一方面,强大而果敢的父亲会使你有安全感和荣耀感,另一方面,作为个体却因为自由受限,没有独立成长的机会,没有自由发挥个人理性的空间。
小说中的柔性流散超越传统的政治书写。流散文学与跨界的流动分不开,蕴含了对文化中心主义、本位主义思想的反抗与对抗。“流散现象突出地昭示了异质文化之间以不同文化态势(强势或弱势)进行的文化接触以及在这种文化接触中所呈现的各种文化规则”,不仅是人口迁徙和物质流动,同时引起政治版图,文化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变动。[17]106《红发女人》的政治书写不持特定立场,与政治活动保持距离。小说展示了各种政治潮流的众生相,杰姆的父亲作为革命激进分子,他的半辈子岁月都投入到与政府为敌的革命事业中,最终在强大的西化改革中丧失了斗志,不得不接受现实。从他推荐儿子杰姆的书籍中不难看出,他认可的是东方的制度,可惜在土耳其已不可能,故而不得不被迫接受西化现实。红发女人曾是激进政治派别的成员,借剧场表演在各地开展政治宣传活动,最后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左派政治人物同样无法免俗,也存在派系内部的斗争,崇高的革命理想也可以与个人的利益并行不悖。帕慕克描绘了各个政治派别,土耳其的西化现象、世俗倾向、女性意识、伊斯兰文化、现代化都在小说中得到展示的空间,但他不替任何派别发声,不持明显的政治立场。
帕慕克反对文学卷入政治斗争,呼吁文学远离政治宣传。帕慕克理性地区分作家的政治意识与文学作品的政治性,反对“将文学的政治性概念泛化”,否认文学即政治、一切即政治的论断。[18]22在《红发女人》中,大量的讨论涉及欧盟、西化、暗杀、抓捕等议题,引人关注,但整体上,小说还是反对狂热政治,抵制政治宣传文学。尽管具有政治责任感,呼吁关注政治,但却反对过度介入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帕慕克的柔性流散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书写。红发女人对激进的政治派别没有好感:“我小心翼翼地裁下来挂在墙上,但我丈夫对照片并不感兴趣。我的丈夫,一副左翼和国际主义者的姿态,实则极端固守成规。”[2]283帕慕克认为政治充满了虚假和欺骗,无异于“你先吊死诗人,再于绞刑架下哭泣”[2]184,而在文学中,才能安然地找到生活的实质。在小说结尾时,红发女人乐于看到恩维尔在“远离政治的监狱图书馆里有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埃德加·爱伦·坡的故事、古诗书和名为《你的梦,你的人生》的一本选集”,她显得特别地安然。[2]301由于政治的羁绊,吉姆和红发女人错过了属于自己的写作生活,然而这一梦想最终在恩维尔身上得到传承和实现。[19]52
帕慕克的政治书写包含文学回归日常生活的期待。文学不是政治宣传,而是对于美好事物的挖掘和肯定。东方女性的柔性美、相夫教子、自我牺牲等性格,在小说中也得到了肯定。小说凸显女性回归日常生活的渴望,以此来摆脱政治和历史的负担。小说不否定对俗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吉姆的父亲看来,“最大的幸福,是年轻时和一个姑娘为了理想一起兴致勃勃地读书,然后娶她为妻”[2]41。红发女人时刻无法忘记,与吉姆父亲一起激昂地读书的浪漫与幸福。[2]272小说的日常生活美学不仅指世俗化,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生活理想。红发女人将人生融入戏剧中,她坦言:“想演戏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戏剧。”[2]274这种自我实现与杰姆的经历也有关系,作为当代土耳其成功人士的代表,他力图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耳其人,可是他发现全球化背景之下,土耳其传统文化越来越缺失,他能抓住的就是事业和金钱。他一直力图和那个古老的充满传奇故事的土耳其建立联系,可是他最终未能找到自己的精神乐园。
对于帕慕克而言,“小说在本质上是关乎政治的”[15]。作为一个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有责任感的作家,他深刻地感受到政治动荡对土耳其人生活的影响。在他看来,具有文化属性的文学应避免充当政治的工具,而是与其保持距离,才能够以更广阔和中性的视角来捕捉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核。
4 结 语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之下,文化不仅是包含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创造,更是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角度,从文化入手能更清晰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属性。基于多元文化交汇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的创作充分汲取东西方文化的养料,协调各种矛盾冲突的文化意识,成为文学书写介入社会现实的典范。《红发女人》语言精练,内容庞杂,寓意深远,呈现了隐藏在土耳其父权体制之下的柔性文化,饱含女性解放、文化和解和自然关怀等意识。帕慕克的流散美学不仅关注社会政治、文化融合、文明演进等主流议题,而且强调了静谧、持续、包容、综合的柔性风格,根植于土耳其的多元文化传统中,与其独特文化地理特征以及历史现实紧密相联,代表了作家对厚重的民族文化及其未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