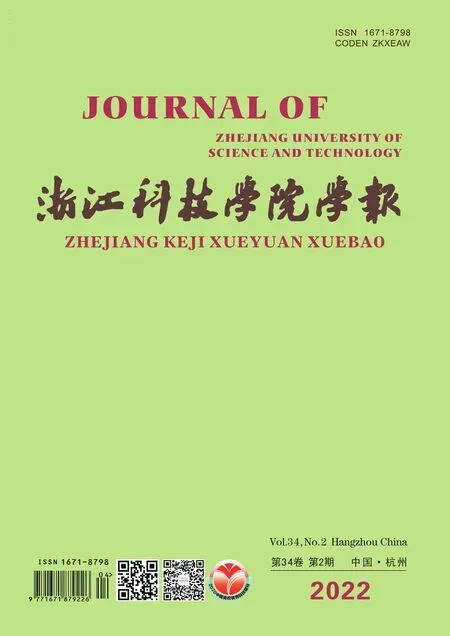真情与个性的绽放:《海明威西班牙内战通讯》中的文学书写
何小聪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海明威是美国“迷惘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海明威之所以迷惘,是他以前形成的价值观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现实粉碎,失去了信念寄托,产生了认同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反战、厌战和失落彷徨等“认知失调”上。然而他并没有失去信心,最终重新选择了思考角度,走向新的“自我建构”[1]。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问世,这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长篇小说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海明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有较强的思想性,在相当程度上克服和摆脱了迷惘、厌战等情绪,表现出有为正义事业奋斗的精神;反映出海明威在这一时期思想上产生了重大变化并明显与“迷惘一代”拉开了距离,并实现自己的“精神救赎”[2]。作为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与“田野调查”,海明威此前所做的西班牙内战报道,无疑成为他最初走出“迷惘一代”的洗礼。当然,至于海明威的一生最终有没有完全摆脱“迷惘”的困扰,或正如其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哈里的叔叔留下的谜一样,也许有一个永远发现不了的谜底。
1 记者海明威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因种种社会矛盾而爆发。1937年2月底,海明威作为北美报业联盟(the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NANA)的特派记者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事,曾先后四次深入战地采访报道。这些宝贵的实地战场接触给了海明威对西班牙内战最直接的观察和体验,而这些最直接的观察和体验的文字记录,最早、最真实也是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在西班牙的最初报道成果——西班牙内战通讯里。海明威的西班牙内战报道以写战地通讯为主,他与NANA签署的工作合同里强调了他的报道任务是记录“从被炸的城镇到被炸的战壕,反映战争中人的一面,而不是去描述参谋部门正在地图上玩的兵棋推演。”[3]这是NANA迫于美联社等新闻机构在消息采集上的优势,转攻新闻通讯而以求自身特色。因肩负报道任务,海明威报道西班牙内战,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在写西班牙内战通讯。所以,西班牙内战通讯是研究海明威当时思想状况和他怎样报道西班牙内战的重要途径。自1937年3月中旬海明威到达西班牙至1938年11月最后离开,他的战地通讯涵盖了其亲身经历的战事,如马德里战役、特鲁尔战役等,正式发表了数十篇作品,供当时超过60家北美和欧洲的媒体采用[4],后于1988年结集出版名为《海明威西班牙内战通讯》(Hemingway’sSpanishCivilWarDispatches)(以下简称西班牙内战通讯)。时隔六十余载,在由全美知名专家和纽约大学新闻系推选的《美国20世纪100部新闻作品》排名中,他的西班牙内战通讯名列第33位[5],在美国新闻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海明威对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持同情态度。海明威对反法西斯阵营的同情和支持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而是长期在“迷惘”中探索思考的结果,成为他写西班牙内战通讯的思想与情感基础。早在1935年,他在给《绅士》杂志(Esquire)写的“关于下一场战争的笔记”中就认为:“现在,战争是由个人、煽动者和独裁者发动或策划的,他们利用人民的爱国心误导他们,使他们相信战争这个伟大的谬论……”[6]阐述他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思考。1936年,他提到:“那时支持西班牙共和阵营的至少有五派……我没有派别,但却对共和阵营有深厚的兴趣和热爱……我从很早以前到它宣布成立的那天,我就一直站在共和阵营一边。”[7]
同情是指对他人的际遇产生情感反应或共鸣。狭义的同情多指个人的情感体验,广义的同情则是一种普世关怀的情感反应。海明威对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成员和他们正义事业的同情,二者兼而有之。正如认知模式的理论基础创始人贝克(Beck)[8]所言,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内心的体验和反应。情感是一种体验,表达是一种反应。情感表达其实是某种以思想为驱动的态度传递。而以思想认识为基础的同情会随不同场合或机遇的激发,衍生演化乃至迸发出多样化的情感表现,诸如友情、温情、热情或激情。当西班牙内战来临,海明威笃信民主,反对法西斯,选择支持人民阵线。他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抨击法西斯[6],并呼吁美国、法国出兵参战。为支援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军队,海明威在美国筹款四万多美元,购买救护车和医疗器械,亲自押运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西班牙内战通讯是战地报道,海明威将作品内容的真实性牢牢地放在第一位,正如他所言:“我的西班牙材料始终如一地精准。”[9]弗农(Vernon)[10]等人也在其相关研究中对此加以肯定。记者的职责是真实写作,西班牙战事是真实的存在,而海明威对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同情也是真实的存在;前者要求真实地加以报道,后者则是海明威真实报道时的需要;海明威运用小说家的文学技巧完成了写作:融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对所报道的事物带有自己的感受和倾向,诚如他自己所言:“在做诚实的精确报道时,不出卖自己”[11],他还认为在没有逃避确凿事实的同时,“如果仅是做报道,他们(读者)不会记住什么”[12]。为此,海明威写西班牙内战通讯时,在坚持真实性的前提下,走出自己的写作路子,给受众和自己的作品以一种全新的感受和生命,在文章中呈现出一个具有真实情感和多彩写作风格的作者海明威。
2 情感释放:显性与隐性
在写西班牙内战通讯时,海明威不仅仅介绍战地的战事和生活,有着强烈个性的海明威忍不住要把自己的情感带入自己的文章当中,可谓情感的真实释放。这种真实情感释放是海明威西班牙内战通讯的一大特点,而这一切皆来源于他明确的思想认识。通讯行文中的情感释放应解释为英文“Sentiments”的表达,即基于思想或情感的观点、态度、情绪等的传递,或是以言辞传达的见解及感想。海明威将战争中撼人的片段写下来,对正义一方充满了富有情感的叙述,表现了他的信念与立场。笔者将其通讯中的情感表露分为显性释放和隐性释放两种方式。显性释放指将思维所得与情感体验用语言明白地表示出来;隐性释放指述说以隐秘的方式婉转地表达出思想情感。
2.1 显性释放
小说创作中,海明威主张将自己的思想情感隐藏起来,按照“冰山原则”[13]将八分之七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揣摩。但在写通讯时,海明威多数情况下并不刻意回避情感的释放。有时,在写作中他的情感表述直接而纯叙事,主要体现在描写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时所表现出的支持与同情(本文例句均由笔者据原文译成):
例1当地的西班牙部队,主要由去年11月入伍的从未受军训的青年男子组成。他们不仅同其他训练有素的军队一起,顽强抗敌,而且发动了攻击,其计划的复杂和组织的完善,只有一战中最优秀的军事行动可与之媲美[4]22。
例2他让你明白了为什么当弗朗哥有机会时,仍然占领不了马德里。希珀利多和像他一样的人会逐街逐道、逐屋逐室地战斗——只要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还活着;而最后剩下的一人则会焚毁这城。他们非常顽强[4]46。
例3抛开所有的乐观情绪以外,这趟行程对从加泰罗尼亚前线飞来的记者而言,是一个启示。马德里没有改变,比任何时候更加坚固。每天不分昼夜,战壕与坑道都正在延伸,从侧翼包抄敌人,最终将解除对城市的围困[4]92。
从例1可以看出,这些话显然是作者对反法西斯战士们的赞美之词,稍有夸张,而夸赞就是情感和态度的显性释放,反映了作者的立场观点和心之所向。例2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推断(或见解)和赞叹,而这些有倾向性的推断是基于他坚信那些战士的无比坚强和勇敢,并对他们十分敬佩。例3是作者的那篇报道的结语,表达了作者因受到感动而获得启发,或更像是他的一个期许,明确释放作者在思想情感(或态度)上对马德里保卫者的坚定支持。
以上句子抒发了海明威对反法西斯战士们英勇气概的赞叹之意。在刻画西班牙民主力量军队及支援他们的国际志愿者的形象时,海明威更不掩饰对他们的由衷支持与钦佩之情:
例4自去年春天我见到他们,他们已成长为真正的战士,神情已然稚气全褪。那些不愿意待下去的人已同重伤员一道离去,当然,阵亡的,不在其中。剩下的都是硬汉,脸,事实上已变得黝黑,而且过了7个月,他们熟练了战斗技能[4]48。
在报道中也可以看到他个人的“硬汉”形象和亲自参与战斗的豪情展露:
例5睡在我旁边的那个战士的步枪出了问题,那枪每开一次火,就阻塞一回,于是我就教他怎样用块石头把枪栓砸开[4]65。
透过弥漫的战火硝烟,海明威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他采访时遇到的人物,让读者感觉到在那场武装冲突中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比如,海明威这样报道:
例6我们在马德里雇了多位司机。第一个名叫托马斯,身高四英尺十一英寸,看起来特别缺乏吸引力,却非常成熟;他是一个来自韦拉兹克斯的矮个儿男子,穿着个蓝色工作服,他缺了几颗门牙,然而有着满腔的爱国情感……托马斯透过漏风的牙齿,高喊:“万岁,马德里!我灵魂的中心!”“也是我心中的都城!”我也说道[4]43。
有研究者曾怀疑海明威对西班牙人民感情的真实性[14],而上述例子显示出海明威风趣幽默的笔调,简洁的字句里藏着反讽和喜剧色彩。这些轻松活泼的描述,反映出作者内心充满了与西班牙群众亲近的情感,并洋溢在字里行间。
2.2 隐性释放
有时,海明威会以一种近乎是旁观者似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情感。展示些许“冰山理论”的意境。例如,海明威写特鲁尔战役时的一个惨烈场景:
例7一位西班牙战士,他的嘴唇因为寒冷而发紫,披风裹着他的下巴,正在往火里添一些绿色的木头,唱着一首歌。“我有一笔来自父亲的遗产,那就是月亮和太阳,我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而它们的花费就从来没有过”。“你父亲现在在哪里?”我问道,“死了”。他答道,“但是看看那儿,他们现在要为法西斯分子开辟新坟场”[4]62。
例7中作者细致地描写了战士在严寒条件下的面部表情和御寒动作,用低沉的形象衬托出他们坚毅的神情。作者选择这些歌词就是想从侧面展示出战士虽然有些伤感却仍有着立于天地之间的博大的胸襟和气概,树立了战士的伟岸形象,隐性释放他对反法西斯斗争事业的崇敬之情,同时为提到父亲做好铺垫。虽然父亲(可能)已经因战争亡故,但是战士并未沉浸于伤悲,而是用继续战斗的意志和歌声纪念父亲,表现了人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与法西斯做艰苦斗争的英勇风貌。战士的这种精神面貌透过作者的描写得以呈现,不但隐性释放了作者对反法西斯战士的关切之情,同时借用战士的豪迈悲歌和激情话语,隐性释放作者自己坚决反法西斯的心声。
作者巧妙地利用对话,免去繁杂的交代,用含蓄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情感,用简单的对话结构[15]寄托深刻的内涵,让对话去“展示”情感,而不是自己“直述”;发言权交给了报道对象,让他占据舞台中央,作者退居一旁,好像故事中的配角,造成某种“模仿”的错觉,却真实地传达出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无畏牺牲精神与坚韧开阔的襟怀;同时,作者的留白也腾出了空间让自己深深的同情和那位西班牙战士的哀伤与刚毅一道回荡出悲壮的共鸣。
通讯中有些段落看似只是单纯地记录行程,但实际上是作者寓情于景,就好像一段优美的插曲,在战火的背景下提示着生活的美好,以下是一经典片段:
例8穿过数英里开着花朵的橘子林,队伍在黑暗中来到巴伦西亚。橘子花开的芬芳,又浓又烈,甚至盖过了路上的尘土味,这倒让这位睡意蒙胧的记者好像闻到了婚礼上的味道。尽管是半醒半睡,但是望见透过尘土射出去的光线,你知道这不是一场人们正在庆祝的意大利式婚礼[4]18。
这里,作者仿佛在同读者或听众交流他个人的感受,其实是这位硬汉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温情的流露,流露出他内心对和平的渴望。这也是战场抒情的一段,此时静谧而几近梦幻的氛围与打仗时的烽火连天和血腥纷乱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如同用油画般的色调从侧面勾勒出身上满是战火硝烟气息而又十分疲惫的人们在朦胧中似乎又与往日熟悉的甜美生活重逢的场景,但仍然不得不面对战争的残酷现实:这里没有浪漫的异国情调婚礼。这种印象主义式的描述,给作品增添了文学气息,并“帮助作者传达微妙的思想”[16]。
通讯中情感显性释放的量大大多于隐性释放,显示了作者的率直个性和“粗中有细”的写作技巧,其中所蕴含的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情、与他们的友情、参与战斗的豪情,以及眷恋和平生活的温情等,其实都折射出海明威对正义与和平的笃信,只有这种真挚而强烈的信念才能激励一个硬汉为捍卫正义与和平奋起挥笔和战斗。从文学的美学价值来看,抒情语言中的感情典型性程度越高,其美学价值越大,即海明威的情感表露具备文学的美学价值,这种文学的美学价值在受众阅读或聆听过程中会升华为一种蕴涵正义和真情元素的审美感受。
西班牙内战通讯突破了西方传统报道模式。为此,有西方评论家批评道:“战地记者的职责是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双方情况,海明威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强烈地站在共和派一方反对民族主义者(叛军)。”[17]海明威之所以不进行一般的“中立”报道,因为他此时的思想认识已经发生变化[18]。此时的他不再盲目反战和悲观失落,而是明确支持正义的战争,对战争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成为一位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记者。他当时经常出生入死,参与战斗行动和进行火线报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不但反映出新的思想认识给他整个人带来的变化:不再低迷、彷徨与迷惘,而且把他对正义事业支持的情感通过他的通讯报道真实表达出来,通讯中对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和抱有必胜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也一扫往日“迷惘”的雾霾。西班牙内战通讯中真实情感的释放显示了在报道战事之际,海明威在思想认识乃至情感能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3 战事叙述:多彩风格彰显写作个性
海明威在报道西班牙内战时展现出强烈的个性。个性,是指个人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或言语方式不同于他人的特质。从行为方面看,他在采访报道中,参与了几乎所有与战斗相关的活动,比如他驾驶救护车,抢护伤员,制作燃烧瓶,甚至直接加入作战行动,为此还曾负过伤,是公认的“出格”记者[19]。他勇敢的行为方式也反映在了他的通讯中,因为他常常具体地将他在前线的行动细节都报道出来,树立起他“硬汉”记者的形象。作为战地记者,海明威的个性特征最终体现在他的通讯作品当中,见诸于他的文字表达上,体现为其风采独具的写作个性:直面现实,敢于将残酷的事实如实写出来;不但释放情感与立场、穿插个人感受,而且在真实观察和记录的同时,借用多种文学技巧来表述适合的事实,超越了一般的新闻叙事而打破体裁之间的界限[20];不拘一格地(尽管保持通讯的基本形式,即包含真实、时效等新闻要素)进行跨越新闻—文学语体和文体的写作,彰显了其独特的写作个性。
3.1 高度文学语体特征的语言:形象直观
海明威此时通讯写作的独特的风格业已成熟。除了早期的报业写作训练、他的性格、战争经历及他对西方传统通讯报道写作方式的叛逆等因素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海明威的写作经历除小说外几乎总是与通讯有关。从中学时为《堪萨斯之星》(theKansasCityStar)写新闻故事起,直到1936年间为纽约《绅士》杂志撰稿,他大都采用的是通讯体裁。通讯报道的篇幅一般相对较长,内容相对更丰富,在做进一步的特写时,为了能更加吸引读者,对写作的技巧和风格还有更高的要求。此时的海明威,经过多年的磨练,已将他早期养成的言简意赅的行文习惯同浓缩、紧凑而有力的电讯稿写作特点,即“电报式语言”[21]融合在了一起。他的表述洗练、精准,体现了文学语体语言高度的艺术特征,即形象性和直观性。为了使场景得到最有效的描述,海明威常用短句,并会在句子里连续使用短促而富有表现力的动词词组,以增强描述场面的直观效果。他“摄影机”[22]式地描绘战火中的马德里:
例9他们炸中了一个刚从集市回来的老妇,她身体被裹在了一堆黑布里,她的一条腿,突然间被拆卸掉,旋转着被抛向了一座临近房子的墙上……在一阵强烈的火炮的闪光和咆哮后,一辆沿街开来的汽车骤然间转向停下,司机摇晃着出来,他的头皮垂在眼睛上,用手托着脸坐到人行道上,血流淌过他的下巴,形成一层光滑的色泽[4]27。
例10不管我在何时何处,整整一天,当200发炮弹袭来,我无法视而不见,无法摆脱灰白色花岗岩粉尘和刺鼻的烈性炸药气味,也无法避免看到死者、伤者和人们用水管洗刷街道和人行道,他们不是在清除灰尘,而是在冲洗鲜血[4]34。
海明威在此冷静地描写了人们遭受炮火肆虐的情形,给读者或听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感。他写血淋淋的战争场景的冷静反映了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正视和对战争责任的思考。
3.2 独特比喻:二元结构
为了能更形象地描述战争场面,海明威在报道中大量使用明喻:
例11……场面壮观,战斗在我们面前四处展开。政府军的火炮,夹带飞驰火车般的呼啸,对准叛军的工事,一发又一发地直接命中……[4]25。
例12一颗炮弹打中了其中三个,他们看起来不像人,而像是奇怪的破玩具木偶。第一个玩偶失去了双脚,他躺在那儿,蜡白的满是胡茬的脸上毫无表情;第二个玩偶丢掉了半个脑袋;第三个玩偶残破得就像你口袋里的巧克力碎渣一样[4]19。
上述例子中描写反法西斯阵营的炮火像“夹带飞驰火车般的呼啸”,描写战场死去的敌人“像是奇怪的破玩具木偶,残破得就像你口袋里的巧克力碎渣一样”等事实细节报道,是存在于词间搭配的一种形象描绘手段,即明喻。从这些明喻的修辞效果来看,它们属于海明威个人创造的“独特比喻”。这种“独特比喻”也可细分为语义上的“二元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指字面上的比喻,表现为作者对事物的客观描述;深层结构则是包含了作者隐含的寓意和激发读者或听众的联想,是发挥独特比喻效果的部分,由所喻事物的本质属性联想开来。如“飞驰火车般”“像是奇怪的破玩具木偶”是对所喻事物的物理表层特点的一般联想,即比喻的表层结构;而反法西斯的炮火像“飞驰火车般”地雄壮,代表正义的力量似无坚不摧的压倒性力量;而战死的敌人“像是奇怪的破玩具木偶”,木偶是没有思想而盲目任人操作的,而人如果就这样被利用而战死是“奇怪的”、无法理喻的,被炸死后的身体残状犹如“破碎”了的木偶那样没有价值。这里反映出作者对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持和必胜的高昂情绪,同时也表现出对法西斯分子无情鄙视或对被法西斯利用的敌方战死者的怜悯,可解读为比喻的深层结构。
这种个性化的独特比喻手法包含了海明威当时个人的感受和想象,帮助他塑造出生动的战斗场景或形象,揭示了与法西斯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事实本质,深化了反法西斯主题,引发了受众的联想,有很强的感染力。海明威使用这种修辞手法的作用在于:在确保报道真实的同时,可以使报道表达得更生动形象。而对读者或受众而言,那些具体而生动形象的联想或许更易于让他们产生“主体间性”特征,从而以“视域融合”[23]的姿态完成解读过程。
3.3 用小说家的笔叙述通讯
在西班牙内战通讯里,海明威广泛使用不同的人称叙事,如上文所举例子中“你知道这不是一场……婚礼”“战斗在我们面前四处展开”和“这位睡意蒙胧的记者”等的使用,拉近了作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激活了作品和受众间的心理联系,使受众更容易进入他的语境。这种写法会产生作者/作品与受众互动、作者与文中人物互动的“动态效果”。他经常改变他作为报道者的身份:他一会儿以记者或作家身份,一会儿又以叙事者或事件人物的面貌出现进行报道。所有这些都表明,海明威采取了不同的叙事角度。用叙事理论中的“聚焦”论来解读,就是他的写作视角经常在外部聚焦和内部聚焦之间不断交替,实现来回的切换。海明威在写报道时,他的角色不但是当事人之一,即内部聚焦,而且他还是外部聚焦的“全知叙事者”。由于海明威在写作中采用了动态的、不断转换的叙事角度,他的报道不但现场感极强,而且显得生动活泼。
有评论家认为《海明威西班牙内战通讯》并不能称为上佳作品,比如奈特利(Knightley)[24]等人就批评海明威的西班牙报道内容贫乏,凌乱而又自我中心,并且“太多的比喻,刻意的形象塑造”[25]。在笔者看来,这恰恰证明海明威个性化地纪实和在运用文学技巧时秉持了毫不含糊的正义立场;说西班牙内战通讯在内容上“贫乏、凌乱”,有失公允,海明威只能从他所在的不同战场,在不同时段多个层面和角度介绍战况。
根据沃森(Watson)编辑出版的《海明威西班牙内战通讯》,从内容结构上看,它可分为3类:第1类,局势分析篇,包括《富兰克林的护照》《意大利和德国的干涉》《今日西班牙的战略形势》《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和后方》和《马德里在自己战斗》5篇;第2类,人物刻画篇,包括《一个美国受伤志愿者》《马德里的司机》《难民逃亡》《美国志愿者从格兰德萨撤退》和《詹姆斯·拉德纳-支持政府军的志愿者》5篇;第3类,其余战事通讯20篇。从在巴伦西(Valencia)1937年3月17日发出第一篇战地通讯《踏上征程》开始,海明威的通讯报告了他的足迹:巴黎—图卢兹(Toulouse)—巴伦西(Valencia)—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马德里(Madrid)—阿拉贡(Aragón)—特鲁埃尔(Teruel)—托尔托萨(Tortosa)—莱里达(Lérida)—卡斯特利翁(Castellón)—加泰罗尼(Catalan)—马德里(Madrid)。
从篇章结构层次看,西班牙内战通讯一般先介绍战争的战略态势和战役进程,然后开始以“摄影机”式的方式“扫描”战场的具体景象,并通过对材料的选取来展示战争场景,塑造战时众生的群像,应该讲内容还是丰富而综合性的。客观地说,在紧张的行军打仗中和亟须及时报道战事的任务压力下,不可能精雕细琢,不少文稿略显粗糙,但它们却真实有力。尽管西班牙内战通讯是战地报道,但海明威却采用叙事体写作,运用了多重叙事视角,叙述方式灵活而个性化;采用多种文学技巧,诸如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印象主义式的描述和诙谐幽默的笔调等,加上比喻等修辞手段的大量应用,使他的报道超越了一般的新闻通讯写作,呈现了现实主义作品的风范。甚至有研究者将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与之相提并论[26]。如果说海明威的小说被称为“新闻体小说”,那么他以小说家的技巧来写作的通讯被称为“小说体新闻”或“小说体通讯”可能也不为过。作为一位叙事大师,海明威在烽火硝烟的西班牙战场上不惧危险,从容挥洒自己的写作个性与才华,用准确、精练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反映西班牙内战的逼真画卷,同时也成功展示了他自身在思想境界方面的重大突破和走出迷惘的新形象。
4 结 语
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全身心地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和报道中;同时,西班牙人民和国际志愿者顽强抗击法西斯所展示的伟大力量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鼓舞,他以旗帜鲜明的立场和饱蘸情感及个性风格的文字,成功将那些力量传递到他的通讯作品之中,使他的通讯作品显示出极强的表现力,而被称为报道那场反法西斯战争“特别强有力的篇章”[27]。正是西班牙战场上血与火的淬炼驱散了海明威心中的迷惘,在真实报道的同时,他的真实情感与写作个性在西班牙内战通讯的写作中得到了绽放,成为西班牙内战通讯写作成功的要素。西班牙内战通讯是他首批不带迷惘色彩的正式发表的作品,而西班牙内战报道成为标志着他走出迷惘一代的一次洗礼。
西班牙内战报道对海明威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经历了对这场战争的报道,使海明威开始走出迷惘,由一名此前厌战、反战的孤立的“迷惘”者发展成为具有反法西斯正义信念的记者和作家,而告别“破碎的美国梦”和“无意义生活对他的困扰”[28],找寻到为正义而写作的身份角色。这种转变是他告别“迷惘一代”,进行个人自我重新建构过程的重要步骤,成为他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经历为海明威创作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积累了宝贵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创作素材,做了相当充分的前期思想准备。海明威的西班牙内战通讯和他的小说一样,都可归属到现实主义作品的类目下,而他不拘一格的笔触成为其作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