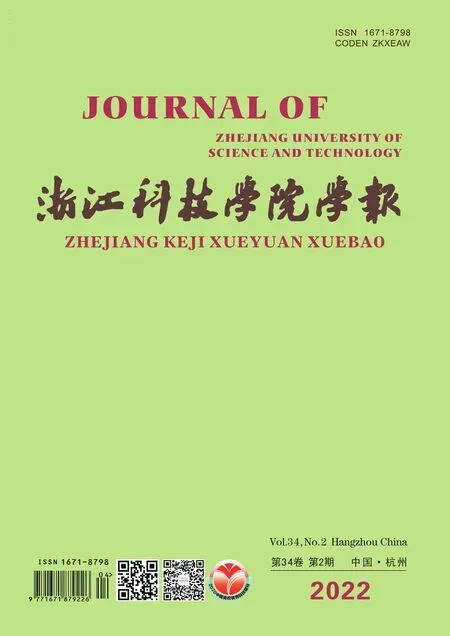“中国能力”在德国:溯源、现状与对策
黄 扬,黄建滨
(浙江科技学院 中德学院,杭州 310023)
中德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马可·波罗游记》在德国出版后,历经“东学西被”在德国掀起“中国热”,“西学东渐”中,德意志文化远播中国,官方、民间文化交流前后历经五百余年历史[1]。当今,中德关系进入崭新历史阶段。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德国总统高克会谈时指出:“当前中德交流合作紧密程度超过历史任何时期。”高克总统引用默克尔总理的话:“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良好,那么全世界都从中受益。”2016年6月,习近平接见在其任内第九次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时,这样描述中德关系:中德“相向而行”、应“拉紧互信纽带”及“在高起点上深入推进中德合作”[2]。
在此背景下,德国的“中国能力”应运而生。2018年5月,德国外交部(Auswärtiges Amt,AA)、德国联邦教研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和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Stä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联合对外发布,将共同促进“中国能力”在德国的提升与发展[3]。
1 德国提出“中国能力”的溯源
1.1 理论溯源: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人类认识与旨趣相互交叉,旨趣是认识的先导,认识是旨趣的力量。哈贝马斯将人的认知旨趣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三种类型,并认为每种旨趣都会导致科学的不同形式,即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4]。准确地说,技术旨趣可实现经验-分析性科学,实践旨趣可实现历史-解释性科学,解放旨趣可实现社会批判性科学。哈贝马斯还认为,三者中的核心是解放旨趣,因为解放旨趣是引导人类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反思和批判的力量[5]。正是在解放旨趣的指导下,人类认识活动才成为自我反思活动。在日常言语交往行为基础上,哈贝马斯构建了“交往理性”,由此将批判理论转向语言学方向,基于语言实践的“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重建的批判理论之核心。他认为,语言是交往活动的桥梁和纽带,“交往理性”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语言交往行为[6]。他相信,不同的主体通过语言对话达成共识,可以形成一种平等沟通、协作互动的社会语境。通过交往而达成的共识,使得社会互动和生活语境成为一个整体[7]。总体而言,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论主张褪去意识形态色彩,转向主体间的沟通、对话、协作与共赢,追求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语言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沟通中介。
德国提倡发展“中国能力”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德相互理解。正如联邦教研部国务秘书格奥尔格·舒特(Georg Schütte)所言,“我们国家必须有足够的人了解和理解中国,这非常重要。在掌握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后,我们才能自信地倡导自己的立场和理解对方。如果您在中国学习、工作或生活过;如果您能说中文,保持与中国的联系和交往,那么您就可以获得这种知识和经验。提升各个领域的‘中国能力’需要联邦政府、州政府齐心协力[3]”。德国提出“中国能力”,体现了哈贝马斯批评理论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
1.2 经济溯源
近年来,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6年起,中国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第2季度,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国。然而,德国缺乏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了解,这与中德经贸发展层次不对等,不利于德国企业扩展与中国的业务。
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主席,图林根州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赫尔穆特·霍尔特(Helmut Holter)认为:“我们无需人人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但重新认识中国,并向这个庞大的国家靠拢,这对德国有益。借助教育机构的帮助,我们可以做到这点。同时,工商业协会和企业也需要参与其中。中德双方的中学生大学生、教师及学者的交流非常重要。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和兴趣,以何种形式进行的交流都能为彼此创造更多理解、建立信任、减少偏见。未来几年,德国应大力加强‘中国能力’。”[8]
1.3 政治溯源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德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朗普指责德国拖欠北约和美国巨额防务经费,并敦促德方向美国及北约支付更多防务费用;签署了针对包括欧盟在内8个贸易伙伴的钢铁和铝的初步豁免权;特朗普提出的汽车惩罚性关税更是剑指德国。2018年,德国电视二台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达82%的德国人认为“美国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9]不难看出,特朗普任内的美德及美欧关系仍面临巨大变数与考验[10]。虽然美德间的种种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两国关系,但也给德国地缘政治外交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联邦外交部文化和传播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格尔根(Andreas Görgen)表示,“智慧的德国外交政策需要国家能力。亚洲是德国和欧洲未来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中小学、大学、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一起促进‘中国能力’的重要原因。”[3]
自2021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以来,美德关系、中欧关系均已发生变化。欧盟和美国在很多事情上存在争议[11],但这仍改变不了美德传统盟友的关系。而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连续第6年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伴。鉴于稳中加强的中德经贸关系,德国没有改变推行“中国能力”的指向。
1.4 现实溯源
中德互相了解程度的不对等状况使德国发展”中国能力”的举措具有紧迫性。德国机构曾对10名经济领域的德国专家、11名社会领域的德国专家、11名政治和管理领域的德国专家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果表明,6名德国专家认为,经济方面中国对德国了解较多,3名认为中德双方了解对等,仅1名认为中国对德国了解较少;11名德国专家都认为,在社会、政治和管理领域中国对德国了解较多。可见,中国的“德国能力”远胜过德国的“中国能力”[12]27,德国推进“中国能力”具有紧迫性。
1.5 “中国能力”的内涵
德国联邦教研部认为,笼统地讲,“中国能力”是指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所有能力和知识。具体地讲,“中国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以及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各领域情况的能力,主要指语言能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行为能力,即汉语和国情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其中,汉语是重中之重,譬如在经济领域关于中国合作方的信息,中国社会运行机制、权利范畴、国家计划和法律框架尤为重要。同时德国联邦教研部提出,在中国长期驻留是培养“中国能力”的重要举措。
2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的现状
既然汉语和国情知识,特别是汉语处于“中国能力”的中心地位,那么与二者相关的课程即是培养和发展“中国能力”的主要方式和关键手段。
2.1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的优势
2.1.1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在高校的优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德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增多,合作形式包括汉学、跨学科专业、特殊课程、资格认证、中德合作项目和中德双学位等。特别是中德高校合作居多,合作以增强“中国能力”为目的。据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HRK)统计,截至2017年,正式的中德高校合作项目已达1 347项。60所德国综合性大学与中国高校的合作协议达525个,以经济学、医学、法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居多;18所德国工业大学与中国的协议达283个,以工程学、机械制造和经济学专业居多;137所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与中国的协议多达539个,集中在工程学、机械制造和经济学专业。在中国开设的专业课程,如经济学课程,如果用英语授课,同时又能转换为在德高校学分,这类课程会特别受中国学生的欢迎[12]31。良好的中德高校合作为德国推广“中国能力”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多年来,学习汉语和在中国驻留较长时间的德国学生人数一直比较稳定;但同时,赴德留学的中国学生数约是德国在华学生的4倍。在合作项目中,德国学生有驻留中国的机会,希望去中国的德国学生人数呈增长趋势,这些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学和经济学专业。2015年,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DAAD)和德国高校与科研中心(Das Deutsche Zentrum für Hochschul-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DZHW)以“德国高校学生赴中、美、英、法四国留学的原因”为主题展开流动性研究,德国大学生留学四国的原因统计见表1[12]43。

表1 德国大学生留学四国的原因Table 1 Reasons for German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in four countries %
德国众多高校还开设了关于中国的课程,集中在3个范畴。一是古汉语。重点是语言的构成,介绍古汉语字,同时还学习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哲学、文学和文化。二是现代汉学。起始点由高校自行拟定,有的高校将其设定为1949年,有的设定为1844年。内容为学习中国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三是以中国为重点的跨学科学习。如科隆大学将汉学和法学相结合。可见,德国高校推广“中国能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方面。
2.1.2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在研究合作中的优势
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国际伙伴之一,是除美国之外的第2个最受德国科学家欢迎的国家。研究机构把中国作为重要伙伴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的研究领域和框架更有活力、更加灵活,研究成果投入使用的市场更大。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DAAD)、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协会、德国研究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DFG)、亥姆霍兹(Helmholtz)协会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0年、2003年开设了驻华机构。众多德国高校也陆续在中国设立研究办公室。中德技术合作领域包括城市建设、机械制造、交通体系、消除工业化后的弊端等,譬如土壤改造。2018年是《中德科研技术合作协议》生效40周年。40年来,中德合作的内容和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方的研究质量大幅度提高,中方本身也已具备某些高端技术水平和一流实验室条件。
德国联邦教研部的专家认为,掌握“中国能力”是中德研究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8]。因此,德国团队的工作人员需要具备“中国能力”。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很多德国科研团队已经开始吸收汉语作为母语的团队成员,这一措施加强了中德研究合作中推广“中国能力”的优势。
综上所述,“中国能力”在德国高校和中德研究合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丰富的推广经验和实施经验。
2.2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的劣势
2.2.1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在中学的劣势
迄今为止,在德国的16个联邦州中,只有5个州的综合中学里涉及有关中国的教学,主题有“中国的人口和环境”“中国的经济”,还有专业相关的主题,如“中国和印度的丝绸业”;仅有4个联邦州(巴登符滕堡、巴伐利亚、下萨克森、萨尔)将与中国相关的课程作为重点课程,主要是历史课和地理课,如在萨尔州,其地理课的主题是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国的人口分布、中国的移民和中国的经济[13]。
缺乏有关中国的课程造成德国中学生对中国知之甚少。同时,由于经费原因,德国学校里的关于中国的资料普遍过时,不能全面反映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
2.2.2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在职业学校的劣势
职业学校的教学计划鲜有涉及“中国”的内容。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职业学校,开设了“全球化中的中国”课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州,开设了“中国的人口政策”课程。在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职业学校已开设汉语课,通常全校5%左右的学生需要学习汉语,并且人数在增加。很多学校扩展了与“中国能力”相关的课程和活动,如汉语课和跨文化交流,但规模还不够大。在下萨克森州1所职业学校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4所职业学校里,外贸方向开设了和中国相关的课程,学生需要接受额外的、为期两年的课程。这些学校对在中国的实习要求不同,其中两所学校要求必须在中国实习,其他学校则要求和中国的学校互访或参观中国公司。
采用农产品重金属危害风险、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重金属生物可利用性和土壤重金属污染源输入风险相结合的评估方法,评估指标包括农产品重金属污染指数(E)、土壤重金属污染指数(P)、重金属生物可利用风险商(QBCF)、土壤污染源输入指数(Qs)。
德国职业学校里开展的关于中国的课程和活动均由教师或学校管理人员组织和实施。其中大多数的中国主题活动由当地企业和协会发起,其活动内容也与当地经济有关。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为关于中国的课程投入了大量时间,甚至动用个人资源;而职业学校对有关中国的信息需求非常强烈,迫切需要得到更好的、更高层面的支持。
2.2.3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中汉语课的劣势
1998年4月,德国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就“会考汉语统一考试”(EPA)达成一致意见。第一版汉语教学大纲于1993年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1995年在巴伐利亚颁布。在2000年和2010之间,其他8个联邦州也颁布了汉语教学大纲。自第一部汉语教学大纲颁布以来,汉语课已发展为德国较多学校的固定课程。过去的20年,在德国的很多地区,汉语课从教学计划外的环节成为教学设计的固定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学毕业会考的必选科目。德国各联邦州的汉语会考情况见表2[13]。

表2 德国各联邦州的汉语会考情况Table 2 Chinese language examinations in the German federal states
但是,德国推行汉语课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数少,比如2017年,德国的汉语学习人数仅5 000左右[12]37;二是有些学校因种种困难仍没有开设正规的汉语课。
3 德国推广“中国能力”的对策
3.1 德国的对策
3.1.1 加强德国政府部门的引领作用
除各级各类学校外,德国联邦政府、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起到了引领作用。近几年,德国外交部、德国联邦教研部和各州文教部的部长联席会议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德国外交部宣布对外文化教育政策的核心任务是中德学术交流、大学合作和德语推广,通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促进中德高校合作。外交部还支持两国中小学的校际合作和中小学友好学校网络(Schule:Partner der Zukunft,PASCH)项目,中国中小学在该项目的参与度居世界第一。2016年,德国联邦教研部出台支持德国高校发展“中国能力”的专项资助计划,计划4年内投入数百万欧元。近几年来,各州文教部的部长联席会议与中国教育部签署多项声明,计划加强包括职业培训和师生交流在内的教育合作。2016年,中德两国主办了“中德青少年交流年”系列活动。2018年5月,德国外交部、德国联邦教研部和各州文教部的部长联席会议还表达了共同准备和实施联合项目的合作意愿,将推出量身打造的专门项目,双方协同开展推广活动。
3.1.2 改变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的汉语教学现状
结合推广“中国能力”过程中产生的有效经验与面临的短板,德国倡议以中小学为推广重点,将其作为扩展“中国能力”的最理想场所。全面深入的汉语课是培养“中国能力”的前提,只有具备足够的语言知识,才能在后期展开跨文化或者和专业相关的能力培养。中小学可将汉语作为第二或第三外语,使更多的学生更早地接受汉语知识。中小学还需要采取一系列举措:首先,建设关于中国的网站供学校扩展“中国能力”;其次,举办以中国为主题的高级研修班,通过教师进修和继续教育提高教师的汉语水平,大力培养胜任推广“中国能力”的专业师资;最后,鼓励德国学生和相关人员短期或长期驻留中国,从而近距离、全方位了解中国。
2016年,德国联邦教研部实施“在德国高校形成更广泛‘中国能力’的创新理念”资助方案,为以高校为主体的各类机构开展“中国能力”建设的创新项目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计划持续至2022年。经过筛选,11个德国高校的项目被资助。比如宾根大学的“中国论坛”项目(Das ChinaForum Tübingen,CFT)。“中国论坛”成立于2016年,目标是培养德国高校将中国看作重要科研伙伴及贸易伙伴的意识,提高其“中国能力”,包括汉语语言能力、日常交际能力和信息检索及表达能力。项目核心内容是及时识别、关联和更新现有中国专业知识的能力。又如霍恩海姆大学“霍恩海姆的中国能力”建设项目(China-Kompetenz in Hohenheim,CHIKOH)。该项目以提升与中国在经济与科技等领域开展交流的实践能力为目的,以期为高校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14]。事实上,项目已初显成效,该校大部分毕业生被当地与中国有合作的企业聘用。
德国联邦教研部的资助方案,将“创新”作为促进“中国能力”的指导路线,从理念到方法都与传统的推广方式不同。在提升了德国高校“中国能力”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德国高校的创新能力。
3.2 中方的对策
德国高度重视“中国能力”,表明德国希望增进中德相互了解、扩大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在当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可因势利导地提出相应对策,以加强中德互信,促进中德合作共赢。
3.2.1 客观看待德国推行“中国能力”
德国对其二战历史罪行进行深刻反思,导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偏向积极一面。“德国制造”对大多数中国人意味着较高品质。反观德国,对中国存在一定的偏见,时常主观看待中国事务。中国人对德国的单方面盲目好感其实不利于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中国应客观、清醒地看待德国推行“中国能力”,其现实原因是为了与中国开展成功的合作,主要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3.2.2 加强中德学校间的交流
加强中德两国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互动交流。双方可组织假期交流营,德方学校带领德国学生团到中国的学校进行交流,亲身体验中国语言与文化,促进双方心意相通。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化发展程度较高的高校应当成为校际交流的生力军。高校不仅要对中德双边关系发展开展学术研究,而且要提供建议与方案,努力帮助双方切实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分歧与问题[15]。譬如在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中有多家高校的德国研究中心,它们就充分发挥了智库作用。
3.2.3 加强中德机构间的合作
在中德合作框架下,促使中德两国的科研机构围绕项目任务展开合作。通过与中方人员合作,通过在中国驻留,德方人员有机会亲身了解和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从而减少隔阂,增进彼此了解,保障项目任务的顺利实施。
3.2.4 促进民间交流
除学校与科研机构之外,还应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民间交流,如组织文化经济互访团、开办展览、举办比赛等。民间交流越是生机勃勃、精彩纷呈,也就越能增强了解和互信。譬如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汉语桥”,分为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汉语桥——在华留学生中文比赛和汉语桥——商务汉语大赛,旨在增强世界对汉语及中华文化的了解。自2002年开始,每年一届,吸引了来自全世界150多个国家,140多万名学生参赛,德国赛区名列其中。“汉语桥”已成为世界人文交流领域的知名品牌活动。
3.2.5 发挥语言平台的作用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是有效的语言与文化海外推广平台。截至2022年2月,德国共有孔子学院19家,孔子课堂4家[16]。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需结合德国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地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尤其是针对德国的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师资和汉语资料能够对接德方学校的汉语需求。
4 结 语
德国提出“中国能力”,理论维度受哈贝马斯批评理论的影响,现实维度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愈加强烈,面向中国的“德国能力”建设和面向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都是当务之急[17]。面对德方推广“中国能力”的计划和措施,中方应积极应对,在基于尊重和互信的基础上提出补充性对策,以实现“沟通、对话、协作、共赢”为理念支撑,以展开语言为主的系列交流活动为实践支撑,从而提高双方认知对方的能力,促进德国的“中国能力”,同时继续增强中国的“德国能力”。
——写在中德建交45 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