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反战电影遮蔽战争责任的模式化叙事策略
胡雨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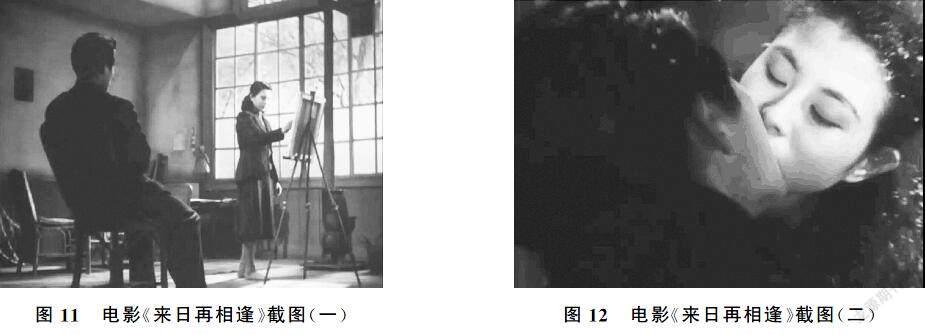
摘要: 日本反战电影既有反思力度强、能够深刻自省的影片,也有大批影片在反战主题中遮蔽了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这些遮蔽战争责任的反战电影普遍形成了三种模式化的叙事策略:一是虚化战争责任主体,发动侵略战争者从电影中集体消失,导致战争责任无承担主体或承担主体潜隐于幕后而被虚化;二是塑造受害者群像,大部分影片都以年轻的士兵、学生兵以及妇女儿童为主人公,反复书写他们的悲惨命运,强化受害者意识;三是彰显个体生命情感,影片表现战争中普通士兵和民众的私人情感,以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抒写,凸显个体生命创伤,从而回避战争责任问题。通过对这几种模式化叙事策略的分析,我们既可以深刻认识到日本反战电影在日本社会中艰难生存的文化处境,也能警醒人们对日本社会右翼崇战倾向和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警惕。
关键词: 日本反战电影; 遮蔽战争责任; 模式化; 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J904; J905文献标识码: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5.003
在日本,对于自己国家发动的以“二战”为代表的侵略战争历史事实,既有一批左翼正义力量潜心于揭露二战历史真相,表达对受害国诚挚的歉意,致力于和平主义文化建设,也有一批右翼政客和国民企图掩盖历史事实真相,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助长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幽灵的复活。日本社会正义力量与反动势力并存且后者不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政治和教育领域,也深刻地反映到文学和电影艺术中。日本的战争文学和战争电影中,也同样是崇战和反战、美化和批判这两种对立倾向并行不悖的。邵瑜莲曾说:“日本反战电影有一种双重性:既有要效忠于天皇的一面,又要有堅持艺术个性的一面;既要有听命于当局的各种审查,又要在审查的夹缝中寻求一条生路,这便使得日本反战电影充满着犹疑和矛盾,反战立场很模糊,反思力度也不够彻底。”[1]这种矛盾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导致大批日本的反战电影在反对战争、吁求和平的整体性进步思想倾向中,仍然保留着对侵略战争责任问题的暧昧态度。虽然日本反战电影中也有一些反省力度强劲、自我批判深刻的影片,如《人间的条件》《战争与人》《神军》《日本鬼子》等,但多数反战电影都在遮蔽侵略战争责任,模糊战争罪行。日本大批反战电影之所以选择逃避或模糊侵略战争责任问题是有着深刻原因的,笔者曾对这些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在日本社会,掌管国家政权的一直都是右翼势力,这说明大批日本选民是支持日本右翼政治家崇战政治立场的。日本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一贯性坚持“崇战”思维,这一大批社会受众都是打压左翼反战电影的。例如,影片《日本鬼子》的制片商曾向多家电视台推送这部影片但均被拒绝,经过多重努力终于有一家艺术影院同意放映,但上映后依旧受到了右翼分子的破坏与阻挠,正是这样一部真实反映侵略战争历史的纪录片在其他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却在日本受到冷遇。可见,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阻碍下,日本反战电影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电影业不仅具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还具有商业性和市场性。电影业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律,没有票房的支撑,再优秀、再伟大、再进步的影片都无法走向社会,走向未来。所以,日本电影阵营中的左翼进步人士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这就导致他们创作的反战影片在表达反对战争、期盼和平的诉求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事实,普遍采取了回避、遮蔽乃至模糊的方式予以处理,从而形成了几种模式化的反战叙事策略。邵瑜莲曾将日本反战电影的制作模式总结为“官兵对立、阵营分化、士兵残忍、战争受害、战争罪恶、他者视角等”[2]几种类型,这里面已经涉及到一些模式化叙事策略问题,但作者并不是针对“遮蔽战争责任”而言。笔者认为,日本反战电影遮蔽战争责任的模式化叙事策略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虚化战争责任主体、塑造受害者群像、彰显个体生命情感。通过对这几种模式化叙事策略的分析,我们既可以深刻认识到日本反战电影在日本社会中艰难生存的文化处境,也能警醒人们对日本社会右翼崇战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警惕。
一、 虚化战争责任主体
通观日本的反战电影,之所以给人造成战争责任遮蔽的普遍性认识,从电影制作本身来看,主要是因为在影片思想内容的建构中,大多让战争责任主体即以裕仁天皇为核心的军政内阁要员从影片内容中集体消失,一般都不设置有关他们的镜头影像和话语内容,即使出现了他们的镜头,也会转移责任主体或责任对象。这样制作既有导演的主观意图,也有社会现实存在客观因素的制约。像《日本的悲剧》等少数几部影片出现了天皇形象,并承担了部分战争责任主体的功能,但它们很快就遭到官方的禁映。反战影片普遍通过战争的责任主体缺席、虚化、弱化、转移等方式,既可以避免将战争责任问题予以大众化、舆论化,又可以让影片能够通过官方审查,同时又能唤起民众对战争的批判和对和平的向往。
首先,战争责任主体的虚化。日本反战电影中普遍将施战的天皇和大臣等战争责任主体虚化,将责任主体抽象到“战争”这个符号上来,从而达到战争责任虚化的遮蔽效果。在日本传统观念中,“日本的天皇是日本主权的拥有者,是继承了天照大神以来万世一系皇统的‘现人神’。”[3]天皇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子孙,是君权神授的代表,神圣不可侵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天皇成为日本统治者起就向国民灌输天皇是神的子孙的信念,国民对天皇也必须绝对服从和尊崇。因此,日本人拍摄的任何类型影片都不会轻易将天皇推到追问罪责的位置上予以批判或审判。美国占领军撤离后,一部分左翼民主人士就提出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立即遭到当权者的抵制。所以,电影导演只好规避这个话题,才能在电影界求得生存。于是,一些影片通过隐喻和象征手法,将天皇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符号,与父权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父权的坍塌来隐晦地暗示皇权的弱化与危机。如《大曾根家的早晨》中,作为父权代表的叔父来到大曾根家指手画脚,擅自规划侄儿侄女们的人生道路,最后被赶出家门,对父权的反抗象征着对皇权的反抗。非反战片《破碎的太鼓》中,也刻画了一个集封建顽固无礼于一身的独裁式父亲形象,被家人孤立,最后达成和解。而更多的反战影片都未曾出现过对天皇和其领导的政府集团的直接控诉,也没有反思战争的起因和发起者,战争责任主体消失,而批判的对象就是“战争”本身。《人间的条件》等少数几部反战电影将批判的触角明确指向军国主义,但也未涉及对天皇等军国主义领导者的批判。
影片《日本最长的一天》中,有天皇现身的场景,但导演故意将天皇的正面形象遮蔽起来,主要拍摄背影、半身、侧面的中远景镜头。图1是众臣进行战争指导会议,此时的天皇是不在场的、缺席的。图2是天皇坐在正中间与众臣商议投降事宜,画面以天皇为中心左右对称,显示了天皇的绝对权威,镜头上方的屋顶呈倾斜状,在格式塔心理学中倾斜的线条寓意压迫、不安和紧张的心理,这种紧张和压迫感一方面源于对日本不利的战争局势,另一方面源于日本政府军队内部强烈反对投降的声音。图3中的天皇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众臣的围坐下他依旧处于中心地位,但被遮挡住了半个身子和面容,带着神秘感和庄重感让人无法亲近。图4则是非常罕见的天皇特写,在表达了对战争中牺牲受伤的国民的同情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落寞的姿态凸显了天皇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这四个镜头画面分别以天皇的缺席、背影、半正面和侧脸特写来表现天皇一步步走下神坛成为人的完整历程,也是日本帝国走向衰落的标志。但实际上天皇完整的形象始终未出现,而且从他在众臣会议上所表达的言论和意愿来看,他认为持续战争只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他想要终止这一切,不愿日本民众陷入更深的泥淖中,言语中刻画了一个体恤、同情、爱护民众的天皇形象,传达给观众的印象是想要终止战争的天皇,绝不可能是发动战争、导致无数无辜民众在战争中遇难的罪魁祸首,如此一来,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被消解了,而天皇依旧是人们所信奉尊崇的统治者。这部影片本身以中立偏反战的立场来讲述日本投降前后所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导演的初衷是想尽力还原一段未被大众所知晓的历史,所以反思战争责任也并非影片的主旨。
其次,战争责任对象的转移。少数反战影片出现了天皇的形象,但并不是作为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设置,而是作为对自己国民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主体来设置,是作为向死难者表达忏悔和哀悼者角色。如影片《在飘扬的军旗下》,片头将天皇夫妇哀悼死难者的记录式影像剪接进电影中,采用微微俯拍的角度,从侧后方记录下了身着西装的天皇渐渐佝偻的身影,表达了对死者的尊敬及对自我的省思。天皇的出現说明战争已经过去,但逝者已去,他们身上承载的故事也大多烟消云散、不为人知,即便天皇为死者鞠躬献花,为国家祈福,也总会有像富江一样的人为了获得历史真相而不辞辛苦,对战争真相的追究也不会停滞,影片以此来表达了追问战争责任的意思,但并非追问天皇对外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对自己国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所应该负有的责任。在影片《萤火虫》中,天皇最后一次出现的画面是主人公的葬礼,代表着昭和时代的远去,但并不意味着战争死难者和幸存者能因此遗忘战争创伤而获得安宁,影片也只是隐约地表达出天皇与民众的战争创伤有着必然的联系。野村芳太郎于1963年导演的影片《拜启天皇陛下》,表现了一位对天皇极度崇拜的“赤子”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影片通过反讽的方式表现战时民众对天皇的愚忠,表达导演的反战思想,但对天皇的战争责任却未提及,包括天皇的形象也仅存在于山正的“崇拜”和幻想中。影片最后的字幕呈现了主人公山正写给天皇陛下的信——“陛下啊,您最后的‘赤子’在这个夜里战死了。”日本学者矢野宽治对这部影片评论道:“山正在被碾之前,朝着行在路上的美军故意大喊‘天皇陛下万岁!’,还一边哼着‘喜欢你’的曲子。这一瞬间,这部作品完完全全是一部反战电影,展现了野村芳太郎对战争的反抗之情。”[4]影片将战时一批对天皇极度迷恋愚忠的人物通过喜剧化讽刺予以呈现,天皇并没有被作为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而是愚弄欺骗国民的人,应当对本国民众经受的战争创伤承担责任,而不是对被侵略国家和他国人民应该承担侵略战争责任。
还有一些反战电影思考战争中人性的异化,淡化了现实中有具体指向性的反思。如《野火》将主人公置于荒凉的自然环境中,在荒野中没有敌人,敌人不是美军、不是游击队,现实指向性较弱。影片反思批判的是因战争导致军人内部的互相残杀,以及人潜在的兽性所产生的毁灭性力量,而激发这种兽性或是这种力量本身的即是抽象的“战争”。对于“战争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战争责任应该由谁承担”等问题没有作深入的思考,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优秀的反战电影。
总之,除了个别影片将天皇的形象与天皇的战争责任联系在一起之外,其他影片普遍将天皇形象消隐在影像中,即便出现了也是通过掩饰的方式让天皇不能“直面”观众,从军装过渡到西装,从神坛走向民众,只是从天皇外观和形式上表现了战争时代的终结和天皇神话的幻灭。少数对天皇战争责任的思考也只停留在对国内民众所负有的责任,几乎没有涉及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意识。
二、 塑造受害者群像
区别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要看敌对双方哪一方是受害者,而哪一方是加害者的问题。日本反战电影对矛盾双方的设置策略普遍是尽量回避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而突出日美之间的太平洋战争。普遍将矛盾冲突从敌我军队之间的冲突演绎为形形色色的不涉及战争性质的其它冲突,塑造出一系列“战争”的“受害者”群像。在“加害者”不断琐碎化、生活化、空洞化的基础上,将矛盾冲突不断归纳到抽象的“战争”上去,或者演绎到琐碎的生存条件等对象上去,从而遮蔽了战争的责任主体。
从总体上看,日本反战电影的受害者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对战争的加害者批判主要是三种对象:一是国内军国主义权力机构,二是军队和民间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三是美国的报复性反击。这三种主要矛盾构成了这些受害者群像的加害者角色。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三种主要矛盾几乎没有涉及到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的直接对抗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影片并没有把受害者与加害者设置为日本国家与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等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
首先,日本反战电影通过塑造日本下层民众受害者形象,将加害者指向国家权力者,将战争的矛盾转化为国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而遮蔽了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沟口健二导演的影片《夜之女》(如图5),影片的主人公家庭主妇和子是一位典型的“受害者”悲剧角色,丈夫参军未归,她艰难地维持着家中生活。不久她收到丈夫身亡的噩耗,家中还有身患肺结核病的孩子,无奈之下她出卖肉体救治幼子,但最终儿子还是病重死去。之后和子与公司社长相恋,但社长私下干着违法的勾当,还与和子的妹妹厮混,得知这一切的和子辞去了工作沦为站街女,而她丈夫的妹妹在被骗后也堕落风尘,她的妹妹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幸福。欺骗和子与妹妹感情的社长象征着权力阶层,就像军国主义政府欺骗愚弄大众一样,他们都因被骗而饱受磨难,而沦落的女性是下层民众受害者的代表。影片中这些女性的悲剧表面上是生活现实导致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国家权力集团发动的战争导致的,加害者直指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木下惠介的影片《日本的悲剧》(如图6)讲述饱受战乱之苦的母亲不惜出卖肉体抚养两个孩子长大,但儿女没有丝毫感激之情,自私地将母亲逼上绝路。剧本中有一段台词,老师说:“在战争期间,大家都受了很多苦,都为日本能打赢这场战争而作出了努力。但是,因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所以,现在日本国民陷入了苦难之中!今后,大家一定要正确地判断事物,不要再受军部和那帮坏家伙们的愚弄啦!”学生举手问老师:“老师!那么,您把错误的历史教给我们,把错误的战争说成是正确的;是不是老师也愚弄了我们。”老师说:“不是这么回事。老师同你们一样受了他们的骗。所以,为了今后不再受骗,我要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这段师生对话直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对整个社会的愚弄。此类影片很多,如小津安二郎的《风中的母鸡》和铃木清顺的《春妇传》《肉体之门》等,都明确通过日本底层的战争受害者形象塑造,将加害者指向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其次,日本反战电影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形象塑造,将加害者变成各种具体的矛盾对象,或者“抽象的战争”,将人物的悲剧命运定位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上,从而遮蔽了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以刻画底层士兵的反战电影为例,影片《真空地带》将加害者设置为“中尉”以及军队的士兵同伴,批判对象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从广泛的军国主义制度和政府到具体的军队集团和个人,揭露了日军内部的腐败和管理混乱,充满欺瞒、压迫、歧视等等丑恶的现实。《人间的条件》中的受害者梶的加害者也是军队中的小军官和战俘营中的管理者。《我想成为贝壳》中的受害者清水的加害者也同样是自己的上级军官。虽然这些影片不同程度上都有对军国主义和军队整体的批判性指向,但这些具体的矛盾冲突必然制约了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对造成人物悲剧的对象作出了客观限定。还有一些影片普遍将战争责任主体提升到“抽象的战争”上去,遮蔽了具体的战争加害者责任。如影片《二十四只眼睛》中受害者角色大石老师和学生们所遭遇的加害者则是“战争”,至于何种战争,在作品中并没有予以具体说明。“战争”让她失去了丈夫和女儿,“战争”让她的学生一个个死去,一个个陷入贫困、疾病。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影片传达出的印象是,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永远拥有他们孩童时代的纯真。观众们并未见证这些少年如何成长、如何参与海外的侵略和杀戮。如此一来,孩童的纯真,就成为了表达战死者纯洁性的手段。”[5]可见这里的加害者变成了抽象的“战争”,这类影片还有《战争与青春》《纸屋悦子的青春》《待到重逢日》等。
再次,日本反战电影以日美战争对抗中的受害者形象塑造,或隐或显地将加害者转移到美方,遮蔽了具体的战争加害者责任。日本的战争电影中不少影片是反映日美作战的历史事件,一类是表现在日美战争中日本军人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和誓死战斗到底的必胜信念,这类影片一般不具有反战意识。如《虎!虎!虎!》(《偷袭珍珠港》)等。另一类则是描写日美战争中的日本受害者形象,反映日方遭受的伤害和苦难,这类影片具有较强的反战意识,但它们普遍模糊了日美战争的历史和动因,弱化了这场战争的加害者日方责任主体的罪责,甚至将战争的加害者转移到美国一方。当然,美国为了报复日本军人的残暴,最后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非常规战争手段,对日本的几十个大城市采取无差别轰炸,并最终投下了原子弹。可见日本对美国的这些报复性措施不能说没有怨恨乃至仇恨,也不能说美国完全没有“加害者”角色性质。于是这就给日本人带来了又一重要理由,他们只肯承认败给了美国,并不愿意承认败给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因此,这类反战影片中的立场态度和情感倾向都是值得深思的。
日本反战电影中,有很多对神风特攻队、鱼雷回天特攻队、姬百合部队等与美军正面战争的群体与个体的叙事,也有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群体与个体的叙事,这些战争受害者形象的反复书写,一方面有将战争责任归结到日本统治者的意图,但作为“加害者”的统治者并不一定就是侵略者;另一方面,则有将加害者归结到美国的意图,从而转移了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也许聚焦于二战末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才能凸显日本的被害意识……通过‘被伤害’的影像,这些影片宣传的是美国等盟国的反攻给日本人带来的极大伤害,而非日本发起的战争给他国人民造成的伤害。”[6]这类影片在日本的反复上演,如《最后的特攻队》《爱与梦飞行》《月光之夏》《永远的零》等影片讲述了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故事,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让年轻的特工队员送死,有学者对这类影片评价说:“日本的反战电影不问战争的发动者,不追究战争的正义性与目的性,无关乎‘为什么而战’的命题。”[7],以《姬百合之塔》为例,从1954年到2007年间就被重复拍摄了6个版本①。今井正导演在影片前半部分渲染了少女们唱歌跳舞、洗澡玩耍的天真烂漫的生活场景,她们并未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如图7表现女孩们团聚的场景。接下来用很大的篇幅描绘伤兵的状态,药物不足、陷入癫狂、濒临死亡等,如图8表现女孩受伤的画面,花季少女直接目睹了战争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恐惧场景,也体验到军队内部的压迫,在一步步撤退的路上军方抛弃了受伤的士兵和女孩,在听到战败的消息后,老师和学生们在战壕里用手榴弹自杀了,影片谴责的是战争及军国主义对平民的荼毒和伤害。有学者评论说:“這场战争之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是一场悲剧,并不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而是日本人过于顺从了军国主义。”[8]影片中的少女们集纯洁和无辜于一体,是战争受害者的典型代表。与特攻队员一样,他们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努力执行着上级的命令,对体制是顺从的,当然也是无法反抗的,所以他们的自我牺牲和献身行为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同情感。这类影片在塑造受害者形象时,不知不觉间将战争责任和罪行转移了,让人感觉到施暴的是美军,影片蕴含着潜在的对美军的仇恨。岩崎昶评论道:“看过《山丹之塔》的中学生们在作文中写道:‘此仇必报’。……尽管打着批判战争、反对战争等等冠冕堂皇的招牌,其实是在煽动许多日本人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对战争的怀念和对日本帝国时代好日子的向往”[9]这充分说明,这些看起来具有反战精神的影片,其实质上遮蔽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体责任,却将新的仇恨和敌对情绪植入到年轻的日本人心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此外,日本反战电影中的原爆受害者形象塑造,普遍直接将美国作为“加害者”对象,从而遮蔽了日本作为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原爆电影中描绘的受害者普遍是日本普通民众,这类影片普遍以女性和儿童为主人公,在展现原爆受害者苦难群像的同时,无形地将战争责任主体转换成为美国了。以《原子弹下的孤儿》为例,影片讲述原爆幸存者孝子回到广岛看望她曾经的亲友和学生,家仆在原爆后视力受损已沦为乞丐,儿子死在战场,儿媳死于原爆,唯一的孙子也被送进了孤儿院,孝子的好友也因核辐射失去了生育能力,她的学生大多也成为孤儿,住在贫民区靠打工赚取微薄的薪水,有的因原子病濒临死亡。影片依旧将日本人群体描绘为团结和谐的集体,通过展现原爆后普通民众的悲惨现状来凸显核战争的残酷性,孩子寓意着未来和希望,而原子弹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也将希望摧毁殆尽。影片《八月狂想曲》中,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前,有各个国家送来的祈愿和平的雕塑,弟弟问为什么没有美国的,姐姐回答道:“原子弹正是美国投下的啊!”道出了对美国难以化解的怨恨。这类影片还有很多如《广岛昭和20年8月6日》《广岛》《长崎之钟》《不忘长崎之歌》《留下这个孩子》《明天》《赤足的小元》等等。日本学者在评价《若与母亲同住》这部影片时说道:“影片最后一幕,空气中弥漫着幸与不幸、绝望与希望、生与死的对峙,但恰恰回避了‘为什么日本会被原爆’这个根本问题。”[10]以原爆为题材的影片标举和平主义旗帜,将日本人塑造为绝对受难者,以悲剧化的人物形象和命运来化解日本自身的战争责任,甚至有将责任与仇恨转移给美国的嫌疑。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日本反战电影创造了许多“受害者”形象,但由于导演对这些看似相同命运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悲剧冲突对象的不同设置,导致“加害者”身份各不相同,并因此遮蔽了日本作为二战侵略者的战争责任主体身份,从而失去了对二战战争责任的认定与接受。
三、 彰显个体生命情感
在战争时期,任何表现私人情感的影片都是被禁止的,因为一旦士兵和民众被私人情感所左右,那么军国主义的宣传话语就变得空洞无意义了,受大众欢迎的爱情电影直到战后才重回银幕,而且往往与反战联系在一起。在塑造受害者形象的同时,反战影片尤其注重对小人物情感的凸显,主要描绘战友情、母子情和恋人之间的情感和命运,借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话题来表现战争对普通人情感的压制与摧残,即将或已投身战场的男性是为了保护家人或爱人而去参与战争,参与战争的行为不再仅仅是为天皇而战,也不仅仅是为国“玉碎”,而是为了守卫自己的家人和爱人。这样,作为个体的私人化情感的书写,不仅被赋予了一定合理性,也让侵略战争的罪责在民众个体情感之下被无限缩小了。因而,日本反战影片通过对私人化情感的彰显,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战争责任主体的罪责。
首先,表现战友情是一些日本反战影片的共同特征。它们通过个体化和小群体的战友之间的互助互爱、共同克服困难,表现出个体小爱对天皇之大爱的超越,从而超越了对战争性质的理解和追问。许多士兵是在被国内亲人与民众夹道欢送、唱着军歌和效忠国家使命口号等崇高精神的激励下走向战场的。但是,战场的现实是极为残酷的,这里只能依靠战友之间的相互帮助才能更好地自保生存。如《巧克力与士兵》就是表现战友情和亲情的一部影片,影片描写一个出征士兵在战场上牵挂家人的故事,真实表达了生活在黑暗年代的平民对战争的无奈态度和悲伤情感。一位手艺人收到参军令被送往中国战场,但他没有勇于奋战的精神,而是热心收集战友慰问袋中的巧克力包装纸,因为集满几百张包装纸就可以获得巧克力公司赠送的巧克力,他把包装纸寄给家中的儿子,当儿子换来巧克力的那天传来了父亲战死的消息。影片强调集体内部的战友情,“日本人之间是生死与共的伙伴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气氛在战争电影中被强烈地感受到了”[11]。不仅是战友情,士兵在前线思念牵挂家人的情感也被凸显了,对天皇的忠诚被淡化了,战争的意义也变得模糊,一旦观众被这样的情绪感染,就不会去思考为什么士兵会被送到中国前线,他们战斗的目的是什么,更不会考虑到战争责任的问题。这部影片作为战争宣传片拍摄于1938年,由于政治形势对电影界的压迫使得导演几乎不会往战争责任方面去反思,战争时期的反战影片也几乎都是通过烘托战友情来委婉地表达反战思想,包括影片《五个侦察兵》《土地和士兵》《坦克队长西住传》等,都以表现战友情来隐约表达反战的主题。即便是战争结束之后,也有很多凸显战友情的反战电影,如描绘空军飞行员和海军士兵的影片《爱与梦飞行》《听,海神之声》等,都是以戰友间感人至深的友谊来表现死亡的无意义。然而这些个体化情感的凸显,既淡化了效忠天皇和国家的大我之情,同时也遮蔽了对战争责任的思考。
其次,表现亲情的可贵也是日本反战电影的重要内容。影片通过对亲情这种个体化私情的弘扬,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公情(爱国情、忠君情),并遮蔽了对战争责任的表达。如山田洋次导演的《母亲》,影片刻画了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式的主人公形象,故事背景设定在15年战争时期,丈夫因发表反军国主义言论被逮捕,但她对丈夫的信任始终都未动摇,母亲悉心照料家人、孤身带着两个女儿熬过战乱年代,再现了战争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母亲的坚韧和善良给予了同情和褒扬。母亲不仅要照顾狱中的丈夫,还要养育女儿,为了解决生计她进入小学当教师,却目睹了孩子们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当师生集体向天皇照片致敬时,母亲因体力不支而晕倒,也意味着战时意识形态对个体精神层面的压迫。父亲劝说她与丈夫离婚,但她坚决拒绝了,依旧选择在精神上追随丈夫,伟大的母亲所压抑着的痛苦和不甘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才释放出来,是对战争时代最直白的控诉。影片以母亲的视角展现了战争爆发前后时代的变化,也表现了战争对普通人的摧残,强调家庭与亲情的弥足珍贵,但依旧没有脱离“受害者情结”的影响,“通过完美的传统母亲,影片完成了对于昭和时代旧式人情礼道的温情怀旧,传达出的观念是:战争虽然可怕,军国主义(具体化为宪兵的形象)虽然可恨,但平民是善良、无辜的,就连满口国家主义话语的邻组组长也不是坏人。”[12]影片《陆军》的结尾,旁人挥舞着旗帜为参战士兵助威,而母亲含泪目送儿子参军,眼中充满着万般不舍与无奈(如图9、图10中母亲的表情)。影片《战争与青春》描写一位母亲在战争中丢失了女儿,她的余生都在寻找,等待女儿的出现,战争使得无数母亲和她们的子女分离,失去子女的她们余生都在思念和悲痛中度过。描写战争让亲人生死分离的影片还有《赤足的小元》《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我的广岛父亲》等,因为所有人都是战争年代的受害者,战争责任问题也就此被隐去了。
再次,通过爱情的渲染来凸显战争时期个体感情的重要价值,以此淡化对天皇和国家的大爱之情,既消解了军国主义精神,也冲淡了战争责任的思考。如反战爱情片《来日再相逢》控诉了战争对恋人之间纯洁的爱情和美好青春的摧残与毁灭,将爱情和反战联系在一起,战争和军国主义成为批判的焦点。战争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总是出现在爱情世界中,如图11,萤子给三郎画像,窗外是建造战壕发出的刺耳的爆破声。他们在街头相见,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三郎保护着萤子,这些都时刻提醒着他们,战争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在很多影片中,军人出征前都会考虑要不要和恋人发生关系,但三郎始终没有向萤子提出要求,只是出门后在窗外与房间内的萤子留下了经典的隔窗之吻(如图12),不仅传达了恋人间热烈又含蓄的爱情,又避免了落入平常接吻画面的俗套,这一吻与窗外的白雪互相映衬着,将分别的无奈和欲望的克制等情感展现无遗。还有影片《纸屋悦子的青春》同样是即将要出征的军人深知自己可能无法回来,面对心上人,他将爱深藏于心没有表露,因为他不想辜负心爱之人的后半生。对战争年代的人们来说,爱情只是奢望,和平年代再回看这类悲剧爱情故事就显得和平尤其珍贵。正因为爱情成为主题,所以战争责任的问题也就自然遮蔽了。这类影片还有《春妇传》《为了伽椰子》《刚才发生过的事情》等。
除了私人化情感之外,还有以人道主义思想强调自我救赎而隐去了侵略战争罪孽的影片,如《缅甸的竖琴》等。故事发生在战争末期的缅甸战场,缅甸也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士兵水岛在受伤后被僧人所救,他冒充僧人想要和战俘营中的战友会合,因为僧人的身份他得到了民众的帮助和礼拜,在这一路上有数不清的日军士兵暴尸荒野,当他到达战俘营看到神父和医生为死去的日本士兵安葬的场景后被触动,他决定留下来安葬死去的战友,让他们的灵魂安息。水岛从士兵到逃兵,到伪装为僧人,再到亡灵超度者,身份上的变化也是他在精神上的超越。从水岛留给战友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并没有异化他的人性,而在这罪恶的环境中他始终怀着一颗纯粹的心完成了对生死的参悟,对灵魂的救赎,以及对亡灵的安顿。“影片抛开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以宗教悲天悯人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精神去反思战争给人类、民族和个体生命造成的灾难,表达厌恶战争、渴求和平的主题。”[13]影片以佛教思想为支撑,淡化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也存在逃避现实的批判,屏蔽了更深刻尖锐的反思,但作品所拥有的宗教情怀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和平主义的诉求,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还有影片《战争弥撒曲》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在一战时期,日本德岛的俘虏收容所所长不顾上层反对,宽容对待德国俘虏,尊重他们的人权,宽恕逃跑的战俘,让他施展烤面包的手艺,影片处处充盈着人性的温暖,战争结束后,德国战俘怀着感恩之心为所长和当地居民演奏贝多芬交响曲。影片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表现了人性的真善美,但同时也遮蔽了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罪孽和残忍。
总之,日本反战电影叙事普遍通过虚化战争责任主体、塑造受害者群像、彰显个体生命情感的方式来遮蔽战争责任主体,形成了几种模式化的反战叙事方式。强调友情的可贵、亲情的无价和爱情的美好,以人道主义精神来批判战争的残酷,在刻画受难者形象的同时,也细致描绘了这些普通人的情感,个体情感是对抗极权主义和战争最有力的武器。但这些影片依旧沉浸在本国国民的情感伤痛中,只是谴责战争,并未对发起侵略战争的责任展开深入思考,对个体情感的强调本身就限制了对战争进一步的反思,也是遗忘战争责任的有效方式之一。“战后日本大多数战争片虽然通过不断再生产的各类战争表象强化了人们的反战意识,但同时也不可忽视的是,除去少数作品,许多影片过度宣泄被害意识演变为一种国民文化记忆,从而淡化了日本人对亚洲各国殖民、侵略等加害行为的反省。”[14]这些日本反战电影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作出了选择性遗忘,也会导致此后的日本文化和日本青年对自身的战争历史作出选择性的遗忘,即只记住了自己民族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与耻辱,却忘记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他国人民带来的破坏与伤痛。这种对本民族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反思与批判的不彻底与当今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猖獗,这二者间显然存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关联。这也警醒我们,对日本社会自上而下的军国主义侵略性需要时刻具有清醒的认识,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回潮保持高度警惕!
注释:
①这包括今井正的《姬百合之塔》(黑白片,1954),小森白的《太平洋战争与姬百合部队》(1962),舜天利雄的《啊,姬百合之塔》(1968),今井正的《姬百合之塔》(彩色片,1982),游川和彦的《姬百合部队》(2006),柴田昌平的《姬百合》(2007)。
[参考文献]
[1] 邵瑜莲.日本反战电影的历史考察与艺术探析[J].当代电影,2015(09):98-101.
[2]邵瑜莲.反战电影制作模式类型探析[J].东岳论丛,2013(05):139-142.
[3]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M].赵自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91.
[4]矢野宽治.反戦映画からの声 あの時代に戻らないために[M].福冈:株式会社弦书房,2017:64.
[5]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M].胡博,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506.
[6]干瑞青.反战与否:简论日本二战电影塑造战争记忆的方式[J].艺苑,2016(04):41-43.
[7]李素杰.日本“神攻”电影透视[J].当代电影,2018(03):150-153.
[8]汪晓志.日本戰争电影[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120.
[9]岩崎昶.日本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244.
[10]北村匡平.日本反战电影:加害者责任岂容逃避[N].温潇,编译.文汇报,2017-02-22(8版).
[11]佐藤忠男.日本电影史:(中)[M].应雄,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7.
[12]陆嘉宁.银幕上的昭和:日本电影的二战创伤叙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203-204.
[13]黄献文.东亚电影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1.
[14]晏妮.战争的记忆和记忆中的战争:简论日本电影的战争表象[J].当代电影,2015(08):81-86.
(责任编辑文格)
Patterned Narrative Strategy of War Responsibility
Obscurity in Japanese Anti-war Films
HU Yu-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anggang Normal College,Huanggang
438000, Hubei,China)
Abstract:Despite reflective and self-reflective Japanese anti-war films,there ar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films that obscu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Japanese wars of aggression in their films with the anti-war themes.These films have generally developed three patterned narrative strategies: Firstly,the subject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s are fictionalized,and those who initiated the wars of aggression disappear from the films collectively,resulting in the absence of the subject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or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the subject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by hiding behind the scenes; Secondly,the portraits of the victims are created,and most of the films feature young soldiers,student soldiers,women and children as the main characters,repeatedly wrote about their tragic fates; The third is to highlight the emotions of individual lives.The films show personal feelings of ordinary soldiers and people during the war,highlighting the trauma of individual lives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family,friendship and love,thus avoid the issue of war responsibility.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patterned narrative strategies,we can both gain insight into the difficult cultural situation of Japanese anti-war films surviving in Japanese society and alert people to the right-wing war advocating tendencies and ideologies of Japanese society.
Key words:Japanese anti-war films; obscuring war responsibility; schematization; narrative strateg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