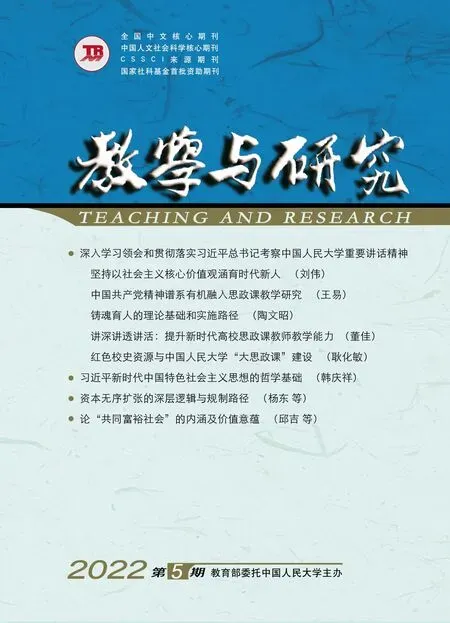多边主义理论辨析与全球治理实践危机
许嫣然,曹司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60-161页。在应对世界变局诸多冲击中,西方关于多边主义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实践都令世人失望。西方多边主义理论与实践总是存在某种偏差或者“割裂”(gap),因为不同主体间的观念差异与竞争,导致多边主义的实践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边主义行径常以同质化和管制其他国家来维护其霸权秩序稳定, 所以容易产生在某些特定议题、同一地区下的竞争性多边合作实践,甚至一些具有排他性、精英主义式的“伪多边主义”。
中国的多边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实践中也积极捍卫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内化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精神气质,外化为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反恐、数字经济等全球治理的具体行动。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多边主义的真正要义。面对西方“伪多边主义”向中国的一再发难,本文旨在从学理上厘清多边主义理论困境和实践的发展问题,深入剖析美式“伪多边主义”对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危害,探究我国促进多边主义的理论主张、主要路径和中国方案,力图对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
一、 多边主义的理论困境
多边主义理论最初兴起是为了弥补旧有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对于解释战后发达工业国家间的合作行为,“零和”的国家间无政府状态与国内政治的“权威”之间的传统两分法已经失去部分效力,(2)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8页。而多边主义与国际机制等概念的提出或再定义则为填补“国际政治与正式组织安排之间”的鸿沟提供了可能。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较早对多边主义作出界定,他认为多边主义是协调三个或以上的国家政策的实践活动。(3)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0, 45(4):731.随后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对多边主义进行更精准的界定,他表示多边主义的特质“不仅仅在于其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组成的国家团体的政策——这些其他组织形式也在做的事情,同时也在于它是在调整这些国家间关系的一定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协调活动。”(4)[美]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载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苏长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詹姆斯·卡佩拉索(James A. Caporaso)进一步为多边主义研究出一套成熟的衡量标准(5)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an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la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2, 46(3):601-602.:一是非歧视性。各成员国的法律地位具有非等级性与非歧视性,任何成员国不享有凌驾于其他成员国之上的特权。二是不可分割性。不可分割性体现整体利益,它是一种社会构建,不是一种技术性的状态,不考虑在任何特定时间下忽视甚至牺牲某些成员国的利益以达到目的。三是扩散的互惠性。成员国之间所达成的协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以往会在量上给它们带来大致平等的收益。
二战后的多边主义和美国主导的多边制度被直接划上等号,任何美国模式以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都被严重边缘化,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引发的政治极化打破了之前二者的高度重合。(6)李晓燕:《多边主义再思考与世界秩序重构》,《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6期。美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扎根于二战后支撑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制度体系,这也能解释为何所谓的选择性多边主义、小多边主义等“伪多边主义”理论内核还是对原有制度体系内进行修补或改革,并未考虑霸权国推进路径之外的其他选项。(7)David A. Lake, Lisa L. Martin, Thomas Risse, “Challenges to the Liberal Order: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1,75(2):247.这些伪多边主义理论意指一些行为体将焦点从已有制度转移到另一制度上又或重新建立新的多边制度挑战现存多边机制的规则,使全球治理中出现了“制度嵌套”(nesting institutions)、制度重叠(overlapping institutions)和制度复杂性(institutions complexity)(8)参见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叶成城:《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当代亚太》2020年第1期;Andrew I. Yeo, “Overlapping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Determinants and Potential Effec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018,18(2):161-191;Howard Loewen,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GIGA Working Papers, 2006, No.17,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47789/1/604938888.pdf.等理论困境。
多边主义理论发展是动态的,必然受到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可以看出,主流的多边主义理论已无法有效地解释和解决新时期的全球性问题。理论困境之一是现有多边主义理论过分注重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并没有提供一个能理解制度竞争的完整理论范式。其叙事逻辑既不是商讨以协调和合作为实质特征的多边主义,也不是对各制度能和平兼容的战略考量。这种叙事逻辑一方面夸大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多边主义制度的优势,更是为了契合制度主导国或霸权护持的战略需求,容许主导国随意更改规则或排除成员国的行为;另一方面当新兴国家对旧理论和规则提出更公允或更合理的修改时,却被斥责为现行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9)宋伟:《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行为与国家》,《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3期。将冲突视为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本质和世界发展动力,是西方学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将主导国和新兴国家置于冲突辩证法的认知框架中,势必强调其对立性和冲突性,在这种思维定势导致的认知框架中,多边主义理论很难得到良性的提升。
理论困境之二是现有多边主义理论沦为霸权国私有化的工具属性明显。多边主义理论既为一个国际制度的成员国提供了平等普遍的公共服务,又被制度主导国“私有化”为特殊性的权力对象,私有化的多边主义理论为制度主导国提供制度性霸权的基底。从历史分析发现,二战后国际制度的维持实质上是美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种交易。多边主义制度为制度主导国赢得的制度红利(10)汪海宝、贺凯:《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外交评论》2019年第3期。(institutional dividends)是通过制度赋予国家的权利增加收益、降低霸权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同时也是将权力转化权威的一种方式,是保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表象。苏姗·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曾说过,国际制度霸权就是一种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如何办事的权力”,它是美国霸权得以维持并降低衰落速度的一个重要支柱。(11)[英]苏姗·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
理论困境之三是现有多边主义理论解决全球治理议题方面的效能降低。一旦制度体系中多个核心制度同步滞转,会催生碎片化的小多边机制、新旧制度替代等现象,使整个制度体系呈现竞争性多边主义,从而导致原有秩序架构摇摇欲坠。(12)刘昌明、杨慧:《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4期。所以当IMF和WTO等多边组织功能性不足、各国的自身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时,选择性或小多边主义成为制度主导国填补国际机制有效性和合法性真空的工具。要想有效推动国际秩序改革走向深入,美国唯有抱持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灵活性,在制度关键决策中更尊重其他主要大国的意见(而这通常也意味着“去美国化”),从美国学者角度看,这最终将侵蚀美国对现今自由秩序的主导权。面对两难困境,美国一般会采取两种方式应对:第一种方式是以退为进,秩序主导国主动退出现有多边制度。例如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威胁退约及对各种多边制度的退出亦是如此。第二种方式是拒绝批准或加入由新型大国发起的新制度,否认新制度的合法性,转而更专心地建立自己与其他盟友的“俱乐部”。拜登政府现在主导的国际组织和规则的主要方式已由开放的“全球模式”,转为排他式、精英主义式的“俱乐部模式”(13)参见陈庆鸿:《当前亚太小多边合作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Chris J. Dolan, “Selective Multilateralism: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Emerging Post-9/11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3, 40(3): 425-431;Jeff D. Colgan and Robert O. Keohane, “The Liberal Order Is Rigged, Fix It Now or Watch It Wither”, Foreign Affairs, 2017, 96(3);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Robert O. Keohane(ed.),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Routledge, 2002., 衍生出美式“小多边主义”这类向单边主义理论发展的“伪多边主义”,让全球治理愈发走向失衡。
二、美国“伪多边主义”的现实危害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这也说明近年来一系列经济、卫生、环境、能源与数字空间等领域的危机事件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缺陷,增加了我国维护多边主义的难度。针对复杂的世情,须揭开重重迷雾披露问题本质,为多边主义的真实内核正本清源。
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4)《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这明确了真正的多边主义所涵盖的基本原则,为各国鉴别和实践多边主义指明了方向。2021年拜登政府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多边主义似乎呈现了一个回归之势,从宣布美国重回巴黎气候变化协议、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撤回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等,(15)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拜登有意向世界表明新政府重回多边主义、重建美国全球领导权的决心。但从当前来看,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外交还是试图继续维持自身在旧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新政府更多是打着多边主义旗号行“伪多边主义”之事。(16)《“美国优先”是对多边主义的最大伤害——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力事实》,《人民日报》2021年7月27日。
首先,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只能导向有限的多边主义。美国的核心外交思想是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其主张的全球治理中内嵌着一种“制衡意识”,笃信它的道路可以重塑人类命运。(17)董贺、袁正清:《中国国际秩序观:形成与内核》,《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7期。美式外交理念主要以管制和同质化为目标,缺乏包容性与灵活性,与中国的外交思想大相径庭。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核心,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强调不能把西方价值观视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而美国的多边主义常常以“民主改造”为使命,将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非西方国家视为救赎的对象,借以传播美式普世价值,引导其他国家学习美式价值观。
拜登政府的“伪多边主义”外交是依托“新”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呈现出来的,制度制衡是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通过多边机制追求影响力等议题的一种新型制衡方式。(18)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8, 14(3):489-518.与前两任政府不同,拜登政府一边喊着与奥巴马时期全球主义同源的“多边主义”的口号,一边采取比特朗普更严重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新政府的外交理念具备强烈利益导向,意在弱化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权威性。比如美韩首脑级会议声明中反对一切威胁或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行为”(19)“U.S.-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May 21,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5/21/u-s-rokleaders-joint-statement/.,规则是美国率先制定,维护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目标直指中国。它极为强调西方“普世价值”的绝对性,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和对抗性,遵守少数国家构成的“俱乐部”制定的“规则”而非国际普遍遵循的规范。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的:“‘小圈子的多边主义’仍是一种集团政治。”(20)《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21年3月8日。
其次,美式“小集团”模式导致全球治理共识的弱化。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大国更应该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不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而二战后美国先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自诩多边主义的天然主导国和全球治理的现状定义者。进入千禧年后,一旦制度不再符合其利益,美国则扮演制度破坏者的角色,多边主义在美国霸权影响下具有浓厚的工具性色彩,美国可以根据自身利益改变原有多边框架内的议题。(21)Stacie E. Goddard, “Embedded Revisionism: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Challenges to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8, 72(4):765.这种“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à la Carte)在美国历届政府中屡有体现,使得国际规则丧失其原有的功效,沦为美国的工具。
拜登政府及其盟友对自身利益的优先追求等因素破坏各国间的信任基础,利用盟友打压中国,追求“情景式”联盟孤立中国的企图和行为,是恶化国际环境的罪魁祸首。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认为各个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能够参与全球性的多边制度,并有自己的发言权,共同决定多边事务。(22)陈志敏:《真正的多边主义的理论内涵》,《人民日报》2022年1月17日。但拜登政府从执政以来就在逐一确定支持美国方案的“盟友”定位与责任份额,强化对盟友的差异化的“责任分担”理念,煽动盟友建立排他性的“小集团”。相较于之前单一的全面反制中国的联盟,美国根据不同国家对中国的差异化担忧,建立多层次、有针对性且灵活性的“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以美日澳印(QUAD)为核心建立多层次议题联盟,其中美日同盟尤为重要,美国深知日本对周边安全领域的重视,积极怂恿日本加强与“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在欧洲,美国鼓吹“共同价值观”,在拜登访欧之行后,北约更是首次宣称中国是“系统性威胁”,愿意参与对华制裁。在中亚、南亚、非洲等地,美国新增人手调查中国投资的港口、交通设施、能源产业等,离间发展中国家对华关系,重新重视这些地区的支点作用。(23)Jared Cohen and Richard Fontaine, “The Case for Microlateralism: With U.S. Support, Small States Can Ably Lead Global Efforts”, Foreign Affairs, April 29,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4-29/case-microlateralism.新的差异化联盟利用盟友在多边制度中的不同维度围堵中国,阻碍新兴国家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佼佼者。
再者,议题联盟加深全球治理议题的碎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24)《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不少学者认为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当一些成员国对某项议题产生了利益诉求,既有制度中无法实现充分利益供给,成员国会将关注点从一个已有的制度转移到另一制度上,或新建一个替代性的多边制度。(25)参见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史田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议题联盟”行为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3期;Randall Schweller, “Opposite but Compatible Nationalism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8, 11(1):32-46;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Governing the World in a Post-Hegemonic Er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 16(3): 399-413;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14, 9(4):385-412.议题联盟现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行为中的一种“新常态”,主要原因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在具体议题上遇到挫折,而是其话语权的权威性下降,无法解答当前世界遇到的新挑战。例如在规则竞争领域,美国对IMF改革采取消极态度,在金融议题领域,中国创建亚投行又被视为在“修正主义”式地挑战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制度的地位和话语权。当中国的优势不断显现,美国对中国在不同议题中攀升的地位和话语权的上升倍感焦虑。(26)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作为资深民主党建制派人士的拜登一直是价值观外交的坚定拥护者,因为民主党领导人在共同议题立场上具有一般性的集体趋同,通过唤起群体利益来吸引他者。(27)[美]迈特·格罗斯曼、戴维·霍普金斯:《美国政党政治:非对称·极端化·不妥协》,苏淑民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249页。拜登在上台前就高举“民主国家联盟”的旗帜,宣称要与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密切合作,以占据全球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体量形成“规则联盟”和具有“普遍韧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应链联盟”,从而强制中国接受符合美国与西方利益的改变。(28)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21年3月发布的报告称将与盟友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向中国施压,以“人权”为由抵制中国新疆出产的棉花。(29)202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0 Annual Trade Report,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March 2021, p.5.这种议题联盟形式可以充分发挥联盟的功能性优势,实现特定议题的利益最大化。
同时,拜登对过去的板块式的、僵化式的联盟进行修改,努力想将多边合作变为具有议题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拜登政府认为世界具有领先技术的民主国家应该为美国及其盟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到来前争夺新科技霸权,有必要建立“技术多边主义”下的“技术联盟”。“技术联盟”是以“小院高墙”为原则的选择性脱钩策略,设立以5G安全规则、半导体管控、联合人工智能和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北约同盟组织”。科技产品供应商被安上不同的政治标签,划分为不同安全信任等级,形成“分层金字塔”式的供应链梯级,跨层次流动基本被阻断。(30)唐新华:《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拜登政府还要求盟友禁止使用华为与中兴通讯的设备,企图将高科技创新限制在同层流动,对供应链中的高技术要素流动形成“硬性”的约束条件。(31)Ryan Hass, 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拜登政府的价值观联盟和技术联盟分化地区供应链和经济一体化,导致非传统安全领域意识形态化更甚,造成全球治理局面更加碎片化。
三、多边主义的中国方案
全球疫情大爆发引发的经济、社会和治理危机,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疫情过后各国必定会对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和现行全球治理秩序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反思。随着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原有的美国霸权体系下形成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符合国际关系现状,排他、孤立和分裂只会导致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因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变得更为严峻。突破西方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方案,是中国向世界传递出“更团结”和“一起向未来”的强烈信号。
(一)中国推动多边主义建设的主要路径
中国是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积极担当负责任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为多边主义守正出新贡献新理念和新方案:从2013年的“命运共同体”到2015年的“五位一体”的总体路径,从2017年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总体布局,到2020年倡导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再到2021年提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在丰富多边主义的内涵和实践版图中与时俱进,不断拓展,为全球治理指明前行方向。
从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愿景看,我国一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共商共治的价值理念。从最初的主动融入,到面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乃至新近创建的“群”——中国始终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前提下,坚持多边、开放、共享等原则,在不取代现有国际机制、不搞小圈子的基础上实现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在2022年的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32)《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光明日报》2022年1月17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找到应对并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正确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中国醇厚的传统文化为价值观超越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包容性多边主义,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边主义价值期许。这超越了西方多边主义理论的“表象性偏见”,体现了多元性特征,为全球治理开辟新的道路。
从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愿景看,中国一直向世界传达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中国超越了传统的同盟关系,坚定地在周边和全球开展伙伴关系的实践,推进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型国际关系,而不是建立“找敌人”的同盟关系,这是对二元对立观的超越。尤其在疫情蔓延的两年多,中国以行践言,以行动推动合作共赢,扎实地践行“要疫苗多边主义,不要疫苗民族主义”(33)《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1年8月6日。的呼声。中国不仅以实际行动打造了疫情防控的全球样板,而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树立起团结抗疫的标杆。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价值旨归,中国努力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迄今已供给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超过20亿剂疫苗。(34)《中国疫苗,为人类健康构筑“免疫长城”》,《人民日报》2022年1月20日。作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树立了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团结抗疫的标杆,为弥合“免疫鸿沟”贡献了中国力量。
从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愿景看,我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由接受者、参与者到倡议者、主导者的角色转换,凸显中国作用和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构建新型全球治理的大国责任,是中国参与多边主义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以与世界接轨的开放理念为行动遵循,以最广泛的国家和地区为合作对象,努力达成治理规则的对接,致力构建一个兼具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特质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从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1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相关合作文件,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地,丰富了多边主义的内涵和实践。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投行等多边机制有效运行,成为现有国际机制的新生力量。亚投行先后进行多次扩员,现今成员数量增至104个,其中贷款前四位用于南亚、东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使既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体系得到了改造和完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定的国际金融机制与规则也是充分认可的。
从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愿景看,我国历来抱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初心与各国进行相互尊重、平等的交流。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到中国—拉共体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的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充分诠释了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的理念。如中国助力非洲工业化和深化基础设施合作、加强金融合作和分享减贫经验等,都是切实地帮助非洲经济发展创造内生动力。2021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的规划下,共同实施以卫生健康、数字创新等“九项工程”,(35)《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非合作论坛》2021年11月29日。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凝聚力量。随着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与大国命运共同体携手并进,一个更宏大更整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初具规模,在这个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作为纽带之一,不断扩展与全球的联结。
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愿景看,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一方面大力帮助和扶持那些生态环境脆弱以及环境治理能力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也向国际社会提供从议题议程设定到制度政策设计的中国方案。2020年12月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到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减排、非化石能源发展等目标;2021年10月,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及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1+N”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同时,中国还秉持“授人以渔”的理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支持。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的节能灯,中国的绿色行动为加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强大动力。
(二)守正出新的中国方案
2017年习近平主席达沃斯演讲的核心是阐明中国如何看待和推进全球化的时代潮流,2021年演讲的重点是中国主张维护和践行什么样的多边主义,2022年演讲的主题就是如何开辟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36)《把握时代之变,擎画人间正道》,《光明日报》2022年1月18日。之前的全球治理模式与道路显然已无法解答正在成为现实的“人类世” (Anthropocene)的各类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成为应对的最佳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类整体高度看待国际政治,着眼于当前现实世界的重大变化,其出发点和最终形成的新型国际规范正契合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国际社会将基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实和共商共治的方式,进一步发挥联合国及所有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制度的作用,大力促成国与国平等共处、推动形成在联合国多边制度及国际法基本规则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从而实现中国推动多边主义的最终价值追求,也是回答时代、世界和人民三问的意义所在。
第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代替“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本质上是地域性认知与实践,以绝对的普遍性为方法的唯心主义价值观,着“价值”之衣行“真理”之事,无视主客观差异性和具体历史条件。(37)郇庆治、赵睿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及其时代拓展》,《党政研究》2021年第6期。更重要的是,“普世价值”并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是深度浸染于西方意识形态,为全人类预设了“欧美模式”的普世前景,即存在一种假设,西方目前的方向,是各国都应该努力去追求的方向。与之相反,我们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要把中华文明自身的价值观与发展模式强加于人,而是要加强跨文明交流,促进跨国家理解,一起面向全人类的共同未来。我们的多边主义是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而不是某一个或者少数国家的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把西方和非西方都包括在内的“以关系改善和互惠建构”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制度安排。作为主场外交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过和平良性竞争来团结世界,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也是中国向世界传达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核。世界各国运动员和各国政要齐聚北京,参加冬奥会和出席开幕式,既是对奥运会的重视,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第二,以多元主义代替“霸权治理”。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领导构建的自由主义秩序,是一个等级性的政治秩序,美国在这一秩序中享有绝对支配地位,而其他国家被赋予了搭便车的权利。美国的全球治理是基于西方理念和经验,与后殖民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多元诉求的现实不相符,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当新兴国家群体出现时,“霸权—多元化”的鸿沟更加突显。而多元主义是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的,是面向世界各地的历史和文化,不是仅仅依赖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国提出的多边主义理念强调立体多维的关系网络,(38)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8页。这个关系网络存在不同的关系者,每个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倡导“同舟共济”“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理念,展现我国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和多样性。“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39)《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伴随中国实力的不断跃升,中国逐步加大了对新型多边制度的投入力度。面对新的复杂性的全球治理问题,“一带一路”倡议融合了不同体制、相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需求,具体提出“创新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多边主义方案,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呈现发展中国家应对复杂的全球治理问题的新成果。
第三,以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代替“利益攸关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意味着多边主义中的各个行为体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受利益驱动的“理性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的思想根源鼓励各国参与国际社会活动,参与国际制度设计、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在合作中塑造集体身份,增强伙伴感,而不是成为现有国际规则的被动“攸关方”。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是多边主义区域化的体现,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它有效破解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困境,为差异化程度较高的亚太各国搭建有效协作的制度性平台。它的许多制度设计的灵感来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例如提倡发展优先、普惠包容的理念。其中以发展为导向的规则强调差异性,关注成员国的个体发展需求;以标准为导向的规则兼容统一性和包容性,强调对标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它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推动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多边主义机制的发展提供新思维。
第四,以面向未来的和平与发展代替“大国战略竞争”。中国构想的未来多边主义及全球治理构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前瞻性,如数字技术、开放创新、绿色发展等,既能把握时代的变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指向未来的技术方向与发展理念。这些理念相较于国际规则体系原有的丛林价值理念,更多地瞩望和平与发展,更大地化解其中的“冲突”与“竞争”,并形成一对可推动当前多边主义继续发展的动态关系。(40)徐坚:《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笔谈》,《国际展望》2021年第5期。如中国2021年底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协定》(DEPA),表明我国愿意在数据领域进一步向成员国开放,也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数字鸿沟。中国是目前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最快、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丰富的运营经验的国家。中国不仅可以助力发展中国家消除空间中的数字鸿沟,更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这说明中国的多边主义敏锐把握时代动向,走在时代的前列,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结 语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美国的伪多边主义行径等多重要素共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合作面临多重危机。中国一直秉持多边主义原则立场,以切切实实的意愿、能力和行动参与全球发展合作,与国际社会一起探索应对新挑战的全球治理机制。拜登政府对多边主义的有限回归,给原本就“机制拥堵”的国际多边制度平添了大国间竞争的阴霾,中国的包容性多边主义才是合理适当的多边制度形态。真正的多边主义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美国主导的制度形式,不应局限于旧有的制度和组织,而应是有效促成合作的原则框架。中国要清晰而坚定地向国际社会传达自己的行为逻辑,从而破解被动应答的状态,争取行动的话语权优势。中国提出的多边主义理念是对当前全球治理秩序之争的超越与升华,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构建更加成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多边主义理论和全球治理实践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