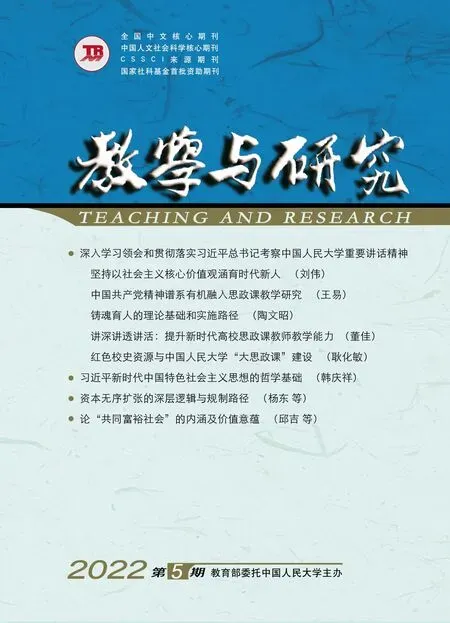信息技术条件下生产网络的特征与影响
——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
秦 臻,王生升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生产网络逐渐成为生产组织的新形态,这不仅有力推动了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变革,而且深刻重塑了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方式。生产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日益加速的生产集中化发展趋势。生产的分散化现象日趋明显,垄断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并攫取利润的形式相应地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新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获得了更具现实性的可能空间。以生产网络这一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为切入点,分析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推动的组织变革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变化的影响,既有助于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更有助于我们以之为借鉴引导和规范资本增殖和积累的运动,加快并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生产网络是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生产组织新形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网络”(network)逐渐进入理论界的研究视野。卡斯特将网络定义为相互连接的节点(nodes)的集合,这些节点为实现网络的整体功能和目标所必需。作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结构,网络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随着内部节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Manuel Castells,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51(1): 5-24.以计算机互联互通形成的技术网络为基础,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形成了经济网络。(2)杨志、赵秀丽:《网络二重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解——网络经济与生产方式关系研究系列之一》,《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网络。随着一些行业(如汽车行业、电子行业)率先取得了生产组织的网络化变革,理论界也开始以“生产网络”来描述不同经济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基于不同方向的复杂联系,通过持续互动所建立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网络化组织结构。(3)Peter Dicken et al., “Chains and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Scales: Towards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 Networks, 2001, 1(2): 89-112.(4)Timothy J. Sturgeon,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2, 11(3): 451-496.
当前,生产网络已经成为生产组织的一种普遍形式,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同学者对不同具体形态的生产网络作出了考察。例如,托尼·史密斯以“精益生产网络”(lean production networks)来描述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和不同级别、不同大小的供应商、分销商所共同组成的一种生产和分销系统。精益生产网络以“准时生产”(just-in-time)制度为基础,能够消除不必要的库存,保证供应商和分销商准时交货,并且实现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5)Tony Smit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Lean Production: A Marxism Critique of the “New Econom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0.史特金重点分析了美国电子行业基于模块化技术和设计原则所形成的“模块化生产网络”(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这种组织模式改变了既有的垂直整合的工业组织传统,能够有效地应对市场需求不稳定等外部条件的变化。(6)Peter Dicken et al., “Chains and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Scales: Towards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 Networks, 2001, 1(2): 89-112.(7)Timothy J. Sturgeon,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2, 11(3): 451-496.派尔和赛伯(8)[美]M.J.派尔、C.F.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李少民、刘英莉译,林剑秋校,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哈里森(9)Bennett Harrison, 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rporate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 The Guilford Press, 1994.分析了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形成的包括众多小企业在内的生产网络,即“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这些产业区在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失业率等方面较之意大利的其他地区都有更良好的表现,因而也被称为“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亨德森等(10)Jeffrey Henderson et al..“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c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2,9(3):436-464.、赵秀丽和段晓明(11)赵秀丽、段晓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资本关系的演化——基于资本运动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谢富胜和黄盛(12)谢富胜、黄盛:《全球生产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8期。考察了跨国公司编织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指出全球生产网络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同时内含着深刻的不平等特征。
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生产组织方式在数字信息时代的新演化趋势。在生产网络出现以前,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化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被加以集中和扩大,并成为强有力的生产杠杆。(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列宁指出,“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14)《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2页。。此后,集中化的大企业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方式,基于规模效应形成的竞争优势使之成为所在行业的主要供给者,大企业的规模生产日益成为整个产业供给的代名词。但是在数字信息时代,集中化的大企业日益让位于多主体协作的生产网络模式,中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产业链主体,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从单个企业组织扩展为不同生产单位共同构成的产业组织,这使得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化表现出新的分散化趋势。
事实上,生产网络是大企业分散化改组的产物。对于大企业而言,通过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而形成的规模优势既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也是实现和维持垄断地位的基本前提。但随着规模的持续增大,大企业的组织弊端也得以显露,尤其是内在的僵化性使其难以灵活地应对外部市场条件的变化。在20世纪前半个多叶,流水装配线成为大型工厂运转的主要技术基础。流水装配线的应用起于美国的亨利·福特在汽车生产过程的引入。随着整个生产过程被分解为简单步骤,同时采用了精确的、标准化的零部件和易于操作的机器,汽车生产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15)[美]M.J.派尔、C.F.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李少民、刘英莉译,林剑秋校,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22、341页。(16)[英]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主译,沈宏亮、沈尤佳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4-285页。这种生产模式开启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并且促进了欧美国家的战后繁荣。但流水装配线生产出来的多为标准化产品,并且要进行不同产品的生产转换通常需要调整或改装机械设备才能实现。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欧美国家福利制度下工人收入的提高,市场需求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流水装配线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便难以为继。(17)[美]M.J.派尔、C.F.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李少民、刘英莉译,林剑秋校,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22、341页。(18)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23-226页。此外,由于大企业多为金字塔型结构,其内部的管理等级制逐渐深化了官僚主义作风,这导致了信息沟通不畅,降低了组织协调和运转的效率。(19)[加]罗伯特·W.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而20世纪70年代危机又导致了欧美国家企业利润率的大幅下降。(20)[美]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王生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在此背景之下,集中化的大企业便开始了生产经营的弹性化转型之路。
组织重组是大企业弹性化转型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为大企业重组提供了技术上的契机,特别是网络技术和模块化技术成为变革生产过程的重要突破。其中,网络技术是各种电子技术在通信领域汇聚结合的产物,进而产生了互联网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媒介。(21)[西]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2-53页。“模块化”(modularity)技术则使许多复杂系统的分解与重构成为可能。(22)根据鲍德温和克拉克的定义,模块是系统中的单元,不同的模块在结构上相互独立,但它们能够共同发挥作用。参见[美]卡丽斯·鲍德温、金·克拉克:《设计规则:模块化的力量》,第1卷,张传良等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55页。青木昌彦指出,模块化包括“模块分解化”和“模块集中化”两个过程:模块分解化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分解为可以独立设计的半自律的子系统(即模块);模块集中化则是将这些子系统再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统一起来。(23)[日]青木昌彦:《产业结构的模块化理论》,载[日]青木昌彦、安藤晴彦编著:《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周国荣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3-27页。不同模块之所以能够重新组合,在于标准化接口(standardized interfaces)的设计。(24)Richard N. Langlois, “Modularity i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2, 49(1): 19-37.借助于模块化技术,原本在大企业内部生产的产品就能够分解为不同的零部件或子产品,并分别由不同的生产单位进行生产;依托于网络技术,这些企业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协调,最后再对零部件或子产品进行多样化的整合。由此,大企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便得以分解与重构。
以网络技术和模块化技术为条件,大企业进行了分散化改组,特别是通过生产外包将非核心的生产流程或业务剥离出去,而仅仅保留核心功能。这使大企业不仅实现了组织精简,由等级森严、僵化的组织转向更小规模、更具灵活性的组织,而且能够“回归核心竞争力”或实现“精益生产”。(25)Bennett Harrison, 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rporate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 The Guilford Press, 1994, p.40.(26)Tony Smit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Lean Production: A Marxism Critique of the “New Econom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0, p.38,p.183.(27)Jeffrey E. Lewin and Wesley J. Johnston, “The Impact of Downsizing and Restructuring on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mpetitiveness Review, 2000, 10(1):45-55.由于大企业的供应商同样会继续进行分包,因而能够形成层层分包的生产体系,例如丰田汽车就拥有大约十层不同级别的供应商。(28)Tony Smit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Lean Production: A Marxism Critique of the “New Econom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0, p.38,p.183.(29)Jeffrey E. Lewin and Wesley J. Johnston, “The Impact of Downsizing and Restructuring on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mpetitiveness Review, 2000, 10(1):45-55.这一过程同时为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许多小企业作为大企业的供应商而繁荣起来。(30)John H. Dunning, “Reappraising the Eclectic Paradigm in an Age of Alliance Capit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5, 26(3):461-491.(31)R.F. Imrie, “Work Decentralisation from Large to Small Firm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Subcontract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6, 18(7):949-965.经过大企业的分散化改组,各生产单位之间虽然表现为分散化生产,但能够基于一定的合同约定共同完成一种最终产品的生产甚至销售,因而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个既松散又紧密的新型整体结构。这种新型的组织方式打破了原来由单个企业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的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这些生产单位之间既建立了纵向的生产上下游关系,也形成了横向的工序或职能分工,使得组织整体呈现出纵横交错的复杂网络形态,即形成了相对扁平化的生产网络。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突破也使生产网络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数字化变革中,提取、分析、使用海量数据的数字平台成为中介整个生产过程的关键基础设施。数字平台能够将包括生产商、供应商、广告商、客户等不同的群体聚集起来并使其得以互动。(32)[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9-50页。在数字平台的中介作用下,企业内部、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信息流动和资源协调得到强化,生产经营活动得到了更深层次的网络化整合。(33)Javier Cenamora, Vinit Paridab and Joakim Wincent, “How Entrepreneurial SMEs Compete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The Roles of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y, Network Capability, and Ambidexterit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9, (100): 196-206.依托数字化技术,生产经营活动经常被分解为极其分散且疏远的微型任务(micro-task),散布在全球各地的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一系统中的“独立承包商”,这就形成了“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即外包关系在数字化时代的新形式。(34)Aurélien Acquier, “Uberization Meets Organizational Theory: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the Putting-Out System”, in Nestor M. Davidson, Micheèle Finck and John J. Infranca(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haring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3-26.(35)Matthieu Montalban, Vincent Frigant, and Bernard Jullien, “Platform Economy as a New Form of Capitalism: A Ré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amm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43(4): 805-824.伴随着这一过程,数量众多的个体劳动者大量涌现,这既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生产分散化和小型化,也使得生产网络更加扁平和灵活。
二、垄断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形式发生历史性变化
在生产网络产生之前,具有规模效应的大企业是垄断资本攫取垄断利润的基本载体,并以此实现对整个产业的控制。生产网络的出现,没有改变垄断资本控制的实质,改变的不过是控制的具体形式。相较于大企业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生产网络是一种更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部没有分工等级制度。如前所述,大企业在分散化改组中通常将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等技术或资本密集型活动保留下来,而将制造、加工等低技术环节或劳动密集型活动外包出去,这就形成了大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分工等级差异。另外,大企业虽然缩减了自身的规模,但相对于小企业仍然具备较强的规模优势。在很多情况下,一定的资本规模仍然是维持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许多高技术产品行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需要巨额的资本投资,中小企业就难以胜任。(36)John Smith,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230.
以分工的等级关系为基础,大企业和中小型生产单位之间形成了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是决定整个生产过程如何安排的重要依据。由于具备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的优势,除非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大企业在外包关系中基本都明显居于更主动的地位。小企业经营业务单一,并不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和资金条件,则经常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37)M.J. Taylor and N.J. Thrift, “Industrial Linkage and the Segmented Economy: 1. Some Theoretical Proposal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2, 14(12): 1601-1613.由于仍然垄断着整个生产过程中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等关键环节,大企业实际上构成了生产网络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关键节点。
作为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大企业不仅改变了以往集中化生产的垄断模式,而且通过层层分包体系获得了对更大规模的资本的支配权力。在生产网络的不同分包层级中,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等级关系都有所体现,而依托层层分包体系,大企业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就能够直接或间接支配更多的生产单位,从而能够控制远大于自身规模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大企业还会选择自身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作为承包商,即掌握着后者一定的股权份额。这时,就法律方面而言,这些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是独立的法人,能够以自身的名义从事经济活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但在经济方面,发包大企业能够直接以大股东的身份实际控制子公司的经营决策等活动;对于被持有少量股权份额的关联公司,发包大企业通常也能够通过垄断技术、销售渠道甚至资金等来获得一定的支配权。(38)林康:《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1页。因此,尽管生产网络中生产的分散化实质上是资本所有权的分散化,但这并没有否定控制权的集中,构成关键节点的大企业反而以更小的生产规模控制了更多的经济活动。
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就充分体现了垄断资本的这种控制形式。以信息、交通运输等技术的变革为条件,跨国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跨国生产转移。通过计划、指导、协调等手段,跨国公司的总部将位于世界各地的研发中心、生产工厂以及销售市场联系起来(39)Dan W. Nabude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Its Theoretical and Polemical Treatment from Mercantilist to Multilateral Imperialism, Zed Press, 1977, p.250.,形成了在全球范围运转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就是相对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但仍然内含着明显的分工等级制度和与之相对应的权力等级体系。跨国公司通常控制着研发、设计、营销等关键环节,垄断着核心部件的知识产权,并且能够负责制定技术和产品的标准,因而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而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往往被分包给发展中国家的承包商。基于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等级差异,这些承包商与跨国公司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权力不对称关系,并且往往依附于跨国公司。(40)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与此同时,在跨国外包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同样经常会选择自身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作为承包商,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进行国外直接投资。作为母公司或股东,跨国公司能够直接依托股权关系实际控制或影响与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之间的分工格局、产品交换、利润分配等各个方面。(41)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W. McChesney and R. Jamil Jonn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2011, 63(2): 1-23.通过国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还能够利用东道国提供的吸引外资的特别税收优惠,并且获得更多的海外市场份额。(42)Bennett Harrison and Barry Bluestone,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Basic Books, 1988, p.48.除此之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非股权模式(non-equity modes)的跨国外包活动,将生产活动直接外包给东道国的本土企业或者其他跨国公司的当地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即进行独立外包(arm’s-length outsourcing)。这时,跨国公司还能够避免由于股权关联而产生的风险,在污染、压低工资、抑制工会等方面做到“推卸责任”。(43)John Smith,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p.79-84,p.82.在市场风险发生时,非股权外包模式还能使跨国公司更为迅速地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地点而不需重新投资设厂。(44)Intan Suwandi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 Monthly Review, 2016, 68(3):114-131.近年来,这种非股权模式的独立外包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跨国公司所采用。(45)John Smith,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p.79-84,p.82.而通过层层分包体系,全球生产网络实际上呈现出“核心—外围”式的整体结构,构成关键节点的跨国公司居于核心地位,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居于外围的承包商。
而在数字化变革的背景之下,掌握数字平台的工业巨头获得了行使垄断权力的更有利的技术条件。在工业领域,数字平台的引入使“工业互联网”得以产生。在工业互联网中,传感器和计算机芯片被嵌入生产流程,跟踪器被嵌入物流过程,由此,整个生产过程的每个组件都能够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并进行通信,有关生产和物流的状态的数据也能不断被共享。目前,通用电气、西门子等老牌工业巨头都致力于开发自己的工业数字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位于全球的软件开发商、工厂、消费者等不仅更为有效地被连接在一起,而且生产网络中每一个节点的运作情况都能够被有效、及时地监控。(46)[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76页。此外,在众包模式下,许多数字巨头将除了数字研发、营销等关键业务的其他活动都进行了外包,自身则成为签订合同、进行算法处理等活动的中介,并实际构成了网络中一个灵活的中心。(47)Aurélien Acquier, “Uberization Meets Organizational Theory: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the Putting-Out System”, in Nestor M. Davidson, Micheèle Finck and John J. Infranca(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haring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3-26.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所有权进一步分散化,但构成关键节点的平台巨头仍然主导着整个网络,众多的个体劳动者被纳入了垄断资本的势力范围。同时,平台巨头与个体劳动者之间不仅没有所有权关联,而且不存在正式的雇佣关系,这使得垄断资本不用承担相关风险责任而行使控制权力的情况得到进一步强化。(48)K. Sabeel Rahman and Kathleen Thelen,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2019, 47(2): 177-204.
三、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在弹性雇佣模式中得到强化
伴随着技术进步,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不断加深,这一方面源于机器替代活劳动所造就的庞大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更源于机器大工业体系对活劳动的局部化分解和去技能化效应。马克思曾指出,在机器大工业时期,机器挤进了生产过程,简单劳动逐渐代替了复杂劳动,非熟练工人逐渐代替了熟练工人,这降低了大量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使之更容易受到资本的支配。(4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290页。布雷弗曼对垄断时代大企业劳动过程的考察表明,不管对于车间的体力劳动还是对于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劳动过程的不断分解都强化了劳动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能力及其增殖能力相应地得到加强。(50)参见[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生产网络的出现和发展将大量中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纳入生产体系,生产组织方式因此表现出分散化趋势。这无疑促进了生产要素结合方式的创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再局限于企业组织形式,而是日益采取产业链协作的行业组织方式。由于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没有改变,因此,更为灵活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客观上赋予资本以更大选择权,由此形成的弹性雇佣模式进一步提高了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
事实上,伴随着大企业向弹性化转型,稳定的雇佣模式就开始逐渐转向兼职、临时合同等不稳定的雇佣安排。阿特金森指出,在弹性转化转型中,企业寻求三种弹性:功能弹性(functional flexibility)、数量弹性(numerical flexibility)以及财务弹性(financial flexibility)。(51)John Atkinson, “Manpower Strategies for Flexible Organisations”, Personal Management, 1984, 16(8): 28-31.哈里森进一步指出,功能弹性是指经理人重新部署资源,重新安排工作任务,或者重新调整与供应商的关系;数量弹性是指经理人重新进行雇佣安排,以合同工、兼职工、临时工等来代替福利健全的全职员工;财务弹性(或称薪资弹性,wage flexibility)则指经理人采取各种方法提高工人之间的竞争程度,以节约薪酬和其他雇佣成本。(52)Bennett Harrison, 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rporate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 The Guilford Press, 1994, pp.129-131.正是基于这种弹性追求,企业开始采取一种弹性雇佣模式,将劳动力区分为核心群体和外围群体。其中,核心群体掌握着较高水平的知识或技能,执行企业内部关键的、特有的活动。他们是全职、永久型的员工,一般由经理、设计师、技术人员等组成,有助于企业实现功能弹性。外围群体的工作保障水平相对较低,职业机会较少,流动性较高,有助于企业实现数量弹性和财务弹性。此外,企业还会采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自我雇佣者或专业承包商,这有助于企业实现更大的功能弹性。⑦
20世纪70年代危机以后,利用劳动力过剩和工会力量减弱的机会,资本大力推行了这种弹性化的雇佣模式。(53)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p.150.在外包过程中,大企业不再维持内部稳定的雇佣关系。(54)Bennett Harrison, 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rporate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 The Guilford Press, 1994, p.130.而随着外包制度的发展,大企业内部的核心劳动力数量还呈现出缩减趋势。在日本的丰田精益模式建立之初,大企业还保持着内部核心劳动力群体的就业。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大型汽车总装厂就修改了丰田模式中的“终身雇佣”制度,不再在自身内部保障核心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而是使他们在整个企业集团(如总装厂及其主要供应商)内部流动。欧美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习日本的精益生产模式时,也只是学习了日本企业的成本削减措施,并没有承诺保障核心劳动力的工作,这大为削弱了工人对资方的谈判能力。实际上,这种精益生产模式已经越来越演化成为“精简”(lean and mean)生产模式。(55)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2-71.
家庭代工和个体劳动者的日益增多,同样是弹性雇佣模式的结果。在生产网络中,中小企业经常会将承包活动继续进行分包,特别是将很多劳动密集型或专业技能型的工作转移至外部家庭工人,这使得家庭代工得以复兴。家庭代工制度也称包买商制度(putting-out system,或称外包工制),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彼时,商人向农村或城市的家庭手工业者提供原材料,甚至提供设备、资金等,使后者完成被分发的活计,并给付报酬。(56)[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交换》,第2卷,顾良译,施康强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33页。此后,这种分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逐渐被集中化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但即使进入到机械化生产的时代,家庭代工也没有完全被消除,仍然存在于一些市场狭小、需求不稳定的地方。(57)[美]M.J.派尔、C.F.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李少民、刘英莉译,林剑秋校,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270页。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市场的快速变化和竞争的环境都迫使利润率较低的中小企业使用家庭代工。服装鞋帽、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甚至各种零部件都是部分或完全由家庭代工完成的。与此同时,家庭代工也越来越出现于“新技术”行业。比如文书、电脑编程、系统分析等工作,都可以被分散给家庭工人,全球或海外的“远程工作”也得以实现。(58)Sheila Allen and Carol Wolkowitz, Homeworking: Myths and Realities,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7, pp.20-56.这些家庭工人实际上是没有工作保障的隐形雇佣群体,常常直接受到小企业或代工头的控制,地位更加没有稳定性。(59)Andrew L. Friedman, Industrial and Labour: 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7, p.106.通过生产网络的权力等级体系,这些家庭工人的剩余劳动同样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源泉,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一部分。
在众包模式中,许多平台企业甚至完全放弃了标准的劳动合同,用“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的独立承包者来代替正规的工薪雇员(60)Matthieu Montalban, Vincent Frigant and Bernard Jullien, “Platform Economy as a New Form of Capitalism: A Ré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amm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43(4): 805-824.,不再承担对个体承包者的工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责任。(61)K. Sabeel Rahman and Kathleen Thelen,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2019, 47(2): 177-204.在这其中,形成了大量廉价的、基于不稳定需求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数字劳工(62)姚建华:《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研究——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例》,《新闻大学》2020年第7期。,催生了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63)Marc Steinberg, “From Automobile Capitalism to Platform Capitalism: Toyotism as a History of Digital Platforms”, Organization Studies, 2021,pp.1-22.凭借基于算法技术的数据收集能力,平台大企业不仅可以对数字零工做到更为精细的控制(64)K. Sabeel Rahman and Kathleen Thelen,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2019, 47(2): 177-204.,还能够将作为消费者的用户转化为了自身的“产消者”(prosumer),不仅不需要给付报酬,而且还能够获得更为精准和全面的市场信息(65)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获利的能力。此外,由于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来分配和管理任务,很多数字零工实际上以匿名的方式领取工作任务,因而成为隐藏在算法后面的“隐形工人”。这些工人的极度分散化和隐形化更加削弱了他们相互团结来对抗资本的能力,而全球化的劳动力池也使得平台企业获得了更广空间范围的不稳定劳动来源。(66)Uma Rani and Marianne Furrer,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New Forms of Flexible Work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lgorithmic Management of Work and Workers”, Competition and Change, 2020(1): 1-24.
四、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多重矛盾的累积与深化
借助于生产网络,垄断资本有力地拓展了控制范围、提升了增值效率,生产的分散化并未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和资本之间、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多重矛盾也得到不断累积和深化。
首先,垄断资本借助生产网络将更多的小资本纳入了自身的势力范围,强化了垄断时代资本之间的权力分化。在生产网络中,资本所有权的分散化并没有改变垄断资本的权力地位,构成关键节点的垄断大企业反而更有效率地控制了更多的中小企业,后者的生存空间明显受前者的抑制。同时,垄断资本之间的联合也从未消退,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仍然为垄断资本所掌控。阿明将当代资本主义概括为一种“总体垄断的资本主义”(A Capitalism of Generalized Monopolies),明确指出垄断企业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生产系统,中小企业都被锁定在一个由垄断企业所建立的控制网络中,作为垄断企业的供应商而存在。(67)Samir Amin, 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p.15.这一描述与生产网络所体现的垄断特征几近完全契合。此外,在这种不平衡的组织结构中,大企业垄断和中小企业竞争同时并存。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规模和技术门槛相对较低,这降低了其他企业进入网络的壁垒,因而提高了中小型承包商之间的竞争程度。特别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基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位于发达国家的垄断跨国公司经常可以向发展中国家的底层供应商施加压力,这不仅使后者经常处于“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状态,压低了后者的利润率,而且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来避免利润率的进一步下降。(68)John Smith,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203.
其次,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与劳动之间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对抗性矛盾再次强化。尤其在弹性雇佣模式下,专业性较强的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之间进一步分化,这在整体上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使资本能够实现对劳动的“分而治之”,而最具权力优势的垄断资本则成为最大赢家。例如,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一个碎片化的、层级分明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通常情况下,对于具有同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明显更高,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越来越便宜的劳动力则成为推动跨国外包的重要因素。利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工资水平差异,跨国垄断资本通过向低工资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外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利润率,从而实现“全球劳工套利”(global labour arbitrage)。(69)John Smith,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p.187-189.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由于承接外包活动而增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其中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活动,并且很大一部分被分包至非正规工作安排下的家庭代工。例如服装行业的很多女性制衣工人就被迫根据分包合同安排在家中工作,这只是由于雇主并不会以更有保障的工作安排来雇佣她们。(70)ILO, Decent Work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Geneva, 2002, p.38.而在数字化的生产网络中,数字零工虽然获得了表面上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但众包模式同样降低了许多工作的门槛,在数字零工之间引入了激烈竞争,这延长了后者的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强度,形成了平台大企业的“算法专制”。尤其是对于低技能的全职数字零工而言,他们迫于生活的压力更是不得不进行自我规训,主动选择了超时的和高强度的劳动,更加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并强化了自我剥削。(71)Kathleen Griesbach et al., “Algorithmic Control in Platform Food Delivery Work”,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2019, (5): 1-15.(72)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
最后,资本积累的两极分化特征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再次凸显。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随着广泛的跨国外包实践,很多跨国公司自身已经不再生产产品,而是将其委托给国外的企业,特别是血汗工厂。而由于垄断着技术研发、品牌渠道等关键的环节或资源,跨国公司仍然能够在不参与制造、加工等生产流程的情况下控制并获得南方经济体中所产生的利润。(73)Intan Suwandi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 Monthly Review, 2016, 68(3): 114-131.但对于生产和资本转移出去的发达国家而言,跨国外包也引起了工作岗位的急剧减少,这不仅涉及传统的制造业蓝领工人,而且波及到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尤其是许多中层管理人员随着企业的业务和组织精简而被解雇。(74)Bennett Harrison and Barry Bluestone,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Basic Books, 1988, pp.37-38.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而随着弹性雇佣模式的推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也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特征。在日本,20世纪末以后,随着正式员工相对减少,非正式员工相对增加,他们之间的薪资等级落差也不断显现。日本原先是中产阶级占大部分的社会,但随着“中低阶层”比例的扩大和高收入阶层的略微增加,逐渐演变成了“M型社会”。(75)[日]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刘锦秀、江裕珍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7-43页。而在众包时代,数字零工基本以计件工资的形式获得收入,平台大企业还通过薪酬、补贴以及奖励规则的频繁变更使数字零工的收入水平迅速下滑,后者面临着日益不稳定的生存困境。通过全球化的劳动力池,数字零工之间同样经历着逐底竞争,这尤其恶化了生活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低技能零工的生存状况,使他们无法获得一个确保维持日常生活的、稳定的最低收入水平。(76)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总体而言,随着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也将成为生产网络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这必然将再次造成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形成普遍的相对过剩进而抑制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正常循环。
五、生产网络开辟了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空间
作为资本运动的组织载体,主导性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能够折射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不断发展。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来,垄断组织的发展伴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加速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也更为凸显。马克思曾经对此作出了一定预判,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集中和垄断将不断加强,直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874、409、409、439、439页。而“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874、409、409、439、439页。
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律,垄断组织和生产社会化再次获得了同步发展。前文分析表明,生产网络体现了企业内部分工向不同生产单位(包括企业、个体劳动者)之间分工的演化,但这里所形成的新的分工并不等同于社会分工,而是介于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中间性质的分工模式。(79)有学者也称这种中间性质的分工模式为“企业网络分工”或“企业社会性分工”。参见:钱书法等:《分工演进、组织创新与经济进步——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2-35、160-162页;李翀:《论社会分工、企业分工和企业网络分工——对分工的再认识》,《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马克思曾经指出,手工工场或工厂内部分工发展会相应地增加社会分工。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874、409、409、439、439页。,特别是“在制品是一个由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劳动又可以独立化为特殊的手工业”(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874、409、409、439、439页。;在机器大工业时期,“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8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874、409、409、439、439页。,机器制造业也“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874、409、409、439、439页。。从而,工场或工厂内部的有规则的分工就转化为社会内部的自由分工。(8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在社会分工中,企业之间形成偶然的、随意的商品交换关系,并在市场调节之下呈现出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但在生产网络中,尤其是依托外包关系,不同生产单位之间既表现为分散化生产,又处于相对稳定的生产联系。由于生产网络还具有一定的分工等级,最具权力地位的垄断大企业主导着整个网络的运行,这就使得生产网络更表现出一定的有组织性和有计划性。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网络在空间上还扩散至全球范围,将更多生产单位纳入了自身的运行体系,体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社会化新高度。因此,生产网络尽管包含着生产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有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判断,但仍然扩大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85)《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不可否认,作为体现社会化大生产最新发展的组织形式,生产网络再一次释放出了新的生产力。以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为条件,生产网络中不同节点之间形成了相对有序的连接,这一点在精益生产网络中的“准时生产”制度已经有所体现,并在当前的“工业互联网”中更为突显,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得愈为有序和高效。而随着数字平台在生产组织中的应用,供给方和需求方能够得到迅速和准确的匹配,这也提高了整个社会再生产循环的效率。另外,随着分工协作的深化和细化,中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同样能够提高自身的专业化程度,这也将增大垄断大企业维持控制能力的难度。例如,生产网络就为部分中小企业实现技术进步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外包关系中,大企业虽然通常相对于中小企业更具技术上的优势,但同时成为中小企业重要的技术来源。西口敏宏指出,为了适应市场条件等的变化,日本的发包企业愿意对承包企业进行技术援助的情况非常普遍。(86)[日]西口敏宏:《战略性外包的演化:日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范建亭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托尼·史密斯也指出,在精益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还经常保持着长期的外包关系,这既保证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生产联系的相对稳定性,也鼓励了整个网络中的信息共享,使得中小型承包商能够相对稳定地成长。(87)Tony Smit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Lean Production: A Marxism Critique of the “New Econom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0, p.188.另外,由于小企业在周期短、小批量的产品供给方面更具优势,大企业经常可以将周期短、小批量、需求不稳定的零部件或产品外包转移给小企业,从而使后者获得经济中的一席之地。(88)John H. Dunning, “Reappraising the Eclectic Paradigm in an Age of Alliance Capit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5, 26(3):461-491.在数字化的生产网络中,高技能的个体劳动者也能够通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巩固自身的专业技能优势,从而提高自身的自主性。除此之外,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供应商的转型升级也并不鲜见。通过“干中学”,一些供应商能够不断积累经验与技术,提高生产与研发能力,实现从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向ODM(原始设计制造商)、OBM(原始品牌制造商)的转型,从而提升自身在生产网络分工及权力层级中的位置。因此,随着生产网络的不断发展,将逐渐演化出“多中心”或“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这将进一步促进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种种迹象表明,伴随着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再次凸显,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也正在消失。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客观上更加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最新发展,能够通过社会化地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组织和管理生产过程、共享劳动成果等来平衡积累和消费。因而,对我国而言,生产网络这种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为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效能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将有助于我国迅速、稳步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并赢得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权。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应当充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契机,适应和促进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网络化变革,增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内在联动与协调平衡。在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智能化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这都将使全球生产网络面临深刻重大的变革,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循环的既有路径也将面临深刻的转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国适时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成为我国适应全球政治经济重大变化的主动选择。对此,我国应坚持科技创新的牵引作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特别重视在核心技术、关键领域等取得重要突破,既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提升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在适应生产网络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不能忽视对垄断资本的规范和约束。特别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既鼓励、支持和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提高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效率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坚决防止平台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保证社会再生产循环的正常运转。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规划和监管措施,这些都是我国促进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举措。事实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最新发展中获得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机遇,资本主义也将在自身的不断否定中加速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