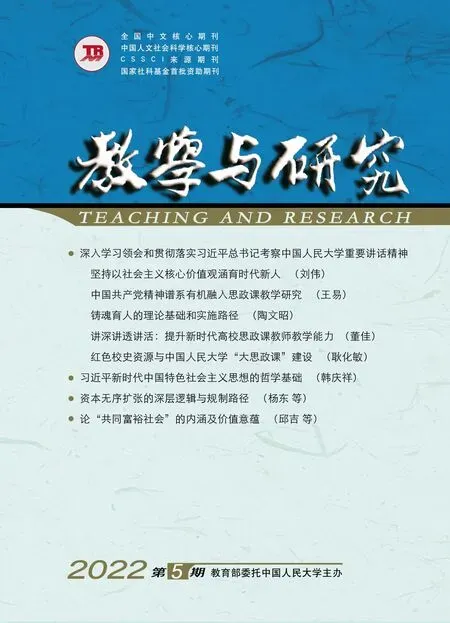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逻辑探究与争论评析*
刘召峰
1919年5月6日,北京《晨报》刊载了河上肇著、渊泉(陈博贤)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其中摘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可以说,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迄今已逾百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五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被作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本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蔡和森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一书,阐述了五种社会形态(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参见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第216页);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的演进逻辑,研究了中国古代史(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目录”,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1939年,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采纳了“五形态说”(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页)。此后,“五形态说”还被写进《社会发展史》教科书(比如华岗1940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社会发展史纲》、解放社1948年编的《社会发展简史》、沈志远1949年出版的《社会形态发展史》等),广为流传,逐步成为学界的主流看法。20世纪50年代,虽然我国史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奴隶社会并非“必经阶段”(2)参见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李鸿哲:《“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文史哲》1957年第10期;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但这种看法难以见容于当时的学界,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后,黄现璠先生重提“我国没有奴隶社会”(3)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质疑“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普适性。197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6卷上册出版,其中有马克思关于“三大形态”的论述。此后,“五形态说”受到了“三形态说”的强烈冲击。(4)参见张亚芹、白津夫:《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颜虹:《应恢复“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6期;刘佑成:《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哲学研究》1988年第12期;张凌云:《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片论——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段忠桥:《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当然,也有学者论证“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只是从不同视角考察社会形态演进得出的结论,二者并无根本冲突,因而是可以并存的。(5)参见贾高建:《当代社会形态问题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66-67、69-77页;杨文圣:《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多重维度》,《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赵家祥:《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黄斌:《传承与创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2页。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分歧甚多。本文将在广泛借鉴哲学界、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同仁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追问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问题的理论逻辑,评析相关学术争论,即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可寻?若有,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之间是否是“势不两立”的关系?如何理解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五形态说”与“三形态说”究竟哪一个才是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的阐述?以期深化与拓展相关研究。
一、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问题的理论逻辑
无论是“五形态说”还是“三形态说”,都是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结论。与其围绕这些具体结论进行争论,不如着重追问这一问题:马克思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考察内蕴了怎样的理论逻辑?
(一)社会结构与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的视角
马克思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联系、变化发展的整体(有机体)来看待的。在这一有机体中,经济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在经济生活的诸环节中,“生产”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形式的生产”,因而不仅要考察“生产什么”(生产的物质内容),还要考察“怎样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础,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是一定的经济形态的标志。
当然,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采取多个不同的视角,而不能把某一种划分方式理解为唯一正确的。马克思本人就从不同的视角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剖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1-522页。;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时,他特别强调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阶段的影响;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资产阶级社会而告终时,他实际上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和“真正人的社会”两大阶段(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人的社会”的说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4页的“名目索引”。;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三大社会形式”则是对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关系”及其表现形式的考察。
不过,由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在整个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尤其注重从“经济形态”演变的视角(我们可以称其为“首要性视角”)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使用其他视角,都不能否定这一“首要性视角”。在我国历史学界,有些人借考证“封建”的中国古义、西义和“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之名,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经济形态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成果,进而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形态理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11)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林甘泉、李根蟠、卢钟锋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之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12)参见林甘泉:《“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李根蟠:《“封建”名实析议——评冯天瑜〈“封建”考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另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二)抽象地研究“一般社会”,还是具体地考察特定“社会形态”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我们先来考察马克思是如何理解“生产”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承认“生产一般”是 “一个合理的抽象”,但又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本质的差别”,因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考察“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就需要“生产方式”出场了;而且,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谈论“生产方式”,而是致力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知,马克思是以“生产一般——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化逻辑来考察“生产”的。
同样,马克思也是以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思维方式来考察“社会”的。此时,我们需要悉心品味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的相关论述。列宁揭示了“主观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14)在列宁看来,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15)《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65页。在此,列宁强调的是,与热衷于谈论“一般社会”的人不同,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的是特定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剖析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剖析,重点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马克思的批判性研究彰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与历史性。
在马克思眼中,奴隶、服徭役者、雇佣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重大差别:奴隶的必要劳动也表现为为主人的劳动,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必要劳动和为地主的剩余劳动是明显分开的,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雇主的劳动)也表现为必要劳动(为自己的劳动)。(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9、619页。由此可知,封建社会的剥削是显而易见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被“平等交换”的假象掩蔽起来了。
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需要破除资本可以“自行增殖”的假象。资本的增殖是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中发生的。(18)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雇佣劳动相对立时才成为资本;只有当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时,劳动才能表现为雇佣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5页。但是,在资本的生产、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被层层假象“掩盖”起来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是,在工资的形式上,好像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9、619页。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只是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但资本的流通过程造成的假象是,剩余价值来源于流通领域(它是在“贱买贵卖”的“交换关系”中产生的),而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无关。(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剩余价值只是可变资本增殖的产物,但利润好像是全部预付资本的“增加额”(21),好像来自资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质;而且利润的平均化使得利润在数量上也与剩余价值量不同。(22)本来,无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还是利息、地租,都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它们表征着资本家阶级(包括土地所有者)与雇佣工人阶级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是,商业利润和货币经营业利润都是以流通为基础,都好像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企业主收入与利息的分割,表现为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生息资本好像是一个能够“自行增殖”的“物神”;地租好像是土地的“自然力”的产物。(23)马克思破除了上述种种假象,揭示了资本的拜物教性质。
马克思揭示资本的拜物教性质的思想立足点在于,他明晰地区分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劳动、土地是“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而雇佣劳动、“现代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私有权”则“像资本一样”,都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4、57、57、939-940、922-924页。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的区分,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历史暂时性彰显了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剥削与商品生产的“内在结合”(虽然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业已存在,但是,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并非建立在“商品交换”之上;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剥削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是“外在”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也是“历史的必然性”“暂时的必然性”,而非“绝对的必然性”。(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244页。
马克思运用具体的历史的思维方式,明晰地区分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揭示了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彰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和历史性。究竟是秉持具体的思维方式考察特定的“社会形态”,还是抽象地谈论“一般社会”,这是马克思与“主观社会学家”的重大分歧。正如我们需要在“生产一般——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化逻辑中来理解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我们也需要在“一般社会——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中来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
二、历史发展规律及其与人的活动的关系
研究者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关系的理解分歧很大:有人为了给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留出空间,否认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26)参见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无论在理论世界中,还是在实践世界中,我们都不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27)王南湜:《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还有学者致力于探究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异同。
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人的活动的参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对规律客观性的否定,还是只改变了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这里,我们以活塞式抽水机为例来说明自然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水会从高处向低处流,这是万有引力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人类发明的活塞式抽水机则可以利用活塞的运动排出空气,从而造成内外气压差而使水在大气压的作用下实现由下到上的移动(被抽出)。抽水的全过程,万有引力规律的作用一刻没有停止;人类的活动只不过是引导了内外气压差的形成,造就了大气压克服地球引力的物理学效应罢了,或者说,只不过是改变了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罢了。把自然规律的作用发挥作为一个环节纳入人的劳动过程中去,这是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的前提。
我们也可以以价值规律(28)对价值规律的具体内涵的辨析,参见骆耕漠:《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44-173页。为例说明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商品价格由商品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是支配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核心内容。不过,价值规律恰恰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实现的,也就是经由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实现的。由此可知,价值规律并非外在于商品生产当事人的规律,而恰恰是只有在人们的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他们当然在其中发挥了“主体能动性”)中才能存在的规律。
“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说人的活动的一切社会后果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完全可以率先开发或引进先进技术,改进经营管理,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获取更大利益。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只有“无视或否定客观规律”一条道,还有“认识和利用规律为实现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广阔空间。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三、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自然历史过程”的涵义与适用范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1995年之后,这句话的译文修改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而《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的译文是:“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la formation économique de la société)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页。另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页。法文原文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Dietz Verlag,Ⅱ/7,1989,S.14.不同的版本、译文的差别,给了研究者阐发其不同意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们有必要把这句话放到具体的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在说这句话的前一自然段阐述的观点是: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2)很明显,马克思在此着重强调的是规律的客观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可跨越。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自然史的过程是相似的”那句话的之前和之后,马克思阐述的观点是: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在现实中不可能超脱各种关系,因而,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10页。由此可知,所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自然历史过程“是相似的”,是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社会关系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等意义上来谈的。
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自然历史过程是相似的,那么,这种相似性是永恒的,抑或只是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才具有的阶段性特征?张一兵先生认为,社会发展从其客观规律的特征来看可分为“自然的必然性社会”“经济的必然性社会”“人类的自由发展社会”三个阶段;我们不能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异在为自然规律的历史现象”理解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的永恒法则”。(34)张一兵:《社会历史发展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吗?》,《天府新论》1988年第1期。后来,张一兵多次撰文阐述自己的这一思想。(35)参见张一兵:《析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似自然性的特设规定》,《哲学研究》1991年第2期;《再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1期;《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规律”的批判》,《江淮论坛》1994年第3期;《似自然性:人类社会发展异在为自然过程的特殊历史状态》,《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永恒的自然规律在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考察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问题,需要区分多个问题层次。首先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永恒的必然性”。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讲道:“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根本不能取消“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9页。在此,马克思强调:“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对于人而言是永恒的,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其次是存在于多个社会形态中的“似自然性”——比如商品生产中的“似自然性”。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本规律,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多个社会形态,不过,它仍然是具有历史性的规律——在劳动不表现为产品的价值的地方,价值规律当然就不复存在: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劳动也不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个人的劳动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的。(3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3-434页。最后是存在于特定社会形态的“似自然性”——比如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的“铁的工资规律”。针对《德国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中“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说法,马克思以嘲讽的口吻说道:“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页。
四、历史发展规律:“五形态”还是“三形态”?
如果说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那么,这一规律是“五形态”的依次更替,还是“三形态”的先后更迭?
“五形态说”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看作依次演进的五种社会形态。这种理解存在的问题,在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时凸显了出来。对于中国曾经存在过奴隶制度,中国史学家大都是认可的,可是,是否经历了奴隶社会就分歧严重了。按照张广志先生的说法,“有奴隶、从而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就是奴隶社会。……要想论证古代东方的奴隶社会的社会性质,就不能仅仅限于证明这里有奴隶制存在,还应进一步论证奴隶制在这里的确是占主导地位的剥削方式。”(39)张广志:《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另可参见张广志:《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某种生产方式是否存在,与这种生产方式是否占据主导地位,的确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社会”,其研究结论也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的四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演进,只是“大体说来”是如此。按照庞卓恒先生的说法,列举那些形态和更迭顺序都只是作为“大体上”讲的历史例证,是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形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而绝不是认定其中每个形态和更迭顺序都是各个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绝不是想描绘一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40)庞卓恒:《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历史哲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如果把“五形态”的依次演进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把“五形态说”等同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本身,就会“矮化社会形态理论”(41)周群:《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回溯及其当代应用》,《东南学术》2017年第5期。。如果说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需要捍卫,我们也要把着力点放在内蕴于其中的理论逻辑上,而不是放在某个具体结论上。
“三形态说”的直接文本依据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无论“人的依赖关系(Persönliche 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s)”,系词“是(sind)”,还是“最初的社会形式(die ersten Gesellschaftsformen)”都是复数。(43)德文原文参见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Werke,Dietz Verlag,Band 42,1983,S.91.因而“最初的社会形式”不是一“个”,而是包含了多个社会形式的一“类”。“三大社会形式”更为准确的理解是“三类社会形式”,因而,我们有必要对“社会形式”进行更为精细的划分,而不是到处套用“三大社会形式”。
有“三形态说”的主张者认为,“第二大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此,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能否仅仅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来概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否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具备这一特征?我们在前文指出,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实现了“剥削与商品生产的内在结合”。因而,不能仅仅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剥削与商品生产的存在有着不同的社会机理:剥削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占有出现社会分化的产物,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奴役另外一部分人的劳动;商品生产的存在缘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并不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生产者们需要通过交换、把产品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手里,其中的劳动才能证实自身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44)对此问题的详细阐述,参见刘召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劳动的耗费、凝结与社会证成”为中心线索的解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剥削与商品生产之间并不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否定了产生剥削的生产关系,并不意味着必须消灭商品生产与交换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在其不发达阶段,也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社会形式”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从而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所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具有这一特征。
“五形态说”的主张者通常并不否定“三形态说”,但是,在“三形态说”的主张者中,否定“五形态说”的则大有人在。他们否定“五形态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其实,论及“适用性”,“三形态说”也将面临与“五形态说”类似的困境——在当下的地球上,依然存在一些尚未进入“第二大社会形式”的人类群体,他们将来是否一定会过渡到这一发展阶段尚未可知。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die Vorgeschichte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就以这种社会形态(指“资产阶级社会”——引者注)而告终”(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德文原文参见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Werke,Dietz Verlag,Band 13,1961,S.9.时,他实际上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和“真正人的社会”(46)“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人的社会”的说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4页的“名目索引”。两大阶段。这一“二形态说”要比“三形态说”更具“普遍适用性”——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群体的发展阶段都无一例外地处于“史前时期”!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划分社会形态时,分的阶段越少,“适用性”越好;但是,分的阶段越少,越不利于我们具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
庞卓恒等先生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规律”,实际上有两个类别:一类是对事物运动变化的“不变秩序”所作的单纯的经验性归纳,这属于经验规律,其中没有包含“为什么”重复出现的“因果必然性链条”,就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规律;另一类规律包含着对事物运动变化的“因果必然性链条”的“不变秩序”的全称判断,这属于“因果必然性规律”或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规律”,就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规律。(47)长期以来,人们把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误解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遵循某种统一的演进序列的规律,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48)参见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3、134、153-154页。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49)参见庞卓恒:《历史学·发展学·人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庞卓恒:《生产能力决定论》,《史学集刊》2002年第3期;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3-154页。以此观之,无论“五形态”还是“三形态”的依次演进,都不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本身,而只是它的具体表现。
结 语
在我国,不少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关注的往往只是带有“社会形态”等字眼的词句,往往抽象地考察社会形态的演进序列,却不曾悉心梳理马克思是如何考察某一具体社会形态的;也有些学者非常认真地考察某一具体社会形态(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却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本身缺乏整体的把握,特别是不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的深刻意蕴(51)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刘召峰:《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辨析》,《江汉论坛》2013年第10期。——正是因为马克思细致剖析了资本主义这一当时的“最高级的社会形态”,并“立于高山之巅”对于之前的社会形态的某些核心问题进行了“俯瞰”,才建构了系统的社会形态理论。
——《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基于国际理论家的视角》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