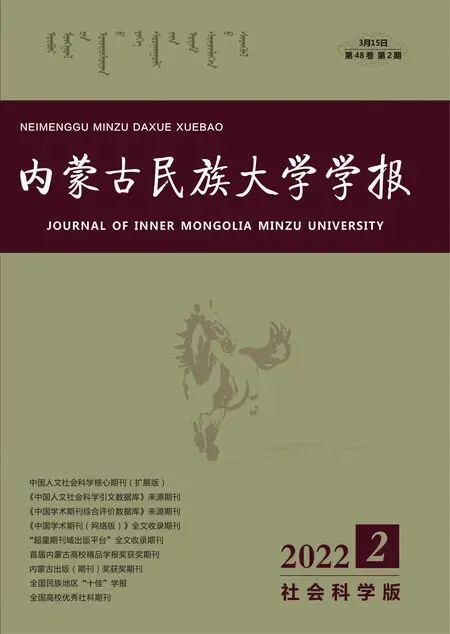蒙古族戏剧文学渊源考
王满特嘎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蒙古族戏剧文学,尤其是研究20世纪整个蒙古族戏剧文学,必须要特别关注与之血脉相连的蒙古国同一时代戏剧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因为中国蒙古族戏剧文学和蒙古国戏剧文学是在同一文化渊源基点上产生且又在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遗憾的是,国际蒙古学界对蒙古族戏剧文学的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迄今为止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成果甚少,国内只有极个别学者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对整个蒙古族戏剧文学的研究远未深入。
探讨蒙古族戏剧文学的源头,可考察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作家杨景贤①用汉文创作的杂剧《西游记》。据考察,杨景贤作有杂剧18种,今存《刘行首》《西游记》②两种。杂剧《西游记》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民间传说,写唐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从玄奘出世写起,一直写到取经东归、功成行满,其中包括唐僧收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为徒,降服鬼子母,逃离女儿国,火焰山除害等事件,又穿插了孙行者因偷仙桃仙衣被压在花果山,猪八戒骗娶裴海棠等情节。全剧人物众多,文臣武将、闺秀村姑、神佛妖魔一应俱现。主要人物孙悟空的性格虽然不如后来吴承恩小说所写的那样鲜明、完整,但对他的疾恶如仇、抱打不平以及诙谐风趣的性格特点,已有比较着力的描写,例如第5出写唐朝文武官员为玄奘饯行,第6出接写“村姑演说”,从一个村姑的观察角度,描写百官饯送的盛大场面,不仅饶有风趣,也见出作者布局的匠心。
只可惜杨景贤虽为蒙古人,但久居汉地,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不是很熟悉,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民族特点极不明显。杂剧《西游记》反映的社会生活、作品的文化内涵、作品所用语言、显示的文化心理素质等,从内容到形式均欠缺蒙古民族特点,所以笔者认为将杨景贤所著杂剧《西游记》直接认定为蒙古族戏剧文学源头尚待斟酌,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考察蒙古族戏剧文学的渊源。
一、游牧民戏剧
戈壁第五世诺彦呼图克图丹增拉布杰的戏剧作品《月鹃传》的问世,标志着在蒙古地区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的戏剧表演形式,19—20世纪在戈壁莫尔根王旗流传的《月鹃传》按其表现形式可归类为歌剧。西藏活佛罗布桑丹必扎拉森于1737年用藏文创作了《月鹃的故事》,由固什阿旺丹丕勒于1770年翻译成蒙古文,丹增拉布杰在此基础上于1830年撰写了剧作《月鹃传》,并自编自导进行演出。该剧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社会生活、上层社会的斗争,深刻揭露了他们为了权位和官位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同时反映了提高贫民及妇女地位的进步思想。《月鹃传》有别于《月鹃的故事》,据蒙古国学者D·查干介绍:“与作者其它作品相比较不难看出,剧中赞歌和英雄人物口中的诗箴(训谕诗)毫无疑问出自丹增拉布杰之手”。TS·达木丁苏荣院士也说道:“亚木西的儿子拉甘汗成为儿子侍卫时说的训谕诗同样出自拉布杰之手。”[1]
丹增拉布杰的《月鹃传》在喀尔喀蒙古地区戈壁莫尔根王旗哈木仁寺、查干陶力盖寺和察哈尔地区一直演出到20世纪20年代。该剧在第六世戈壁诺彦呼图克图时期停演了一段时间,到第七世戈壁诺彦呼图克图时期又恢复了演出。从目前保留下来的两本演出手册来判断,是在第七世戈壁诺彦呼图克图丹必扎拉森(?—1932)时期重新撰写的。
1902年写的蓝皮演出手册内容比1888年写的红皮演出手册更加具体,尤其从“场面的宏大”可以看出,是进行了修改之后才上台演出的。从宗教仪式的范畴来讲,该剧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月鹃传》共有9本,为了便于舞台演出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大量修改,不同于传记,更有配套的演出规则。剧中舞台设计、幕布、道具、着装服饰等均符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这部剧作在游牧民族心目中占有较高位置,“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是真正的蒙古剧。”[2]
二、戏剧性小品
现在我们可以查到一些有关探究蒙古戏剧文学的发生发展脉络的可靠论据,当时蒙古民间戏曲演出正式产生和发展的相关记载与消息流传至今。
蒙古国国家奖获得者、知名剧作家E·奥云提出过关于1910年在现在的蒙古国东戈壁省有两个叫查克达尔和巴乐丹敖德斯尔的青年周游各地演出题为《贫穷小和尚和鬼的对话》的两百多段对话场景。[3]在《民间戏剧游乐文学》一书中收录的《喇嘛和鬼》的对话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4]158鬼原本想赢小和尚,然后谋害他,但自己却输了,无地自容地说了句“装故事的口袋忘在乡下,没想到人的威力这么大”便逃走了,这是以喜剧的形式反映人的智慧比鬼略高一筹的艺术作品。鬼赢不了小和尚,所以万般无奈地说:“见过在须弥山顶上种田的吗?见过在大海水里起火的吗?”小和尚不屑一顾地说:“见过牛与马赛跑吗?见过人与鬼对话吗?”在他们俩的对话中用斗智辩论的方式阐明了善与恶之间的区别,对话具有戏剧性效应。
三、蒙古对唱歌
蒙古民族戏剧有一种形式是民间对唱歌。E·奥云在《蒙古剧院艺术在民间的传承》一文中认为蒙古民间对唱歌是民族戏剧的形式。对唱歌中富有个性特点的多种人物角色的设置及开端、发展、结尾等故事情节就是依据。对唱歌以其类型可分为:1.英雄话剧形式的对唱歌,如《陶莱班迪》等;2.喜剧搞笑对唱歌,如《苏米亚诺颜》(又称《北京喇嘛》)、《万丽》等;3.悲伤抒情对唱歌,如《母子之歌》(《金帐白桦树皮书》)、《红斑点的小黄马》、《黄羊山丘》、《阿丽格尔玛》等;4.哲理性对唱歌,如《老人与鸟》等几种。
《苏米亚诺颜》(又称《北京喇嘛》)[4]140这个对唱歌开初是以苏米亚诺颜和九月姑娘两个人的对唱歌作为抒情手法,两人相互有了感情之后因思念对方而进行对唱。九月姑娘唱道:“梦见西边山头上,盛开了莲花,梦见和心爱的你,商量咱俩的喜酒”。苏米亚诺颜回唱道:“梦见天上下起了雨,人间有了甘露,梦见和心爱的九月,分喝一碗美酒”。
从这段歌词可以清楚地看出人间感情的珍贵,甚至可以看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但后来与九月姑娘有旧情的北京喇嘛赶来了,他唱道:“跪着爬着的你们俩是,没爹没娘的孤儿吧?肩膀上坐着的小伙子是,江河里小鱼的鬼魂吧?”从这里开始是该对唱歌的搞笑部分,但是这部分也反映失去心爱姑娘的喇嘛爷悲伤的悲喜剧曲调。该对唱歌的搞笑部分是北京喇嘛企图从已经变心的九月姑娘那儿讨要以前赠送的礼物的一段描写,九月姑娘嘲弄喇嘛爷,最终没还给他的礼物。喇嘛爷唱道:“所谓礼物就是礼物,是北京绣花纹的珍宝,要是你的心在苏米亚诺颜身上,那请把我的礼物还给我,啊九月”,对此九月回唱道:“当初给我礼物的时候,你的心也在我身上吧?对礼物念念不忘的话,那就带喇嘛嫂过来拿吧”。还有:“当初给我靴子的时候,爱上了我美丽的躯体吧?对靴子还念念不忘的话,在胡同口磕三个响头吧”[4]142。
就这样,北京喇嘛什么也没拿到,就被轰走了。这首对唱歌里不仅嘲笑北京喇嘛不顾清规戒律勾引女人,还有像达·那楚克道尔吉著名作品《喇嘛爷的眼泪》小说的主人公罗顿格西一样的悲喜剧的格调,这类例子在对唱歌中很常见。1922—1923年在大库伦(今乌兰巴托市)有剧团上演过这个对唱歌。这方面蒙古文学研究家G·扎木苏荣扎卜曾进行过采访,从演员达西德乐格、伊沁浩日劳等人处记下了比较详细的变体。[5]
《阿丽格尔玛》这首对唱歌深受人民喜爱,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位严厉的婆婆的形象,还反映了无限期服兵役的清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欺压。
对唱歌从阿丽格尔玛与阿拉坦苏和两个人骑着马恩爱并肩赶路的画面开始:“花斑马的慢步小走,相伴而行,阿拉坦苏和,上面大走下面小走,并辔而行,阿拉坦苏和”。先阿丽格尔玛独唱,后两人合唱,这样既和谐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地赶回家的时候,衙门诺颜处来了从军的指令信。阿拉坦苏和从军之后,有一天,婆婆故意难为没犯错的阿丽格尔玛唱道:“把他家的阿丽格尔玛,赶紧送回她娘家,当初送的牛马,全部要牵回来”。紧接着轰她回娘家去了,阿丽格尔玛没办法只能走,这时她以歌唱的形式表达了想见阿拉坦苏和的心愿,阿丽格尔玛被送回娘家之后阿拉坦苏和安全复员归来,然后这样问他爸妈:“我的爱妻阿丽格尔玛,怎么见不到呀?”对此他妈妈说谎且不认错,阿拉坦苏和听后回唱道:“没能祭祀祖先是阿拉坦苏和,没能照顾父母亲是阿拉坦苏和,送她回娘家,拿回来牛马,妈妈做的这个事,确实很合乎情理”。这时妈妈提出让他再另娶的想法,但是被阿拉坦苏和拒绝了,“两人互相喜欢,喜结连理之后,如若还像上次,有辱父亲名声”。阿拉坦苏和没有答应,朝着心爱的阿丽格尔玛姑娘奔去。故里乡亲支持他而唱道:“心里想起念起,最心爱的妻子,已经无心顾忌,慢走还是快马”。就这样,阿拉坦苏和想着心爱的阿丽格尔玛,来到她的娘家。阿丽格尔玛的母亲是个聪慧之人,她说道:“你心爱的阿丽格尔玛,有你父亲的准许才来,距你父亲给的假期,还延迟了十天”。阿丽格尔玛看到自己的丈夫唱道:“不要误会你的父亲母亲,是他们减轻了我的苦难”,这时阿拉坦苏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带着爱妻回家。两个人回家后对父母亲唱道:“可怜的花斑母牛,在思念她的牛犊,心爱的阿丽格尔玛,不是二老的孩儿吗?”[4]128—137这样,阿丽格尔玛在真诚地等待了十三年后,与丈夫重聚了。这首歌在反映婆媳矛盾关系的时候,描写阿丽格尔玛是有智慧、懂礼数,虽然被婆婆刁难,却不说婆婆坏话,反而把错误往自己身上揽的既善良又忠贞的好媳妇形象。
四、查玛舞(跳神舞)
查玛舞(跳神舞)有配套的音乐和舞蹈、专用面具、戏装,具有明显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还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因此完全有依据把跳神舞归类为舞台表演艺术当中。L·胡日勒巴特尔教授介绍查玛舞的发展时说道:“从宗教内部的密宗舞延伸到有宗教内容的内部舞蹈,再逐渐向外扩张发展成大众化的舞蹈,阎王为首的各路凶煞、却仲(护法)形象逐渐更加独立,甚至分别开来,吸收了藏舞(面具舞)和地方舞种的精髓,慢慢演变成了适合剧场表演的戏剧艺术。”[6]
20世纪初,蒙古社会深受佛教影响,这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反映,因此在戏剧艺术中可以提到查玛。当时因为其他种类的舞台表演很少,所以查玛除了宗教的色彩之外,还是一种供人欣赏的演出形式,尤其是库伦查玛具有添加民间剧艺的人物描写的特点。每个寺庙的查玛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其中库伦查玛一直进行舞台表演到1937年。1953年苏俄学者N·P·沙士媂娜记录过查玛的相关事宜。查玛不是平常的一种娱乐,是一种密咒的活动且佛爷会现身,具有去除灾难、开启转世之路的目的,通过查玛舞蹈拯救苍生于病痛、战争、饥困。关于查玛,N·P·沙士媂娜写道:“很明显在寺庙中以宗教活动和修行舞蹈的形式形成了最初的舞台表演”,并认为蒙古查玛相比较于藏族查玛更具有舞台性,他甚至写道:“这面具、舞蹈、咒文,不仅如此,还有修行舞蹈的详细规则和作用、动作中夹杂的喜剧效果等,让其成为了新的宗教修行舞蹈”,并说“其中类似于米拉日巴查玛等直接具有宗教戏剧性”[7],这些均成为重要的结论。
在库伦查玛舞第18序(场)中,白须老人被俩孙子挽扶出场,摇摇晃晃跳起醉舞,接下来还出现摔倒装睡的场景。此时出场两只白狮子和两只绿狮子戏耍绣球,白须老人试图抓获狮子,之后骑上其中一头狮子分发瓜果。库伦查玛中的凤凰查玛、鹿查玛、雄鸟查玛等体现出受民间舞蹈的影响。
上述盛行在蒙古国地区的带有戏剧因素的作品、舞台艺术活动以及《月鹃传》之类的戏剧文学为蒙古国现代民族戏剧艺术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21年蒙古革命后,蒙古国的现代民族戏剧正式诞生,其公认的标志是蒙古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著名功勋作家S·宝音尼木和编写的大型历史剧《三多办事大臣》(又名《近代简史》)③。
结论
本文对1921年蒙古革命以前蒙古地区戏剧文学的渊源进行分析、探讨和研究,概括出如下结论。第一,从宗教仪式的范畴来讲,深受藏族文学艺术影响的丹增拉布杰的《月鹃传》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状况,剧中舞台设计、幕布、道具、着装、服饰等均符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在蒙古民族心目中占有较高位置,故被称作游牧民戏剧,笔者认为《月鹃传》是蒙古戏剧文学的开端。第二,20世纪初盛行在蒙古地区的戏剧性小品、蒙古民间对唱歌及库伦查玛舞等艺术形式中已经蕴含了诸多蒙古戏剧因素,这对蒙古国现代民族戏剧文学的产生奠定了艺术底蕴与基础。
[注释]
①杨景贤,元末明初杂剧家杨讷,原名暹,后改为讷,先世为蒙古族人,从其姐夫姓,生卒年不详。《录鬼簿》记他“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家居钱塘(今杭州),逝于金陵(今南京)。杨讷与贾仲明相交五十年,作有杂剧18种,今存《刘行首》《西游记》两种,《玩江楼》和《天台梦》仅存残曲。明永乐初,杨讷与贾仲明、汤式一起受到明成祖朱棣的宠遇,约在永乐年间卒于金陵,曲作有特色。
②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共六本二十四折,结构宏大且较为完整,为元杂剧中的鸿篇巨制,它是根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民间传说改编而成。故事从陈光蕊赴任遇盗开始,到玄奘取经归来结束。孙悟空爱打抱不平的性格特征已经充分表露出来,但还缺乏神力,擒妖伏怪多要观音、如来相助。杂剧《西游记》充分反映了元末明初东南沿海社会和思想的变化,是具有市民意识和个性解放、心灵自由要求的,这种思想开了明中后期思想解放潮流的先河。在元代后期曲坛上,杨景贤杂剧《西游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品。它第一次将民间流传的唐僧赴西天取经故事敷演成大型连台本杂剧,围绕取经过程塑造了以孙悟空为典型代表的一组充满神奇色彩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大大丰富了戏剧舞台和古典文学人物画廊,展示了元末文人带有市民化倾向的审美创造能力,为神魔小说《西游记》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论在艺术成就或者在杂剧体制的改革创新方面,都有重要的推进,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③S·宝音尼木和著:《三多办事大臣》(又名《近代简史》),手抄本,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蒙古文手抄本书库馆藏,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