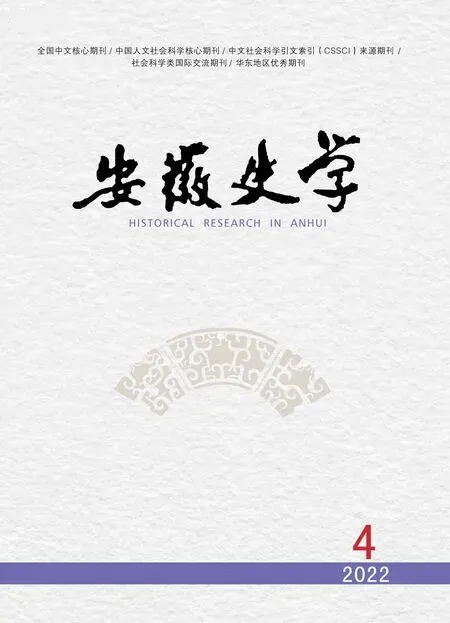沈家本恤幼人道思想探析
姬元贞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怜恤弱小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不论是出于善良本性还是道德束缚,在古代中国体现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理念——“恤幼”之中,而在西方则体现于人道主义之中。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清廷修律大臣们逐渐将这些理念用现代律法的形式表达出来,初步形成了近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
关于沈家本法律思想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时至今日有关沈家本思想的论文、著作依然不断涌现,并被赋予不同的时代意蕴。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有关清末变法修律的研究。主要有沈厚铎的《玉骨冰心冷不摧——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沈家本》;(1)沈厚铎:《玉骨冰心冷不摧——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沈家本》,《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43—148页。霍存福的《沈家本“情理法”观所代表的近代转捩——与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较》;(2)霍存福:《沈家本“情理法”观所代表的近代转捩——与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99—115页。曾尔恕、黄宇昕的《中华法律现代化的原点——沈家本西法认识形成刍议》;(3)曾尔恕、黄宇昕:《中华法律现代化的原点——沈家本西法认识形成刍议》,《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第93—104页。段凡的《论沈家本司法人道主义思想及其历史意义》;(4)段凡:《论沈家本司法人道主义思想及其历史意义》,《法学评论》2017年第2期,第172—182页。李贵连、俞江的《论沈家本的人格平等观》;(5)李贵连、俞江:《论沈家本的人格平等观》,《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3期,第309—321页。等。第二,有关沈家本刑法观的研究。主要有姜晓敏的《晚清的死刑废除问题及其历史借鉴》;(6)姜晓敏:《晚清的死刑废除问题及其历史借鉴》,《法学杂志》2013年第12期,第109—116页。李交发的《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7)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189—192页。徐忠明的《古典中国的死刑:一个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考察》;(8)徐忠明:《古典中国的死刑:一个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考察》,《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第257—276页。等。既有研究多着眼于“礼法之争”的过程和刑法修律改革等法律整体变化,类似“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刑事司法制度”等法律具体改革的研究还较为少见。伴随着当下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本文拟追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历史本源,考察中西交汇背景下,沈家本的恤幼人道思想如何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影响近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思想逻辑和形成路径。
一、沈家本恤幼思想之传统文化根源
虽然“未成年人”这一抽象概念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对未达到一定年龄的“幼”“小”者,各朝各代都有相关刑事司法方面的特殊保护机制。沈家本对传统恤幼法律制度有深入考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代表作《历代刑法考》中。在该著作中,有关古代恤幼制度的研究,散见于“刑法分考”“赦”“律令”“明律目笺”等篇中,其中“刑法分考七”“赦五·述赦四”“明律目笺一”“明律目笺三”等篇目列举了元、宋及明代的恤幼法律规范。其中“刑法分考十”“刑法分考十四”“刑法分考十六”等篇目分别阐述“屯戍”“杖”“赎”中对未成年人的减刑政策。“赦一·原赦”“赦八·赦例二”“赦九·赦例三”“赦十二·论赦二”等篇目更是详细分析了《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等律典有关老幼的特赦条文。
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恤幼法律制度的考据与传统中国的“仁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显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未成年人一直被当作弱势群体来特殊对待,并作为统治阶层推行仁爱的举措。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9)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6页。《管子·入国》开篇便点明“慈幼”与“恤孤”的主旨,“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10)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33—1034页。沈家本认为,这些表述都与未成年人保护有关。另外,中国古代社会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以“仁政”思想为主导,这种“仁政”在未成年人刑事保护方面,主要体现为倡导“恤幼”思想,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一系列宽宥之刑罚措施。沈家本高度评价中国古代“仁政”“德教”思想,并认为:“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11)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5、2024、1801、628页。,“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12)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5、2024、1801、628页。沈家本对普通民众尚且如此,对待“幼”“小”更是以“仁政”为先。所以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从中国古代围绕未成年人犯罪减免处罚等恤幼思想的特征进行深入剖析。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免除或减轻处罚
沈家本的恤幼思想来源于传统法律思想,其曾言:“老小不加刑,其法甚古。”(13)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5、2024、1801、628页。翻检历史资料可以发现,沈家本探究的恤幼问题在汉代相关律令中就有体现。西汉时期,惠帝即位初年就有规定,未满十岁的未成年人触犯应当被刑罚制裁的律条时,不再按原罪处罚,均以髡刑(剃头发)代替。(14)班固:《汉书·惠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5页。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新律令规定:年龄未达七岁的未成年人,在彼此残杀格斗过程中杀人或者犯其他应被斩首的死刑罪时,可以“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15)班固:《汉书·刑法志》,第1106页。,这说明犯重罪的未成年人并不能完全免除刑事责任,但可以通过“上请”的方式减轻处罚,免除死刑。“上请”是中国古代“仁政的体现”,一般皇亲、贵族等身份显赫之人才有此殊遇,可见汉代对未成年人特殊关爱程度之深。
唐代法律规定,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反、逆、杀人”等重罪的,可以有“上请”的机会,这与前述汉代“不满七岁犯死刑罪可上请”相比,显然从年龄和罪名两个维度扩张了“上请”的适用范围。唐律对“上请”程序的适用对象也有明确规定,皆为身份尊贵之人,可见唐律对待十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政策非常宽仁;而“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这种规定可以推断出,唐律已经非常明确地规定七岁为完全免除刑事责任的年龄,并且认为七岁以下无判断是非的能力,如果有成年人教唆其犯罪,需要追究该成年人的刑事责任。(16)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赦五》中摘录了《宋真宗纪》的记载:“虑囚,老幼疾病,流以下听赎,杖以下释之。”(17)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5、2024、1801、628页。可见,沈家本认为除了法律规定的减免刑罚,“赦”也体现出对“幼”“小”的充分宽恕。
明清两个朝代,延续了唐代的“恤幼”理念,律典多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从轻处罚。据《明实录》记载,明太宗曾明确反对将二位年十五岁犯强盗罪者处以死刑。永乐二年(1404年)二月,刑科给事中奏,有一起强盗案涉及到是否追究涉案未成年人的问题,他们认为:“臣等揆理论之,彼虽年幼,既能行劫,亦当被刑,不宜免死 ”,但“上不从”,曰:“童稚未成人者,本无知觉。向非成人者诱之,岂能自为盗耶?朕特推此情矜之。尔岂肯屈法滥恩?”(18)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8,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版,第510页。可见,明太宗反对大臣们对二童行刑,认为未成年人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应对其宽宥处理。
沈家本认为,未成年人不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其所应承担的课税徭役和刑事责任都应与其年龄相对应:“夫此相长相强之义,固专为役事而言,而刑事亦可类推矣。”(19)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第1340、2235页。因此,沈家本对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减免刑罚的做法深入研究,并从中国传统恤幼理念中提取精华,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犯罪所受惩罚应与成年人犯罪明显区分,只承担符合其年龄的责任。
(二)以人性化的方式对未成年人执行刑罚
中国古代,除了对未成年人在刑罚种类和程度上宽宥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也给予较为人性化的关怀。首先,从两汉开始,未成年犯罪人在收监、刑罚执行过程中可以不戴刑具,称为“颂系”,注云:“颂,读曰容。容,宽容之,不桎梏。”(20)班固:《汉书·刑法志》,第1108、1106页。一方面,大多未成年人在监狱或执行过程中也许不具有危险性,没有戴刑具的必要;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未成年人犯罪者一种体恤之情。同“上请”一样,汉代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犯罪才可以免戴刑具,足以见得中国古代在刑事政策细节上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照。例如,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规定:“八岁以下”犯罪者应当囚禁审讯的,免于戴刑具,“鞫系者,颂系之”;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也有同样的规定:“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鞫系者,颂系之。”(21)班固:《汉书·刑法志》,第1108、1106页。唐代同汉代一样,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也有不戴刑具等人性化的宽宥之策。例如,《唐六典》规定,对待八十以上、十岁以下、有疾病、怀孕以及侏儒病的人,“皆颂系以待弊”。(22)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6《刑部郎中》,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88页。从汉“八岁以下颂系之”到唐“十岁颂系”,可见唐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进一步宽宥。
明代《大明律》中也有“老幼不拷讯”的规定:“凡应八议之人,及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2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6页。这意味着年龄十五岁以下者甚至有不拷讯的优抚待遇,这比前代未成年人可不戴刑具更为宽厚。明洪武元年(1368年)还规定,十五岁以下未成年人在被关押期间,应与其他成年囚犯分别关押,“不许混杂”。(24)万安中:《论中国古代监狱管理制度的沿革及其特征》,《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101页。这一分别关押的措施显然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来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遭受其他成年囚犯的欺凌,二来能够避免未成年囚犯沾染更多成年囚犯的不良习惯,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再教育。
沈家本在论证中、西法之间“供、证”关系时,也提到“老幼不拷讯”,“中法供、证兼重,有证无供,即难论讯。……虽律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及老幼不拷讯,据众证定罪之文。”(2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第1340、2235页。虽然沈家本是在讨论“证”在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但也从侧面证明沈家本的仁恤思想,承接中国自古“老幼不拷讯”思想,进而延续于修律改革中;肯定对幼小者的矜恤之情,并扩大到刑事司法规则中。
(三)以金钱处罚替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制裁
未成年人犯罪用钱财来代替刑罚的历史由来已久,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的“刑法分考十六”中梳理“赎”的发展时也提到“幼”的赎刑适用问题。溯其本源,唐代“恤幼”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较为突出,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则完备详实且有可操作性,发展出了以金钱处罚替代刑事制裁的“收赎”方法。《唐律疏议》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专门“老小及疾有犯”条,这一条款名称及主要内容被后代沿袭。该条规定: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流罪以下罪行的,可以用“收赎”的惩罚方式代替,即用金钱赎罪。《唐六典》中也有类似规定:“凡赎者,谓在十五以下”和“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盗与伤人者”,“并以赎论”;(26)李林甫等:《唐六典》卷6《刑部郎中》,第187页。《元史·刑法志》“名例”篇载,七十岁以上的老者和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承受杖责的,可以用赎刑替代。(27)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刑法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9、2111、2096页。
元代针对成年人犯罪的“征烧埋银”制度要求犯罪者除本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外,另需额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未成年犯罪行为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除刑事责任,只付“烧埋银”。《元史·刑法志》“杀伤”篇载:“诸十五以下小儿,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诸十五以下小儿,因争毁伤人致死者,听赎,征烧埋银给苦主。”(28)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刑法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9、2111、2096页。显然,十五岁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责任年龄点,主观上没有伤害他人的故意,疏忽大意致人死亡的不承担刑事责任,但需承担民事责任以弥补受害者;主观上有伤人故意,如果受害人死亡,需以赎刑进行刑事处罚,同样也要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庭以补偿。《元典章》刑部卷之四“年幼不任加刑”中记载有如下案例:汪驴儿系八岁孩童,用土块掷打十岁赵引儿,赵引儿还手却不慎打中五岁的汪黑厮,汪黑厮最终因破伤风死亡。对于这件事,“有司”认为:由于赵引儿是孩童,所以他误伤汪黑厮的罪责可以不予追究,由其父支付受害者家庭银五十两,作为丧葬费予以安抚。(29)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刑部卷四,典章四十二,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2页。此案例就是对前述《元史·刑法志》中“杀伤”篇“烧埋银子”相关规范的具体适用,证明未成年人误伤致人死者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对受害者家庭要进行民事赔偿。
此外,元代对未成年人在累犯及共同犯罪情况下也持宽宥态度。《元史·刑法志》“盗贼”篇,关于未成年累犯规定如下:“诸年未出幼,再犯窃盗者,仍免刺赎罪,发充警迹人。”意思是说,对未成年人屡次盗窃者依然持从宽的态度,仍免去刺字,可以用赎刑替代,并将其纳入“警迹人”(需要监督警戒的人)的范围。关于未成年人参与的共同犯罪,其规定:“诸窃盗年幼者为首,年长者为从,为首仍听赎免刺配,为从依常律。”(3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刑法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9、2111、2096页。意思是,在共同犯盗窃罪中,即使未成年人为主犯,成年人为从犯,未成年人也依然免去刺字和发配的刑罚并可以用金钱来赎罪。沈家本也在《历代刑法考》中引用了《元史·刑法志》的这一规定。(3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4页。
明律只是将唐律中“老小废疾”条改为“老小废疾收赎”,内容基本相同。(32)薛允升撰,怀效锋、李鸣点校:《唐明律合编》,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52页。《大清律例》的“老小疾废收赎”条规定:十五岁以下犯流罪的可以收赎;十岁以下杀人(谋、故、斗殴)应被判处死刑的,有上请的机会,伤人的,也可以收赎;七岁以下虽然犯死罪但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33)张荣铮:《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118页。结合该条下的解释条(第一百一十条):“七岁以下致毙命之案,准其依律声请免罪。至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死者长于凶犯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若所长止三岁以下,一例拟绞监候,不得概行双请。至十五岁以下,被长欺侮,殴毙人命之案,确查死者年岁亦系长于凶犯四岁以上,而又理曲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34)张荣铮:《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118页。这条判例是依据雍正年间发生的未成年人斗殴案子所形成的,是对“老小疾废收赎”条的细化。此“条例”不仅考虑到年龄,也考虑到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年龄差和犯罪原因。
沈家本在引用该判例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修改后成文为:“七岁以下致毙命之案,准其依律声请免罪。至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死者长于凶犯四岁以上,或长于凶犯不及四岁而理曲逞凶,准其依律声请。若所长不及四岁而又非理曲逞凶,一例拟绞监候,不得概行双请。”(35)沈家本:《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可以看出,沈家本拟扩大本判例的适用范围,注重考虑未成年人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即考虑犯罪原因——“理曲逞凶”和年龄的结合。这就说明沈家本的恤幼思想较之传统恤幼思想更为具体且周全。沈家本删去“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八字,将判例规范化,也更加靠近近代西方的法典编纂体例、规则。
(四)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遵循“从幼从轻”原则
中国古代的恤幼思想还体现在刑事责任年龄认定方面,遵循“从幼从轻”原则,即对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罚时,是以犯罪行为实施时的年龄为标准,而非以犯罪行为被发现时的年龄为标准。《唐律疏议》中“犯时未老疾”条规定,实施犯罪行为时年龄较小,进行刑事审判时年龄已大,按照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36)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第93页。按照唐代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七岁犯死罪的未成年人,即使八岁再进行审判认定,也不予追究责任;十岁实施杀人行为或犯其他重罪,十一岁时才被发现,依然可以获得“上请”的机会;十五岁时犯非重罪的罪行,十六岁时被发现,“收赎”的代偿性惩罚措施依然可用。(37)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第93页。这种以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年龄为判断标准的原则,不仅体现出唐代立法的先进性,也充分表现出对“小”“幼”者的特殊保护。
唐代以后的朝代借鉴沿用了唐律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宋刑统》延续了《唐律疏议》的大部分内容,对未成年人的怜恤政策也不例外,包括承袭唐律的“从轻从幼”原则。《元史·刑法志》“盗贼”篇规定:“诸幼小为盗,事发长大,以幼小论。”“其所当罪,听赎,仍免刺配,诸犯罪亦如之。”(38)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刑法志》,第2096页。幼时实施的犯罪行为,成年之后才被发现并审判的,按照实施犯罪时的年龄认定 。
沈家本在考证古代恤幼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还从深层次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老小”怜恤思想的根源,他认为,从《礼记·曲礼》的“悼(七岁)与耄(八十、九十)虽有罪,不加刑焉”,到《尚书大传》“老弱不受刑”(39)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1800页。,以及后世宽仁恤幼理念皆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承接。
二、沈家本恤幼人道理念之西法借鉴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势,让参透中外局势的沈家本意识到融通中西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筹备“修订法律馆”,组织翻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并整理中国律文旧籍。同时聘请西方法学家为法律顾问、派遣留学生赴日本等国考察学习,清廷也派官员出席万国监狱会议等(40)周颖:《万国监狱会议之少年决议——以近代中国少年司法启蒙为视角》,《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 年第1期,第79页。,这些都为学习西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修律变法奠定了基础。
在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中,对少年儿童的特殊关爱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人道主义的概念最早来源于拉丁文,意为“人的,仁爱的”,拉丁语 Humanitas 是指“人道、人情以及教育、教养”等涵义。(41)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2页。资本主义初期,形成了“人道主义”的词汇 ,即英文中“Humanism”这一专有名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道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将这种理念运用到包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等内容的法律领域当中。
(一)考察欧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
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逐步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体系,这引起了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清廷修订法律大臣的关注,除了组织学者翻译引介欧美、日本相关法律文献,还组织官员赴欧美、日本参观未成年人法庭和监狱。此期,欧美发达国家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以各种形式呈现,主要体现为:
一是设置教育感化机构,以教育感化代替惩罚。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欧洲各国就出现了一系列儿童福利政策以及教育感化机构。1823年,法国设立收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职业学校(42)贾洛川:《罪犯感化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1908年,英国将在成年监狱服刑的未成年人移出并单独设立青少年感化院,对青少年进行特殊的管理和教育。(43)刘强:《英国青少年社区刑罚执行制度及借鉴》,《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3期,第105页。这说明此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已经逐步将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思想融入到其司法体系之中。挪威的儿童福利政策已经存在100多年,早在1896年就制定了《儿童福利法案》,其主要涉及的对象为有犯罪行为或存在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根据该法案的规定,对这些“问题”少年的教育引导应当取代对他们的监禁惩罚。
二是设置专门的“少年法庭”,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关照。1908年英国颁布了《儿童法案》,在普通法院中设立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涉及青少年的案件,将青少年所涉行为细分为不同种类,并以此进行针对性矫正。同年,德国也设立了第一个专门审理青少年犯罪的法庭,1911年又建立第一所青少年监狱,1923年颁布《少年法院法》。美国伊利诺斯州于1899年颁布《少年法院法》,并于同年建立起第一个少年法院,随后美国部分州相继建立起专门审理青少年犯罪的法院。187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中方参会人物李圭惊叹于美国少年司法的专业化程度,并写出《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将参观所见未成年人监狱和专门法庭以及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状况记录其中。有关专门监狱和法庭,“公堂审案处,内有监房,分男、女、幼童三等,各约五六间”;(44)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72、247、248页。有关教育感化机构,“费城有习政院。凡童稚男女,父母已故,无依倚者;或有父母而不能教者;或子女不肖不受教者,皆由院中收留,使习正道,俾免流于不齿,诚善政也。其制男女自八岁起至十六岁止无依倚者,由地方绅民报院收留,不能教不受教者,由其父母禀官酌拟年分发院收留”。(45)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72、247、248页。他在评价中流露出羡慕赞誉之意:“闻此院各省皆有之,非独费城也。各国亦皆行之,又非独美国也。观夫习政院与轻重犯监狱,皆主于化人为善也。”(46)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72、247、248页。
沈家本对欧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种感化教育对未成年人犯罪有较好的约束效果。他指出惩治教育始于德国,管理之法类似于监狱管理,但又以学校的名义命名,这便是强迫教育。各国效仿且都有显著的效果。所以沈家本建议清廷也应采用这种方法,设置类似的学校,对未成年人区别其犯罪情节轻重,并以此决定教育时间长短,便能达到感化的效果。”(47)《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并清单)》,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页。
(二)日本成为清廷模仿欧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桥梁
日本近代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发展主要以欧美等国为蓝本。日本早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一系列宽刑政策;后又受西方国家“拯救儿童运动”思潮的影响,建立民间感化院;1900年颁布的《感化院法》规定感化院既收容触犯法律的青少年,也收容还未实施犯罪行为但有较大可能触犯法律的青少年。感化院由私立机构逐渐变为公立机构,由福利性机构转变为强制性机构。(48)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向欧美各国学习的日本对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变革影响颇深,主要体现在《大清新刑律》和《大清监狱律草案》中。日本的“微罪不起诉制度”与“感化院运动”是日本刑事政策转变的标志(49)周颖:《近代中国少年司法的启动》,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57页。,对清末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对清末少年刑事司法改革有直接影响的是日本的小河滋次郎。小河滋次郎是沈家本聘请来中国协助指导监狱改革的授课老师之一,他撰写的有关监狱学方面的论著也较为广泛地被清政府翻译学习。(50)孙雄:《监狱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2页。如前所述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主要体现在《大清新刑律》中,而对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思想则主要体现在《大清监狱律草案》中。(51)周颖:《近代中国少年司法的启动》,第62页。“未满18岁之处徒刑者,拘禁于特设监狱,或在监狱内区分一隅拘禁之。”该草案虽然未被颁布实行,但其中的分别监禁制度和以感化教育为原则的制度均能体现日本教育感化思想对清末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建立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民国时期的相关法律条文中亦有体现。
总之,在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美各国开始建立起少年司法体系,感化教育机构和少年专门法庭的设立让保护弱小的人道主义关爱理念具体化、规范化。日本在学习欧美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过程中,也摸索出了适合本国的少年司法体系,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清末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走向。
三、恤幼人道思想对近现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形成之影响
西方人道主义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恤幼思想,成为清末修订法律时保护未成年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理论基础。沈家本既重视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学习借鉴,也重视对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延续。沈家本强调中西法律思想的融汇,认为:“旁考各国制度,采撷精华,有补于当世。”(52)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页。对西学的研究让他意识到脱离西方法学视阈的单纯修律是行不通的,融会中西、取各自之精华才是变法修律之道。这种汇通中西的思想,具体到未成人刑事法律体系上,体现为沈家本对西方刑事责任年龄和感化教育的移植引进。沈家本结合中西,最终形成的恤幼人道思想对近现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刑事责任年龄概念在法律中得到确认并逐渐系统化;其二,构建未成年人教育感化体系。
(一)“丁年”与“刑事责任年龄”的接轨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的“丁年考”篇,对“丁年”进行了解释,认为其类似现代“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丁年考》中,引用古籍解释“何为童”“何为幼”“何为未成人”,对“丁年”概念进行了区分和界定。《曲礼》:“童子不衣裘裳”,疏曰:“童子,未成人之名也。”《释名》:“十五曰童。”《冠礼》曰:“弃尔幼志。”是十九岁以前曰幼。在此基础上,沈家本得出结论:古者二十而冠,凡未冠者为未成人,则曰幼,曰童,不得谓丁也。(53)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页。由此,“冠”与“未冠”、“幼童”与“丁”被系统梳理、界定出来。
沈家本对中国古代唐律中的刑事责任年龄规范进行了详细解读,具体体现在《历代刑法考·丁年考》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总结。(5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页。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丁年考》中按照刑事责任年龄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不等,列举出各朝各代的“丁年”;同时也对西方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详实梳理。沈家本认为,按照《周礼·乡大夫》中的记载,周朝时已经用身高来判断年龄,并以此作为判断其是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标准,“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沈家本还认为,“丁年” 的说法大概源于晋代,其概念也大致如此,即不论是何朝代,达到一定年龄就需要承担赋税徭役的义务,同时享受被授予田地的资格权利。(5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页。沈家本强调,中西方在划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理念上颇为相似,中国古代的“丁年”与西方“承担罪责的年龄”均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年龄门槛,那些年龄未达到一定标准的人“辨别是非之心尚未充满,故无责任”。(56)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页。他还对西方多个国家新旧法律中的“绝对无责任”“相对无责任”“减轻时代”和“刑事丁年”进行了详细的列表总结,其中,最低的刑事丁年为十二岁,最高的为二十三岁。(57)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42、1332、1340、1331—1337、1340、1338—1340页。综合中西方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标准,沈家本最终在《大清新刑律》中确定“丁年”为十二岁,并强调:“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58)《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并清单)》,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下卷,第71页。这应该是我国近代有关刑事责任年龄最早的法理阐述。
实际上,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从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确定的十六岁,到1911年公布的《钦定大清刑律》(即通常说的《大清新刑律》)确定的十二岁,经历了数轮激烈的“礼法之争”。起初,《大清刑律草案》第十一条为“凡未满十六岁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命以感化教育”(59)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20、226、284、290、356、360、363、374、384、397、429、434、441,628—632页。,但之后学部、直隶、湖广、闽浙等地的签注清单均表示,不按照罪行轻重区分,直接将刑事责任年龄设定为十六岁过于宽柔,十六岁以下之人“亦有知识、臂力发达之时,若狂悖横行概不为罪,流弊滋甚”(60)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20、226、284、290、356、360、363、374、384、397、429、434、441,628—632页。,无法达到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的目的。于是,1910年《修正刑律草案》结合多国经验将年龄降为十五岁,但各方又认为十五岁“尚涉过宽,难保不别滋流弊”。(61)高汉成编著:《〈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补编汇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2页。最后,经过陈树楷、陆宗舆等众多议员又一轮论辩研讨(62)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20、226、284、290、356、360、363、374、384、397、429、434、441,628—632页。,《钦定大清刑律》正文最终确定“凡未满十二岁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命以感化教育”。(63)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第720、226、284、429、480页。十二岁的刑事责任年龄甚至沿用到1912年颁行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并认为,十二岁“最为适中,兹拟采用其制”。(64)高汉成编著:《〈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补编汇要》,第272页。可见,将刑事责任年龄设定为十二岁对中国近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影响甚为深远,这个年龄的确定也经过多方验证,具有一定合理性,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共识。
(二)近现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初步形成
沈家本认为,对未成年人应更注重教育而非惩罚。所谓:“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罚之主体”,因为未成年罪犯如果同成年罪犯一样被“拘置于监狱”,易受成年罪犯影响,出狱后的再教育会更加困难;(65)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而且,“未成年所贵乎教者,正以其识虑之未充满,而是非或有未当也。”(66)(67)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1341页。所以,对未成年人而言,刑罚更应是“最后之制裁”。(68)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沈家本针对未成年人“教”“罚”的辩证关系,指出:“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习,使为善良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69)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1341页。这种表述可以看出沈家本对未成年人犯罪感化教育的重视。同时,沈家本还建议,朝廷应学习西方的教育感化之法,设立感化院和少年监狱。可见,沈家本结合了中国传统恤幼文化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进而提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理念。
沈家本在其主持修订的《大清刑律草案》中提出,应效仿西方建立感化教育院,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提前预防和教育。但各省对于是否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意见并不统一。两广、两江、东三省在签注清单中都表示“俾施教育而资感化,命意甚善,宜可照行”。(70)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第720、226、284、429、480页。但如何建立,表示支持的省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建议。甘肃、直隶则在签注清单中提出反对意见,“置诸感化场施以特别教育,是纯用感化而非惩戒,断非中国所宜”。(71)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第720、226、284、429、480页。反对者认为,中国不可以直接设立西方模式的教育感化机构,否则会使实施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成为法律惩罚的漏网之鱼,于社会无益;“恐触法者既毫无惩戒于前,而施教者亦万难补救于后,弊端百出,莫可究诘,此万不可行于近日者也。”(72)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第720、226、284、429、480页。基于此,朝廷在《修正刑律草案》中对各省各部提出的反对意见予以反驳,认为:“感化教育乃减少犯罪之良策,各国行之其效卓著,不论何时何国俱可采用,从未闻有以民智未睿为口实而避之者。”(73)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第720、226、284、429、480页。最后,在《钦定大清刑律》中还是保留尝试感化教育的想法,但因其规定过于笼统,感化院的建立过程不尽如人意。
与感化院筹建同时开展的,还有改良旧式监狱和规划设立未成年人监狱。虽然沈家本力推的感化院的实施情况并不顺利,在“礼法之争”中被各方认为“为时尚早”,但为民国时期幼年监狱的设置奠定了一定基础。1910年《大清监狱律草案》第二条论证了设立少年监狱的必要性:“幼年犯罪之人,血气未定,往往一入监狱,传染种种恶习,不惟不能改良,且愈进于不良。”所以,应该“特设或区划拘禁场所,拘禁十八岁以下、刑期两个月以上的少年犯,对之进行惩治教育”。(74)尤志安:《晚清刑事司法改革整体性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252页。
清末设立感化教育机构和专门少年监狱的想法影响着民国时期少年司法发展的方向。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拟写司法计划书并送地方征求意见(75)民国司法部公报处、司法院秘书处等编:《司法公报》第1册第4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页。,其中包括设立少年专门法庭、筹备建立教育感化院的规划。(76)《司法计划书》,首都图书馆藏。但该计划实施之初便因人才、经费等问题不断变通、展缓,1913年司法总长许世英因宋教仁案等原因对袁世凯不满辞职(77)民国司法部公报处、司法院秘书处等编:《司法公报》第2册第10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页。,其司法计划遂基本搁浅。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感化学校暂行条例》,虽然该条例并不能被全面贯彻落实、较之他国的相关法律也显得单一且薄弱,但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未完善时也可视为具有进步性的过渡性文本。《感化学校暂行条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地专门教育机构及少年监狱的建成,如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济南少年监”,1935年建立的“武昌少年监”等。(78)朱胜群编:《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46页。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司法工作规划,拟定《司法部训政时期工作安排》,其中包括对少年司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79)民国司法部公报处、司法院秘书处等编:《司法公报》第55册第32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751—767页。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借鉴日本《少年法》制定出台的《审理少年案件应行注意事项令》,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则做了规制,并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少年法庭”的组织形式和审判程序。(80)李相森:《论民国时期的少年司法制度建设》,《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年第4期,第86页。遗憾的是,该草案同样未被实施,但为以后的少年司法建设奠定了基础。
梁漱溟说:“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81)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黄克剑、王欣编:《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沈家本认为,脱离西方国家的部分先进理念,单一延续中国传统法律,是无法立足并推广于世界的。(82)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23页。沈家本会通中西的恤幼人道思想,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仁”融入其中,又兼收西方人道主义的感化教育理念,已有百余年历史,并成为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源头,从根本上、长远地影响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样貌。这就需要我们深化对近现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起源、衍变规律的认识,从沈家本恤幼人道思想中寻找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历史解释方法,以预防、教育、惩罚相结合为原则,增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完善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