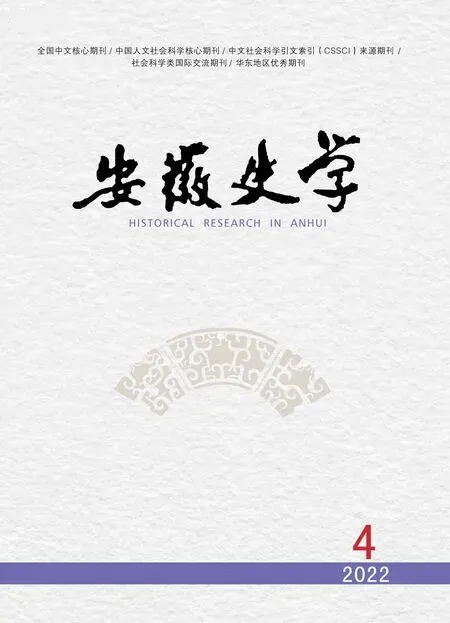清季士人群体的“明遗民”记忆及其政治文化效应
贾 琳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清季庚子(1900)至辛亥(1911)年间出现的前朝“遗民”记忆种子,究竟以何种方式作用于当时以及影响到民初“清遗民”的言语行为,仍然是一项有待深入探讨的学术议题。(1)关于明遗民及清遗民的研究,就所涉时段来看大都以朝代鼎革为限,较为缺乏两者之间内在关联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孔定芳《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版)、吴盛青Modern Archaics: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3)、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关于清末历史记忆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目前主要见于具有革命特质人物的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者如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87页。从“清遗民”生成角度来看,清季出现的前朝“遗民”记忆,似乎是以一种思想潜流和富于隐喻的方式与其发生关联作用;但是,清季“明遗民”记忆的效应远不止于被动展衍和接受。如果记忆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言说故事的行为(2)心理分析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曾提出“记忆行为”命题,“记忆是一种行为:本质上是讲故事的行为” (Memory is an action:essentially it is the action of telling a story)。参见Mieke Bal,Jonathan Crewe and Leo Spitzer eds.,Acts of Memory:Cultural Recall in the Present,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9,p.39.,那么按照“言语行动”(speech acts)的逻辑(3)参见[英]约翰·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著,杨玉成、赵京超译:《如何以言行事》,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我们便可以有从“记忆行为”(acts of memory)到“记忆行事”(memory acts)的视域转换,进而便有了考察清季士人群体或者说以之为泛主体的知识群体,如何将前朝“遗民”记忆作为一种能动性力量并转化为自身的政治言行生成逻辑,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改革讨论之中。此一时期由历史记忆激起的政治参与,必然涉及到政治认同以及前朝“遗民”记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果借用“景深”的表述,前朝“遗民”记忆的景深或者说具有内在张力的层累图景,有时反而会客观造就一种多孔性的思想结构,辗转构成清末民初国族认同的关键催生元素,从而呈现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复杂关联与跨时空互动。
一、记忆的政治参与:科场中的“明末三先生”
清季新政初期的科场一方面面临着自身被更新的压力,但同时也发挥着承载新政改革议题和各方话语的公共平台作用。新政改革施设时期包括官方命题与考生答题在内的科场书写,已远不止一般意义的知识性问答,而是带有更多切于时事层面的政治改革讨论意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江南乡试首场第三题为“宋神宗置太学三舍,厥后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起李纲即出自太学论”。(4)徐沅、祁颂威撰:《清秘述闻再续》卷1,法式善等撰、张伟点校:《清秘述闻三种》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2页。该题出自“靖康初金人围汴京,朝议罢李纲以谢敌,太学生陈东率诸生千余人上书宣德门”(5)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0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4、43—44、46页。这一北宋末年著名事件,并追溯其源头至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被取中第一名的曹清泉在解答该题时开篇即言:“国家之建设学校也,其为诸生砥砺气节,储蓄经济之地乎!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亭林顾氏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然则受朝廷豢养与名师长启迪,当国政日秕,不能发抒长策以扶持朝纪,岂所望于诸生耶?”(6)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00册,第351页。关于士子取中名次见于试题前履历页,以下不一一出注。其所引“亭林顾氏”语,出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原文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7)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中册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页。该题设计者的原初考量,是担心改科举、兴学堂后可能出现的学生议政以至言行不羁等问题,也即当时有人指出的“然而自兴学来三年于兹,学堂之规制既未大定,学堂之成绩亦尚未可预期,而学生之藉端龃龉相哗噪者时有所闻,未获学堂之益,先得学堂之害”这一情形。(8)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29册,第355—356页。曹清泉在试卷中肯定了学校及学生本应具有的弼政功用和社会担当,而做出这一肯定所基于的重要论据即来自对北宋相关人物和“明末三先生”之一顾炎武的历史记忆。
明清之际黄宗羲也曾对学校功用做过专门论述,这一历史记忆也被士子援引至科场之中。被取中江南乡试第六名的李筠寿在回答首场第三题时,有如下论述:“宋神宗初改科举以经义、策论试士之岁,立太学生三舍法,增其员、广其舍、优其途焉……其视太学之重如此。迨至养之既久,才之既成,则以匹夫之贱,而可与天子争是非之权。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则士遂不能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而争之天子;天子亦遂不敢以其是非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太学。夫士而能正天子之是非,斯真天下士矣,斯真太学生矣。”(9)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0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4、43—44、46页。其中便化用黄宗羲之语,来证成“太学”及“太学生”应当具备“伸是非之公论”和“争是非之权”的功用。其所引黄宗羲语出自《明夷待访录》“学校”篇,原文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李筠寿随后还在试卷中针对某些士人“丧其浩然之真”并指责“伸是非之公论”为“学校之习气”予以谴责:“气节之衰也,是非一出于当事者之口,方以荣辱人者为驭士之具。而士亦且科举嚣争,熏心富贵,遂以朝廷之势利,丧其浩然之真,稍有人焉欲伸是非之公论,则以为学校之习气,于是怀才负志者,自拔于草野之外独守其是非,而无与于学校,则国家于养士之道深失之矣。”(11)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0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4、43—44、46页。李筠寿此处同样化用黄宗羲语,却翻新其意。黄宗羲原文为:“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1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黄宗羲原本用来指责学校异化的句子,被该士子挪用转化为批评科举流弊并反衬学校优势的论据。
“明末三先生”记忆不仅出现在士子书写当中,还出现在考官阅读之中。担任光绪二十九年(1903)会试同考官的恽毓鼎在锁闱期间,即以阅读王夫之《宋论》充实闲暇时光:“初九日,晴。晓起查问节气,知今日已清明矣。棘闱扃密,孤(辜)负春光,不免触动旅思……午后剃头,阅王船山《宋论》卷七、卷八中两篇,一论元祐诸公,一论蔡京绍述新法。精识深论,皆从无字句处看出,绝非寻常死煞纸上之谈,数百年无此议论也。”(13)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九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从当时整个考官群体来看,考官对“明末三先生”的阅读记忆并非一闪而过,而是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命题行为。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作为国家级别的甲辰恩科会试首场第三题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14)徐沅、祁颂威撰:《清秘述闻再续》卷1,法式善等撰、张伟点校:《清秘述闻三种》下册,第1002页。该题干即出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其原句为:“申、商之言,何为至今而不绝邪?志正义明如诸葛孔明而效其法,学博志广如王介甫而师其意,无他,申、商者,乍劳长逸之术也。无其心而用其术者,孔明也;用其实而讳其名者,介甫也。”(1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2页。中式第二十五名士子章祖申在回答该题时说道:“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无其心而用其术者,诸葛孔明也;用其实而讳其名者,王介甫也。夫孔明之志正义明,介甫之学博志广,要皆有大过人之才,乃同此申、商之学,孔明用之而蜀小康,介甫用之而宋大乱,何欤?窃尝就船山之言推而论之,盖申、商者,可以用其术而必不可有其心也,既已讳其名则必不可用其实也。”(16)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90、92页。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所引用,与王夫之原句相比,多出“诸葛”“王”三字姓氏衍文。这种情形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造成:一是因晚清科场管控不严(17)这种不严由多种因素造成,如制度层面的管理松圮、印刷技术提升带来的防弊难度加大以及晚清重视实策背景下官方一定程度的默许。如时人提到:“盖自石印书大行,诸士子率以对实策相矜,凡场中可用之书,无不携入。”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8页。,士子得以挟带王夫之著述入场。如张謇丙戌科会试即被同号舍的张一麐发现:“视其舍则垒垒者,《文献通考》,辽、金、元、明史满坑满谷,夹带特多。”(18)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古红梅阁笔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434页。但是,章祖申征引文字与王夫之原句并非完全吻合,且考虑到考生入场前恰好选中王夫之特定书籍卷册挟带的概率较小,故此种可能性不大。另一种便是,当时士子完全凭借对王夫之著述的熟稔记忆默写作答,其中两处姓氏误差似乎更反衬出这一可能存在的合理性。但无论哪种可能情形,都在一定程度表明王夫之著述的广泛渗透以及考官和士子对于王夫之著述接纳程度之深。因为单凭机械记诵,即使士子挟带相关书籍入场,其结果也很可能如前述张一麐和其描述的张謇那样,虽有“满坑满谷”书籍在侧,“对策题下,余所不知者,问之则亦无有,但曰:‘吾惟以比例之法遁空耳。’榜出俱落孙山。”(19)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古红梅阁笔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434页。在答卷末尾,章祖申亦不忘给当时的新政改革致思方向提供建言:“后之为治者,当政宽民慢之日,为厉世磨钝之图,申、商之法术未尝不可用之,夫亦视用之者为何如人耳!”(20)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90、92页。不过,此点显然已超出王夫之原著中“知其为导谀劝淫之术也,能勿腼然而汗下与”(2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2页。的批判本意,而带有了更多的引申理解。
二、记忆的共相与殊相:围绕“尚武”“爱国”的赋义和政争
章祖申答题中“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与梁启超所撰《王荆公》中“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22)梁启超:《王荆公》,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6、1739页。的表述完全相同。虽然《王荆公》正式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2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3页。,但是梁启超从最初构思到零星写作和陆续成篇则较为靠前,所谓“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24)梁启超:《王荆公》,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6、1739页。如果再联系章祖申对王夫之原意的引申理解,这就让人进一步想到清季士人群体或知识群体间“明遗民”记忆的互通和共享,以及对这些记忆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赋义并由此发生的政治论战,亦即“明遗民”记忆的“共相”与“殊相”问题。
光绪三十年甲辰会试首次在国家级别的考试中出现“国民教育”类试题,题干中对“国民教育”的释义为:“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25)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119、253—254页。取中名次较为靠前的试卷中,普遍出现士子对国民教育的“尚武”特质予以充分认可并重点阐发的倾向。如第六十八名傅增濬在试卷中答道:“普之败于法也,奋发淬厉,人无不学,而国民教育之制昉于此,不数十年摧奥败法……日本变政,事事步武德国,其人民宿重武士道,于尚武之精神尤近。三十余年,以残弱破败之邦,骤几强大,寰球惊悚。”(26)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119、253—254页。如果梳理此一时期“尚武”话语的衍生脉络,就会发现其与“明遗民”记忆亦发生密切关联,并在不同群体间形成互通和共享。
一方面,当时代表性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刊载但焘《黄梨洲》一文,其中提到:“起视其世,不明权限,不尊人格,其国民无尚武之观念,无进取之志略。虽永乐间郑和游踪达于南洋诸岛,沿亚非利加之东海岸而归,为航海术之发达,而于拓地殖民之业无影响,真黄族近世之遗恨哉!”(27)但焘:《黄梨洲》,《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第19页。此处虽是论述“黄梨洲当时之时势与学风”,但根据后文“吾人由今日遥想吾旷世英雄黄梨洲,当地折天倾山哭海泣之时,而发此宏大之福音,其属望于未来之国民者甚厚”(28)但焘:《黄梨洲·第四章黄梨洲之爱国心》,《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第21页。,作者以黄梨洲时代“其国民无尚武之观念”比附“今日”情形并且寄寓改观的意愿甚为明显。
另一方面,梁启超自1902年在《新民丛报》陆续刊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29)该系列1902年12月《新民丛报》第22号刊毕“第六章第四节”后中辍,至1904年9月《新民丛报》第53号续刊,题为“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参见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将明末清初“五先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学术思想的“共通性”归纳为四点,分别为“以坚忍刻苦为教旨相同也”“以经世致用为学统相同也”“以尚武任侠为精神相同也”以及“以科学实验为凭借相同也”(3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04—106、105—106页。。对于第三点“以尚武任侠为精神相同也”,梁启超从上述“五先生”又集中于顾、黄、王“三先生”进行论述:“顾、黄、王三先生,历参鲁、唐、桂三王军事,其勇略章章在耳目也。船山《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诸作,痛叹于黄族文弱之病,其伤心如见也……以口碑所述,梨洲绝擅技击,亭林亦然,习斋亦然。凡此诚不足以为诸先生重,虽然,此亦国粹之一种,言尚武者所不可废也,而诸先生皆躬娴之。”(3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04—106、105—106页。如果联系到1903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发的《论尚武》,包括其中提及的“顾乃能摧奥仆法,伟然雄视于欧洲也,曰惟尚武故”(32)中国之新民:《新民说》第17节《论尚武》,《新民丛报》第28号,第2—3页。该句意与上述傅增濬作答“不数十年摧奥败法……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亦有相似逻辑可寻。,以及湖北士子朱峙三观察到的当时科举考试各省中举卷多有模仿《新民丛报》《中国魂》等刊物者:“午后将郑宅借来之《新民丛报》《中国魂》二种,一一阅读之,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33)朱峙三著、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我们甚至可以约略看到《新民丛报》《中国魂》等海外具有改良或革命倾向的书刊所负载的“尚武”话语,向当时科场渗透并与之发生互动关联的作用脉络。出现国民教育试题的甲辰会试甫结束,梁启超又撰成《中国之武士道》,他在自叙中说:“今者爱国之士,莫不知奖厉尚武精神之为急务”(34)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自叙》,《梁启超全集》第5卷,第1386页。,颇有回应和总结国民教育试题的官方设问与考生作答之意。(35)该策题设问为“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119页。此一判断如果结合梁启超在该书凡例中所述缘起,似乎更加能够坐实:“初撰此编,原欲以供士夫之参考,一二友人见之,谓宜稍整齐之,使适教科用。盖欲使全国尚武精神,养之于豫,而得普及也,故为今体。”(36)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凡例》,《梁启超全集》第5卷,第1387页。倘若再考虑到此一时期乡、会试题纸进呈、朝廷磨勘以及试卷刊刻等建制性传播渠道,如恽毓鼎日记中所述:“晨起,写进呈头场题目纸。阅已荐之二场卷,尽有极通达者,吾辈断不如也。傍晚仍偕闰、聘至大、明两处稍谈。光堂交下拟刻湖北卷第三篇,灯下细为删润。”(37)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第219页。前述承载“明遗民”记忆的相关文字亦可上达至朝廷中枢,并最终在朝廷决策层、考官、考生以及处于权力边缘的改良者或革命党人之间,形成一种覆盖广泛、跨越边界的记忆共相与共享。
当然,这里的“明遗民”记忆共相之下还隐藏或者说潜在关联着至少两重记忆殊相:一重为对于“爱国”“国民”等“国”的理解,另一重为对这些记忆进行不同政治赋义后发生的政治论战。
就第一重殊相而言,《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续刊但焘《黄梨洲》一文,作者在第四章“黄梨洲之爱国心”中说道:“立于社会进化之时代,而不能养成国民之爱国心,利用民族之能力组织一团体国家者,其国土必夷为殖民地,其国民必降为贱种……黄梨洲之爱国心,非文学家的爱国心,而历史家的爱国心也。”(38)但焘:《黄黎洲》,《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第20页。他还特别提醒读者:“梨洲有哭沈眉生逸民诗,云‘中间我寄书,同怀千岁忧。人种系一粒,霜雪宜共耰。宛其两人死,茫茫来者愁’。吾人由今日遥想吾旷世英雄黄梨洲,当地折天倾山哭海泣之时,而发此宏大之福音,其属望于未来之国民者甚厚,此实崇拜黄梨洲之爱国心者所不可不提出之问题也。”(39)但焘:《黄黎洲》,《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第21页。原诗中“人种系一粒”作“人种系芒粒”。黄宗羲:《读苏子美哭师鲁诗次其韵哭沈眉生》,《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显然,这里的“爱国”之“国”更多是指被清廷征服“人种系一(芒)粒”之“人种”或者说基于一种种族预设。此点在后来《复报》刊发的《中国灭亡小史》第二章“灭亡后之中国·三大思想家”中展露得更加明显:“痛陈夷夏之防,发愤君民之际……其诸民族主义之导师而革命军之鼓吹者欤?若船山王氏,若亭林顾氏,若梨洲黄氏,盖遗臣佚士中之巨擘而近世所称三大思想家者也。”(40)中国少年之少年编:《中国灭亡小史》,《复报》1906年第5期,第13页。但对于清廷而言,所谓“爱国”“国民”等“国”,所指显然不同。就在但焘《黄梨洲》刊发当年,1903年顺天乡试第二场策题有“学堂宜设国文专科策”。(41)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130册,第99、102—103页。被取中第六十九名的史纪常将“国文”理解为中国之文字,也即从“国”字的国家预设或者说国族预设来理解:“论者谓,中学深则西学浅,西学深则中学亡,其庶几免欤?呜呼,文字者,一国之精神所寄,而尤为我中国数千年之经常政教所赖以留贻者也。人不通文字,则无知无觉之动物耳,合四万万余人而半为无知觉之动物,欲种族之明且强,顾可得耶?”(42)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130册,第99、102—103页。其中虽然出现“种族”一词,但完全可以等同于“国族”概念。史纪常这种基于“国族”的理解显然符合清廷出题本意。不过,将“国文”理解为“满文”,也即将“国”理解为“满洲”者亦不乏其人,如沈钧儒卷中出现:“夫国文与汉文等也……今之醉心西学者,沾沾于英、法、俄、德之文,而国文顾未之及,不特有违忠君爱国之志,即其以西语为适用,亦未为知各国深情矣。”(43)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129册,第441—442、421页。沈钧儒这一理解显然越出了官方命题本意,但考官并未将其黜落,而是在荐批中写道:“首以国文为满洲文,解虽误会,而能源源本本,藉抒忠君爱国之忱。末举俄人设立满语学堂为砭,尤足发人深省。”(44)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129册,第441—442、421页。最终沈钧儒同样被取中,且位列该科第十九名。这里的“国”字同样是基于种族预设,却得出与革命党人完全相反的训释,而考官荐批中“藉抒忠君爱国之忱”的“国”,按照出题本意和前后语境,又系指“国族”意义的国家。
另一重殊相为对“明遗民”记忆进行不同政治赋义后发生的政治论战,这也可以视为“明遗民”记忆及其所隐喻不同政治观点的角力竞争。早在戊戌前后,章太炎就曾以王夫之的著述来抗衡“康氏之门”对黄宗羲学说的推崇,并且将其视为种族革命与维新改良的分野:“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亦或儳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45)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72),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第15—16页。虽然“太炎于前明遗老,推服船山至上”(46)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199页。,但即使同为革命党人,亦有极度推崇黄宗羲而稍贬抑王夫之、顾炎武者。如署名“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亚子)(47)柳亚子此署名亦有与梁启超角力意味:“当时的梁任公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蔚丹和他闹别扭,翻一下身,便变做了‘中国少年之少年’,意思是少年中间的少年,当然更近一层了。记得蔚丹是把这七个字送给我,当作我别署的。后来我写《中国灭亡小史》,在《复报》上发表,还用它做笔名呢。”柳亚子:《五十七年》,柳无忌、柳无非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54页。所撰《中国灭亡小史》第二章中说道:“比较三家之学说,思想高尚议论精辟,而高掌远跖足为他日新中国立国之基础者,其梨洲哉!船山政见稍偏于过去,而专精致一于种族之义,则虽梨洲犹稍逊,今日复仇主义之先导,非船山莫属矣。亭林学术似近专制,近世有不满之者,然读其遗诗,虽顽佞者犹当激发天性,作驱除光复之想,其视匍匐异族之下而高谭梦俄罗斯者,相去宁能以道里计耶?”(48)中国少年之少年编:《中国灭亡小史》,《复报》1906年第5期,第14页。“高谭梦俄罗斯者”特指梁启超,柳亚子曾道:“以后他撰《新大陆游记》,说什么‘游美利坚而梦俄罗斯’,觉得非常可笑,简直是在开倒车。”柳亚子:《五十七年》,《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144页。不过,在其后关于“明末三先生”从祀孔庙的讨论中,一些满洲贵胄极力摒斥黄宗羲的行为竟又与章太炎不谋而合,这颇让章太炎感到奇怪,他在《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中将黄宗羲与杨度列为“异世同奸”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乃满洲贵胄无所恶于衡阳王氏,而恳恳欲黜余姚,汉人之处枢密者则愿为余姚藩蔽,斯可怪矣!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余姚者,立宪政体之师”,“今之言立宪者,左持法规之明文,右操运动之秘术,正与余姚异世同奸矣。满人方主立宪,而竭其唇吻之力以斥余姚,此可异也!将以蔑视君主为嫌耶?蔑视君主之为忧,未若攘斥胡虏之为忧,衡阳所著则有《黄书》《噩梦》,其尊汉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今于衡阳反无一言,岂彼满洲贵胄未睹衡阳之书耶?”(49)章太炎:《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民报》1908年第22号,东京秀光社1908年7月10日,第41—42页。言“满洲贵胄未睹衡阳之书”,根据前文所述显然与事实不符。但在此点清廷的实际作为又确与一些革命党人客观上形成一种合力,使得关于王夫之的“明遗民”记忆在清末扶摇直上,其政治效应亦如章太炎所述:“明末三大儒,曰顾宁人、黄太冲、王而农,皆以遗献自树其学。宁人书自初刻已被删改,近世真本始见于世;太冲议论不甚系民族废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50)章太炎:《重刊船山遗书序》,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第441页。章士钊对此更是简洁表述为:“果也,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51)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199页。至此,“明遗民”记忆作用于当时政治异乎寻常的能动性和辐射力已是显露无遗。
三、记忆的“国族”进阶:传统族群认同的迭代转化
清廷之所以默许或接受“明遗民”记忆进入科场甚至孔庙,主要基于朝廷试图通过将其经世学理尤其是与当时国民教育内涵密切相关的“忠爱之特性”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来获取更多的变革理论与合法性资源。如甲辰恩科进士章梫所言:“或有议者谓,三儒皆胜国遗老,有不满本朝之隐衷……又有议者谓,近今种族之说发于夫之之《黄书》,其流为革命排满,民权之说发于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其流为平等自由。不知《黄书》乃惩明弊,规画治世之大纲,并无所谓革命之语;《待访录》依据《孟子》《周礼》,亦惩末世骄君谄臣之失而反之于正,更无所谓平权自由。凡革命排满、平权自由等语,皆中国浅人略涉东西国一二家之学说,如染狂毒,如饮鸩酒,不自知其身之生死,并未尝窥见船山、梨洲之书。苟略读船山、梨洲之书,忠爱之心油然兴发,岂复有革命、平权等事乎?”(52)章梫:《一山文存》卷8《先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29),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371—372页。但根据辛亥之际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谬》序中描述,“如以君为‘天下之大害’及‘在君为路人’,与夫伐鼓号众、士子哗而退长官之说,皆为今日之革命独立、监督政府诸悖说所藉口”(53)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谬序》,《明夷待访录纠谬》,1911年铅印本,第1—2页。,清廷此举似乎近于冒险与失当。
由“明遗民”记忆激起的基于种族预设的“民族主义”,直到章太炎所谓“光复之绩”完成的民国初年,仍被认为影响着当时“国民教育”大计的推进。(54)参见《一月一日大总统申令》及《国民教育》时评,《申报》第132册,1915年1月3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8页。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但易被忽略的问题面向值得注意,即但焘在《黄梨洲》文中所揭橥:“吾闻西方之学者曰:‘支那者,一家族之社会也。’吾尝纵观历史,遍察内地,未尝不引西人之言,以自悲吾国人国家思想之薄弱。”(55)但焘:《黄梨洲》,《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第17页。如果联系到前述关于“爱国”“国民”等“国”的不同诠释,这种殊相的造成固然有知识群体依据自身政治立场对“国”字进行主观赋义这一因素,但这些赋义行为能够在社会层面被不同程度接纳并传播开来,客观上得益于或者说更深层面折射出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国家思想之薄弱”,以及与之伴生的“国”概念界定与认知的模糊含混。更为关键的是,对于“国家思想之薄弱”的传统政治实体,如何跃迁和达致近代意义的国族认同,其实存在较大的跨越级差。而经由狭义预设的国民概念,渐次替代臣民概念并强化国家观念,以之为过渡进阶到广义也即整全意义的国族认同,便构成一条被认为可行的逻辑进路。当时确有人观察到在列强扩张背景下,也即梁启超所谓“况今日迫我之白人,挟文明之利器,受完备之训练,以帝国之主义,为民族之运动,其雄武坚劲,绝非匈奴、突厥、女真、蒙古之比”(56)中国之新民:《论尚武》,《新民丛报》第28号,第5页。,清季“明遗民”记忆激起的“民族主义”恰可以经由这种广义的进阶转化,发挥出积极的效应:“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57)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4年6月24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1899年杨昌济所定课业中即包含王夫之著述:“余之自课凡有六焉:日记一也,《皇朝经世文编》二也,《御批通鉴辑览》三也,《宋论》四也,闱墨五也,英文六也。”(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第1页。)这也构成其对明遗民记忆形成通贯理解的必要条件。
“明遗民”记忆的此种进路在清末民初鼎革之后继续被保有,并在团结国民、抵御外侮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胡山源在1938至1940年间,陆续刊布《明季忠义丛刊》系列书册。(58)该系列包括《江阴义民别传》(世界书局1938年版)、《嘉定义民别传》(世界书局1938年版)、《各地忠臣遗事》(世界书局1940年版)、《各地义民遗事》(世界书局1940年版)等。陆高谊在“丛刊”序中提到:“或曰:今兹五族共和,汉满一家,胡为乎旧事重提?余曰:非也。《明季忠义丛刊》者,以外形言,固为表彰明季忠臣义士,动人观感;以内容言,则为提倡民族思想,发人深省者也。盖凡为国民者,皆有民族自卫之责任,苟有一技之长,即当出其全力,以为国用。”(59)陆高谊:《明季忠义丛刊序》,胡山源:《各地忠臣遗事》,第1—2页。至此,如果我们回溯此一进路的源头,就会在本文探讨的清季“明遗民”记忆中找到其带有异样感的远端,并且可以看到前朝“遗民”记忆的进阶尝试与传统族群认同的迭代转化,而这也构成“明遗民”记忆参与之下清末民初国族认同重塑或再生的一种演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