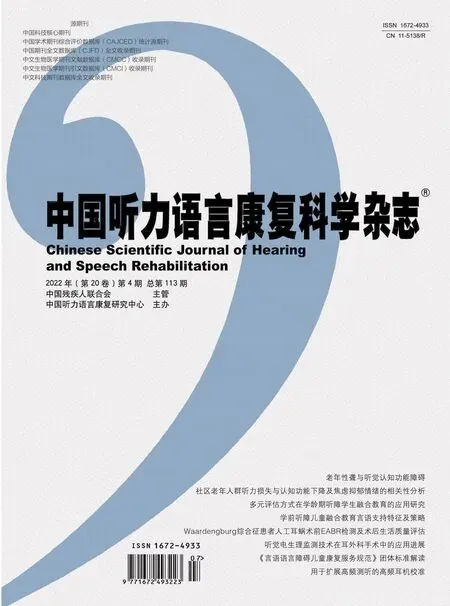老年性聋与听觉认知功能障碍
刘玉和
1 老年性聋概述
老年性聋是当下老龄化日益显著的社会中非常普遍的疾病,是严重威胁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慢性疾病。在老年群体中,老年性聋发病率仅次于心脏病和关节炎[1],成为老年人第三大常见慢性病。老年性聋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从40岁时的2.8%~3.9%增加到65~75岁的18.7%~26%、75岁以上的34.8%~43.6%到85岁时的51.8%[2]。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老年性聋患者占听障患者总人数的34.1%[3]。在高发病率的基础上,老年性聋会对老年人产生多维度的危害,因此逐渐受到重视。首先是言语沟通障碍:老年性聋会直接导致聆听困难,进而产生沟通障碍,使老年人交流和表达的欲望下降,言语表达能力下降[4]。第二,情绪改变及社会交流障碍:在沟通障碍的基础上,老年性聋会导致老年人社会孤立、心情低落、孤独感,产生一系列抑郁情绪等心理问题[5]。第三,安全及健康隐患:老年性聋是老年人体质脆弱的独立危险因素[6],主要表现为无意识的体重下降、自我感觉疲惫、虚弱、步行速度减慢和体力活动减少。进一步导致老年人行走缓慢、步态不稳、摔倒增加以及反应性、警觉性下降[7],使住院率和死亡率升高[8]。老年性聋还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Uhlman等[9]首次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听障老年人患痴呆的风险明显提高;Lin等[10]报道了在长达10年的随访时间里,轻度、中度、重度听力下降者患痴呆的风险各增加了2、3、5倍;每10 dB听力损失,将提高痴呆风险约1.27倍,且听力受损与认知加速下降率相关[11]。年龄相关听力下降(尤其是中枢听觉系统功能下降)可以早于(约5~15年)认知能力下降及老年痴呆症的发生,使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提高两倍[12]。2017年和2020年《柳叶刀》痴呆症委员会将听力损失确定为痴呆症的最大可调整风险因素[13,14],预计如果消除听力损失,痴呆症患病率将降低8%[14]。如果每个老年性聋危险因素的患病率每10年降低10%~20%,到2050年,全世界的老年痴呆诊断数量可能会减少880万~1620万[15]。可见老年性聋与老年性认知功能障碍间具有密切联系。
2 老年性聋的发病机制
从病理学角度,老年性聋可分为感音性、神经性、血管纹性、耳蜗性、中枢性及混合性6种类型[16]。突触障碍型也是老年性聋一个重要的类型[17]。从病因学角度,老年性聋致病因素繁多:外在因素主要包括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噪声暴露时间、耳毒性药物使用剂量、病毒感染、工业化学品接触史、不良生活习惯(吸烟、饮酒)及慢性病等。内在因素包括线粒体功能不足(线粒体DNA突变)导致耳蜗供能不足、某些核基因突变导致老年性听力损失的易感性增加(例如GRM7、GJB2、MYO6)、耳蜗细胞凋亡增加、氧化应激及自由基增加导致耳蜗及毛细胞的损伤、耳蜗微循环障碍等原因。上述病因中部分因素本身也是老年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针对老年性聋病因学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其与老年性认知功能障碍之间关联的理解。
3 老年性聋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老年性聋可以对听觉皮层的形态和功能两方面产生影响。老年性聋患者可出现默认模式网络的神经节、右侧岛叶[18]、右侧角回[19]、右侧颞叶[20]出现灰质萎缩和体积下降,皮质变薄[21],这种形态学改变可能反映了一种代偿性机制。扣带回-盖神经网络(cingulo-opercular network)被认为是注意网络的中枢,老年性聋患者中可观察到前扣带回皮层体积下降[18,22]。老年性聋与脑脊液中Tau蛋白水平升高有关[23]。此外,老年性聋及噪声下言语识别表现下降可能与兴奋性(谷氨酸)和抑制性(甘氨酸和GABA)神经递质氨基酸功能降低有关[24],从而导致听觉系统中的抑制机制随年龄增长而减少[25]。老年性聋患者出现视-听皮层整合功能下降,影响感觉皮层间的功能连接[26];老年性聋患者皮层下边缘网络、默认模式网络、执行控制网络和注意网络的功能连接明显降低,同时,听觉网络、视觉网络和默认模式网络的功能连接增加,表明老年性聋与网络内及网络间功能连接的改变有关[27]。
除了对听觉皮层的影响,老年性聋也可以通过影响中枢听觉通路导致中枢听觉处理障碍(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 disorder,CAPD),进一步提高认知功能下降及老年痴呆的发生率[28,29]。老年性聋会对认知体系中的不同维度产生影响,其中主要包括选择性注意力下降[30]、执行处理能力(工作记忆[31]、认知灵活性[32])下降及抑制控制能力不足[33]。由于认知系统是一个交错的资源网络,各维度间密切关联,且处理速度、注意力、抑制控制力本身易随年龄老化而下降,晶体智力、长期记忆相对不易受年龄或听力状态影响而下降,因此不同维度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增加老年性聋患者的认知压力。
近年来,学者不断关注老年性聋与认知功能的关系,逐渐总结归纳了以下共病假说以解释老年性聋与老年性认知功能障碍间的紧密联系[34]:①共同病因假说:老年性聋及老年性认知障碍均由于大脑广泛神经元退化导致,存在共同病因对两者产生作用,如全身性疾病导致机体抗氧化能力降低、血管弹性下降[35]。②感觉剥夺假说:听力下降导致听觉皮层受声学刺激减少,从而使大脑的功能和结构发生改变,听觉皮层功能重组[35],即老年性聋通过影响听觉认知系统导致整体认知功能下降。③信息退化假说:由于老年性聋导致语音信号的编码和利用能力下降,因此需要调动更多认知资源对其进行加工和处理,使其他任务认知资源不足,从而导致整体认知能力下降[36]。④认知资源分配失衡假说:认知功能减退先于听觉障碍,导致可分配至听觉信号处理的认知资源减少,从而导致听觉能力下降[37]。⑤听力下降导致社会孤立,甚至产生不良情绪的,增加了认知功能减退风险,两者恶性循环[38]。
4 老年性聋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具体表现
基于上述对发病机制及共病机制的认识,老年性聋的临床表现不仅限于外周听觉系统、中枢听觉系统,还存在于听觉皮层及非听觉的神经网络。其中外周听觉系统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的进行性加重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其中拓展高频(10~12.5 kHz)听力下降可出现更早,且程度更严重[39]。老年性聋也会导致在不利聆听条件下的语音感知障碍,例如聆听方言以及在噪声环境、回声下聆听。中枢听觉系统障碍主要表现为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下降,双耳整合能力和分听能力下降[40],表现为声源定位能力下降、语音分离能力下降(gap detection),进一步表现为言语理解能力下降和语速对言语理解能力的影响明显增加。中枢听觉系统功能障碍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比外周听觉系统功能障碍更显著[41]。中枢认知系统功能障碍可表现为对语音信号处理速度和处理水平下降[42],如双人对话时反应速度下降,言语理解能力下降、语言信息维持能力下降,如记忆力下降,难以进行深度交流[43],听配能增加(如自觉聆听费力,注意力下降,甚至放弃聆听等。长此以往将导致老年人严重的沟通交流障碍、性格孤僻、社会隔离等精神心理和社会问题,最终导致轻度认知障碍,甚至老年痴呆等[44]。较高的智力、受教育程度、职业等级,以及积极参与业余活动和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老年性聋患者的认知表现[45~47]。
5 老年性听觉认知功能障碍的检查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老年性聋与老年性听觉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已经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的相关性和针对其发病机制的探索,如何进行有效的听觉认知能力评估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成为老年听觉认知障碍领域的一大挑战。目前国内对于听觉认知障碍的评估主要分为主观和客观评估。主观评估主要包括认知评估筛查量表、全面成套式认知功能测试以及各认知维度的单项测试。认知功能筛查量表主要应用于早期认知功能障碍及老年痴呆的临床筛查,包括简易精神状态筛查量(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等。全面成套式认知功能测试尝试从不同认知维度解释受试者的整体认知状态,主要包括H-R神经心理测验(halsteadreitan neuropsychological battery,HRB)、剑桥自动化成套神经心理测验等。这些评估关注受试者的整体认知表现。考虑到听觉认知功能的特殊性,这类评估并未对听觉能力进行考量,且评估听觉认知功能的敏感性稍差。此外,有些学者使用阅读、空间、数字广度测试等方法对受试者工作记忆能力进行评估;使用连线、词语流畅性等测试方法评估受试者处理速度;使用Stroop色词测试、Go/Nogo任务等方法评估受试者抑制控制力。由于听力损失影响评估过程中的语言交流,可能影响认知功能评估结果而产生一定偏倚,因此有些研究人员采用非言语的认知功能评估方法评估这类患者听觉认知功能下降程度。但其问题在于测试材料缺乏听觉言语信号的特点(例如背景噪声及信噪比),无法反映现实生活中受试者的聆听状态。此外,通过双耳分听和双耳整合能力的评估,可判断中枢听觉系统处理能力[29]。
客观性测试主要包括近红外光学脑成像、脑电、脑磁图、PET脑显像、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新兴的脑功能成像技术,从而评估在不同刺激条件下各个脑区的功能以及脑区间功能的连接,窥视大脑的活动情况。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技术主要记录各个脑区的血流动力学变化,通过含氧量的改变判断脑区的活动。脑磁图是对脑内神经电流发出的生物磁场信号的直接测量,定位准确,反映脑功能的瞬时变化状态。脑电则将脑部的自发性或诱发性生物电位加以放大记录而获得的图形,用于判断大脑的功能变化。PET脑显像则通过不同的显像剂,观察大脑功能活动与血流代谢变化的关系,从而完成痴呆的鉴别诊断、癫痫病灶定位、认知激活显像等。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通过采用弥散加权及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BOLD)法,利用氧合血红蛋白和脱氧血红蛋白磁性的差异,判断局部神经元的活动,阐明高级神经生理和神经心理活动方式和皮层间的功能联系。客观性测试在认知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探索,但由于其操作过程复杂,测试时间较长,或时间、空间分辨率等原因无法在临床中快速应用和评估。
此外,听配能检测评估是近年来关注的主要用于听觉认知资源分配的评估方法,采用主观或客观方法进行检测。听配能是指人们在执行听觉任务过程中主观支配调动的各种认知资源[48]。目前常用的听配能检测手段包括主观评分、心电、脑电、皮肤阻抗以及瞳孔检测等。用瞳孔测量的方法评估听配能是目前较为新兴的手段。瞳孔大小被认为是认知加工负荷的指标,也是评估听配能的常用方法。这种方式测得的听配能具备良好的时间分辨率。
针对听觉认知能力,目前国内团队率先开发了“重复-回忆”检查(repeat-recallTest,RRT),要求受试者在不同噪声环境下对扬声器播放的语句(关键词)进行重复及回忆,并评估其主观听配能及对噪声的忍耐时间。通过这样的范式达到评估听觉工作记忆、语境利用和维持能力,并反映聆听者现实聆听状态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兼顾注意力、抑制控制力、处理速度的评估。但对其他听觉认知功能维度,例如抑制控制、注意力等老年性聋较易累及的维度,有针对性的评估手段仍待进一步开发和临床实践。
6 老年性听觉认知功能障碍的展望
有意识的避免噪声暴露及减少耳毒性药物使用有助于预防老年性聋的发生;定期听力检查及认知功能筛查有助于老年性聋及认知功能障碍的早期发现。国内最主要的听觉认知功能康复方式是改善听敏度,主要通过配戴助听器及植入人工耳蜗使老年性聋患者获得基本正常的听力,甚至正常的语言交流能力。这一点在国外的研究中得以证实:助听设备有助于改善老年性聋患者的认知功能[49]。但并非所有听觉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人都能够达到如此理想的康复状态。此外,药物治疗主要包括抗氧化剂,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其可以减缓老年性聋的发生,但用药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药物能够运输至内耳,这也增加了药物治疗的难度[50]。计算机辅助听觉认知能力训练及言语康复治疗在国外广泛开展,但在国内仍缺乏相应研究,且国外经验表明依从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