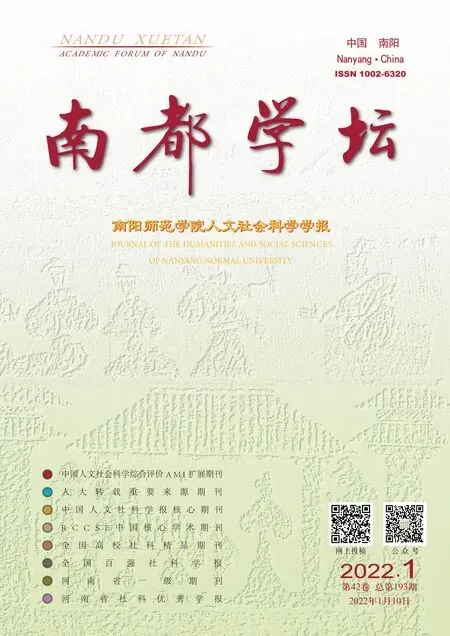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岳 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488;南阳师范学院 a.历史学院 b.汉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南阳 473061)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革,即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中国兴起、传播,并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成为20世纪中国人民探寻救亡真理的有力思想武器。在长期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渐确立了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以其崭新的思想元素、基本范式,在引领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迄今为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已有上百年历史,虽历经曲折,但始终在探索中发展前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百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接受与传播: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与指导地位的确立
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积极探索救国救亡之道路,涌现出了各种新思潮,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受到中国人的重视。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随后李大钊又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史学要论》等宣传或阐释唯物史观的论著。自此,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胡汉民、李达等把唯物史观作为改造落后中国的社会理论,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20世纪的中国还活跃着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以胡适、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时常围攻批判唯物史观,但是在多次“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唯物史观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影响力越来越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活动并未停滞,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大论战中,不仅提出了新的历史论题,同时也基本确定了历史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了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论著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初步建立[1]。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突破了旧史学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致力于“史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探寻中国历史的未来出路。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结合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根本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说明,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做了深刻阐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研究和认识中国历史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建设影响深远。
二、探索与偏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马克思主义在探索中成长与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全方位确立了自己在史学界的正统权威地位。成立于1947年7月1日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通过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要求新中国史学研究者“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养成实事求是作风”,目的是“建设新史学”[2]。这一时期,出版了大批马克思主义原著作品,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通过对经典原著的学习,激励了史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培养了史学工作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自觉意识[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出现,范文澜将原著《中国通史简编》扩充为《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了《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吕振羽修订《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及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等,均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指导下具有中国历史特点的鸿篇巨制。上述论著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史学研究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打破旧史学,设立新史学的目标已基本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间,围绕着“中国历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史”“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重大历史问题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探讨,既深化了人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又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呈现更多细化和学科化的发展方向,研究视野也更为广阔。通史研究成果丰硕,断代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代表性作品有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林增平《中国近代史》、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世界史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批判和改变了欧洲中心论,加强国际共运史、苏联史、亚非拉史等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绩斐然。各知名高校设立了考古专业,人类起源化石、石器时代遗址、夏商周时代文化遗址等大量考古发现对以后的考古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影响深远。考古学理论建设也有进一步发展,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后增订为《新石器时代》)、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以辩证法为主,突出斗争元素,缺乏对唯物史观“真”的理论挖掘。因此,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倾向[4]中文摘要。例如过于关注具有庞大体系的宏观历史的讨论,而忽略微观历史的探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解释中国历史问题时,往往忽视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等。尽管如此,这17年中成就还是巨大的,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深化奠定了基础。
1966—1976年这段时期,“四人帮”倡导的以实用主义为方法基础的“影射史学”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向,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立面——主观唯心主义化[4]19,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三、回归与繁荣: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注重构建中国特色历史话语体系
1978年,苏双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敢闯禁区的大无畏精神,批判矛头直指标志着‘文革’发端的‘源头’”,呼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5]。《历史研究》也连续刊文反驳陈伯达,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历史学的成就。随后大批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章陆续刊载,史学的批判与反思,助力了当时全国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打好了思想基础。在此过程中,主张回归历史主义的思潮代替了20世纪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观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确立,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进一步倡导克服史学领域中的“左”倾思想,回归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属性。1979年3月开始,史学界打破了“文革”期间沉闷的局面,开始活跃起来,许多中断了的历史问题开始重新讨论,兴起了“历史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的关系”等问题的论争,打破了原有的学术禁区,开始理性反思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中国历史的核心观念,如有学者针对学术界运用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社会形态套用中国历史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奴隶社会未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甚至有学者提出,新时代历史研究需要在一新的理论层次上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在研究方法、角度、领域中贯以新的历史精神[6]。可见,在对以往历史研究的反思中,人们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界“教条主义”“公式化”的枷锁,而用理性的态度来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研究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同时也反映了史学工作者已有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本土化的自觉意识。20世纪80年代初戴逸、侯外庐、刘泽华、周谷城、谭其骧等历史学者都主张正本清源,完整正确地学习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1984年《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他指出苏联哲学家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观点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延伸和附会,他认为苏联理论家“关于这个学说的这一类说明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他认为应更准确地界定历史的创造者[6]。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关注,并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较之20世纪80年代显得较为沉寂,张艳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一文中指出原因:一是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一部分史学工作者成为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更多的学者则转入具体的研究领域,这符合学术发展规律。二是随着学科调整,在90年代,史学学科发展呈萎缩趋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也不可避免减员。三是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声势要大些,为了引起人们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视,开始造些声势是必要的;进入90年代后,主要是开展默默无闻的扎实研究工作,自然研究理论的人就少了。但是他认为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水平要高于80年代,理论观照的特征要浓一些,在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关于史学主体、史学认识、史学发展等领域都有收获[8]。王玉德在《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反思》中提到90年代史学走上了大史学的路子,90年代出现国学热、新儒学热,史学界用更理智的态度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冷静的反思、热切的期盼。史学理论和方法呈现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地位的多元格局[9]。他们都总结出了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特征。其实这一时期,不应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影响和冲击,以及开放国门后学术上的对外交流,史学界引进了不少西方理论,对国内史学界尤其是理论界有较大影响。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再度活跃起来,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反思与讨论。新的世纪,在新的语境下,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建构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和认识,出现了大量论著。如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王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庞卓恒等《真理、规律与历史研究——兼论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于沛《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刍议》(《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等。上述论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一些新生代的历史学者也纷纷投入这一领域,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这一议题。如关于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问题,更多学者认为这只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能用来套用中国历史。侯树栋在《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学说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普遍规律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只能表现为特殊规律,绝不应把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普遍规律释读成适用于一切民族、时代的历史发展模式[10]。田昌五在《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新构想》一文中谈到,五种生产方式是按照欧洲历史提出来的,必须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另行考虑解决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途径和方法[11]。更多的学者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看法。晁福林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中认为,目前必须突破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制约,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12]。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梳理与回顾直接关系到对其地位的科学判断以及以后的发展走向问题,因此是当前研究中重要的环节。这方面的论著有很多,代表性著作有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陈其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卢钟锋《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瞿林东《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王学典、陈峰《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东岳论丛》2002年第2期),胡逢祥《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传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何刚《“和而不同”: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对郭沫若史学的批评》(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参会论文),乔治忠《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等。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学者治学方法与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2000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中,谢保成的《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的《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陈其泰的《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等著作分别对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有卓越贡献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梳理。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也很多。周书灿《郭沫若对〈古史辨〉的超越——郭沫若史学研究之一》(《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1期)、侯德仁《吕振羽的民族史研究成就及民族思想》(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参会论文)、刘春强《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刘芹《学术视野下的金毓黻与范文澜交往考察》(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参会论文)、陈峰《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卜宪群《林甘泉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界》2018年第11期)等论著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治学方法以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治学历程。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方面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历史研究的评价。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侯云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评价与唯物史观的价值》(《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胡尚元《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剑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2009年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专题资料汇编)、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二,对“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受重创的历史影响进行深入挖掘。如李金铮、邓红《“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王镇富《论武训批判对新中国史学领域的影响》(《学术探索》2008年第4期),赵庆云《中苏论战背景下的史学“反修组”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杜学霞《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等论著。第三,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对史学界错误思潮进行的严肃批判。自苏东剧变后,史学界涌动着一种错误思潮,即否定、篡改、歪曲中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者对历史虚无主义作出积极回应,维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统地位。朱佳木先生在《以唯物史观推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一文中,提出史学理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要理直气壮地批驳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挑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13]。不少学者也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如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张海鹏、龚云《马克思主义岂是历史虚无主义》(《求是》,2015年第10期)、史宏波《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逻辑、现实展现和抵御策略》(《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12期)。
四是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本土化问题是自马克思主义史学扎根于中国就受到关注的一个话题,并始终指导、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都自觉地承担这一任务,并进行了有益探索。进入21世纪,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化,这一论题更是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张艳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1期)、张国刚《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陈其泰《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剑平《走进历史学家群体探索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读邹兆辰著〈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辑刊)、张剑平《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左玉河《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河北学刊》2013年第3期)、陈其泰《新时代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问题》(《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本土化理论建构和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
四、深化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发展和研究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危机,但是成就是巨大的,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与封建史学、资本主义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并长期引领着历史学正确的研究方向。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中间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化,尤其是在面临世界局势严峻挑战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如何面对新形势,仍然是当代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找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偏重史实的研究而轻视理论探索。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逐渐出现淡化理论、淡化唯物史观,甚至鼓吹回到乾嘉去,回到考据去[14]。这种倾向也影响了史学研究领域,从而导致史学研究理论空缺的怪现象。二是史学研究处于琐、碎、小的碎片化格局,呈现出研究狭隘化、微观化的特征,虽然这种从局部切入的个案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这一学科来说,人为的割裂和取舍会降低理论建构和规律探索的成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三是过度依赖于西方史学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断深化,一些西方的史学理论被引入中国。一方面,开阔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史学理论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有较大冲击。不加辨别地照搬照抄西方史学理论,会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论”的学术陷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原本的思维结构和认知方式,不能不引起警惕。四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和概念问题认识不清。一些史学研究者在研究中或错误释读唯物史观或避开重大理论问题,不利于解决研究中存在的困惑和争论,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这些问题也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趋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要坚持独立自信的史学观念,避开“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厘清唯物史观重要概念和问题,注重重大理论建构,开拓宏观视野,多观照现实问题,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话语体系。
ACentennialReviewofandProspectforMarxistHistoriographyinChina
YUE Li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ies,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473061, Henan)
Abstract: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rxist historiographers in China have been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inherent law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le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As a result, Chinese scholars have nurtured a distinct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 different from those adopted by capitalist or feudal historiographers, one that has been lead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research forwar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lthoug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experienced many twists and turns or even crisis moments in the course of its one hundred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witnessed enormous achievements and displayed ever-growing vitality. At present, confronted with the impact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Marxist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ers should take it upon themselves to adhere to a correct historiographical view based on independence and self-confidence, steer clear of the interference of “Western-centric” ideologies, re-visit Marxist text per se, clarify the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ssue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ay attention to major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expand the macro scope of research while address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actively construct a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odality.
Keywords:Marxist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entennial review and reflection; discours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