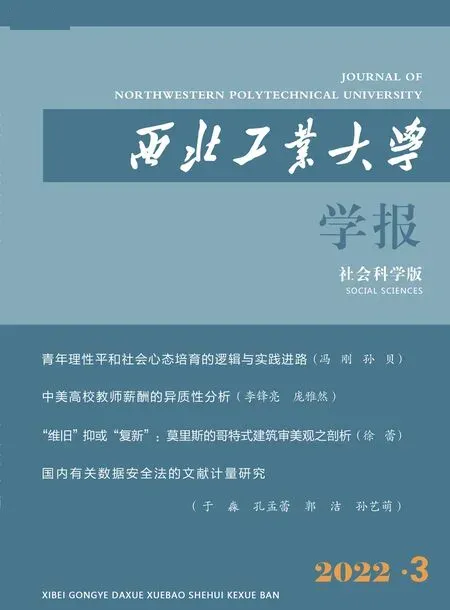“维旧”抑或“复新”:莫里斯的哥特式建筑审美观之剖析
徐 蕾
中外学界对19世纪英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手工艺运动先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政治思想与美学理念常作区别对待,用“深刻道德洞见”[1]与“生动有力”[2]赞誉他的社会主义信念与政治艺术著作,指出这与他对欧洲中世纪艺术及其时代的推崇与向往矛盾重重,其所描绘的未来社会蓝图传递的实乃中世纪主义的内核。对于关注莫里斯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们来说,“其思想显在的倒退性与进步性之间的张力,成为讨论他的社会主义理念政治特色与实用性的起点”[3]。而从工艺美学史的角度来看,虽然莫里斯是19世纪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但这并不能遮蔽其转向中世纪主义所带来的思想局限性。佩夫斯纳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一书中坦言,莫里斯“在复活手工艺方面的工作是建设性的,而他的学说本质却是破坏性的”,因为“他不愿在他的工厂里采用任何中世纪之后的生产方法”[4]。国内工艺美术研究学者许平认为莫里斯是背负着前进与倒退两种矛盾力量的悲剧人物,“他维护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却又不能把传统变为发展的动力;他挚爱人民的生活,却离人民生活的切实需要相去甚远;他喜欢结交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却选择了一条‘海市蜃楼’式的斗争道路”[5]。这种矛盾在李敏看来,根源于这位艺术家“固执地将一只脚深深地踩在现在过时的生产方式中”,试图用落伍的方法应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痼疾。[6]
不难看出,莫里斯的“原罪”大抵来自其提倡从中世纪艺术及其生产方式出发,寻求解决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艺术颓坏、劳动异化、道德崩塌等诸多问题的基本立场。诚然,浸淫19世纪英国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的莫里斯,对中世纪的文学与艺术有着特殊的情结。①他的文学创作大量取材于中世纪传奇文学,从第一部诗作《为吉尼维亚辩护及其他》到最后一部奇幻小说《世界尽头的水井》,都传承了中世纪文学的基本元素与主题;在艺术设计理念上,他积极取法中世纪哥特艺术的精神,振兴中世纪以来的行会制度以推动手工艺术的复兴,亲自设计制作包括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中世纪风格的壁毯和壁挂,委托建筑师好友韦伯(P.Webb),为自己和新婚妻子建造融合了哥特式元素的宅邸——红屋(Red House),甚至他去世前监制凯姆斯科特出版社(Kelmscott Press)制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采用中世纪印刷技术和植物颜料,被誉为“袖珍大教堂”的《乔叟作品集》。但值得关注的是,莫里斯的怀旧情结并非可以用“感情用事”或“伤感主义”一言以蔽之。[7]按照威廉斯的说法,“这些怀旧情结能够弥补那些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实现的生活品质”“尽管它们指向过去,关注的却是现在和未来”[8]。实际上,莫里斯的怀旧不乏理性思考的底蕴,他对中世纪艺术的倡导也绝非盲目的崇拜与单纯的模仿。要考察莫里斯对中世纪艺术的理性认知,我们不妨由此设问:复兴中世纪的艺术与文化生产,是否就是莫里斯为振兴19世纪工业时代英国艺术生活而给出的答案?具体就建筑美学而言,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是属于19世纪英国的建筑风格吗?本文将以莫里斯创立的古建筑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SPAB)为着眼点,将其建筑美学思想植入19世纪中期英国文化界围绕修复或保护古建筑展开的论辩,揭橥莫里斯与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复兴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探寻其发轫于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美学、指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审美政治的立场。
一、普金的议会大厦与莫里斯的“爱好古物的团体”
与普金(A.W.Pugin)等倡导哥特式复兴(Gothic Revival)的建筑师一样,莫里斯对“所有装饰艺术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艺术”——建筑艺术——在他所处时代的发展现状极为不满。[9]普金在《为英格兰基督教建筑复兴一辩》的开篇感慨道:“我们生活在英国艺术命运多舛的多事之秋,刚刚经历了可以被称为建筑的黑暗时代”“四个世纪的缓慢衰退之后,风格——如果还有的话——每况愈下,其恶劣程度已无可复加,品位也一落千丈”[10]。不过令普金倍感振奋的是,随着中世纪的哥特式被重新引入英国各地教堂的设计与改造,他所推崇的“尖券或基督教建筑的真正原则”把异教文化元素(如希腊式、古典主义式)清除出严格的哥特式建筑规范,“一种可喜的反应便开始了”[11]。在普金看来,“具有民族风格的国会大厦便是迄今为止在这一正确方向获得的最大进展”[12]。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普金和巴里爵士(Sir C.Barry)共同设计修复的议会大厦(又称威斯敏斯特宫)在莫里斯的眼里却是一记不折不扣的败笔。这座建筑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象征着英国国家政体。它在1834年一场大火之中被摧毁,后在断壁残垣基础之上,耗时近二十年,被修复为哥特式风格,从此雕塑了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的天际线。然而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威廉斯·盖斯特到访21世纪伦敦的一段旅程,“畅想”了这座建筑毫无希望的未来:当乌有乡的主人迪克·哈蒙德带领盖斯特穿越新伦敦的市中心时,后者得知曾经的议会大厦早已被挪作它用——作为附属市场的“粪便储藏所”,而这样做的好处是“因为房子就坐落在河边”[13]。议会大厦遭遇火灾那一年,莫里斯刚刚出生,及至巴里的设计从一百种方案中胜出,他不过学步之龄,但议会大厦漫长的修复过程无疑给少年时期的莫里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到了晚年依然要通过文学想象,对这处修复的建筑物进行快意恩仇般的嘲讽。
向异乡人介绍完议会大厦的古今差异后,迪克话锋一转,提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好古物的团体”,该“团体对于大多数人认为毫无用处的、对公众有妨害的其他许多建筑,就提出过意见,反对拆毁”[14],由于这个团队奋力争取,居然把议会大厦留存了下来。众所周知,《乌有乡消息》设定的故事背景与莫里斯个人的生活经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处提及的“爱好古物的团体”有其真实所指,那就是莫里斯在1877年创立的,旨在保护古建筑免遭“修复之殇”的古建筑保护协会。如果说在古建筑基础上“修复”哥特式是普金等哥特式复兴者们做出的选择,那么“保护”则是莫里斯和他的支持者们面对甚嚣尘上的风格性修复浪潮而做出的坚决回应。
1876年夏天,莫里斯途经英国最美乡村考兹沃尔德(Cotswold)地区时,得知布尔福德(Burford)教区某教堂要被修复为哥特式建筑,他便萌生了成立保护协会的想法。1877年3月5日,他在《泰晤士报》上读到建筑师斯科特爵士(Sir G.G.Scott)向公众呼吁为修复蒂克斯伯里大教堂(Tewkesbury Minster)计划募款时,更加坚定了要在建筑委托方(各地教会)与建筑设计者之外建立起一个由建筑界、文化界,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组成的第三方组织的决心,以共同保护英国古建筑遗产。短短五天后,他在《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明确提出“必须着手建立一个看护旧建筑的协会,以防止各种超越为建筑物挡风遮雨的‘修复’行为,务必以文学或其他方式唤醒人们的情感,即我们的古代建筑不是教会的玩物,而是国家成长与希望的神圣纪念碑”[15]。雷厉风行的莫里斯在两周之内向好友们发出邀请信。1877年3月22日召开的“古建筑保护协会”第一次会议,便已集结了包括建筑师老友韦伯、艺术评论家史蒂芬斯(F.G.Stephens)在内的十位文化艺术界精英。短短一个月后,协会吸引了文化批评家卡莱尔(T.Carlyle)和罗斯金(J.Ruskin),拉斐尔前派代表艺术家伯恩-琼斯(E.Bourne-Jones)和米莱(J.Millais),以及法学教授布莱斯(J.Bryce)、历史学家斯蒂芬斯(L.Stephens)、生物学家卢伯克(J.Lubbock)等英国思想界、艺术界精英的加盟。协会成立第三年时,成员名单已扩充至三百人以上,且多为知识精英与社会名流。此外,协会在英国各地拥有二十多位通讯员,还在威尼斯、巴黎、罗马设有特邀通讯员,跟踪海外古建筑的保护状况。[16]古建筑保护协会虽然没能成功阻止蒂克斯伯里大教堂的修复项目,但这个公益组织借助英国媒体的公共平台,大力宣传古建筑的审美与历史价值,抗议破坏古建筑的各种行为,并向公众免费提供古建筑的维修咨询、研究支持、专业培训以及知识宣传,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以及欧洲产生持续而广泛的影响,让保护而非破坏性修复古建筑的基本立场深入人心。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该协会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古建筑保护组织,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修复”“反修复”与“保护”
回到莫里斯号召成立协会的发端,创始人能在短时间内做到一呼百应,一方面离不开他作为知名艺术家与政治活动家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也与古建筑修复派与反修复派之间的思想对垒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欧洲,“修复(restore)古建筑”意味着刮除古建筑的外观表面或拆除古建筑的局部,然后按照建筑师偏好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在原建筑基础上进行重建。根据“restore”的希腊词根和拉丁构词,它最初的含义为“更新栅栏、加强防御”,与军事工程相关,直到近代才慢慢进入古建筑维修的话语范畴。[17]在贝利(N.Bailey)于1730年出版的《英语词源字典》中,“restauration”被解释为“复原,或者重新建立;在之前的地基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房子”[18],已经赋予了这个词语非常明确的叠加在原建筑之上的重建意义。而随着18世纪末的哥特风复兴,这一内涵也被深深嵌入时代的文化思想语境中。
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出现了建筑设计上的复古主义现象,这一倾向在英国的表现便是哥特式风格的复兴。[19]哥特式是欧洲建筑与艺术的传统风格,莫里斯认为,它来源于罗马建筑与拜占庭艺术在君士坦丁堡的相遇,兴起于欧洲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在14世纪达到全盛并风靡欧洲,直到16世纪初逐渐被文艺复兴风格所取代。[20]19世纪初期,英国建筑师和艺术家对哥特式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认为这种风格才是能够抗衡文艺复兴风格的唯一手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哥特式风格建筑开始出现在英国各地:18世纪英国哥特文学的先驱沃波尔(H.Walpole)在1749—1790年间把位于萨里郡草莓山(Strawberry Hill)的17世纪家宅改造为一座哥特式小城堡;建筑师怀亚特(J.Wyatt)受哥特小说家贝克福德(W.Beckford)委托,在1796—1807年间设计修建了作为私宅的方特希尔修道院(Fonthill Abbey)。这一阶段的哥特式复兴主要是私宅的改造与修建,表达的多为宅邸主人与建筑师的个人审美喜好。前文提及的普金是哥特式复兴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这位热情洋溢的天主教信徒毕生大力推崇哥特式建筑的美学与宗教价值,认为这种风格对于建筑来说,具有无上的重要意义。他特别强调准确模仿哥特建筑的重要性,发表了《对比,或中世纪崇高建筑与当前崇高建筑之比较:表明当前品位的低俗化》《尖券或基督教建筑的真实原则》《为英格兰基督教建筑复兴一辩》等论作,较为完整地勾勒了哥特式的实用美学原则。主持修复蒂克斯伯里大教堂的斯科特爵士也是这一阶段哥特式复兴的重要代表,虽然他是新教徒,但在把哥特式引入教堂与楼宇改造方面绝对是同辈人中的翘楚。②
哥特式复兴在1850—1880年进入全盛时期,英国涌现了许多以哥特式为设计灵感的建筑师,如斯特里特(G.E.Street)、巴特菲尔德(W.Butterfield)等。他们的出现恰好满足了英国教会大兴土木、改造教堂的需求。仅在1840—1873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有大约七千多座大教堂和小教堂被修复,这一数字约为同期新建教堂的三倍。[21]事实上,建筑师们偏好修复,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省力的机会,在现成的建筑物上留下他们‘创造性’的印记”[22],而与总造价比例固定的佣金(常规为百分之五)无形中也推动他们提出预算更高的修复计划。[23]与新建一所教堂相比,修复的方案总归成本更低,且哥特式的改造模式符合英国教会对中世纪宗教典仪形式高涨的热情,因而成为教会普遍采纳的方法。随着哥特式在英国日益成为主导的建筑风格,被修复的教堂多被“改头换面”为建筑师和教会共同青睐的哥特式,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古代建筑的表面与局部被刮除、拆解,甚至改造,而这就是又称“反刮除协会”(Anti-Scrape)③的古建筑保护协会反对的“修复”——新哥特式的“复新”。
莫里斯本人曾差点进入“修复者”的行列。1856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随后便加入了斯特里特主持的建筑事务所,在那里做过一年的学徒。这位七岁开始阅读司各特的中世纪浪漫历史传奇小说,八岁就参观过坎特伯雷大教堂,大学期间两度前往法国北部实地考察教堂建筑的青年,对中世纪有着特别的情愫,对哥特式建筑心驰神往,渴望未来在建筑行业中施展抱负。然而,当他深入了解到建筑师修复教堂的一般做法时,便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旋即放弃了建筑师的梦想。[24]
实际上,莫里斯并不是第一个批判修复古建筑的思想家。早在18世纪晚期,深受“如画”(picturesque)传统影响的艺术家们便开始担心修复会剥夺古建筑原本不规则的、有机的外观,破坏几个世纪的自然风化与沉淀形成的微妙平衡。④在莫里斯的协会成立前数年,为《雅典娜神殿》长期撰写艺术批评专栏的史蒂芬斯就开始公开批评以斯科特为代表的修复派建筑师对古建筑进行的批量修复工作。[25]而更早的批判之声来自莫里斯在牛津大学的精神导师——罗斯金。罗斯金在1849年发表的《建筑的七盏明灯》的“记忆之灯”部分指出,一个民族拥有的建筑艺术肩负着两项无比重要的职责,“一是要令当前之建筑风格也能呈现历史意义;二是要将过往之建筑当作最珍贵的遗产予以保存维护”[26]。但修复工作却完全与之背道而驰,它甚至意味着“一栋建筑所能遭遇的破坏毁灭中最彻底与绝对的行为”[27]“人们无法从这种破坏里寻得任何属于过往的痕迹”,仿制而成的赝品与冰冷无味的模型自始至终、从头到尾“都是一则谎言”[28]。古建筑因年久失修、风化颓倾而化为废墟,甚或消融软化为黏土,都及不上修复“对它下手之无情、破坏之完全。人们从人去楼空、荒烟蔓草的尼尼微遗迹里,曾经捡拾搜罗起的点点滴滴,一定比重建整个米兰可以带来的更多”[29]。强烈反对修复工作的罗斯金继而提出:重要的是在古建筑尚未毁坏之前采取及时的维护措施,“对有纪念意义的古迹提供妥善恰当的照顾,日后你便无需加以复原。及时替屋顶嵌入几面铅版,或者及时替水道清除残枝枯叶,就可令屋顶与墙面皆免于毁损崩坏”[30],这样才能让后人依然有机会分享这份珍贵的遗产。
显然,莫里斯继承了罗斯金保护古建筑的立场与方法。在1877年颁布的《古建筑保护协会成立宣言》中,他把“保护”定义为“防止建筑物破败的日常护理,通过显而易见的支撑或覆盖措施,以支撑危险的墙体或修补屋漏”,他特别强调这些保护措施“不要以伪装成其它艺术风格的方式进行展现,否则就要抵制所有篡改建筑原本结构或装饰的行为”[31],因为“伪造”(forgery)正是19世纪欧洲修复派建筑师们的实践内核,英国的西敏寺、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圣马可大教堂等欧洲著名古建筑都留下了他们的深深印迹。
莫里斯的不少反对者们断章取义地把“保护”看作“如画美学”影响的结果,认为保护派们反对涉及建筑结构的改造工程,“倾心于断壁残垣”[32]。针对修复派对保护内涵的故意曲解,1879年莫里斯在公开信《古建筑保护协会的目的》中重申,“敦促公众及时对古建筑进行结构性修补、防止风吹日晒的侵害是协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必要的结构性保护对于延长古建筑的使用寿命相当重要,但采用的维护措施一定要尽可能简约且“显而易见”[33]。1885年3月,莫里斯参加英国政府工程部为议会大厦的威斯敏斯特堂(Westminster Hall)修缮工程召开的专家听证会时,在皇家工务委员会首席大臣等重要政府官员面前,表达了对修复派工程计划的强烈反对,完整地呈现了“保护”的具体内涵。1882年皇家法院搬离了威斯敏斯特堂外墙边的旧址。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法院楼被拆除后,充分暴露出威斯敏斯特堂侧墙外六道建于14世纪的拱形支撑物——飞扶壁(flying buttress)、英格兰国王威廉二世时期建造的外墙与基础的遗迹,以及西外墙下部罗马风格的大片石雕。⑤为重振威斯敏斯特堂的昔日荣耀,工程部委托建筑师皮尔森(J.Pearson)设计修复方案,这位哥特风复兴派主张在外墙与飞扶壁之间建造一段两层式的回廊,既可以遮蔽暴露的外墙和石雕,同时扩大了原建筑的使用空间。但皮尔森的设计在莫里斯看来,完全基于建筑师个人的臆想,属于典型的“臆测式修复”,显然违背了他所提倡的保护措施必须简约与显而易见的原则。因此,莫里斯在听证会上大声疾呼,“所有能做的措施只能是对外墙的保护,只能是清晰可见的保护体”。他建议在外墙之外、飞扶壁以内搭建斜坡,这段斜坡必须具有“显著的现代感”,不能带有任何装饰性色彩,其材质也“绝不能表现为对古建筑的修复”。当问询者提出保护古建筑是否要考虑审美品位时,莫里斯毫不客气地回应道:“这得取决于你所说的‘品位’是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我认为这当然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方法,它会赦免你犯下违背品位的罪行。”[34]对于莫里斯而言,最大限度地保持古建筑的完整性与原始风貌,不进行不必要的增加、拆除、装饰、改造,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维多利亚时代多数人审美品位的需求。这,恐怕就是“保护”的实质——维旧。
三、真实性的问题与哥特式复兴的问题
当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审美趣味建立在中世纪的哥特风之上时,一生挚爱中世纪艺术的莫里斯却对哥特式复兴对古建筑带来的问题有着独立的价值判断。在莫里斯的建筑价值体系中,建筑审美的前提是真实性,当建筑的真实性原则被践踏,美也无从谈起。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罗斯金提出了建筑美德的真实之灯,建筑范畴内对真实的违背意味着“在材料性质或劳动力数量上,直接做出与事实不符的主张”[35],他列举了“暗示有别于自己风格的构造或支撑模式”“建材表面上色上漆”“使用任何一种预铸或由机器制造的装饰”三种类型的欺骗。[36]模仿古代建筑风格修复古建筑恐怕是莫里斯眼中最糟糕的建筑造假。
抛开审美趣味的差别,莫里斯与修复派之间的争论焦点在于对“真实性”的不同理解。修复者主张“忠实地”恢复或重建古建筑的早期风格,在造型、布局、装饰细节上实现建筑外在形式与内在结构的完整统一。莫里斯代表的保护派强调的是“历史时间”的真实,每幢古建筑的成形都有其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19世纪工人们的修复工作绝不可能还原古建筑的原初状态。与其打着修复之名、行破坏之实,不如时刻关注古建筑的现状,保护它免受日晒雨淋,加固其结构稳定性,为子孙后代守护好这份历史遗产。
莫里斯对“真实性”的历史主义立场无疑承袭了罗斯金的古建筑观。罗斯金认为修复的根本误区在于“他们认为恢复过去时代遭破坏雕塑的原初之美是有可能的”[37],然而“欲将曾经存在于建筑物上的伟大与美丽加以复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就如欲将已经死去的生命予以复活一般不可能”[38]。罗斯金认为,优秀的建筑物具有“一种作为整体,无法分割的生命,以及那种唯有经由工匠的双手双眼才能赋予的精神与灵魂,当它们一旦逝去,就再也不可能将其重新召回世上”[39]。即便在当下依葫芦画瓢般地复制出古建筑的外观和内部结构,也绝不能实现真正的复原。因为当代的建筑师“没办法召唤当年工匠的灵魂,命令他们担任其他工人的监督,指挥这些工人的手脚,导正他们的观念”[40]。换言之,“真实性”意味着建造主体与劳动过程的历史属性。1883年莫里斯在古建筑保护协会的年会演讲《建筑与历史》中进一步阐释道:“文物的不可复制性并非偶然,而是必然。文物并非是一时流行或风气之果,而是所有过往历史沉淀下来的结晶。因此,任何人、任何团体,无论他们拥有多么渊博的古代艺术知识,多么出色的设计才能,或者对美有着多么深刻的热爱,都无法劝服、诱哄或逼迫如今的工人像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工匠那般去劳作。”[41]
那么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工匠究竟是如何劳作的?他们的劳作方式又为何不能被维多利亚时代复制?莫里斯认为,中世纪的工匠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劳动分工和发达商业经济的前工业化时代。他们是手工艺者,而不是机器的奴隶。他们精通整个工艺流程,在创作上享有相当的自由,“中世纪的手艺人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进行劳动,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甚至有可能会在进行编织、制陶或其他类似工作之前先亲手制作相关工具、器具或简易机器,他还可以自由决定手工艺成品上的点缀装饰,通过双手和心灵完成设计、付诸实践。虽说在这个过程中,工艺传统或前人的思想会以所谓工艺惯例的具体形式给予其引导和帮助,但是除此之外,他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即便是生活在城镇,他的家和美丽的乡村田园相隔也不远。他可以时不时地劳作于乡村田间。他的一生中会有那么一两次,需要从墙上取下弓箭,在战场上与伟大的奥义不期而遇,更有可能在别人的争吵或自己与他人的争吵中,不无成功地悟出工艺诀窍”[42]。
16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兴起与手工行会制度的衰落,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手工艺者的身份与劳动方式发生了巨变。一方面,资本主义初期的失地农民成为手工行业的主力军,“他们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讨生活,每天都不得不向那些一心只想利用他们赚取利润的人出卖劳动力”[43],相对自由的个体劳动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的劳工关系。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制度“迫使人们的生产目的从以前的谋生变为牟利”,生产者与消费者脱钩,也导致了“工匠们不再是以前的艺术家,而被划分成了不是艺术家的工人和不参与劳动的艺术家”[44]。于是在建筑领域,设计师是“鄙视人们生活的老学究”,凭借着对历史的“一知半解”[45],热衷于把古建筑修复为哥特式风格;工匠则演变为“机器苦力”,卑微地为谋得生存,从事一份毫无尊严且朝不保夕的低级体力工作。“工人最多能做的就是弄明白机器(而不是他)在生产什么。设计和装饰与他有何相干?”[46]
莫里斯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进行批判。这与他在19世纪80年代积极吸纳的社会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在人生的最后十余年间,他积极投身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加入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后又创立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League),深入阅读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在1883年发表的《建筑与历史》演讲中,他提到一个不便在公开场合中指名道姓的伟人:“他的论著厘清了我对劳动及其产物的几点认识。”这里指的便是马克思。[47]既然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形态及其上层建筑,维多利亚时代又怎能产生哥特式的建筑艺术呢?因而修复派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用别人丢弃的衣服来乔装打扮自己”[48],犯了把中世纪建筑艺术强行植入19世纪工业社会的时代错误——“它们虽然在这个世纪建造,却并不属于这个世纪”[49]。
如何振兴英国建筑艺术——这是令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建筑师与艺术思想家冥思苦想的命题。如果说普金、斯科特、皮尔森等修复派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中世纪的哥特式,那么倡导保护的理念并创立了保护古建筑协会的莫里斯显然并不认同这条路径。在维旧与复新之间,他有着自己的选择。
毋庸置疑,莫里斯和他的启蒙导师罗斯金一样,高度推崇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但与其说令他折服的是建筑有形的尖顶结构和彩色玻璃,不如说是化于无形的哥特式的本质深深启发了他,推动他在艺术沦为财阀统治下“竞争性市场的区区玩物”[50]时,在“过去的秩序时代与将来的秩序时代之间的野蛮时期”[51]能够畅想艺术未来的美好图景。在莫里斯眼中,外在特征甚至不是评判一件建筑作品是否可以归入哥特式的标准,他在题为《哥特式复兴》的演讲中比较过意大利维罗纳古城的两座古教堂,认为圆顶的圣柴诺教堂(St Zeno)在精神气质上更符合哥特式的本质,而尖顶的圣阿纳斯塔西亚教堂(St Anastasia)只是一座“冒充哥特式的古典式建筑”[52]。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为全体人民所共有,自由的、进步的、希望的,充满人性情感与幽默气质”[53]等诸多精神特质,当然也不可能通过精准的外形模仿在维多利亚时代实现重生。
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们之所以青睐哥特式的建筑艺术,多少源自对所处时代建筑发展的不满。复古的浪潮寄托着对建筑艺术创造力衰退的其中反抗,其中隐含的社会文化批判立场也为莫里斯所认同。但当这股复古浪潮发展为以哥特式为优选标准对古建筑进行修复与改造时,他越来越意识到哥特式的当代复兴绝非建筑师品位或教会选择能够左右,而是由19世纪英国社会与中世纪社会本质的差异所决定的,“成了‘机器奴隶’的工人必然无法完成那些中世纪自由自在的手艺人的工作”[54]。只要竞争性的商业经济和大机器生产的劳动分工依然存在,艺术必然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从这一刻起,莫里斯围绕哥特式建筑的审美话语便具有了政治批判的鲜明底色。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为莫里斯提供了想象未来社会艺术形态的考古依据,但他深知“范围过于狭小,仅限于一群受过良好教育人群”的哥特式复兴“并非能长足发展的一种富有活力的生长”,它既不能为古建筑提供修复的范本,更无法引领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通向未来。因为在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的心中,“为了人民,既为创造者也为使用者带来幸福的艺术”只能借由社会主义的变革方能实现。[55]
注释
①莫里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深受三种与中世纪表征和价值化密切相关的文化运动影响。这三种文化运动分别是:高教会运动、中世纪主义运动,以及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参见麦克唐纳:《审美、行动与乌托邦——威廉·莫里斯的政治思想》,黄文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
②G.G.斯科特爵士(1811—1878)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成功、最多产的哥特式复兴建筑师。作为英国最大规模的建筑设计公司的老板,他设计修复了800多幢建筑物,影响了500多座教堂的修复与改造工程,主持了包括西敏寺、蒂克斯伯里大教堂的修复。
③“反刮除协会”(Anti-Scrape)是莫里斯私下与友人通信时指代SPAB的常用昵称。参见:William Morris,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Morr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381,413,445,489.
④兴起于英国18—19世纪的“如画美学”欣赏自然的粗糙感,认为荒野中的废墟产生的崇高美,远胜一座状态完美的希腊风格的神殿或宫殿。参见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张箭飞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⑤ 威斯敏斯特堂修复工程的前因后果。参见Chris Miele,“The Battle for Westminster Hall,”Architectural History 41(1998):22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