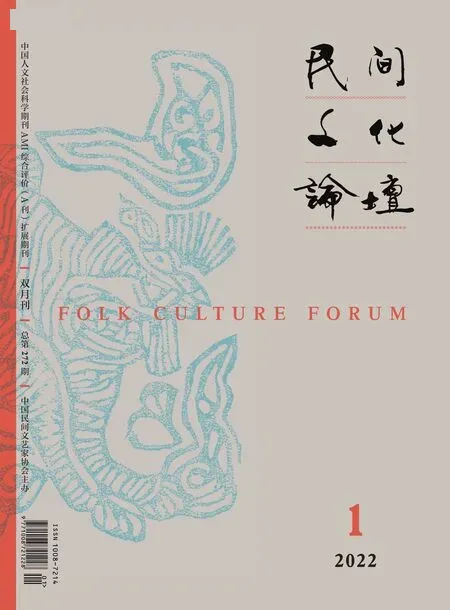发端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
—— 以胡适与康德、杜威的侨易关系为例
户晓辉
如果说侨易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由物质位移之侨带来的精神质变之易,那么,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侨易发生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假如没有物质位移给现代学者带来的精神质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发生就不仅难以设想,而且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在思想观念的启蒙方面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发生起过决定性影响的两个重要人物——胡适和周作人就曾分别在美国和日本求学,还有一些现代学者不一定留过学,却由于思想侨易带来的精神质变而参与促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发生。
一
仅就胡适而言,李小玲在新著《白话文学再思考》①本文据作者为李小玲《白话文学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以下凡引此书,不再标注页码)一书写的小序《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喜读李小玲教授新著有感》改写而成,承蒙李小玲教授以及叶隽教授先后约稿,叶隽教授还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中已经对胡适的民间文学思想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之间的侨易关系做出独到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开创性学者,胡适和周作人都是综合型人才,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拥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知识背景,就难以理解他们繁复而博大的思想内涵。显然,李小玲不仅对此心领神会,而且以理论慧眼和思想洞见来烛照胡适的关键概念与核心思想,并且通过细致的材料爬梳和广博的历史考证表明,在接触杜威之前,胡适曾在以研究康德与黑格尔哲学见长的康奈尔大学哲学系接受过五年的哲学训练,由此对胡适的民间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侨易作用。站在侨易学的立场,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补充说明。
首先,从当年的选课和得分情况来看,胡适初入康奈尔大学时原本学农科,三个学期后改习文科。他第一学期的德文课得了90分,“曾经考过全班第一名”②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204页。。胡适后来回忆说,“学习德文、法文也使我发掘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我现在虽然已不会说德语或法语,但是那时我对法文和德文都有相当过得去的阅读能力。”③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在康奈尔大学2014年公布的胡适“成绩单”中,1911—1912年的“道德观念及其实践”课的授课老师是曾在德国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梯利(Frank Thilly,1865—1934,他的《西方哲学史》在中外学界都是名著),胡适得78分;1913—1914年的“德国哲学选读”课的授课老师是擅长美学和古希腊哲学的哈蒙(William Alexander Hammond,1861—1938),胡适得78分;1914—1915年的“康德的批判哲学”和“经验论与唯理论”两门课的授课老师都是研究形而上学和英国哲学的艾尔比(Ernest Albee,1865—1927),胡适得分均为OK。④参见席云舒:《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关东学刊》,2017年第1期。正如江勇振所指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五年选修了十四门哲学课,而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只选了四门哲学课,可见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五年是他一生思想成熟的关键期,“我们甚至可以说,要了解胡适一生的思想,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发掘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所学、所读、所思。”⑤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第291、245、294页。另,江勇振文中将康奈尔大学写为康乃尔大学,遵照原文,不予统一和修订。
其次,从侨易学的影响环节来看,胡适与康德的接触还有一个重要的中间人物,那就是厄德诺(Felix Alder,1851-1933)。厄德诺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1873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国学习期间,厄德诺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胡适回忆说:
就在康乃尔这个伦理俱乐部,我第一次听到厄德诺教授的讲演。我对他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十分折服,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
后来我又选读了厄教授的一门课,因而和他的本人乃至他的家人都熟识了。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记了很多条厄德诺语录。让我抄几条在下面: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的人——的最好部分。
只有对别人发生兴趣才可使自己常是活泼泼地,常是堂堂正正地。
要生活在深刻地影响别人!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
从这些语录里我们很容易看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和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道德规律对他的影响。所以厄德诺是[当代思想家中]对我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人之一。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6—97页。
由此可见,厄德诺不仅堪称胡适与康德发生思想侨易作用的重要桥梁和媒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对康德思想的理解和接受以及胡适后来有关民间文学与白话文学的思想和实践。
第三,从思想侨易的发生契机和选择倾向来看,厄德诺的讲演最吸引胡适的是“他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胡适已经看出厄德诺“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恰恰来自康德的侨易作用,他摘录的厄德诺语录与康德的道德律令非常接近,因而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胡适对康德哲学发生兴趣的原因。由此可见,在思想侨易的发生过程中,胡适并非单向接受和被动选择的一块白板,而是以自己此前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为侨易的资本,这正是李小玲所谓“胡适对西方思想的选择和吸纳有他的前基础和前理解”。胡适不仅研究过康德哲学,而且多次提到康德的影响。
第四,从思想侨易的内容和细节来看,在李小玲新著的启发下,笔者查阅了胡适本人早年写作的几篇英语文章:大约在1915年,胡适在题为“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一个东方人在大战中看到什么》)的英文演讲中说:“在看到这个重大教训之后,我们怎样才能从中获益呢?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文明,让它基于更加坚固的基石之上,基于人道法之上,而不是基于丛林法之上。如果我们的文明想让自身持续下去,就必须建立在对所有人都公正、正义和爱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我说的人道法”②户晓辉译,胡适的原文是“Having seen the great lesson, how can we profit from it? My answer is that we must rebuild our civilization, base it upon a firmer foundation of rock, upon the law of humanity, not the law of the jungle. Our civilization, if it wishes to perpetuate itself at all, must be based upon the law of justice to all, righteousness to all, and love to all. That is what I call the law of Humanity.”(《胡适全集》第3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0—141页)。。胡适所谓的“人道法”,也可以理解为“人性法”,基本上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出一辙。1915年3月14日,胡适用英文写了“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一文,在对康德的实践哲学原理做出复述和分析之后,胡适说:“政治道德的这种严格的观点,无论它看起来对于身处政治的实用主义时代的我们是多么行不通和‘过时’,都是不无理由的。对我而言它仅仅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正如在私下关系和公民关系中一样,以某种善良或权利原则作为行动的目标是绝对必要的,而不是仅仅按照戒律去谨慎行事,就像盲人在黑暗中摸索那样笨拙的尝试”①胡适:《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席云舒译注,《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0期。。当然,在概要地论述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之后,胡适也指出时代对康德哲学的挑战及其得失。关于胡适的这篇重要文章,李小玲评论说:
1915年3月19日,{胡适的}日记记载:“上星期读康德之《太平论》(Zum Ewigen Frieden),为作《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一文。”《太平论》即康德写于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也就是试图从哲学的根基上寻求解除战争状态,实现永久和平的方案。很显然,胡适那时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应该和康德的这篇文章有关,而且在当时他已用英文写作了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一文。此文甚为重要,胡适后来很多的思想,包括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的端倪和脉络来源都可在此找到踪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甚或是修正我们过往对他的一些偏见。
1915年 5月 26日, 在“The Argument of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in Kant’sCritique of Pure Reason”(《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分析论的论证》)一文中,胡适详细概括了康德哲学的论证要点并做了简要评述。这两篇有关康德的论文显然是为艾尔比“康德的批判哲学”课所作。②关于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和写作目的,参见席云舒:《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关东学刊》,2017年第1期。这些文章及其核心观点可以与李小玲新著中列举的材料一起表明,胡适所受的康德影响非同小可。
第五,胡适在1910年8月进入康奈尔大学,1915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上文列出胡适几篇有关康德的重要论文大多写于1915年前后,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胡适对杜威的接受不仅与康德有关,而且在较大程度上以胡适对康德的理解为基础和侨易环节。不仅如此,所谓实验主义本来就与康德有关,而且康德思想对胡适产生的侨易作用不仅影响了胡适的民间文学思想,而且首先影响了胡适对实验主义的接受和理解,“康乃尔大学哲学系对他的影响要远大于杜威对他的影响”③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第292页。。按照实验主义创始人之一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说法,由于practicalism或practicism具有康德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含义,所以他没有使用这两个术语,而是改用pragmatism,因而这个术语的提出本身就与康德有关。④参见 Marcus Willaschek,“Kant and Peirce on Belief,”in Gabriele Gava and Robert Stern(ed.), Pragmatism, Kant,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Lon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6, p.134。实验主义是以先验理想为准则的实效主义⑤胡适本人也把pragmatism译为“实效主义”或“实验主义”,参见席云舒:《胡适的哲学方法论及其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6期。,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经验主义,正因如此,胡适的老师杜威才会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教育做出很大的贡献。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每个有理性的探究者都被置于平等的地位,谁都不是绝对的权威,谁都需要接受他人的质疑和批评。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和杜威比皮尔士更多地把这种民主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用于审美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试图打通康德在理性的理论用法与实践用法的隔阂并克服二者的冲突,它是培养反权威的、实行自我批评的社会理性和民主理性的一种实验主义方法。杜威和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也应该在这种意义上才能得到深入的理解。至少杜威和胡适都相信,民主是个人生活的一种人际方式,它隐含的超验信仰和先验理念是:无论个人禀赋有多大差异,每个人都有权利与别人享有平等的机会来发展自己的才能,都有能力不受别人的强制和强迫而过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理念显然对胡适的“白话文学”构想有很大影响。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胡适更多地从方法论角度接受并理解杜威的实验主义,因为胡适更感兴趣的是唯心主义如何贯彻和实施的问题,而实验主义恰好能够为这些理念如何通过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而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在文化理念上弃旧图新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法。可以说,在接触康德和杜威之后,胡适更是在思想上发生了侨易学意义上的精神质变,这种精神质变至少体现在从康德和杜威的概念侨入到胡适的概念侨出的重要转换方面。在这个思想侨易的过程中,一方面,康德在受到杜威的改变,另一方面,杜威在受到康德的改变,与此同时,胡适在改变着康德和杜威,也在受到康德和杜威的双重改变。胡适并不仅仅把实验主义用于认识论意义上的考据学领域,更重要而且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的是胡适还把实验主义用于实践论意义上的新文化实践和白话文学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认识论领域和实践论领域,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具有完全不同的来源和性质。简言之,认识论领域中“大胆的假设”主要来自经验归纳,而在实践论领域中,除了有来自经验归纳的“大胆的假设”之外,尤其不可或缺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作为实践法则的那些“大胆的假设”,这些作为实践法则的“大胆的假设”并不来自经验归纳,而是来自先验的和超验的理性推论,因而具有真正的普遍性。例如,自由和民主作为实践领域“大胆的假设”就不是也不能来自经验归纳,而是出于先验演绎和超验演绎的理性理念和实践目的,因而才具有普遍必然性和逻辑自洽性。如果我们承认胡适是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发生起过决定性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那就不能忽视康德和杜威通过胡适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结下的侨易之缘,这种历史渊源和侨易作用至少从胡适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对民主和自由问题的关注至少在胡适那里就已经有了发端并且深深地埋下了伏笔,这就进一步表明,为民主、争自由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与生俱来的胎记和先天基因,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绝非从实践民俗学才开始的“横空出世”,而是早已潜藏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之中。
第六,从因侨致易的思想效果来看,通过对康德和杜威的双重侨易和综合改造,胡适用实验主义方法把康德的自由理念与杜威的民主理念接入中国文化语境,并且开启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崭新格局,最终导致的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性特征及其精神质变。胡适更愿意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因为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都是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运动,当此之时,“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73页。。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在发生时所设定的学科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拾遗补阙的意义上发现新材料、新领域,而主要是为了在前无古人的意义上发现并维护民众个体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和权利。在这方面,李小玲的新著一针见血地指出:
事实上,我们长期以来对胡适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的解读有流于表层化和浮泛化倾向,更多是从政治观念出发,严重缺失政治观念后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上的考量和细察。胡适信仰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很大程度上和康德的道德律令及永久和平论有关,他的人道主义、民主观念、自由、平等意识,及其后来所发动的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学都和此有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不打通胡适与康德之路,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深入理解胡适孜孜以求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实质,也就难以把握其哲学思考背景下的文学革命和文学思想理念。而不真正了解胡适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康德背景,我们对胡适及由其所发动的文学革命,涵盖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等的内在基质依然会陷于云山雾罩之中。
胡适自由、平等、民主的概念并非附庸于政治属下,而是基于康德的主体精神和纯粹理性的层面立论,至于“人的文学”的倡导乃是切合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纯粹人的身份,由此寻找到民间文学以哲学为逻辑起点的学术预设,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关键问题即民间文学何为给出了明晰的答案。
这样的真知灼见立刻为我们开启了理解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发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且为民间文学的学科目的展示出全然不同于通常理解的理论基础和侨易格局。经过康德的自由理念、杜威的民主理念与中国宋明儒学“新民”观念的侨易作用,正如李小玲所指出,胡适将“人道本身视为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个手段”,而且把对每个民众个体的绝对尊重看作理性法则,这种理念恰恰是胡适民间文学思想背后的哲学根基。“胡适对道德和自由的理解既超越了经验世界的思考,但又有着客观实在性,兼有先验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双重特点。”实际上,胡适在1914年10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今读葛氏书,深喜古人先获我心,故志之。吾前年在西雷寇大学大同会演说‘大同主义’之真谛,以康德‘常把人看作一个目的,切勿看作一种用具’(Always treat humanity as an end, never as a means. 此语最不易译)之语作结,葛氏亦然。”①胡适:《读葛令<伦理学发凡>与我之印证》,《胡适全集》(第27卷),第535—536页。由此可见胡适受康德“常把人看作一个目的,切勿看作一种用具”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之深。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根基,李小玲的新著对胡适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代表性的概念与方法做出重新阐释,让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发生轨迹展露出簇新的风貌,这在整体上也可以理解为康德和杜威的理念侨入与胡适的思想侨出所带来的新格局。
二
我们进而可以看到,思想的侨入和侨出并非像物质东西那样的简单输入和单纯输出,而是思想融汇的因缘际会所带来的精神质变。
首先,胡适之所以能够对“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做出重新发现和崭新评价,恰恰以对“人”的价值重估和全新的“人”观为前提,而且,“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恰恰是康德的自由理念和杜威的民主理念侨入胡适的思想之后又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再次侨出的思想成果。胡适和周作人对民间文学的根本见解在“人的文学”理念上发生交叉和会合,并以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导引。作为“人的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不仅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而且是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哥白尼革命”意义上的重新理解,因为经过康德自由理念和杜威民主理念直接的或间接的侨入作用,胡适和周作人眼中的“民”首先必须是“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首先要改变“人”观,因为要把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变为“人的文学”,首先就需要让汉字本意为奴隶和“氓”的“民”成为公民意义上的“人”。所谓“人”,以独立人格和理性精神为基本规定。不理解这一点,就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在起点上所蕴含的现代性初心和现代化使命,这种初心和使命的自由民主理念核心不是中西之争,而是古今之变,或者说,虽然迄今仍然表现为中西之争,但实质是古今之变。它从根本上要求“民”“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接受并且经历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现代价值观的洗礼,由此使“民”成为“人”,让“白话文学”“民间文学”成为“人的文学”。
其次,面对中国国情,胡适并没有直接侨入并照搬康德的自由理念和杜威的民主理念,而是因地制宜地提出实验主义意义上的侨入概念,“白话文学”正是这样一个负载着自由民主理念并且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中层概念,这个实验主义工具论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为了从理念和国情的双重立场出发,首先通过一场表达工具的革命来实现并贯彻“常把人看作一个目的,切勿看作一种用具”的自由民主理念。因此,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虽然主要被用于实证考据方面,但也适用于实践上的先验理想和超验原则,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和本质性的区别在于:实证考据方面“大胆的假设”基本上来自经验归纳,但实践上的先验理想和超越原则却并非来自经验归纳,而是来自先验的和超验的逻辑演绎,因而这种“大胆的假设”并非用现实经验来加以验证的认识工具,而是用于改变现实经验的实践法则。来自经验归纳的“大胆的假设”最多具有相对的普遍性,而康德的自由理念和杜威的民主理念正是通过理性的逻辑演绎得出的“大胆的假设”或实践法则,因而具有绝对的和真正的普遍性,也就是能够概莫能外地适合于并且适用于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所有民众个体,违背了实践法则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从侨易学立场来看,康德的自由理念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对胡适产生的侨易作用所造成的独特性之一恰恰表现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自一开始就绝非单纯的“自下而上”,而是先有理念的“自上而下”作为理论上“大胆的假设”,再有现实的“自下而上”作为实践路径,而且事实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本是同一条路,只不过这里的“上”并非指的是知识分子,而是指理性的理念或理想类型。李小玲的新著已经指出,“如果启蒙运动不是建立在康德意义上的启蒙,而是将自己高悬于民众之上,那么,没有对启蒙的超越,根本就不可能有‘民的文学’的发现,有对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确认,有对民间文学的一种自觉意识。”胡适关于“活的语言”和“活的文学”的定义有其道德哲学力量的支撑,作为“活的语言”并且作为国语的“白话”是作为理性法则而提出的,它们不仅仅是开启民智的工具,而且体现了人与人绝对平等的根本理念,胡适当初为民间文学预设的正是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文学”的学术轨道,而“民间文学也就在此‘假设’之前提下脱颖而出”。这些无疑都是难得的洞见,笔者想强调的是,胡适和周作人对民间文学的“想象”,固然与安德森所谓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相同的经验内涵,却更有不同于安德森的超验原则,那就是康德的自由理念和杜威的民主理念。这种可以普遍化的超验原则虽然被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忘在脑后,但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来说却无比重要、不可或缺。在李小玲新著的基础上,笔者还想把胡适的整体思路还原为理念先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康德的自由理念和杜威的民主理念所产生的侨易作用,胡适就不大可能把民主看作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习惯性的行为①参见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87页。,就难以对“人的文学”和“白话文学”做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tion of all values)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74页。的崭新思考,更难以想到要像康德在思维方式上的哥白尼革命那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②同上,第243页。这首先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理论思路,表现在实际的历史中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现实进路。具体而言,胡适和周作人不仅有顶层设计和“大胆的假设”,而且是理念的预设先行,正如胡适自己所说,“我的白话文学论不过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一部分(小说词曲等)已有历史的证实了;其余一部分(诗)还须等待实地试验的结果。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③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第126页。正因为这种“大胆的假设”并非来自经验归纳,所以它不仅能够在认识上烛照过去,更可以在实践上开辟未来。胡适“大胆的假设”的实验主义理论顺序至少表现为逐级下降的三个层次:从“人的文学”到“白话文学”再到对民间文学各种体裁以及其中的“箭垛式”人物和“滚雪球”式情节的具体研究。胡适提出“双线文学史观”并撰写《白话文学史》,周作人提出“文艺的”和“学术的”双重目的,都不过是实验主义意义上“小心的求证”而已。这体现的正是康德和杜威对胡适产生的双重思想侨易所带来的精神质变。“按照胡适先生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推论他思想的逻辑:唯有思想的独立,才会有人格的独立;唯有人格的独立,才会有人格的平等;唯有思想的自由,才会有权利的自由;唯有人格的平等,才能保证权利的平等;人格和权利上能够自由平等的人才是现代人,唯有现代人才能组成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④席云舒:《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在首届海峡两岸“胡适奖学金”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关东学刊》,2017年第10期。也可以说,只有这种“现代人”才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应该努力去认识并在实践上加以促成的“民”,才应该是该学科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就诞生在“人的文学”与“白话文学”的交叉点上,而实践民俗学恰恰试图在这个交叉点上返回康德和杜威的自由民主理念,以此彰显并推进以胡适和周作人为代表的先驱学者所开创的事业,使它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用胡适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继续做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挥光大。”⑤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全集》(第11卷),第216页。
第三,单就“白话”和“白话文学”概念来说,在1919年发表的“A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中国的一场文学革命》)一文中,胡适把“白话”称为plain language(大众化用语)或vulgate Chinese(通行的汉语)⑥胡适:《中国的一场文学革命》,《胡适全集》(第35卷),第237页。,这是民主化的自由理念在语言上的双重体现,旨在以语言的普遍权利为突破口来争取民众个体在文学表达上的自由权利,以人道法来破除并取代身份等级的丛林法。正如李小玲的新著所指出,胡适的“白话文学这一概念从提出伊始就是兼顾语言和文学、价值主体和学术主体的双重考虑的”,因此,“我们对胡适有关民间文学的理解就不能仅局限于文学的范畴,还应该纳入到哲学的考辨当中,而关于哲学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人的问题。”继而,李小玲的新著超出单纯语言层面对“白话”和“白话文学”概念做出深入阐述,认为“胡适对于民间的主体定位,没有选择直接进行定性的划分,而是从语言的角度切入——使用白话的群体。不论其具体身份是什么,只要是使用,且较多(或几乎全部)使用白话的人就是民间文学的主体。”当然,在胡适生活的年代里,他首先需要把白话文学视为实验主义工具,正如他在《四十自述》中所说,1916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①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第108页。后来他又回忆说,“今日回思,在1916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②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44页。在很大程度上说,这并非胡适本人的思想局限,而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使然,因为胡适本人已经意识到:“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新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③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第121页。所以,在胡适看来,白话文学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实现“常把人看作一个目的,切勿看作一种用具”这个根本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在白话文学已经实现了工具革命并且已经变成普遍的表达工具的今天,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白话文学的“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从内在形式上来重新审视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本身所蕴含并要求的内在对话形式和先验伦理原则,因为“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都要求把“我们”作为体裁叙事行为的纯粹发生形式和先验基础,而且“我们”就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发生和存在的公共伦理条件。④参见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这个“我们”不再是非人格化的、面目模糊的、可以被任意解说的那种集体和群体形象,而是由一个个民众个体组成的现代共同体。当此之时,民间文学就是“白话文学”,“白话文学”也就是民间文学,因为它们在内在形式或本质形式上都是“我们”文学⑤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第160页。,都是有可能让私民成为公民的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实践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促成“我们”这个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纯粹发生形式条件由内而外、由潜而显,由此得到真正的觉识和普遍的实现。
三
唐代诗人杜荀鹤有诗云:“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小松》)经过李小玲新著的深入挖掘和重新阐释,经过我们对胡适与康德、杜威的侨易关系的再度突显和理论还原,胡适民间文学思想这棵“凌云木”才显出其原有的和应有的高度,才等来“直待凌云始道高”的时刻,它“在中国民间文学学科领域中被遮蔽的光芒”才重新焕发出来。尽管胡适在理论上的确存在着李小玲新著指出的一些缺点,比如,“更多是感悟式和灵感式的概念方法的提出”,“没有系统的论证”,但胡适提出的根本理念和远见卓识以及他在身体力行方面做出的非凡业绩,都无愧于他的时代。通过思想侨易带来的精神质变,胡适不仅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建立了新范式,而且“毫无疑问地已尽了他的本分。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学术与思想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我们究竟决定怎样尽我们的本分了。”①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该在先驱学者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并且以往鉴来。李小玲新著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返回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实践理性起点,接续学科的伟大传统,并以扎实而新锐的理论研究实绩表明,尽管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学理思考和实践觉醒发端于西方学者,但我们并不能说这些问题就不是中国学者自身的问题,相反,我们应当看到:这些问题不仅自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内在问题,而且是更严重、更紧迫和更应该得到优先应对和严肃思考的中国问题,更是侨易学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胡适与康德、杜威的思想侨易关系表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自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验研究,而且更是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理念引导与规范之下产生的人文研究。尽管这样的“凌云”高度并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领会和发扬光大,但实践民俗学需要返回胡适为我们开启的学科起点而重新出发,从研究理念的逻辑原点上寻求更加明确的实践理性目的和更加丰富、更加具体的理论规定。
实践民俗学不反对在认识民俗时做出必要的经验性假设,也不否认经验性假设在实践领域常常能够起到各种各样的实用效果,而是反对在实践领域中仅仅停留于、仅仅满足于经验性假设和单纯的试错性假设,反对胡适早就批评过的那种“仅仅按照戒律去谨慎行事,就像盲人在黑暗中摸索那样笨拙的尝试”。这种反对不是反对这样的做法本身,而是反对仅仅停留于、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做法。实践民俗学主张在实践时以“常把人看作一个目的,切勿看作一种用具”这一具有大爱的实践法则来引导和规范经验性假设,以此在实践中减少各种有可能违背实践法则的任意假设和盲目试错。因为如果没有实践法则的引导和规范,各种经验性假设就会缺乏统一的实践目的和实践方向,就有可能偏离人性和理性的正当使用范围而把实践引入歧途,甚至可能在损害民众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之路上越走越远、愈演愈烈。这样一来,不仅民间文学实践、民俗实践和学科实践缺乏甄别的普遍标准和评判的通用尺度,而且必然导致侵犯人权的民俗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苦难。反过来说,只要不违背实践法则,民众个体在民间文学实践、民俗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任何一种经验性假设都是应该被允许和被宽容的自由选择,都可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理所当然。这些都是胡适的自由民主理念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启示。
胡适与康德、杜威的思想侨易关系,或者康德和杜威通过胡适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所产生的侨易作用,也再次印证了吕微的敏锐断言:
一门学科的理论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终极关怀),并不是在其起源处就一劳永逸地被固锁住的,学科理论的基本问题需要该学科的学者不断地追问。就此而言,学科问题是学科的先驱者和后来人不断对话并通过对话得以解决的结果。②吕微:《反思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