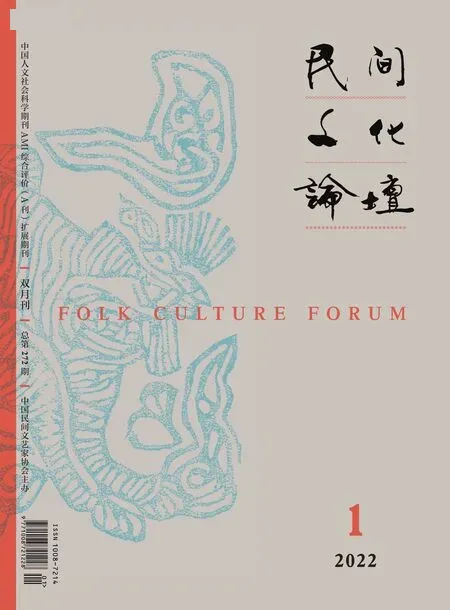记忆建构视阈下的口述文本研究
—— 以天津老会为例
张 洁
引 言
随着非遗普查工作基本完成以及评估认定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跨过第一个普查与认定的十年,进入“非遗后时代”,工作重心由“艺”向“人”的转向推动了全国范围内传承人口述史的采录、整理与研究热潮,并逐渐成为非遗工作者广泛应用的田野方法与写作体裁。当前正值非遗保护工作第三个十年的到来,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亟待从田野到理论的提升与转化。
传承人口述史的资料性、档案性及知识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口述史的主要特点①冯骥才:《为传承人口述史立论》,《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年,第2页。,目前相关论点主要集中于方法论探讨,缺乏对传承人叙事文本及叙事语境的整体关照。作为一种民间叙事,传承人口述史往往隐含着民间社会的文化心理与叙事策略,这对于理解民间文化传承人及相关文化事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传承人口述文本及其口述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切入点,结合相关史料文本思考权力话语影响下的传承人叙事心理,探讨传承人“记忆”之所以被“如此构建与讲述”的原因。
一、口述文本研究的理论维度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之“文本”一词的理论范畴及其与记忆、口述之间的互文关系。“文本”(text)原意为编织之物,随着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的革新与转向,文本的意义结构从单一指向延伸为多重阐释,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史学等领域的文本批评与分析中,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关键词之一。目前国内关于文本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其一,在一般语境中,“文本”常被用来表示书面化的语言形式,包括手稿、印刷品等具有表意功能的实物载体,研究者主要关注文本与作者之间的意义指向关系。其二,在文本意义的结构层面,文本被视为理解事件之进程中的一个阶段①转引自潘德荣:《文本理解、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该视角突破了物质形态的文本限定,强调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互动过程及其形态,符号学则进一步将文本视为一个被社会文化因素浸透的复杂构造,②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认为符号的意义取决于解释者在特定场合的解释,凸显了共时性分析在文本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新史学领域,共时性视角为传统的历时性述史方式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意义空间。较为典型的案例如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王明珂对羌族弟兄祖先故事的研究以及赵世瑜对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研究等,均指明了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记忆的研究经历了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到文化记忆的理论拓展,研究对象从心理结构、社会结构转向记忆、文化、群体三个维度的总和③刘慧梅、姚源源:《书写、场域与认同: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图式重建理论”认为选择、抽象、解释、整合、重建五个过程以及记忆个体的动机、目标、信仰等都会影响记忆的重建④程岭红、黄希庭:《记忆准确性的认知取向研究》,《心理学探新》,2001年第4期。,可见记忆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过程显现,会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而主动或被动地重建记忆。因此,在非遗语境中,动态生成与循环建构的记忆共享成为保障传承人集体认同与文化传统承续的基础,如果将传承人视为民间文化的建构者,传承人口述文本的研究可推动文化研究由一元向多元的发展,并呈现出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⑤[美]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基于这一角度,笔者认为个体记忆生成的来源有三,一是源于个人经历的具体事件,二是源自他人个体经验的诉说,三是源自社会事件的集体参与。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人记忆生成后又不可避免地经历个人回忆、受他人引导回忆、与他人共同回忆的自我互动、与人互动的记忆建构过程,同时每一次的交流、访谈都是一次新的意义建构活动。可见,记忆不存在绝对真实,口述史也不存在客观真实,而将口述资料视为意义文本,则可通过研究口述文本来思考影响传承人记忆导向的内在逻辑。
二、历时性回溯:口述与文献的互文
自元代始凿大运河后,天津逐渐发展为南北漕运的重要枢纽并吸引了各地商户聚居于此,因毗邻历代政治中心,其地域文化中融合了宫廷贵族的精致规矩与商会码头的市井之气,南北民俗信仰在此地互融共生,逐渐形成了众多以村社为单位、以“会”为名的民间结社组织。在历史发展中,民间老会作为以皇会为代表的酬神祭典活动中的重要组织而受到官、商、绅、农各阶层的支持,其兴衰极大受制于这一依附关系,数百年来经历了从精神需求、政治需求、经济需求再到当前作为地域文化名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嬗变历程,通过老会群体记忆的代际相传而构成了共享的历史记忆。
(一)皇权制度对老会历史的形塑
天津皇会原称娘娘会,是在妈祖信仰与民间花会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酬神祭祀活动,因其独特的组织结构和行会方式而区别于台湾、湄洲两地的妈祖祭典。传说由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亲临现场观会而始称“皇会”,这一传说无疑树立了皇室权威在皇会活动及一众老会历史记忆中的核心地位。
天津老会关于“皇赐”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甚至载入文献。据《天津皇会考纪》所述,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天津时曾赏赐乡祠前远音挎鼓中幡会八件黄马褂、两面龙旗,赏津道鹤龄会四个金项圈、两面龙旗。①望云居士、津沽闲人撰,张格点校:《天津皇会考纪》,转引自来新夏编:《天津风土丛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0、75页。在乾隆己亥年(御赐之后38年②冯骥才:《年画古版<鹤龄老会>发现记》,《年画行动:2001—2011木版年画抢救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3页。)制作的木版年画《鹤龄老会》中清晰描绘了金项圈与龙旗的样式,鉴于图像本身所具有的叙事功能,尚不能排除“图像造史”的可能性。而后来关于天津皇会的相关著述中均沿用了《天津皇会考纪》中皇帝御赐说,使其成为皇会鼎盛时期的“真实”写照。现存的挂甲寺庆音法鼓銮驾老会因祖传的半副銮驾而声名在外,相传该銮驾由明代一位娘娘所赐,会中鼓箱上的“从明朝崇祯末年赐给挂甲寺”“同治五年岁次丙寅巧月合会人等制”等字样从时间上强化了这一传说的信度。
王秦庄同议高跷③为行文简洁考虑,下文一律以老会名称指代受访者。:过去天津皇会只限天津城里的老会参加。那时候城里的老会多,离得近,郊区老会没机会参加。另外,皇会对老会的身份也有要求,不是想去就能去。就算是有五百年历史的高跷会也进不了香道,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擦眼抹粉的都属于下九流,只能在会道边上候驾,等娘娘路过的时候表演,演完就撤。不像现在咱们都叫民间老会,只看你传承了几百年,所以现在天后宫有庆典我们也能去了。④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1.8.23;采访地点:天津市杨柳青镇东寓法鼓老会会所。
这段口述描述了旧时天津老会存在空间及身份的等级划分。一方面,高跷会作为“擦眼抹粉”的“下九流”被限制参加皇会,但在文献记载和《天后宫行会图》中均有高跷会在列。另一方面,城中会因其地缘优势享有香道行会资格,地域差异导致了老会表演机会的失衡。
相较于城中老会“皇赐”传说的多文本叙事,津南葛沽西茶棚关于慈禧太后赏赐娘娘衣袍的传说显然缺少说服力,但在现实世界中,其通过对皇室权威的借力使太后御赐的娘娘袍成为茶棚地位的权力象征。
有些学者认为,即使是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口述史亦应重点关注其作为“史”的属性,如无法对口述资料辨伪,则无法称之为史。约翰·托什(John Tosh)指出,与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表述相比,口述研究的重要性更应“作为表明社会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珍贵证据”⑤[美]约翰•托什:《口述史》,定宜庄、汪润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关于历史真实的讨论在学界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个世纪之前,顾颉刚提出的“层累造史说”已经作出了解释。层累的历史如同建构的记忆,都可以视作社会建构的过程,个体、集体与社会相互影响使这一过程呈现动态且非客观真实的特点。
(二)政府、商会介入下的老会变迁
据记载,清政府曾严格禁止各种民间组织的形成及相关送神游行活动,①吴效群:《皇会:清末北京民间香会的最高追求》,《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但与一般民间香会不同,妈祖祭典历来受官方扶持。根据《元史》中记载的“海漕粮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②宋濂主编:《元史》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第0292册,第0402c页,http://www.guoxuemi.com/siku/122914ehee/344869cxbl/,浏览日期:2021年12月15日。,以及代祀使臣张翥对当时天妃宫祭典活动的诗文描述③张翥:《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尚洁:《天津皇会》,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2页。来看,天津妈祖祭祀活动自元代已享受国家正祀,这无疑推动了天津成为北方妈祖信仰的传播中心。
此后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妈祖祭典活动逐渐成为当地官商、民众、庙会各方利益高度统一的集体盛会,其反映于商品贸易、文化娱乐等方面的社会功能逐渐超越原来的信仰功能。据天后宫已故住持张修华回忆:“清朝政府更特许在皇会期间,各地商人运货来津者,只要在车、船上插一面写着‘天后宫进香’的黄旗,就可一律免税。”④张修华:《我和天后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且数日之内,天后宫周边商铺销售利润高于市价三倍之多⑤来新夏编:《天津风土丛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页。,足可见皇会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基于此,在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天津政府仍组织了最后一次皇会活动以求缓解经济颓势,参加过此次皇会的民间老会莫不以此为傲。
皇会这类祭典活动的组织、运行对当地商会的依附性极强,商会也借力于皇会的影响力来标榜自己的商业地位,这为民间老会的存续提供了土壤。但在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情境下,日常生产生活难以维持,政府、商会无暇再组织此类活动。一方面,外国势力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后信仰和皇会活动的地标化与民族化,使之成为促进国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正因其与“封建制度”的紧密关系,引发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全力抵制,在较长时间内,皇会与相关民间组织成为科学语境下“封建、迷信、落后”的代表。可见民间花会的兴衰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除了官方对于皇会活动的赋能以外,官方认证对地方民间信仰的影响亦十分明显。葛沽宝辇会由八驾宝辇构成,以天后宝辇为尊,按照传统,出会之前,其余七辇需与天后宝辇“对脸”以示接驾。
葛沽天后宝辇:宝辇供奉的是大奶奶。我听老人们说是妈祖,受过皇封。就这个大奶奶早……其他辇过去都和大奶奶对脸,打换了会头,东茶棚开始不对脸了。
葛沽东茶棚:东茶棚供奉的是海神娘娘。东茶棚那个时候是天妃圣母,我现在改为天后圣母……东茶棚1986年恢复后,始终和天后宝辇没对过脸……因为以东茶棚为老,以宝辇为尊,宝辇是官家的,是商务会制作的,有权势,东茶棚是私人的。⑥史静、路浩:《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葛沽宝辇老会》,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5—153页。
通过对比天后宝辇与东茶棚的口述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其中隐含的两对关键词,“老”与“尊”和“私人”与“官家”,充分体现了老会传统观念中的二元特征,民间社会对于资历和权威的崇尚表征着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礼俗等级思想。葛沽地方著述中多有提及东茶棚成立于明万历年间,曾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接驾并获赞赏,虽其资历深入人心,但地位仍不及官府、商会扶持的天后宝辇。顾颉刚在《妙峰山》一书中提到“‘老会’是香会中的领袖,别的香会逢到疑难时,都要去请教老会中的会友”①顾颉刚:《妙峰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9页。,因此老会对于资历的强调不失为一种对抗策略。
口述中还呈现了关于两家女神身份冲突的问题。东茶棚为海神娘娘(妈祖的别称),现任会头依据历史上官方对妈祖的最后一次册封将其改为“天后圣母”,无疑是对天后宝辇官赋权威的挑战。根据调研资料来看,当地普遍认为天后宝辇供奉的“大奶奶”应为云霄娘娘,而非妈祖,三霄娘娘(云霄、琼霄和碧霄)信仰在葛沽地区拥有大量信众基础,但由于东茶棚在1987年天津市举办的首届民间花会比赛中获奖,加之近年来对于妈祖信仰品牌的打造逐渐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东茶棚地位得以提升,引发了天后宝辇在外部环境导向下形成的话语冲突,进而推动了记忆的重新建构。
可以看到,葛沽地区存在妈祖信仰与三霄信仰地位的重构。葛沽女神信仰可溯至元代,清代重建娘娘庙时供奉了“全供刹”十三位娘娘(也有十四位之说),当时位列其首的是三霄娘娘,而眼光娘娘、痘疹娘娘、碧霞元君、天妃娘娘位居其次,可见妈祖至少在该庙清代重建以前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再次复建时,“娘娘庙”更名为“天后宫”,意味着妈祖成为官方认可的女神之首,一方面可以借力于妈祖文化全球化以及三岔河天后宫的品牌影响力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另一方面可通过重塑“合法”身份来巩固自己的信众群体,其地位与优势不言而喻,种种可能性都指向民间记忆的可塑性与不确定性。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将通过书写系统来长久储存信息的形式分为“正典”与“档案”两种类型。与后者相反的是,前者特别强调其“活跃的记忆”以及“社会有意筛选”的特征,这有利于一个社会的共同定位和共同回忆,“正是由于这种双层结构和两种记忆维度之间的互动,文化记忆自身具备了持续改变、创新和重构的潜能”②阿莱达•阿斯曼著,王蜜译:《重塑记忆: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建构过去》,《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个体和集体对特定的过去如何索取和表达取决于相关的个体和集体分别处在怎样的意义关联体系中,需要从过去引申怎样的意义。③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传说本身就是记忆建构的产物,而各道老会的光辉历史亦是基于集体利益而进行的塑造与调适。
(三)民间信仰与老会变迁
在华北地区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女神信仰包围下,妈祖作为外来神祇传入天津并发展至今天的信众规模,并非完全依靠南方移民信众的推动,而是入乡随俗,不断社会化的改造成果。④姚旸:《论皇会与清代天津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为中心的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
葛沽天后宝辇:天后宝辇的大奶奶抓全面,有求子的,有求升学顺利的。⑤史静、路浩,《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葛沽宝辇老会》,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0页。
民间信仰的发展及消亡较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选择。显然,想要受到民众广泛的信奉和供养,首先得迎合民众需求,社会选择取决于社会需求,社会需求制约着社会选择。
海河西岸三岔河口小直沽地方……正当经北运河运粮往大都的联运起点,自然也需一番祭祀,于是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在海河西岸小直沽也建另一处天妃宫,从此天妃又在护海以外兼负了保护河运的职责。……因天后既身为女子,最易得妇女的信奉……主持庙宇的人,为了吸引更多的香火,根据群众这种迷信心理,迎合习俗,给天后加上了兼管子嗣和天花的职务。①该文成稿于1965年,其中表述亦可结合时代背景考量。张修华:《我和天后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162页。
妈祖原为海神,专司庇佑海运安全,传入天津后,妈祖的职能转向全能,并进一步取代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北方女神体系在天津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妈祖信仰的在地化重构,在此过程中,妈祖被赋予了更加全面的职能,在不断完善与建构中顺应不同时代下的社会需求。
民间信仰与口头叙事的发展变迁存在着相似的内在逻辑,神祇的身份等级与职能变换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众之间权与利的博弈。在皇会活动中,天后宫为皇会带来了观众与消费群,皇会为天后宫吸引来了潜在信众,庙与会的结合又满足了民众的信仰需求、娱乐需求及消费需求,三者在互惠互利中达成默契。可以说,皇会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并反哺于宫庙香火。例如戏曲、杂耍等民间演艺文化的发展皆得益于庙会所提供的文化空间,参与民众在香客、顾客、看客的身份中转换,严肃的宗教活动逐渐发展为酬神娱人的庙会。
传统社会的神圣信仰不仅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亦是统治者借力强化统治地位的有效手段。民众对神的依赖性越强,制约越大,相应的禁忌与规矩也越多,而皇会等祭神活动在历史中愈发凸显的娱乐性也正是其所处的社会情境的折射。对于当代人来说,如今的妈祖与皇会更多是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符号或者是一个标志性的地域文化景观而存在。
除了参加皇会涉及妈祖信仰以外,民间老会在日常生活中多呈现出信仰的离散性特征,即各会有各会信奉的神祇,亦有各自的祭祀活动。
杨柳青东寓法鼓:根据普亮宝塔的记载,东寓法鼓会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时期,于五爷是第一代会头,他从北京皇姑门学道还俗回来建了佛堂,后来就有了法鼓会,法鼓会是为佛堂服务的。②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0.1.18;地点:天津市杨柳青镇东寓法鼓老会会所。
贾沽道善音法鼓:过去每个村子都有自己供奉的神仙和庙宇,村里普遍流传着关于这位神仙到来的传说和风俗,比如我们村过去供奉的是华佗和孙思邈,所以每年4月27日华佗诞辰那天我们村都会设摆表演,很热闹。从表演形式来说,主要分为文、武两种,西郊这边的法鼓会大部分是做善事(吹会、坐会),属于文法鼓,市里、北郊等地都是带有表演形式的武法鼓。每道法鼓的特点不太一样,我们老会原来的轿在“文革”时期销毁了,现在的轿是80年代后期根据老人们的印象,村里集资请人复原的,所以除了颜色以外,它的体积、图案跟原物都有一些区别,过去每个村子都有专门的会所和维护资金,一代一代的村民也都愿意出钱去维持这个传统。③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1.8.23;地点:天津市杨柳青镇东寓法鼓老会会所。
以上口述中出现了两组关系概念。一是“会”与“庙”的依存关系,明清时期民间道、释教派及佛堂众多,村庄多拥有自己的保护神并建有庙宇供奉,在传统的农耕思想中,定期举办酬神活动往往关系到村庄集体的直接利益。“庙”成为村落记忆的重要传承空间,为民间老会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人文基础。
二是法鼓的“文”“武”之分,法鼓是天津独有的民间表演形式。传说最早在佛事活动中由僧人演奏,因其具有超度、酬神的功能,清初由津西大觉庵传入民间并得到广泛传播,④郭忠萍:《法鼓艺术初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6页。其应用场合逐渐从一般的丧俗祭祀逐渐延伸至大型的庙会、皇会以及自娱活动。在法鼓的传播流变过程中,其原本的宗教信仰逐渐弱化,除了西郊杨柳青一带的法鼓会仍发挥其善事活动的功能之外,其余法鼓会多以表演为主,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民间记忆的传承与传播通常以口头的方式实现,话语实践和身体实践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传承人口述史因其传承性在记忆视域中呈现出更为鲜明的集体化倾向,这种集体特性是个体参与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集体记忆填充与维持了欢腾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空白①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另一方面,节俗仪式及其相关的符号文本为社会活动中的交流与操演提供了长期、稳定且合法的时间周期,强化了文化记忆的共享性和共同体的联结性。以上两个方面从记忆与生活、仪式与表演两个维度体现了民间记忆建构的阈限性。
三、共时性互动:“我”的期待与“社会”的期待
(一)认同、调适与合作
天津有冯高庄、王文庄等几处林姓聚居地,均自称妈祖后人。传说为燕王扫北后由福建北迁至此,因妈祖未婚未育,这些林氏后人尊称其为姑奶奶。近年来随着皇会活动的复兴,每逢有祭典活动均受邀为天后执事扶辇,并以妈祖后人的身份参加两岸三地的妈祖祭典。由于定期出席活动,他们统一定制了标有“林氏家族”字样的服装,不仅重新维系了宗族关系,也加强了在津妈祖后人身份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此外,他们还积极寻求与其他知名宗亲的联系,并通过家族集资为各类走亲活动筹集经费。
冯高庄林氏后人:我们是春祭大典、妈祖诞辰和妈祖文化节的时候来天后宫。明年我们要去河南新乡比干庙,他是我们的太师祖,姓林的都是他的后代,费用都是大伙集资。我们村姓林的都是一家,家谱都在,现在是第十五代了。②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0.1.17;地点:天津天后宫。
随着各地对历史名人价值化的利益需求及对地方名人文化活动扶持的加大,此类寻根问祖活动逐渐升温。正如段义孚所言,“如果人类要建造一个共同世界,战胜自然和其他的族群, 合作是必须的。”③段义孚、韩红宇:《论社区、社会及个人》,《教育教学论坛》,2013年第38期。
个人、群体之间的认同往往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身份认同也即身份塑造的过程。个人出于对群体归属感的需求促成了社区的联结,在社区中的成员往往有着相同的语言体系、交往习惯,在社区形成之后需要不断采取一些维护手段使其得到巩固,社区联结的背后除了满足个体需求之外还应符合集体利益。
作为依托社区力量形成的组织,天津老会对于增强社区意识、社区认同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随着传统文化空间的重新规划,抱团取暖、建立合作网络,向外寻求发展成为当下民间文化传承的主要策略,也是提升话语权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信俗活动受政策影响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脱离了民众日常生活,加之医疗科技的发展与反封建迷信的号召,使原本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俗活动被烙上“封建落后文化”的标签,许多传统观念在现代生活中表现得格格不入。
葛沽天后宝辇:痘疹娘娘那儿有弄香灰回去的,弄点香灰水让孩子喝,专门治疗水痘的,这都是以前的做法,现在也少了。
葛沽阁前茶棚:现在入会不讲究了,只要你抬得了就行。过去不行,得查三代,看你的家庭出身,没有邪门歪道,不是二流子才行,否则就是对奶奶不敬。想摸,想当受累的角都不行。①史静、路浩:《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葛沽宝辇老会》,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
刘园祥音法鼓:过去来讲,法鼓会根本没有女的,也不允许参加,传内不传外,只能本村的学,现在哪的都行,先得传下去。②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0.1.17;地点:天津市北辰区刘园祥音法鼓老会会所。
由于传统信仰的接受度与约束力大大降低,现代医疗、科技常识的普及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本能选择发生转变,并加速消解了神性的超自然能力,使得传统信众与老会成员大幅减少。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引导着民众的思维方式,在昭示神性弱化的同时,传统的民俗心态与行动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在旧时的杨柳青,东寓法鼓源于皇姑门,香塔法鼓属于混元门,法鼓会与佛堂相互依存,西郊各道法鼓会成为当地人记忆中白事活动的象征。会员提到“开业之类的活动请这个(出会)的太少了,因为这个以前是伺候白事的”③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0.1.18;地点:天津市杨柳青镇东寓法鼓老会会所。,这一特征既使其区别于其它老会,又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对丧俗活动的限制迫使西郊法鼓开始寻求转型。笔者采访时,一位在音乐学院就读的年轻会员说:等我以后结婚的时候就要把这些法鼓会请来,我觉得白事需要这些东西,同样开业庆典等各类活动也得需要,他们不应该被否定和贬低。④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0.1.18;地点:天津市杨柳青镇东寓法鼓老会会所。此话显然出于一种在困境下主动建构传统的心态,文化事象的传承与变迁往往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作出调适来融入当代生活。
刘园祥音法鼓:咱们这有条制度,就是学生得了“三好”“文明生”会长马上就给三百块钱;还有70周岁以上的老会员,我们每年过年给六百块钱慰问金。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传承,这是共识的。我总结出来几种传承方式:家族传承是最好的,给这个钱可以鼓励他加强家族传承力度。还有一个是滚动式传承,学生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到六年级,这么循环式走,一个靠学校支持,一个靠我们的制度吸引。⑤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0.1.17;地点:天津市北辰区刘园祥音法鼓老会会所。
葛沽阁前茶棚:以前抬辇的人员不用给钱,现在得给会员钱。⑥史静、路浩:《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葛沽宝辇老会》,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78页。
上述文字中可以留意到几个变量,一是从会员制转向学员制,二是从无偿参与转向有偿参与。首先,刘园祥音法鼓是国家级非遗,也是众多老会中传承较好的一道会,除了传统的入会方式之外,老会提出了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进行“滚动式”招生与传习的策略来应对后继乏人的现实问题,即以学校为平台,宣传并招收学员进行培训,培训不仅免费,甚至还会得到现金奖励,这种方式下的传承虽不符合传统,但可以吸引人气。
(二)传统、坚守与诉求
尽管老会在复兴传承的过程中极力寻求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可行路径,但仍然无法避免传统日渐衰颓的趋势,会员入会标准也明显降低。随着时代、环境和语境的变迁,新旧审美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形成巨大反差,当代与传统价值观的背离导致皇会、商会与老会的依存关系被消解,随之而来的是经费、人员的紧缺所引发的仪式日趋简化、人员流动性大、技艺不精、传统会规的约束力降低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在当代老会复兴过程中将仪式、执事进行简化的行为也是将历史文化符号化的过程。
20世纪初至70年代,天津老会在战乱、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度停会甚至解散,80年代曾短暂复兴,90年代后随着村落城镇化与会员老龄化的问题日益凸显,社区搬迁、会员流失,老会与新型社区之间无法自洽,以村养会的传统难以维持。尽管近二十年来重新恢复的老会依然沿用了历史上的会名,以此标榜历史与传承,但事实上其中的大部分老会早已断了传承,因此传承人在访谈中往往流露出对于当下发展的焦虑与需求。
贾沽道善音法鼓:法鼓表演的时候为什么要挑食盒和茶炊呢?因为过去走会要走很长一段路,没有车,所以要提着一些吃的、喝的,后来逐渐变成一种轻盈优美的表演形式,但现在没有人再去挑。相比之下轿子更重,配上跑、停、转、弹等表演动作,更体现了人的宝贵。我们有两顶轿子,如果按照传统的表演形式,一边要鼓乐齐鸣,一边要抬轿表演,需要几十人的庞大队伍,所以现在只能表演一顶,另一顶沦为摆设,这样起码保证了表演形式在概念上的完整。说实话,没有人想去简化它的形式,只不过确实是无能为力去做。
民间老会算是一个小型社会,有自己的礼仪流程,所以请会、拜会都有一定的规矩。请会时必须亲自把请帖送到对方手里,只用电话通知是非常不尊敬的行为。拜会时要先互道辛苦、一躬扫地、互换拜帖,然后到棚子里给神上香,中国人的神仙概念还是很深。如果带会(携带会具)到场,要先给神表演,同时也能制造热闹的氛围。如果没带会,提两盒点心、茶叶或一面锦旗也可以表示重视,礼数、面子还是要有的。中国人讲究尽兴,表演结束后可以留下多玩一会,有流水席招待大家。现在有了电话、微信、电灯、录音录像可以简化很多流程,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当面下帖、点蜡烛、现场表演呢,这说明大家都在遵循一个传统。①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1.8.23;地点:天津市杨柳青镇东寓法鼓老会会所。
80年代以来逐渐恢复的老会主要借助政府的政策扶持,期间的城镇化进程使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场域与群众基础,除当地老人相继故去、村落拆迁等因素之外,原有街道、村庄名称的重新规划也逐渐淡化着当地民众对于老会的历史记忆。
贾沽道善音法鼓:原来天津有一百二十几道法鼓,但是由于九十年代平房改造、村民搬迁导致会里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达不到过去的水平,另外缺少场地、声音扰民这些现实问题又导致我们没有地方排练表演,几十年来已经有很多老会陆续消失,即使有一些老会还保留着会具,可是会员没有了,只能把会具放到文化馆以照片、录像、实物展示的方式去还原老会的基本面貌,但这个时候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杨柳青东寓法鼓:过去杨柳青有三道法鼓,十五街永善法鼓,十四街香塔法鼓,十六街东寓法鼓。咱们这街都是顺着南运河的河沿建的,从东边数一街、二街、三街……所以咱们的村名就叫十六街,会名叫十六街东寓法鼓,老会所就在十六街村委会,当时出会都是大队里请,给记工分,现在是个人出钱了。1991年左右大队房子扒了,会所没了。这几年刚给批了这个新会所,平时不能随便出会,时间、地点得经过批准。现在这些路名都是文革以后又重起的名,你要是问我柳霞路(新会所地点)在哪,我们还真不知道。②采访人:张洁;采访时间:2020.1.18;地点:天津市杨柳青镇东寓法鼓老会会所。
人员、经费、场地、会具是维持老会正常运转的主要条件,而这些的缺失造成了传承人的缺位。东寓法鼓恢复之后,会员年龄层分化明显,主要集中于70岁以上的老年层和20-30岁的青年层,老年会员多为七八十年代之后见证甚至参与老会复兴的一批人,材料中对80年代“大队出钱”“出会记工分”与当下“没地方”“没经费”的描述体现了老龄会员潜意识中将老会衰败的大部分原因归结为官方扶持力度的不足,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柳青老会的生存机制已经由民间主导转向政府主导,缺乏自身的能动性与造血能力。而作为复兴主力的年轻会员并未被老年会员被动、悲观的态度所影响,而是积极展开对当地老人的寻访,申报非遗项目,利用网络手段与外界开展交流。
四、结 语
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一批传统老会得以恢复或重组,与之相关的记录工作随之展开,当传承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掌握话语权时,口述访谈为其自我建构、重塑历史提供了契机。韦伯(Max Weber)指出:“要想考察任何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的根本成分,首先应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入手。”①[德]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第149页。转引自[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扉页。口述人在记忆表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当下性,记忆主体伴随着当下社会的需求、对话者的期待以及个人的心理预期对记忆进行有目的的筛选与编码。而口述文本的意义解读亦呈现开放性与无限性,符合“我”和“社会”的共同期待,是一种基于理解差异的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
由于传承人口述史概念诞生于非遗抢救的时代语境中,且在多年工作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界往往将其视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或档案储存形式而忽略其文本价值,其特有的知识性特征也在实际工作中被囿于档案与资料的形式。因此,传承人口述史应通过对传承人记忆的书写使其与历史文献和其它文化线索形成互文,以期从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复杂互动中呈现历史事件的时空踪迹和共同的意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