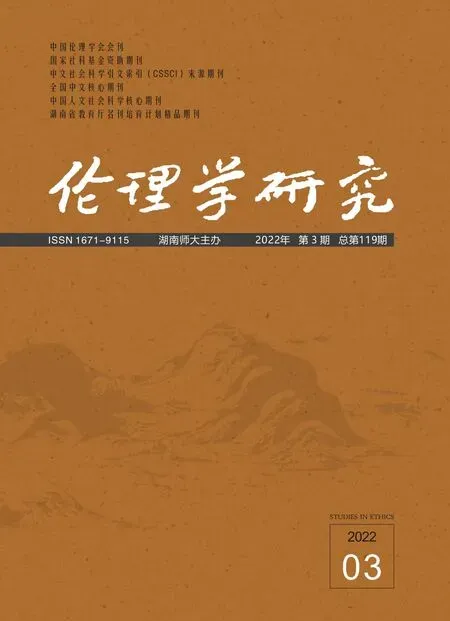个人基本私德六论
——基于儒学资源的分析
肖群忠
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社会救亡图存、奋发图强、革命建设、发展复兴的社会任务的急迫和繁重,社会主流价值往往比较重视引导青年和民众注重社会公德,从而把热情、精力投身到社会事业中去,甚至,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从道德上加以反思,如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最初认为是因为传统中国人只重私德而轻公德造成的。在百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后,加强文化建设、重铸民族道德之魂、重树礼仪之邦形象,都需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从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律反思,人们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自然离不开人们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这些涉及人际、己群关系的社会道德,更离不开纯粹个体品质或者美德意义上的个人私德或者个体品德。虽然,道德生活中的社会与个人总是处于一种相互联系与影响的互动过程中,但笔者更相信儒家的道德思维方式的真理性:即私德是公德的基础,这就像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明明德是亲民、新民的基础,内圣是外王的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 年10 月印发的道德建设文件《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几大具体领域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的基础上,明确将“个人品德”纳入并首次对其内容进行了规定和表达[1]。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2-4]。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社会在百年之后,在道德生活与社会道德建设中又重新重视个人私德,这可以说是一种符合古今中外道德生活内在规律的巨大进步。作为一名伦理学工作者有责任自觉推动这种进步,笔者曾撰有《论“个体品德”及其培育的当代意义》,对个体品德与私德概念的交叉区隔、一般意义的个人私德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国家对公民基本私德的道德期待的联系与区别也作了分析,并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规定表述的“个体品德”内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论述了培育个体私德的当代意义[5](25-32)。之后,笔者又进一步思考:有无可能提炼概括出超越中西古今的时空差别,超越国家对个体品德的期待,而从一个人纯粹做人美德角度的所有好人和君子都应该追求或者具备的基本美德呢?也就是个人基本的或者普遍的德性是什么?钱穆先生有言:“窃谓惟德性乃大众之所同,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问者即当问之此,学者亦当学于此。只有在大众德性之共同处,始有大学问。只有学问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处,始是愈广大。”[6](2)这段话可以说对研究这一问题给予了很大鼓励。拙文是根据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经过思考探索,提出的一个基本思考及论证,供方家讨论指教,也期望从实践上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对个人私德重新重视的进步潮流,对提升民众整体道德素质有所助益。
什么是个人私德的基本或者普遍德性?对此问题,钱穆先生的下述意见也是深具启发意义:“人性不是专偏在理智的,理智只是人性中一部分,更要还是情感,故中国人常称‘性情’。‘情’是主要,‘智’只是次要的。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有性情才发生出行为。那行为又再还到自己心上,那便叫作‘德’。人的一切行为本都是向外的,如孝父母,当然要向父母尽孝道。但他的孝行也影响在自己心上,这称德。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故中国人又常称‘德性’。这一‘德’字,在西洋文字里又很难得恰好的翻译。西方人只讲行为造成习惯,再从习惯表现为行为。中国人认为行为不但向外表现,还存在自己心里,这就成为此人之品德或称德性。性是先天的,德是后天的,‘德性合一’,也正如性道合一,所以中国人又常称‘道德’。”[7](15)这段话的重点在于,德虽然离不开智性要素的参与,但重要的是情,德性、情操、品质的根本特性在于由内在的性情发出于外在的行为,而又由外在行为还归于性情,是内在性情(心理)和行为的高度统一。本文六个基本概念,也作这样的理解。它是个体的心性与行为的统一,之所以称个人或者个体,就在于它不会或者不太涉及人际交往,是个人的一种心性和德性。正如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但这种心性和行为总还是要表现或者投射或者应用于人际交往中去的,因为善恶总是在关系中体现的,但我们还是力图从个人德性的角度去分析,而尽力避免后者。比如,目前中央有关文件中对个体品德的规范表达就有“爱国奉献”“明礼遵规”,笔者认为这是国家希望个体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应具有的道德态度与品质,但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私德,其实质内容应该是公民道德与社会公德。另外,什么是基本的或者普遍的德性?这需要我们借鉴伦理学史上先贤的思考,立足于既有的体验、概括,力图达到更为科学的认知。
一、论善良
“善良”显然是一个现代合成词,也是中国民众在对一个人德性进行评价性表达常用的词,如果给它一个简单界定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良心善行(举)。良心就是一个人的善心、好心。实际上我们在认识和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善良”德性和品质时,往往是指其有无恻隐同情心和亲爱博爱心。一个人善良首先是有这种出于恻隐同情基础上的爱心,一个人有爱心才会对别人和万物产生善意,因此,儒家讲“亲亲、仁民、爱物”,就是这种推扩思维,“民胞物与”“天下一家”都是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一切推扩的原点、基础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的那点爱心和善意。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善根的本源性和重要性,因此,慈悲心、同情心、爱心普遍受到世界各大宗教的重视,佛教讲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基督教讲爱人如己,世俗教育也都特别重视“爱的教育”(既是教育名著书名也是教育理念),可见爱心或者爱情(广义的)、善意或者良心实在是所有个人美德和人格的最根本的基础。
人的德性或者品质是心与行的内外统一,人的爱心与善意是存于人的内心的,它需要也必然会表现于外在的行为中,这样才能使别人感受到他的爱心和善意,那么,一个善良的人必然有很多“善行”“利行”,这些才是一个善良之人的外在行为特征。比如,一个有同情心的人看到别人的苦难肯定不会生出幸灾乐祸的心态,而总会生出悲悯同情之心,就如孟子所举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又比如,当人们观赏影视剧时,看到悲伤的情节就难免流泪,如果在这时不仅不伤感反而发笑,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拂人之性”,是一个很可怕的恶人。这种同情心不仅对人是如此,还会扩展到万物生灵,过去农村一些“善人”连蚂蚁都不愿踩死,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蚂蚁虽小,也是一条生命,这也与佛教不杀生、道家中之“慈”即反对武力伤害的思想是一致的。这种基于恻隐同情之心所生发出来的爱心善意,不仅会停留在心情与心意上,而必然会见诸实践交往中的善行利行中。
善行一定是在人际利益关系中有利于他人,别人才会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和善人,因此,朱熹解忠为“尽己之谓忠”,而冯友兰先生则将“忠”解为“尽己为人”为忠,“若只尽己而不为人,则不是普通所谓忠的意义。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尽自己的力量为人谋是忠,否则是不忠。但若为自己谋,则无论尽己与否,俱不发生忠不忠的问题”[8](14)。这即是说,任何一种善良必然是为人利人的,尽己就是主体必须有所付出和奉献,其行为的目的是“为人”“利人”。因此,在生活中常见一些善良的人或者好人,总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乐于奉献。这种利人之行有大有小,小的可见之于任何一种具体的善行中,见人吃力时搭把手,对别人的一个微笑和礼貌,大的功德如遇到灾难时的救人财产性命、捐钱捐物,平时的助人求学、修桥铺路、慈善公益,等等。更大的善行就是那些圣人如佛祖、圣雄甘地、马克思等“为人类工作”。虽然奉献巨大,但发心都是对人类生灵的那份爱心和善意。善行不仅是这种行为上的实际利益奉献,一个人是否有爱心善意,人们其实在交往中都会感受到的,如能否彼此同情、相互理解和尊重,还是事事以个人为中心、自私自利。
善良除了具有这种正面的爱心善意外,还有其反面价值的限制,即一个善良的人首先是一个不害人的人,孟子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非常准确:“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一个善良的人首先要扩充自己的无欲害人之心,这样爱人之仁爱感情就会不可胜用而爱心永驻。总之,从善良就是人的爱心与利行的角度看,它相当于传统美德中的仁与忠在个体身上的凝结。
人为什么要做一个善良之人?这个问题似乎与“人为什么要行道德”有同类性,这正好证明善良在人的私德中的基础地位,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道德是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辉,一个期求活出个人样、不甘堕落的人自然会崇德向善,做一个善良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不是为了什么,而是我们自身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需要。“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做一个善良的人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追求,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坏人或者恶人。
做善良之人可能吗?有人可能相信“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也不能说绝对不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这种感叹了,但是,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还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另外,行善积德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功利回报算计,更重要的是求得自己的心安即安身立命,因此,“吾欲仁,斯仁至矣”,“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做一个善良的人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加强自己私德修养的首要追求。
二、论正直
善良与正直作为个人基本私德,已经写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关于个人私德的表达中了:“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1]这说明,此两德是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的个人私德的重要德目。
那么,什么是正直之德呢?《周易·坤卦·文言传》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用恭敬心、敬畏心来规范我们的内心,要以“义”(合宜、恰当)来规范、约束我们的言行举止。这也就是坚持道义原则而不“枉道”即丧失原则,正如孟子所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一个有正直之德的人往往心有原则,行事合宜且正,直言快语、仗义勇为,不苟且、不奸诈、不谄媚、不凌弱。其反德用孔夫子提出的观念表达就是“乡愿”之人。“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之人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古之所谓乡愿之人就是今天所谓的老好人,就是不讲原则、不分是非、四面讨好、八面玲珑之人,孔夫子认为这种人实际上是道德的破坏者。为什么呢?因为乡愿之人不顾道义,一切行为都是在算计自己的得失,而且在外表上具有伪善性,这种人当然会破坏道德,而且在人际交往中是很危险的,因为其表面现象很能迷惑人,可到了涉及其利益时,他就会露出真面目而翻脸不认人。可见正直之德就是传统“五常”中的“义”德在人身上的凝结。而“有义”“守义”在荀子看来是人区别于水火、草木与禽兽的根本所在,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
当我们把义与利相对时,当我们说“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时,这时“义”就代表整个道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直”就是对“义”的坚守,或者说是对道义或者正义的担当与坚守。这可能是正直一德的质的规定性,其他的都是其行为表现。“宜者,义也。”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宜,就是善、正确或恰当,它是指对一切事物的裁断合于节度,处理一切事物合宜,都被称为“义”。
《墨子·天志下》曰:“义者正也。”道家的《文子·道德》也说:“正者义也。”总之,以“正”释“义”较之以“宜”释“义”,使“义”具有明显道德意味的应然,而非宽松的“合宜”“恰当”。孔子的义,也明显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正当,如在义利之间,他坚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得思义”,“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这都是把义当作“当为之事”或“道德上的标准”,而非考虑多方因素的“合宜”。道德上正当的、当为的一定是“合宜”的,但却不能反过来说“合宜”的必然是正当的、当为的。因此,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常常用“正义”。
这种对正义的坚守与担当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具有重大义利冲突的不同场景,我们所说的“正直”一德多指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对道义的坚守。比如,见得思义而不见利忘义,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巴结奉迎利益相关者,也不为了利益而出卖朋友,交友、处事均有原则而不是以私意为准。这种人是“靠谱”君子,而非奸佞小人。因此,孔夫子将益者三友的第一条就定为“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坚守义就可以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也是立人之节、成德之基。正直一德更高的体现就是面临义利严重冲突时的取舍,正直之人往往能临难不惊,见义勇为,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人我们已经往往已有“义士”“君子”“英雄”“圣贤”等不同层次的评价语去表达了。比如在抗击诸如地震、水灾等天灾时,很多人积极投身奉献、捐钱捐物,当别人遇到危难和困难时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不怕牺牲,当在战争中个人生命受到威胁时,还能够坚守道义,不叛变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去保守机密、维护道义,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义士、君子、英雄。我们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很少碰到这种极端境遇,但这些人的高尚品质还是令我们高山仰止。这种人在临变关键时期之所以有这样的高尚义举,就在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首先是一个坚守道义的正直之人。
同善良一样,正直的人从正面价值看,始终表现出对道义、原则的内心信念与行为坚守和践行,同时也包含不逾越、守规矩之意,同样如孟子所言:“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人如果能经常扩充自己的无穿逾之心,就会遵法度、守规矩,在原则问题上不可“枉道从利”,不可妥协,不可牺牲、抛弃道德原则,“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样,义就不可胜用,会成为一位坚守道义的正直的人,甚至在面临鱼和熊掌、生与义不可兼得时而舍生取义,这样的义士自然是正直之人的极至和楷模。
董仲舒认为,利以养体,义以养心,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我们每个人不仅要做一个有爱心的善良之人,也要做一个义以正我的正直之人,方显人性的光辉和人格的尊严。在待人接物中以义相交,坚守原则,这样不仅可以得人心,而且也是自己人生的安全阀。从积极义务的角度看,我们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世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做人,当:多行善事,积德积福;尽伦尽分,承担天下道义;对所有人公平对待,不偏不倚,“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忧国忧民,利济苍生,“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自觉增强义务意识,不断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无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刘向:《说苑·复恩》)中国古人十分欣赏这种“厚道”的品格,把它视为人的一种美德。一般来说,正直之人必是厚道之人,因为他们怀义相交,厚德待人。
三、论真诚
“真诚”一词表达个人私德,在现代中文语境中,似乎有更多的正面道德肯定的语感。“诚实”也有赞扬的意思,但似乎更为中性,我们不用“诚信”是因为“内诚于己,外信于人”,信是一个人的诚之心性和品质的外在发用,在现代社会虽然作为人际间的“信”德较之传统社会变得更加重要了,但当我们这里论及个人基本私德时,我们还是要首选“真诚”。
信与诚,在中国古代是互训的,含义是相同的。许慎《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信,诚也”。“诚则信也,信则诚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正是因为诚与信的相通与相互依存,才使得诚与信逐渐演化为一个统一的道德范畴——诚信之德。所谓诚,就是不自欺,诚实无妄,表里如一。所谓信,在古代最初是指在神前祈祷时,实事求是,不敢妄言,后来用在人际关系上,是指不说谎话骗人,能说必能行,内外相统一。所谓内诚于己,外信于人。诚是人内在的德性,信则是诚的外在表现。诚于中,必信于外。古人认为,诚是信的基础,信生于诚,无诚则无信,如诸葛亮曾说“不诚者失信”(《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阴察”),张载说“诚故信”(张载:《正蒙·天道》)。
“诚”字一般指向内心,指一种真实、诚恳的内心态度和内在品质,而“信”则涉及自己的外在言行,涉及与他人的关系。单纯的“诚”重心在“我”,是关心自己的道德水准,关心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单纯的“信”字则重心在人,是关心自己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关心他人因此将对自己采取何种态度。“信”字有“诚”字所没有的一种含义:这含义就是“信任”,“信任”就不是一己之诚,而是必须发生在至少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之中。在现代,比较强调信用的关系性和制度性,而不仅仅是个道德品质问题。
人有心性品质上的诚,必然发用体现为外在行为上的言行一致,这种言行一致可体现为以下方面:其一,对人言真实无伪,“无便曰无,有便曰有。若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便是不以实,不得谓之信”(陈淳:《北溪字义·忠信》)。对人不可作无根之谈,做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八年》)。其二,说话算数,不可“口惠而实不至”(《礼记·表记》)。要严格践约,不违背自己所许诺的诺言,“不食其言”,切不可“面诺背违”,“阳是阴非”。其三,常常“言顾行,行顾言”(《中庸》),言行一致。所以朱熹对信又作了这样的说明:“信是言行相顾之谓。”(《朱子语类》卷二十一)朱熹弟子陈淳曾说:“信有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有就事说,是做事之实。”(《北溪字义·忠信》)信不仅要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而且办事也诚实可靠。孔子说:“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便是对事而言。做事之诚即全神贯注,用尽心力,实际上就是“敬”,因此,我们经常诚敬连用,有真至精神是诚,常提起精神是敬。朱熹曾说:“凡人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
真诚是一个人私德的基本要素,能够真诚地对待自己,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心安理得,活得坦荡。只有自己真诚,才能感动人,吸引人,受人尊重,因为真诚就是一种道德力量。《中庸》认为,“不诚无物”“至诚不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思诚修诚是一个人修养之要务,“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文明要求人效法天道,回归真诚无妄,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唯有诚,才能悦亲有道,行善有道,才能有真仁真义,无诚必然是假仁假义。
由于真诚在人的私德和品质中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它和善良、正直一样都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色,因此,各民族文化都特别重视这一品德的教育和塑造。生活在中国文化环境里的很多人,在儿时可能都听老祖母或者自己的妈妈讲过“狼来了”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寄托着父母亲祖对子孙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的道德期待。《论语》记载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信被列为四教之一,可见其备受重视。老百姓也经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海岳尚可倾,一诺终不移”等,这些都是对诚信作为人的基本私德的重视。诚信为立身进德修业之本。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人不信实,诸事不成”(石成金:《传家宝》卷一“从事通”),“言非信则百事不满(成)”(《吕氏春秋·贵义》)。朱熹把忠诚、讲信用看作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如此,便失去了做人之道。他说:“人道惟在忠信,不诚无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朱子语类》卷二十一)陆九渊把诚信看作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人不讲诚信,就和动物无异。“人而不忠信,何以异于禽兽者乎?”(《陆九渊集·主忠信》)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现代经济是契约经济,现代生活也变得日趋复杂化,这一切都特别需要社会诚信与信任,试想现在的网络经济如果没有诚信,如何能够存在与运作?因此,现代社会不仅需要诚信之德,而且需要通过制度和技术建立诚信体系和机制,但这一切背后还不都是人在做吗?正如前面所说,信是以诚为基础的,因此,培育人们的真诚美德不但是基础,而且是永恒的主题。
四、论儒雅
“儒雅”表达私德,与“文雅”类似。“文雅”因文而雅,“腹有诗书气自华”,但较之“儒雅”似乎多了些文化的智力要素之感,而“儒雅”约定俗成,使人联想这种雅是由儒家这个强调道德为本的学派所塑造的一种人格特质,不仅强调了德性的内涵,而且具有中国特色。因此,用“儒雅”比“文雅”更准确些。其实文化与道德本就是一种属关系,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就是道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二者的表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具有儒雅品质与气质的人是什么样的?这表现在他们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待人接物都体现出有礼、委婉、文雅从而凝结其身形成一种气质,并给人留下一种综合的文明印象和美感。由于他们胸有文墨,因此,说出来的话总是有文采、有趣味,文明礼貌、恭敬待人。他们的举止即态势语言总显得很有修养,即坐得正、站得直、行如风,行为有矩守礼,有自我控制感,不会让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麻烦和不适。他们的穿着打扮总是那么得体,符合文化时尚,体现对别人的尊重,注意自我形象,善于根据不同季节和时间场合,穿出自己的文明与风格来,即使是小的配饰,也别具匠心。正如孔子所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论语·尧曰》)穿衣并不是一味追求奢侈豪华,而是“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中庸》),崇尚朴素与低调。他们待人接物总是奉行恭敬、辞让的礼的精神,尊人卑己,克尽伦分,客气有礼。甚至,他们还有非常优雅的个人爱好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琴棋书画、品茗插花等,这样的人显然是具有儒雅之品性和气质的雅人与雅士而非俗众。一位儒雅有修养的人可能既有外在风度又有内在涵养,德性就是这种内外的统一。
这是商景兰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和思考,是女性觉醒的可贵声音。以“才”为归结点,商景兰把现世幸福的失落,在“立言”以求不朽中得到了超越,从而将文学活动作为生命苦难的感性慰藉,升华到扬名后世的理性追求。商景兰后半生的生命探索与价值追寻,至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显然,这种儒雅品质、气质的来源自然是全部文明与“礼”德经过主体学习修养而在其身上的凝结。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仁、义)是也”(《孟子·离娄上》)。《礼记》说:“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礼记·冠义》)在中国古代,礼的要求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荀子所说:“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荀子·修身》)。“有礼者敬人”,而“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礼是教导人在言行举止上有合宜的行动,达于时时事事皆中节的中庸境界。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全部文化与道德修养的外在体现,对于人际来说,它是对别人的尊重与谦让,因此,显然是一种文明与教养。
现代社会有很多反文化的现象,以说话粗鲁、行为无矩为时尚风俗。穿衣打扮,追求露、透、少,硬是要把一个好衣服挖个洞才显得新潮和酷,有的是内衣外穿,有些人穿衣服竟连隐私线都暴露无遗,有的人在公开场合和自媒体平台穿的之少被人批评为几乎到了软色情的程度。在人际交往中,有的人缺乏基本的恭敬和辞让精神,对长上、对别人无论言谈举止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比如,晚辈称自己父母为“老爷子”“老妈”;在公共生活中不是礼让而是争抢;在大众生活与文化中人们尽力在满足和发泄自己感官性的欲望,如暴饮暴食、追求外在刺激,而很少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内在修养。这诸种现象都与我们中国文化的礼仪之邦和君子之道的价值取向相反,难道这就是现代化吗?固然,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象并不违法,按照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现代社会似乎人们只要不违法,公民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但是,作为一名文化与伦理学工作者,如果对这种现代文化的粗俗化不进行反思批判的话,公序良俗将日趋坠落,儒雅之士将越来越少,显然有损于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也无助于中华民族整体道德素质的提升。因此,在当前培育个人私德的过程中,还是应该弘扬传承我们的礼文化,努力培养儒雅之士。
儒雅之士的现代培育,首先要求我们在观念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分清什么是野蛮与文明、文化与反文化、文雅与粗俗、自由与教养、个性与良俗公序,如果不对这些在观念上加以厘清,就会丧失培育儒雅守礼之士的良好社会环境,就会潜移默化地消解道德和文明。在现代社会中这只能靠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而不能强制。当然,这其中也有质和量的规定性,比如在公共场合穿得少、露、透可能被看作是失德或者不雅,但如果是裸体,即便在西方也会被警察抓起来。有的人以行为粗俗为美,有的人以奇异个性为美,这些都体现出对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的反动。我们并不是要一味地复古,而是要增强文化与文明意识,以个体的儒雅品德彰显文明、文化和礼仪之邦的风范。
五、论温和
温和,是儒家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在主体人格身上的体现,一个人温文尔雅到极致可能就具有某些儒者气象了。
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人生与道德智慧的价值目标,除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外,重点在于追求人和。倡导“和为贵”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大特色和精华。文化培育人格,长期生活浸润在这种文化环境里的人,如果学习、认同并践行了这种和谐价值观,那么,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形成一种温和而不暴戾的性格。
那么,什么是温和之德呢?笔者曾撰有拙文《论和德》,指出:“人的道德品质是一种经常的、持久的行为方式,是主体身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境界和精神气象,以此而思考公民之和德,笔者认为,它主要体现为:公民主体自我修养的中庸温和;公民在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亲和;公民在组织与团体生活中的团结求和;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守礼达和。中庸、友善、团结、守礼是和德在公民行为方式上的体现,也可作为社会建设和德的主要行为准则和善恶评价标准;而温和、亲和、求和、达和就成为公民和德的一种修养境界、性格特点。”[9]中庸温和是性格,而友善亲和、团结求和、守礼达和则是这种中庸温和性格在人际、团体、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发用和体现。当我们在分析个人私德的时候,应着力分析其主体心性或者德性的内涵。
温和之德的根本就是中庸的思维方法、行事风格和人生境界。“中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之道在孔子那里是指行为的恰到好处,这是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也是实行道德的最好办法。据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中就是适度、适宜、恰当,中就是合乎礼的无过无不及,是价值标准。“庸”为对“中”的固守,庸有“用”和“常”两种意思,因此,中庸也可解释为“用中”。中庸作为人的一种德性,在任何时间、地点、场合、境遇都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得体,处事得当,也就是“中行”,“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荀子·儒效》)。具有这种中行之德的君子,行事不偏激,这种用中的精神,本质上是对礼义道德的奉行,“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礼》曰:‘心广体胖’,心既宏大则自然舒而乐也”(张载:《经学理窟·气质》)。有了这种修养,必然在性格上就会具有一种圆融温和的儒者气象。他们遇事冷静,待人温和,能容乃大,心态和平,不固执己见,兼容并蓄,彼此唱和,美人之美。“和”是生命之本,“和”需要清除贪念,不贪常清静,万物自和谐,温和之人较少因人际关系而产生如气愤、苦恼、抑郁等不愉快的情绪,即使偶尔有之也会因为自己的德性而能克服之。中和的实质是“发乎情而下乎礼义”,“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和或者温和,既是个人私德有修养的表现,也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必然使人能达到“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的良好效果,实现“仁者寿”的健康幸福人生。
六、论豁达
豁达,显然是一种智慧和觉解渗透在人身上的气质凝结,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度的人生与道德智慧和高远的人生觉解,是很难达至真正的豁达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要形成豁达的私德和性格,肯定离不开道德智慧和人生智慧。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它告诉我们如何过一种善和幸福的生活。如何正确地行动?要做什么样的人?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要具有何种美德?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人生实践、价值观选择,也离不开人伦关系的处理和自己的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我们认为“道德智慧”的内涵或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人生觉解、价值澄明、知世明伦、修身立命。人生大道的觉解,可以从根本上决定我们人生实践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一个追求道德智慧的人,总是要能够分清是非善恶,才能称得上有道德智慧,这就是价值澄明。知世故、明人伦是道德智慧的又一重要方面。所谓“人世”也就是人与人组成的现实社会的人伦关系,道德智慧无非是一种审时度势、善处人际关系的明智。知世故要求人们能够审时度势,知先后、掂轻重、择缓急,体现为实践过程中的明智恰当。“识时势”就是通常所说的“审时度势”,也即道德主体在行道过程中对于“道”之行与不行的现实性及可行性的客观条件的判断。所谓“明人伦”就是要求我们了解自己与他人、环境的关系,善识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具有自知之明,正确地认识自己,被儒家看作比“使人知己”“知他人”更为高明的德性,儒家将之视作君子的基本德性之一。这一见解与儒家强调的“反求诸己”思想是一致的。知己是道德智慧的认识活动,而修身则是道德智慧的实践活动。要改变世界先改变自己,心外无物,反求诸己,这样才能遇事想得开,放得下,从而也能真正地素位而行,安身立命。
以上所说的道德智慧是一个人具备了豁达的认识与智慧前提,真正的大智慧必然是道德的觉悟、人生的大觉解。凡是豁达的人不仅是认识上清楚,关键还在于态度和行为上能够真正放得下。在面临义利、人际、群己冲突时能够放弃自我利益,在顺逆、荣辱、名利、进退甚至生死考验面前也能从容对待,那才是一个真正豁达的人。比如,孔夫子就其个人一生的命运来看并不是很顺,为了传道可谓是颠沛流离,困于陈蔡之间,但他仍能弦歌不断,这才是真正的豁达。颜渊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孔颜之乐”不仅是儒家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二圣豁达人格的再现。
我们生活在世俗社会的常人只要学习儒家的道德智慧和人生智慧,就可能成为一个豁达的人,不必像庄子这位大隐士那样“齐彼是”“齐是非”“齐善恶”,因为他在山中独自隐居,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脱离了世俗生活,自然是非善恶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可是对于我们生活在世俗世界里的人来说,豁达并不是不分善恶是非,一味做和事佬,否则就是前面所说的“乡愿”之人。但庄子的思维方法对我们无疑还是有一些启迪和参考价值的。一个人要豁达,想得开、放得下,就不能太较真,大是大非有原则,小是小非则要“难得糊涂”。庄子追求精神的自由和超脱的精神境界对于我们想要成为豁达的人也是有启迪价值的。要获得这种精神自由,人就要从追逐名利和恐惧死亡的双重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达到“忘物我”“齐生死”的精神境界。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人们要从思想上放下并看轻这种外在的功名利禄,获得精神的自由,自然无为,无求无待。“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佛教也教人参透生死、看破红尘、放下一切,这种基于宗教觉解的豁达,虽然不是常人都能做到的,但却是我们培育自己豁达品性时的一种思想资源。
一个豁达的人不会那么斤斤计较,不会那样小家子气,会对别人很包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而善处人际关系;会有大觉悟、高境界,既利于人,又利于自己人格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显然这是人的一种个人美德,我们每个人都应在人生长河中努力培育养成。
结语
上面分别论述了个体私德的六种基本德性,从总体上看,就是古代儒家所说的“五常”加“和”德,即仁、义、礼、智、信、和,也许这样讲更容易认知与记忆。之所以给出了不同的排序,是有思考逻辑的,主要立足于这几种德性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仁与义居于首、次,这是符合古今道德生活的内在规律的。《易传》有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常“仁义道德”连用,说明仁义是全部道德的核心与灵魂,这两种道德凝结在个人身上主要体现为“善良”与“正直”,而这也是一个人私德中最重要的品质。之所以把“真诚”排在第三位,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信”在现代生活中其重要性较之古代社会更重要了,要建立现代诚信社会,也需要不断加强个人私德方面之“真诚”品质的培育。
如果对上述六种基本私德再进行另一角度分析的话,可以说前三德具有更多的人际间的内投射性,而后三者则较多地呈现为一种外投射性。这里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善良”“正直”还是“真诚”,都是主体做出了某种有利于他人的行为,而别人对其评价为具有这种品质,也正是上述钱穆先生所说的德性的概念,即出于心性发自于外又回到心性。而“儒雅”“温和”“豁达”这一组德性则大多呈现为主体对外在的文化与文明成果经过主体的积极学习与掌握,对人生的认识与觉解而在自己身上形成的一种内在素质、行为风格和人生境界,因此,我们觉得它具有相对于前三个德性的内投射性(由内而外),而它的特点称为外投射性(由外而内),这样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这几种德性的基本性与普遍性及其逻辑联系。
如果说“真诚”是人的内在心性之德,而“儒雅”则是人的外在行为文明。传统中国,儒家文化以和谐为价值观,以追求和谐有秩序的社会为理想,文化塑造人格,这种文化长期浸润,必然在主体身上形成“温和”之个人美德。把“豁达”放在最后,是因为这种德性是智德在人身上的凝结,智慧或者道德能力,是对实质德性的一种支持性精神资源,虽然在道德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智力智商只有投射运用到道德上,才能够成德,如果仅仅为智,那也可能成为算计、心计、权谋、狡诈等。当然它如果与道德结合,就成为一种“道德智慧”,从而成为德性,如果再上升为“人生觉解”,那就更是一种大智慧、大境界了,但较之前五者而言,就德性本身来说它毕竟不是那么纯粹,但又是道德所不能离开的,因此,将之放在最后。各大宗教都是强调德智双修,但必须是智与善、与德的结合,否则便是奸智,不仅不能为善,而且会助恶。
本文将这几个德目视作个人私德的基本德性,暗含了传统“五常”之德与和谐的精神,“常”者,恒常、普遍之意,和谐则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与理想,这正说明,人类道德生活是有其古今不变、延续传承的基本价值的,另外,也证明古人“五常”与和谐的概括是精准的,是具有跨越时代的精神价值的。
——柏拉图《美诺》中的德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