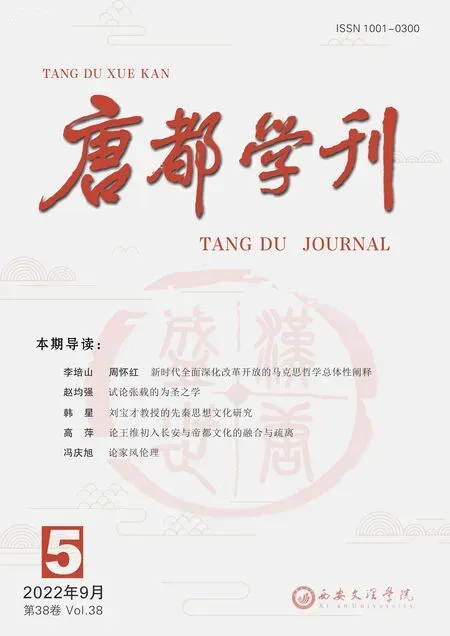老子观道思想中的有无之辩
——以《老子》第一章为中心的考察
冀志强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先秦儒道两家都对那种与感性欲望相联系的视觉抱有一种强烈的戒备。孔子从“礼”的角度对人的视觉提出了限制,而老庄则从“道”的角度抵制身体性的视觉。在老子那里,身体性的“视”作为一种单纯感官层面的视觉行为,是达到“道”的障碍;而“观”则是达到“道”的重要方式。当然,老子所说的“观”并不是“视”,不是通常的经验直观,而是以“玄鉴”的方式来与“道”发生关系。所以,“观”已经不是一种对象性的观看行为了。在老子讨论的观道理论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有与无的关系,这对我们理解老子思想非常重要,本文尝试结合《老子》第一章对此做一探讨。
一、“道”的言说
老子的观道理论首先且主要是在通行本《老子》第一章中得到体现。《老子》开篇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王弼本第一章,以下只注章目或未提版本的均指王弼本。我们通常认为,这是关于道的言说问题,并且对于道的可说与不可说已成聚讼纷纭的公案。由于先秦时期作为动词的“道”通常有“引导”或“取道”之意,所以我们先讨论把“可道”之“道”解释为“言说”的合理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考察“道”在老子那个时代或其前时代有无可释为“言说”的用法。在先秦文献中看到有这样的使用,如《诗经·鄘风·墙有茨》中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1]这里的“道”显然即为“言说”之义。张祥龙在《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中考察了“道”在早期作为“言说”之义的用法[2]。其中《尚书》中有两处:其一,《周书·康诰》中说:“既道及厥辜,时乃不可杀。”[3]166其二,《周书·顾命》中说:“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3]235这些内容应该属于较早的文献,为《老子》此处的“道”释为“言说”提供了依据。
《老子》第一章讲“道”,主要是通过讨论“名”的问题而展开,因“名”是言说某物的前提条件。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开篇引用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中的单个词语都是对事物的命名,而句子则是由这样的命名组成的。”[4]这是现代语言哲学的重要观点。由此视角看,《老子》第一章所涉及的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且将“名”与对“道”的言说联系起来。尽管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道”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但开头显然将“名”放在与“道”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将“道可道”中“可道”之“道”释为“言说”,才能与老子本章讨论的问题相契合。如此,我们就可以考察《老子》开头所涉及的“道”之言说问题。对此,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道是不可说的。王弼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5]1至今人们也大多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道是可以说的。远如司马光,近有朱谦之、詹剑锋等人持此观点。那么,老子的“道”到底应该是可说的还是不可说的呢?我们先从通行的王弼本与帛书本的比较来分析。
王弼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帛书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当然,我们这里的讨论有一个前提,就是认为帛书本比通行的王弼本更为接近《老子》一书的原貌。这句话在王弼本中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假设句,但在帛书本因多了“也”字,则明显是判断句,这样比王弼本的意思更为明朗(2)刘笑敢先生也是根据“也”字认为帛书本应该是古本,参见《老子古今》。。司马光认为“常道”为常人之道,这种理解显然不妥,因“常道”在帛书本中是“恒道”。《说文》释“恒”为“常”,《周易·序卦》释“恒”为“久也”。这样就可将“恒”释为“常久”,“恒道”即为常久之道,所以,“恒道”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道”。这样,从帛书本中更易看出,“道,可道也”中的第一个“道”就是通常的形下之“道”了,河上公称其为“经术政教之道”。这样,就可将“道可道,非常道”理解为,可以言说的道不是那种恒久不灭的道。反之,“恒道”就是不可说的了。同样,“名可名,非常名”也是否定了俗常的“名”。也就是说,被人称颂的“名”也不是恒久的名。显然,老子是从反面来阐发“道”与“名”的,因“道”是不可说的。对于不可说之物,维特根斯坦说:“关于何者我们无法言说,于此我们必须保持沉默。”[6]157海德格尔则说:“对沉默保持沉默。”[7]143按照这种哲学逻辑,如果道完全不可说的话,那么老子的五千言则完全是多余的。但问题是老子的“大道”也是以“道”为名的,而命名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言说。尽管“道”是“可名”的,但这并不是说它本身是“可道”的。如果要通达于“道”,仍需借助于这个“名”。我们的确需要在无法言说之处保持沉默,但言说也通常是我们达到这种无法言说之物的必要途径。维特根斯坦并未堵死达至不可说之物的道路,他说:“哲学通过清晰地显示可说的东西来意味不可说的东西”[6]53。老子哲学也并没有违反这种逻辑。维特根斯坦说的“显示”(darstellen/display)在老子这里则体现为“观”。这样的话,关于“道”的言说就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道”的现象,它是可以言说的;其二是“道”的本身,它是不可言说的。老子总是通过对道的现象的言说让我们领会“道”的本身,“观”则是老子沟通这二者的核心方式。
二、“名”的有无
因为命名对于言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道”的可说与不可说问题就与后面讨论“名”的阐述有了逻辑的承接关系。这样再来分析后面论“名”的两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其中“天地之始”与“万物之母”说的当然就是“道”。这里历来有两种断句方式,但如果仔细分析,不管怎样断句,都不能否定道的可命名性。如果“名”与前读,“有名”则当然是说“道”有其有名的一面;如果“名”与后读,那么“无”与“有”就都成了对于“道”的命名。为了澄清此问题,可参照《老子》其他章节中那些与“道”直接相关的谈“名”之句。这些章句主要有:(1)“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第十四章)。(2)“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第十四章)。(3)“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第二十一章)。(4)“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5)“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第三十二章)。(6)“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三十二章)。(7)“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第三十四章)。(8)“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第三十七章)。(9)“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第四十一章)。在这些章句中,最为明确地表明“道”与“名”之间关系的就是第五句中“道常无名”与第九句中“道隐无名”。其中“道常无名”在帛书甲乙本中都是“道恒无名”,所以这两句明确地说明了“道”的本身是没有名称的,而上列第二句中的“不可名”就应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所以老子说“吾不知其名”。
但其中又有“可名”“名曰”“其名”之语,为何?我们以第四句来解释。说“道”可名,并因而有名,是因为这个“名”是勉强命名的。《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8]“名”是人初生时父母起的,“字”是行冠礼时宾客赠的。古代在称呼他人时,多以“字”称,以表示对“名”的尊重。其实,抛开礼仪的问题,“名”与“字”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都是拥有名与字者之外的人赋予的。同样,“道”本身也并无“名”与“字”,而是人所赋予的。不仅“大”是勉强的命名,“夷”“希”“微”等都是这样的“强名”。所以第一章说:“名可名,非常名”,即可名之“名”是“非常名”,这也是由于道“常无名”。
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道”这个“名”作为能指与其所指(道本身)的关系是任意的,“道”并不是其所指的本然名称,这个名只是我们施加上去的。尽管这样,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必然需要有一个命名,不管它是一个什么名字。所以,海德格尔说:“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9]如果没有语言,物将始终无法“是其所是”。他还引用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3)所引诗句德文原文为“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这里的“sei”是“Sein”的现在时第一虚拟式形式。赫慈(Peter D. Hertz)对此的英译为“Where word breaks off no thing may be.”见: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60.[7]150这个“存在”即是“是”。无物可存在,就是说无物能够是其所是。没有语言,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都将堕入无其所是的黑暗之中。也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说:人是一种言说的存在[10]82。所以,赋予对象以“名”,是我们与事物打交道的基本方式。《老子》中说:“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这句话也可以如是理解:我们是通过我们所赋予“道”的这个“名”来领会它之为“众甫”的。这样,在人的言说中,“道”当然也就“有名”了。
我们还可以通过佛家的相关讨论更为深入地理解这种“名”的实质。用佛家的话说,我们给事物所命的“名”其实是一种“假名”。青原惟信禅师曾说到关于山水的“三般见解”,实际上也就是对“名”的三种态度。他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11]1135这对山水的三种态度,实质上也是山水对他的三种存在方式。在第一个阶段,山与水呈现出不同的表象,因而有了不同的名,而这不同的名,显示出的是山与水存在着质的差别,所以山是山,水是水。在第二个阶段,山与水的区别得到了消解,但却也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因为它们本身都是佛性的现象。此名当然即是假名。大珠慧海禅师说:“迷人不知,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遂唤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11]157青原此言即可如是理解。他在第二阶段虽然消解了山水的区别,但却还有这样一种对法身般若的执著。到了第三个阶段,他观到了山水真正的存在,这个“是”已经不是以前的“是”了。这是自在的“是”,是本真的“是”,这就是再度减去将法身、般若加于山水的执著。这时候,“山”“水”之名当然亦是假名,即非常名之“名”。我们将“山”这个名施加于我们称之为“山”的这种事物,通常也就意味着我们给它施加了崇高、坚硬等意义,但从佛家看来,这些都是不真的。当然,对这种“不真”通常也是以语言来领会的。
事物的存在无法离开命名与语言的言说。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命名是一种召唤[7]12。命名,使万物得以成为万物。在老子这里,命名同样也是这样的一种召唤。这种召唤将“道”带入我们的境域,使其达到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说它不在场,因为道不是一个存在者,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但通过对它的命名而进入我们的境域当中。如果没有这种命名,道对于我们就永远是一种黑洞般的陌生。当然,命名只是一个条件,除了命名,还需要有其他的通达方式,在老子这里就是“观”。
三、“欲”的有无
我们在讨论了“无名”与“有名”的问题之后,接着就是关于有无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老子》第一章接着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里历来也有两种断句方式:一种是在“欲”前停顿,一种是在“欲”后停顿。如果我们可以参考帛书本,显然就要在“欲”后断开:
甲本:〔故〕垣无欲也,以观其眇(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徼)。
乙本: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又(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徼)。
帛书甲乙本在“欲”后都有一“也”字。按照通常的读法,停顿需在“也”字之后,那么“无欲”之间则当然是没有句读的。况且第三十四章中明确有“常无欲”,此处文字在帛书本中为“则恒无欲也,可名为小。”故“无欲”之说,在《老子》中自然无甚问题:(1)“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2)“常无欲,可名于小”(第三十四章);(3)“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第三十七章);(4)“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然而,“有欲”却令人费解,因为“欲”在《老子》中基本上是被否定的,而第一章这里明显又不是对其进行否定。并且,帛书本中第二十二与三十一章都有:“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4)王弼本第二十四章、三十一章,其相应的文字却是“有道者”。这里明显也是对“有欲者”的肯定。对于这种矛盾,高明先生断然认为这二章中的“欲”乃为“裕”之假借[12]。但如果我们将帛书甲乙本对照的话,“欲”字多达30处,除此二章外,其余明显均非“裕”之假借。如说此为假借,而为何第一章中的“有欲”之“欲”又不为假借?所以假借之说实难成立。其实,《老子》中的“有欲”与“无欲”在意义上也并非完全牴牾。帛书本第五十七章与六十四章都有“欲不欲”之语;而在王弼本第五十七章中却是“无欲”,第六十四章则没有变化。所以,如果我们非要说有一种可以肯定的“有欲”,那么这种“欲”就应该是那种“不欲之欲”。如果我们把“有欲”理解成“不欲之欲”,那么其中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
如果说帛书《老子》肯定了“有欲”,我们将其理解为“不欲之欲”,那么它与“无欲”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把《老子》否定的“欲”理解为日常生活的各种欲望,那么这种“不欲之欲”则是对否定这种欲望的欲望,而“无欲”则不仅是对日常生活各种欲望的消解,同时也是对否定生活中各种欲望之欲望的消解。试图否定某种欲望,这本身也是一种欲望,无欲的极致就是连否定的意图也不在心中出现。也许这种诠释染上了浓重的佛学色彩,但恐怕也只有这样,才能消解《老子》某些概念之间的冲突。况且,老子也确实有某种类似佛学的观念,这在关于“妙”与“徼”的阐述中有所体现。
对于《老子》第一章中所说“两者同出而异名”中的“两者”所指为何,历来也有不同的见解。如果将前文解释为“无名”“有名”与“无欲”“有欲”,那么这里的“两者”就不能单指前两者或单指后两者。所谓“两者”,应该指“妙”与“徼”,二者就是对于“道”的命名,如同以“夷”“希”“微”命名道的几种状态一样。“妙”,帛书甲本作“眇”,悠远之意;“徼”,帛书甲乙本均作“曒”,明朗之意。王弼注:“妙者,微之极也。”[5]1朱谦之说:“徼者,光明之谓。”[13]那么,观“妙”与观“徼”就是观道的两种状态。“妙”与“徼”都是《老子》中所说的“玄”,即“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则内在地包含了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妙”是“道”的代名词,“众妙”则是说“道”的诸多特征。所以,达到“道”的境界也就是达到“妙”的境界,而“玄之又玄”则是达到“妙”的途径。何谓“玄之又玄”?可将此理解为“玄”的层次,即“玄”有两层:一是玄,二是(玄之)又玄。“玄”是上文所说的“有名”与“有欲”,这里的“名”是“假名”,“欲”是“不欲之欲”;而“(玄之)又玄”则是去假名之“无名”,去“不欲之欲”之“无欲”。这也就是一个从“观其徼”到“观其妙”的过程。
四、观“有”之“无”
在结合帛书本考察《老子》第一章中的若干问题后,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通行本中老子关于观道的思想。以上的讨论在有些方面实际上是要有意地化解帛书本《老子》中某些似有抵牾的地方,而这些问题在王弼本中就不太明显,因为帛书本导致问题的“有欲者”在通行本中却成了“有道者”。这样,第一章中的“有欲”也就可以通过句读分开。尽管王弼长于有无之论,但还是以“无名”“有名”与“无欲”“有欲”来理解《老子》第一章的[5]1。如果我们有意地要使本章突出“有”“无”的问题,就可以这样断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本)我们前面说过,本章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讲“道”的“名”。改变句读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如是解读:“无”与“有”都是对“道”的命名,而章句中的“两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此二者。“无”与“有”是对“道”的“命名”,但二者都不是其“常名”。我们对道以“无”命名,是要以此“观其妙”;对道以“有”命名,是要以此“观其徼”。“无”与“有”都同出于我们对道的命名,出于我们要对道本身的通达。所以,观“道”的“妙”与“徼”,其实也就是观“道”的“无”与“有”。
在老子“观”的方式中,我们直接与“有”的“无”相遇,因为“无”不是“思”的对象,而“观”也不是一种对象性的行为,它是一种存在境域的敞开。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是者是而无却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对“无”提出“它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老子的“有”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是者”(“存在者”),在老子这里,“无”同样是不能言说的。海德格尔说:“谈论无的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说无,就通过这种说的行为将无变为某物。他有所说的说就与他所意指的东西相反,结果自相矛盾。但是自相矛盾的说违反了说的基本规则,违背了逻辑。”[10]24所以道禅哲学就强调,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进行言说之后,必须还要达到对言说本身的否定。王弼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14]在王弼看来,老庄都没有在言“有”之后彻底地摆脱“有”而达到“无”。他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由于他对老庄存在着误解,而且也由于他与老庄对有无关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在《老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于生成的逻辑,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无”是“道”最为根本的方面,是对“道”作为天地之始的命名,观道的根本也就是对“无”的领悟。从层次的逻辑说,观道是从“有”到“无”的过程。“玄之又玄”,就是从“徼”到“妙”,也就是从“有”到“无”。《老子》中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第十六章)万物芸芸而作,这就是“有”;但万物的“作”,最终也归于其“根”,这个“根”就是“无”。这个“归”不在于时间上的终结,而在于逻辑上的还原。所以这个“观其复”,也就是从万物的“有”观到万物之根的“无”,这样也就达到了对于“道”的观照。“观物”的目的是要达到“道”,“复”即“复命”即“归根”,也即达到恒久不灭的道。
在老子这里,对“有”的观是一种经验的意识;而对“无”的观则是观“有”时的一种体验,这样的观也是一种“反观”。老子提出有无双观,是因为道统有无。要想体认大道,必须要从“无”与“有”两个方面来把握。如此,才能认识大道之全。既不是单单观“无”,也不是单单观“有”,统而“观”之,方可得道。这个“观”也就是老子说的“玄览”。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达到有无双观,既观“有”又观“无”呢?这应该就是,在观有的时候,将“有”“无化”,也就是消解对于“有”的对象性意识(5)本文所用“无化”这个表达借鉴于彭富春《无之无化》,这种“无化”与老子论有无关系的观点相通。。我们通常将“有”视为存在者,但它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存在者,是由于它处于这样的存在境域中。有了这样的存在,它才成为这样的存在者,但存在本身却是一种“无”。如果我们“观”到了这种存在的境域,这就是“观”到了“无”。其实,“无”就是一个“无化”的过程,“无化”的实现与完成就达到了“道”。正如彭富春所言:“无之无化,就是世界之整体的敞开。”[15]道,就是这个敞开的世界之整体。老子的有无双观有隐与显两个层面的意思。“无”是隐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直接经验到“无”,而只能借助于观“有”。但如果执著于“有”,则始终不能把握到“无”;必须使这个“有”归于“无”,即“有”的“无化”就是“观其复”。无与有还包含了一与多的意思。道是一,万物是多。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道为万物根,根为一。这样,有无双观又体现为既观多,又观一。观多以达一,观一以统多。有无双观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看,而是以无欲作为条件的,所以它不是功利的观,而是以道为旨归的观。
老子观道的前提是心的纯化,这也是实现观道所具备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致虚极,守静笃”,即达到“虚静”;而达到虚静,就要祛除所有的杂念。只要将心上其他事物的遮蔽除去,即可观“道”。老子主张的“观”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因为“道”的本身不是经验的现象,“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四十一章)。“为道”所需要的“虚静”也就是对经验知识的搁置与减损。这样,“观”就是不带有任何特殊立场的视角,这就是“道”的视角。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说:“这就是说,一个人应当使自己摆脱关于事物的所有预想,所有知识以及所有的偏见。这就回归到本源。”[16]这种不带有任何观点的“观”就是“道”的“观”。“道”,就是事物的本来样子。在“观”的方式中,“道”作为世界的整体向我们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