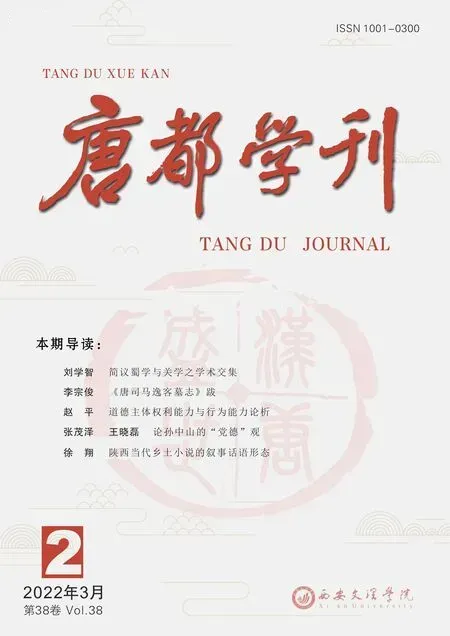论孙中山的“党德”观
张茂泽,王晓磊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安 710127)
王晓磊,男,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史专业硕士生,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儒学史研究。
中国近代政党是西方民主政治传入中国并中国化的产物,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传统对中国近代政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德”便是近代中西政治文化融合、会通的历史产物。我国近代“党德”的首倡者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党建思想中,“党德”观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关于孙中山“党德”观的相关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孙中山1912—1913年间有关“党德”的言论,尚未能总体考察孙中山在不同革命时期“党德观”的思想内容及其历史变化;学者们注重阐述其政治伦理意义,而从党建实践角度总结和提炼孙中山立党的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即从党建角度,将孙中山在兴中会(1)孙中山曾以“革命党”称呼“兴中会”,可见他早年理解的“党”,还有政治派别或政治团体的含义。因此,本文将兴中会时期也纳入孙中山“党德”观的考察范围。、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各个时期的政党观念联系起来,对其“党德”观进行总体研究,概括其思想内容、理论特点和历史意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在这一历史交汇处探讨孙中山党建思想中的“党德”观,对于我们总结近代党建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一、孙中山“党德”观的革命实践基础
政党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基础,他的政党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党德”观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国建立前的革命会党时期,即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至1912年孙中山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这段时期;第二阶段,民国初年,即1912—1913年的政党时期;第三阶段,1914—1925年的革命政党时期,即“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继续探索建设近代政党,先后组建、改组了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从孙中山整个政党活动历程看,其所领导的政党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组织原则,体现出不同的政党组织特点,他的“党德”观的内容也因之略有不同。
孙中山在海外学习、生活多年,熟悉西方政党活动。他早期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支持改组国民党,都重视以民主原则进行党的建设。如《兴中会章程》《中国同盟会总章》《国民党党纲》等都强调了自由、民主、平等原则,规定了其成员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但因集中统一领导的力度不够,对成员缺乏必要的组织和纪律约束,使得早期革命会党显得组织松散、成员言行比较随意。孙中山早期领导革命党,主要从事海外筹饷,联络会党、绿林、新军或由革命党人自身发动起义。由于革命活动需要秘密进行,起义力量主要依赖会党[1],因此受会党组织方式的影响,孙中山早期党建思想尚不成熟。在早期政党活动中,孙中山主要依靠其个人的领导魅力,以及他对成员道德品质的要求,以保障革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武昌起义爆发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2],但因中国缺乏政党政治传统,反有朋党文化遗风,时人批评当时政党,“既无政治上、道德上的结合,其所谓政党,非真如欧美各国之政党以福国利民为主旨者。盖不过一二野心家,借政党名目,以为争权夺利之具也。”[3]洎民国成立,为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同盟会于1912年3月改组为公开政党,并于同年8月与其他四党合并为国民党。由于革命斗争不彻底,革命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依旧存在。这种矛盾在民国政制下,演化为以国民党为主的制袁方和以统一党为主的拥袁方的斗争,各党以“蹙灭他党为惟一之能事,狠鸷卑劣之手段无所不至”[4]。这便是孙中山明确提出“党德”问题的历史背景。
革命活动是孙中山“党德”观的政治基础。他反思革命屡次失败的原因,尤其是革命组织因素,可谓孙中山“党德”观产生的直接动因;而他对近代中国国家形式的思考和向往,也是引领其“党德”观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民国建立后,革命党与袁世凯的斗争逐步激化,及至“宋案”发生,“二次革命”失败,民国初年的民权建设基本流产,促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长期的革命实践经历,使他认识到仅仅照抄西方政治理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孙中山开始从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寻求近代国家建设的资源。
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对以后的革命对象、革命的艰巨性,也逐步产生了更清晰的认识,他的立党思想也随之发生转变。在筹组新党时,孙中山明确意识到,他应该组建一个以他个人为绝对权威,有严密组织、富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这样的政党还可以作为“未来国家之雏形”[5]184,为建立近代新国家探索组织经验,以“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权威转换和政治造型问题”[6]。为此,孙中山于1914年另组了中华革命党,并于1919年将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党建思想上,孙中山这一转变标志着其民主革命指导原则从“民主”到“民本”的转换。转换的结果,是孙中山“以党建国”思想的产生,“党国”体制的出现。从孙中山建党思想的演变角度看,这一转换也可谓是孙中山儒家“先知先觉”德治思想的反映,以及过去会党式领导风格的遗存。这时,传统儒家德治色彩十分浓郁,贤能政治的人才观念十分明显,而“党德”正是这一近代德治追求和党国体制的思想基础,标志着孙中山“党德”观趋于成熟。
二、孙中山“党德”观的主要思想内容
从孙中山革命历程和政党建设过程看,可将其“党德”观概括为革命党道德、政党道德、革命政党道德三方面的思想内容。
(一)革命党道德
在革命党时期,孙中山的“党德”观还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为了解决革命党的组织结合问题,确立革命目标,其“党德”观的主要思想内容有二:(1)确立革命目标;(2)对会员道德品质提出明确要求。这时的党德,党组织意义小,革命道德意义大,可以视为革命者都应具备的一种革命道德。兴中会与同盟会都贯彻了自由、平等的组织原则,但这与残酷的革命斗争并不适应。既然革命组织涣散无力,就需要从个人思想道德入手,加强道德建设,以提高革命组织的行动力。为此,孙中山除依靠他个人的强力领导外,还在革命活动中采用类似于会党的盟誓,作为“团结内部和约束成员去完成某项事业的纽带”[7]。
这一时期孙中山“党德”观的主要内容有三:第一,用入会誓词统一会员思想和行动。在吸纳会员时,孙中山要求会员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8]20,用组织任务和目标的心理认同,加强会员的团结。第二,要求会员“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8]22,且超越个人利害得失,“不以名位为吾党进退之征”[9]。第三,以“天下为公”作为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提出革命党人要“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志,方为满志”[8]22,时刻以国家隆治、民众福祉的远大目标自励。
(二)政党道德
政党时期,是孙中山“党德”观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为了解决民国初年的党争问题,孙中山提出了“党德”概念,明确了“党德”的规范内容。在他看来,党德表现为“立党之德”和“党员之德”两个层次。“立党之德”是政党组织的根本道德原则,“党员之德”则是这一原则在党员身上、在党员政党活动中的具体落实。所谓“立党之德”,指孙中山提出规范各政党活动的具体道德要求。孙中山明确提出:“今后之兴衰强弱,其枢纽全在代表国民之政党……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5]1在孙中山看来,政党道德,简称“党德”,乃是巩固“社会之信仰心”的组织基础和精神支撑。具体应该如何建立“党德”?孙中山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第一,从政党的性质和作用入手,提出“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9]469代表人民心理,即代表民意,这是孙中山所认为的政党的基本性质。如何巩固国家?孙中山认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10]158因此,孙中山重视国家的精神文化建设,强调以政党为载体,以先知觉后知,加强国民教育,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从精神上提升国家软实力。社会安宁,即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这是孙中山认为政党应具有的国家、社会功能,并将之简明概括为“为国家造幸福,人民谋乐利”[5]36。孙中山强调,革命党人有提携国民进步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应在政治活动中发挥“帅以正”的引领作用;应努力追求以党德改善国民道德,进而促进社会革新。这些内容表明,孙中山领导的政党,在根本宗旨上与谋一己私利的朋党已经有了质的区别。孙中山的“党德”观不仅为近代政党发展指明了历史的大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思想前奏。
第二,孙中山强调议会政治建立后,各政党竞争要遵守相应的道德。他要求政党竞争,“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5]37,“严守文明,不为无规则之争”[5]45。政党竞争应是“文明”竞争,应该遵守一定的“法则”。这是孙中山“党德”观具有近代色彩的体现。此“法则”实即道德和法律,其中道德是标杆,法律是底线。孙中山所谓“党德”,既指党组织本身的道德建设,也指对党员的道德要求。他强调“党德”必须由党员来践行和遵守,党员要“以正道公理谋国家人民之福利,不用不正当行为”[5]37。其中,对“正道公理”的认识、掌握是基础,“谋国家人民福利”是目的。
(三)革命政党道德
革命政党时期,孙中山的“党德”观得以定型。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党德”更多地针对党员的道德观念,要求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11]283。党员道德的主要内容包括“服从”“牺牲”“立志”“知难行易”等,以解决革命政党组织无力、党员涣散等问题。
“服从”即“主义是从”,指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和贯彻,进言之则是服从“把个人做主义”的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认为“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党中主义,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11]服从主义,是对理念的认识、遵循和服从,何以演变为服从现实的个人?这是由于孙中山一直有革命“先知”的意识担当,并将自己当作“三民主义”的“人格化身”,因此自然便强调“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12]。
所谓“牺牲”,即“能够为主义去牺牲”[13]281。在这方面,孙中山要求党员“第一要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14]。他还提出革命党人的道德标准,即“真革命党,是为国牺牲的,是来成仁取义的,是舍性命来救国的”[15],“要不顾身不顾家之志愿而后可”[16]。所谓“立志”,其意指“为党员者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13]269。
“知难行易”,即“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是中国古代“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反命题。此说主要不是认识论命题,而是伦理学命题,是其“党德”实践观念;它针对革命党人在民国建立后“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10]158,理想信念丧失而发,凸显了近代国民革命觉悟之艰难程度。
三、孙中山“党德”观的重要历史意义
孙中山的“党德”观强调道德在党建中的积极作用。孙中山在自己革命人生的每个时期都关注“党德”,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德”概念,思考和解决近代政党道德问题,并结合革命形势的变化,持续阐发了“党德”的具体内容,形成了前无古人的“党德”观,有力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组织理论的近代化。虽然孙中山的“党德”观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问题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又有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即都坚持了“谋国利民福”的立党原则,都坚持了“天下为公”的崇高、远大政治理念,正如有学者言:“‘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终生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17]这可以视为孙中山推动传统政治道德近代化的理论表现。同时,孙中山将政党建设视为国家近代化的抓手,没有局限于就政党论政党,就党德谈党德。这种大局观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博大胸怀。孙中山重视党员道德建设,发现党员道德建设有推动国民“心性建设”和国家近代化转型的积极作用,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要求,应该予以历史的肯定。
从孙中山的“党德”观的革命实践效果看,其最终走向了失败,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正如有学者所言:“先前世代遗留下来的全部条件是多么有力地规定了他(孙中山)的活动所能达到的限度。”[18]孙中山受中国传统的德治主义影响,寄希望于党德修养使执政者能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从而促成贤能政治,但这也使其“党德”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德治主义的局限,即偶然性和不可控性。在孙中山看来,党德修养,应该领袖引领、党员带头。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观念与领袖引领观念相结合,固然有提倡党员为国民奉献牺牲的积极面,但也潜藏有在国民面前高人一等的自大心态,慢慢就割裂、阻断着国民党与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国民党作为本来要为国家、民众奋斗的革命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完全蜕变为骑在劳动群众头上的独裁者、压迫者,完全违背了孙中山提出“党德”观的初衷。就孙中山“党德”自身的内容言,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其革命道德对于政党建设实践而言,比较抽象,难以落实为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作风;又如其政党道德本来即针对民初政党政治而立,但袁世凯篡权、段祺瑞复辟、北洋军阀实行军事统治等等,都逼使政党政治退出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在军事实力面前,政党道德无力而又无奈;又如其党员道德,注重党员对领袖的服从和牺牲,固然有强化党的团结、提高党战斗力的积极效用,但同时也难免异化,引起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领袖独裁、党员为虎作伥的恶政乱局。
孙中山“党德”观及其实践可谓儒学德治主张的近代尝试,这成为近代儒学政治实践不可忽视的亮点,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孙中山的“党德”建设与组织制度建设脱节,是我们应汲取的教训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坚持“民主和法制、纪律不可分”原则,使思想道德作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补充而发挥作用。孙中山“党德”观片面要求党员服从、牺牲,是我们应汲取的教训之二。我们党强调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主体能动作用,更好地发挥党组织“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主旨。孙中山“党德”观凸显“先知先觉”观念,不自觉地脱离劳动群众,是我们应汲取的教训之三。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始终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在工作中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等等。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理论和实践,是在继承孙中山“党德”观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
总体而言,孙中山的“党德”观是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德治、民本等优秀政治思想传统在近代结合西方政党政治经验后的新探索、新发展,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道德在政治组织理论上近代化的产物。他的党组织理论建设思想汲取西方政党政治经验,又不照抄照搬,努力追求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实际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在思路和方法上针对党组织建设问题,立足革命实践,而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