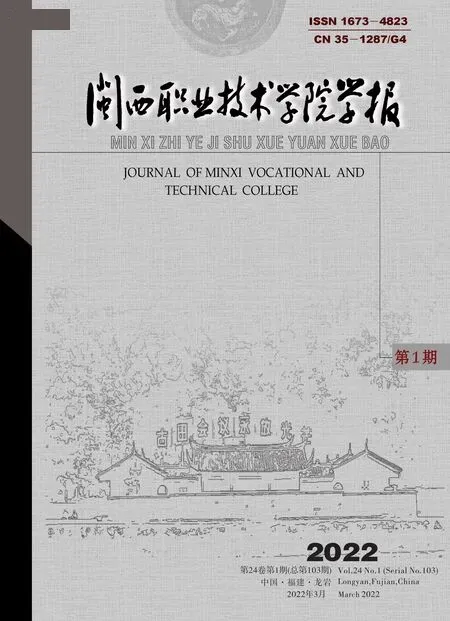选本视角下钟嵘和萧统诗学观比较
王佳薇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王运熙认为,研究古代文学时应注意左右前后的关系,“所谓左右关系,就是指一个作家同时代的与之比较密切的人物,他们在创作上常常彼此互相启发,相互影响,因而应当把他们联系起来研究”[1]。钟嵘和萧统所处时代接近,钟嵘的《诗品》选目与评语曾对萧统有一定的启发,他们的诗学观是梁代乃至汉魏六朝诗学风尚的写照,对研究古典诗歌的脉络和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选本:选家文学观念的载体
钟嵘的《诗品》开启诗歌品评的风气,是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萧统的《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的优秀作品。《四库全书》将二者划入总集类中。总集是集部的一种,在别集的基础上形成。“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2]总集编选的主要目的是“网罗放佚”“删汰繁芜”,对文籍予以整理归纳。“网罗放佚”说明总集有力主全面的意图,实际操作却很难做到,所以部分总集将重心放在“删汰繁芜”上,决定了此类总集有一定的选择性质,因而也被称为选本或选集。《文选》就属于选本的范畴。
在传统的目录学中,《诗品》多被置于总集下的诗文评类中,一般不将其作为选本看待。但据部分学者的考证,以及《诗品序》中“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诸语来看,《诗品》原初是有选文的,只是后来佚失,所以只能见到钟嵘对诗人的总评。虽然选文不得而知,但《诗品》有完整的序文,钟嵘对诗人的择选、分品和评语同样说明《诗品》的成书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具备了除选文外选本的基本体例,因此也可以将《诗品》纳入选本研究的范围。
“早期选集表达文学批评的意见,主要还是通过选集的序文,选目的多寡或以何种作品入选来体现的。”[3]选本前的序文多说明选择目的和标准,直接流露选者的文学观念。有些序文虽没有明确的选文标准,但读者可根据选本收录作品的体裁、内容、多寡、排序等推断出选家的文学偏好。选本的布局经过选家的深思熟虑,优秀的选本多建立在选家成熟的文学观念上。因此,选本是选家文学观念的载体,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品》《文选》分别承载了钟嵘、萧统的诗学观念。
二、《诗品》《文选》选目的同与异
《诗品》虽然没有选文,但序文中提到了28句诗,其出处可视为《诗品》提及的选目。通过比对《诗品》《文选》选录的诗人诗作,可以发现二者具有极高的一致性。
其一,《诗品》划分的12位上品诗人作品,《文选》均有收录。39位中品诗人中,只有秦嘉、徐淑、何晏等8人的诗歌没有在《文选》中收录,收录率近80%。72位下品诗人中,只有范晔、殷仲文、曹操等11人的诗歌被《文选》收录,收录率15%。
其二,诗歌没有被《诗品》提及,却被收录在《文选》中的诗人有11人,除束皙、苏武、张衡外,每人只收录1首。束皙被收录的诗歌有6首,但均为同一类别的组诗。
其三,《诗品序》提到的“未用故实、仍为佳作”4个范例,只有曹植的“高台多悲风”被《文选》收录。钟嵘不甚满意的“日中市朝满”“黄鸟度青枝”未被《文选》收录。有22位诗人的代表作被钟嵘认为是“五言之警策”“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其中18首被《文选》收录。
选家对某一位诗人的偏爱,表现在作品收录的数目上。能够在《文选》中收录多首的诗人,必然受到萧统的青睐。《文选》收录10首以上的诗人有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2首)、曹植(25首)、颜延之(21首)、 朓谢 (21首)、鲍照(18首)、阮籍(17首)、王璨(13首)、沈约(13首)、左思(11首)、张协(11首)、刘桢(10首)、潘岳(10首),统计他们在《诗品》对应的品级,发现《文选》和《诗品》又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性。上品诗人中,古诗并非独立的诗人个体不参与统计,李陵、班婕妤由于时代久远、流传篇目有限等,收录的篇目较少,余下9人全部收录10首以上。但是,位列中品的江淹排到第三位,同为中品的颜延之、谢朓、鲍照的选目数量仅次于曹植,沈约被收录的诗歌达到13首,超越左思、张协等上品诗人,说明《文选》的选目与《诗品》的分品产生一定的分歧,显示钟嵘、萧统在诗歌选择方面有差异。
三、钟嵘、萧统诗学观的同与异
《诗品》《文选》的选目具有一致性的同时,也不乏一定的差异性。由于选本是选家文学观念的载体,从选本可以推断出钟嵘和萧统的诗学观也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一)强调情在诗歌中的地位
关于诗的产生和本质,钟嵘和萧统都强调情的引发作用,自然界带来的视觉享受是触动诗人情思的重要原因。钟嵘说:“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4]萧统曾说:“‘倦于邑而属词’‘睹纷霏而兴咏’。”[5]二人都认为自然界可以触发诗兴,引起诗人的吟咏。社会生活、人生境遇甚至具体的物象也可以作为情产生的条件。萧统评论陶渊明时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6]认为陶渊明好喝酒、好写酒是有意为之,陶渊明在饮酒时触动心肠进而赋诗,酒是陶渊明的精神寄托。钟嵘也列举大量实例,他认为:李陵由于处于声名狼藉、家破人亡痛苦中,方写出沉痛之音;秦嘉、徐淑夫妇情深,离别时伤感由衷而发,诗歌方真实感人。萧统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7]认为诗歌是诗人以语言形式呈现情感的产物,而诗人在抒情时应把握尺度,达到感情上的平衡。钟嵘将古诗放至全书首位,称赞其“温文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4],以温柔敦厚的方式抒发绵延的情志。萧统说:“寄遇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5]认为诗情应以中和的方式得到释放,需要作者有真挚的情感和高超的语言功底,以求情感与文字的完美契合,达到字字珠玑的高超境界,进而创造典雅的诗风。
(二)倡导典雅的诗风
“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8],取法儒家经典是创造典雅诗风的重要途径。钟嵘对12位上品诗人进行溯源,认为《诗经》的国风、小雅以及楚辞是诗歌的源头。《文选》不录《诗经》,萧统认为《诗经》属于经典,“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7],不能擅自择选。萧统盛赞《诗经》“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7],高度肯定寄托理想、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而吟咏女性的宫体诗和直抒男女情爱的民歌,由于不符合温柔敦厚的抒情方式和有所寄托的风雅精神,未被《文选》收录。
文质并重是创造典雅诗风的重要方式。《文选序》记载:“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7]“事”“义”“沉思”侧重内容,“翰藻”侧重辞采,萧统认为文质结合是理想的创作方式。钟嵘亦表达类似的观念,“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4]。“兴”是作者蕴藏在诗歌中的思想内涵和深意,是需要读者体悟之后方能领会的言外之意,倾向于诗歌的思想内容层面;“比、赋”偏重于诗歌的艺术形式层面;“风力”指诗歌表现出的刚健之力,“丹彩”即文采。“兴”和“风力”是内蕴,“比、赋、丹彩”是外在。可见,文质并重的创作方式是钟嵘、萧统的共识,但在具体实践中,两人各有侧重。
(三)文质的不同倾向和诗歌功能的不同解读
陆机被《文选》收录的诗歌达52首,居首位。《诗品》将陆机列于上品,但又批评他“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4],钟嵘认为陆机的诗歌过于注重规矩而显得繁琐。颜延之被《文选》收录的诗歌数量排第五位,但在《诗品》中仅位列中品。钟嵘认为,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4],诗歌雕刻痕迹过重而缺乏自然之美。显然,萧统更偏爱陆机、颜延之。
萧统对艺术形式发展比较包容。在“四声八病”问题上,萧统评论道:“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7]萧统认为,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我们难以全部搞清它的变化规律。《文选》收录沈约近体诗13首,说明萧统包容对声律的追求。而钟嵘则相对保守,他严厉批评四声,“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4]。钟嵘认为,诗歌只要能让诗人抒发真情,诵读流利即可,无需过多的规矩。钟嵘给予曹植极高的评价,认为其“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4],曹植诗情感自然、真实深沉、震撼人心,同时又不乏辞采装点,文质完美结合。同时,钟嵘借用儒家“兴观群怨”阐明诗歌“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功能[4],强调情不仅是诗歌的发端和力量,而且是诗歌的功能。
萧统编纂《文选》是为了给后人提供学习范本,将诗歌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等24小类,多数与社会活动相关,希望文人能为己所用、匡助君王平天下,“他们积极投入历代文学选本的编著,不仅对文人学者编纂的选本进行审定,为之撰写序文,而且还亲自对前代诗歌加以甄选别裁、纂为总集,以此来引导整个社会诗文创作和欣赏的方向、趣味”[9]。在对陶渊明的评价上,钟嵘肯定陶渊明作诗的真情、简净的风格和高尚的人格。而萧统则直言自己欣赏陶渊明是因为“有助于风教”,“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此亦有助于风教也”[6],肯定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和坚贞守节的人格。萧统认为,陶渊明的《闲情赋》主张隐逸、不问世事,是白玉微瑕之作。
钟嵘、萧统都提倡用温柔敦厚的方式抒发诗情,主张通过取法经典来创造典雅诗风,强调文质并重。钟嵘重视以情为核心的质,反对以“四声八病”为代表、有碍于抒情的艺术形式。但萧统更注重词藻,所选大多为典雅之作,对艺术形式的运用和发展持包容态度。“昔人之论南朝文学者,每议其淫靡而远于情性,实则由当时一般的作风而言,或不免多犯此病。若由当时一般的批评主张而言,则外形内质,同样重视;或且因欲矫正一时风尚之故,转有较重于内质的倾向。”[10]钟嵘、萧统在实践上的偏重与文质并重的主张并不矛盾。
四、钟嵘、萧统诗学观背后的时代价值
钟嵘、萧统诗学观的异同反映了齐梁时期的诗学趋向,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具有较高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映汉魏六朝诗的地位和五言诗流行趋势
中国传统诗歌的源头是先秦时期的乡野民歌,隶属于通俗文学。先秦以后,中国传统诗歌迈入雅文学的行列。到汉魏六朝,诗歌越来越受到重视。《诗品》对诗人诗歌进行品评,钟嵘认为诗是“动天地,感鬼神”的文学体裁。《文选》所选文学作品包括赋、诗在内38种文体共60卷,其中诗占12卷半,说明诗具有重要地位。
五言诗起源于民间,到汉末达到成熟阶段。但在初期,五言诗被认为是一种“俳谐倡乐多用之”的诗体,不登大雅之堂。由于字数的限制、语音的复杂和音节的单调,四言诗已无法满足诗人吟唱的要求,至魏晋时期,五言诗逐渐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形式,进而取代四言诗占据文坛的重要地位。钟嵘和萧统在选目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力推举五言诗。钟嵘认为五言诗“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2],在《诗品》中只品评五言诗,对四言诗不置可否。《文选》主选五言诗,但并不排斥四言诗,认为四言诗和五言诗都有存在的价值,“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8],认为四言诗是正统、五言诗是旁流。
(二)彰显齐梁儒、释、道多元文化融会贯通的现状
咏物、宫体诗的兴起,给人以纤小气弱和浅薄艳情之感,破坏了儒家的传统诗学观。钟嵘、萧统重视儒家经典和温柔敦厚抒情方式,不满儒家诗学观受到打压,诗歌向奢靡繁缛趋势发展。钟嵘对诗歌进行溯源,划分出国风、小雅、楚辞三大源头,呼唤寄托理想、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钟嵘、萧统强调文质并重的创作倾向体现儒家的中和思想,钟嵘强调诗歌的情怨因素,萧统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是儒家“兴观群怨”诗教观念在齐梁的延伸。
萧统受佛教的影响,对受佛经转读影响而产生的“四声”持包容态度。而对陶渊明隐逸精神的向往又显现道家思想的文化因子,萧统曾感叹:“谭经之暇,断务之余,陟龙楼而静棋,掩鹤关而高卧。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5]虽然以统治阶级的立场否定《闲情赋》的隐逸思想,但萧统向往闲云野鹤的生活,渴望处理政务之余在自然中沉醉。钟嵘、萧统的诗学观说明齐梁文学受到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受儒、释、道共同影响产生多元之美。
(三)构建汉魏六朝诗歌的基本框架
钟嵘以时间为序,将汉魏六朝诗划分为六个创作阶段:以李陵、班婕妤为代表的汉诗;以曹植为核心、曹氏父子为中心,刘桢、王粲等人共同环绕的建安诗歌;以阮籍为代表的正始诗歌;以陆机为领袖,陆云、张载、潘安、左思等为代表的太康诗歌;以孙绰、许询、郭璞等为代表的永嘉诗歌;以谢灵运为核心,颜延之、鲍照等为羽翼的元嘉诗歌。由此,钟嵘构建了一个以建安、太康和元嘉为重要节点,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核心的诗歌框架。
萧统重申了钟嵘建立的诗歌框架,除了表现在诗歌收录的耦合性之外,也体现在类别的分布上。24个分类中,陆机占据10类,曹植、谢灵运、鲍照占据8类,颜延之、谢脁占据7类,说明这些诗人创作丰富且质量较高。根据“《文选》诗大多数类录有多人多作,每类中所录诗作最多者,且多出的幅度较大,那么此人该是此类的代表诗人”的思路[11],陆机(赠答类12首、乐府类17首)、谢灵运(游览类9首、行旅类10首)、阮籍(咏怀类17首)、江淹(杂拟类30首)、曹植、 朓谢 (杂诗8首)得以成为典范,陆机、谢灵运、曹植是评价最高的诗人。钟嵘对诗歌框架构建的下限止于元嘉,对之后的诗歌评价不高。萧统补充了以沈约、谢朓为代表的永明诗歌体系:收录沈约诗13首,占据5类;谢朓诗21首,占据7类,且在杂诗类中和曹植同为第一。如此,诗歌框架的下限被延长至梁代初期,得到进一步完善。
此后汉魏六朝诗的选本,虽然选目时有偏差,但均受到钟嵘、萧统的影响。《诗品》《文选》均收录的诗人共54位,《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录其中的31位,《古诗源》收录其中的45位,《古诗笺》收录其中的40位,《采菽堂古诗选》收录其中的44位。曹植、阮籍、陆机、谢灵运、陶渊明等22人在上述选本中均有收录。按《诗品》的分品将22人进行归类,上品诗人5位,中品诗人15位,收录率均在40%以上,而下品诗人仅2位,不足3%。除傅玄外,其他21位诗人《文选》均收录多首他们的诗,5首以上的就有15位。虽然在后世选本中,陶渊明后来居上,成为汉魏六朝诗人的冠冕,但曹植、陆机、谢灵运等人同样收录可观。钟嵘、萧统依然得到后人的广泛认同。
五、结语
钟嵘和萧统在《诗品》和《文选》中分别书写各自的诗学观,反映汉魏六朝诗的地位和多元的文化背景,总结了南朝梁代之前诗歌的发展脉络,得到后世认同。“文学批评理论,常常是总结历史上和当代的文学创作经验,又回过来指导创作实践。因此,把文论和有关创作联系起来研究,就能更好地认识文论产生的背景、针对性、理论实质、思想倾向等等。”[1]钟嵘、萧统构建的诗歌框架厘清了汉魏六朝诗的发展线索,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总结。正因为有了汉魏六朝诗的经验和积淀,后世诗歌才得以持续发展。
《诗品》《文选》为后世提供学习的范本。《诗品》被誉为是“百代诗话之祖”,其摘句和品评的方式,开启诗话的先河。《文选》成为必读的经典,“案昭明旧本,唐人奉为蓍龟。以杜甫诗材凌跨百代,犹有熟精文选理之句,余子可以知矣”[2]。钟嵘、萧统重新确立了文质并重、温柔敦厚和风雅精神的儒家诗学观,为唐诗摆脱齐梁诗风的余韵提供支持,奠定诗歌发展主流基调。钟嵘将兴放至比、赋之前,奠定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 璠影响之后殷 “兴象”说、司空图“韵味”说、严羽“兴趣”说、王士祯“神韵”说乃至王国维“境界”说。萧统对教化诗歌的选择,提升了后人的社会责任感。杜甫的诗史精神、白居易的讽喻之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和沈德潜“诗以载道”的论诗宗旨,都将诗歌作为反映事实、教化民众、宣扬人伦的工具。而钟嵘、萧统将情作为诗歌的发端,与韩愈的“不鸣则平”、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袁枚的“性灵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诗歌的抒情性和教化性均得到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