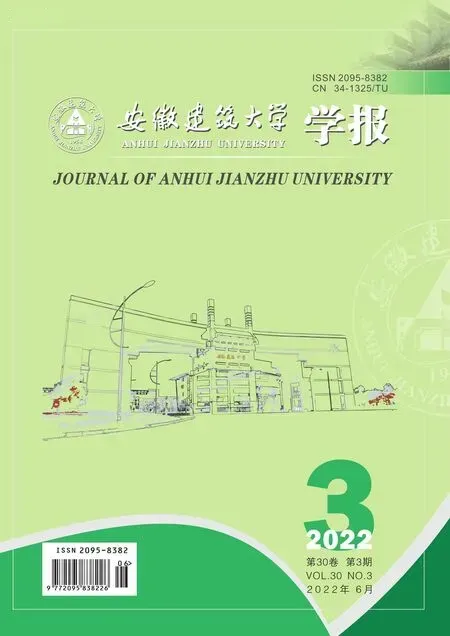论中国人物插画艺术中的审美变革与发展
董瑞子
(合肥学院 设计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插画艺术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插画源于先民对神话传说和天象的非文字形式记录,在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神话→宗教→世俗生活”的内容演变。不论内容如何变化,人的生活始终是最重要的描绘对象,且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插画中的人物形象作为记录生活的艺术载体,也随之发生转变。不同时期的插画人物反映着其创作年代绘画风格和审美观的特征,同时也是创作时代大众审美标准的真实反映。中国数千载的人物插画创作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变化过程,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社会、经济、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各个时期的人物插画审美既有反映时代特征的个性、亦存在共性及内在关联,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物插画审美特征,成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 技法带来的审美转变
绘画技法与审美观念的形成密不可分。技法是插画表现的基础,也是创作者表现审美观的媒介。不同时代的主流绘画创作技法会让插画人物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些技法在中国人物插画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插画创作技法特征,是当代中国插画人物多元化审美的基石。
1.1 传统技法体现民族核心审美观
1.1.1 白描奠定中国人物插画的基本技法
中国源远流长的绘画艺术是中国插画的鸿蒙和雏形。有别于西方绘画以块面塑造形体的技法,中国古典绘画在技法上最显著的特征即“以线造型”,这是由中国传统书写及绘画工具——毛笔的特性所决定的。毛笔作为中国从古沿用至今的主要绘画工具,其动物毛制成的软质笔头具有弹性,能够画出流畅有力且富有变化的线条。中国最早的插画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帛书十二月神图》及西汉的《导引图》,均以毛笔绘制简单的线条勾勒人形,人物具有简洁传神的特点。随着魏晋时期中国人物画的兴起,脱胎于早期线描的白描技法成为中国古典人物绘画的主要创作技法,对中国人物插画的审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白描是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技法,是一种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画法。中国早期古典插画创作者亦是历代人物画名家,均是白描画家中的佼佼者。东晋顾恺之擅长游丝描,其代表作《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所绘线条“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自然流畅”;唐代阎立本擅长铁线描,绘有《历代帝王图》及《步辇图》,刚劲有力的线条精准地体现了帝王的气度和威严;画圣吴道子擅长兰叶描,代表作《天王送子图》是其“吴带当风”绘画风格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以线造型”的白描是中国人物画表现和审美的双重基石[1]。白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生动、凝练、简约、质朴的种种特性使其成为最适合勾勒人物的绘画手法。白描技法在中国走过了几千年的时光,由稚拙发展到成熟,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绘画所固有的程式之一[2]。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人物插画创作技法“自白描始”,且无论后期技法如何发展,及至今日白描始终是中国人物插画的基本技法。
1.1.2 木刻是人物插画审美传播的媒介
除白描外,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中国古典插画逐渐由纸上绘画转向印制画,中国古代另一种主要插画创作技法——木刻应运而生。中国传统木刻表现技法脱胎于白描,以刀为笔,以木板为纸,以线造型,多以阴刻法制版,在纸质媒介上呈现类似白描的印刷效果。因其具有可复制性这一相较于白描的绝对优势,逐渐在印刷技术成熟和通俗小说流行后成为古典插画的主流创作技法。
远至唐咸通九年《金刚经》篇头插画《祗树给孤独园》,近至元明时期的小说插画,如元代《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和明代《三遂平妖传》中的人物绣像,这些时间上相差数千年的古典插画在创作技法上竟无明显差异,唐代的佛祖僧侣、元代的三国人物和明代的神魔均通过流畅生动而又简洁质朴的阴刻线条印制而成。因此,单从技法及其表现风格上很难分辨创作年代,只能从人物具有时代特征的衣饰及插画内容上进行识别。
数十个世纪以来,木刻因其与白描相似的艺术效果尤其是其他技法无可取代的可复制性,一直是古典人物插画的主要创作技法。木刻作为图像传播媒介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古典插画中慈悲的菩萨、飘逸的仙人、豪迈的英雄和狰狞的鬼怪通过刻印大量复制并广泛传播,使得古典人物插画的创作得以一直保持活跃并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创作高峰。
1.2 中西技法融合体现审美的包容性
民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典插画向现代插画过渡的时期,民国插画创作时间虽然不长,却对中国人物插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对技法的革新。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绘画工具和技法被引入中国,使得人们对绘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以透视学、解剖学、化学等科学为基础的西方绘画技法在塑造人物时能够表现写实的造型、逼真的质感、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都是中国传统绘画技法所欠缺的。这也促使中国画家,尤其是受西方美术教育的中国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等将油画、速写、水彩等技法与传统技法相结合,从而创造出兼具东方审美意趣和西方造型技巧的符合新时代审美需求的中国人物插画表现风格。民国的插画创作者们尤其擅长“洋为中用”,以西方绘画技法的外衣诠释中国审美的内涵,也由此中国传统人物审美渐渐出现了新的转变,不再一味地追求线条塑造的美。且在经历了数千年传统审美的熏陶洗礼后,外来绘画技法依然能够在人物插画的主流创作技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足见中国人物插画创作所具有的强烈的吐故纳新,从优秀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的特性。
在诸多外来绘画技法中,尤以现代版画技法对中国人物审美影响最为深远。20 世纪初由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将其介绍到中国,随之成为有力的插画创作武器。不同于中国传统木刻的“刻画分离”,相较于中国本土木刻绘画和雕版作者分别为不同的人,现代版画家们既是版画内容的创作者,亦是雕版的工匠,创作技法和审美观念是一体的。现代版画较之传统木刻单一的阴刻技法,以阴刻、阳刻、反阴、反阳等多种刻法相结合,媒介也由木板发展为铜板和石板等。在画面效果上具有线条与块面相结合、黑白对比分明且肌理形态更为丰富等特点,在当时的人物插画名家作品中均可窥见。如黄新波1936 年为小说《东北抗日联军》创作的《祖国的防卫》系列插画,以强烈的块面感,大面积的黑色和小面积的白之间的对比塑造了立体生动的义勇军形象,较之由单纯线条表现的传统版画具有更加强烈的视觉效果。至此,以线造型不再是插画人物唯一的表现形式,技法的变化使得民国时期的人物插画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味的审美特征。
1.3 当代技法体现审美的时代特征
而在当代,人物插画的表现技法日新月异,创作者们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绘画技法,其创作方法、演绎方式和艺术语言不断拓展,在平面设计、影视动画、数字媒体等领域被广泛运用[3]。当今新媒体时代,人们的阅读媒介已从纸质转向多媒体,利用绘图软件和电子设备创作人物插画已成常态。为了更好地适应手机等移动设备的观看习惯,甚至动态人物插画创作手法都已普及,即通过技术手段使原本静止的人物在电子媒介上呈现出动态效果。数码和交互设备的介入,使得当代插画已实现了二维向三维艺术、静态艺术向多媒体艺术的转变。当代人物插画因创作技法所具有的先进性和多样性,在人物上已经不再受技法的限制,因而当下中国人物插画显示出丰富、多变和前卫的时代特征。
2 人物插画艺术美学思想的变革与发展
中国当代画家的审美品格具有双重性:一是立足当代艺术的国际化来创新求异,体现作品的时代意义;二是继承传统审美的价值观念,来凸显民族古典的艺术精神,弘扬中华的艺术文脉[5],这是不同时代、不同思潮和不同需求交织的结果。因此,当代人物插画审美观的形成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
2.1 以形写神的传统绘画美学思想
中国画崇尚写意之美,顾恺之主张的“迁想妙得”即是从现实中升华艺术的典型做法[4]。在此种美学思想的引导下,自魏晋开始,以白描为表现基础的“气韵生动”的审美观念深入中国本土人物画家的创作基因。人心向往的“意象”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散发出中国古典美学独有的气质和神采。“意象”的呈现和表现形态也彰显出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独有的审美特征和品格。概言之,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独特内涵的极有意味的概念[6]。
与西方古典绘画以块面和光影塑造人的形体,连毛发皮肤的质感都力求逼真的手法截然不同,中国传统人物画并非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客观描绘上,往往只用概括的笔墨勾勒出基本的人物特征和动作,不做过多的细节描绘。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古典人物画家深谙自然之美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艺术之美,故以特有的艺术语言将人物的精神气质寓于飘逸的线条和简单的渲染之中,更多体现了创作者自身对于美的理解,同时也给予了观者更多想象的空间。
2.2 西方新艺术运动带来的装饰性
中国当代人物插画审美观的形成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虽然当代人物插画核心审美根植于本土美学思想,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需求的转变,传统的绘画审美观逐渐融入了新的血液。尤其是近代西方美术和设计思潮传入后,对中国人物插画审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决定性的转变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稍早于新文化运动的新艺术运动。
这场主导20 世纪初艺术审美思潮的设计运动主张在绘画造型上运用富有装饰意味的自然形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对这一审美十分赞同及欣赏,他认为“装饰性”对于提升中国插画创作的美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早在20 世纪30 年代便将新艺术运动插画的代表画家如英国的奥博托·比亚兹莱介绍到中国,为民国时期的人物插画创作提供了可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比亚兹莱以极富个人风格的黑白插画成为西方插画艺术的代表人物,其塑造的众多颇具装饰性的插画人物形象成为众多中国插画家学习和借鉴的“模板”。如有“中国比亚兹莱”之称的叶灵凤,其人物插画呈现出与比亚兹莱人物造型的高度相似。叶灵凤在1925 年为《洪水》杂志设计的一批人物插画很能说明问题,如其中一幅《希求与崇拜》,对比比亚兹莱1894 所做《梳妆中的莎乐美》,两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在动作,表情、发型和衣饰的细节刻画中不尽相同,但从塑造人物所用的线条、装饰、留白等绘画技巧及其所体现的装饰感中,前者对后者近乎狂热的模仿与崇拜是不难窥见的。叶灵凤在其书中写道:“只要留心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现代画家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接受过他的线条和装饰趣味的影响,就是毕加索也不例外”[7]。
由此看出,西方现代设计运动中的“装饰性”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物插画审美观的转变。相较于古典时期插画人物完全描绘客观的朴素主义审美观,新艺术运动的“装饰性”打破了这种观念,在塑造客观人物的同时融入了“非客观”的装饰形态。如将女性的裙摆有意绘制成花瓣形状以增加画面形式感,在创作中融入增加美感和个性的装饰元素,使得插画较之纯粹的绘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设计作品”。
民国时期是中国人物插画审美从古典转向现代的过渡期,相较于中国传统人物插画朴素的审美观,在新思潮影响下逐渐占据一席之地的“装饰性”审美观将插画从纯粹的绘画艺术转变为装饰艺术,使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连接绘画与设计的艺术,使得插画更具实用性,从而使其在新的年代开始发挥新的社会价值。
2.3 新时期注重真实感的人物插画创作理念
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当代社会对人物插画的认识已和古代产生了根本的转变。艺术源自生活、源于真实的创作理念,使得具有符号化、脸谱化等局限性的古典人物插画在某种程度上已和现代审美脱节。真实感不等同于单纯的写实技法,而是以表现技法为基石塑造人物鲜明的个性,在人物创作中力求和同类人物形象有所区别。当代人物插画创作者擅长以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赋予人物真情实感,因此,当代插画人物形象摆脱了旧时代呆滞、刻板、模板化的局限性,体现出时代赋予活生生的人的真实感。如著名画家华三川80 年代为桂林市建设印刷厂挂历所绘林黛玉插画,其以极富韵律的线条勾勒出一位天真活泼的美丽少女,脸颊圆润、神态娇憨,不见半丝病态,体现出少女应有的健康与纯真。这与读者脑海中固有的林黛玉形象大相径庭,一改以改琦《红楼梦图咏》为代表的清代人物绣像中纤细、忧郁、弱柳扶风的传统林黛玉形象。且画家在人物造型时通过对人物五官、脸型、肤色等体现人物特征的部分加以个性化处理,摆脱了清代绣像绘制人物时面部塑造雷同、少女与老妇仅靠服饰发型区分、“千人一面”甚至男女不分等局限性。当代人物插画创作所提倡的真实生动、不拘一格的审美观消除了虚构人物和读者间的距离,使他们从书中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3 功能与审美的有机统一
插画作为一门实用性艺术,不是单纯的绘画创作,而是功能和审美相结合的有机统一体。总体上说,中国人物插画审美朝着大众化和实用性的方向发展,但不同时代的插画从题材到表现技法都表现出较大差异,这源自时代需求以及功能的变化,体现了插画这一实用性艺术形式追随功能的创作理念。
3.1 绣像画
绣像是明清时期描绘人物装饰与故事情节的插图。明清是中国古典插画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人物插画最广泛的题材即带有显著世俗化审美特征的戏曲小说绣像。究其原因,这一插图术语的兴起既是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需要,也是书商的营销操作所致。它们发展与变化的背后,是社会风尚与阅读者的审美趣味在推动[8]。如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为梁山好汉塑造了正面形象,是融合文人审美与大众通俗娱乐的巧妙产物,体现了插画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
此外从印制工艺层面来看,由于明代雕版印刷的高度成熟和普及,印制插画的难度及成本均大幅降低,使得为印刷品配图的情况趋于普遍。比起唐代只能供少数上层人士阅读的珍贵佛经中才能配图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插画艺术的受众。贵族与平民的审美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之传统印制插画因纸张、用墨、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性,人物造型具有不可避免的粗糙简陋之感。明清绣像画的人物美感和艺术性虽有所降低,但仍具有古典人物画质朴、纯粹、典雅的特征。
3.2 商业宣传类插画
民国时期的插画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插画,这一时期的插画主要用于宣传抗日救亡与社会生活,插画被广泛运用于街头散发的抗日传单、家庭墙壁悬挂的月份牌以及香烟肥皂的包装盒上,开始承担宣传媒介的作用,相较于古典插画更具实用性和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也是中国商业插画的开端,人物题材被用于商品的包装与美化。商业插画人物形象多为年轻的美女形象,以杭犀英、郑曼陀等人创作的月份牌美女像为代表,是大众审美的典型产物。这些符合时代审美的女性形象大多具有美丽亲切、生动活泼、讨人喜欢等特征,大大提升了产品的销量,故而作为插画人物具有了一定的商业价值。民国奠定了商业插画人物兼具艺术与实用性、以大众审美为设计导向的特点。
3.3 文化普及类插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插画迎来了新的创作时期,插画创作重要的功能之一即进行文化宣传和普及,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形态意识,为丰富和创新插画语言的本土化个性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与领域[9]。以连环画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插画塑造了众多经典人物形象,多样的风格为新时代插画构建了全新的视觉体系。连环画是我国特有的插画类型,脱胎于早期卷轴画,以图叙事,不需过多阅读文字的特点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化普及和娱乐工具,在贫瘠的年代大量青少年以及文化层次较低的受众通过阅读连环画增长见闻。特殊历史时期的需求为插画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创作契机和广阔的创作空间,也使得创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大众性是连环画的根本属性之一。只有解决好“大众化”的问题,连环画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10]。因此无论从选题还是人物塑造上,连环画都体现出雅俗共赏且通俗易懂的特征。
当代连环画题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旧作新画”。此类题材在当代常被作为寓教于乐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工具,是连环画最常见的表现题材,也是当代连环画名家们热衷创作的题材。如刘继卣所绘《闹天宫》、王叔晖所绘《西厢记》等,虽取材于古典小说、戏剧、民间传说等,但在人物审美上具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画中人物较之古典时期的刻板,在形象塑造上明显更为生动真实,和读者的距离更为贴近。另一类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插画创作。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众多当代现实主义创作题材,画家们用画笔呈现了新社会的种种新面貌,连环画中出现了以往各个时期不曾出现过的人物类型及形象,而对新的人物形象的诠释必然反映的是新时代的人物审美特征。如贺友直在其代表作《山乡巨变》中塑造的邓桂梅这一建国初期的女性干部形象,是全新的新中国职业女性形象。这一睿智冷静、尽职尽责,颇具领导才能的基层女干部形象,反映出背后隐蔽的时代内涵与代表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深层心理图谱[11]。此外,作品中刻画了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栩栩如生的当代农民形象,画家以朴素有力的钢笔线描赋予农民这一中国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群体独立而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他们在新时期的连环画创作中不再只作为背景和陪衬。以普通人为艺术创作对象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最大限度上达到文化宣传的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人物插画发展历经时间的洗礼,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总体上,中国人物插画审美集中体现在大众化和实用性两个方面,在不同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是受时代、技法、题材、功能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普罗大众对美的认知是人物画创作的审美导向,同时也使得人物审美向着世俗的认同发展,这是插画艺术得以延续和不断进步的基础。但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大众审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使得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物插画风格不能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在大众审美的引领下,中国人物插画创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物风格朝着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使得插画艺术从纯粹的绘画艺术中剥离出来,因社会的需求产生了实际的功能,这是插画区别于纯美术最显著的特征。功能赋予插画实用性,使插画区别于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绘画创作,因此插画中的人物形象会因功能的不同而呈现出商业性、装饰性等特征,以满足社会和受众的需求。总之,中国人物插画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在审美大众化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当代具有自身独特艺术语言的多元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