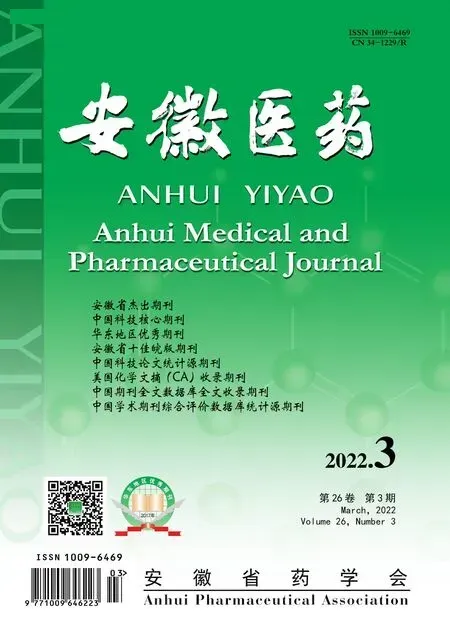半乳糖凝集素-3与脑卒中:从病理生理学到临床的研究进展
张永康,韩燕
作者单位: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脉管病科,上海200082;
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上海200437
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gal-3)又称作碳水化合物结合蛋白-35(carbohydrate binding protein-35,CBP-35),是凝集素的一种。它由人类第14条染色体上LGALS3 基因编码[1]。gal-3 在人体的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感觉神经元、上皮和内皮细胞中均有表达,广泛分布于人体细胞内外,如在细胞核、细胞质及细胞膜上均有存在[2]。作为一种多效蛋白,gal-3 会影响细胞的活化、增殖、迁移与凋亡。并在脑卒中后的组织损伤中起到重要作用,对脑卒中临床诊治有独特的指导意义。
1 gal-3在脑卒中发生后的病理生理学作用
脑卒中发生后,病人颅内缺血缺氧区域将产生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反应。gal-3 参与到了缺血缺氧初期损害到脑卒中后期康复中的所有阶段。其病理生理学作用主要涉及颅内的炎症反应和组织重塑。
1.1 gal-3在脑卒中后颅内炎症反应中的作用
1.1.1 gal-3 脑卒中后颅内炎症反应中的促炎作用 脑卒中急性期时相应区域会发生炎症反应。其中作为颅内产生gal-3 最主要来源的小胶质细胞被快速激活[3],并在形态和功能上发生改变,表现为细胞增大增厚、产生促炎物质、增殖、迁移和吞噬行为的改变。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亚群中gal-3 的表达强烈上调,导致因缺血缺氧损伤的脑灰质损害加重[4]。研究证明了gal-3 参与到脑卒中后早期的炎症反应中,同时在各种神经炎症的刺激下,小胶质细胞中gal-3的表达增加。相关研究发现,gal-3在缺血性脑损伤后具有有害作用,而这种作用很可能取决于缺血损伤的类型和时间、gal-3 的细胞亚型定位以及机体的免疫状况[5]。在脑缺血模型中,gal-3 依赖的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4的激活介导了小胶质细胞的持续性活化,从而延长并加重大脑中的炎症反应[6]。与此同时,gal-3 还可以通过抑制炎症细胞的凋亡来发挥促炎作用[7-8]。
1.1.2 gal-3 脑卒中后颅内炎症反应中的抗炎作用 除了上述的促炎特性外,gal-3 也具有抗炎的能力。有研究发现gal-3 增强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 growth factor-1,IGF-1)的作用,进而触发了小胶质细胞的抗炎特性[6]。同时,gal-3 能够直接结合脂多糖,抑制它与TLRs 的作用。若使用gal-3 中和抗体阻断两者相结合,则会增加LPS 诱导的炎性因子的表达[9]。另有研究发现gal-3 的缺乏会使促炎细胞因子如白介素(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LR2 和TLR4 的水平显著升高[10],导致加剧炎症反应和加重神经损伤。缺乏gal-3 也会导致对双环己酮草酰二腙诱导的脱髓鞘反应的敏感性增加,这进一步支持了gal-3 神经保护作用的潜能[11]。并且体内外研究同时表明一定水平的钙调神经磷酸酶(calcineurin,CaN)活性是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所必须的。而在细胞膜上的gal-3 通过发挥多价螯合作用以增强IGF-1 受体信号传导,延迟了内在化过程,诱导了CaN 活性水平升高[12]。在脑卒中发生后,活化的小胶质细胞通过分泌gal-3 来诱导邻近神经元中钙离子信号传导,最终通过CaN/活化T 细胞核因子(NFAT)3 的途径达到神经保护作用[13]。也有研究发现脑卒中后gal-3可介导小胶质细胞重编程,使促炎因子的表达下调和抗炎因子IL-4 的表达显著上调,从而减少脑卒中后梗死面积[14]。
综上所述,脑卒中后颅内产生的gal-3可影响小胶质细胞内IGF-1,CaN和先天性免疫等多种信号传导方式,进而改变小胶质细胞的表型。这种改变可能与gal-3 在卒中急性期与非急性期所发挥不同的病理生理学作用相关,继而小胶质细胞对缺血性损伤作出动态反应,即从早期的促炎表型再过渡到抗炎表型。这便解释了各项研究观察到gal-3 的炎性效应差异。
1.2 gal-3在脑卒中后组织重塑中的作用
1.2.1gal-3 促进脑卒中后组织重塑中的神经发生 脑卒中后除了颅内炎症反应的发生,往往也会触发颅内内源性神经形成。有研究表明炎症反应对成人脑神经的形成具有不利的影响[15]。同时其他研究发现脑卒中后长期使用米诺环素抗炎治疗可诱导脑回中神经发生并促进神经功能恢复[16]。这说明炎症反应在体内神经发生中的作用比较复杂,并且可能和神经母细胞与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17]。而损伤诱导的神经发生有助于卒中后大脑的重塑及恢复。在此期间,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合成的gal-3 可能影响脑卒中后神经修复的相关通路。有研究表明gal-3 促进了神经母细胞的增殖,若抑制gal-3的产生则降低了同侧脑室下区中5-溴脱氧尿嘧啶核苷染色细胞(即神经母细胞)的数量[3]。也有研究表明影响小胶质细胞的增殖与选择性激活的关键因子是IGF-1,从中枢或外周给予IGF-1 有助于脑卒中后恢复及神经保护。IGF-1 可以减轻不同实验环境下的脑损伤,促进神经发生并增加神经存活[18]。然而,关于gal-3在脑卒中后神经发生中作用的研究仍旧不足。
1.2.2 gal-3促进脑卒中后组织重塑中的细胞存活、迁移和血管生成 分泌到细胞外的gal-3 增强了细胞存活、迁移和血管生成。有证据表明BV2 细胞在含有gal-3 的培养基中显著增加了体外促血管生成结构的形成[19]。相关研究认为gal-3 通过影响白介素激酶(Interleukin kinase,ILK)来调控细胞的增殖,存活和迁移。其中,ILK 可调节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1α 介导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达,它对内皮细胞迁移、管状形成和肿瘤血管生成至关重要。gal-3 在缺血环境下可调控ILK 水平升高,若沉默ILK 则会导致血管生成和小胶质细胞迁移减少。因此,gal-3 激活ILK 信号通路可能是脑缺血损伤后新生血管形成及小胶质细胞迁移增加的原因[19-20]。不过通过gal-3 调节神经细胞增殖、影响神经形成的确切分子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gal-3 通过激活多种生物途径来调控脑卒中后的神经发生、神经细胞迁移及颅内血管生成。
2 gal-3对脑卒中的临床指导意义
gal-3 对炎症、组织修复以及细胞迁移有着多效调节作用,并且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2,21]。大量研究表明gal-3 是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志物[21-23],较高的gal-3 水平往往提示心血管疾病预后不良[24]。然而人体内gal-3 水平与脑卒中之间关系的研究则较为有限。近年来,逐渐有少量的临床研究开始关注人体内gal-3 水平与脑卒中发病及预后之间的关系。
2.1 gal-3与脑卒中发病率 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血管疾病是诱发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且gal-3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部分临床研究展开了对人体gal-3水平与脑卒中发病之间相关性的探索。
2.1.1 gal-3 增加脑卒中发病率的文献支持及分析 在一项探索gal-3 与心血管疾病和心衰关系的大型前瞻性研究中调查了8 444 例既往无脑卒中史受试者,随访15 年后发现较高的gal-3 水平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病之间呈弱相关(HR=1.40,95%CI:1.01~1.94),在多变量调整模型中,这种关系进一步减弱(HR=1.22,95%CI:0.88~1.69)[25]。最近一个旨在探讨地域与种族差异对卒中影响的队列研究中观察了1 473 例病人,他们发现脑卒中的发病率随着血清gal-3水平的升高而增加。在较年轻(≤64岁)的病人中,血清gal-3水平伴随着脑卒中发病率的升高而显著升高(gal-3 水平上四分位数比下四分位数:HR=2.4,95%CI:1.1~5.3,P=0.03),尤其是心源性和隐源性脑卒中的发生;而在年龄较大(>64 岁)的病人中,血清gal-3水平与脑卒中的发生未见明显关联(gal-3 水平上四分位数比下四分位数:HR=1.0,95%CI:0.6~1.5,P=0.85)。这种在不同年龄段间gal-3 水平与发生脑卒中风险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26]。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gal-3 出现了平台效应,导致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失去了原有的生物标志物的灵敏性。
以上两项研究都表明较高水平的gal-3 可能增加脑卒中的发病率。一方面是由于gal-3 与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疾病及心房颤动等心脏疾病有关,表明gal-3 可能是具有血管疾病倾向的生物标志物。同时gal-3与房颤之间的关联,使其与栓塞性脑卒中的关系更为紧密[22]。另一方面,由于gal-3在动脉斑块的稳定性及重塑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gal-3对因动脉粥样硬化而诱发的脑卒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患有症状性颈动脉狭窄的病人血浆gal-3 水平更高,并且gal-3 水平较高的病人脑卒中发病率增加[27]。
2.1.2 gal-3 与脑卒中发病率无关的文献支持及分析 然而,另一项招募了1 013 例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的心血管事件高危病人的研究,在随访10年后发现gal-3水平与病人既往卒中史无关,同时也无法预测卒中的发生[28]。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矛盾的结果,可能是部分研究针对的是高危心血管事件的病人,既往的研究已多次证明gal-3 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因此这部分病人的gal-3水平可能受原有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相对于脑卒中涉及大、中、小等不同管径的血管病变来说,心血管疾病往往累及大血管,而gal-3与大、中、小血管病变相关性如何还尚待研究。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所服用的相关药物与脑卒中一级或二级预防的人群用药有大部分重叠,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同时就能很好地预防脑血管疾病,卒中发病率因此下降。另有部分关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检测了受试者体内gal-3水平,但没有将脑卒中作为或单独作为首要终点事件[29-30],也没有观察到gal-3 与卒中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未来需要开展以脑卒中作为首要终点事件的大型研究来进一步探索gal-3 水平与脑卒中发病率之间的关系,甚至需要把责任血管分层,验证gal-3水平与大、中、小血管闭塞之间的相关性。
2.2 gal-3 与脑卒中预后脑卒中预后判断一直是神经病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既往研究表明炎症和血管生成是缺血性卒中病理反应的关键因素[31]。包括白细胞计数在内的炎性标志物升高、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和红细胞沉降率升高与缺血性脑卒中短期临床结果相关[32]。同时,几种其他血清炎性标志物如降钙素原,超敏C 反应蛋白则与缺血性脑卒中后长期随访的死亡相关[33]。因此,gal-3 作为能够影响颅内血管生成及神经发生的新型炎性标志物,对脑卒中预后的预测有着潜在的价值。
既往大量研究表明,人体内较高的gal-3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血管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不良预后相关[2,23,34]。近年来,逐渐有研究者关注人体内gal-3水平与脑卒中预后之间的关系。
2.2.1 gal-3与缺血性脑卒中预后 最初,有几项研究探索了gal-3 在作为心血管事件发生后预后生物标志物的价值,但其中只有一项小型研究同时调查了缺血性卒中后gal-3的预后价值。该研究发现gal-3 水平不能预测接受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治疗的缺血性卒中病人急性期或3 个月的预后[26]。但是,缺血性卒中病人确实具有比对照组更高的gal-3 水平,这也许是血管负荷增加或者脑损伤后的应激反应。不过,该研究的样本量十分有限,仅有26 例病人及10 例健康对照,在该样本量的条件下,还难以给出准确的解释。
随后有临床研究观察了gal-3 水平与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预后之间的关系。此研究共招募了130 例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卒中的病人,随访时间为90 d。研究结果表明高血清gal-3 水平的病人在90 d后的预后较低血清gal-3水平的病人更差[良好预后gal-3 水平比不良预后gal-3 水平:(7.48±1.64)ng/L 比(8.25±1.66)ng/L,P=0.013][35]。另一项纳入了233 例首次急性缺血性卒中病人与252 例健康对照的研究,在经过1 年的随访后发现血清gal-3水平与病人的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评分(NIHSS 评分)以及改良Rankin 评分(mRS 评分)高度相关(gal-3 水平与NIHSS:r= 0.871,P< 0.001;gal-3 水平与mRS:r=0.728,P<0.001);高血清gal-3水平提示卒中的神经缺损程度较重,并预示出院12个月的神经功能结局不良(mRS 评分≥3 分)。此项研究的体外实验部分发现在氧葡萄糖剥夺处理下,用siRNA 敲除gal-3 基因可以显著提高神经元细胞的生存能力并减少其凋亡。随着gal-3被抑制,促炎因子的表达降低[36]。这一结果为gal-3 如何影响缺血性卒中预后提供了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另有一项纳入3 082例急性缺血性卒中病人的研究,在随访3 个月后发现高血清gal-3 水平与急性缺血性卒中后三个月内死亡或严重残疾等综合结局风险显著相关,这种关联独立于已知的危险因素(多变量校正后gal-3水平与3 个月内死亡:OR=2.10,95%CI:0.89~4.95;多变量校正后gal-3 水平与严重残疾:OR=1.63,95%CI:1.31~2.03)[37]。以上3 项研究都证明了gal-3 对缺血性卒中预后的预测价值,尤其是最后一项大型研究,发现了高血清gal-3水平和缺血性卒中不良预后的独立相关。
2.2.2 gal-3 与出血性脑卒中预后 相对于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预后与gal-3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局限。缺血性与出血性卒中之间的病理生理学差异明显,出血性卒中的血脑屏障破坏更严重,其调节的炎症反应更早、更剧烈。由此推测gal-3对出血性卒中预后的预测作用可能更敏感。有研究发现出血性卒中发病最初24 h 内检测出的高血浆gal-3 水平可预测病人1 周和6 个月后的病死率以及6 个月后的不良预后。此外,高血浆gal-3水平还提示脑卒中程度更为严重(gal-3 水平与NIHSS:r= 0.603,P<0.001)[38]。这也说明gal-3 可能在出血性卒中的结局预测中存在一定价值。
综上所述,卒中预后与体内gal-3水平的关联十分紧密。临床上对脑卒中病人进行常规的血液学gal-3 水平检测或许能够提供重要的预后信息,并为下一步在卒中病人中开展降低血液学gal-3 水平药物的临床研发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