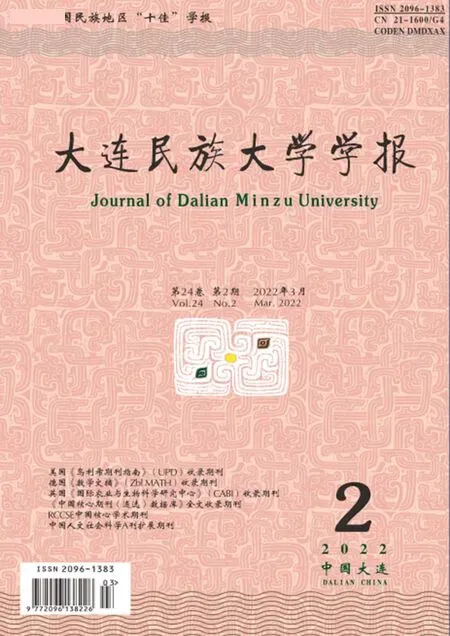地域景观、民族文化与辽西地区高质量发展(1)此文曾于2020年9月10日在辽宁省喀左县举行的“‘东蒙民间故事’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感谢与会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郭永平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和河南考察时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1]的重大国家战略。2021年,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推进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的时代议题。已有的“高质量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涉及到“发展模式选择”[3]“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4]“数字农业”[5]“财政分权、产业结构”[6]“建设生态走廊”[7]“打造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8]等议题。从研究空间来说,没有涉及到东北地区,且对文化在区域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不够。众所周知,东北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新时代的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总书记曾强调:“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下一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要有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9]要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就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相对于汉族聚集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历史原因在经济方面发展较为滞后。辽西走廊处于中原农耕区与东北游牧、渔猎区的交汇地带,在此民族廊道居住的蒙古族是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文明交流与传播的结果。新时代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在整体观理念的指导下,将人类文明发展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整合起来,并实现其从景观到遗产、再到资源的转化。这是总体营造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辽西走廊的形成
辽西地处辽、蒙、冀交界,是重要的“历史、地理枢纽”与“文化廊道”[10]。早在上古时期,东北的古老民族肃慎就与中原建立了联系。春秋时期,齐桓公伐山戎、孤竹和屠何等,走的就是辽西走廊。公元前215年,秦始皇首次东巡,在辽宁绥中“刻碣石门”。汉武帝再次东巡建“汉武台”。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在辽西白狼河大破乌桓后凯旋,路过碣石,写下《观沧海》。此后直到辽金时期辽西傍海道开通以前,辽西走廊一直发挥着“文化大熔炉”[11]的作用。明清时期,在辽西走廊的核心地带,今辽宁省喀左县、建昌县、凌源市,主要由蒙古族乌良哈、土默特、喀喇沁部蒙古人和后来的随旗汉人在此驻防,后蒙古族喀喇沁部在喀左境内的敖木伦河流域逐渐定居,生产方式转为农耕。辽西有两个蒙古族自治县,分别为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喀左县)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简称阜蒙县)。喀左县是辽宁省朝阳市下辖的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地处辽宁省西部朝阳市南部、大凌河上游的丘陵地区,是辽西走廊北通道要冲。截至2020年,喀左县境内有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等10个民族,共41.94万人,少数民族中以蒙古族为多,共有9.2万人,占总人口的22%[12]。截至2021年,阜新县总人口为74万人,有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锡伯族、朝鲜族等24个民族,其中蒙古族人类最多,有15万人,占到全县总人口的20.3%[13]。
喀左蒙古族是辽西地区历史上的重要民族支系,也是中国较早实施定居农耕的蒙古族,亦可称为“辽西农耕蒙古族”,其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已近200多年。1947年,包括旗王府在内的公营子五大府邸都毁于战火,这些在历史上因防御战争及动乱而设置的聚落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逐渐转变为农耕村落。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辽西北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该区域没有辽河平原肥沃的土地,且多山导致交通不便,近代以来逐步衰落。另一方面,辽西北处于辽西古廊道上,是多元文明汇聚的地带,受现代化冲击较少,故而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得相对完整。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区域复兴中,就要充分保护、挖掘其丰富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不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是宝贵的人文资源,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
二、地域景观的表征
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辽西走廊属于中原和东北以及东北亚重要的交通枢纽;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这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其在文明起源进程中意义重大。历史时期,不同族群在长期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共同影响、形塑了该区域独特的地域景观。地域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是地方性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认识和理解地方性的重要路径。辽西地区的地域景观“遗存量大,形式多样,类型繁多,历史信息含量高”[14],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1.独特的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伴随着自然美进入人的视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得以重新建立。辽西蒙古族主要活动于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六股河发源和流经的水草肥美的沿河流域。由东北向西南走向的松岭、黑山、医巫闾山等山岳自然景观则具有雄、奇、险、秀的特点,辽西蒙古族就聚居于这种山水交错的自然环境中。喀左主要河流有大凌河及其支流榆河、牤牛河、蒿桑河、渗津河、芍药河等。在尤杖子乡境内,有集奇石、怪柏、古刹、异洞于一体的龙凤山。2010和2011年,龙凤山森林公园获得“游客喜爱的辽宁省50佳景”的称号。位于喀左县老爷庙镇、尤杖子乡、羊角沟乡交界处的楼子山海拔1091.1米,是喀左境内最高的山峰。铁沟里景区位于喀左县羊角沟乡境内,由此可通往龙凤山景区、楼子山自然保护区。喀左凌河第一湾位于水泉镇、东哨乡和羊角沟镇三个乡镇交接处。“该景区充分利用喀左县大凌河旅游资源,以自然生态为依托,构筑了‘一带十景’。景区以敖木伦河(大凌河)为纽带将十个天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贯穿一体,以观光、采摘、骑射、竞技、漂流、垂钓、体验农家生活、泛舟、鸽子洞访古、天门洞探奇为主要内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15]
阜蒙县地热资源极其丰富,被誉为中国“小苏打第一泉”。该县有海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木图山风景区等。海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辽西保存较好、森林生态类型最完整、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天然林区,被称为辽西的“绿色明珠”,是蒙古高原到辽河平原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位于阜蒙县八家子乡境内的乌兰木图山海拔高度831.4米,是阜新市第一高峰。
2.文化景观的再造
文化景观是人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融合到“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之中”[16]而形成的文化复合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区域特征。辽西蒙古族地区主要文化景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人类早期活动景观,二是建筑景观,三是宗教景观。
(1)人类早期活动景观。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和大凌河上游,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新曙光”[17],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红山文化的发现始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一批学者对赤峰红山遗址的发掘。1954年,尹达正式将其命名为红山文化。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喀左东山嘴等大型祭祀遗址的发现,红山遗址引起了轰动。1979年,在位于辽宁大凌河西岸的喀左县发现了东山嘴遗址。随后,考古人员在距离此处约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村又发现女神庙、积石冢等建筑遗迹,经确定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苏秉琦先生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列入六大区系之首,并通过北方与中原这两大区系的关系来探索华夏文明的源流问题”[18]。2014年,赤峰市与朝阳市共同签署了《红山文化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备忘录》,宣布将联合对红山文化进行申遗。2017年,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展示馆开始试运营。展馆以东山嘴遗址为核心,通过文字、图片、影像、实物等手段展示了华夏文明的新曙光——红山文化,这是地方政府再造的一处新文化景观。
位于喀左县水泉乡瓦房村西汤山南侧,大凌河边悬崖陡壁上的鸽子洞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距今5~7万年,这是迄今辽西大凌河流域最早的古人类居住址,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2019年10月,该遗址入选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阜蒙县沙拉乡查海村西五里“泉水沟”北坡向阳扇面台地上的查海遗址距今已超过8000年,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96年查海遗址被批准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建筑景观。这里的建筑景观主要指的是民居“海青格热”。“海青格热”是今天在辽西蒙古族聚居区见到的最具有历史与民族特色的民居,它混融了北方汉族囤顶式民居与东北满族海青房民居的某些建筑特点。海青格热的发展共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初(初建期)。蒙古族人就地取材,搭建土墙、土坯、木檩硬压山平房。第二阶段是清代中期(发展期)。随着生活的稳定,财富的积累及汉族工匠的介入,出现了修建四梁八柱、砖石结构、一明两暗的海青平房。第三阶段是清朝晚期至20世纪50年代前期(建造技术的完善期)。随着砖、石和石灰的采用,海青平房更加坚固美观。第四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至80年代末(成熟期)。随着砖、石、木、瓦、水泥和石灰的全面应用,海青格热的建造材料和技术有了质的飞跃,更加坚固、美观、实用。海青格热民居的优点很多,构造上防风、阬震又防雨。现今的海青格热民居无论是建筑材料、空间格局,还是建筑功能等方面都是非常标准、成熟和完善。(2)参见陈福奎:《喀左蒙古族民居——海青平房》,打印稿,2017年3月17日。陈福奎,蒙古族,曾任喀左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县政协秘书长。第七届、第八届辽宁省政协委员。现为喀左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聚落也在发生变化。喀左县在1949年有17000所海青平房,1985年还有约76000所。据2017年调查,该县海青房主要集中于白音爱里和官大海,加起来也就600所,预估全县不超过3000所。鉴于营屯的衰落,对于“海青格热及其营屯聚落整体的保护需要加快推进”[19]。对辽西蒙古族传统聚落及“海青格热”民居的保护,不能完全依赖文化持有群体的文化自觉,而应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情况下,将局部的重点保护与广泛的建筑更新引导结合起来,以此实现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事实上,“绿色原则”与所有权支配性并不矛盾。一方面,对所有物的“节约性使用”符合理性的所有权人的内心意志,所有权支配性与“节约资源”的理念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物既有经济性,也具有生态性,物的归属和利用必然要对环境产生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所有权绝对主义观念也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大背景下日益松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要求[29],在民法中引入环保规范已成为现代物权制度的重要发展趋势。[33]例如,在自己院落或土地中储存有毒污染物或滥伐该区域内林木的行为,存在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法律后果,非属私法保护的利益范畴,传统所有权绝对理论需要修正。
(3)宗教景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辽西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互动与交流。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应喀喇沁部封建主白洪大之邀来喀喇沁传教,是为喇嘛教传入喀喇沁地区之始。清朝建立后,大力兴建喇嘛庙宇,到清朝末年,在喀左县境内藏传佛教寺庙已达90余座,仅官大海就有吉祥寺(铜顶庙)、经升寺(车轱辘庙)、西升寺(双大庙)、西庙,共四座藏传佛教寺庙。据解放后统计,仅在喀左县境内,较大的喇嘛寺庙就有91座[20]。著名的喇嘛寺庙有普佑寺、全安寺、天罗寺、仁隆寺、普善寺、吉祥寺等。以吉祥寺为例,在清代鼎盛时期,这里曾住过40多名藏传佛教教徒,先后出现过7位活佛,是该区域重要的宗教圣地。进入民国后,藏传佛教开始衰微。20世纪50年代以后,官大海的大部分藏传佛教教徒还俗,剩下为数不多的喇嘛接受了政府劳动光荣的教育,并获得土地,自食其力,年老的喇嘛也得到适当的照顾和安排。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吉祥寺又开始重新维修,并对外开放[21]。重修后的吉祥寺是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从南至北分别为天王殿、三世佛殿和大雄宝殿,东南角为关老爷殿。如今,寺院里除了正常的庙会活动外,还于每年的10月25日举行盏灯会。吉祥寺已成为当地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在阜蒙县,“玉龙故乡”“契丹摇篮”“三丰故里”“佛教圣地”正在成为其向外界展示的重要符号,也成为全县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产业的重要依托。
人文地理学家赫西认为:“景观意味着一种人与自然环境、景物、土地之间的关系,即人如何为景观赋予意义或建构一定的文化意义的过程。”[22]因此,保护自然、维持生态、构建景观、发掘遗产、传承文化,为人类构建“诗意的栖居”之地,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机制
景观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现代社会,只有再造、重构景观,将景观遗产化、并实现从遗产到资源的转换,景观的重要价值才可能被充分认知。这就需要“从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开始,深入层层的记忆和表象,通向深埋于几世纪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最初基岩,并再一次地激活它,使它重获现代社会的认知。”[23]这就要借助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将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打造、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建设的保护连接起来,研究、挖掘、整理民族文化,并将其转化为文化资源,构筑区域特色鲜明、有竞争力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体系,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机制。
1.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2016年2月5日,国家旅游局公布首批262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喀左县入选。在此情况下,喀左县提出了打造“全景喀左”、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发展思路。在“打造全景喀左、发展全域旅游”的过程中,喀左县政府的定位是“全域旅游与特色经济并行的营屯聚落发展”。要“将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将部分农村转变为旅游景区(点)、将部分农民转变为旅游从业者,以旅游开发带动乡村旅游发展。”[24]全域旅游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旅游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思路为蒙古族营屯聚落创造了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这些代表喀左的特色旅游品牌也在形成。
《2020年喀左县政府工作报告》共有13800字,其中“旅游”出现了14次,尤其是强调“文化旅游”,指出“集中力量做优文化旅游产业,发挥资源优势互补作用,推动‘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辽宁省以及朝阳市也积极支持喀左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5]。2020年,朝阳市市长谢卫东《在朝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继续支持喀左县争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26]。目前,喀左县正在倾全县之力争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第一,通过喀左县明确责任分工,积极引导舆论,强化各乡镇街区、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的旅游参与意识、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针对各乡镇街区开展了以洁化绿化美化、污水垃圾处理提升等为主要内容的全域环境整治工作。”[27]
全域旅游是一个整体,环境的营造是基础工作,上述任务的完成离不开民众积极主动地参与。然而,到底怎样开展全域旅游其实并不清晰。实际上,全域旅游不外乎丰富的旅游资源,完善的旅游设施,全面、周到的旅游服务。这就要挖掘与打造特色资源,并将这样的文化资本转化经济资本与符号资本,在全域旅游与特色经济并行的营屯聚落发展定位中,带动聚落经济的提升、文化的传承,以及区域社会的整体发展。
2.创建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
从2007年到2017年,文化部在全国共设立了21个国家级保护实验区。2019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第一条明确指出:“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维护和培育文化生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8]。《办法》突出了“以非遗保护为核心”的理念和“区域整体性保护”的原则。目前,喀左县有7个非遗项目,分别为喀左紫砂、喀左面塑、喀左糖画、喀左陈醋、喀左剪纸、喀左背歌、喀左东蒙民间故事。2006年年初,“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4月,喀左县文化馆根据县委下发的《关于在全县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喀左·东蒙民间故事”普查采录工作的通知》,迅速展开了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在白音爱里先行试点采录;对重点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保护故事传承基地,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边普查边出成果,向自治区五十年庆典献礼。”[29]8-112008年,十二卷本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出版,2018年,《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第二部十二卷本出版发行,24卷共收集了1544篇故事,共计1009万字。这套丛书被学界称为是民间故事界的“二十四史”。该丛书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喀喇沁及东蒙各部的蒙古族由游牧转向农耕的曲折历程,蕴含着鲜明的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特色,“不仅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工程,贡献了一处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展示平台,也为世界心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地域各民族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关注的窗口。”[29]21
喀左以非遗保护为重点,同时也加强了“整体性保护”,到2017年,国家民委公布的两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中,喀左县共有四个村入选,分别为白音爱里村、三道营子村、东官村、十家子村。以白音爱里为例,该村拥有集群性海青格热,县政府明确提出对村内的海青格热民居实施分等级保护与修缮,并制定出了“打造农耕蒙古族民俗文化品牌,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规划。2013年以来,白音爱里不仅建造了文化娱乐广场,整修了部分海青格热民居,而且陆续在聚落附近的山下开发修建起蒙古族风情园、跑马场、射箭场、垂钓场等观光旅游及娱乐设施,开始吸引一些远近游客。2015年,当地政府已开始筹划将白音爱里申报国家住建部等部门审定的中国传统村落。
为打造特色村寨,喀左县扶贫开发局将白音爱里村列为整村推进重点村;县体育局提供体育健身器材;县文化局为村里图书室建设提供图书;县交通部门为主要街道实施硬化治理工程;县旅游局也将白音爱里村纳入全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2008年,朝阳市民委在喀左县南哨街道白音爱里村开展了“建立民族语言文化生态保护基地”[30]的试点工作。2009年,白音爱里被列为“全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试点村”。2012年,在白音爱里村东的一座高山上,建造了一个敖包,到2019年共举办了第五届敖包文化艺术节。
“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目的在于实现非遗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然而,怎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和旅游开发相结合,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四、从社区营造到区域再造
辽西蒙古族地区蕴含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下,部分人文资源得到了发掘,但“这种自上而下、自外向内的保护方式推进下,并不意味着作为辽西蒙古族民族身份表征的传统文化就会自然延续”[31]。这就要在整体观的视角下发挥多元主体的合力作用,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在政府层面,高质量发展要求“抓紧开展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1]。在地方层面,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当地民众积极主动的参与。在实现二者有效地结合中,可以借鉴社区营造的相关理论。“社区总体营造”简称“总体营造”。“总体营造”致力于为社区“造血”而不只是“输血”,主要包括民间自主能动性、市场需求推动、社区自组织(社区居民主动性)、政府引导,NGO帮扶,文化创意等。在近年来,又提出了“要在兼顾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将全球、国家、地方与社区结合起来,从环境、社会、经济等面向实现社区的永续发展”[32]。可见,总体营造有如下特点:第一,强调政府的“顶层设计”与“主动出击”。第二,在营造过程中要将地域性“特色文化”“特色产业”以及二者融合作为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突破口。第三,要激活地方民众,并发挥多元主体的合力作用。第四,在全球化时代,进行社区营造、实现永续发展也是社区的未来。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国家顶层设计要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将社区营造上升到区域营造[33],以实现区域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进入21世纪,地域景观的发现、再造与民族文化的活化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辽西蒙古族高质量发展,需要“借用民族符号,活化文化产品”,需要“具有自身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同时配合大规模的商业运作,通过这种运作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再生产”[34]。这就要发挥国家顶层设计与地方积极行动的合力作用,需要在总体营造理念的指导下,发挥多元行动主体的合力作用,以实现区域再造与永续发展。这是实现辽西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蒙古族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结 语
在全球化时代,原本封闭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已转换为“流动的村庄”;原本以土地为生的乡民已经离土又离乡。随着“乡土本色”渐渐淡去,后乡土社会的地域景观变得陌生,民族文化变得疏离。从后乡土时代到新乡土时代,不仅仅是时间的变化,而且在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中,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复兴中,首先需要在总体营造理念下,通过开展以文化为核心的经济生产,以文化生态场为资源,在塑造社会记忆的同时,“再次确立以自然、历史、文化为轴的生活方式”[35],逐步形成新的、适应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魅力故乡”。其次,需要重塑民众与社区环境在“人”的层面与“社会”的层面的关系。最后,通过对当地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来实现区域再造与“人”的再造。可见,总体营造所开展的对社区空间的重塑和生活共同体的再造,可以凝聚社区乃至区域意识,并建立文化认同,以此促进区域再造与区域的复兴。
总之,辽西历史文化资源厚重,文化多样性鲜明,从渔猎、游牧,到农耕,再到今天的生态文明,在该区域都有很好的展示。在高质量发展中,如何将上述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式串联、整合起来;如何将当地独特民族民俗文化活化;如何实现从景观到遗产、再到资源的转化;如何在构筑精神家园的同时,凝聚共识、增强认同,以实现永续发展,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中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