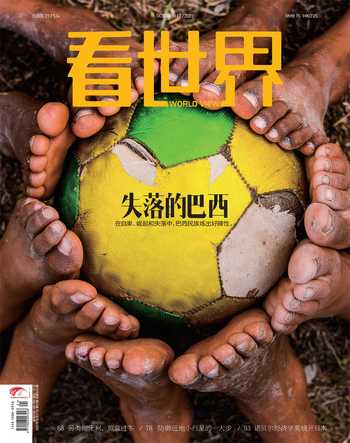“后种族”巴西,告别自卑
何任远

2008年,巴西圣保羅,人们在日本社区欢迎德仁皇太子
十年前,波兰女孩苏珊娜在广州学习中文。在那时,她还是一个典型的中东欧女生:喜欢化淡妆,穿修身的长裙,留金黄色长发,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斯拉夫女性。约莫在2016年,她认识了同样在广州工作的巴西男友布雷诺,俩人最终成婚。
在婚后,苏珊娜的外貌开始发生变化:她更爱浓烈颜色的眼妆和更加鲜艳的唇膏,发型也变得颇具南美洲的奔放味道。离开中国后,她跟丈夫布雷诺往返波兰和巴西两国生活,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苏珊娜的丈夫布雷诺,尽管外貌是典型的南美拉丁人,姓氏却不同寻常:他姓“前地”(Maeji),那是一个日本姓氏。布雷诺的祖父来自日本,属于19世纪末到二战前夕移民到南美的那一代日本侨民。
1917—1940年,约16万日本人移居巴西,让巴西成为了拥有最庞大日本侨民群体的南美洲国家。这些巴西日本侨民的75%定居在圣保罗,多数在咖啡种植园里工作和生活。跟中国在外漂泊的单身男性不一样,日本劳工倾向于举家迁往南美,毕竟微薄的薪酬难以让当年的男性务工者支付回日本的路费。第一代日本劳工,除了跟家人在当地生活到生命终结之外,基本上别无退路。
跟那些没能回到日本故土的日本侨民一样,布雷诺的祖父逐渐在巴西扎下根来。随着后代跟其他文化背景的对象通婚,到了布雷诺这一代,子孙的外貌基本上跟南美拉丁人没有区别。可是,为了缅怀祖父的日本根源,这个糅合了多层血统的家庭,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日本氛围。
“我丈夫的家庭到目前依然坚持吃日本菜,也有严格的日本家教,遵循日本传统家庭的礼数。”跟丈夫结合后,苏珊娜的名字前也填上了“Maeji”这样一个来自日本的姓氏。
多年来,日本侨民与巴西政府并非没有摩擦。早在1920年代,日本侨民在巴西就形成了一个凝聚力颇强的社区。在当时的日本帝国外交部支持下,日本侨民接受日文学校的教育,自己圈地种菜,并且禁止与外族通婚。他们试图在巴西的土地上建立纯粹的日本社区,遭到了巴西中央政府的谴责,舆论风评也不好。当时的巴西社会认为,日本侨民试图推行他们自己的一套“quistos raciais”(种族隔离)政策。
到了二战时期,巴西与日本分属两个阵营。两国在1942年断交后,日本侨民在巴西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直到二战结束前,日本侨民在巴西不得随便迁徙,在公众场合说日语会面临刑事处罚,日语报章和书籍更加成为非法出版物。
二战结束后,当地日本侨民的境况开始出现逆转。日本侨民的勤劳性格开始获得巴西社会的肯定,战后日本腾飞的经济多少也为侨民的颜面增光。随着与异族通婚的日本侨民数量增多,不少侨民最终选择返回日本,剩下的侨民后代更愿意说巴西葡萄牙语,那些纯粹的东方脸孔还是越来越少了。
苏珊娜对记者说:“我的孩子看起来也不像亚洲人,因此他们在巴西社会里被认为属于白人群体。”

巴西圣保罗最大的日本塔
他们试图在巴西的土地上建立纯粹的日本社区,遭到了巴西中央政府的谴责。
在南美洲国家中,巴西可以被视为一个异类:它是唯一一个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南美国家,几乎完全被西班牙语国家包围;它是唯一一个由原殖民宗主国王室和统治阶层一手操办宣布独立的南美国家,巴西建国期间树立起的民族意识中并没有自下而上的抗争传统。
巴西有1. 2亿国民具有非洲血统,占了该国总人口的56%。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在巴西建国200年来试图塑造一个“巴西民族”的历程中,国内种族关系的融合政策,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是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结果。在20世纪早期,这种自上而下的种族整合政策往往“偏右”,指引思想是纯粹的种族主义。
在1888年结束奴隶制后,大量非裔奴隶被解放,而让白人殖民者感到大为紧张的,是“巴西黑化”的问题。讽刺的是,在废除奴隶制一年后,巴西君主制被推翻,军政府取代了原本愿意推动废奴事业的巴西皇室。巴西共和制度的开端,就是伴随着充满种族焦虑的军人专政开始的。
在当时的军政府白人精英阶层看来,巴西要“现代化”就必须以欧洲民族国家为楷模,控制有色人种在国内的人口数量,打造一个被“提纯”的、以白人为主的天主教社会。在这种思维下,以军政府和中产阶级为执政基石,巴西主政者崇尚白人文化,以“白化”为目标,以“黑化”为诫。
从1920年代到二战结束前,巴西国会出现富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动议,包括“禁止黑色人种个体移民巴西”以及“亚裔人种移民巴西数量每年不得超过巴西国内原族群的5%”等;巴西的主流媒体在很长时间内也充满种族主义色彩,把亚洲移民称作“难以驱散和稀释的硫黄”。直到如今,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一句“我的肤色,就是巴西的颜色”,依然被认为是流露出某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感。
在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下,日本侨民实际上被视为阻碍军政府“白化”政策的不受欢迎群体。但亚洲侨民远非受巴西军政府长期打压的最底层群体,因为巴西有着世界上除非洲以外最大的非裔人群。

1887年,巴西公主伊莎贝拉

2013年11月20日,巴西舞蹈音乐家们在“黑人觉悟日”表演。该节日是为了纪念1695年巴西原住民部落领袖祖比遇害而设
根据2022年的巴西人口普查数据,巴西有1.2亿国民具有非洲血统,占了该国总人口的56%。其中,“深色肤色人种”(preto)占总人口的7.6%,有43%属于带有黑人血统的混血人种(pardo)。数据显示,2000—2010年这十年是这两个族群人数激增的阶段。随着巴西人口构成的改变,巴西的社会面貌和文化意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听说巴西也挺多黑人的,是不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一次与巴西总统的聊天中,轻描淡写地问了这样一句。
16—19世纪,共有400万黑奴被带到这片土地上,他们一直到1888年为止,都是在种植园里没有基本权益的奴隶。在19世纪末西方种族优生学的思维影响下,这个族群被认为智力低下并且崇尚暴力,他们的文化长期被歧视和打压。用巴西黑人权益活动家和文学家莱莉雅·冈萨雷斯的话说:“巴西的种族主义在于否定和抹去我们的文化和面孔。”
随着军政府在1985年走向瓦解,巴西社会反思过去的种族政策,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让巴西的有色人种为自己的文化、历史乃至身体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过去,巴西女孩子连自己的头发都觉得丑。而这种自卑的心态,正是巴西黑人权益活动家希望导正的地方。再譬如,黑人学者着手挖掘非洲黑奴在逃离种植园后自发形成的社区历史文化遗产,让巴西黑人文化的历史渊源一下子延长了许多。
在过去多年的书写中,巴西公主伊莎贝拉被认为是推动废除奴隶制的关键人物。但在当下黑人运动的推动下,这种以白人为书写中心的自上而下历史叙事被推翻。在黑人活动家看来,奴隶自身的反抗带动社会意识,才是巴西奴隶制寿终正寝的关键。
自二战结束后,巴西政府一直推崇“种族民主”社会制度,也就是所有国民无论种族,都可以参与国家日常的民主生活。用巴西社会学家吉尔伯托·福莱尔的构思来形容,那就是巴西进入20世纪的民族构建时期,种族分野即将成为过去,随着一个糅合东西南北的巴西主体民族崛起,巴西社会将会进入“后种族”时代。
波兰人喜欢抱怨;而在巴西,生活的乐趣是基本价值观之一。

在51a1ca8417120495c94ba04aae79310b过去,巴西女孩子连自己的头发都觉得丑
即使是在军政府时期,巴西的“种族民主”制度也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优于美国南方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二战期间欧洲大陆的排犹主义情节。德国犹太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流亡到巴西后,一度认为这里的种族和文化隔阂比纳粹德国少得多。那些厌倦了旧大陆狭隘民族国家思潮的知识分子,一度认为巴西是指向未来的新国度。
当然,“种族民主”有这样一道后门:那些被归类为“文盲”的人群,被剥夺参与选举和政治活动的资格。而哪些族群最容易被归类为“文盲”?那就是诸多印第安原住民和黑奴后裔。推广识字率,让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巴西社会发光发热,也许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苏珊娜看来,某种程度上,巴西人已经提炼出某种文化特质。“这里的生活方式也很有吸引力,与我来自的国家波兰不同。例如,在波兰,牺牲被视为一种价值观,生活更像是一系列需要克服的困难,而在巴西,享受生活是值得向这里的人们学习的事情。”
“有趣的是,波蘭语中没有‘享受’这个单词。波兰人喜欢抱怨;而在巴西,生活的乐趣是基本价值观之一。有时候我去理发店的时候,店主会为客人们提供免费的气泡酒,这真的是在其他地方闻所未闻。”
让所有文化背景的国民参与国家的建设和巴西主体民族的构建,巴西的文化面貌变得千色多元。就好像是一个还没被充分发现的宝库一样,巴西社会的隐藏族群到近年还依然不断重新浮出水面。譬如,一个隐藏在巴西南部的波兰移民小镇,在今年才被挖掘出来。这个与阿根廷接壤的边境小镇,在1906年由一群波兰裔移民建立。如今,这个小镇的居民有90%依然自认为具有波兰血统。
这个小镇在经过波兰媒体曝光后,终于成功获得了把波兰语注册为该镇官方语言的权利。当然,他们的波兰语是100多年前的波兰语,是没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洗礼的老式波兰语。
用苏珊娜的话来说:“南美原住民、非洲文化、意大利和葡萄牙移民,甚至中国、波兰或德意志移民,所有这些都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整体,品尝起来就像我们品尝巴西国菜feijoada一样。”
特约编辑姜雯 jw@nfcmag.com
——以美国、爱尔兰和印度为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