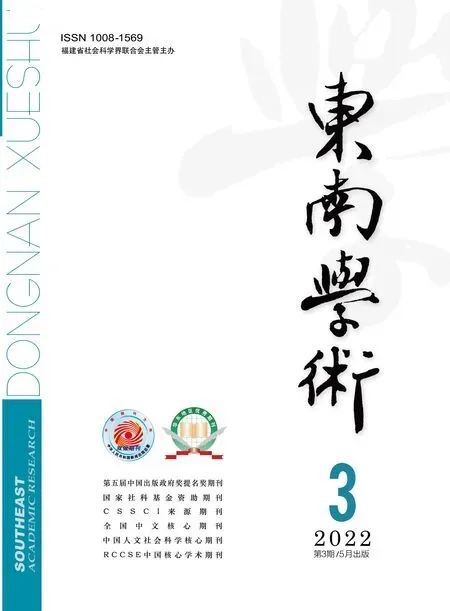从训蒙工具到参与建构中华传统文化
——“位列”诗在清代民间的流布与转身
黄科安
俗曲唱本是一种说唱的文学,题材广博,涵括了中国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社会新闻、劝世教化等内容,在明清之际的中国民间社会颇为流行。笔者在校勘、研读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东方图书部收藏的一批清代唱本以及台湾地区图书馆收藏的《台湾俗曲集》时,(1)关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东方图书部收藏的清代木刻版唱本和台湾地区图书馆收藏的《台湾俗曲集》的详情,可参考黄科安:《清代木刻版闽南语歌仔册考释》,《中国音乐学》2020年第3期。有趣地发现清代民间广为流布的一首五言诗隐匿于其中。该诗无题名,具体文本是:“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克己由乎礼,存心本以人。”该文本共计30个字,是一个较全的文本;而一般的通行版文本是前4句。遵从前人的惯例,笔者遂取该诗开头“位列”二字,当作它的名称。
应该说,该诗很不起眼,名不见经传。其通行版文本首次出现在明代《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随后清代诸多的民间文化领域如蒙学、宗教和说唱文学等,不断闪现其“身影”。那么,该诗为何在清代如此广为流布?它到底有何不为人知的身世和文化内涵?清代民间艺人对其进行过哪些创造性的移植和编创?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尝试通过多种路径的稽考,以期揭示该诗如何以“小”见“大”、从“边缘”靠拢“主流”、从训蒙工具转向参与建构中华传统文化。
一、现象揭示:从训蒙字帖到辑录于《神童诗》
在传统中国,由于蒙学教育的发达,蒙学教材层出不穷,据学者统计有1300多种。(2)参见徐梓、王雪梅编:《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338页。蒙学读物有识字写字、伦理道德、诗歌教育、历史教育、自然常识等不同类型,类型指向不同,其发挥的功能自然也就不一样。笔者发现,在清代蒙馆里有两首诗常被用于识字、习字的描红字帖,一首是“上大人”三言诗,该诗自唐末开始流行,宋元明清时一直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关注,一些文献典籍对此有颇多记载,关于此诗笔者将另文探讨;另一首就是“位列”诗,其知名度没有“上大人”诗显赫,清代之前的史料对此也少有记载,但该诗在清代甚为流行。
有两则材料可以佐证这一文化现象。一则是湖北文史研究馆馆员朱国南回忆清末自己在蒙馆所学内容时称:“清末蒙馆的课程主要是经书,如《三字经》、‘四书’、‘五经’。其次是习字,其他如‘上大人,孔乙己……可知礼’等红影本的内容,也是初入塾的蒙童必读必写的东西。读熟了,才换影本。什么‘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伦先父子,八卦定君臣’……均是清末蒙馆儿童必读之物,且须读得滚瓜烂熟。”(3)朱国南:《清末民初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湖北文史》2004年第2期。这则材料说明,当时湖北江汉平原一带的蒙馆曾将这首“位列”诗列入作蒙童入门习字的描红字帖。另外,朱国南在此回忆中有一句“五伦先父子”与通行版文本“五行生父子”有出入,这是朱国南回忆有误,还是该诗在流行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有待考证。
另一则是台湾著名企业家吴修齐回忆民国初年祖父对他进行蒙学教育时,也提及学习该诗的情形:“记得在无忧无虑的童年,他教我念:‘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位正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他教背三字经,还教我写字。”(4)吴修齐(1913—2005),台湾统一企业董事长、“台南帮”领袖。参见谢国兴:《吴修齐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可见,在清末民初的闽南语流行地域,“位列”诗与“上大人”诗一样,都被塾师或长辈视为蒙童习字的教材。这里还需特别指出,吴修齐的回忆也有出现与通行版文本不同的现象,通行版首句是“位列上中下”,而吴修齐回忆的却是“位正上中下”,此句中的“列”被改为“正”。然而,从句子语意观之,应该是通行版的“列”字比“正”字讲得通。那么,为什么吴修齐会取“正”字,难道是他晚年追忆出现的差错?不过,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时,意外发现闽南区域乃至台湾地区流行的版本均弃“列”取“正”,从清代闽南语歌仔《位正花会歌》,到20世纪30年代台南市印行的描红字帖均属于此类情形。(5)参阅《海国春来似画图:且道台湾古雕版余韵流风》,2012年5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zhangzhigongfang。需要追问的是,当时闽南人为什么在传授该诗时会弃“列”取“正”,是底层庶民识字不多,在流播过程中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现象,还是“列”字显然比“正”字难写且笔画多,不利于儿童初学者的描红而被更替?在笔者看来,后一种推测更有可能,这主要是与“位列(正)”诗在蒙学教育领域的定位相关。作为为初入蒙馆的小孩准备的仿字或描红,笔画简易而又能代表汉字最基本字型结构的字,才是优先选择。这样看来,“正”字显然胜过“列”字。
那么,“位列”诗仅仅扮演蒙童习字初阶教材的角色吗?其实不然,笔者在追索其踪迹的过程中,发现它还以一首富有文化内涵的诗作而被小儿吟诵。最突出的事例是越南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阮朝嗣德十六年(1863,清同治二年)学文堂本《幼学五言诗》,该书末页刊有“辛巳之岁孟春幼学书成”。所谓的“辛巳年”,即阮朝明命帝阮圣祖明命二年(1821,清道光元年),这意味着该书在1821年就已编成。(6)参见刘怡青、徐筱妍《越南〈幼学五言诗初探〉》的注释2,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5页。该书正文共计270句,最后4句以“位列(正)”诗作收束:“位正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该诗也是以“正”字取代“列”字,看来此类变化并非闽南区域所独有,因而不属于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据考,越南《幼学五言诗》主要以流行于广东的《训蒙幼学诗》进行改编。而《训蒙幼学诗》又被称为《状元幼学诗》,现存35首五言诗共136句,成书年代不详,属于清代广东版的蒙学教材。
广东流行的《训蒙幼学诗》,其祖本是从传统蒙学《神童诗》编改而来。相传,北宋汪洙从小善赋诗,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于是,后人将其诗作和他人作品混编成集用作训蒙读物,并以“神童诗”名之。清代翟灏对此有过考证,且持类似意见:“其前二三叶相传皆汪洙诗,其后则杂采他诗铨补。”(7)翟灏:《通俗编》卷七,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54页。一般说,通行本《神童诗》为34首,另有些版本增加卷首诗24首或28首。(8)本文所采纳的《神童诗》篇目数据源于:谢宝耿主编:《中国蒙学名著鉴赏辞典》,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杨文丽:《中国古代主要蒙书叙录》,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9页;刘静芳:《科举制度下的明清蒙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1页。经研究比对,广东的《训蒙幼学诗》完整引录《神童诗》的诗作有6首,其余诗作则是在辑录基础上进行的改写与扩编。但是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笔者翻遍了《训蒙幼学诗》,也查阅了全国出版社整理或翻印的一些与《神童诗》相关的蒙学典籍,却始终找不到这首“位列”诗的踪迹。那么,越南编的《幼学五言诗》所出现的“位列(正)”诗从何而来呢?难道是受到流行于中国的蒙学描红字帖“位列”诗的启发而辑录的,抑或是清代还存在一种鲜为人知且有异于一般版本的《神童诗》?
正当笔者为此大惑不解之时,却意外从一则新闻报道中获得重要线索。该报道称,市民赵师傅从一位村民手中淘得一本较为珍贵的清末石印《三字经》,并附有图片。该书正文内容分上下两栏,上栏是《神童诗》,下栏为《三字经》。其中,《神童诗》的大部分诗作与流行于全国各地的版本大致相似,最大的差异是此书辑录了“位列”诗,即:“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也。”(9)张春茂:《临汾赵师傅:清末石印〈三字经〉》,2019年11月16日,https://linfen.focus.cn/zixun/e0b3b16e3f30b544.html。该报道充分表明,清代《神童诗》在个别版本中确实有将“位列”诗辑录在内的现象,越南编的《幼学五言诗》是有本可依的,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难寻踪迹。因此,“位列”诗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仅仅作为训蒙初阶的描红字帖,它还有另一面,即作为“神童诗”的诗作之一,在蒙学教育中享有难得的文化尊荣与美誉。如此一来,该诗定有不凡的身世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二、探源溯流:从易儒结合到儒释道杂糅
按理说,“位列”诗在清代如此普遍与流行,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应该有明显的来历与身世。可是,笔者经过一番文献的稽考钩沉,却发现直接记载“位列”诗的相关文献异常稀少,其历史线索也晦暗不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对该诗进行考释。如前所述,它在清代蒙学领域不仅被用作于习字的描红字帖,而且被辑录在《神童诗》内,这一切均指向博大渊深、一脉相承的中华传统文化。
“位列”诗的完整文本为:“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克己由乎礼,存心本以人。”其关键的文化内涵在于前4句,这些诗句的核心思想可追溯至中华传统文化宝典《周易》。《周易》又称《易经》,由“经”与“传”两部分构成。一般认为,“经”的形成经历了伏羲画八卦、文王著卦爻辞(也有一说,文王著卦辞、周公著爻辞)的过程;而“传”被认为系孔子所撰,《易传》共有10篇,又称“十翼”,即《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以及《杂卦》。(10)宋代欧阳修对《易传》均为孔子所作提出疑问,由此开启了对《易传》的疑古风潮,此风潮在清代至民国时期尤盛。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易传》作于“春秋战国期间,经传作者均非一人”,当是孔子及其门徒完成。因此,班固在《汉书》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11)班固:《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武英殿本。即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此二圣代表“经”的完成;而孔子为下古,其撰著的“传”通过创造性的解读与诠释,使易学与儒学形成一种互为激发、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
所谓“易道深矣”,宜从两个层面观之:一方面,通过孔子及其后世儒者的诠释,先前被视为卜筮之书的《周易》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开启了经典化进程。何谓为“易”,唐代孔颖达阐释:“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12)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周易注疏》,清阮元刻本。人文始祖伏羲观变阴阳而立卦,其所画的八卦由三画构成,上代表天,下代表地,中间代表人,“天地人”合称为“三才”,这就是“位列”诗所谓的“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不过,“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1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571页。先前的易学凭借筮法的特点演绎阴阳法则,透过钩沉筮法的体例揭明吉凶之理。到了春秋时代,孔子赋予《周易》儒家义理,认为《周易》是德义的渊薮。而阴阳运行,刚柔相推,易道周流,生生不息,揭示了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因而,《周易》被后世尤其是汉代之后的儒者尊崇为群经之首。
另一方面,《周易》中的“易道”为孔子关注世事人伦找到了立论的基石,助力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571页。从天道中的“阴与阳”、地道中的“柔与刚”,再到人道的“仁与义”,孔子对“易道”的阐释显然带有儒学印记。因为孔孟儒学以“仁”贯通天下,连接天道、地道与人道,由此构成人伦秩序,并作为社会人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15)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599、493页。《系辞》亦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6)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599、493页。这就把亲亲尊尊等伦常道德体系置于天经地义的原则框架之下了。另外,五行与八卦也有对应关系:金为乾、兑,火为离,木为震、巽,水为坎,土为艮、坤。而“五行生父子”是根据八卦方位和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决定并形成家庭伦理次序及其关系的。因而,“父子”“君臣”就有了“上下”之别、“尊卑”之分,这也是“位列”诗中所谓“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的来源之意。
在翻阅后世儒者探讨《周易》的相关文献时,笔者发现“位列”诗中的“八卦定君臣”一句,曾出现在宋人张文伯撰著的《九经疑难》(17)张文伯:《九经疑难》卷二,明祁氏澹生堂抄本。中。张文伯从伏羲观“天地人”而立三爻(三画)卦说起,天充阳气,画三阳爻表示乾卦;大地聚集阴气,画三阴爻(六画)表示坤卦。乾坤相求而生六卦(震、巽、坎、离、艮、兑),如此成就八卦,父子男女的伦次规则已具备矣。他将八卦用于表示八方,乾位居西北,表示父道,父道重视尊严,西北方是肃杀严懔之气最旺盛的地方;坤位居西南,表示母道,母道重视养育,西南方是最适宜万物生长的地方,而万物成熟在乾位(秋冬),故其功归于乾;震、坎、艮的方位不依次排在靠近坤位的地方,而是依靠在乾位,表示依从于父,此三位(东、北、东北)分别表示长子、中子、少子;巽、离、兑依靠在坤位,排位在子位之后,此三位(东南、南、西)分别表示长女、中女、少女。显然,张文伯的“八卦”论述,旨在借重“天道”以定位“人道”,推行“易道”以明了“人事”,从而为尊卑长幼的封建伦理纲常张目,此所谓“八卦定君臣,男女父子之位”也。
据考,“位列”诗的通行版文本(即该诗前4句)最早出现在明代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18)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明万历十年高石山房刻本。编者为戏剧家郑之珍。该戏文下卷《五殿寻母》中记述道:“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六龙杖凤辇,一样定君臣。”接着,是“末”“外”出场的自我介绍云:“自家乃阎罗天子殿前判官鬼使是也。今当我王升殿,只得在此伺候。”可见,“位列”诗的援引其实是君臣秩序的一种体现。不过,上述4句诗与“位列”诗通行版文本还是有出入,主要是后两句有些差异。第3句“六龙杖凤辇”,完全是根据戏文具体情节改写的,铺叙阎罗王作为“君王”的身份排场,诚如戏文所言:“天上至尊惟玉帝,人间最贵是君王。天人两下皆兼理,地府阎罗独主张。自家阎罗天子是也。”第4句“一样定君臣”,是将过去熟悉的“八卦”二字改为“一样”,抽去了易学的内涵而糅合了儒释文化,旨在告知即便是阴曹地府也有“君臣”之分。如,阎罗殿前有听差的判官与鬼使,而阎罗王作为最高统治者“职掌中央,如土贯五行之表,位居五殿,即信成四德之中。东西南北尽皈依,天地鬼神皆统属”。阴曹地府的伦理纲常其实也是人世阳间的翻版,而阎罗王的威严与独尊由此可见一斑。儒家的伦理纲常挪移至佛家世界,呈现出儒释杂糅的文化流向。
进入清代以后,“位列”诗流入宗教徒的日常活动。其一,甘肃北石窟寺留下的墨迹,即第178窟的南壁门上有书云:“大清乾隆六十年二月……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19)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著:《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据说该诗是由流落至此的八卦教徒写上去的。(20)刘治立:《明清时期的北石窟寺》,《陇东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所谓的“八卦教”,是康熙年间山东刘佐臣按《八卦图》“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组织形式创立的,属于儒释道三教杂糅的民间宗教。“位列”诗成为规范八卦教徒日常行为的一种口诀。其二,八卦教的一支派后来演变成嘉庆年间反清的天理教。据清代托津等纂修的《钦定平定教匪纪略》记载,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等人以宗奉的经书有“白洋劫”等谶言为由,密约于九月十五日起事,插白布小旗,写“奉天开道”,以是记号,另有四句话:“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21)托津等纂修:《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清嘉庆武英殿刻本,第33页。后来,清末民初徐珂在编撰的《清稗类钞》“天理教”条中亦称:“今岁孟冬,一月中行三节气,此即白洋劫,劫前七日白旗传遍,凡无旗者杀,杀之留而不杀者,分上下,其要诀云:‘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22)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四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73页。此时的“位列”诗已由规约教徒内部行为举止的口诀,摇身一变成为教徒反清起事时的通关“暗语”,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江湖行话”。
从该诗的流传中可以看出,八卦教和天理教自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位列”诗作为天理教反清起事时之口诀,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文化想象空间。因此,该诗在清代宗教活动中的流布,显示出其不同于蒙学领域的面目与作用,也为其神秘的身世平添几分宗教色彩。
三、劝世讽谕:民间说唱的移植与创编
“位列”诗在清代之前基本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可是在此之后却广为流布,其流向呈现出三个领域:蒙学、宗教和说唱。前二者上文已有所述,本部分着重探讨对该诗的移植与创编。
从易学视角出发,直接传承和移植“位列”诗的是清代评话小说《小五义》,其刻本由北京文光楼于光绪十六年(1890)刊行。其刊行时间虽属于晚清,但据出版者文光楼主人石铎在《增像小五义序》中云,此书为著名民间艺人石玉昆的原稿,石铎花重金从石玉昆门徒手中购得。石玉昆何许人也?崇彝称:“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23)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阿英根据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43—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有《叹石玉昆》一目,判定石玉昆应系“道光时说书人”。(24)阿英:《关于石玉昆》,《阿英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由此可见,《小五义》极有可能是石玉昆在道光年间说书的一个内容。
说书人石玉昆在编创《小五义》时顺手拈来,将这首流行于乾嘉年间的“位列”诗引入故事情节的设计中。襄阳王赵珏为了谋逆造反广结党羽,并将一份盟单存放于冲宵楼。为了防范他人盗取,他不仅在府邸设下木板连环八卦连环堡,而且在冲霄楼也巧设机关:“冲霄楼三层,有五行栏杆,左有石像,上驮宝瓶;右有石犼,上驮聚宝盆。宝瓶、聚宝盆两物当中,有两条毛连铁链,当中交搭十字架,两边挂于三层楼瓦檐之上。此楼三层按三才,下面栏杆按五行,外有八卦连环堡。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前有两个圆亭,左为日升,右为月恒。铜网阵在于楼下。”(25)石玉昆:《小五义》,《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可见,说书艺人在介绍该楼的营建结构时,将四句“位列”诗文本穿插其间,其目的在于体现巧设机关的易学文化理念。外号“锦毛鼠”的白玉堂,显然对此处设计的“八卦连环堡”阵图颇为稔熟,并通过八卦方位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轻而易举地闯到冲霄楼的楼前。接下来,文本记述了“黑妖狐”智化故意考问白玉堂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白玉堂机械拆解这首“位列”诗的含义,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他以为八卦阵图无非如此而已,忽略了该楼底下还设有一个“铜网阵”,最终,骄傲轻敌的白玉堂闯关失败,坠网身亡。由此观之,编创者移植“位列”诗于说唱文本中,旨在透过八卦数理、阴阳五行机制来建构“八卦连环堡”,借以彰显其间所潜伏的吉凶祸福之玄机,从而达到渲染襄阳王处心积虑“造反”之目的。然而,易学文化的相生相克反而让一些所谓的“聪明人”到头来还是一枕黄粱梦,反误了卿卿性命。
如果说,“位列”诗在《小五义》中侧重于渲染易学“术数”一路,那么它流入清代俗曲唱本所起的作用则重在发挥易学“义理”的面向。从现有文献来看,“位列”诗流入清代的俗曲唱本可追溯至华广生编的《白雪遗音》。该俗曲集于嘉庆九年(1804)编订,道光八年(1828)由玉庆堂刊刻。“位列”诗辑录在《白雪遗音》的“八角鼓”一栏,具体曲词为:“才分天地人,八卦定君臣。五行生出父子恩,阴阳配合夫妻顺。兄友弟恭朋友信,此所谓,十义纲常人之五伦。诗书易礼,春秋学问。钟鼓礼乐把玉书分,教化流传孝悌忠信。自古至今,谁不敬,万代为师的孔圣人。”显然,与“位列”诗通行版文本相较,该曲词不仅缺了首句“位列上中下”,第3句“五行生父子”也被改为“五行生出父子恩”,且位次置于“八卦定君臣”之后。该曲词的主旨在于传递儒家思想与文化,所谓“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而“诗书易礼,春秋学问”,是指《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五本文献,儒家尊之为“五经”。曲词最后唱道:“自古至今,谁不敬,万代为师的孔圣人。”该曲词的编创体现了儒学透过对易学的借重,完成“纲常伦理”的建构,从而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该曲词还十分推崇包括《周易》在内,代表夏商周三代王官之学的“五经”。这是孔子及其后世儒者通过不断地收集、整理、诠释,才最终完成建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化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备受后人景仰,并被尊为“万代为师”,乃实至名归。可见,改编后的“位列”诗作为“八角鼓”演唱的一首曲词,是满人入关后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江山而选择尊崇儒家思想,主动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圈的一个生动注脚。
而在清代东南一隅的福建南部及其台湾的闽南族群,“位列”诗不仅流行于训蒙识字领域,还出现在民间方言的俗曲唱本中,闽南人习惯称此唱本为“歌仔”或“歌仔册”。现存清代最早一批的闽南语歌仔分别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东方图书部和台湾地区图书馆。其中,牛津大学藏本《选刊花会新歌》镌于道光七年(1827),内收一首《位正花会歌》;而台湾地区收藏的《台湾俗曲集》也有辑录一首《当今花会歌》,未标明刊刻时间。经比对,《位正花会歌》与《当今花会歌》虽题名有异,但具体文本一致。由此观之,这应是清代书商在不同时间刊刻的同一首歌仔,但为了吸引读者眼球略施小技,更改了题名。
那么,“位列”诗在闽南语歌仔《位正花会歌》中是如何呈现的?以具体文本为例:
位至九官心志高,正顺和气家合同。上招合伙去经商,中心扶国汉云长。下船合海出江游,才源银玉真得意。分开福孙去耕田,天龙化入青云上。地上起庙龙江祠,人心意爱光明就。五子相争夺占魁,行到坤山砍茂林。生财有利得明珠,父做火官心元吉。子孙意愿板桂来,八拜观音会如来。卦念只得三槐事,定国安邦是太平。君王坐位青元殿,臣办国家陈安士。克得五谷逢春时,已时行到日山中。由你去做天申愿,乎烦吉品不成熟。礼路叫化徐元贵,存忠存义必得官。心中爱得荣生儿,本多经商井利闹。以爱天中月宝照,人人都爱万金富。花会有三十七名,大男小女想卜赢。此是位正来凑是,读了就知有分字。(26)吴守礼校注:《清道光咸丰闽南歌仔册选注》,从宜工作室(台湾)2006年版,第66-67、86-87页。
该歌仔为七言歌词,每两句为一联,长达34句。其题名为《位正花会歌》,可是直接与这一题名相关的只有最后4句歌词:“花会有三十七名,大男小女想卜赢。此是位正来凑是,读了就知有分字。”所谓“花会”,清人欧阳昱曾有详细记述:“东南赌之最著者,无过福建花会。其法用三十六字为轮转。主花会者,先暗写一字,以纸裹悬梁上,下用大案,排列三十六字,欲押某字者,即以钱放其字上。自一枚以至十百千万皆可押。中者,一枚偿三十二枚。”(27)欧阳昱:《见闻琐录》,恒庵标点,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33页。不过此处用法是“三十六字”,歌仔是用“三十七名”,大概花会在闽南地区流行过程中用法有些变异,但均大同小异。可见,“花会”并非字面所理解的鲜花博览会,而是清代前期在闽南地区流行的一种赌博形式,参赌者只要押中其中之一即可获利30余倍,因而极易引发民间社会“大男小女想卜赢”的疯狂行为。可是,除了这两句歌词以外,该歌仔其余文字均未直接涉及“花会”相关内容。既然如此,为何题名还要与“花会”沾边呢?再者,“此是位正来凑是”其中的“是”疑为“事”,是闽南方言的借音字,那么用“位正”来凑什么事呢?
其实,解开该歌仔的密钥在于最后两句:“此是位正来凑是,读了就知有分字。”让“位正”来凑事,且读了能“知有分字”,难道是将蒙学领域当作描红的那首“位列(正)”诗移植进来了?如果是,它隐匿在哪里?其实该歌仔的奥秘在于,摘取每句首字便可拼出一首30字“位列(正)”五言诗:“位正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克己由乎礼,存心本以人。”原来,编歌者以游戏的心态化整为零,将“位列(正)”诗的字句拆散,再分别嵌入每一句的首位,从而巧妙地组成一首新的歌仔生命体。但是,如果人们缺乏对该五言诗及其相关知识背景的了解,就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台湾地区著名闽南方言专家吴守礼在勘校《位正花会歌》时就出现了误读现象,如“上招合伙去经商”中的“上招”被改为“相招”,“卦念只得三槐事”中的“卦念”被改为“挂念”,“已时行到日山中”中的“已”实属原刊本误植而吴校本沿袭,“乎烦吉品不成熟”中的“乎烦”被改为“平烦”。(28)吴守礼校注:《清道光咸丰闽南歌仔册选注》,从宜工作室(台湾)2006年版,第66-67、86-87页。上述文字之所以出现校勘误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上招”被改为“相招”,是从语意上去考虑,且“上”“相”两字在闽南方言中发音相同,应是方言借音字,但改为“相”就不是“位列”诗的字了;“卦念”被改为“挂念”,同样也是借音字,因为“卦”“挂”在闽南方言中发音相同,可是如果弃“卦”取“挂”,语义虽通但却失去了“位列”诗的藏头字“卦”;以“已”替代“己”,虽然让新编歌仔的语句通顺,但同样也失掉藏头诗“己”的本义;“乎烦”被改为“平烦”,在闽南方言中有“乎烦”一词的说法,即“令人厌烦”之意,然而吴氏在此将它改为“平烦”一词就不知所云了。可见,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些问题,主要原因还是校勘者没有及时发现该歌仔中潜藏的一个秘密——一首藏头的“位列(正)”诗。因而,每一位学者都应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历史文献,在具体字词的校勘过程中,最好采用下注的方式,从而既能体现校勘者的文字功力与学术水准,又不至于使文献丧失本应有的语言风貌与史料价值。
必须看到,在闽南语歌仔中,民间艺人对“位列”诗的移植与创编,所承担和表现的功能还是多元、复合的。从浅层面看,《位正花会歌》利用流行于清代蒙馆的用于描红字帖的“位列(正)”诗,移植了最完整的30个字的版本,为大部分失去蒙馆教育机会的闽南底层民众打开了一扇学习窗口,因而是继承和发挥该诗在蒙学领域的习字识字初阶功能,达到民间艺人所谓“此是位正来凑是,读了就知有分字”的写作意图。从深层次观之,该歌仔题名《位正花会歌》,说明民间艺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劝诫人们远离“花会”赌博这一社会毒瘤。然而“花会”毕竟极为蛊惑人心,那么民间艺人力图以何种方式抵御人们心中所产生的贪婪欲望呢?细读该歌仔,不难看出编歌者欲借助“位列(正)”诗所蕴含的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智慧,以达到“劝世讽谕”之目的。
当然,民间艺人在此没有简单地扮演“位列(正)”的“搬运工”角色,而是透过一场拆字编歌游戏活动,将该诗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精神主旨,作最扩大化和最充分的诠释。他们从闽南地域出发,认为底层民众的人生追求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去追求功名,“五子相争夺占魁”,“位至九官心志高”;也可以经商做贸易,“下船合海出江游”,“上招合伙去经商”;还可以拓荒务农,“分开福孙去耕田”,“行到坤山砍茂林”。人生百业,各凭禀赋。然而,无论在哪条道路上,都应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进入仕途者,“存忠存义必得官”,“中心扶国汉云长”,国之栋梁者应以忠心扶国的关云长为榜样,“君王坐位青元殿,臣办国家陈安士”;下海经商者,善于机变,敢于逐利,“心中爱得荣生儿”,“生财有利得明珠”;而专致务农者,则应“克得五谷逢春时,已时行到日山中”,懂得农时,勤于稼穑。如果说前面所提倡的这些文化理念,是基于个人应遵守儒家的纲常伦理要求,以及恪守君臣之道而阐发,那么接着歌仔提及的“地上起庙龙江祠”“八拜观音会如来”,则属于从宏观上倡导如何建构和解决闽南族群的精神信仰问题。“地上起庙龙江祠”,兴庙建祠堂是作为中原后裔的闽南族群格外重视的一项公共宗族事务,祠堂可以作为崇祖敬宗、敦亲睦族之场所,旨在引导底层民众重传统、溯本原,以达到建构中华传统文化的崇儒重德之风气;而寺庙是膜拜佛教神灵的精神圣殿,旨在规训民间信众诸恶莫作、祛除贪婪、众善奉行,以达到脱离轮回。可见,这位民间艺人想通过编创歌仔,教育和影响民众远离“花会”、抵制赌博,期待还给闽南底层社会一个干净、安宁的乡土世界,其心拳拳,诚挚可嘉,令人感佩。
总之,经过上述一番文献搜证与考释,一首鲜为人知的“位列”诗逐渐清晰起来。该诗在明代之前晦暗不明、文献异常稀少,但其核心意蕴可追溯至群经之首《周易》及其儒家思想。该诗通行版文本首次出现在明代《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到了清代,该诗的传播显得异常活跃:一方面,它充当着小儿的“训蒙”工具,被广泛用于闽台两岸私塾识字的描红字帖,又辑录于小儿吟诵的《神童诗》和越南选编的《幼学五言诗》;另一方面,其文化“转身”流入宗教和说唱领域,既深度参与八卦教徒的宗教活动以及演化为天理教反清起事时之口诀,也参与评话小说《小五义》、俗曲唱本《白雪遗音》、闽南语歌仔《位正花会歌》等说唱文学之改编。这就意味着,该诗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分别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与应和之关系。由此可见,该诗虽“俗”,却含有养“正”之价值,体现了以“小”见“大”,又能从“大”收回到“小”的特点,形成在诸种领域与不同文本形式之间的扩散与传递,从而为传承和创新中华传统文化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