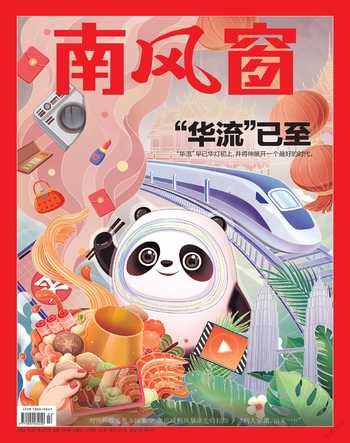谁将重塑经济的空间潜力?
何欣

过去十年,伴隨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和资金加速集聚,一批大城市快速崛起,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在这过程中,万亿GDP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2012年,中国大陆(以下同)有7座城市GDP突破万亿,而到2021年,中国万亿GDP城市已有24个,且6个城市GDP突破2万亿。
城市经济总量攀升的同时,大城市人口规模也快速增长。近日,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纸质版《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下简称“七普分县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683个城市,从规模评级来看,有105个大城市,其中,7个超大、14个特大、14个Ⅰ型大城市、70个Ⅱ型大城市。具体来说,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而300万~500万为Ⅰ型大城市和100万~300万为Ⅱ型大城市。
毫无疑问,这105个大城市代表中国城市化的最高水平,它们也将重构中国城市发展格局,而它们的分布和未来发展方向,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潜力。
众所周知,城市层级关乎城市面子,也影响城市发展资源的可得性和未来发展潜力。
在我国,关于城市的层级,主要有两种定级方法:一是,通过行政级别,划定了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层级;二是,通过城市规模定级,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将城市分为五类七档,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含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含Ⅰ型小城市、Ⅱ型小城市)。其中,城市的人口规模主要看两个指标,城市常住人口(全域)和城区人口,城区人口即城区常住人口,也是超大、特大城市的划分依据。
据此次七普分县数据,7个超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
14个特大城市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
而根据住建部在2020年底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符合“超大城市”标准的城市为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等6座。而符合“特大城市”标准的共有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等10个。
不难看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纷纷扩容,其中,成都成功升级为超大城市,且排名反超天津;佛山、长沙、哈尔滨、昆明、大连这五座城市成功晋级为特大城市。
此次唯一升级为超大城市的成都,也是中国超级强省会的代表。过去十年,成都常住人口(全域)增加581.89万人,这一增量在全国仅次于深圳和广州,位列第三。目前,成都城区人口排名第六,已经反超了直辖市天津。作为西部第一城,成都未来的潜力同样不容小觑,因为根据《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草案,2035年,成都的常住人口目标为2400万人,这一数字在全国仅次于上海的2500万,且远高于广州的2000万。
此外,在超大城市的排名中,深圳反超重庆、广州,坐上了第三的宝座。要知道深圳的常住人口比广州少119万,为啥排名能反超广州呢?原因是,深圳是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的城市,这就意味着,深圳全市人口几乎为城区人口,可以看到,深圳常住人口 1749万,而深圳城区人口1744万,比广州多256万,而超大城市的排名是以城区人口规模而定的,所以深圳在超大城市的排名中反超广州。
在这波超/特大城市的扩容中,另一个亮点是佛山。因城区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佛山这座外来打工人的城市,过往统计年鉴中城区人口不到300万,这次陡增到854万,一举超越南京、长沙、郑州等省会。而佛山的晋级也让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里面,有4座城市成为超/特大城市,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
值得一提的是,这21座超/特大城市中,除佛山、东莞两座普通地级市外,其余都是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其中,直辖市(4座)、计划单列市(3座)、省会城市(12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层级在城市集聚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规模是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一个城市GDP突破万亿,通常会被认为是经济大市或强市。
2021年,中国有24座万亿GDP城市,但如果对照21座超/特大城市,会发现这21座城市中,只有17座是万亿GDP城市,这意味着,有7座万亿GDP城市并非超/特大城市。
最为典型的,是被称为最强地级市的苏州。2021年, 苏州GDP为2.27万亿,位列全国第六,且常住人口超过1200万,而苏州的城区人口只有400万左右,只能算Ⅰ型大城市,而从行政级别来看,苏州也只是地级市。
这些年,苏州经济与城市层级的反差,俨然已成为苏州城市发展的特征,而这种反差的背后,与苏州行政建制有关。苏州目前代管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4个县级市,它们的常住人口合计达600多万,这导致苏州常住人口和城区人口之间出现巨大差额,苏州也因此沦为Ⅰ型大城市。浙江省内的经济第二大市宁波也同样是这样的情况,宁波因代管了慈溪、余姚两个县级市,导致城区人口占比下降,也是Ⅰ型大城市。
归根结底是因为,历史上乡镇企业发达的江浙地区,经过数年的发展,形成了县域经济发达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而随着经济强市的扩张,掀起一波撤县建市潮,这些经济发达县率先被改成县级市。可以看到,在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百强县报告中,江苏独占25席,且在百强县前10名中包揽6席,足以窥见江苏县域经济的强大;当然,浙江也不逊色,在全国百强县中占18席,仅次于江苏。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宁波代管的这6个县级市中,有2个(昆山、慈溪)县级市超越全国大部分地级市,跻身105个大城市阵营。与此同时,还有浙江义乌、福建晋江这两个县级市,成功跻身大城市阵营。
此外,在万亿GDP城市中,无锡、合肥、福州、泉州、南通等,也都没能进入超/特大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去年5月,合肥统计局曾宣布城区人口已达511.82万人,迈入特大城市行列,从国家统计局的榜单来看,合肥却并不在列。但合肥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并且无论是从合肥“米”字形高铁网络、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还是从其产业布局来看,合肥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都不容小觑。
或许,苏州、宁波、合肥等万亿GDP城市落榜超/特大城市的遭遇是在暗示,以人口规模判定的城市层级,固然能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但真正的大城市不能仅限于通过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等方式,扩大城区人口规模从而提升城市层级,而应该着力提升城市的综合经济力、公共服务水平、居民文化生活水平等。这些才是城市抢人大战乃至未来城市竞争中制胜的关键。
以城区人口判定的城市层级之所以备受社会关注,也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因为它不仅关乎城市的面子,还与城市地铁申报、超高层建筑审批、户籍管理等直接挂钩。如城市在申报地铁中,一个硬性要求是,“市区常住人口不得低于300万”。
从目前的大城市名单来看,武汉、东莞和西安三市未来都有进入超大城市队伍的可能,而南宁、石家庄、厦门和太原则有冲击特大城市的可能。
超大与特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不言而喻,这些城市代表了中國城市发展的顶尖水平。但不容忽视的是,即便晋级了顶尖的超/特大城市阵营,阵营内部城市间的分化和差距依旧不少。
从地理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有11个,即五成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东北、中部地区分别只有3个,西部4个。而从经济体量来看,以2021年的数据为例,在21个超/特大城市中,有GDP突破4万亿的北京、上海,也有GDP不足8000亿的大连,相差5倍多。
分化的同时,当前这些超/特大城市内部开始呈现由中心向外围发展的态势,这一点在北上广三座超大城市过去5年的人口流动动向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以北京的数据为例,2015年到2020年,北京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比下降9.1%。
当然,这是这些超大城市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外溢效应,在人口向郊区流动的同时,也将伴随一波产业的转移,而郊区如何才能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这涉及这些超大城市的新一轮产业布局和行政功能区的重新规划,也是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可以看到,广州、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都试图通过规划城市副中心,并以此为支点,承接人口和产业从中心向郊区转移。
如果将这些超/特大城市看作一个整体,它们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GDP在全国的占比,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以经济数据为例,2022年上半年,21座超大与特大型城市的GDP总量达33.3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三成,是不容忽视的增长引擎。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耀认为,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这些特大型城市更应当积极作为,主动担当起“顶梁柱”“压舱石”的重任,要确保经济增速和经济份额两个关键指标保持领先。其中,经济增速不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份额不能低于人口份额。
同时,陈耀还建议,作为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这些超/特大城市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稳定和畅通中,要发挥好重要“节点”和“枢纽”作用。此外,分布在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超/特大城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形成挑大梁的“雁阵”格局。
可见,这些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当前重要的稳经济的关键之一,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