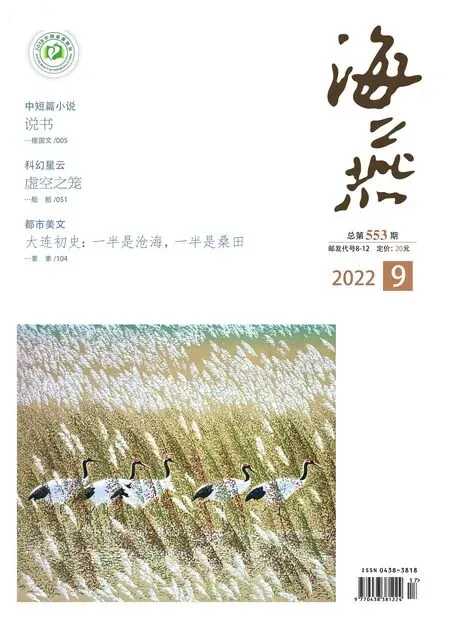近乡关
文 杜茂昌

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这一天,是打发灶王爷上天的日子,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也预示着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来,家家户户都期盼着灶王爷能来年下界保平安。“二十三,祭罢灶,小孩拍手哈哈笑。再过五六天,大年就来到。辟邪盒,耍核桃,滴滴点点两声炮。五子登科乒乓响,起火升得比天高。”这首童谣不知传唱了几世又几代,却又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东来当然懂得这个道理,腊月二十三这天,东来收拾行囊,踏上了返乡的行程。这些年,在外面上学读书,毕业后又到处求职打工,他乡异地奔波,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老家的概念仿佛成了记忆里一幅发了黄的年画,陈旧却又深刻,张贴在内心深处,刻骨铭心想撕也撕之不掉。那么就回吧,回家看看,回家团圆,更何况,这一年里,东来所在的公司效益还是蛮不错的,平常经常会发一点小奖金,还发了一大笔年终奖。仗着这笔年终奖,东来一下子有了衣锦还乡的底气,回家的心思便更加坚定,恨不得脚下生风,有梁山好汉戴宗的本事。
乘车的路上,人满为患颠沛不已,却丝毫不影响东来的兴致。东来挤上了火车,找见座位,把行李安放妥当,想着长路漫漫,便靠在座背上闭眼养起了神,思维一下子又活跃到公司里。
还不到元旦,公司里的同事就私下里吵嚷开来,关心的全是年终奖,纷纷猜测年终奖的数额及发放的时日,谈话的中间眼睛里全冒着灼热的火焰。爱叽喳的小张说,怎么还不发年终奖?可都指着年终奖活呢,要不这年可怎么过呀!消息灵通的老余说,听说今年的年终奖比往年都高,但高是高,又不搞平均,东来你们技术部研创项目多,怕是今年的奖金还会更高。那个经常吵着要跳槽的大王也在这个节骨眼上,绝口不提跳槽这么敏感的话题,逢人便讲,先把今年的钱挣上,总不能亏待了自己呀。甚至连一向刁钻的菲儿也有话说了,她居然跟东来开起了玩笑,是呀,东来哥哥,你的年终奖应该会多一点吧,潘总他呀肯定会照顾你的。菲儿说完了话,诡秘地笑着。
东来想起公司里围绕着年终奖派生出来的氤氲氛围,不由得悄然而笑。他大学毕业后,没有回老家谋事,而是毅然到南方打工,几经周折,几度寒暑,终于在这家公司站稳了脚跟,并且凭着过硬的自身素质,深得公司领导器重与同僚赞许,优厚的年终奖待遇便最能说明问题。发年终奖那天,技术部的主管谭部长亲自找的东来,说,东来呀,这一年,大家都辛苦了,你更是不容易,扑下身子干了许多事,这些老总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这不,老总同意给大家多发些年终奖,鼓舞一下斗志,明年再创辉煌,你想不到吧,你的年终奖是三万。
公司里发放年终奖是有规矩的,一般员工是按照底薪收入的比例进行分配,当然,更多考虑是员工日常的绩效表现,至于公司的高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老总一高兴,说不定还能给高管们发一些公司的股票呢。这一年,公司开发了许多新产品,开拓了很多新市场,在他们这一行的领域里赚足了面子和票子,给员工多发一些年终奖似乎也是应该的,但一下子就来个三万,东来还真有点兴奋到不敢相信。
银联卡是菲儿从财务部给东来代领回来的。菲儿把银联卡放在东来的桌子上,对东来说,你的卡,密码是六个1,回头你赶紧改了密码吧,别丢了钱怨我呀。东来拿起卡,看着卡外面用一个半面是纸半面是透明塑料的袋子密封包裹着,纸袋子那面打印着自己熟悉到有些熟视无睹的名字,脑海里忽然莫名地闪现了一下潘总的形象。东来接过来装了起来,对菲儿说,我能不相信你呀,我还巴不得你花呢,你花了我的钱好做我的媳妇。菲儿冷笑着,轻轻地哼了一声,你想得倒美。东来问菲儿,你的年终奖是多少?菲儿说,就不告诉你。
实话说,公司想得还真周到,调动大量现金,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干脆给每人另外一张银联卡,有别于原先的工资卡,这样的话,好多有家眷的人,可以毫不费力拥有一份自由掌控的私房小金库,公司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东来料理利索手头上的活计,跟谭部长请假回家,因为离老家远,索性连年假一块休了,也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手有钱粮心不慌,想着丰裕的年终奖已然到手,至于搭什么交通工具回家,那选择的空间也就更大了。最初,东来是想乘飞机潇洒一把,没承想年关紧张客流爆满,死活订不上机票,只得改坐火车。可火车也照样人多,在网上查询到一趟临时加开的列车,紧赶紧才订购了一张车票,好歹算是踏上了归家的路。东来不免阵阵感慨,四年一届的奥运、亚运都能办得井井有条,可这一年一次的春运啥时候才能办得像个样子呢?
一下子又想起自己有些时日没有回家了。去年就忙得没有回成,在外面漂得久了,更加眷恋故乡的根。离家愈近,思念亲人的心情便愈迫切,旅途的劳顿那又算得了什么,根本掩盖不了内心那一波又一波冲浪似的渴盼。
东来想起了哥哥,他的眼角有些湿润,都说长兄如父,在东来看来,这话一点也不差。小时候家里困难,父亲常年身体不好,哥哥早早就辍学务工,挑起了家中的大梁,挣上钱帮着接济家用,也帮着资助弟弟妹妹们上学的费用。有一回,学校里给学生统一做校服,前提是每人必须先交三十元钱。那时家里父亲正好生着病,吃药打针,花销很大,他哪里还有勇气张口要钱,只好满脸怨气地默默忍着。眼瞅着同学们一个一个都穿上了崭新的校服,老师的催促,同学的嘲讽,加上他自己强烈的自卑,使他脸色更为阴郁,后来还是哥哥看出了端倪,询问了他半天,问清原委二话不说给了他三十元,他很快也有了自己的校服,帮他找回了些许尊严与自信。还有考上大学的那年,昂贵的学费令他望而却步,他决定不念了,也跟着哥哥去挣钱,哥哥劈头盖脸地把他臭骂一顿,说,你只管安心念书,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跟上我出苦力挣钱,将来能有啥出息?哥哥筹措够了学费、生活费,为他送行,临别,还额外递给他三百元,说,穷家富路,在外面别亏待了自己的身体。他拿着这三百元,感觉沉甸甸的。
父亲在他大二时去世了,剩下的两年,全靠着哥哥才攻读完学业。在他看来,对哥哥的感激之情,世间那些浅薄的词汇都是无法形容的,父亲一走,哥哥身上的担子更重了,风里来雨里去,挥大汗出苦力,一年到头也落不下多少积蓄,却还拉扯弟弟妹妹长大成人。在东来的印象中,哥哥似乎就没几件像样的衣裳,吃饭也从来不讲究什么营养,简单到穿暖吃饱就行,哥哥年岁不大,已是饱尝人间的酸辛,两鬓不少的黑发悄悄演变成缕缕白丝。
好在,弟弟妹妹们都拖拉着长大了,东来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妹妹也出嫁了。哥哥才回过头盘算自己的日子,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嫂子组建了家庭,但也可想而知,没有好的经济基础,生活照样是艰难拮据。
想到这里,东来一阵心酸,觉得哥哥付出的真是太多了,而自己亏欠哥哥的更是言说不清,总想尽可能回报哥哥一些。想想哥哥费尽力气一年撑死了也就三万多块,还不如自己一个年终奖来得痛快,自己能有今天,哥哥功不可没呀,年终奖说什么也得有哥哥一份。往常,东来也给哥哥些钱,哥哥说什么也不要,再往后,有了嫂子,东来回家的次数少了,定期也给家里汇些款,嫂子默然接受了,哥哥却打来电话,要东来别往家里再寄钱了,家里的钱够用,让他自己留着,原先寄来的钱也给他留着呢,以后找对象、买房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哥哥就是这样朴实,宁愿自己多受些累也不想给自己的亲弟弟添麻烦。可是,东来过意不去,这次回家,说什么也得给哥哥放一些钱,或许亲人之间提钱多少显得有点俗气,但表达心意真的没有比钱再实际的东西了。即使哥哥不要,也得交给嫂子,嫂子总会要吧。
年终奖的银联卡,东来随身携带,他早就想好了,回到家,就近找个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取上三千现金交给哥哥。尽管三千只是年终奖的十分之一,可按照家里的消费水准却也恰到好处,不是多了不想给,怪只怪哥哥那执拗的脾气,给多了未必接受。再说了,自己在外独自打拼,无根无基的,也正是用钱的时候,菲儿曾一连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女友,相处没几天,对方那准丈母娘一听说他没房没车的,便宣告拜拜了。面对现实,东来既气恼,又没有办法。是呀,自己确实是要啥没啥,连个房子的首付也出不起,哪里还有资格去谈一场奢侈的恋爱呢?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东来渐渐懂得了金钱的重要性。要想攫取硬邦邦的物质必须有鼓囊囊的口袋。否则,挨饿的时候便只能在地上画两个饼。东来明白了这一点,更庆幸自己明白得还不算晚,他开始调整心态,刻意地追逐名利,既羡慕谭部长、潘总那样滋润的生活,又不得不埋下头来拼命奋斗,希望早日出人头地站在人前,一如谭部长、潘总那样体面。
要想被公司领导赏识、垂青,得到重用、提拔,努力工作是少不得的。可仅仅工作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就好比诗人想写出好诗,往往功夫都在诗外。公司里的人际交往,人情世故,人脉关系,微妙而复杂,举重又若轻,仿佛蜘蛛在墙角精心编织的一张网,掩盖了墙角下许多的真相,以及被蜘蛛吞噬掉的,那些蚊虫的挣扎。
毫无疑问,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公司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发展的第一步就是要向谭部长、潘总这些公司的当权派靠拢、亲近,或者叫做妥协。谭部长是他们技术部的主管,接触的机会自然很多,潘总是公司的副总,分管着他们在内的好几个部门,公司里制度健全,等级森严,要想和潘总直接打交道还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东来想起了初见潘总时的情形,那是在他应聘的面试环节,主考官有好几位,其中就有潘总。东来走进了面试厅,朝端坐的主考官们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自报家门,说出了姓名、年龄、籍贯、毕业院校等基础性的信息。其实,这些信息主考官们的手上都有资料,再从东来自己嘴里说出来却别有一番滋味,大家把含笑的目光全都齐刷刷地投向了潘总。
面试厅的阳面有一面硕大的窗户,一整块的玻璃擦得格外透亮,视野显得特别开阔,充沛的阳光暖融融的,如春风一般洒在潘总的脸上。潘总的脸上瞬间漾出了微笑,他审视着眼前的东来,开口说话了,东来,紫气东来,你这名字起得好呀。
东来有些发蒙,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样表白,略作镇静,才说,名字都是父母起的,寓意肯定是美好的,但有个好名字并不能说明什么,要想做到名副其实,自身的努力,机遇的把握,还有领导的提携,样样都是缺不得的。
东来一口气说了这些,自己都有些脸红加心跳,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哪里有什么涵养给他起好名字,无非是赶了个巧,他知道,他的哥哥叫东生,也就是在东屋出生的,到了他这里,恰好冬天来了,便顺着“东”字辈的谐音叫了个“东来”,说到底,也没什么别的讲究。
连同潘总在内的主考官们,对东来的表现十分满意。余下的几位主考官,也就关心的话题接连向东来提问,东来没了初进考场时的紧张,沉着应对,侃侃而谈,发挥得可圈可点,惹得一旁静观的潘总频频点头。临了,潘总递给东来一张名片,笑着说,小伙子,能不能进公司,还得看最后全部的排名成绩,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不过,进不进公司不要紧,咱们也可以交个朋友,今后,有什么生活上的私事需要帮助,你也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记得你的。
东来接过潘总的名片,一个字一个字仔细瞧了一遍,顿时惊讶不已,嘴巴不由张得老大,他之前是不认识潘总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潘总的名讳,更不了解潘总在公司位高权重的事实。一边的主考官笑着打圆场,说,年轻人,你遇上贵人了,潘总说你行,说明你真行呀,还不快谢谢潘总。东来这才反应过来,再次向潘总他们鞠躬致谢,随后忐忑不安地退出了考场。
招聘成绩公布后,东来名列前茅,被公司顺利录用到技术部。在技术部,天天和谭部长打照面,再见潘总却有了难度,除非有紧急公务,否则,谁会闲着没事老往潘总的办公室转悠。即便是公务,中间还有部门主管,也不会轮到一般员工出面。
当然,毕竟同属一家公司,上下班时间,一些会议的场合,东来还是能时常看见潘总的身影。潘总的形象高大健朗,风度卓然,浑身上下散发着成功男人的魅力。东来有时在公司不可避免地碰见了潘总,总是友好地点一下头,问一声潘总好,潘总也极其礼貌地笑着回应一下。
在与潘总的谋面中,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公司公关部组织的一次酒会上。那次酒会是公司专门答谢客户准备的,来的大都是同公司往来密切的商团。公司内部为烘托热闹的气氛,给各个部室派了些参会指标,谭部长带着东来和菲儿这一对俊男靓女盛装赴会。酒宴过后,音乐响起舞会开始,菲儿感激谭部长带她出来玩,首先就邀请谭部长跳舞,谭部长毫不客气,爽快应允,又回头大声对东来说,东来呀,一会儿你也找个美女跳一曲吧。东来落了单,独自坐着,他本来就对这样的酒会不是太感兴趣。正在怅然间,迎面来了一个漂亮的女郎,一袭长裙翩翩,秀色撩人,笑靥如花,近前与东来搭讪,潘总呀,没想到你这样年轻,肯赏脸跳支舞吗?东来赶忙辩白,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我指给你看,那边那位才是潘总。女郎的脸色骤然变了,不理东来,朝潘总的方向径直去了,蜂腰一扭一扭地都快闪断了。对女郎的眷顾,潘总并不拒绝,笑着答应了,那女郎同潘总一块步入舞池,瞬间又恢复了秀色撩人,笑靥如花。
东来远远地看着舞池里面的动静,菲儿和谭部长各怀心事,没多大一会儿,便各自换了舞伴,漂亮女郎却和潘总情意绵绵,边舞边聊不知说着什么。潘总有妙女揽怀,状态不免轻松惬意,女郎的脸上则甜蜜地笑着,刚才还互不认识,现在暧昧的灯光下又熟得老情人似的。东来不禁想,假如刚才自己欺骗她,默认自己就是潘总,她会不会也这样对自己笑呢?又或者假如自己有朝一日真成了潘总一样的人物,有资格沉湎在纸醉金迷一般的生活里,这样的女郎会不会主动投怀送抱呢?
火车上邻座的两人可能是老乡,聊了一路,聊着聊着投机了,无话不谈。一个说,你们那里让回家过年,发没发年终奖?另一个说,发了,就是多发了一个月工资,相当于年终奖了。一个就骂起来,把黑心的老板骂了个够,最后又羡慕另一个,说,还是你们好呀,还有个年终奖,我们连个西北风也没有。另一个说,说不定你们老板过完年给你们发呢,迟饭是好饭。一个说,屁,算了吧,都是工薪阶层,谁不想多发一点,去年过年,我们每人就只发了一壶不知哪里的地沟油,今年还能指望什么?另一个说,那就有啥算啥吧。一个说,管它呢,有钱没钱,咱也得回家过年呀。另一个说,那倒也是。两个人聊到痛快处,哈哈大笑起来。
两个人的谈话,把东来从回忆中拉回了现实,他就是他,他怎么可能成了潘总呢。他睁开惺忪的眼,冲说笑的两个人望了望,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个招呼,继续听他们攀谈。从他们的衣着穿戴,言谈举止上看得出,他们都是平凡的务工人员,外出打工一年也挣不到多少辛苦钱,这一点和老家的哥哥是何其相似。这样再一细想,自己也算是幸运的,起码还有个不菲的年终奖,比上不足,比下却也有余了。
好几个小时的行程,连困带乏,迷迷糊糊,东来想着自己的心事,听着别人的故事,总算坚持下来了。一夜颠簸,天色渐亮,车窗外,北方冬季独有的肃杀缓缓映入眼帘,远处的山峦起伏绵延,灰蒙蒙的看不真切,黄土地上空旷冷清,散漫地残存着农作物的茬子。近处的一排排杨树叶落殆尽,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眼前如风般一晃而过。偶尔会有一半个村落闪现,房屋相连,街道寂寥,因为天冷的缘故,路上并没有几个行人。
尽管如此,东来的心却按捺不住地跳动,离家是越来越近了,漂泊的游子马上就能踏入故土。东来盘算着要给每个家人都买些礼物才对,母亲是不用说了,哥哥嫂子不在话下,就是那未曾谋过面的侄子也是有份的,还有正月天走访亲戚们的一些物品。
九点刚过,车到他们县城,东来急切地下了车。终于到了站,终于可以回家了。到底是县城,毕竟不同别处,又临近春节,街上自是热闹异常,满大街都是年货,满大街都有闲人,有写春联的,有卖年画的,不大的几家超市还将货物全摆在了门口,音响里播放着动听的流行歌曲,任由欢喜的人们挑选采购。年味愈发隆重,勾起了东来小时候许多美好的回忆,东来决定在县城里好好转转,看看家乡的变化,也精心挑选一下送人的礼品。
东来他们村子,离县城二十里路,不远不近,说到就到。东来的打算是,先找个银行取钱,然后购物,最后再打一辆出租车满载而归。
主意已定,东来便开始分步实施。如今县城发展的速度挺快,转了没多会儿,正好有家银行,东来走到自动取款机前,插入那张年终奖的银联卡,要把给哥哥的三千元先取出来。
插卡的时候,东来的心里还隐隐有些不安,有些焦急,生怕这三万元放在小小的一张卡里不保险,会不翼而飞,摁密码时手抖了一下,险些多摁一个键,还好,立马出来一长串数字,打头的是3。东来这才平静下来,又摁取款的操作键,要取三千,取款机里哗啦哗啦过钞的声音提神凝气,一会儿便蹦出了一沓崭新的人民币。
东来把钱攥在手里,感觉一下它的厚度以及分量,想象这微薄的资金总能对哥哥的生活有些许改善,心里便涌起一股暖流。
把这三千元放入羽绒服夹层的口袋里,东来又取了几百元现金。虽说现在购物时微信和支付宝都能搞定,但现金总归还是有它的用处。孝敬母亲一些零花钱,总不能拿微信转账吧;给侄子发几张压岁钱,也不能支付宝支付吧。母亲和侄子的那些钱,东来自信都没问题能够名正言顺地送出手,他只愁如何将给哥哥的那部分顺顺利利地交给哥哥嫂子,就怕他们硬撑着不要,实在不行,自己走的时候偷偷给他们留在家里。不想了,总会有办法的。
东来离开银行,转到一家小超市,计划给家里买些东西,他来回踅摸着,心里并不确定是该买特仑苏还是安慕希。这个时候,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妇女开口了,问他,是要走亲戚吗?走亲戚你拿这种的,这种的今年走得快,要是自己喝就拿边上的。说时,那妇女还拿手左右指了指。听着亲切的乡音,想到自己多久没回家了,东来忽然便笑了。他用略显生涩的土话回了一句,那我都要吧,也走亲戚也自己喝。老板娘挺高兴,东来掏出手机准备结账。
刚拿出手机,手机便响了起来。起初,东来以为是哥哥的电话,他昨天已告诉哥哥他要回家过年。一看,却是菲儿的。东来刚接起来,立刻听到那边菲儿的哭腔。东来赶忙问,菲儿,你怎么了?菲儿哭着说,东来哥哥,我被隔离了,我们这里一下子有了疫情,我来时经过风险区,这会儿有家也回不去,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跟你回家过年呢。
东来知道,菲儿的老家在相邻的另一省,菲儿比他早走一天。走之前,菲儿跟他抱怨,说是每次回家父母亲都是催婚,搞得她烦不胜烦,真不想回去。东来开玩笑,说,那你跟我回去吧,假扮一下我女朋友。菲儿顺着他的意思跟着开玩笑,说,可以啊,今年你家,明年我家,不信咱们假戏成不了真。那时候,东来真以为菲儿是在跟他开玩笑,可现在听着手机里菲儿的声音,竟听出几分别样的意味。
在公司,他和菲儿算是走得近的人,两人因为地缘相近,年龄相仿,且都是单身,在一起的话题自然多一些。有一段时间,东来甚至想追求一下菲儿,可菲儿对他的态度始终忽冷忽热,若即若离,好的时候能勾肩搭背无话不谈,差的时候针锋相对互相讥讽,搞得他吃不准菲儿到底是个啥意思。菲儿心血来潮,还会接连不断给他介绍认识的小姐妹,问他和那些小姐妹相处是个啥感觉。看到东来一脸的窘迫,菲儿总是笑得很得意。东来想,他和菲儿怕是轻易不来电,倒或许能试着和菲儿做个好“兄弟”,可是做这样的“兄弟”,他明显又不甘心。
菲儿在手机那头还说话,你也是的,光知道说嘴,就不能真心邀请我去你家一回啊,要是去你家,哪有这倒霉事。东来只得在电话里好言抚慰,说,安心隔离吧,过段时间就好了,隔离结束,你要真想来我家,我去接你。
东来摸不准菲儿究竟是什么想法。他想起他前几次回家的情形,母亲和哥哥也总担忧着他的终身大事,让他碰到合适的对象多上些心,该花的钱一定要花,这方面不能抠,要不然怎么能留得住女孩子的心。平常和家里通话,每次说到最后,也必谈找对象的事,母亲说你也不小了,在村里你这样的年纪孩子都会跑了,你哥哥便是耽误了好些年,你可不要学他。东来没办法,只得哼哼哈哈,装聋作哑。这次回家看来是照样少不了这些应付的环节。他想一想,便觉得头大,苦笑一下,走一步看一步吧。
菲儿听了东来的表态,渐渐平复了情绪,说,好吧,我信你一回,你要记着你说的话,我可等你呢。东来的心里一阵过电般的颤抖,他也说不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对于未来的日子不由生出诸多不一样的期待。他对菲儿说,放心吧,我会的。
东来挂断电话,回想起与菲儿在公司的时光,尽管两人时常言语尖酸互相调侃,可也有无法取代的快乐成分在里面,此刻想来竟是格外甜蜜。东来一高兴,又买了一些其他物件,结过账,双手满满当当提着出了超市。
在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东来先把东西放在后备箱,拉开车门刚要钻进车里时,手机又一次响起。
这次是哥哥。东来正要接听,身后猛地蹿出几个顽皮的小孩童,手里拿着一些摔炮,一枚一枚掷在地上,互相喊着闹着追打着,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东来想,年是近了,家也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