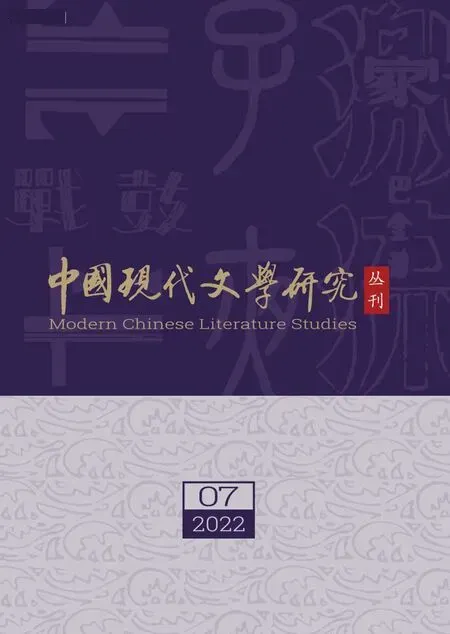郁达夫《毁家诗纪》中的情感经验与伦理修辞
孙慈姗
内容提要:《毁家诗纪》是郁达夫于1936年3月至1938年底创作的一组旧体诗,诗歌详细记录了作者与妻子王映霞感情裂变的过程,并先后在《大风》旬刊等杂志发表,这段文人家变因此广为人知。本文拟在前研究的基础上对《毁家诗纪》诸篇诗作及注文进行细读,将关注点转向文本修辞层面,并将之与作者身份意识、情感经验及伦理认知相勾连,探究郁达夫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构建某种伦理框架解释自身所处境遇,并在旧体诗这一形式中处理不断溢出的复杂感情。进而通过对《毁家诗纪》的解读探寻修辞行为与情感抒写、伦理建构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旧形式”对文学家在时代巨变中选择行为方式、实现自我安置的重要意义。
《毁家诗纪》是郁达夫于1936年3月至1938年底创作的一组旧体诗,主要记录了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感情裂变的过程。在作为组诗发表前,其中的一些篇目零星见于郁达夫的日记、书信与及散文中。几相对比可以推测,这并非一部事先已有完整写作计划的组诗,将这些作品遴选编次用于言说自己的“毁家”经过应该是郁达夫在两年的经历与心态变迁中逐渐萌生的念头,而诗作部分语句的改动以及陈明“本事”的注文的加入也都应在其作为组诗编定之时。
1939年3月5日,《毁家诗纪》在《大风》旬刊第30期发表,或许是因为读者对文人家事的兴趣,这一期《大风》销量激增,相继印行四版。①亦有人认为《毁家诗纪》及郁达夫王映霞夫妇相互揭短指摘的一系列文章的刊发是《大风》发行人简又文、主编陆丹林策划授意的结果。狂风:《〈大风旬刊〉销数激增》,《幽默风》第1卷第2期,1939年6月16日。而《毁家诗纪》也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先后被上海《时代文选》《古今》半月刊、《永安》月刊转载。①《时代文选》创刊号,1939年3月20日;《古今》第1期,1942年3月;《永安》月刊第91期,1946年12月1日。1946年第91期《永安》月刊在刊登《毁家诗纪》时附有《大风》旬刊编辑陆丹林的短文《郁达夫“毁家”前后》,指出当年在《大风》上“为了环境关系”不得不删去原稿的部分内容,而这次刊出的才是诗作的“全豹”。对照《大风》与《永安》月刊可以发现,两个版本的诗句本身并无改易,差别主要体现在部分诗作的注文中。相比较而言,《永安》月刊的注文更加明示了所涉人物的身份,并对妻子的“出轨”经过及作者本人面临家变时徘徊犹豫的心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叙述。另据学者考证,在诗作公开发表之前,郁达夫已将手稿分赠予文坛友人,而在《大风》刊载《毁家诗纪》后,郁达夫更是要求陆丹林将这一期杂志寄给蒋介石、邵力子、叶楚伧、于右任、柳亚子等政界和文化界人士阅读。②方忠:《郁达夫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可见郁达夫对这组旧体诗的创作、发表和流传十分重视,不仅无意遮盖“家丑”,反而力图细腻刻画夫妻二人情感破裂的全过程并使其为更多人所知。这般有悖于常情常理的做法自然招致了许多不解,也直接导致了郁达夫、王映霞婚姻的解体。
长期以来,前研究不乏对这组诗作细致的笺注与诠释,然考其类型,大都是依托郁、王婚变的事实经过对诗歌内容的梳解,或是将之作为传记研究的材料。此外,这些研究也或多或少地关注到了《毁家诗纪》与郁达夫小说共同具备的某种“自叙传”风格,以及组诗中儿女私情与家国大义的相互关联。这种联系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自觉建构,而一以贯之的自叙因素也是解读这组作品的关键所在。③有关《毁家诗纪》的前研究多集中于文本疏解方面。其中,詹亚园、朱学忠在查考史实及诗作用典的基础上对组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笺注;许凤才结合郁达夫、王映霞及其友人对夫妻二人关系裂变的叙述,对《毁家诗纪》进行了传记式解读,并试图探寻组诗中未能明言的事实经过。此外,也有研究对组诗的核心特征做出概括,并将之置于郁达夫旧体诗写作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如贺祥麟认为《诗纪》有两大突出特色,一是“将国难家难交织在一起”,二是“首首诗皆有注解”,且诗人原注对于读解作品发挥着巨大作用;刘斐则认为郁达夫创作于1936—1938年间的组诗自叙传特点愈发明显,并与《沉沦》等小说文本呈现出相似的结构特征。以上研究详见詹亚园、朱学忠《郁达夫〈毁家诗纪〉笺注》,《淮北煤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许凤才《〈毁家诗纪〉的多维诠释——写在郁达夫遇难60周年之际》,《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贺祥麟《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民主》1990年第11期;刘斐《郁达夫旧体诗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在此基础上,对《毁家诗纪》诸篇作品进行细读,将关注的重点转向文本修辞层面,并将之与作者这一时期的身份意识、情感经验、社会认知及伦理境遇进行勾连仍是十分必要的工作。由此,或可进一步揭示修辞、情感与伦理间的微妙关系,并对这组诗词的表现形式及其所承载的文人心曲做出更为深入细腻的理解。应该看到,《毁家诗纪》的创作发表不仅仅是郁达夫一时义愤加之办报人营销手段的产物,更是一介文人在社会性、制度性的震荡动乱中为自身寻求身份位置、价值信念、情理依托的某种文学实践,其背后还隐现着一时代人在语言要素、文学形式、情感结构、伦理准则、人际关系的“新”与“旧”之间的游移、困惑与选择。
一 “旧伦理”的有效性——从“儿女”说起
伦理问题涉及个体的行为准则及其与其他个体、群体间的关系模式,并关乎“善善恶恶”的价值判断,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文学实践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现代史上,与新文化及新文学有关的一系列变革活动,便以召唤一个新的伦理形态为重要旨归与内核。
在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彻底抛弃视为“吾人最后之觉悟”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期,1916年2月15日。,因其触及的乃是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然而“新文化”的发展历程似乎不断昭示着这一“最后”时刻的到来远非如此斩钉截铁。在实践过程中,它不得不面临诸如此类的困惑:如何评价某种伦理观念的新或旧?何以社会伦理道德观的整体演进总呈现出参差曲折的样貌?伦理观念与具体的社会实践怎样相互作用?
卡尔·曼海姆认为,衡量某种伦理标准有效性的依据在于遵循规范的个体和群体能否适应现实社会情境并在此规范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其能动性。而“如果通过传统的思想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力量,并不包括调节思想和行动适应新的变化了的情境,因而最终在实际上掩盖和妨碍了人们的这种调节和转变,那么这种道德说明就是无效的”②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6~127页。。这意味着在整体意义上,伦理观念的有效性在于其使个体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情境的能力。一种有效的伦理观念应该能够为个体在事实或心理层面确立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模式与社会位置,帮助个体实现自身行为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然而在每一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同个体与群体的实际处境或许有很大差异,伦理态度作用于具体对象的有效性也就因人而异。这就决定了伦理观念的演变并不是统一、线性的进程,而是在每一个时空横截面上,都呈现出交织驳杂的样貌。在社会情势激荡变化之时,这样的样貌就更加凸显。即如以一夫一妻多妾为基本婚姻形态、以男性家长为权力中心并作为其他一切纲常伦理生长基点(“夫妇,人伦之始”)的传统性别—家庭伦理就正因对某些群体尚有解释、指导,使之适应处于新变中的社会情境的能力,而具备了存续的可能,并在特定时刻成为个体解释自身情感境遇的伦理依托。
在最为显见的层面,面对“不忠”的妻子与战争状态下夫妻情感的变故,郁达夫在诗歌创作中首先召回的正是这样一种伦理形态,它作为一种保护性机制疗愈着“毁家”的创伤,并为身为男性的郁达夫提供着在“儿女”与“家国”间想象自身身份位置的方式。
《毁家诗纪》对女性情感、行为逻辑的认知方式与态度便能说明问题。在诗作与注文中,郁达夫屡屡表示妻子的“琵琶别抱”是其轻薄无知、贪慕富贵的结果①如《毁家诗纪》第八首“武昌旧是伤心地 ,望阻侯门更断肠”用崔郊《赠婢》“侯门一入深似海”典,暗示妻子在武汉追随富贵而去;第十二首“九洲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注文云:“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并云×君尚有存折交映霞,似乎意在痛惜妻子的轻薄爱财终铸成大错;第十一首注文提及王映霞在战争逃难期间还须乘汽车、住洋楼,并因郁达夫“太不事生产”而变心;第十八首注文又分析:“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也都反复强调了妻子出轨的缘由。郁达夫:《毁家诗纪》,《大风》旬刊第30期,1939年3月5日。郁达夫:《毁家诗纪》,《永安》月刊第91期,1946年12月1日。以下《毁家诗纪》诗作引文如无特殊说明皆出自同一版本,注文则采纳《永安》月刊的“全豹”。,而“绿章迭奏通明殿,朱字匀抄烈女篇”②“绿章迭奏通明殿” 语出陆游《花时遍游诸花园》“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荫护海棠”。这一有关惜花的典故或许能让人联想起郁达夫在《日记九种》中对与王映霞相恋后自身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这段感情上之情状的比喻性描述:“叹我一春无事为花忙,然而这花究竟能够不能够如我的理想,一直的浓艳下去,却是一个疑问。因为培护名花,要具有大力,我只觉得自家的力量还有点不足。”见《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绿章”一句的行为主体自然是惜花的“我”,而顺承前句,“朱字”一句的主语也应如是。等诗句则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对女性的保护、纠正与教导姿态。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烈女”的意象至少有双重意指——既代表两性关系领域的贞洁操守,又指向了对民族复仇大业的忠贞献身。面对不贞的妻子,丈夫要对她施以德行的教导,不仅使其守妇人之德(“亦欲赁舂资德曜,扊扅初谱上鲲弦”一联,化用孟光“举案齐眉”、百里奚妻“烹伏雌,炊扊扅”两典,突出贤良妻室的言行准则),更要明家国之义——所谓“闺中日课阴符读,要使红颜识楚仇”,就是要让视日寇来侵为“一时内乱”的妻子了解国家危亡的形势,并斩断不道德的私情。在这样的表述中,烈女的双重道德意涵都要由男性向女性进行灌输与训导。劳燕分飞已不可避免,而丈夫对妻子犹存怜惜规劝之心,这至少是令郁达夫本人唏嘘感慨之处。然而,这些诗句所承载的作者对女性的怜爱与教诲更近乎古典世界中多情文人的怜香惜玉,而与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两性关系想象有很大不同。这并非单纯指责郁达夫在性别观念上的“落后”。事实上,对待包括妻子在内的女性的态度更关联着郁达夫对自己身份与行处方式的想象。在自称为“骸骨迷恋者”①斯提(叶圣陶)在1921年11月12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9期发表题为《骸骨之迷恋》的文章。叶圣陶反对《南高日刊》的《诗学研究号》刊发旧体诗,认为旧体诗已然成为骸骨,“要用他批评或表现现代的人生,是绝对不行的”。然而此语一出,郁达夫、郭沫若等新文学作家纷纷用“骸骨迷恋者”表达自己对旧文学因素的不能忘怀。时,郁达夫透露出自己对古典社会文化情境的选择偏好:
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但是我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即使不要讲得那么远,我想我若能生于明朝末年,就是被李自成来砍几刀,也比现在所受的军阀官僚的毒害,还有价值。因为那时候还有几个东林复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侠妓名娼,听听他们中间的奇行异迹,已尽够使我们现实的悲苦忘掉,何况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说演呢?②郁达夫:《骸骨迷恋者的独语》,《文学周刊》第4期,1925年1月10日。
侠骨柔肠、风流潇洒、共负国仇而情深意笃的公子名妓成为乱世中最为理想的人际关系与生存模式。借由旧体诗这一文体形式,郁达夫所召唤的正是这样一种角色想象和与之相关的文化语境,以此确认“儿女”与“家国”的勾连方式。如研究者所言,郁达夫旧体诗中以晚明情事为底本③晚明士子与秦淮名妓之间的情事在郁达夫的艺术世界及角色想象中占据重要位置。如郁达夫1921年自安庆赴日本前写给妓女海棠的《将之日本别海棠》其中一首“绿章夜奏通明殿,欲向东皇硬乞情。海国秋寒卿忆我,棠阴春浅我怜卿。最难客座吴伟业,重遇南朝卞玉京。后会茫茫何日再?中原扰乱未休兵”(詹亚园笺注:《郁达夫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便不仅在典故层面出现了吴伟业卞玉京的情事,更是在整个诗歌结构语式上照搬了吴伟业的《琴河感旧》,可见与晚明情事有关的文学资源怎样影响了郁达夫对自身情感经历的体认。对自身情感经历的书写可视为其对现实情感/爱欲匮乏的艺术性补偿①Haosheng Yang,A Modernity Set in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p.71.,而一旦乱离的情境再度凸显,这样的身份与情感想象在心理安抚与行为指导层面似乎都变得更加有效。在这个意义上,战火中因女方“不贞”而导致的婚变固然为男性个体带去了屈辱与创伤,却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以纳入艺术审美范畴的非常态的浪漫,是儿女乱世情的又一变体。在《毁家诗纪》中,能够教导红颜识楚仇、来日“鸳冢傍岳坟”②《毁家诗纪》第十首“东南何日平夷虏,鸳冢终应傍岳坟”,这句诗后来被改作“而今劳燕临歧路,肠断江东日暮云”。固然是好;倘若不能,则为家国重任抛弃儿女私情几乎就是士子的必然选择。所谓“绝少闲情怜姹女,满怀遗恨看吴钩”“自愿驱驰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便是对这一选择不无豪情的言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份与情感想象的有效性有其制度文化根基。在分析当代语境中的旧体诗时木山英雄认为,“作为旧体诗词基础的文言文文化之支柱的诸种制度,随着王朝的崩溃已然成为过去”③木山英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60页。。在这种情形下,由旧体诗创作所塑造和维系的传统伦理与情感世界将有意无意地遮蔽实际社会制度的质变,从而无益于支撑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正确的身份认知。④在《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中,作者分析了旧体诗写作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面临的困境,其中一点就在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剧变使得传统诗歌的某些主题、情感模式和表达手法(如“边塞诗”)不再适用。用胡适的话说,在“假古董”中寻不出“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诗”。见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然而,所谓诸种“旧制度”事实上并非完全解体。这其中,规约着两性关系的婚姻制度的过渡性、模糊性便使得“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形式和家庭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客观存在⑤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并提出了在法律上反对多妻制的原则。1930年公布的《民法》之《亲属编》第985条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肯定了一夫一妻制。但社会形势的动荡与情感观念的杂糅等因素实际上导致了妻妾关系或多妻家庭的存在。,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自由恋爱”等婚恋观念和形态的杂糅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催生、加固了这样的婚姻形式及与之相对应的性别观念与情感模式①王风在《张爱玲〈五四遗事〉中的“五四”话题与40年代“遗事”》中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五四遗事》视为一则文化寓言,既关乎新文化传统尤其是新的婚姻恋爱观(其小说英文副标题既为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又涉及张爱玲个人的创作与情感经验。王风认为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恋本就是一场误会,是在男女关系方面胡兰成的“旧式才子”与张爱玲“极为前卫的现代观念”错位耦合的结果。(王风:《张爱玲〈五四遗事〉中的“五四”话题与40年代“遗事”》,《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4期)某种程度上,新旧婚恋观念进而是伦理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交织、错位、妥协与合作的确导致了事实上一夫多妻家庭形态的存在,也使“旧式才子”们的想象得以延续。。此外,秦楼楚馆、歌女舞姬的存在或许也使得这一种身份想象更具备安放空间。
但在这些事实因素之外,传统文学想象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力量更不可小觑。对吴伟业等人状写艳情诗作的多般模仿或许表明郁达夫谙熟此种文学表达形式,《毁家诗纪》诸篇对两性情感与相处模式的描摹时时与此类文学传统暗合,相应的性别伦理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而成。以此伦理形态叙述自身的情感变故不仅意在洗刷“曳尾泥涂之耻”,更为作者提供了从儿女之情上升到家国之义的有效途径。这里存在着的不再是“零余者”被压抑的情欲与“弱国子民”的自卑无力,而是在传统性别与家庭关系模式中占据知识与权力优势的一方的主动选择与担当——从对不识亡国恨的姬妾的保护教导到最终放弃对“尤物”与儿女私情的耽溺投身报国大业,凡此表述不难见出男性个体在处理情感问题时的主动性,而这也使其在事关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叙述中占据了能动位置。②这种对儿女私情的文学表达方式或许受到了元稹白居易一脉文学观念的影响。元白作品中有关男女情事的描写多含有讽世之意,并对“尤物”持有警戒和贬低心态。《莺莺传》叙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经过,以“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 ……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作结,视弃尤物而忍其情为修身立业的基础。白居易将《长恨歌》列为“感伤诗”,不无对唐明皇、杨贵妃之情事的唏嘘感慨,其好友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也仍要彰明诗歌的讽劝之旨,“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样一种“尤物观”为男性文人克服、超越儿女之情提供了途径。但在这样的伦理观念与表述模式下,男性主动性、行动力的获得某种程度上必然以压抑女性的相应能力为代价——在《毁家诗纪》最后“国倘亡,妻妾宁非妓”的“高唱”中,作为“妻妾”的女性似乎已然沦为无法行动、只能等待着保护、救赎或“奸淫”的客体。她们的贞洁与否标志着家国内部男性的力量与团结程度,也象征着国家的受辱或新生。
如果认为文学表达形式亦是伦理态度的载体,或者说形式本身就带有伦理意味,那么可以继续追问的是,“新/旧”形式与“新/旧”伦理间是否总构成稳定的对应关系?仿佛天然携带着旧的伦理意识的“旧形式”在遭遇社会情境的变化时能否以及怎样生成新的质素?
二 诗注之间——战时新伦理框架的构建
如上所言,《毁家诗纪》刊出时在各诗作后附有郁达夫的注文,主要记叙了作者本人在全面抗战前后两年间的行动轨迹,以及妻子婚外恋情的始末。有了这些注解文字,原本有些暧昧难解的诗句也就仿佛具备了明确的所指对象,而这些详细披露婚变过程的注文或许比诗作本身更具“吸引力”,也成为了杂志畅销、组诗一刊再刊的重要缘由。
细读《毁家诗纪》诸篇及其注文,可以注意到诗注在具体内容、言说方式及情感色彩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而这类差异所构成的张力为进一步探究《毁家诗纪》的修辞形式、情感状态及伦理图景提供了空间。如上所述,《毁家诗纪》诸篇的写作时间跨度较大,原本也散见于郁氏其他文本中,而这些注文则应是在作品发表前统一加入。可以认为有了注文作依托,作为组诗的《毁家诗纪》才得以生成。这些文字不仅使得诗作中的诸种意象、典故、隐喻等修辞有了具体着处,更为形式风格不同的诗歌提供了较为连贯的叙事线索,是确立作品整体性不可或缺的因素。陈寅恪在解读《长恨歌》时提醒研究者注意当时各文体之关系,进而指出白氏《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本诗与序文,而是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因此《长恨歌》真正的收结不是“此恨绵绵无绝期”,而是见于陈氏之传文中:“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5页。诗与传在共同的文本“机构”中承担着不同的表意功能,唯有重视其各自的文本职能及相互阐发的关系,作品在艺术与意涵上的完整性才得以体现。或许解读《毁家诗纪》亦需秉持这样一种诗注一体观,其目的不在于在字句的参差对照间求得事实之“真”,而在于观照“诗”本身怎样以文学的言说方式建构着某种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
《毁家诗纪》中诗作与注文的差异张力从第一首诗便开始体现: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这首诗出现在1936年3月27日作者致友人曹靖陶的书信中,彼时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赴闽担任省府参议已有一月。郁达夫之所以甘为“俗吏”,多半是出于生计考虑,此诗亦较为明显地承袭了传统士大夫宦游倦旅的情结,于团圆佳节遥念闺中儿女,在杜鹃声里感慨“不如归去”。据《闽游日记》所载,此首诗作成于花朝节夜与同僚宴饮归后。单从诗作来看,整首诗意在描摹一种孤寂的情境与心境。这既饱含着传统士子的忧愁(元宵、花朝、杜鹃等意象),又似乎有属于现代漂泊者的茫然与孤独(在“灯火高楼”中的“寂寥”)。然而篇幅是这首七绝好几倍的注文却从“和映霞结褵了十余年”叙起,讲到杭州的“风雨茅庐”、美满的小家庭生活,直到作者只身南下,意欲“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而留在杭州的妻子又与“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君”往来甚密。南下就职的经过被郁达夫叙述得不乏雅兴与诗意,然而在后设视角下,这一次南行“实就是我毁家之始”。这是点题之句,叙事线索就此展开。而与诗作所勾勒的宦游人独居情境相呼应,这段注文突显出“我”的“羁留闽地,私心恻恻”,诗歌情境由此成为叙事的一部分。
从郁达夫的信件及其在闽所作文章来看,此时他的恻恻之心不仅源于对杭州妻子的思念,还有着对国土沦亡的担忧。文士风雅在战争威胁下并不能长久,郁达夫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悲观地指出“国难来时,恐与玉石将同焚也!”①郁达夫1936年3月27日致曹靖陶,《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所谓“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破家亡后,对花洒泪岂成诗”②郁达夫:《赠〈华报〉同人》。这首诗刊于1936年6月1日福州《华报》,又见郁达夫《闽游日记》及《记闽中的风雅》两篇散文。郁达夫:《记闽中的风雅》,《立报》1936年4月1日第2版。,在“风雅”同“气节”,“诗”与“国”之间,后者显然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风雅”之诗文教化,须得在关键时刻服务于维持“气节”、保卫家国,这里还是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的责任伦理。
国土危亡在即,郁达夫于1936年11月被派至日本。关于安排郁氏赴日的策划者与具体动机历来众说纷纭③有关这方面的史实考证详见武继平《1936年郁达夫访日史实新考》,《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李丽君《郁达夫1936年访日新史料》,《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而组诗第二首即记述了郁达夫出访日本的见闻:颔联“诸娘不改唐妆束,父老犹思汉冕旒”套用陆游、范成大诗句,或许意指殖民地(途经的台湾地区)人对祖国文化的坚守,抑或指旧友对故土风物的牵恋①据云郁达夫此行的任务之一便是动员昔日创造社好友郭沫若回国。;颈联用“秦关赤帜”暗指西安事变的发生,也隐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独愁大劫到清流”);尾联所谓“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或是对居于高位而政治上无能无节操之人的影射,或可直接解释为对汉奸混淆正伪的斥责。而无论是对沦陷地百姓心态的确认、对西安事变及国情变化的揣度,还是对无节操之人的指射,都不难见出作者在中原危难之时出使“小瀛洲”的责任感与道义体认,整首诗是站在“国”的角度把握战争初期各方势力及社会图景。反观注文,则是在简单交代出使经过后,详细写出了妻子在此期间的“行迹不检之谣”、对×君的亲热以及对自己的疏离等“家”事。两相对比则讽刺之感愈发明显——在自己为国奔波之际,妻子居然与昔日同僚好友行“不轨”之事。
这种诗歌与注文内容的错位在接下来几首作品中越发突显。1938年4—6月,郁达夫以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的身份赴前线视察,目睹了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作战情况,途中也创作了不少诗文。“千里劳军此一行”一诗出现在散文《黄河南岸》中,诗歌所言中原春色、战壕布置(“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在文章中皆有较为详细的描写,文章进而提及战场留诗的背景和意义:郁达夫一行人登上五龙山顶以瞭望黄河北岸的敌军,但因风沙遮蔽,他们实则并未看清北岸的情形,也未在战区多做停留,只得题诗以为纪念,“好于他年收复北平、重经此地时,做个参证”②郁达夫:《黄河南岸》,《烽火》第17期,1938年7月1日。。因诗文之才而被推举为“书记”写下此诗的郁达夫虽未亲自参与战争,但“驱车直指彭城道,佇看雄师复两京”等语已然塑造出历史见证者的姿态。在这里,旧体诗写作似乎可以成为行旅者与环境发生有机互动的一种方式——以边塞诗为模板的“劳军行”里隐含的“自我”终于不再是旅途中“困顿的、苦涩的、烦恼的”③李欧梵:《孤独的旅行者——中国现代文学中自我的形象》,见《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个人,而是凭借书写能力在集体、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中获得了一定位置的主体(战场的“书记”)。写于台儿庄战区的“水井沟头血战酣”一诗同样如此,可与作者《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这类战地通讯式散文对照阅读。然而两首诗后的注文却展现了这个“历史的书记官”所面临的难堪家变——映霞与×君纠缠不清,而×君又似乎很快别有所爱,与映霞疏远。诗注之间的内容差异揭示出参与着全民族战争这般宏大历史事件的诗人个体在家庭与私人情感领域所遭受的纠结创伤。对郁达夫而言,这样的情感伤痛终究无法被历史的大叙事所遮盖弥合。无论怎样追念“平原立马”“佇看雄师”的丰姿,似乎都不能摆脱夫妻情感变故所带来的耻感与痛感。而当诗里的劳军与诗外的私通反复共同出现,其所形成的强烈讽刺性对比或许就具有了某种社会象征的意味——一面是前线军士的血战,一面是党国官员的淫乱;一面是国土危亡,一面是儿女恩怨;一面是历史见证者的崇高,一面是情感受伤者的屈辱,最终——“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①这是苏联记者伊里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的话,曾被鲁迅、茅盾等作家反复引用。见黎烈文译《论莫洛亚及其他》,《译文》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16日。。类似但不等同于“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般针对具体现象的批判,这一在战时逐渐流行的表述句式将世界分为截然对立的两部分,诸如“前方”与“后方”(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受苦”与“享乐”等区分亦从属于这样的对立结构。进一步,这种表述形式在全民族战争情境下建构着一种新的社会图景与伦理框架。即在日寇与汉奸之外,在抗日阵营内部,也有着鲜明的善恶之分,其依据标准就是是否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抗日战争而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战争背景下,“工作”被赋予庄严的意味,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形势下的工作伦理支撑着无数饱受流离贫病之苦甚至性命之忧的个体在艰难的岁月中有所坚守和行动——工作的具体方式及形态不妨多种多样,要紧的在于一种超越私人、超越眼前生活的信念,以及最终落回到私人层面、作用于生活日用的道德规训、行为操守与积极实践。回到郁达夫所面临的家变,则这样一种伦理认知在诗注之间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妻子的不贞不仅仅是妇德的亏损,更是她向另一个营垒——以×君为代表的“荒淫与无耻”一方的倾斜。而“我”对她的诸般劝导挽留,也可以视为将她争取到“庄严工作”的世界所做的种种努力。这样的伦理意识在后面几篇诗作与注文中得到延续。如第十一首“闺中日课阴符读,要使红颜识楚仇”,就诗句而言可以看作男性对不谙世事的女性的教育,而注文所言妻子贪恋舒适的生活、指责丈夫“太不事生产”,则似乎又暗示着作者要让妻子明白何为真正的“生产”——这自然指向上述所言的工作,而非郁达夫笔下妻子所向往的博取名位、获得金钱。在最后的《贺新郎》一词中,郁达夫以“衡门墙茨”“桑中芍药”“私欢弥子”等典故反复暗示了自己所遭受的“奇羞”,而又以“匈奴未灭家何恃”一语表明了为国事而弃私情的决定。然而对不轨之事的指涉,“拼大敌”与“歼小丑”的并置仍呈现着抗战阵营内部的社会图景与伦理结构。“大敌”当然要拼,肃清我方队伍里的“小丑”也同样重要。这或许是郁达夫在战争期间以组诗写私事、以诗歌加注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并分送文坛政界诸人的又一内在动机——揭露“小丑”的面目,并在对立的两个世界间明确自己的选择。同较为传统的性别伦理内核相似,战时新的伦理框架在文学中的呈现与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疗愈着个体的情感创伤,并帮助其在社会历史中确立着自身的身份位置与行动的可能。
值得关注的是,这类诗注互文的文本形态在现代作家的旧体诗创作中或许成为了某种典型现象。如冯沅君作于1939年的《丁戌纪事并注》就以教会学校中人的视角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城形势氛围的种种变化,其诗注之表达方式与情感内涵的差异亦被研究者发掘:“注释就事论事,平铺直叙,不掺杂个人的感慨、议论;而纪事诗的结构方式,则跳出燕园这个安稳的小世界,引入‘塞北江南’的战争场景,与校园内外的歌舞升平形成极大的反差,褒贬之意寓乎其间”①冯沅君:《丁戌纪事诗并注》,《宇宙风》1939年3月1日创刊号;对这一组诗的分析见袁一丹 《沦为“孤岛”的教会大学》,收入《此时怀抱向谁开》,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62页。;再如沈祖棻《涉江诗词集》中作于抗日战争与两年内战时期的部分作品在结集出版之时由其夫程千帆加以笺注,意在记述词作所对应的时事及作者之情思寄托②沈祖棻:《涉江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对于程千帆笺注的分析参见舒芜《前无古人的笺注》,《读书》1996年第5期。;金克木晚年亦将所作旧体诗整理结集并自加注解,以发其“隐情”③金克木:《挂剑空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对于金克木旧体诗与注文的分析参见檀作文《诗可以隐情——金克木旧体诗读后记》,《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一辑,2004年1月15日。,可见即便以辞意较为隐晦、相对脱离“现实/现时”的旧体诗为表达工具,作家们也大都不愿放弃直面时代经验、言说心曲并寻求交流共感的可能。而这类旧体诗笺注的旨归和效果已然不限于记录“本事”发明“题旨”①任二北:《词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7页。,变“隐”为“显”从而寻求更多人的同情理解,还在于将断片化的诗歌情境连缀为有逻辑可循的叙事脉络,并将一己的情感经验融入历史进程——借用已有的说法,这其中或许体现着“抒情”与“史诗”追求的某种辩证。然而在诗注之间,在多重时空与不尽相同的视角下,体验与追忆,本事与演绎,“古典”与“今典”,讽喻与感伤乃至叙事与修辞间的种种张力也得以体现。或许从中亦可窥见现代社会中人的伦理处境之一面。
三 伦理、情感与修辞
在《毁家诗纪》及与之相关的文本序列中,如果将诗歌的注文及郁达夫讲述国变家变过程的散文作品一并视为作者对自身情感经历及国家战争情势的“叙事”,那么与之相对,这组旧体诗作本身则更可以被看作“修辞”式的存在。②这里借用了袁一丹在《隐微修辞:北平沦陷时期文人学者的表达策略》一文中的说法。文章从修辞的角度分析了沦陷区文人学者的历史经验、伦理境遇与表达心曲的途径。认为“与波澜起伏的战争叙事相比,沦陷——军事占领区的非常状态,久而久之成为生活的常态,一种‘无事可叙’的状态。由于大写的历史主体的缺席,沦陷区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是破碎的,很难捏合到一块……而芜杂的‘修辞’正适于搜罗、打捞这些无事可叙的、零散的经验碎片”。袁一丹进而指出,修辞总包含着一种历史意识,“历史是修辞的材源,或者不妨将其视为修辞的底本、范本”,修辞不仅能为历史场景命名,还可以提供相应的处理方案,“一份囊括思想、行动、态度、情绪的词汇表,引导人进入并逐渐适应某种不可逆转的环境”。与此同时,修辞冲动还时常与个体遭逢的伦理困境密切相关。见袁一丹《隐微修辞:北平沦陷时期文人学者的表达策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这里借用叙事与修辞的对比,意在突出后者对细碎个体经验的赋形能力与微言大义、一言多义的可阐释性,以及相比于“史实”,修辞与“心事”间更为内在的关联。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形态或许更为细碎多样,昭示着言意之间的多种勾连方式,以及语言表情、达意、审美、正名等繁复的功能,亦是见微知著、通向语词深处文化层累及个体心事的路径。也正是在针对情感经验的修辞性表述中,新旧伦理的碎片及作者对之进行取用整合的过程逐渐浮现。如上所言,在《毁家诗纪》中,郁达夫通过化用典故成句等修辞方式召唤、建构了以传统性别伦理为基础的旧文人的身份想象与伦理世界,又在诗作与注文的张力间呈现了战时社会分化与新的伦理认知,以此疗愈着自身在情感经历中遭遇的创伤并最终以“家国”大义统合、超越了“儿女”私情。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组诗作中旧典新用、情境叠合、表达的跳跃性与对词句细节的多般斟酌调整都透露出诗歌修辞技术进而是情感态度、伦理认知层面所具备的复杂特征。
对于郁达夫而言最为关键之处或许在于,无论以新或旧怎样的伦理框架解释“毁家”的经过,都无法安置不断搅扰其心神的各种形态“余情”。如在“戎马间关为国谋”之际,诗作仍不忘以“梅妃里”“燕子楼”指称所到之地,仿佛此行不是劳军视察,倒是去游历南北考察各种艳事,这仍是郁达夫文人情致的体现。再如组诗中的第七首:
清溪曾载紫云回,照影惊鸿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
伤心王谢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后杯;
省识三郎肠断意,马嵬风雨葬花魁。
颔联“琵琶别抱”“稽郡重来”用朱买臣贫贱时遭妻子嫌弃、衣锦还乡后另改适他人的妻子羞愧不堪的典故,自然是在上述所言新旧伦理结构的共同支撑下对妻子之私情的判定,但首联化用陆游与唐琬分离后重游沈园所作诗句,则分明携带着对夫妻感情的不舍与留恋。颈联的情理样貌则似乎更为复杂:“王谢堂前燕”原作本是对朝代更迭盛衰无常的感喟,“新亭之泣”的典故背后则是“风景”与“山河”、自然景物的恒常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之间令人痛惜的对照。而结合注文所言“沈园再到之感”(沈园的意象和典故在组诗中反复出现),则这里的两个典故与其说表现了面对国家危机的兴亡之忧(此时郁达夫负担着战区视察的任务),不如说更多地流露着针对家事变化的今昔之情,这或许是溢出了伦理结构的情绪。关于尾联“马嵬坡”之典,则还有他意可寻。郁达夫曾在《历史小说论》一文中提出并赞赏了朋友(应为鲁迅)对马嵬坡史事的“新解”:以唐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指杨贵妃)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恶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所以这时候(指马嵬坡兵变),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①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如此以恋爱心理学的方式考察历史,则“三郎肠断”之意大概会获得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另外考虑到郁达夫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这里的“三郎肠断”就不仅指唐玄宗,或许也是自指。
更有甚者,情感因素似乎在几首诗歌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比如第十五首: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应陈仪之邀,郁达夫在避居湖南汉寿两月后再度赴闽,途经浙江一带复被熟悉的景物牵动情思。前一首诗尚以伍子胥自比申明报国之志,此首则基本是对儿女之情的叹惋流连。或许是桃叶、红儿等名姬美妾的韵事勾起了郁达夫对王映霞的怀恋,“君去我来”之间纵有种种不轨之事的疑影,也仍不免在旧地重游之时做一番“天荒地老”的慨叹遐想。他日之“讼”(注文所言“离婚的讼词”)自是极为烦琐难堪的人间事,此时之“情”却似乎仍有无限放大、超越时空的意味。在这样的诗作中,国难、战火等时代痕迹也几乎消失不见,所剩下的只有一个徘徊于酒楼歌馆的多情士子,沉浸于文学想象所搭建的内部世界,百转千回,顾影自怜。
建构伦理图景与处理不断溢出的情感因素的努力也许终于让郁达夫意识到现代化战争为家事国事带来的深切变化。即如组诗第十七首几乎完全照搬了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一诗的模式,但在原诗中尚且存在的恒常风景也已消失不见,便是“梦中”也难寻“去年”的踪迹了。原作浅淡的伤感在这里演变为面对剧烈变化的震惊。接下来的第十八首也出现了“人面桃花”之典,与“丁令威化鹤”的典故(“身同华表归来鹤,门掩桃花谢后扉”)一同言说着对“变”的体认(“江山依旧境全非”),并企图获得某种超越性视角。但随后却以樊素之“肥”暗讽妻子的追慕富贵,以乐天与樊素的对比再度凸显“一方面……一方面……”之伦理体认(“老病乐天腰渐减,高秋樊素貌应肥”),似乎意在用讽刺化解感伤。尾联则再一次出现了朱买臣的典故而又赋予新意:朱之求官实是“多情”之故,“量似太窄,然亦有至理”。此是为古人开脱,亦可视为自述。而这般“多情”在文学想象中被一遍遍加深描重,以至诗句对家国伦理的追寻也被紧紧裹挟在情感的旋涡中,似乎缺乏了真正进行理性推衍的可能。
这样一种情与理、个体境遇与社会认知的交错缠绕实则是郁达夫旧体诗的某种普遍状态。即如为人所熟知的《钓台题壁》: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①郁达夫:《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见詹亚园笺注《郁达夫诗词笺注》,第326~327页。
这首诗作于1931年1月23日郁达夫在上海时,题目又作“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而在1932年写就的游记《钓台的春昼》中此诗亦有出现,它穿插在白话散文的表达中间,似乎与整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构成了互文性。有学者注意到《钓台的春昼》风景描写的美感来源与审美视角,指出如“照片上威廉·退儿的祠堂”“珂罗版色彩”等比喻意象背后正是19世纪西方的印刷资本主义文明,而这样的风景书写亦可被纳入西方现代性的美学谱系。②吴晓东:《拟象的风景》,见吴晓东《文学性的命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8~90页。但另一方面,这里用以观照和书写“风景”的文化资源仍是多样的。相比于审美兴味,出现在其中的这首旧体诗则更多呈现出作者对社会情势的判断(对“时事”的指涉,比如“劫数东南”“帝秦”)与自身的伦理选择——结合上文,在鸡鸣风雨、东海扬尘、“义士纷纷说帝秦”之际,诗人以之为言行模板的是从往古到近代能够独善其身的圣之清者。旧体诗的引入为游记在审美维度之外丰厚了伦理政治等意涵。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恐怕仍是诗歌中的情感表述——所谓“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自我感伤之外也流露出某种自得之感。若向深处挖掘,这恐怕仍与作者在性别伦理意识中的优势心态有关。但其实,这首诗中“佯狂”的说法更值得仔细玩味。佯者,假装也。在郁达夫这里,无论醉酒还是多情,有时都可视为一种扮演。而文学表达中的这类模拟或扮演,更宜从修辞行为的角度审视之——“自叙”的说法太容易令人相信作者与笔下形象经验感觉的一致性,而“修辞”则揭示出作者以文学的方式对情感经验进行夸张、细化乃至“编造”的诸多步骤。进而,对这种文学化的情感状态的建构和自我赏析与伦理意识一并构成了郁达夫消化历史经验、确认自我形象和位置的重要途径。
在文学表现技术之外,“修辞”的古老目的还在于说服。①详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论述,亚氏的修辞学不止于说服技巧与言语逻辑,其本身也与诗学、伦理学、政治学密不可分。日本学者佐藤信夫在梳理修辞学发展史时概括出修辞的双重作用,即“说服的表现技术”与“艺术的或文学的表现技术”。见佐藤信夫《修辞感觉》,肖书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对郁达夫而言,写作《毁家诗纪》的过程大约首先是一种面对社会形势变化与情感创伤时的自我劝服。进而通过发表与流传,诗作或许还被期待着召唤出共通的伦理意识,或寻求情感的理解与共鸣。只是如此跨越“公”与“私”的界限、模糊“生活”与“艺术”的分别②Haosheng Yang,A Modernity Set in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p.88.,则又会为有关修辞本身的伦理带来新的困境③比如,在修辞行为中怎样定义“公”与“私”的界限?文学表达是否应该或如何保护所涉对象的隐私权利?报刊出版等市场运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甚至制造修辞?“修辞”与“诚”的古老关系又该怎样理解?。
经历了婚变远走南洋的郁达夫依然需要在战争烽火里为自己寻找安顿身心的渠道,而旧体诗写作仍旧承担着这样的功能。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新加坡撤离隐居于苏门答腊岛的郁达夫又创作了组诗《乱离杂诗》④这组诗作的写作及发表过程详见詹亚园笺注《郁达夫诗词笺注》,第562~563页。。在这里,“旧”与“新”的交织碰撞及诗人面对时代风雨和自身遭际时的情感变化表现得更为复杂缠绕。⑤这一组诗亦与郁达夫的又一段情感经历有关。彼时郁达夫的女友在新加坡任联军广播电台广播员,故而诗中有“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之句,呈现了硝烟烽火中现代爱情的独特传达方式。比起“伤心王谢堂前燕”对物是人非的感慨、“夕阳红上海边楼”式的风景观照,《乱离杂诗》中 “空梁王谢迷飞燕,海市楼台咒夕阳”之语似乎更加体悟到传统认知与表达方式的失效性。“古今合一”的幻境也终于被不断遭逢的新经验打破。历经乱离的个体时而试图摆脱优柔感伤的姿态,追慕先贤在乱世中实现道义担当(“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时而沉浸在对儿女之情的无限牵恋中(“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时而渴望与相爱之人共同隐居(“终期舸载夷光去,鬓影烟波共一庐”),时而又意识到自身所处乃是完全迥异的时空环境,旧有的经验模式乃至伦理框架已然面临失效。这不是宦游、不是流放、不是公子名妓遁走江湖,而是真正未知前景的漂泊。在这种境地里,一介文人究竟能做什么?郁达夫对此的回应颇有几分沉痛无奈,所谓“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①郁达夫:《乱离杂诗》,《郁达夫诗词笺注》,第571页。,化用黄仲则的诗句(“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却也没有了原诗在沉郁中焕发出的些许奇情异想,而只得在对自身之“微情”的反复咀嚼中安顿身心。在这里,属于个人的情感经验甚至不再能导向某种社会认知与伦理建构,而只做了“苦吟”的诗料。或许在修辞行为中,郁达夫最终获得的仍是情感的满足与耽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