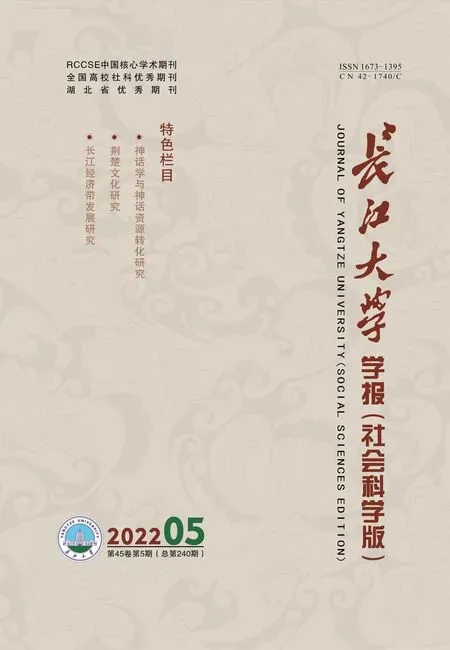楚国商贾文化透视
孟修祥
(长江大学 楚文化研究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自华商始祖王亥“肇牵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1](P206),开华夏商贾文化之先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都曾有着高度发达的商贾文化。从文献中所描绘的楚国繁华都市,即可见其一斑:“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2](P23)当时的郢都堪称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之大都会,车辆、民众、商铺都显得十分拥挤,以至于“朝衣新而暮衣蔽”。与其有着相似描绘的是齐国临淄:“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3](P33)由此可见楚齐两国都城繁华富庶的商贾文化状态。楚国深厚的商贾文化土壤不仅产生了商圣范蠡及其丰富珍贵的商贾理论思想,而且产生了楚人可贵的商贾文化精神。本文试作文化透视,以探寻楚国商贾文化生成的主要原因。
一、丰富的自然物产与手工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商品经济基础
楚国物产之丰富记载于历史文献者甚多。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重耳之言:楚国盛产珍禽灵羽、异兽皮毛、角牙犀革、丝绸锦帛,波及到晋国的只不过是楚王享用之余而已。(1)参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子女玉帛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73页。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4](P356)楚国不仅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自然物产,而且非常重视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以增加粮食作物与农副产品的产销。如孙叔敖担任令尹之前,“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5](P326),这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名为“芍陂”,因灌溉农作物而使百姓受益,从而得到庄王的赏识。到战国时期,楚国农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同时也重视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由于楚国地广人稀,吴起变法时曾向悼王提出自己的看法:“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当他的变法主张得到悼王的支持后,果断“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6](P283)。这项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减贵族特权,却促进了边地开发,增加了国家粮食作物与农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后来的“宣威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苏秦游说楚威王所说的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7](P500)并非虚言。张仪曾称道秦国“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然后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7](P504~505)。可见当时楚国军队的强大与粮食的储备与秦不相上下。从而形成“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的对峙局面。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到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楚国尚能对抗秦国半个多世纪,足见其如苏秦所言“粟支十年”是有依据的。
楚国丰富的物产与充足的粮食自然衍生出各样各色的农副产品,如《楚辞·大招》描绘其丰富的农副产品云:“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8](P442)《楚辞·招魂》亦云:“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梁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籹蜜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8](P414)这里既有五谷加工而成的各式各样的点心、饮品,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加工而成的美味佳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更确证了当年楚国自然物产丰富、粮食充足,从而衍生出农副产品的丰富性。战国时期的楚国不仅粮食丰收,农副产品的种类甚多,与文献资料所记载的完全吻合。加上铁器冶炼技术成熟(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昭王语:“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73页。,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楚国农业的生产力,从而带动商贸业的迅速发展。
楚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促进了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不断提高的纺织技术,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纺织品种,从而使其成为楚文化六大支柱之一。仅从1942年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算起,到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大量丝织品的出土,几十起之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了《楚辞·招魂》所谓“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8](P408)描绘的真实性。纺织业的兴盛,带来了管理上的提升,楚国当时至少有“织室”“中织室”两个官方专门机构来管理纺织手工业的生产。市场的需求带动纺织业的繁荣,但进入市场的纺织品必须符合销售标准,当时国家的统一规定是:“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不鬻于市。”(3)参见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32页。严格把控质量关,使精美的纺织品不仅销售于华夏地区,而且远销阿尔泰,在原苏联乌拉干河流域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保存完好的中国丝织品,就是确证。(4)(苏)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记载:巴泽雷克发掘了一些石顶巨墓,“由于墓土封冻很结实,墓中还很好地保存了中国丝织品和其它物品。”潘孟陶译,《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另外,战国时期,楚国的髹漆工艺水平极高,从而创造了人类物质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漆器。战国后期的漆器,不仅纹饰富丽,造型生动,而且数量众多。还有各种青铜器、陶器、玉器、竹木器、革制品等等各种手工产品的出现,足以说明楚国丰富的自然物产与手工劳动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商品经济基础。
二、完善的管理制度提供了商品交易有序进行的制度保证
根据《易经》记载,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9](P86)这应该是商品交易管理伊始的现状,故《汉书·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10](P112)炎帝时代的这种临时性商品交易市场具有原始特点,而真正建立商品交易管理的明确记载始于《周礼·司市》: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价,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涖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涖于介次,而听小治大讼。凡万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11](P734)
由此可知,周代商品交易的市场管理已很规范,且具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胥师、贾师则在市场管理办公场所“思次”“介次”,负责处理商品交易中出现的各种争讼之类的事务。故桓宽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12](P1)由于管理到位,市场秩序井然。
楚国当时已有“郢市”“蒲胥之市”“鄵之市里”等各种类型的商品交易场所。所谓“郢市”,即郢都城中的市场。按《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记载,(5)《周礼》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一夫是计量单位,“方各百步”,而市场大都设在宫殿北部。《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7页。商品交易市场大都设在宫殿北部。《古竹书纪年》所说的(梁)惠成王十七年“有一鹤三翔于郢市”中的“郢市”即是,因为郢都是君王所居之地,亦也可称之为“王市”“国市”。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有一段关于“郢市”货币管理的记载: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13](P339)
当时楚国市面流通的是“蚁鼻钱”,因为“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请遂令复如故”,使金融流通秩序得以恢复,“三日而市复如故”。市令就是“郢市”管理的政府官员,可以直接跟令尹孙叔敖汇报市场货币使用情况,应该是市场管理的高级官员。另外,还有“市工”“市人”等下属吏员与“市庸”等市场雇佣人员。[14](P154)楚国既有“市令”“市工”“市人”的分工管理,那么,肯定也有类似于《周礼·司市》“思次”“介次”这种负责处理商品交易事务的市场管理办公场所。据《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记载:“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15](P103~104)所谓“贱丈夫”,即不良商贾,为了避免不良商贾垄断市场,就必须“有司者治之”。至于司治之职的名称,不同地域的称呼不同,如周称“司市”,郑卫之地称“褚师”,齐国称“市椽”,鲁国称“贾正”,楚国称“市令”“市工”“市人”等即是。
楚国“蒲胥之市”的记载,最早见诸《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16](P136)寝门即君王就寝处之门,即内门,“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则说明“蒲胥之市”离宫城不远。蒲即为生长于江河之滨或湖池之内的蒲草,“蒲胥”又作“蒲疏”,楚国水上交通便利,“蒲胥之市”应该是建在长有蒲草的渡口之类的水边交易市场。
郊市则是都城郊区的市场。包山出土的63号楚简中有“鄵之市里”的记载,很可能就是楚国当时的郊市名称。(6)参见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楚国封君有邑,官员有州,除“纪郢”“陈郢”和“寿郢”是比较明确的三个都城,还有包括鄂、鄢、鄀、陈、蔡、城阳、项城和钜阳等楚之别都,加上邑和州,老百姓为生活所需,必然有各种不同的商品交易市场,只是其名称失于文献记载与地下,尚待发现而已。原楚地的很多地方现在仍然保留“草市”之名,也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民间自然形成的临时交易市场。发展到东晋时,才有“草市尉”,开始对其进行管理。
由于商业发达,市场繁荣,处于鼎盛时期的楚国商贾非常活跃,其中既有如《韩非子》所说的“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的“贩茅者”,又有如《庄子》所说的“索我于枯鱼之肆”“屠羊之肆”等各类商贾小本经营者。而出土五件鄂君启节中的铭文,则明确记载了楚怀王时期对官商税收管理等方面的行政管理制度。鄂君启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的免税通行证。铭文严格规定了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有关折算办法,以及水陆运输的范围与禁运物资等具体内容。如其舟节铭文云:“屯三舟为舿(舸),五十舿。”车节铭文云:“车五十乘。”可见鄂君启拥有一支庞大商队。因为持有“毋征”的免税特权金节,这支由车、船组成的商队从其封地鄂出发,可到达楚国的任何地方。但马、牛、羊等例外,得由朝廷大府征税。(7)大府乃掌府藏会计,掌管朝廷货物、宝器收藏,属国家一级财务机构。楚地出土的《大府置》《大府敦》《大府镐》《大府铜牛》《大府铜量》等均能说明。《周礼·天官·大府》云:“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7页。而军用物资是禁止出境的,故节文云:“母(毋)载金(铜)、革(皮革)、黾(竹箭)、箭。”时间限制为“岁赢返”,即一年之内往而必返,不许长期停留在外。鄂君启节的各项规定,说明战国时代的商业经营,其时间限制与军事物质的管控也是很具体严格的。

到战国时代,楚国的度量衡器具已日趋齐备,从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出土的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不少天平和法码等衡器与铜尺之类的量器来看,更加体现商品交易的有序性与管理制度的完善性。由此可知,当时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市贾不二”(8)《孟子》云:“‘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的价格论不仅在齐地受到孟子的批判,在楚地也是显然行不通的。
三、畅达的交通提供了便利的商品流通渠道
古人早已指出:“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12](P3)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的繁荣与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4](P356)。司马迁言楚都“其民多贾”,指出了所处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商贾众多的原因。战国时期,以郢都为中心,伴随着楚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版图的不断扩大,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得以形成。鄂君启节铭文可以作为力证。楚之北方有著名的“夏路”(9)《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楚适诸夏,路出方城。”《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09页。,经鄢、邓至楚国冶铁基地和商业贸易中心的宛地,再出方城通往北方诸国。(10)以楚之宛、陈而论,“楚之宛丘……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盐铁论》,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页。然后折向东,经淮水流域直达齐地。西面可经丹淅、越武关进入秦境。沿长江东下吴越而至海滨,若溯江而上,西经三峡而通巴蜀。由江入湘、资、沅、澧,南达两广、云贵,西南方已是楚人的畅通之域。庄蹻王滇,就某种意义而言,也为商路的开通提供了条件。庄蹻乃楚之名将,《荀子·议兵篇》说:“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鞍,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19](P182~183)《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有由蜀、滇通向南亚的一条五尺道,又称滇僰古道,庄蹻王滇后对此道云南段的修筑肯定是有贡献的。(11)《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29~330页。关于庄蹻的相关学术探讨不在此展开。自秦时打通五尺道,后世由五尺道逐渐拓展延伸,而演变为茶马古道,对促进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的商贸繁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战争不断,但在相对和平时期,诸侯各国仍然确保商路畅通。如《左传·成公十二年》所谓“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16](P161)。晋楚如此,其它诸侯国之间亦无不如此。
水陆交通的发达,为楚地商品的输出与外地商品的输入提供便利。《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16](P237)北方的燕赵、齐鲁,与楚国“通鱼盐之货”,商品交易很频繁。东面滨海诸国的许多海产品也是楚人生活的必需品。仅从《楚辞·招魂》所谓“秦篝齐缓,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百日些”,《楚辞·大招》所谓“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吴醴白蘗,和楚沥只”,《楚辞·九歌·国殇》所谓“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记载来看,来自秦、郑、晋、吴的物产是相当丰富的。尤其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推动了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众多学者认同,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存在一条丝绸之路。著名文化学者刘玉堂认为,楚国同南亚甚至西亚之间存在商贸往来……有学者从荆楚的国力、影响和地理位置,以及“荆”语音上相近等分析,认为那时摩揭陀王国“支那”一词即指“荆”(楚国)……印度学者哈若帕教授撰文说:春秋时代,有一个叫“荆”的强盛国家,也称作“楚国”。很有可能,中国(China)名称之外播就是这块繁荣地区通过产丝的南方与中国西南部,与域外丝绸贸易所致。这条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其起点是当时楚国的都城——郢都(纪南城),辗转接力式开辟而成。(12)参见《众多历史文化学者提新说:楚人开辟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湖北日报》2018年12月23日。
公元前五世纪楚地的丝织品经过印度传到西方,而西方如“蜻蜓眼”之类的玻璃制品也经印度传入中国。有人根据战国时代楚地大量玻璃制品的考古发现,而将南方丝绸之路称之为“玻璃之路”也无不可。“腓尼基商人经营的商品有杉木、橄榄油、紫色染料、织物和玻璃制品,同时还把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香料以及西亚的珍珠卖给希腊、罗马。正是这些辗转式的贸易和交流,开创了楚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的先河。”[20](P265)
四、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商品流通的安全保证
所谓综合国力,就是指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等综合形成的实力。自古至今,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越强,提供商品流通安全保证的能力越强,商贾文化越发达。从楚国八百年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楚人处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时,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贾文化的。伴随楚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尤其是军事力量逐渐强大,版图不断拓展之后,商贾文化才有了不断发展的空间。如公元前690年,楚武王总结前两次伐随的经验,经过充分准备后,开始第三次伐随。虽然武王于征途中不幸病逝,但“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16](P29)。楚军战前准备了齐全的交通设备,扫清路障,溠水架桥,打通伐随通道,以强大的武力逼随求和。由此而阻断周王朝的金锡之路,使作为战略要地的随枣走廊落入楚人的掌控之中,控制大冶铜绿山矿,将“汉东诸姬”的战略物资基地“铜矿”收入囊中。再如楚成王时代,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不仅北上抗齐签订召陵之盟,而且继续北上,经泓水之战,楚成王实霸中原。至楚庄王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经邲之战大胜晋军,而后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称霸中原,楚国的实际控制范围存在于哪里,商贸活便拓展到哪里。
楚国发展到“宣威之治”,综合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苏秦为赵合纵,游说楚威王曰:
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阳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7](P500)
此虽系纵横家之言,但与历史事实基本吻合。庄蹻入滇,就在威王之时。威王伐越,“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21](P209)。就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吴越青铜兵器而论,不仅因为征伐与吴越文化进行特殊交流,还有政治联姻、工匠流动等成为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化,从而带来商贸活动的拓展也成为必然。
当楚国的综合国力处于鼎盛期时,疆域几乎囊括半个南中国,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强大的国力,带来了商业活动的空前活跃,楚国经贸在诸侯各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荀子·王制》记载:“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19](P102~103)
这里所谓南海、东海,实际上是指楚国控制的广阔疆域。其实楚国与中原各诸侯国进行商品交换远非如此几种类型,自然物产还有洞庭之鳟、云梦之芹、云梦之柚、江陵之橘,鱼鳖鼋鼍、松梓楩楠,手工制品如丝织品、青铜器、漆器、陶器、玉器、竹木器、革制品等等,不胜枚举。楚怀王曾骄傲地对张仪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7](P540)齐相管仲曾充满羡慕之情地说:“楚有汝汉之黄金……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22](P392)可见楚国黄金丰富储藏的商品价值与意义。
《周易·系辞下》有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9](P87)作为“以利天下”的小额商品,互通有无,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进行,但是,如鄂君启由一百五十艘船、五十辆车组成的庞大商队,很可能会遇到“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墨子·贵义篇》),考虑到安全问题,就不可能轻易到他国去进行商贸活动了,因此他的商队也只能活动于有强大军队保护的楚境之内。
五、独特的智慧彰显出楚人的商贾文化理论思想与人文精神
楚国繁荣的商贾文化凝聚了楚人的智慧,产生了楚人的商贾文化理论思想与人文精神。归纳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尊重商贾社会地位的崇商观念。在先秦以及后世对四民的排列顺序一般为“士农工商”,士为先;而楚人的排序则与之不同,是“商农工贾”,商为先。《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16](P129)楚人以商为“四民”之首,反映了楚国对商贾文化的重视,对商贾社会地位的尊重。接此,后面还有一段话:“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16](P129~130)这说明对商贾社会地位的尊重,是贤君无敌于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是军队团结一心,强大无敌而“事不奸”的前提,事实上楚国自上而下形成尊重商贾的社会氛围即如此。
其二,行君子之道的爱国奉献精神。《荀子·儒效》曾云:“通货财,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19](P78)本来荀子意在阐述其“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徧能”的道理,但楚国商贾既能“通货财,相美恶,辨贵贱”,也能行君子之道。如屠羊说不仅善于经营自己的小本生意,更有其爱国奉献的君子精神。《庄子·杂篇·让王》:
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昭王反国,将赏从者。及屠羊说,屠羊说曰:“大王失国,说失屠羊。大王反国,说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又何赏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说曰:“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王谓司马子綦曰:“屠羊说居处卑贱而陈义甚高,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说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也;万钟之禄,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复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23](P190)
从文中不难看出,屠羊说就是大隐隐于朝市、具有极高思想境界的仁人君子。拒三公之位、万钟之禄,而愿重返屠羊之肆,足以说明其立功不受赏的爱国奉献精神。楚国哲学家詹何曾说:“为国之本在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24](P214)做点屠羊的买卖,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一旦国家有难,则挺身而出;功成身退,隐姓埋名,这种精神就越发显得难能可贵。曾国藩曾有诗《沅甫弟四十一初度》云:“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这种感悟尤能给人以启迪。
其三,重视农耕,主张农商俱利的思想。楚国立国之初,就注重“广辟土地,著(赋)税伪(货)材”[25](P272),如孙叔敖一方面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鼓励老百姓秋冬两季进山采伐林木,以便在春夏时,河水上涨便于运木材出山。百姓农商两不误,“各得其所便”(13)《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者……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19页。。商圣范蠡也是主张农商俱利,他提出的三八价格就充满了睿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4](P355)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是否为最佳商业运作,我们姑且不论,但农商利益平衡,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则是基本原则。孙孙敖、范蠡农商俱利的治世理政思想具有代表性。
其四,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自我的利害关系的一致性。以范蠡而论,他离开越国后选择齐地,是因为“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采布帛鱼盐”[4](P355)。具有良好的产业条件,于是“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多种经营,“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21](P210)。就在他发家致富后,“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21](P210)。声望如日中天的范蠡,出于对社会政治环境的考量,举家迁徙,“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21](P210),经过几年的经营,积资甚巨,又成为有名的富商。这与其“持盈、定倾、节事”的思想深有关系。范蠡将“持盈、定倾、节事”与天、地、人结合而论,“不溢”“不骄”“不矜”,充满了“天人合一”的辩证思想,也是其德、法、术三才兼备的智慧体现。
其五,富而好德、儒道合一的思想。范蠡“三聚三散”的人生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他曾与文种辅佐越王勾践,成灭吴兴越之功。而后,毅然辞官远行经商,可谓“一聚一散”;至齐国而为巨富,看到潜在危机,慨然归还相印,将家财散给乡邻,再次隐去,可谓“二聚二散”;于定陶,自称陶朱公,把握商机,又成巨富。因次子犯罪,舍弃钱财而予施救,可谓“三聚三散”。范蠡遵天道而循儒教,是儒道合一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楚商。有人论范蠡云:
蠡岂止知相其君而已哉?知人知世知时知事者也。知天地之玄机,合阴阳之窍节,与时俯仰,当用则用,当舍则舍,当进则进,当退则退。用则忍人之不能忍而全人之国,舍则弃功名富贵如粪土而全其身,进则生聚教训而报国家之仇。一霸越国,退则躬耕力作而泽及戚里,三聚复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犹善其身,蠡殆完人乎!(14)参见孟修祥《荆楚文化之思》,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9~280页。
六、结语
有关楚国商贾文化已有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的大量出土,展示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盛况。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丰富的自然物产与手工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商品经济基础,完善的管理制度提供了商品交易有序进行的制度保证,畅达的交通提供了便利的商品流通空间,而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商品流通的安全保证。深厚的楚文化土壤,孕育出楚人的商贾文化理论思想与人文精神,彰显出楚人在商品经济领域的独特智慧,即或在当今社会,对于致力于发展商品经济的人们,仍有其值得传承与借鉴的文化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