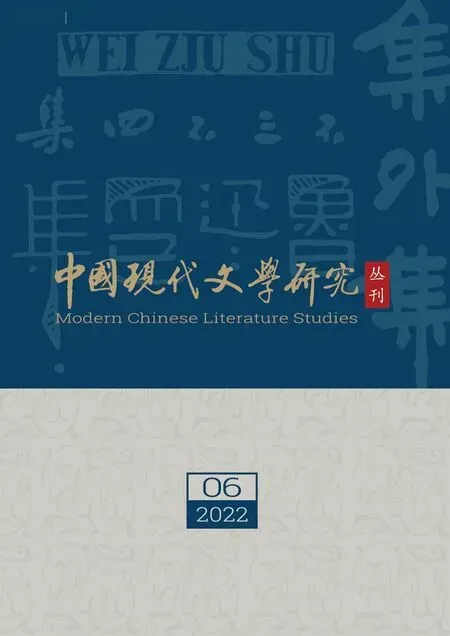主体、抵抗与革命的潜能
——论竹内好的“终末”美学
王 钦
内容提要: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因其鲁迅研究而为国内学界所熟知,迄今已经提炼出诸多意在整体把握其思想方式和问题意识的表述,如“文学精神”“文学的方法”“情境中的思考”“虚线的抵抗”等。不过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很少有论者提到竹内好思想中的“终末观”。强调这一对其思想而言至关重要的视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竹内好的文学或美学思想及其背后的政治指向,也能在一个重要向度上使我们将竹内好和另一位与之若即若离的同时代思想家——保田与重郎联系起来并探讨差异,从而更加分明地辨析竹内好在现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地位。同时,在竹内好的“终末”视角下,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位置的中国和亚洲,才真正显示出新的政治和革命的潜能,甚至提示重新理解和塑造世界的想象力。
引 言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1910—1977)已经因其独特的鲁迅研究而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除了其鲁迅论,竹内好有关赵树理、茅盾、郁达夫等中国作家的研究也已经或正在得到译介;与此同时,在思想史领域,竹内好所探讨的日本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差异和其中蕴含着的中日两国对于欧洲侵略的不同态度——凝结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转向”和“回心”这两个概念——以及他在《近代的超克》(1959)等文章中对于日本在20世纪的亚洲侵略和殖民历史做出的争议性判断,都激发了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重新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源于西方的文明论话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民族的政治主体性的形成等重要议题。面对竹内好的涉猎主题之广泛——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日本战后思想研究,从日本共产党批判到其对于战后宪法的思考——研究者试图提炼出一些能够整体性地把握竹内好的思考方式和问题意识的表述:无论是“文学精神”“文学的方法”“情境中的思考”还是“虚线的抵抗”①分别参见岡山麻子『竹内好の文学精神』,論創社2002年版;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鶴見俊輔『竹内好——ある方法の伝記』,岩波現代文庫2010年版;子安宣邦『「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青土社2008年版。,都试图从竹内好对于主体与知识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事件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的探讨中,找到一条串联所有论述脉络的线索。这些说法都准确且富有启发地把握了竹内好一以贯之的思想关切。不过,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很少有论者提到竹内好思想中的“终末观”,而我认为,强调这一对其思想而言至关重要的视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竹内好的文学或美学思想及其背后的政治指向,也能在一个重要向度上使我们能将竹内好和另一位他与之若即若离的同时代思想家——保田与重郎联系起来并探讨两者的差异,从而更加分明地辨析竹内好在现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地位。根据竹内好的独特理解,“终末观”褪去了它原本的基督教色彩;作为一种历史观、也作为一种政治本体论视域,竹内好通过它来强调事物的生成、变化、发展直至消亡过程中的偶然性,凝视事物在只能称作“无”的状态下所汇集的能量,从而在独特的思考脉络上重新演绎一系列源于欧洲的政治概念,如“主体性”“平等”“权利”“自由”,等等。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竹内好通过“终末观”视野所做出的对于鲁迅、毛泽东、冈仓天心等亚洲思想家的阐释表明,政治的现实从来都不能被还原为既有的、实体意义上的存在,无论它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既定的国际秩序或实利政治(realpolitik);恰恰相反,正是在被压抑的、居于弱势地位的、无法自我表达、甚至无法通过稳定的政治形式而自我呈现的存在者那里——在竹内好笔下,它的名称可以是“中国”“鲁迅”“毛泽东”“亚洲”或“第三世界”,等等——我们才能揭示有待自我实现的革命性政治的潜能,它将会重构国际和国内政治的版图,重构战争与和平的秩序,重构集体的生活方式乃至人性的法则。在竹内好看来,这一前景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弥赛亚主义的信念,而是始终保存于民众对于压迫的具体抵抗之中、保存于“不断革命”的集体运动之中的能量。
一 “终末论”视野下的民族主义
作为历史目的论的一种变体,“终末论”(eschatology)一词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它在西方思想史上与救赎教义和上帝的位格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不过,要讨论竹内好如何在“终末论”的视域下展开政治—文化论述,我们最好还是从其具体使用情况,而非从这个复杂概念本身的辨析入手。1961年,竹内好对其盟友、同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的武田泰淳在战时所写的思想史名著《司马迁:史记的世界》(1943)做出了如下批评:
虽然历史有时候看起来停滞,循环的轨道看起来不运动,但内部或许积蓄着不可预测的爆炸力。如果着眼于此,那么重要的也许不仅是持续性,更是革命。假如《司马迁》在动笔的时候设想了一个与持续世界对抗的默示录世界,那么就作品而言,完成度就会更加厚重;我的这种推定并非不恰当吧。当然,这是望蜀了。因为从写作的时期来说,为了对抗当时流行的流动史观或万世一系史观,这部著作已经竭尽全力了。①『竹内好全集 第十二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161页。
武田泰淳在《司马迁》中将项羽和刘邦视为两个同时存在的世界中心,试图以水平的空间图式来勾勒《史记》的“世界”。武田写道:“史记式的世界,始终是空间性构成的历史世界,因而持续也必定是空间性的。”①武田泰淳『司馬遷』,講談社文芸文庫1997年版,第142页。竹内好在此提到的“持续世界”,无疑指的是当时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所鼓吹的垂直性的“万世一系史观”;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武田的著作并没有直接对天皇制进行批判,但包括竹内好在内,许多论者将它视作战时状态下的一种抵抗——以项羽和刘邦的“两个中心”抵抗天皇的单一中心,以空间图式对抗绵延不绝的天皇制时间,等等——的确不无道理。不过,竹内好上面这段批评的要点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武田所给出的空间图式,认为其中缺乏一种“积蓄着不可预测的爆炸力”乃至促成“革命”的“默示录”因素。中岛隆博敏锐地指出,支撑竹内好做出这一批评正是基于一种“终末论史观”,尽管在这里竹内好没有直接使用“终末论”或“终末观”等语词②参见中島隆博『思想としての言語』,岩波書店2017年版,第102页。不过,中岛认为这种“终末观的史学”的期待在于“一切事物无论巨细的救赎”,并认为竹内好的这一思考方式可以延伸到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弥赛亚主义;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看法。。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可以说: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对于竹内好而言,“终末论”的视域并不是站在事态完成的视点和时间点上回溯性地为既往的历史过程赋予合理性;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找到蕴含在事物看似稳定的、合理的表面下的偶然性和“爆炸力”,找到事态的“事件性”,从而为既定事态设想另外一种可能,或者说重新将事态“可能化”(possibilization)。不过我们已经走得太快了;让我们再次回到起点:竹内好自己如何理解“终末观”或“终末论”③由于竹内好在著作中对于这两个语词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所以下文中我将主要采用“终末观”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竹内好在1948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读毕北森嘉藏《上帝的疼痛神学》,各个方面都很有助益。(中略)在终末观、现代主义的谬误等问题上,学到很多。”(参见『竹内好全集 第十六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13页)。也就是说,竹内好在1950年以后的著作中对于“终末论”或“终末观”的涉及,或许包含了北森神学的某种影响根据北森的说明,“彻底的东西,也就是终末,一方面已然成为现实,同时另一方面也呈现为需要追踪到未来的东西。这两个矛盾的真理结合为一时,这里产生的紧张就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带有终末论性质。……解决之中的未解决——在这一现实中经历的信仰,就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终末论式的东西”(参见北森嘉蔵『神の痛みの神学』,講談社1981年版,第221~222页)。下文涉及竹内好的毛泽东论和革命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北森在此提到的现实与未来、解决与未解决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政治本体论的维度上得到复奏。不过,我仍然想说,如果凭借竹内好日记里的这一记载得出结论认为北森神学深刻影响了竹内好的历史观,那就有失偏颇了。?
诚然,竹内好并没有在特定的宗教背景下发展出一种接近基督教意义上的“终末论”的理论;毋宁说,在有限的几处对于“终末论”或“终末观”进行说明的地方,竹内好的着重点仅仅在于对事物之终结的关注。例如,在1967年与思想家大塚久雄的一次对谈中,竹内好如此谈论他所理解的“终末论”:“我对终末论一词的使用比较随意,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是:就人类历史何时开始何时终结这个问题而言,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图式的话,那么认为历史有终结的就是终末论。”①竹内好、大塚久雄「歴史のなかのアジア」,『状況的 竹内好対談集』,合同出版1970年版,第212页。而在1961年撰写的一篇专门讨论“终末观”问题的文章中,竹内好同样在一个看似非常浅白的意义上阐述了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一切事物有开始就有终结。宇宙也有终结。更何况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一个集团。我无法赞同天地无穷。因为没有终结也就没有开始。人是否能不考虑死亡而生活,对此我表示怀疑。……在过去,我创立并维系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然后最终解散了它。这一经验对我而言至今都是有用的遗产。由此我想到的是,比起创立,解散要难得多。谁都不想横尸街头。我认为,结社应该像人迈向死亡这一目标前进那样,以解散为目标前进。②竹内好「終末観について」,『竹内好全集 第九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293页。
认为万物有始就有终,这种说法本身谈不上什么“终末观”;重要的是,一旦从一开始就为事物设置一个终结的时刻并由此出发,在“有限性”的视域下理解事物的生成变化,那么可以说:一方面,事物在时间或历史中的发展不再是以持存和自我保存为目的,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否定和自我消亡;另一方面,尽管如此或正因如此,事物的消亡不是归于静寂和虚无,而是回归潜能状态以期待新的、不可预期的自我生成。竹内好在上面这段话里提到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是成立于1934年并由竹内好在1943年解散的、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重心的研究团体,核心成员还包括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外,竹内好生前还负责主编了杂志《中国》(1963—1972)并同样亲自将其休刊。似乎对于竹内好而言,解散不仅仅是一个团体的终结,更是其目的的完成。为什么竹内好如此执着于“以解散为目标”?在著名的《〈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1943)一文中,竹内好对此有过一个带有形而上学意味的解释:
通过自我否定来将自己世界化。不是为既有的自我增加一些东西,而是站在将自己无限创新出来的根底上。……我相信,大东亚文化只有依靠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否定才会产生。日本文化必须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成为世界文化。正因为是无,才必须成为全部。回归“无”,便是在自身内部描绘世界。……必须打倒自我保存的文化。舍此别无生存之道。①竹内好「『中国文学』の廃刊と私」,『竹内好全集 第十四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454、450、453页。
对于竹内好而言,由自己创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卷入日本现代历史和现代思想之中——具体而言,就是卷入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向英美宣战的历史进程之中,卷入以“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为代表的思想努力(及其失败)之中——而不是像传统的汉学和“支那学”那样以游离于现实的“客观”姿态封闭于自我划定的学术疆域,因为竹内好强调,只有通过参与历史的激烈变化,研究会才能真正接触中国的现实,也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化和承担新文化的主体。当眼前的历史语境要求日本文化或竹内好所谓“大东亚文化”否定既成的现实和既有的自我之时,越是在体制性的意义上显得完满、自律和自足的东西,就越是丧失生命力。在这个时候,令其终结并回归“无”的做法,反而是研究会迈向新的生命的必要前提。或者说,这是以“无”的方式保留当年促使研究会同人们聚在一起成立研究会的“初心”的唯一方式。所以,竹内好写道:“我相信大东亚文化只有在超克自我保全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我们日本不是已经在观念上否定了大东亚地域的现代殖民地支配吗?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否定殖民地支配,就是放弃自我保存的欲望。”②竹内好「『中国文学』の廃刊と私」,『竹内好全集 第十四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454、450、453页。(当然,现实中的日本只是在观念或言辞上“否定”了自己对于亚洲的侵略和殖民,在行动上则试图通过太平洋战争巩固对于亚洲各国的支配和压迫。我们下文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可是,也正因如此,竹内好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关于日本文化的自我否定的论述,在政治上或许暗示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应该通往的结局:“据说大东亚战争改写了世界史。我对此深信不疑。这是否定现代、否定现代文化,从否定的根底开始形成新的世界和世界文化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③竹内好「『中国文学』の廃刊と私」,『竹内好全集 第十四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454、450、453页。换言之,如果大东亚战争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如果日本的确希望通过这场战争来实现“近代的超克”,那么这场仍然在进行之中的战争的关键就不是战胜敌人,而是否定自己。众所周知,竹内好曾在日本宣布向英美开战时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1942)一文(竹内好后来自己也将这篇文章视为对于时局的一个重大误判),字里行间仿佛充满了对于日本的战争决断的敬意,甚至认为这一决断为日本过去对于亚洲的侵略行径找到了合法性依据。然而,通过《〈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可以看到,竹内好的论述中诡异地(uncannily)包含着一层或许只能称之为“终末论”的政治期待:日本必须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地否定自己——不是在言辞上改弦更张,而是在行动上回归“无”——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竹内好而言日本的战败令人沮丧,但其原因不是日本输给了美国,而是因为日本的战败根本不彻底——他曾认真设想美军进入日本本土、令日本全国化为焦土的前景,并从中思考日本民众发动革命的可能性。①例如,参见[日]竹内好《屈辱的事件》,孙歌译,收入[日]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8~229页。然而,事实却是美军以未曾遭到抵抗的方式进驻日本,并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天皇制。被竹内好批评为一味效仿强者的“优等生文化”的现代日本文化,非但没有通过战争而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反而因为战败找到了新的值得效仿的目标,即美国的现代民主政治。那么,与之相对,竹内好所设想的日本回归“无”的状态,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在写于1954年的一篇题为《当代的理想像》的文章中,竹内好如此回顾自己在战时的思索:
我自己在摆脱青年时期的自我中心主义时,遭遇到了战争。那个时候,我认真思考了日本民族灭亡的问题。说是认真思考,当时是抱着认真的态度的,而现在回想起来,却感到恍如梦境。无论如何,当时我不断思考着日本人作为民族是否有灭亡之日。不是因当下的战争而灭亡,而是在更一般和抽象的意义上,思索着有朝一日是否会灭亡。②竹内好「現代の理想像」,『竹内好全集 第六巻』,筑摩书房1980年版,第379、380页。
这段文字的意思似乎再明确不过:竹内好以当时的战争为契机所设想的“终末”式图景,是日本人作为民族的灭亡。但他马上补充道:“那个时候我得出的结论是,也许会灭亡,但如果以灭亡为前提,当下的生命就不可能。”③竹内好「現代の理想像」,『竹内好全集 第六巻』,筑摩书房1980年版,第379、380页。初看之下,似乎这段话和之前从《〈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中关于“以死亡为目标前进的生命”的论述有些矛盾;但正是这一点提醒我们,竹内好不是在“一般和抽象”的意义上谈论“生命”本身,而是在一个特定的视域下展开其思考:当他谈论以死亡为目标的生命时,他的前提正是一种“终末观”视域;相对地,站在普通民众一边来看,“认为人类生命和大地一样悠久,这是常识吧。这个常识是健全的。因为这里没有夹杂佛教或基督教式的终末观。这是直接生产者所特有的、因而是普遍的、民众式的思考方式”①竹内好「現代の理想像」,『竹内好全集 第六巻』,第381页。。
也就是说,竹内好笔下作为新的文化之根基的“无”,是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一个并不属于民众的思考方式和日常生活的位置,哪怕如研究者反复指出的那样,民众的日常生活对于竹内好而言至关重要。这个不可能的根基只有在“终末观”的视域中才能如真实存在一般呈现出来,正如生命只有通过死亡这一对生命的否定才能获得意义②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在“终末观”的视域下理解竹内好对于鲁迅所做的一个令人费解的判断:“对于鲁迅来说,死是其文学的完成。”(竹内好『魯迅』,講談社文芸文庫1994年版,第9页)。让我们回到政治层面考察这个不可能的根基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上述指向彻底自我否定的思考,竹内好关于日本民族的前景给出了一个颇为荒诞的设想——他在1965年的一次访谈中如是说道:
个人要是成为国家就好了。日本要是分裂成一亿个就好了。一人一国。……无论多少人都好,要是能让日本这个形象彻底分裂就好了。然后再考虑统一。因为不这么做的话,“民族”就无法确立。③竹内好、荒瀬豊「戦後をどう評価するか」,『状況的 竹内好対談集』,第99页。
如果说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实现其“政治主体性”的历史契机之一,那么在竹内好这里,没有什么能比“日本”这一国家形象的彻底瓦解和消亡更能促成主体的自我否定了。同时,正是在这个有关日本之“目的/终结”的荒诞想象中,蕴含着竹内好对于“民族”问题的独特思考。对于竹内好来说,能够承担这种自我否定的“政治主体性”的单位,不是作为“国家”的日本,而是作为“民族”的日本人,或作为民众的日本人。民族不是给定的、自然的实体,不是一种毋庸置疑的身份同一性,而是民众个体的主体性意识的集合——需要强调的是,这注定是一种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不稳定的集合:“民族在明治时期的形成,也可以视为民族形成的失败。而这也是今后日本人必须继承的课题。民族未必是一次性形成的。民族的自立或自力更生,换言之,民族的自我形成,需要反复地再形成……这一可能性仍然要留待将来。”①竹内好、荒瀬豊「戦後をどう評価するか」,『状況的 竹内好対談集』,第94页。为什么说明治时期形成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次失败呢?在1964年进行的另一次访谈中,竹内好对他笔下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行了明确的分疏:“民族主义本身没有价值。它是能量集结的一个形式,因此虽然不能无视,也不能坐视不管。我认为民族主义是必须加以理性控制的东西。……我所设想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重点不在国家而在民族或人民,换言之,人民自由意志的集结形态是根本。日本现代的民族主义更倾向于国家主义,这是否真的是民族主义,是有点问题的。对外政治独立,国内废止身份制、形成单一市场,这是民族的条件,而为了满足这一条件,人民通过自由意志来选择自己喜好的国家。我认为这就是民族主义。”②竹内好、桑原武夫「日本の近代百年」,『状況的 竹内好対談集』,第165~66页。
“民族主义”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借助“民族”之名集结起来的民众的自由意志——在这一理解中,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现代国家称不上是为了日本“民族”而存在的国家,它反而为了自我保全而牺牲了“民族”。换句话说,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政府及其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国家,将“民族”所代表的、民众自我确立和自我革新的政治能量导向了体制的自我保全,炮制出种种有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使得民族的政治主体性丧失在僵化的、机械式的国家体制的日常自我运转和自我维持之中。在竹内好看来,“国家”始终只是服务于“人和作为人之集合体的民族”的“生存目的的手段”,后者才是“本体”③参见竹内好「池田講演をよんで」(1968),『竹内好全集 第十一巻』,第344页。。一旦把主次颠倒过来,将国家本身作为目的和实体,将民众视为服务于国家的自我保存的手段,那么日本将来仍然可能重新走向侵略战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竹内好在这里并不是站在现代欧洲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例如)国家对于个体权利的侵害,更不是将政治的“真实”还原为孤零零的原子式个体。毋宁说,这里不存在西欧自由主义视作政治理论起点的,具备自身权利、能力、欲望和规划的个体;相对地,竹内好强调的始终是民众的“能量”,无论这一能量的来源是个体还是集体:属于民众的每个人因其自由意志而形成“民族”,但由民众汇聚的能量本身不会承诺“民族”或任何一种持续而稳定的政治实体的生成,而是需要不断地回到原点、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①关于竹内好笔下的“民族”,伊藤虎丸颇有启发地写道:“竹内好说到‘民族’的时候……它是关于个人是否有‘媚骨’的所谓伦理问题;他论述的‘民族’无法归结于普遍,也无法还原为全体中的部分,而是几乎和‘个别性’构成同义词。因而在这里,否定‘个人’主义而为‘民族’或‘阶级’献身,这种将‘个人’和‘民族’对立起来的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成立。……在竹内好这里,‘个人的独立’或‘自己成为自己’,意味着个人作为‘国民’而‘独立’,个体的主体性的确立就是个体那里‘民族’性主体性的确立。”(伊藤虎丸『魯迅と終末論——近代リアリズムの成立』,龍渓書舎1975年版,第291页)如伊藤所强调的,竹内好不曾将“个人”和“民族”对立起来,毋宁说两者共同构成了对于“支配者”(无论它的名字是国家、体制、帝国主义或理性)的抵抗。1950年代竹内好所提出的“国民文学论”,也应当在这一抵抗的脉络上来理解。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伊藤的论述中,这样一种不区分“个体”与“民族”、不把“个体”理解为全体之一部分的思考方式,已然带有“终末论”色彩:“根据终末论式的理论……‘个体’直接与绝对者相联系,‘个体’不是相对于‘全体’的‘部分’,因而每个个体都完全独自对于绝对者具有意义(或由绝对者赋予意义)。所以,一头羊和九十九头羊无法根据数量来比较价值的轻重,这种一神教特有的非合理主义存在于这一理论的根基处。”(同上书,第176~77页)换句话说,在伊藤这里,“终末论”意味着个体的主体性自觉和独特性;相对地,竹内好那里的“终末观”则更是一种历史和政治本体论层面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本体”的民族与其说是一个概念和形态上稳定的“实体”,不如说是一种动态的、抵抗“实体化”和“体制化”的力量。很显然,竹内好从1950年代初开始重提民族主义问题,与日本在1951年与美国单方面签署《旧金山和约》并巩固日美安保体制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1951年前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一时成为日本知识界的热议话题——例如,这一年五5月,历史学研究大会将主题定为“历史中的民族问题”,6月举行的日本文学协会大会则以“文学中的民族问题”为论题,等等。在竹内好看来,日本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条约说明,如果日本民众不把自身的力量集结成为抵抗的因素,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再一次为“国家”为自我保存而采取的独断行为背书。如冈山麻子所说:竹内好试图“通过‘民族’的契机来克服日本在实质上成为美国之附属国的状况”②参见岡山麻子『竹内好の文学精神』,第206页。。
因此,当竹内好写道“我想提倡,日本国家也要设置一个解散规定,否则爱国主义就无从产生”③竹内好「終末観について」,『竹内好全集 第九巻』,第294页。的时候,他想说的并不是如何培养民众的爱国主义,而是如何保存体现在爱国主义之中的、由民众的自由意志所代表的政治能量。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竹内好强调了民众作为一种能量的意义:“民众总是多数,又叫大众或群集。支配者总是少数,民众总是多数。……多数就是力量。所谓力量,就是既可以被革命动员,也可以被反革命动员。民众的力量不集结起来革命就不成立,但并不是只要民众的力量集结起来,革命就直接成了。集结起来的力量也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①竹内好「日本の民衆」,『竹内好全集 第六巻』,第247、246页。竹内好在这里的论述看似将民众和领导民众的势力(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势力)理解为亚里士多德主义意义上“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但这是一种很容易犯下的误解。对于竹内好而言,民众始终具有“被支配权力排除出去、处于被支配者地位”②竹内好「日本の民衆」,『竹内好全集 第六巻』,第247、246页。的性质。因此非常重要的是,“革命动员”和“反革命动员”并不是同一层级上的两种不同却对等的动员方式:“反革命动员”将民众的能量引向体制的自我保存,从而始终维系着支配和被支配的等级制社会关系;相反,“革命动员”意味着集结起来的能量的自我连接/表达(articulation)——它所表达的内容无他,而只是民众的自由意志本身。如果说“反革命动员”的历史结果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国家,那么“革命动员”的预期就是作为民众自由意志之表达的日本“民族”的不断的自我确立和自我更新。每一次更新都是重新回到“无”的过程,但并不是回归混乱或虚无,而是当面对新的社会矛盾、新的历史难题时,重新发明和形成抵抗形式的必要前提。同时,这一过程是为了防止形式固化为体制、防止能量被转化为体制自我运转的资源所必需的中介。
二 竹内好的“毛泽东论”
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从1950年代起将目光聚焦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乃至在一手材料和研究资料都很少的情况下动笔撰写《评传毛泽东》(1951),就毫不奇怪了。也就是说,正在进行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竹内好从动态而非静态的角度、从不断自我革新和自我否定而非自我保全的角度思考民众的集结和表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照系。有意思的是,竹内好对于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也与他的“终末观”视域不无关系。同样是在《关于终末观》一文中,竹内好写道:“马克思主义具有魅力的理由之一是,它预定了阶级和国家的终灭。对我来说,这种带有强烈终末观色彩的东西有吸引力。初期的马克思、列宁,还有不做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中国的大同思想没有基督教的终末观那么严格,因此也容易接近。”①竹内好「終末観について」,『竹内好全集 第九巻』,第294页。在这里,竹内好通过“终末观”而将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放在一起,也将中国“大同思想”的时间观和基督教思想放在一起。在对于时间的理解上,这些思想家的认识与中国传统的循环论或交替论形成了对照,呈现出“永劫的过去与永劫的未来相重合的图式”②参见竹内好「日本·中国·革命」(1967),『竹内好全集 第四巻』,筑摩书房1980年版,第333页。;更重要的是,竹内好提到的这些思想家都设想了历史和世界的终结,并站在终结的视域上勾勒出事物的有限存在。在这样的视域中,一切看上去强有力的、意在自我保全和自我发展的东西——政治、支配阶级、欧洲、国家,等等——反而显得最具“虚无”色彩,因为它们误将自身的实体性存在视为亘古不变的东西,而忽略了推动具体历史进程的民众能量的不断运动。
与此同时,正因为竹内好始终强调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并最终回归“无”的民众能量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否定,他也拒斥革命的目的论弥赛亚主义,因为后者在形而上学的抽象意义上、在脱离了主体性参与的前提下,将革命本身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程序乃至一个必然的结果——换句话说,竹内好所理解的“终末观”,是一种抽空了基督教式“预定调和”内容的视域:
我反对先预定革命或社会主义、再从中推断出当下行动的做法。相反,我认为应该从当下的日常生活出发,大家彼此在连续的进程中思考革命的规划。因为从预定的革命反过来追溯的做法,恐怕会将革命目的化。“只要革命成了的话”“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话”,这种弥赛亚思想对革命是有害的。这是投机,说得不好听就是堕落。……哪怕未来会有什么黄金世界,它也无法直接让我们当今的生活内容变得充实。把无可取代的当下生命拿去做交易,是很愚蠢的。③竹内好「政治·人間·教育」(1953),『竹内好全集 第六巻』,第348页。
“非目的化”或“去目的化”的革命,既是对于历史发展阶段论的拒绝,也是对于线性进步史观的拒绝。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竹内好对于革命的“去目的化”和他的“终末观”视域并不矛盾:站在事物消亡的终点思索事物发展的过程,恰恰不是为这一历史过程提前设置某种目的或完成状态,而是在取消这种对于完成状态的“预定”的状况下,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具体性和事件性留出空间。相反,如果提前为日本文化、民族、社会变革设置某种目的,甚至直接从中国革命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借鉴样板,为日本的发展规定精准路线,那么这和日本在效仿欧洲现代性过程中所体现的“优等生文化”没有任何区别。“无可取代的当下生命”呼应着竹内好所强调的民众的能量,它需要在集体的层面上时刻通过具体的现实斗争来自我表达和自我赋形;同时,这一动态的过程在“终末观”的视域中又必定要迈向不可预测、非辩证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消解,“实现”要重新归于“潜能”,从而避免在自我保全的过程中僵化为官僚体制。
因此,革命必定是不断革命,革命不承诺任何完满的目标,而是始终预期和呼唤着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向着某种政治结果迈进的革命,对竹内好而言不过是“投机”甚至“堕落”。事实上,竹内好早在《鲁迅》中就将鲁迅的“抵抗”与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强调“对于永远的革命者而言,所有的革命都是失败的。不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叫喊着‘革命成功了’,而是相信永远的革命,并以‘革命尚未成功’来破却当下”①竹内好『魯迅』,第152页。。因此,如酒井直树所言,“抵抗并不产生解放”,毋宁说“必须抵抗‘抵抗产生解放’的希望”本身②参见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日本」の歴史—地政的配置』,講談社学術文庫2015年版,第87页。。在竹内好的“终末观”视域下,所有在特定历史瞬间承担“抵抗者”位置的主体——无论是鲁迅、毛泽东、孙中山、中国、民族主义、亚洲——都必须在“方法”而非“实质”的层面上加以把握。而我认为,对于这一“方法”层面进行阐述的绝佳文本,正是《评传毛泽东》。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竹内好在1950年代初撰写的这部“毛泽东论”无疑在史料上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是,挑剔竹内好在历史细节的描述上是否充分,不是本文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将着重点放在毛泽东的井冈山时期,竹内好提炼出了一个他称之为“纯粹毛泽东”的概念表述。例如,竹内好写道:“(井冈山的毛泽东)一无所有。这是可以成为拥有一切者的无所有者。这个时期,他丧失了迄今为止生涯中得到的一切。他首先丧失了个人生活。也断绝了与外在世界的关联。他失去了家人。……也失去了党的生活。……共产国际也罢,党中央也罢,省委员会也罢,一切党的机关都排斥他。他在党内陷入了孤立。”①竹内好「評伝 毛沢東」,『竹内好全集 第五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303、304、304页。但是,竹内好认为,恰恰是在毛泽东丧失一切、一无所有的时刻,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
在他一切内外生活都归于无的时刻,在他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时刻,在一切都在可能性的意义上成为他的所有物的时刻,[毛泽东思想]的原型得以产生。迄今为止一切外在性的知识和经验,都从离心变为向心,凝结在他身上。由此,他本来是党的一部分,现在则成为党本身,党也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中国革命的全部。……这就是纯粹毛泽东,或原始毛泽东。②竹内好「評伝 毛沢東」,『竹内好全集 第五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303、304、304页。
竹内好进一步对“纯粹毛泽东”做出如下解释:“什么是纯粹毛泽东?它由一组矛盾构成:一方面认识到敌人强大我方弱小,另一方面则确信我方不败。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原动力,也构成了今日中共一切理论和实践的源泉。”③竹内好「評伝 毛沢東」,『竹内好全集 第五巻』,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303、304、304页。所谓毛泽东成为党本身、党成为中国革命本身的说法,同样对应着之前讨论过的竹内好对于“民族”的理解:在政治能量的自我表达的意义上,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个体/共同体”或“个人/国家”的分化图式不再有效,因为重要问题不是“个体”如何融入、对抗或形成“共同体”,而是民众的能量如何在当下的具体语境中为自己找到恰当的形式。在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这里,“丧失一切”成为在整体性的视野上、在不同于以往的区域性对抗的意义上重新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赋予新形式的契机,成为放弃制度层面的自我保全来自我更新的契机。竹内好曾经认为鲁迅文学的根源只能被描述为“无”;同样,“毛泽东思想”并不诞生于任何既定的政治学说或理念,而形成于一切都“归于无”的时刻。只要鲁迅和毛泽东应对的社会矛盾没有消失,只要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结构依然存在,能量向“无”的回归就不是落入纯粹的虚无,而是自我更新的必要环节。在这样一种“终末观”的视域中,有一个颇为吊诡的地方需要特别留意:竹内好之所以能够将鲁迅和毛泽东的“无”理解为他们的文学思想或政治思想的根源,之所以能够将这种“无”理解为一个包含一切可能、超越实体性规定的主体性位置,之所以能够从中看到巨大的潜能——而不是单纯看到失败、绝望或虚无——是因为“终末观”的后设立场回溯性地笼罩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和消亡。但这一后设立场却不像黑格尔辩证法那样预先承诺了某种概念的综合;毋宁说,竹内好的“终末观”视域重新将辩证法的运动向着偶然、开放的历史敞开,它为所有的辩证综合重新引入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以至于任何一场革命只有在期待下一次革命的意义上,只有在“失败”的意义上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革命——在“终末观”的视域中,任何革命都要回归到自身的“潜能”状态之中。另外,不同于历史循环论,“终末观”强调能量从潜能到实现、再回归潜能的过程中每个环节在每个特定语境下的独特性,以至于可以说,世界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彼此呼应,但没有一次革命是遵照“周而复始”式的社会规律发生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一次不可预期的事件。
就“纯粹毛泽东”由一组敌我关系的根本矛盾构成而言,它对应着竹内好的“毛泽东论”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概念,即“根据地”。“根据地”在竹内好这里并不意味着某个特殊的地域,而是一个“哲学范畴”①竹内好「評伝 毛沢東」,『竹内好全集 第五巻』,第306页。。对于“根据地”的阐述,构成了竹内好的“毛泽东论”和中国革命论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竹内好在不同时期对于“根据地”的论述前后一贯,并且他从中读出,或为之赋予的重要意义,同样延伸至他对于其他论题(例如“作为方法的亚洲”和战后日本宪法)的考察那里,因此理解这一范畴对于把握竹内好的思想将有很大帮助。让我们从几篇不同的文章中引述几段竹内好对于“根据地”的解释:
无论敌人多么强大,根据地都无法被夺走。因此我方是不败的。为什么无法夺走根据地?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均衡。为什么不均衡?因为敌人强大我方弱小。敌人强大这件事本身产生了不均衡,由此使得夺取根据地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根据地)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不应令它固着,而应令它发展。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①竹内好「評伝 毛沢東」,『竹内好全集 第五巻』,第305、306,313页。
根据地无法夺走,所以也无法给予。根据地是根据自己的能量而自生的。就算赋予初动力,如果不蕴含爆发性的潜在能量,那么无论加上多少外力,也无法创造出根据地。②竹内好「評伝 毛沢東」,『竹内好全集 第五巻』,第305、306,313页。
从军事层面上说,根据地是将敌人战力转化为我方战力的装置;从生产层面上说,根据地是将战争导致的荒废转化为具有提高生产力之作用的装置;换句话说,根据地是为解放区提供内部支撑的结构。总之,土地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是三位一体。③竹内好「日本·中国·革命」,第341页。
根据我对根据地的定义,它是使得价值颠倒得以可能的场所。换言之,它是再生产革命的场所。这里的场所说的不是地域意义,而是结构意义。④竹内好「中国近代革命の進展と日中関係」(1968),『竹内好全集 第四巻』,第385~386、388页。
根据地不是一次性创立的,而是不断再生的。毋宁说,根据地之所以为根据地,正是因为它不断地更新能量。那么这运用在历史解释上会怎样?它可以为如下史观确立根据:历史是断绝的,历史依靠不断地返回原点而得到更新。⑤竹内好「中国近代革命の進展と日中関係」(1968),『竹内好全集 第四巻』,第385~386、388页。
竹内好对于“根据地”的阐述还有很多,不过我们的引述已经太长了。不难看到,在竹内好这里,“根据地”作为哲学范畴至少拥有四个性质:第一,根据地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和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根据地无法被消灭或夺取,只会根据社会矛盾的发展而动态地自我发展和变化。也正因此,“根据地”和“亚洲”一样,在竹内好这里是表示支配和非支配关系、强弱势力关系的结构性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地域概念。第二,根据地内部蕴含着能量,而考虑到第一点,可以说这种能量即民众的能量、弱者和被支配者的能量。第三,根据地为民众扭转甚至颠倒既定的权力结构提供了可能性,因为一旦作为哲学范畴而脱离了与特定地域的必然联系,“根据地”就标志着既有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的一个不断被生产出来、无法被消灭或攫取的革命性“原点”,也是一切社会和政治矛盾的集中点;从现有的体制角度和支配者的角度来看,它只能呈现为“无”,但从民众和被支配者的角度来看,它是进行价值颠倒和社会变革的起点,它是尚不具有明确形式的政治能量的汇聚场所,是革命的可能性条件。最后,正因如此,根据地的存在使得任何直线式发展、或按照既定规律发展的历史解释都失效了,因为后者往往聚焦于作为“实体”存在的制度或国家,看不到以被支配者为中心的能量的聚散离合。统治者永远无法预测革命在何时何地发生,但革命注定要打断历史发展的虚伪的连续性,注定要引爆一切将自身自然化、永久化的制度性存在。
可以看到,竹内好关于“根据地”的哲学思考始终在“终末观”的视域下展开。再强调一遍:在竹内好这里,“终末观”并不单单指向事物的消亡,而是站在事物归于“无”的时间点上否定事物固定不变、永久自我保存的可能性,从事物归于“无”和消亡的过程中看到动态的、有待赋形的能量和抵抗的主体性位置——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显得弱势和无力的位置,同时也是文学的位置①关于竹内好思想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作为“无力”的文学构成的独特抵抗,参见拙文 “Literature,Powerlessness, and Modernity: A Reading of Takeuchi Yoshimi’s ‘What Is Modernity?’ ”,positions: asia critique,Vol.29, No.2 (May 2021)。——也强调每时每刻的特殊语境下生成的、不稳定的民众政治的形式。在中国对于欧洲现代性的抵抗中,在毛泽东对于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抵抗中,在亚洲对于欧洲的抵抗中,竹内好始终试图寻求由既有力量对比和权力关系的结构所形成的主体性,一种既否定敌人也否定“自我”的主体性。
于是,当竹内好1960年前后参加“安保斗争”时,他也在群众运动中找到了抵抗的“根据地”:竹内好认为,虽然岸信介政府最终强行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但日本民众在抗争过程中以战后“和平宪法”的条文为依据阻止政府的单方面行动,正是位居弱势的一方将占据强势的敌人的武器转化为自身力量的例证。因此,当许多论者认为“安保斗争”以失败告终的时候,竹内好却相信这次战后日本罕见的社会动员在培养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主体性上,堪称一次重要的胜利:通过运用原本感觉格格不入的、由美国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战后宪法,日本民众将这些被强者(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政府)随意忽视的、仿佛只是漂亮说辞的普遍性原则,真正转化为与自己的生活切身相关的、在当下的具体时刻为自己的抵抗提供表达的武器。
的确,现实历史告诉我们,根据地或许无法被夺取,但可以被消灭,正如群众运动无时无刻不在遭到镇压。——但这并不构成对于竹内好“根据地”论述的反驳:毋宁说,在“终末观”的视域中,“根据地”的“消亡”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一旦在体制上稳固下来,就有可能走向自身的反面,即为了自我保全而趋于封闭与官僚化。“根据地”遭到消灭或镇压,并不意味着它化为虚无,反而是它产生和更生的前提。“根据地”的生成,就具体条件而言是偶然的,没有什么能预言它在特定语境下产生何种明确的形式;但就结构而言,它的生成又是必然的,因为强者和弱者的力量关系总是会带来压迫和抵抗,于是总会在各个冲突的局部形成“根据地”。
三 作为另一种“终末论”的浪漫派:保田与重郎
因此,哪怕是在其1941年对于日本向英美宣战表达的错误称颂中,竹内好对日本的肯定也是基于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我克服的期许,而不是对于现状的无条件承认:对他而言,能够实现“近代的超克”的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更不是在亚洲各国殖民和蹂躏百姓的日本军队,而是既否定欧洲现代性、也否定曾经重蹈殖民主义覆辙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在“十二月八日”,竹内好似乎看到了日本作为亚洲的“根据地”而颠覆欧洲现代性价值体系的瞬间,一个日本国民的意志凝聚成形的瞬间:“日本国民的决意汇成一个燃烧的海洋。”①参见[日]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孙歌译,收入[日]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65页。
无须多言,竹内好的浪漫派式的想象并没有现实的对应。在政治层面,日本针对英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只是其帝国主义战争历史的延续,而非对于现代性的克服;在思想层面,以《文学界》在1942年召开的臭名昭著的座谈会为代表,“近代的超克”甚至都无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确立下来。在《近代的超克》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竹内好如此为这场座谈会定性:“我认为,‘近代的超克’的最大遗产不在于它成为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甚至没能成为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于它致力于思想的形成,结果却是思想的丧失。”①竹内好「近代の超克」,河上徹太郎他『近代の超克』所收,冨山房百科文庫1979年版,第288页。一方面,竹内好的这段话承认了“近代的超克”在思想层面的全面失败;但另一方面,正因如此,竹内好暗示,作为“致力于思想形成”的这种冲动,或许仍然是需要继承的一个“未完的课题”②我认为,考虑到竹内好写作此文时正值群众运动走向顶点的1959年前后,竹内好试图通过检讨战时这次丑闻式的座谈会来探讨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设想“近代的超克”,是完全有可能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说,在“终末观”的视域下,竹内好是在“近代的超克”的延长线上来理解当时正在进行的群众运动的。然而,思想史研究者在探讨竹内好的这篇文章时,常常容易忽略上述时代背景,单纯从述事(constative)的层面讨论竹内好的一些述行性(performative)的论断。不过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这篇复杂的文章展开细读。。换句话说,正因为“近代的超克”未能被形式化为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它所代表的政治能量就无法被回收到如“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圈”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因此,站在1950年代末乃至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当年的这场座谈会,重要的就不是辨析参与者各自如何理解“近代的超克”——从内容上说,这些发言不过通往了“思想的丧失”——而是考察这些彼此矛盾甚至杂乱无章的话语如何可能在形式层面勾勒出一种难以与现实中日本的帝国主义战争确立认同的、自我否定、自我克服的思想潜能。借用竹内好偏爱的语词,可以说,对“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检讨,关键在于如何从中发现那个只在“终末观”视域下才呈现出来的“无”的场所。
正是在这里,竹内好对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的否定和批判,看上去和日本浪漫派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非常接近。如桥川文三指出的那样,竹内好对于自己的这位高中同学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竹内好并没有直接参与后者创办的文学杂志《我思》,但却在杂志上刊登过自己著作的广告③参见橋川文三「竹内好と日本ロマン派のこと」,橋川文三,中島岳志編『橋川文三セレクション』,岩波現代文庫2011年版,第477~484页。——这至少表示,竹内好认为《我思》的读者也可能是自己著作的潜在读者;同时,竹内好也几次在日记里透露出对于保田著作和行动的关注。由于比较竹内好和保田各自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是本文力所不逮的一项宏大任务,这里我仅仅将焦点放在两人对于“终末”式的“无”的看法上,以此澄清竹内好的“终末观”与保田式“反讽”的距离。
保田在写于1940年的一篇回顾日本浪漫派发展的文章《我国的浪漫主义概观》中指出,昭和时代的浪漫派运动兴盛于日本开始向亚洲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期。战后被定罪煽动军国主义并遭到公职革除的浪漫派诗人保田认为,在“日俄战争”中经历“惨胜”后,日本社会陷入了一种“只有靠肉体的诗性表达才能拯救的颓废”状态,而日本浪漫派运动始于“对当时不断崩坏的日本体系的咏叹”①参见保田与重郎『近代の終焉』,新学社2002年版,第42、43,45页。。这里所谓“肉体的诗性表达”,指的是1936年由青年军官发起并以失败告终的“二二六事变”。接着便出现了一段颇具保田风格的论断:“日本浪漫派的基础是日本新精神的混沌和无定型的状态,是同时确保破坏与建设的自由日本的反讽,进而是对于作为反讽的日本的现实主义。”②参见保田与重郎『近代の終焉』,新学社2002年版,第42、43,45页。关于“反讽”作为保田笔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概念的含义,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在此无法涉及;但不管怎么说,通过“作为反讽的日本”这个含混的修辞,保田将种种思想上的张力——破坏与建设、自我完成与自我毁灭——统一起来,一方面在诸多年轻读者那里成功地为“死亡”赋予了美学含义,实现了本雅明意义上的“政治的美学化”;但另一方面,“作为反讽的日本”又必定与现实中的日本发生乖离,以至于如论者所说,“‘圣战’所带来的破坏和颓废正是他无意识中追求的悲剧——也就是‘失败’和‘毁灭’的在场”③参见澤村修治『敗戦日本と浪漫派の態度』,ライトハウス開港社2015年版,第15页。。吊诡的是,保田同时鼓吹战争和战败。在这个意义上,保田战时受到宪兵的监视,乃至遭到歌颂“皇道精神”的右翼文人的攻击,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吧。
因此,在保田看起来“反动”至极的战争歌颂中,始终包含了一层期待自我毁灭和自我否定的“终末论”契机:只有在自我毁灭的时刻,美学理念上的“肉体的诗性表达”才能克服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颓废”,才能实现迈向“作为反讽的日本”的“现实主义”。松本健一简练地概括了保田笔下“终末”美学的特征:
保田的浪漫主义在终末处完成了美的形象。换言之,《日本的桥》的浪漫主义,在歌颂终末之美的凋零美学那里得以完成。……对保田来说,战争针对的既是英美的“现代性”,也是福泽谕吉以降的“文明开化理论”(“现代主义”),后者试图以“现代战争”回应英美“现代性”。换句话说,保田以向着“作为反讽的日本”的激进一体化(“现实主义”),否定了现代日本。①松本健一『竹内好論』,岩波現代文庫2005年版,第110页。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保田通过“作为反讽的日本”这一“终末”美学,把“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上众人未能表达的思路推向了极致,即预先站在当下战争的“终末”处——在战败、废墟、毁灭和死亡的图景中——回溯性地(或“反讽”地)将这一自我破坏和自我否定的过程本身把握为浪漫派精神的实现?如果说保田将“无”本身作为克服“现代性”的方法,那么如何将竹内好的“终末观”与保田的“终末”美学区分开来?
在《近代的超克》中,竹内好已经点出了日本浪漫派作为“近代的超克”的思想来源之一的重要性:“我认为在‘近代的超克’的思想中,‘日本浪漫派’的作用不是来自复古的层面,而是来自终末论层面。为了重新解释‘永久战争’的理念——不是作为教养,而是将它作为思想主体责任上的行动自由——终末论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或缺的。”②竹内好「近代の超克」,河上徹太郎他『近代の超克』所收,第338页。“永久战争”和“不断革命”的区别,也许象征性地标志着保田和竹内好的思想分野:两者都试图通过非常规的政治事件来超越既定的政治体制及其自我保全,但在竹内好的“终末观”视域中,现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矛盾必然会形成“根据地”式的能量焦点,被压迫者、被支配者始终要从这个“无”的位置开始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它必定是具体的、不可通约的、不可预期的、动态的,但在结构上,它也是必然的、迫切的、生成历史的;与之相对,在保田的“终末”美学那里,吊诡的是,既然日本的侵略战争本身不过是“文明开化理论”的延续而非否定,既然只有通过战争实现的自我毁灭才能克服“现代性”,那么为了迈向“作为反讽的日本”的“现实主义”,保田就只能在被动地追认现状的同时期待一个“终末”时刻的到来。换句话说,面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肆虐的事实本身,保田站在毁灭和废墟的“终末”时间点上的评判(如“肉体的诗性表达”),在没有迎来1945年8月15日之前,事实上只能不断成为对于侵略战的证成。在现实中持续“颓废”的日本和保田的理想(无论它以什么名目出现:“自然”“大米文明”或“绝对和平”)之间承担中介作用的,不是如竹内好笔下那种抵抗的主体,而恰恰是浪漫派式的、想象性地实现“矛盾同一”的“反讽”。
竹内好关于保田的下面这段分析,清楚表明了同样坚持自我否定、追求“终末”的两人在思想上的根本差异:
保田发挥的思想作用是,通过破坏一切范畴而灭绝思想。他在这一点上比起令范畴从属于概念之随意性的京都学派走得更远。他倡导全盘否定文明开化,但他所谓的文明开化不是一个思潮,也不是一种流行或理论,但既是思潮也是流行也是理论,换言之即现代日本的全部。因此,当然这里也包含自己。在他那里,自己是难以确定的东西。因为一旦确定,自己就被相对化了,就产生了与他者的关系。而他的方法是通过将自己无限扩大来将自己化约为零。①竹内好「近代の超克」,河上徹太郎他『近代の超克』所收,第334页。
在竹内好看来,保田的全盘否定相当于对责任的放弃,也是对思想的放弃,因为保田站在美学角度对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社会所做的整体否定,一开始就放弃了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寻求抵抗方式的努力:最终,保田的“终末”美学变得与虚无主义难以区分。与之相反,竹内好关注的始终是不同语境下的独特抵抗:每一次抵抗就像每一个坚韧而弱势的“根据地”,尽管没有任何理论可以预先保证抵抗的结果,但通过强调在“终末观”视域下呈现为能量汇聚之所在的“无”,竹内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社会困境,不懈地寻求着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被支配的民众和被压迫的民族在政治上为自身赋予形式和表达的可能性,哪怕这些有待产生的形式与表达注定是偶然的、脆弱的、暂时的,哪怕这些形式和表达始终有着被支配者的话语攫取和扭曲的危险——无论它的名称是“亚洲主义”“三民主义”或“第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