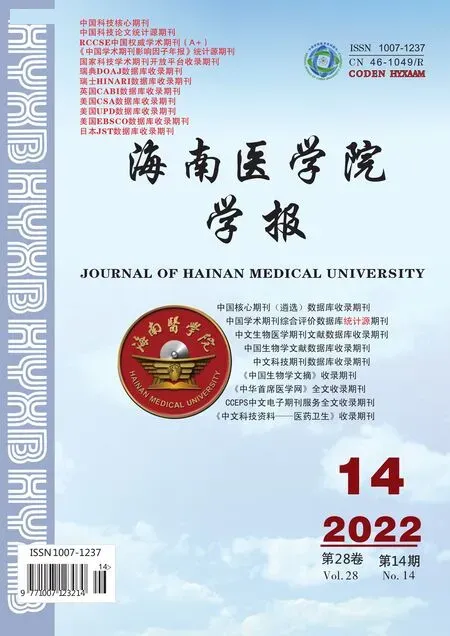新冠肺炎后遗症的临床特征及研究进展
李 娜,汪 哲,包云丽,唐海茹,黄 俊,于晓辉,张久聪
(1.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消化内科,甘肃 兰州 730050;2. 甘肃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自2019 年底爆发以来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截止2022 年4 月24 日,全球已报告确诊病例超过5 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00 万例[1]。随着COVID-19 的治愈人数不断增加,长期持续症状的出现成为了各国专家继急性感染期后关注的另一焦点。既往研究表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及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患者治愈后普遍存在相关系统的持续症状[2],而SARS-CoV-2 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SA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同属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β 属,具有相似的病毒结构[3],尤其和SARS-CoV 拥有共同的特异性结合受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4],从 而发挥致病作用。因此,国内外学者正在对COVID-19 康复患者进行密切随访,目前已观察到涉及呼吸、循环、神经、消化等系统的后遗症[5-8],最常见的症状包括疲劳、肌无力、睡眠困难、抑郁、呼吸困难等[9],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正常工作及日常生活。
1 SARS-CoV-2 致病机制
作 为 冠 状 病 毒 科、冠 状 病 毒β 属 的 新 成 员[10],SARS-CoV-2 的单股正链RNA 基因组可编码刺突表面蛋白(S 蛋白)、核衣壳蛋白(N蛋白)、基质蛋白(M蛋白)和小包膜蛋白(E蛋白)四种重要的结构蛋白。其中,包埋于病毒包膜E蛋白表面的刺突蛋白S是决定病毒侵入宿主细胞的关键结构,包含S1和S2 两个亚基。S1 亚基含受体结合结构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RBD),负责与宿主受体结合;S2 亚基则促进病毒与宿主细胞的膜融合[4]。刺突蛋白S 通过与靶细胞表面特异性的ACE2 受体结合进入细胞[11],最终攻击表达ACE2 的多种靶细胞,除最主要的肺泡细胞外,还包括血管内皮、心脏、胃肠道、肾脏等[12]。同时,肺泡等受损靶细胞释放大量的病毒和促炎因子,进一步激活免疫系统,释放细胞因子,引起细胞因子风暴[13,14],从而进一步加重病情,引起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15]甚至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16]等。
2 COVID-19 后遗症及其原因
由于SARS-CoV-2 可通过多种机制损伤机体,其后遗症可涉及人体诸多系统。研究表明[17],COVID-19 患者在出院14 d~3 个月内,主要后遗症包括持续性疲劳、呼吸困难、生活质量下降,此外还有心肌炎、嗅觉和味觉功能障碍等。一项对武汉金银潭医院出院的1 733 例新冠肺炎患者进行的大型队列研究结果显示[9],在急性感染6 个月后76%的康复患者至少存在一种持续症状,主要包括疲劳或肌肉无力(63%)、睡眠困难(26%)和焦虑或抑郁(23%)等,此外,在急性感染期间病情的严重程度与持续症状的发生有关。这与另外一项对来自56个国家的3 762 例患者长达7 个月的随访结果相类似[18]。国内另一个研究小组[19]对武汉的2 433 例患者在进行了电话随访,有1 095 例患者(45.0%)在感染SARS-CoV-2 后1 年反馈了至少1 种不适症状,疲劳、出汗、胸闷、焦虑和肌痛最为常见,同时提出高龄、女性、急性期重症感染是后遗症发生的危险因素。而对于急性感染期间经历了重症监护治疗的患者,在出院后更容易出现新发的疲劳、呼吸困难、心理认知功能障碍等症状,60%的重症患者出院后因后遗症持续存在而无法投入正常的工作,女性及高龄同样是其危险因素[20]。为了更好地对新冠肺炎的持续症状进行管理,国际上已有指南提出[21],将症状和体征持续4~12 周的COVID-19 定义为“症状持续的COVID-19”,而将长期持续的症状和体征定义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综合征”,指在SARS-CoV-2 感染期间或之后出现的症状和体征,持续时间超过12 周,并且不能归因于其他诊断。有研究发现,大约四分之一的出院患者的鼻咽拭子中SARS-CoV-2 核酸检测仍然呈阳性,而部分受试者的阳性时间超过3 个月[22]。对于COVID-19 相关受累器官出现持续性损伤的原因,除了SARS-CoV-2 对机体的直接攻击外,急性期感染导致的免疫系统失调和炎症反应紊乱可能是引起长期后遗症的病理生理学基础[23]。有关于中性粒细胞、C 反应蛋白等主要炎症指标的研究表明,低度的炎症反应在患者出院后可持续存在,从而引起氧化应激,导致组织损伤[24]。此外,对COVID-19 康复患者的长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患者存在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健康问题,其相关原因可能包括性别、年龄、社会稳定性、经济状况、社会孤立以及对感染的恐惧等多种因素[25]。
3 COVID-19 后遗症临床特征
3.1 呼吸系统
由于肺是受COVID-19 影响最大的器官[15],大量研究显示,持续性呼吸困难在出院患者中是最常见的持续症状之一[17]。对110 例非危重患者进行肺功能测定,结果显示,在出院时,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弥散功能受损[26]。在出院后3 个月,大约55.7%的患者遗留胸部CT 异常,主要表现为毛玻璃影(44.1%),而44.3%的患者存在肺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肺弥散能力受损(34.8%)[27],且这些肺部损伤表现在持续6 个月的随访中仍然占很大比例[9]。而对于危重及重症患者,出院后则更容易出现持续性的肺功能受损[28,29],因此需要对急性感染期间被诊断为危重及重症的患者进行更加长期密切的随访以便及早帮助其进行康复治疗。有研究小组对83 例住院期间不需要机械通气的重症患者出院后进行了3、6、9、12 个月的连续性随访,对其肺功能、运动能力、胸部高分辨CT 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大多数康复患者的呼吸困难程度和运动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然而在随访12 个月时,仍有33%的患者存在肺一氧化碳弥散量受损(<80%预测值),24%的患者胸部HRCT 存在异常,其中女性是存在持续肺弥散功能障碍的高危因素[30]。德国的一项随访研究根据急性感染期病情严重程度将180 例患者分为未住院及住院无需吸氧、需低流量吸氧、需高流量吸氧、需有创机械通气、接受体外膜肺氧合治疗组,结果显示,急性感染期病情严重程度与随访1 年的肺功能损害、胸部CT、呼吸道症状明显相关[31]。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相当大比例的新冠肺炎患者在出院后长期存在影像学和肺功能的异常。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最近的一项随访研究对曾经感染SARS 的71 名医务人员进行了长达15年的观察,结果表明,部分患者仍然遗留不同程度的肺部CT 及肺功能异常[32]。由此推测,COVID-19康复患者的肺部损伤同样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在持续密切随访的同时,进行相关的肺功能康复训练以改善其肺功能是非常必要的。多国已发表了共识和指南,提出应对COVID-19 患者尽早采取出院后的肺部康复措施[33]。例如肺康复(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计划[34],是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多学科、个性化的呼吸理疗、耐力训练、日常生活训练、心理支持等综合措施可显著提高COVID-19 患者的肺功能、运动能力及生活质量[35],对于改善不同严重程度分级的COVID-19 患者的呼吸系统后遗症已被证实是有效、可行、安全的[33]。
3.2 循环系统
研究表明,有基础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与COVID-19 不 良 疾 病 结 局 密 切 相 关[36]。同 时,由 于SARS-CoV-2 的攻击以及细胞因子风暴、缺血、缺氧等直接、间接的机制导致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造成了急性感染期的一系列循环系统的并发症,主要包括高血压、急性心肌损伤、心肌炎、心律失常等[9,37],其中,心肌损伤与院内急性感染期致命结局明显相关[38]。研究表明,心血管症状可持续至出院后,同时可能出现新发的心血管疾病。武汉的一项队列研究显示,出院后3 个月,有13%的COVID-19 康复患者出现了明显的心血管症状,包括心率增快、新诊断的高血压病等[39]。一项对139 例曾患COVID-19 的医护人员的随访结果显示,出院后11 周,41.7%的康复者至少有一种与心血管系统有关的症状,主要表现有胸痛、呼吸困难等,49.6%的参与者存在心电图异常,60.4%的康复患者心脏磁共振成像(cardiac fun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MR)异常,其中共有30.9%的参与者CMR 表现符合心包炎和/或心肌炎的标准[40]。CMR 是心脏功能和组织表征损伤的非侵入性参考标准,对于确诊或疑似活动性COVID-19 并有心肌损伤临床证据的患者CMR 可提供有关心肌损伤病因和严重程度的重要信息[41],在COVID-19 出院患者的心血管后遗症的随访检测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德国的一项队列研究对100 例康复患者进行出院后3 个月的随访,经CMR 检测显示,78%的康复患者有心脏受累,主要为心肌炎(60%)[42]。而在轻症居家康复的64 例患者中进行的CMR 随访结果显示,有71%的参 与 者 被 检 测 出 存 在 心 脏 受 损[43]。Clark 等[44]对COVID-19 康复的士兵进行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纳入了50 例士兵病例和50 例健康士兵,研究结果显示,94%的士兵病例在康复后期出现心血管症状,进一步对确诊为心肌炎的4 名士兵病例进行长期CMR 随访,其中1 名士兵在随访7 个月时仍显示CMR 异常并伴有持续活动性心肌炎。由于心肌炎等持续性心肌受累将会在中高强度体育运动期间引起心源性猝死等不良后果,因此有研究人员对既往患COVID-19 的竞技运动员进行了随访,结果发现,46% 运动员经CMR 检测发现有晚期钆增强(LGE),其中15%的运动员符合心肌炎的CMR 诊断标准[45]。此类结果引起了运动心脏病学专家的关注,并提出相关病情评估及运动恢复计划[46]。此外,在SARS 康复患者中观察到,院内急性期使用大剂量类固醇治疗后可引起长期脂质代谢紊乱,这与心血管后遗症的发生相关[47]。在COVID-19 急性感染期患者中,对于病情进行性恶化的患者需酌情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是否会导致激素治疗相关后遗症的发生需要长期密切检测来观察。既往研究证实,因各种原因导致的需住院肺炎病例是院后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且在出院后1 个月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增加2~8 倍,即使在出院后10 年仍然存在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48]。基于以上诸多现象,对于COVID-19 康复患者进行长期随访至关重要。
3.3 神经系统
既往研究证实,ACE2 不仅可在血管内皮中表达,也可在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中检测到[49],因此SARS-CoV-2 可通过损伤脑循环、神经组织及其继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等机制,引发一系列神经系统的症状,主要包括味觉障碍、嗅觉障碍、头痛、头晕等[50]。嗅觉和味觉障碍是COVID-19 的典型症状,研究发现在急性期后4 周有超过50%的患者存在嗅觉或味觉障碍[51],部分患者(11.7%)可持续到感染后1 年[52]。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在治愈患者中出现听力减弱及耳鸣等感觉障碍[53]。
头痛是COVID-19 神经系统另一持续症状,高达91%的康复患者存在间歇性头痛,且持续时间超过28 d[54]。一项来自西班牙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55],住院期间有74.6%患者存在头痛症状,部分伴有明显嗅觉丧失,且有四分之一患者有偏头痛样的严重疼痛发作,这与最新的一项持续随访3 个月的研究结果相似[5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还发现,在6 周和3 个月随访时,均有超过50%的持续性头痛的患者既往没有反复发作头痛病史。研究表明持续性头痛与嗅觉或味觉功能障碍之间存在相关性,这可能与SARS-CoV-2 引发的高炎症状态及病毒侵入周围神经末梢、同时损伤三叉神经血管内皮等机制有关[56]。
SARS-CoV-2 的嗜神经性还表现在入侵神经系统引起神经炎症及脱髓鞘改变。有病例报告显示[57],既往健康的男性在确诊COVID-19 后53 d 时出现双腿疼痛及足部感觉丧失,随后逐渐累及四肢、面部及呼吸肌,脑脊液及神经传导检查支持吉兰-巴雷综合征诊断。一位女性患者在感染COVID-19 后3 周出现疲劳、肢体间歇性刺痛及麻木感、视力模糊等体征,脑部磁共振成像提示脱髓鞘改变,排除了其他病因后最终诊断为COVID-19 引发的多发性硬化症[58]。
研究显示,COVID-19 康复患者存在认知缺陷,主要表现为短期记忆力损伤、注意力不集中、执行功能及视觉空间处理能力障碍等[59-61]。有研究表明,在感染急性期血浆神经营养因子等中枢神经损伤的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异常增高,直到随访6 个月时逐渐恢复正常水平,然而乏力、脑雾及认知改变等神经症状却持续存在[62]。因此,有理由怀疑COVID-19 引起的神经后遗症可能并不伴随持续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需要进一步对神经系统进行全面长期的随访以明确其后遗症发病的相关机制。
3.4 精神心理障碍
据报道,COVID-19 康复患者存在诸多的精神心理症状,主要有PTSD、焦虑、抑郁、失眠等[25],这和之前的SARS 和MERS 流行过后的精神心理症状报告相类似[63,64]。早期关于确诊COVID-19 后1个月的随访结果显示,精神心理症状普遍存在,包括焦虑(42%)、失眠(40%)、抑郁(31%)、PTSD(28%)和强迫症状(20%)等[65]。当COVID-19 患者出院后6 个月时仍然存在疲劳或肌无力(63%)、睡眠困难(26%)、焦虑或抑郁(23%),其中,女性和急性感染期疾病的严重程度是持续性精神心理症状的危险因素[9]。最新的随访报告显示,部分患者的精神心理症状可持续到出院后16 个月[66]。之前关于SARS 患者后遗症的研究发现,精神卫生疾病和慢性疲劳问题持续4 年之久仍影响着超过40%的康复者[63]。因此,对于COVID-19 康复人群的精神心理健康评估需长期进行下去。
COVID-19 相关的精神心理障碍涉及多方面原因,SARS-CoV-2 引发的免疫调节紊乱及细胞因子风暴等生物因素[65],以及女性、高龄、经济压力、社会孤立、对疾病的恐惧等社会心理因素,共同促进了康复患者精神心理障碍的发生发展,严重影响康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对社会发展造成了影响。此外,既往精神疾病史可能是发生COVID-19 的独立的危险因素[67]。有研究表明,部分COVID-19 康复 患 者 存 在“ 中 度 自 杀 风 险”[68],而 在 感 染SARS-CoV-2 后1 年内,有27.60%患者需要通过精神类药物来缓解自身心理疾病[69]。因此,有必要对已存在精神疾病和确定危险因素的人群进行早期的一级预防,同时尽早对康复患者进行心理健康状态评估,从而积极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以缓解康复人群的心理精神压力,促进其全面康复[70]。
3.5 消化系统
早期大量研究已证实,COVID-19 患者急性感染期伴有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胃肠道症状,同时在COVID-19 患者粪便中可检测到SARS-CoV-2 RNA[71-74]。有 研 究 报 道,在 确 诊COVID-19 后1 个月,胃肠道疾病的总体发生率为6%,主要包括腹痛、食欲下降、腹泻和呕吐等[75]。在感染后90 d 时,伴有胃肠道症状的患者多达44%,主要表现为食欲不振(24%)、恶心(18%)、胃酸反流(18%)和腹泻(15%)[76]。在随访6 个月时,胃肠道症状仍可被观察到,主要有食欲下降(8%)、腹泻或呕吐(5%)等[9]。COVID-19 患者胃肠道症状长期持续可能与SARS-CoV-2 在胃肠道中长时间存在有关。有研究表明,在呼吸道SARS-CoV-2 RNA 检测结果转阴后粪便中病毒RNA 检测结果仍可为阳性,表明当SARS-CoV-2 在呼吸道清除后可在胃肠道中持续存在,其阳性持续时间平均为28 d,在部分患者可长达47 d[72]。此外,由呼吸道感染和肠道微生物环境双向作用形成的“肠-肺轴”,在冠状病毒、流感病毒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中可导致肠道微环境的改变[77]。胃肠道作为SARS-CoV-2 靶器官,有研究证实,SARS-CoV-2 感染可导致患者在急性住院期间肠道菌群的改变,机会致病菌增加而肠道有益微生物减少,即使在鼻咽拭子和粪便标本中病毒核酸检测转阴及呼吸道症状消失后,肠道菌群失调现象仍然持续存在[78]。因此,COVID-19 对胃肠道系统的长期影响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了解胃肠道持续症状的发生、发展机制,从而更加科学的指导患者康复。
3.6 其他功能障碍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是COVID-19 急性感染期常见并发症,COVID-19 患者住院期间AKI 的发生率很高,与院内死亡明显相关,而在出院时大量患者的肾功能尚不能得到恢复[79-81]。然而,有研究发现,COVID-19 引起的肾功能损害尚未达到AKI 诊断标准,原需肾脏替代治疗(RRT)的患者在住院期间肾功能指标稳定,由此提出COVID-19 不会导致AKI 或不能加重COVID-19 患者慢性肾脏损伤的说法[82]。因此,有必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以明确COVID-19 和肾功能损害之间的相关性。对于急性感染住院期间需RRT 治疗的AKI 患者,41%在出院时肾功能好转可停止RRT 治疗,而8%则需继续RRT 治疗[83]。此外,对COVID-19 患者随访6 个月,观察到有13%患者出现肾小球滤过率下降(<90 mL/min/1.73m2),而这些患者既往肾功能正常且在急性期从未发生急性肾损伤[9]。因此,需对急性期存在肾功能损伤以及出院后新发肾功能不全的COVID-19 康复人群进行肾功能密切监测,以便及时采取适宜防治措施改善其肾功能,从而减轻疾病的长期负担。
SARS-CoV-2 可 与 胰 腺β 细 胞 特 异 性ACE2 受体相结合,从而损伤胰岛细胞,导致新发高血糖、糖尿病或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而糖尿病则是明确的COVID-19 严重程度和不良结局的危险因素[84,85]。对COVID-19 引发的糖尿病患者进行血糖监测,在随访14 周时观察到患者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仍需口服降糖药维持血糖平稳[86]。此外,SARS-CoV-2 还可影响甲状腺功能。在甲状腺组织中,SARS-CoV-2 与ACE2 结合以及机体异常免疫反应、细胞因子风暴等可引起甲状腺组织损伤,同时还可影响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从而导致亚急性甲状腺炎、Graves 病、桥本甲状腺炎等甲状腺功能障碍性疾病[87]。有关SARS-CoV-2 感染相关的亚急性甲状腺炎病例报道显示,经积极治疗后,在随访6 周时仍有两名患者被诊断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88]。
男性生殖系统作为SARS-CoV-2 的靶器官,已有研究表明在COVID-19 患者中存在睾丸疼痛、睾丸炎、附睾炎等生殖系统功能障碍[89,90]。来自瑞士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短期随访中COVID-19 康复的年轻士兵的活动精子数量显着降低[91]。虽然有研究发现在男性精液样本中存在SARS-CoV-2 病毒颗粒[92],但其结果并不确切。COVID-19 在男性康复患者中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SARS-CoV-2 是否会影响男性生育功能以及是否存在性传播等问题均需长期随访监测来明确。
持续存在的皮肤问题困扰着COVID-19 康复人群。脱发是COVID-19 康复患者最常见的长期持续症状之一,约有25%随访者存在脱发,且持续时间超过6 个月[9,93]。此外,与COVID-19 相关的皮肤病变还包括荨麻疹、麻疹样皮疹、冻疮等,其持续时间从2~70 d 不等[94]。
COVID-19 相关后遗症在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更容易发生,83%的老年康复患者在诊断为COVID-19 后3 个月至少存在1 种持续症状,主要症状包括疲劳(53.1%)、呼吸困难(51.5%)、关节疼痛(22.2%)和咳嗽(16.7%)[95]。而在儿童和青少年中,COVID-19 持续症状也同样很常见,但和老年人群相比发生率较低。对青少年儿童患者进行3 个月的随访发现,约50%参与者至少可见1 种持续症状,疲劳(38%)仍然是最常见的症状,此外还有味觉或嗅觉丧失(16%)、头痛(15%)、感觉障碍(11%)、认知障碍(10%)等[96]。
4 小结与展望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已与人类共存了将近3 年时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长期持续症状及其发生、发展的相关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康复群体在未来是否会出现新的长期后遗症仍不可知。因此,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复人群进行更加全面、密切的随访是今后医疗工作的重点。随着治愈患者不断增加,相关后遗症的出现给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造成了沉重的疾病负担,同时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多学科介入,建立针对年龄、性别、职业、经济水平、地域等不同人群的个性化的治疗康复体系,以促进后遗症群体的全面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