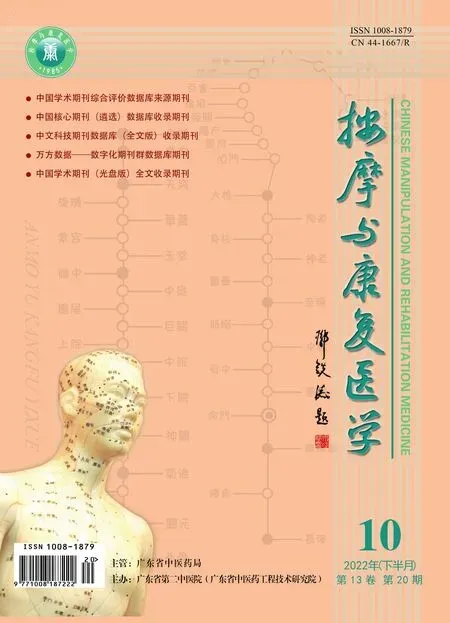基于“肝主筋”理论运用针刺治疗咽肌痉挛合并抑郁症医案一则*
彭坤世,郭锡全,刘佩东
(1.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广州510006,3.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宝安中医院,广东深圳 518101)
咽肌痉挛是一种临床上发病率低的耳鼻喉科疾病,又称为“他觉性耳鸣”,本病以咽喉部不自主异响、耳鸣为主症,查体时可见口腔内双侧软腭有对称的抬举现象。本病尚无共识性的治疗方案[1],笔者基于中医“肝主筋”理论,运用针刺疗法治疗1 例中西医治疗后无效的咽肌痉挛患者,现将治疗过程介绍如下。
1 患者资料
患者施某,女性,47岁,于2019年8月30日就诊。主诉:咽喉异响1 年。缘患者1 年前午睡起床后,无明显诱因出现咽喉不自主异常声响,呈“嗒嗒”声,患者在过去的1 年里曾多次至多个医院就诊,然诊断无法明确,病情未见明显缓解。2019 年8 月27 日于我院耳鼻喉科门诊确诊为“咽肌痉挛”,予口服加巴喷丁治疗,然病情未见改善,患者遂于2019年8月30日就诊我科以寻求针灸治疗帮助。刻下症:患者神志清晰,精神疲倦,咽喉部不自主出现“嗒嗒”声,白天、夜间持续性发作,异响发作频率约78 次/分,无明显发作规律,旁人可闻及,严重时伴有头部巅顶处疼痛,张口时、入睡后异响可自行消失,无颈部肿大疼痛、吞咽困难、进食呛咳,无咽痛,无咳嗽、气喘,无胸闷气短等不适,纳呆,常胁肋胀痛,入睡困难,情绪抑郁,无口干苦,小便正常,大便干稀不调,近1年体重下降约5KG。舌淡红,苔白,脉弦细。既往史:2018 年因心情抑郁,时常半夜惊醒,于外院诊断为抑郁症,服用抗抑郁药物(黛力新、阿普唑仑)治疗后致纳差、体重下降,自行停药约2 月后出现咽喉异响。否认其他基础疾病史。体格检查:一般情况好,神经系统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口腔内可见双侧软腭节律性上举的现象,两侧对称,距外耳道口约5cm 即可听见“嗒嗒”声,与软腭节律一致。辅助检查:2019年8月完善检查,电解质四项、甲功五项、全段甲状旁腺激素、肿瘤标志物五项未见明显异常。颈椎CT 提示退行性病变。甲状腺及颈部淋巴结彩超提示甲状腺左侧叶内结节。双侧颈动脉彩超、头颅MRI+头颅MRA、耳鼻喉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西医诊断:咽肌痉挛;抑郁症。中医诊断:咽肌瞤动、郁证,证属肝郁脾虚,虚风内动,筋脉失养。
治以疏肝健脾,养筋止瞤为法。取穴:百会、四神聪、下关(双)、双侧喉结上排刺、合谷(双)、足三里(双)、阳陵泉(双侧)、三阴交(双)、太冲(双)。操作:患者取仰卧位,局部碘伏常规消毒后,取0.30 mm*40mm 一次性毫针常规针刺,百会、四神聪均平刺约30mm,行捻转平补平泻法;喉结两侧注意避开颈总动脉,直刺约20mm,行捻转平补平泻法;下关、合谷、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太冲直刺30mm~50mm,下关、阳陵泉行捻转平补平泻法,合谷、太冲行捻转泻法,足三里、三阴交行捻转补法。上述操作得气后留针30min,每天1次,5天为1个疗程。
治疗第1个疗程后,患者咽部仍有异响,但持续时间较前缩短约2h,频率较前无明显变化,旁人可闻及异响,头痛较前减轻,食欲、焦虑情绪较前改善,入睡困难较前减轻。
3 个疗程后,患者自觉咽喉部异响基本消失,发作持续时间约30min/次,每分钟发作频率同前,隔日发作,无头痛,纳眠正常,情绪较前舒畅,二便调。
1 年后电话随访,患者诉咽喉部异响偶有出现,发作天数4-5次/月,遇情绪波动时或身体劳累时发作,发作持续时间小于30min/次,频率同前,对日常生活、工作等无明显影响,余无不适,与患者电话沟通约1h,期间未闻及异响。
2 讨论
本病为临床少见的疾病,目前尚无相关的流行病学资料,其发病机制亦暂不十分明确。临床上将本病分为强直性咽肌痉挛与节律性咽肌痉挛两类,前者常见于狂犬病、破伤风、癫痫、脑膜炎和癔症,后者常继发于脑干病变[2]。咽肌痉挛目前临床报道较少,临床报道及科研多集中于继发性咽肌痉挛,如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的神经源性环咽肌痉挛[3]、狂犬病所致的咽肌痉挛[4]等。西医多以缓解肌肉紧张为主要治疗原则,如使用抗胆碱酯酶药、神经兴奋剂、催眠、局部封闭、手术治疗等,但临床疗效参差。如梁美庚[5]运在患者软腭、喉上神经处行0.5%普鲁卡因局部封闭、静滴维生素B1药物后,患者病情较前缓解,但未能彻底根除。李正权[6]采用软腭封闭同时配合静滴普鲁卡因治疗4 天后无效,遂在局麻下行软腭缩窄及腭帆提肌切断术,具体为切除部分软腭,切除两侧腭帆提肌,缝合后7 天拆线,术后6月随访未复发。
本病临床表现与中医文献记载的“筋惕肉瞤”、“瘛疭”、“痉症”等相似[7-9],如《金匮要略》曰:“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素问》提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指出病位在筋,与肝密切相关,中医认为作为五体之一的“筋”,是经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灵枢》记载“筋为刚,肉为墙”,协调全身肌肉正常活动,对人体各部等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反之,筋失养则易出现肌肉痉挛、抽搐、迟缓等病变[10],正如《素问·痿论篇》记载“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筋的生理功能主要通过肝主疏泄及肝主藏血实现,一方面,肝气舒畅调达则人体气机升降有序,筋得以温煦,本案中患者素患抑郁症,自行停药,情志不畅,肝失于疏泄,气机郁结不得透达,筋失于阳气的温煦;另一方面,肝通过主藏血以充养四肢百骸,其中一部分来自脾所运化之水谷精微所生化的精微物质,本案中患者肝旺克土,致气血精微不足,不能濡养经筋,如《伤寒论条辨》载“筋惕肉瞤者,筋赖血以荣,血虚则荣衰,汗多则亡阳而亡津液”,指出病机的关键在于经筋肌肉失于津血荣养。而土虚木亢生风,发为痉挛[11]。故本案患者为筋失养而失用,虚实夹杂,五体病位在筋,五脏病位在肝,治疗上以疏肝健脾,养筋止瞤为法。
本案中患者经西医、中药后病情未缓解,而求治于针灸科。针刺疗法历史源远流长,是重要的中医外治法之一,其因其疗效确切、操作简便、安全性高、主治范围广等优势,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推广。针刺疗法使用一次性毫针,于腧穴局部进针,行提插、捻转等手法,以发挥协调阴阳、疏经通络、调和气血等功效,通过激发人体的自我调节机制而治疗疾病。现代观点认为针刺的原理为毫针进入人体,刺激了人体腧穴的神经末梢感受器、神经干、血管、淋巴等组织在行针过程中,针体与上述组织接触并产生各种感觉和几乎忽略不计的微小损伤,进一步启动或增强人体的自我修复程序以治疗疾病[12]。本案中腧穴处方基于“肝主筋”理论,以局部取穴配合辨证远端取穴为主。患者以咽喉部异响为主诉,故局部取双侧喉结上排刺以疏利局部经气,咽部感觉与运动主要受由舌咽神经、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干的颈上神经节所构成的咽丛支配,有研究认为,针刺咽喉部局部肌群可直接刺激舌咽、迷走、舌下神经,促进咽肌功能的恢复[13],也体现了“腧穴所在,主治所及”的取穴原则。患者在张口时异响消失而闭口时异响出现,而下关穴位于颞颌关节间,司下颌之开阖运动,取之以疏经通络。百会穴居于巅顶,为诸阳之会,并与肝经相通,取之可平泄肝阳以治疗患者巅顶疼痛,配伍四神聪,可协同宁心调神;合谷、太冲组合称之为四关,《针灸大成》解释为“四关者,六脏,六脏有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合谷为肺经的原穴,太冲为肝经的原穴,两穴配伍,气机升降平衡,可疏肝解郁,调节体内气机。阳陵泉为八会穴之筋会,可舒筋止瞤;三阴交为足三阴交会穴,具有调补肝脾肾的功效,配伍足三里以加强培补脾胃之力,则气血生化有源,筋脉得以荣养。诸穴合用,共奏疏肝健脾,养筋止瞤之功。
3 小结
本案患者以咽喉部异响为主诉,辅助检查未见异常,经口服中西药后病情未见缓解,采用针刺治疗简便验廉,治疗咽肌痉挛可取得稳定的疗效,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研究与推广。本案启示在诊治过程中,需详细采集病史,排除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等可能,仔细辨证。同时发现,咽肌痉挛的发病机制尚待探索,目前关于咽肌痉挛的基础研究较少,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