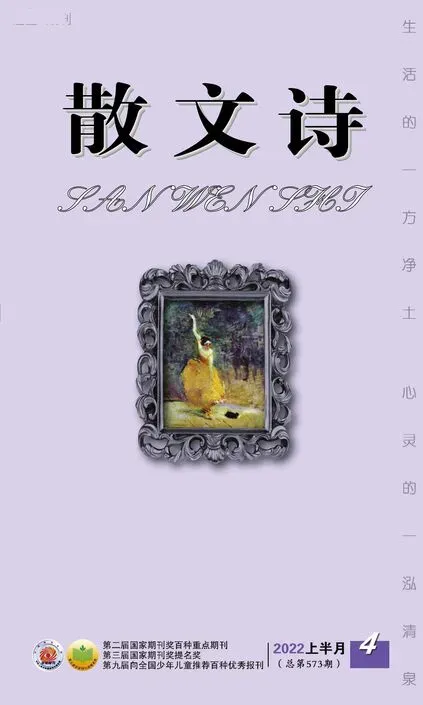诗是最后的身份标识(三)
◎草 树
20世纪80年代初,老房子已经破陋不堪,尽管财力不够,父亲还是断然决定盖新房。作为乡村旧式砖木结构的建筑,最主要的材料就是砖、木头和瓦。舅舅、姑父、表哥都赶来帮忙,老房子附近成了一片原始工地。当一头大水牛在砖场反复地踩着泥,直至踩熟了,强壮的男人们的脚步响起来了,两个人才各提着砖匣子一边,小跑般走向一块空地,当整齐的脚步声再化为一声“嗤”——一块土砖就成型了。在月光下,这样的场景里的人和物,更具雕塑感和节奏感。我曾经久久地站在一边,或在风干后码起的、像巷子一样的砖坯之间穿行,总是被某种东西莫名地吸引。当然,我也亲自尝试——不,是必须——制作红砖,当我把一大团泥在平台上做完简单整形,高高扬起,“啪”的一声砸下去,先前被我洒进砖匣的细灰,有一部分就会跑出来,冲得我头一偏,甚至直接冲入眼睛。满手是泥,无法揩拭,就以衣袖小心擦着,但我没有感觉到沮丧,相反那砖坯“噗”的一声方方正正掉出来,那些伴生的、细微丰富的嗤嗤声,那某一个没有饱满的角被我按下一个拇指形的洞,无不给予我巨大的快乐。
这是关于家宅的原初性记忆之一。很少有人去描绘陋室的原初性,更多的是刻划它的现实。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隐喻式的写胸怀,而非写陋室本身。事实上,这种原初性属于每一个人,无论他富有或贫穷,只要他愿意梦想。家宅是庇护所,是藏身地,所有的卧室都有共同的梦想价值。在家宅,一个人拥有最久远的回忆、最稳固的幸福感和最持久的柔情,好比火与水,一点火星可以照亮并焊接回忆和不可忆起之物的关联,在遥远的区域,记忆和想象互不分离,而似水柔情,始终在这“过程”的水缸里荡漾。这里全部的原初性元素,都是诗歌的元素。如果我们再延伸一点,把家宅当作不冠以家宅之名的居住空间,那么,想象力可以用无形的阴影建造“墙壁”,家宅的维度便可以无限延伸和打开,并依据语言自身运动的轨迹确定边界。如是,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在城市层层叠叠的盒子里无法搭建“家宅”,而非得回到那个山水田园里的空房子中去。恰恰相反,城市文明在不断积累新的记忆和美,有了崭新的自然和细节。我们时代的自然必须以人为主体,一切山水都是人的山水。相比之下,地铁和摩天大楼当然无助于诗意的孕育,但是,在城市的石头下冒出的青草,从神秘的渠道秘密潜入最新小区的青蛙,以及大量的植物移民,如银杏、香樟之属,无不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性在勃勃生长,而这一切,还远未化为词语,跃身我们最新的语言、诗歌和文学传统之中。
现代性是最新的“家宅”的梁柱,不管它凸显于风格形式上,还是隐于建筑装饰的内部,都是当代诗的基本价值所在。没有现代性浸透的史料堆砌或未来想象,不过是故纸堆和空中泡沫,不是当代诗。
家宅作为一个诗歌的场所,它的椅子、桌子、碗橱里的碗盏都成了词语的基本形象。椅子,不单是给你一个位置,主要的是,家宅里的椅子给你的那种自由感和自在感是别处没有的。无论是会议桌前的放有座位牌的对应的椅子,还是一个堂皇讲坛下的不命名的位置,都会让你被某种东西束缚,从而让你和“你”短暂地分离了。在家宅里,椅子给你踏实感和真实感,是别处不能获得的。椅子,作为一个词语,可能会使你在记忆和想象中,听见更多的响动,置身于一首诗,就会带来更多的意外,就好比我们小时候在乡下看见向阳的老墙,由于蜜蜂的嗡嗡声,我们发现凹凸而光滑的土砖出现了小洞和草茎。蜜蜂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不断地停住、敛翅,试图进入那圆圆的、温暖的小洞。草茎发白,纹理清晰,它召唤土砖制作的原初现场:在早晨的晨光里,一个人把稻草散开撒向砖泥,或赶着一头水牛转圈。那些分散的泥巴正是因为水和草茎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水分退场以后,草茎成了最后的组织者。现在它露出来,或者在更晚的时候,某一种不可言说的沉默之物切近它,便获得了意识,为词语担当了身份代言的使命,从而可以开始言说了。而土砖上的圆洞——“关于洞穴,更多的人还没有出来。”(汤养宗《洞穴》)——蜜蜂进去又出来,它的嗡嗡声要到生命的历程中很晚的时期,才能引领我们真正地欣赏一个关于洞穴的形象:它映照了我们青春时代的甜蜜,也把这种记忆导向记忆中的历史之外的根基——洞穴的温暖和甜蜜,不单来自生命,甚或大地。
切·米沃什在意大利的某一家山间旅店,三个人挨着一家意大利人坐在水平排列的松林中。附近是小女孩的吸水声和天空响起的燕子的叫声,不要管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季节——“此刻,我坐在她和她的身旁/以往生命的各个阶段/和摆在方格桌布上的葡萄酒一同到来。”(米沃什《在中午》,张曙光译)“诗歌带给我们的并非都是对年轻时候的怀旧,那样就太平庸了,诗歌带给我们的是对表达年轻之方式的怀旧。”事物从羁绊中解放出年轻,向记忆召唤词语的新形象,一直向原初的记忆掘进,进入记忆的史前史。对于诗人来说,年龄增长了更可能获得真正的年轻。或许在一张明式鸡翅木的八仙桌上,细密的木纹掩藏着风趣的谈话,只有词语能够听见。
在家宅中诞生的孩子从向世界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宣告以后,含着母亲的乳头咕咚咕咚吮吸时突然冒出一个声音:嗯吗。这是一双清澈的、感恩的、充满柔情的眼睛下面那一张嘴发出的。它没有沉浸在奶水甜蜜的享受之中。这个声音,在大人的纠正下,慢慢清晰起来:妈妈。母亲。之后词语被隐喻化了,当它再一次从那个长大的孩子的嘴里说出,已经附着丛生的意义。于坚的《拒绝隐喻》,为当代诗的写作清理了道路。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也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最为响亮的诗歌口号。一场诗歌革命开始了。不管韩东和于坚提出的诗学主张的先后,属于“他们”的他们的观念都是一致的。韩东说,诗人要像一个专业诗人一样写作,要“活出来”。当三月的凤凰冷清寥落之时,他的声音似乎使“摩西,把房梁抬高”这样的内在信念获得了通俗而深刻的表达。韩东身上总是闪烁着某种狡黠的智慧,他有意识地省略了“艰难的战斗过程”而直取城池的高地。于坚则绝不讨巧,而是把来自德国大师海德格尔“回到语言那儿”和被韩东演化为“诗到语言为止”的主题,以《拒绝隐喻》和《诗言体》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做了深入的溯源、解剖、阐述和归纳,“回到语言的元隐喻本性”, “言尽意止”,“诗是语言的在场,澄明”,“诗是语言的解剖学”,等等,对中国古老的“诗言志”这样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几乎是一阵飓风。尽管今天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曼德尔施塔姆和罗兰·巴特那里找到它们的出处,但是,于坚以它们为武器,对汉语诗学几千年的传统和现代(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的诗学观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剖,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这无疑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在写作实践上,于坚也以其具有经典品质的《零档案》做出了回应。它把“写”这一动作真正带入了“写作”本身,基于对“档案”这一个词语本身的长久倾听,获得了真正彰显词语身份的形式——或者说,超越了传统文学的一切惯常形式的形式,展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语言行动,既解剖,又呈现,解剖和呈现共为一体成就“写作”,打破了诗歌史长期以来写作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或割裂,以及传统的反映论思维图式。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它在今天仍然沉甸甸如一部仍待解密的档案。于坚最近十年在诗学上的不断思考和自我修正,进一步澄清了中西文化的源流,确立了自身清晰的坐标。从“去魅”到“返魅”,从回到过去到面对当下,“新陆诗丛”之《彼何人斯》带来《拉拉》《在布里斯本》等一批新的成果,令人眼前一亮。一种即兴的、巫师招魂般的写作,呈现出恢宏气象。《有关大雁塔》和《车过黄河》当初似乎有了某种经典的意味,经过时间的淘洗,今天来看,它们只剩下了一个姿态。韩东后来出版的《重新做人》则弥漫着一种真正的“个人性”的气息,令人玩味。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衍生语言革命,新诗又走过了20年,期间派生的废话诗、下半身写作、垃圾派、物主义、自行车、新湘语等等,可以说在本质意义上都是“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这一源流下的支系,概略来看,无论是下半身写作的从推崇身体到深入器官,还是垃圾派的以审丑反对审美——崇低以反崇高,反传统,其本质是反对意义,强调身体甚至器官的在场,换句话说,不是“诗到语言为止”,而是诗到日常生活的身体性或器官性为止。当一代诗人的语言意识觉醒——也就是以韩东之谓“专业诗人”的区分标识——这些流派或者说泛流派的写作,徒留姿态,再无新发现,普遍呈现为一种线性化、扁平化和散文化的描述及语言向度的封闭,诗和散文也失去边界。事实上,其中一部分诗人也自觉反思了所谓先锋姿态的策略性质,开始转向独立的、沉潜的写作。
老一辈诗人多多宝刀不老,去尽铅华,“直取核心”,他的诗歌语言趋向“干枯”而充满力量。知识分子或者学院派的写作,同样出现了“静悄悄的黎明”。孙文波和臧棣是这一路写作中最具活力的诗人之一,丛书、协会系列和《新山水诗》是他们最新的成果,相对于民间写作的姿态性之苍白,他们为汉语增添了丰富性、新颖性和可能性。臧棣是知识分子写作中少有的抛弃了腔调的诗人,他致力恢复语言游戏的古老天性,并力图在能指层面运作带来新鲜的语言景观,但也因其较少获得现实感而备受质疑。孙文波试图恢复古代山水诗人行吟的传统,从语言层面入手,以诗学为方法论,以谈论的方式“指点江山”,俨然烹制了一道词语的“东北炖”,呈现当下新山水之洋洋大观——人和世界的关系的最新图景。他们的写作本质趋同,开启语言的“观看”,是一种作为世界观的诗,或者说,在他们那里,诗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当然,臧棣说诗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则为诗的定义留出了更多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