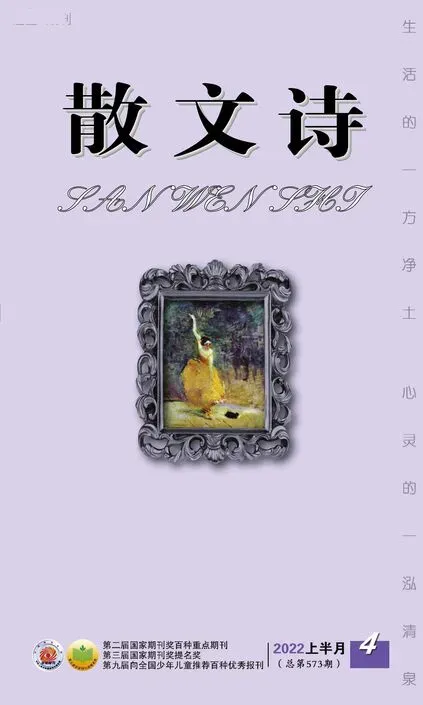大雪日
◎张开翼
荒城
弯曲。绷直。地平线弹开我,从驼峰间,拖出一座黄土夯筑的城。
城内塞满荒草,是另一队驻军,一棵瞄着一棵,充满纪律性。地上方形的砖石塑造了荒草方形的安静。
马羊足迹新鲜,说明有访客刚刚离去。
傍晚的风,在不远处的沙丘上写写画画,让我重温手写体的涂鸦。
城门破败,我来去自由。
马帮、车队、驼铃走失。拄着木棍的我,追赶汹涌的时间。
雁过贺兰
仰头,看见一群大雁,它们的叫声,让贺兰山的秋色,陡然凝重。
沿着咕嘎咕嘎的方向是萧索的行程。天更蓝,云更白,风更清凉。流云在山崖上展开补丁,缝补着岁月的罅隙和裂痕。茅草和矮树,被鸟声沁湿。
有石突出如唇,有洞深陷如眼,环顾皆幽深。
健步登山。两山耸峙的“一线天”,仅容我一人通过。
新生。衰老。从寒武纪到震旦纪,沧海漫过桑田。
崛起。沉沦。分分秒秒上演轮回。
每一块石都有一棵树相伴,每一棵树都有一块石相拥。石被风化,树被霜侵。攀登一步,就离天更近,也离雁叫声更近。
传书故乡,它们匆匆南归的背影,翻山而去。
想妈妈的夜里
想妈妈的夜里,童话醒了。
雪人、布人、稻草人复活。
露水浓重,打湿了裤脚和衣襟;哑泉幽咽,搓洗发白的乡愁。
想妈妈的夜里,雪涂改了大地的颜色、头发的颜色,却涂改不了她走路的姿势和呼唤的声调。
高一声,低一声,全都是我结痂的乳名。
想妈妈的夜里,星星都趴在窗口,一起叫喊。
我梦见,那年深秋,妈妈在拾麦穗。我慌张地扯住她打满补丁的红衣裳……我看见,那年初春,我跟在挖野菜的妈妈身后,难舍难分……
想妈妈的夜冰冷,我划亮一根火柴;想妈妈的夜里,到处流淌着蜜。
星星提着灯,引路。我扑进她怀里。
世界,停顿在我的童年。
我的窗
秋天,草漫过马蹄。
马蹄追赶着草的足迹,一路向前。
大地抖出枯黄的心事,等候一场雪的到来。
我坐等落日。
我的心是恬淡的,我在一块突兀的山岩上画一扇窗。
我的窗里有山,山顶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和鹰的唳叫。有泉水涌流,环绕毡房和炊烟。有牦牛低头吃草,肚腩上的毛耷拉在地上。有状如白斑的羊群散落、游移。有雪粒从天空洒下。有大口喝酒的汉子。有熬煮酥油茶的女人。有怀抱羊羔的小孩。有落日的眼神,平静、辽远。有野兔落荒而逃,有陷入青草漩涡的积雨云。
我的窗默守清欢。一切都闪烁着朴素的光泽。
我窗内的草原,正落日熔金。
在腾格里
我曾跟着一只甲壳虫,赶路。
路是丝绸之路。没有驼铃。
我曾踩痛过骆驼刺的呼吸。
艳阳隐退。我仔细地研究狼的脚印,谛听夜色里,它们凛冽的叫声。
我曾头顶星光低语。
把双脚伸进大漠,企盼制造另一场雪和无边无际。
大雪日
我看到,许许多多叶子坠落。
圆形的,长形的,带齿的,带尖的,带虫洞的,带霉斑的,带裂痕的……桦树的,楸树的,榉树的,梣树的,椴树的……它们彩色的往事,连同带泪飞行的回忆,全部被雪漂白。
今年今日,皆为白色的心跳。
世界宁静。
日子,需要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