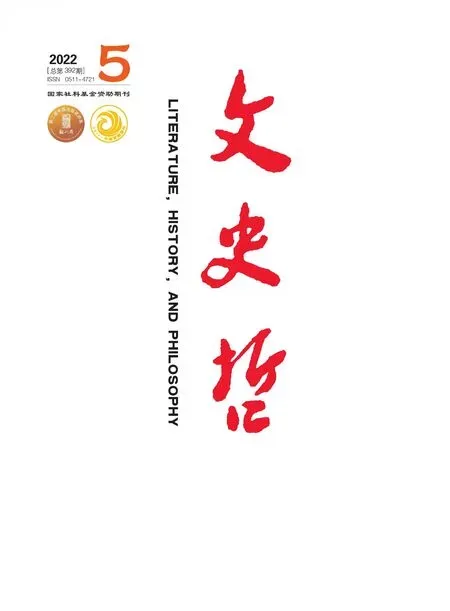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相辅相成
——对梁启超公德论的一个考察
黄启祥

一、“公德”的多种含义
梁启超的公德学说驳杂繁复,散布在他的不同著作和文章中,并非一个集中统一的体系。为了准确地理解他的公德论,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公德概念在其著述中的多种含义,即作为道德规范的公德、作为道德品质的公德、个人公德与群体道德。这几个概念在以往的讨论中常常混淆不清,以至于妨碍了人们对梁启超公德论的领会与理解。
首先,我们宜区分作为道德规范的公德与作为道德品质的公德。
作为道德规范的公德,即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基本规范。例如,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二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作为道德品质的公德,即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是个人或群体在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例如:雷锋忠于职守、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品质。梁启超的著作以不同形式包含公德的这两种含义。
就作为道德规范的公德而言,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缺乏,否则它便难以存续。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爱国都是其国民的一种公德,梁启超倡导公德论的重点也在于爱国。我们如果在道德规范的意义上来理解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传统道德中“公德殆阙如”,那么便不可能不对其产生误解。那些根据这种理解来赞同或批评他的这个表述的人都难免失当。但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公德规范是一回事,国民是否具有公德品质则是另一回事。固然,没有公德规范便难有公德品质,但是承认前者并不必然要承认后者,否认后者也不必然要否认前者。当梁启超说国人缺少公德的时候,他的意思并非是我国历史上没有爱国这一道德规范,而是指当时国人没有如其期望地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
陈来的《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一文在道德规范的意义上使用了公德一词,这可以从他对公德的界定中看得出来。他说:“社会公德一般指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旨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陈来将公德区分为公民道德(政治性公德)与公共道德(社会公德),他说,“公民道德体现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公共道德体现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要求”。我们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公德,无论是公民道德还是公共道德,都是指作为道德规范的公德。从其文章第七部分的论述来看,他所说的公德亦属此意。
既然陈来在道德规范的意义上使用公德概念,他应该理解梁启超在公德的此一含义下所作的一些论述,但他却对之感到有些不解。他说:“梁启超所说的公德也并非都是道德,其中多属近代社会的意识、价值。”又说:“就公德的条目而言,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特别立专节论述的,有国家意识、进取意识、权利思想、自由精神、自尊合群、义务思想等,其实,从伦理学上来说,这些大都不属于道德。梁启超以‘公德’指称这些意识和价值,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淆。”陈来认为梁启超混淆了公德与社会价值。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论述的权利意识、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进取冒险、义务意识等确属近代社会的价值,但是,如诺博托·霍尔斯特所说,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可以转换为道德规范的。以“权利”为例,约瑟夫·拉兹认为,“在道德思想中,权利代表了独立的道德目标”。梁启超阐述这些价值,其目的在于号召国民珍视和追求它们,他是将此作为公共道德规范来加以宣扬的,正如公正、敬业、友善等既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我们的公共道德规范一样。
陈来的这种疑惑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梁启超对于公德一词的模糊使用。当我们说梁启超的著作以不同形式包含公德的这两种含义时,并不意味着他在著作中将它们清晰地区分开来,更不意味着他在每一次使用公德概念时都具体指出了他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它。事实上,他的著作中虽然包含但并未明确区分公德的这两种含义。上述梁启超所强调的那些公德之所以引起一些学者的误解,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对于公德概念的模糊使用。他在《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与私德的界定是,“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这是在道德品质的意义上来定义公德的。而在此后,他又将追求自由、自治、合群等作为道德规范的公德来加以论述。也就是说,梁启超没有清楚区分作为道德规范的公德与作为道德品质的公德,他的一些论述便难免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陈来对梁启超的公德论产生疑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区分作为道德规范的公德与作为道德品质的公德。他在将公德界定为道德规范时,相应地,应将私德定义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公民道德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公共道德体现的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对公民的规范要求,那么相应地私德就是私人生活对个人的规范要求。但是陈来并未给出这样的定义。他虽然说“广义的私德就是公德以外的个人基本道德”,但是他似乎未对私德或个人道德做出一个清晰的界定。透过他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般将私德视为道德品质,与其相对的是作为道德品质的公德。例如他说,“私德是个人的品德、修养,而公德是指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德行”。如此,他对公德概念与私德概念的界定在含义上是不对应的。但是,陈来有时也在道德规范的意义上使用私德概念。概念含义的模糊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淆。
其次,我们通过对比个人公德来澄清作为群体道德的公德。

在梁启超的著作中,作为道德品质的公德包括作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公德与作为群体道德品质的公德。当梁启超说“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时,他所说的公德即个人公德,也就是个人利于群体的品质,这种公德的目的在于利群。与此同时,梁启超借用斯宾塞的话说,“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徳而已定”,他进而论道:“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这里,梁启超所说的是“群之德”即另一种公德,它是一个团体中成员的公共德性或团体德性,其主体是团体而不是个人,尽管团体由个人构成。这里的团体可以指村镇、公司、文化团体、政治团体、军事团体,也可以指国民全体或整个国家。在此我们仍应注意,梁启超的论述中虽然包含个人公德与群体道德,但是他并未对之做出清晰的区分,这使他在论述公德的某些地方将个人公德与国家道德并为一谈,这从他的《新民说》第六至第二十节即可看出。
根据梁启超的表述,与群体道德相对的不只是个人公德,也可以是个人私德。我们在这里把个人公德与个人私德统称为个人道德。由此,与群体道德相对的个人道德既包括个人公德,也包括个人私德。澄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下面的讨论非常重要。一方面,个人道德、个人私德与个人公德是三个含义不同的概念,也是容易混淆的概念。另一方面,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的关系是梁启超公德论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没有群体道德在场,个体道德有时令人难以理解。
陈来批评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强调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与重要性。但是他未明释个人道德与公德和私德的关系,而将个人道德等同于私德。例如他说,“伴随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政治公德不仅排挤了社会公德(即公共道德),更挤压了个人基本道德(私德)”。再如,他说:“个人道德……即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如勤学、立志、俭朴、温和,或谦虚、严肃、耐心、慎重等。”如前所述,他主要是从道德品质的意义上来谈论私德的。但是,就道德品质而言,无论是私德还是公德,其主体都可以是个人。由于陈来没有明晰个人道德的概念,也未区分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他对梁启超关于公德与私德划分的理解难免偏颇。他认为在梁启超那里,“私德既是个人自处的德操,也是个人对待其他个人、处理与其他个人关系的道德,公德则是个人对于群体的道德。这个区分还是清楚的。私德与公德两者并行不悖。这个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私德是个人的品德、修养,而公德是指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德行”。这只是梁启超区分公德与私德的方式之一,根据这种区分,作为道德品质的私德与公德是并列对应的两个概念。
在梁启超看来,私德与公德还有另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私德与公德并非并列对等的概念。他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这里公德也是私德的一种,公德乃私德的集成。其实,梁启超此处所说的私德与公德的关系就是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的关系。梁启超虽然没有从概念上专门区分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也没有像论述公德与私德那样将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作为明确的主题加以阐述,但是他的公德论与私德论中包含着深刻的关于群体道德与个体道德的思想,领会这些思想对于理解他的公德论至关重要。
陈来认为,梁启超重点推崇的公德即爱国利群的政治道德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挤压了个人基本道德(私德)。如果我们从道德规范的意义上来理解公德与私德,陈来的这个看法很难令人信服,因为梁启超在倡公德的同时并未否认作为道德规范意义上的私德。就连陈来在另一处也承认这一点,他说,“梁启超在写作《论公德》时期,虽然着重推崇公德,但对私德并没有加以否定而是肯定了私德的意义”。如果我们从道德品质的意义上来理解公德与个人道德,那么陈来对梁启超的批评表明,他认为作为群体道德的政治公德会压抑和取消个人道德。这个观点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事实上,作为群体道德的政治公德与个人道德在许多方面是相辅相成乃至相互依存的。梁启超公德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一方面他认为唯有作为群体道德的政治公德的改造,才能塑造相应的有利于国家富强的个人道德,另一方面他强调个人道德乃是群体道德的基础。
二、群体道德对个人道德的塑造
梁启超道德学说的一个贡献在于,它在近代社会背景下从不同方面向我们提示了群体道德对个人道德塑造的意义。尤其是他通过分析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对国民的爱国主义的影响,一方面阐明,个人在群体中通过学习和熏陶能够逐渐造就在个人生活中未曾具有的德性,另一方面阐明,如果一个群体没有某种德性,个人则很难具有这种德性。
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论,其核心在于倡导一种群体道德即国民的爱国主义,这一点在他的论述中是十分清楚的。在外患将亡中国的严峻形势下,梁启超认为亡国灭种的危机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民缺少一种抵御侵略的力量即爱国主义。他说:“夫政府民人,痛痒不关,爱国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国人之所短也。”他直言:“吾辈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爱国。”陈来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政治公德,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将爱国主义与个人道德相对立。爱国主义既是一种群体道德,也是国民的个人公德。爱国既是公民个人层面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公民个人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
在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民主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是国家追求的德性,它是我们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根据陈来的观点,民主无疑属于政治公德,而政治公德可能挤压、取代或取消个人道德。但是梁启超认为民主不会取消个人道德,而是会促进个人道德,民主的对立面即专制才会压抑个人道德。在梁启超看来,国家若具有民主德性,则易于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专制体制则是导致国民缺少爱国主义的一大原因。这也可以视为他力推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的一个论证。根据梁启超的论述,在专制政体下,朝廷将自己视为上天的代表,而非国民的代表。国民习惯于为专制统治之奴隶,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以为朝廷和国家的兴亡与己无关,缺少做国家主人的观念,由此导致“群治不进”。“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梁启超慨叹:“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也就是说,这种体制容易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居于社会底层者只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衣食住行,社会上层人士只知浮言空谈,逃避现实,那些没有脊梁者更是卖国求荣,那些有理想抱负者也仅仅满足于寻觅明主。
梁启超在追溯君主私天下的原因时认为,国家皆起源于家族,三代以前,君与民如家人一般,君如家长族长,民如家族子弟,“依于国家,而各有其所得之权利,故亦对于国家,而各有其应尽之义务。人人知此理,人人同此情,此爱国之心,所以团结而莫解也”。“自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来也。后世之治国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议之,专断而行之,民不得与闻也。有议论朝政者,则指为莠民;有忧国者,则目为越职,否则笑其迂也。此无怪其然也,譬之奴隶而干预主人之家事,则主人必怒之。而旁观人必笑之也,然则虽欲爱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既不敢爱不能爱,则惟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
梁启超不否认君主专制国家也提倡爱国主义,但是他认为君主专制国家提倡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爱君主义或者爱皇主义,它不是对于国家的爱,而是对于君主或皇帝的爱,因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反而可能使人们对国家漠不关心。他从朝廷职能的角度分析了将爱国主义混同于爱君主义的原因,“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及爱屋及乌之意云而”。梁启超区分开国家、朝廷与君主,他将国家比作公司,将朝廷比作公司之事务所,将君主比作事务所之总办;又将国家比作村市,将朝廷比作村市之会馆,将君主比作会馆之值理。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会馆为村市而设,这是很清楚的。事务所不等同于公司,会馆不等于村市,“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总办更不等于公司,值理更不等于村市。“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

因此,梁启超认为:“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为君主者,当视专制政体为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种盘于我本群者,虽已数千年,合上下而敌之仇之,则未有不能去者也。……专制政体之不能生存于今世界,此理势所必至也。”由此,梁启超呼吁去除专制政体,唤醒国民的爱国之心,才能救亡图存。他说:“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这正是戊戌变法所志于的事业。只有打破君主专制,才能真正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才能造就新民,国家才能救亡自强。
与去专制相应的,便是兴民权,爱国民。梁启超认为,国家由国民组成,真正的爱国主义必定体现在尊重国民的权利,爱自己的国民,这种爱包括国家统治阶层对于国民的爱,也包括国民的自爱。他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他呼吁国民不要被动等待政府恩赐权利,而应主动争取权利。在他看来,政府压制民权是一种罪恶,但是国民不争民权也是一种罪过。“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权,而能成就民权之政者。”
梁启超还论述了专制政体对其他一些公德的影响。例如,对于国家拥有义务之心是国民个人的一种公德,而“专制政体之国,必束缚其民之心思才力于无可争之地”。这使国民承担无权利之义务,而君主则享无义务之权利,其结果是国民与国家关系疏远。再如,个人以政治能力服务国家,组成有机社会秩序,是国民个人的一种德性,但是专制政体压制国民的政治能力,“专制政体为直接以摧锄政治能力之武器,此稍有识者所能知矣”。梁启超认为:“专制之国,其民无可以用政治能力之余地,苟有用之者,则必将为强者所蹂躏,使之归于劣败之数。而不复得传其种于后者也。以故勾者不得出,萌者不得达,其天赋本能,隐伏不出,积之既久,遂为第二之天性。”他又说:“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斯固然矣。”
梁启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见解独到地指出了国民的德性培养与国家德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君主专制下难以培养超越君主的爱国主义,因为君主等同于国家,甚至超越于国家之上。在民主制国家中,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是服务于国家和国民的,他们的地位在国民的心中是低于国家的,因而爱国主义是超越于他们之上的。梁启超虽然认为专制统治导致国民缺乏爱国主义,但是他仍然承认爱国主义在君主专制国家中也是存在的。君主专制国家中的爱国主义是一个复杂观念,它通常既包括爱国家,也包括爱君主,这两个观念常常混合在一起。它们有时是同一的,有时则是分离的。梁启超认为:“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当君主真正成为国民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的时候,它们是同一的;当君主不再是国民利益的代表或不再捍卫国民利益,甚至背叛国民,成为国民敌人的时候,它们就是分离的。所以,爱君主未必爱国家,同样,爱国家也未必爱君主。


梁启超关于群体道德塑造个人道德的论述远不止此,这里只能择而述之。抛开梁启超的论述,我们通过经验观察也可以看到,个人道德的提倡与培养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群体道德的制约。在儒家的治国理政体系中,可以倡导和推崇“百善孝为先”的道德价值。但是,在基督教会中,人们很难将孝德作为道德之本,因为基督教使信徒把上帝看得高于父母,把对上帝的爱看得高于对父母的爱,这当然会限制孝德的提倡和培养。事实上,任何将群体领袖(宗教崇拜对象、宗教领袖或政党领袖)看得高于父母的群体,都很难将孝德看成基础性的美德。
三、个人道德对群体道德的基础作用

在梁启超看来,群体的许多德性决定于个人德性,只有成员拥有它们,团体才可能拥有它们,若是一个团体中的每个人都缺少它们,则他们组成的团体亦不会拥有它们。他说:“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因此,造就新民群体须首先培养国民的个人德性。
梁启超关于自治的论述非常典型地显示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说:“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身品格第一大事。”“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梁启超所说的个人自治之德即自律。群体和国家也有自治之德,群体与国家的自治亦即法治或律治,也就是遵循法律或规则。“国有宪法,国民之自治也。州郡乡市有议会,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一人之自治其身,数人或十数人之自治其家,数百数千人之自治其乡其市,数万乃至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数万万人之自治其国,虽其自治之范围广狭不同,其精神则一也。一者何?一于法律而已。”

梁启超认为不能自治者必然受制于自治者,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他说:“己不能治,则必有他力焉起而代治之者,不自治则治于人,势所不可逃也。人之能治禽兽也,成人之能治小儿也,文明人之能治野蛮也。皆其无自治力使然也。”他又说:“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不能自治者,他人欲无干涉焉而亦不可得也。”以印度为例,“今日之印度,英人居者不及万,而二万万之印人,戢戢如群羊乎”,乃是因为英国人比印度人更富于自治力。
梁启超倡言,国人今日所当务者,乃求一身之自治,进而求一国之自治。他呼吁:“吾民乎,吾民乎,勿以此为细碎,勿以此为迂腐,勿徒以之责望诸国体,而先以之责望诸个人,吾试先举吾身而自治焉,试合身与身为一小群而自治焉,更合群与群为一大群而自治焉,更合大群与大群为一更大之群而自治焉,则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国平等国独立国自主国出焉矣。而不然者,则自乱而已矣。自治与自乱,事不两存,势不中立,二者必居一于是,惟我国民自讼之,惟我国民自择之。”
梁启超就许多主题阐述了这个思想。例如,他认为国民若无能力,国家便无能力,“国民苟有能力者,则国家有能力,以此因缘,故养政治能力,必自我辈始”。再如,他认为国民若无自尊,国家便不可能有尊严:“夫国家本非有体也,藉人民以成体,故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始。”“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立焉者也。”再如,他认为国民若不享有平等权利,国家便不可能与他国拥有平等权利。“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若是者国庶有瘳,若是者国庶有瘳。”
此外,梁启超还指出,群体道德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个人道德,但是对于一些德性而言,即使团体具备这种德性,若其中一个成员自身不具备相应的德性条件,团体也无法使其具备此种德性。正如瞎子不会因为混在目明者中间,就能突然目光敏锐;聋子不会因为混在耳聪者中间,就能突然听觉灵敏;懦弱者不会因为混在勇士中间,就能突然变成勇士。
上述梁启超的一些具体观点当然可以商榷,这里对此存而不论,主要阐释梁启超对个人道德之基础作用的重视。梁启超曾言,中国道德发达甚早,但是“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这里所说的公德重点指爱国利群的道德,似乎包含这样一层含义,即私德发达则妨碍群体道德的发展。但其实并非如此。根据梁启超的表述,群体道德是个人道德的合成。一方面,群体道德可以是个人公德的共同体现。例如,由一个个爱国者组成的群体必定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德性的群体。另一方面,梁启超认为群体道德也可以由个人私德构成。在这个意义上,无私德之人不可能组成一个具有相应公德的群体。“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学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国民之私德有大缺点云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不但不否认私德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当然,梁启超并不认为私德可以自动转化为群体公德,其中国道德私德发达而公德阙如的看法就暗示了这一点。
简言之,梁启超既倡导群体道德也倡导个人道德,既倡导公德也倡导私德。在梁启超看来,一方面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都有其不可替代性,不能以群体道德压抑和排挤个人道德,反之亦然;另一方面群体道德(包括政治公德)与个人道德又可以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许多群体道德以个人道德为基础,而许多个人道德则以群体道德为条件。通过这个视角,梁启超著作中许多看似彼此矛盾的论述就可以统一起来了。从作为道德规范意义上的公德来说,梁启超所倡导的公德(包括政治公德)并不压抑个人道德,从作为道德品质意义上的公德来说,梁启超所倡导的公德(包括政治公德)也未导致取消个人道德的状况。概言之,我们未必赞同梁启超有关群体道德与个体道德的一些具体论述和例证,但是他对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之关系的独到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研究和道德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陈来呼吁人们加强个人道德的培育,这无疑是重要而又必要的倡议。但是培育个人道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政治公德,相反,只有加强相应的政治公德,个人道德的培植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不是政治公德而是其对立面即政治恶德才是培育个人道德的阻力。如果认为政治公德排斥、挤压乃至取消个人道德,不仅会对梁启超产生误解,而且可能在个人道德培养议题上偏离正途。
梁启超关于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的论述也有些混杂不清。其一,他没有明确区分个人道德与私德,许多时候将私德等同于个人道德,但个人道德不仅包含个人私德也包含个人公德。他有时将公德还原为私德,有时甚至认为对公德私德“不必强生分别”,消弭了私德与公德的区别。其二,他有时又将群体道德还原为个人道德,模糊了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的界限。群体道德有时看似同类的个人道德的简单相加,其实即使梁启超所论述的群体道德——团体中成员的公共德性——也未必如此。而且群体道德有时候并非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单一德性的加和,而是不同种类的个人道德的有机合成。例如,梁启超认为服从是一种民德,若无服从之德,人人欲为指挥者,不愿服从,则群龙无首,团体不存。但是,若是人人都甘于服从,无人愿意指挥,这同样不是一个优秀的团体。所以团队的某种美德有时不取决于成员的单一品质,而是成员的多种品质的有机结合。

这里似乎有一个解释的循环。国民要具有某些德性,首先国家需要具有相应的德性;国家要具有这些德性,又要求国民必须首先培养这些德性。这个困惑也表现在梁启超的变法事业上。他一方面认为维新变法和政体革新需要国民的爱国主义支持,另一方面又认为国民的爱国主义的培育需要维新变法和革新政体。梁启超在分析国民缺乏爱国之心时认为,过去人们将爱国之心混同于爱君之心,只知爱君而不知爱国。这里包含两个观点,其一,国人是具有爱国之心的,其二,国人将爱国之心错付于皇帝。如果中国完成了政体改革,那么国人的爱国之心就不存在错付于皇帝的问题了。换言之,一旦维新变法成功,取消君主专制政体,国人区分开国家与皇帝的不同角色与地位,将皇帝置于国家之下,而不是将皇帝与国家等同,爱国之心就不会混同于爱君之心,真正的爱国主义就会发扬光大。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了,当时中国的政体没有革新,国民如何培养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与维新变法似乎都不可能了。这似乎是梁启超公德论中的一个死结。
在现实中,这个死结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解开的。因为在这种解释循环中,国民是一个整体概念,是一个单一的人格,但是现实中的国民是在知识、视野、德性、能力等等方面存在差异的诸多个体。就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或单一人格而言,要具有珍惜权利、民主、自由的德性,须以国家具有民主德性为前提。但是就每一个具体的国民来说则并非如此,有的人可能在国家立宪之先,就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民主意识和民主德性。在国家层面无法进行根本变革以产生新道德所需条件的情况下,个人与小群体的道德进步就具有奠基的意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梁启超就属于这种先知先觉者。这种先知先觉者的民主意识可能是一个国家内生的(即在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中产生的反向意识,欧洲近代一些国家的情况大抵如此),也可能是从专制国家之外引入的。无论其产生路径如何,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具有民主意识的时候,这个国家必定会具有民主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