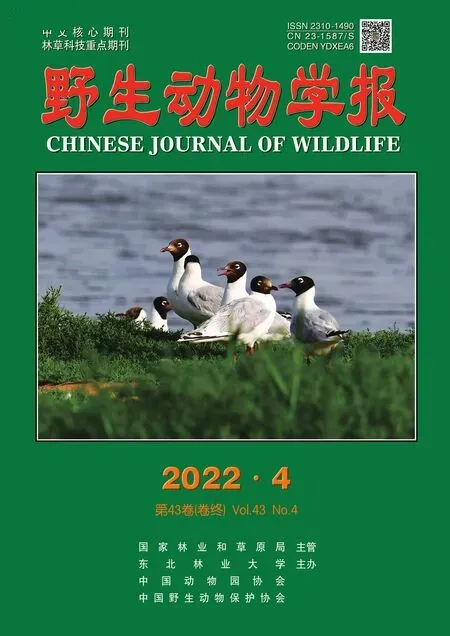人为干扰对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栖鸟兽多样性的影响
刘卓涛 张 玲 周厚熊 李 谦 王晓娟 施小刚 李兆元*
(1.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昆明,650224;2.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北京,100714;3.昆明逸境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昆明,650224;4.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汶川,623006)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45′—31°25′ N,102°52′—103°24′ E)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1],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地貌特征主要以高山深谷为主,海拔高差达5 000 m[2]。古北界与印度马来界的物种在这里实现了过渡与交融,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包括珙桐(Davidiainvolucrate)、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roxellana)和雪豹(Pantherauncia)等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3-4],是动物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地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域之一,物种多样性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多个保护区中处于较高水平[5]。
研究区域内辖卧龙和耿达2个乡镇,常住村民约6 000人,主要以藏、羌、回和汉族为主。当地村民主要从事农牧业活动,放牧的主要家畜有黄牛、牦牛、马和山羊[6];还从事建筑、运输、旅游和中草药采集等活动。农牧业生产、森林砍伐、交通、旅游、偷猎和采药等人类活动影响了卧龙保护区近1/4的面积[7]。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我国政府制定了多种保护措施和法律法规,各保护区也进行了诸多工作与努力,然而卧龙地区的人为干扰仍较为普遍,很多村民的家畜在保护区内放养[8-9]。
人为干扰对野生动物生存的影响长期存在。Verdú等[10]研究发现,适度放牧能提高生境多样性,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但有研究表明,卧龙保护区牧马等放牧活动严重影响了大熊猫的生境[8-9,11]。对于食草动物而言,人为干扰的影响已超过了自然捕食者,对人类的警惕导致食草动物的食物摄取量减少以及繁殖成功率降低[12-13];对于食肉动物而言,人为干扰会改变其生活习性和活动节律,如会选择夜间活动以避开人类活动[14-15]等,这些变化对野生动物生存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研究评估。为此,本研究利用2017年4月—2018年4月采集的红外相机数据,通过网络分析系统探讨人类活动对卧龙地栖鸟兽多样性的影响,为保护区制定相应政策以协调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采集与提取
基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边界,利用ArcGIS生成覆盖保护区的1 km×1 km的公里网格,以海拔为基准,随机选取60个相机位点,每个相机位点位于1个格子中。皮条河以东是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在奥维互动地图的导引下,研究人员进入该区人类可以通达的网格中布设红外相机(易安卫士L710),相机固定在距地面50~80 cm的树干或其他物体上,镜头与地面保持平行,电池和存储卡每3个月更换1次。红外相机仅获得温血物种图像,包括鸟类和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工作时间为2017年4月—2018年4月。相机数据回收后,对物种分类与鉴定,物种鉴定参照《中国兽类野外手册》[16]和《中国鸟类野外手册》[17]。
1.2 种对关联性衡量及其生态学关系分析
20世纪初,Forbes[18]提出种间关联性概念,通过2个物种共现于相同地理空间的频度来计算种间联结。本研究采集二分型数据,因此采用佛爱系数(rø)来衡量物种间的关联性[19],将具有显著正关联的种对连接起来构建物种关联网络。采用兰布达系数(LB)[19]衡量存在显著正关联种对的空间关联对称性,据此判断它们的生态学关系性质,从群落结构角度系统分析人类活动和家畜放牧给保护区地栖鸟兽带来的可能影响。
1.3 物种数与人为干扰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rs)[19]检验相机位点的物种数与人为干扰频次的相关性。
1.4 人为干扰对空间关联影响的分析
采用克鲁斯卡尔-沃利斯单向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KW)[19]探究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以及野生动物相互间的空间关联差异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人为干扰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整理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的有效照片和视频,共记录到6目15科33属35种地栖野生动物;还拍摄到村民、家养黄牛、家养山羊和家养牦牛的照片和视频,这些影像用作人类干扰的数据。
依据红外相机位点数据,共有18个位点拍摄到村民,分布于全海拔(1 749~4 430 m)、坡度6°~30°的中部坡位或山脊、乔木高度5~19 m、灌木盖度0~50%的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中。有8个位点拍摄到家养黄牛,分布于海拔1 749~2 418 m、坡度0~30°、中下部坡位、乔木高度5~19 m、灌木盖度0~50%、草本盖度25%~75%的落叶阔叶林中。有8个位点拍摄到家养牦牛,分布于海拔2 865~4 300 m、上坡位或山脊、坡度6°~20°的缓坡、灌木盖度0~50%、草本盖度0~50%的高山灌丛草甸中。有3个位点拍摄到家养山羊,分布于海拔1 920~2 692 m、中下坡位或沟谷、坡度0°~20°的缓坡、乔木高度10~19 m、灌木盖度0~25%、草本盖度0~50%的针阔混交林中。从出现的位点数来看,家养山羊最少,不是重要的影响源。
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物种数与人为干扰频次间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rs=-0.77,n=60,P<0.01),说明人为干扰对保护区内的物种多样性影响很大,物种数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而降低。
2.2 种间关联性
基于佛爱系数计算结果,卧龙地区存在2个地栖温血物种网络,一个是包括扭角羚(Budorcastaxicolor)在内的20种动物网络,称为低海拔物种网络(lower altitude network,LAN),分布于中、低海拔地区(3 531 m以下);另一个是包括雪豹在内的14种动物网络,称为高海拔物种网络(higher altitude network,HAN),分布于中、高海拔地区(3 531~4 430 m)。黄鼬(Mustelasibirica)处于网络外,保持独立。
在LAN中,包括村民和家养黄牛2种人为干扰。与村民活动呈显著正关联的物种为野猪(Susscrofa;rø=0.32,χ2=4.85,P<0.05)和红腹锦鸡(Chrysolophuspictus;rø=0.33,χ2=4.16,P<0.05);呈显著负关联的物种为扭角羚(rø=-0.31,χ2=4.375,P<0.05)。与家养黄牛呈显著正关联的物种为野猪(rø=0.37,χ2=6.06,P<0.05)、红腹锦鸡(rø=0.41,χ2=6.35,P<0.05)和藏酋猴(Macacathibetana;rø=0.39,χ2=6.5,P<0.05);呈显著负关联的物种为猪獾(Arctonyxcollaris;rø=-0.35,χ2=5.6,P<0.05)和川金丝猴(rø=-0.31,χ2=4.02,P<0.05)。没有与家羊呈显著正关联或显著负关联的物种。大熊猫等15种野生动物与村民活动和家畜放牧没有空间关联(图1A)。

B.高海拔物种网络 Higher altitude network图1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空间关联网络Fig.1 Spatial association network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wildlife in the Wolo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在HAN中,只有家养牦牛1种人为干扰。与家养牦牛呈显著正关联的物种为岩羊(Pseudoisnayaur;rø=0.39,χ2=6.50,P<0.05)、绿尾虹雉(Lophophoruslhuysii;rø=0.34,χ2=4.81,P<0.05)、红喉雉鹑(Tetraophasisobscurus;rø=0.41,χ2=6.35,P<0.05)、赤狐(Vulpesvulpes;rø=0.42,χ2=7.58,P<0.01)、血雉(Ithaginiscruentus;rø=0.32,χ2=4.13,P<0.05)和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himalayana;rø=0.42,χ2=7.39,P<0.01);呈显著负关联的物种为中华斑羚(Naemorhedusgriseus;rø=-0.36,χ2=5.59,P<0.05)、毛冠鹿(Elaphoduscephalophus;rø=-0.43,χ2=8.68,P<0.01)、水鹿(Rusaunicolor;rø=-0.34,χ2=4.81,P<0.05)、野猪(rø=-0.42,χ2=8.22,P<0.01)和中华鬣羚(Capricornismilneedwardsii;rø=-0.33,χ2=4.76,P<0.05)(图1B)。
兰布达系数(LB)结果显示,人为干扰类型与直接显著正关联物种间不存在非对称关系,说明本研究中的人为干扰类型并不会吸引这些物种,这些物种也不会吸引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并非针对这些物种,这些物种也未从人为干扰中获益(表1)。

2.3 人为干扰因素与物种间的空间关联分析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单向方差(KW)分析结果显示,在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物种网络中,人为干扰因素(村民、牦牛、黄牛和山羊)与野生动物物种间的空间关联系数和野生动物物种之间的空间关联系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卧龙LAN:KW=4.218,df=4,P>0.05;卧龙HAN:KW=14.375,df=6,P>0.05),说明人为干扰因素与野生动物物种间的空间关联程度已经达到了野生动物物种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
3 讨论
3.1 人为干扰对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整体影响
Verdú等[10]认为适度放牧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本研究结果显示,人为干扰与物种多样性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随人为干扰程度的增加而下降。基于早期野外普查的经验数据,Hull等[11]认为由于栖息地竞争,卧龙保护区的家马对大熊猫生境影响严重。本研究的数据中没有家马,只发现黄牛、山羊和牦牛等家畜,这可能与卧龙管理局在2012年10月开始禁止牧马的政策有关。据四川省林业厅的调查[20],保护区内人为干扰主要以放牧为主,放牧的家畜包括黄牛、羊和牦牛等,与本研究的数据吻合。野生动物对人为干扰的耐受性较低,往往采取回避措施[21-22],随着人为干扰范围不断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压缩[23]。与狩猎伐木等其他人为干扰相比,放牧家畜通常被认为属于干扰程度较低的人为活动,因此,在保护区内狩猎伐木被明令禁止,而放牧活动往往不受限制[24-25]。本研究结果提醒,放牧等人为干扰不应被保护管理部门忽视。
3.2 不同人为干扰类型对野生动物的影响3.2.1 村民
村民活动与野猪、红腹锦鸡具有显著正关联,不存在非对称关系。在对川金丝猴与水鹿、豪猪(Hystrixbrachyura)、毛冠鹿的空间关联分析中[26]也发现这样的关联属性,这种空间关联的生态学基础是种间资源竞争。野猪倾向于在有灌木丛的阔叶林或混交林中觅食,偏爱有采光冠层的森林[27-28];属杂食性动物,除了觅食中华猕猴桃(Actinidiachinensis)、五味子(Schisandrachinensis)和山葡萄(Vitisamurensis)等植物果实外,还取食菌类、昆虫和小型啮齿类动物等[29],甚至会到居民点附近或农田区觅食[28,30]。村民平常采集的中药材有天麻(Gastrodiaelata)、铁线莲(Clematisflorida)和细辛(Asarumsieboldii)等,这些药材主要生长在海拔较低的阴湿和腐殖质较厚的林下灌丛中[31-32],这些区域是野猪的栖息地和觅食区。因此,食物和生境资源利用导致野猪和村民的活动产生空间重叠,说明野猪与人类存在竞争关系,人为活动会对野猪造成直接威胁。红腹锦鸡偏好选择海拔较低、中下坡位或靠近沟谷的多灌木区域活动[33],常在森林边缘、开阔地和农耕区附近觅食[34],喜欢取食果实、种子、嫩叶和农作物[35]。人类与红腹锦鸡的直接空间正关联,表明两者存在生存空间竞争,人为活动会对红腹锦鸡造成排斥效应。
村民与扭角羚具有显著负关联,表明二者处于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扭角羚主要分布在中海拔、乔木密度较低、坡度适中、中上坡位和人为干扰少的针阔混交林中[36-37],村民不会给扭角羚带来直接威胁。
3.2.2 家养黄牛
家养黄牛与野猪、红腹锦鸡、藏酋猴具有显著对称正关联,表明它们存在资源竞争关系。野猪和红腹锦鸡主要觅食于海拔较低、中下坡位且开阔的阔叶林或混交林林下灌丛中,野猪偏爱在草本覆盖度高的森林中翻拱寻找食物[27,33]。藏酋猴主要选择海拔较低、坡度中等、灌木盖度低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中栖息活动,偏爱水源附近岩石较多的沟谷区域[38-39],食性较杂,以叶、芽、花、果和昆虫为食,也取食农作物[40]。黄牛在野外主要活动于中上坡位开阔地带[41],寒冷季节则偏向于坡底沟谷平原区域[42],与本研究调查结果一致。这种空间活动格局导致黄牛与野猪、红腹锦鸡、藏酋猴产生了空间重叠,形成了一定的空间关联,因而出现种间生存空间竞争。
黄牛与川金丝猴和猪獾具有显著负关联,说明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川金丝猴主要分布在中海拔针阔混交林中,偏爱乔木郁闭度适中、乔木密度较高、灌木和竹林适中且隐蔽性好的区域[43-44],因此,黄牛对川金丝猴没有直接威胁。在伏牛山,猪獾选择分布于灌木密度高、乔木郁闭度高、坡度较陡区域中的洞穴卧息、产仔和躲避敌害[45],避免洞穴被黄牛踩踏,这表明猪獾有回避黄牛的习性。在卧龙,黄牛和猪獾处于不同海拔范围和不同的物种网络中,猪獾是HAN成员,而黄牛入侵LAN;然而,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没有放牧,猪獾分布于低海拔,属于LAN成员[46]。据此推测,猪獾与黄牛的空间负关联可能是猪獾对黄牛回避造成的。
3.2.3 家养牦牛
家养牦牛进入卧龙HAN,与赤狐、绿尾虹雉、血雉、红喉雉鹑、喜马拉雅旱獭和岩羊具有显著对称正关联。在卧龙,赤狐分布的海拔较高[47],栖息于岩缝或其他动物的洞穴中,适应性强,活动范围广,从草原灌丛到针阔混交林都有分布[48],属杂食性动物,主要以植物浆果、啮齿目(Rodentia)和兔形目(Lagomorpha)兽类为食[49]。绿尾虹雉主要活动区域包括针阔混交林、针叶林、灌丛草甸和山脊裸岩,在灌丛中觅食,以叶、茎、种子和嫩根为食,尤其喜食贝母,也捕食昆虫及虫卵[50-51]。血雉分布于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和高山灌丛带,偏爱食物丰富、光照充足的灌木丛,以叶、花、果和嫩芽为食,还取食苔藓和昆虫[52-53]。红喉雉鹑栖息于林线以上的高山草甸、裸岩流石滩和灌丛中[17]。喜马拉雅旱獭作为啮齿类物种,营穴居生活,主要在高寒草甸与高寒灌丛中活动,选择坡度相对平缓、植被种类丰富、草本盖度高和草高适中的区域筑巢觅食[54]。岩羊选择在乔木密度低、靠近水源的开阔区域觅食和活动,并有保持接近裸岩或悬崖的特征,偏爱坡度较陡的阴坡和上坡位休息[55-56]。这些区域均是家养牦牛的觅食和栖息场所[42,57],因此,家养牦牛与这些物种的相似生境或共享食物资源产生了空间关联,共同的需求导致种间竞争,使家养牦牛对这些物种产生了不利影响。
家养牦牛与中华鬣羚、中华斑羚、水鹿、毛冠鹿、野猪具有显著对称负关联。这些物种属于卧龙LAN成员,而牦牛入侵的是卧龙HAN,不会对这些物种产生威胁。
据王晓等[8]和周世强等[2]的研究,家畜放牧侵占了大熊猫的栖息地,影响了对大熊猫的保护。本研究结果显示,村民活动(rø=0.02,χ2=0.01,P>0.05)、家养黄牛(rø=-0.16,χ2=0.71,P>0.05)、家养山羊(rø=-0.16,χ2=0.33,P>0.05)和家养牦牛(rø=-0.16,χ2=0.71,P>0.05)等人为干扰类型与大熊猫均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表明上述人为干扰对大熊猫不存在直接影响。
3.3 保护建议
网络分析显示,村民和家畜与野猪、红腹锦鸡、藏酋猴、赤狐、绿尾虹雉、血雉、红喉雉鹑、喜马拉雅旱獭、岩羊形成了显著的空间正关联,人类活动持续发生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克鲁斯卡尔-沃利斯单向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人类活动变量与野生动物的空间关联、野生动物种间的空间关联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人类活动已经深度介入自然群落。分析未发现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物种间存在非对称空间关联,没有偏利生态学关系存在,卧龙山地自然群落中尚未演化出适应人类的生态学关系,人类活动的影响表现在与上述物种的竞争上。野生动物多样性会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高而下降,随着放牧家畜数量增长[8],野生物种的生存空间会受到挤压,不利于物种多样性保护,建议保护区管理部门严格限制村民进山和放牧家畜等活动。
致谢: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鹏彦、胡强、王茂麟、林红强,以及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古晓东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姜楠、苏腾伟和杨虎参与了数据采集、处理和讨论,刘萍在外业数据采集中提供后勤保障支持。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