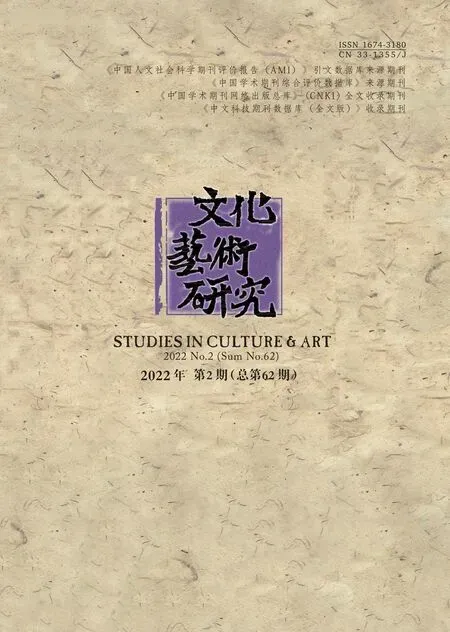从扮演到生成
——虚拟世界的身份与亲密关系
陈嘉莹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数字网络已然全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其中发生的情感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样的研究转向不仅有着现象学的渊源,也受到了新唯物论的影响。前者提醒我们,个人情感以及与他人的联结构成了“我”之所以为“我”的要素。在互联网普及之后,我们的切身体验必然也从数字世界中获得。因此,线上情感的发生、发展与未来转向都影响着个体身份与世界的建构。新唯物论则提出,对象并不是中立之物,它们的物质存在塑造着我们的意义与价值。受此启发的媒介理论家,如萨拉·肯伯(Sarah Kember)和乔安娜·兹林斯卡(Joanna Zylinska)就提出,我们不应将新媒体(media)理解成零散的物件(如电脑、手机或电子书等),而应把它们理解为一系列的媒介(mediation)过程。它们揭示了我们在技术世界中存在并与之共生的方式、我们的涌现,以及我们内行动(intra-acting)的方式。
因此,考察不同的媒介过程将帮助我们认识在技术世界中生成的不同身份与情感图景。早在20世纪互联网出现以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就曾借唯物主义视角对个体身份与亲密关系作出诊断。他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指出,19—20世纪欧洲城市的公共空间趋向同质化,将导致日常社会交往的窒息、亲密关系的专制统治,以及他异性的丧失。最终,公共生活将面临消逝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论断置于当下,并用新唯物主义的视角加以检验,便会发现网络为社会交往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物质环境”。当下的公共空间并不如桑内特所说的仅仅朝向同质化发展。虚拟世界实际上创造了诸多身份建构与情感维系的方式,它虽然进一步瓦解了公私领域的划分,但公共身份的扮演模式并未消失,而是渗透至日常生活之中。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介与多人在线游戏都重新定义了交往关系中的“自我”与“他者”,不同的是,前者构建的是真实世界的身份(real-world identity),后者则是虚拟身份(virtual identity)。本文将试图比较这二者的区别,并阐明由角色与化身实现的虚拟身份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身份范式与亲密关系模型。最后,外族(Otherkin)亚文化群体将作为一个特殊案例,说明虚拟身份对原有本体论范畴的挑战。
一、消解公私领域:扮演
桑内特在其书中曾列举了西方理解公共生活的三种方式:(1)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互动”理论;(2)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市民”理论;(3)他本人提出的戏剧学模式,这个模式指出,公共空间中的自我是戏剧性互动的结果,其社会关系由自我在不同场合对同样一批观众扮演同样的角色维系,并且这种扮演不总是限于一个角色。这三种方式都以公私领域的明确划分为前提。例如桑内特就认为,私领域是自我表露、亲密交往与分享感受的场域,公共领域则不然。在他看来,工业资本主义与世俗化对公共领域的摧残,将影响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城市和政治。在城市中,我们沉迷于寻求亲密关系,以致忽视了城市的本质,即它是一个为真正的、非个人的公共人提供交流机会的剧场,是“陌生人相遇的地方”。同时,由于我们逐渐通过信任或私领域的美德来解决权力和资源分配的问题,政治也由此被非政治化了。桑内特的诊断在如今看来虽仍然有效,但情况显然更为复杂。通过观察人们在社交媒介中展示自我和与他人交往的方式,我们发现媒介的确持续消解着公私领域。然而,这并不必然带来消极的结果。一方面,网络不仅为个体接触他人提供了更广阔的渠道,还为民众构建自我公共形象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自我和形象的维系也涉及私人关系网,这要求个体在私领域也不能松懈扮演,因此更要在行为上表里如一。随之而来的私领域政治化,为家庭伦理或是性伦理等话题的讨论提供了条件。
在网络普及以前,个体曾经可以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中有选择地维系一种身份,比如一个人可以在家中是一位父亲或丈夫,在校园里是一位大学教授,在其他社交场合则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这些角色通常相对稳定且互不干涉。但经过网络渗透之后,这些空间的区隔变得不再明晰,稳定的个人身份也随之动摇。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当大量活动被移至线上开展时,我们身处的空间属性也顿时变得模糊起来,生活起居室可能瞬间变为教室或是发表公共言论的政治舞台。由此引发的“身份紊乱”给扮演带来了挑战,以致个体很难把握交流的分寸。热衷于使用社交媒介的人们,难以意识到日常的信息分享实际上是一种私领域的发布。我们已经见证过无数次这样的事件: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因为一次东窗事发,便被网友起底搜索、收集并曝光其个人资料,顿时沦为公共领域的谈资。
但空间属性与身份的流动也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即个体意识到灵活调节身份的必要性,开始主动建构网络自我(cyberself)的形象。艾莉森·赫恩(Alison Hearn)将这样的行为解释为社交媒体用户对自我“元叙事和元图像”的构建——个体有意识、有目的地打造自身的特定形象,以此影响公众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形象的生产要求一种主动的自我异化,这模糊了私人化自我与工具性对象的区别,同时抹消了自我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客体之间的边界。也就是说,个体能够逐渐意识到社会性自我是何以被建构的。我们不再仅仅是处于他者目光下的凝视对象,而能够在这样的目光下自省,甚至利用这一机制构建自我叙事。艺术家阿马利娅·乌尔曼(Amalia Ulman)的行为作品《卓越与完美》()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她通过分析Instagram网红的“成长史”,自主策划出三个虚构的生活阶段,通过四个多月的图片展演,为自己赢得了近十万的粉丝。观察乌尔曼通过社交媒体自我排演的方式与仿造“网红”的过程,我们发现,网络自我形象的奥秘正隐藏在公私领域瓦解的缝隙之中。正因为那些被传送到社交平台上的私领域信息随时可能成为公共交往的一部分,同时,自我的元叙事与元图像也需要私领域的补足,自我因此也是公共的自我。
另一方面,网络自我的塑造并不是单方面的,它也需要一群“想象的受众”。如同产品在推出市场前需要确立消费者群体一样,通过想象这些受众的偏好,社交媒体用户可以调整自我呈现的形象。举例而言,这让微信朋友圈成了一个微缩的个人形象“修罗场”,因为这里混杂着不同受众,如家人、亲友、同事等。我们都经历过发送朋友圈的困境,即有时希望一个内容被某一群人看到,而不被另一群人看到。微信的研发团队显然意识到了混杂受众对社交媒体用户带来的不便,因此提供了屏蔽功能,让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发送朋友圈内容。但这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想象的受众实际上是被高度操控着的,他们被拣选并被预判为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从而被动接受有关某个自我的形象广告(尽管这个过程有时看起来是主动的)。正如萨特理论中同时是自为与为他的自我,在网络自我的塑造过程中,作为演员的自我与作为观众的他人始终处于相互转换的动态之中。并且,这种转换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公共领域,而是同时在私领域起作用,从而让私领域的伦理得到关注。
如上所述,网络自我不仅存在着多重身份,并且拥有建构身份的自主性,个体得以通过操纵虚拟的、泛化的他人实现身份建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他人也可能从这种操纵模式中挣脱出来,并主动检验个体形象的真假。例如,我们可以在诸多网络事件中看到社交媒体平台的对话记录。这些记录正是被动接受形象的观众转换成主动刻画形象的参与者的结果。这样看来,公共生活的“戏剧学模式”仍在赛博空间中延续,但原本相对静止的“世界剧场”(theatrum mundi)演变成了多重的平行剧场,身份扮演不再仅仅是对一个现成角色的演绎,还是对虚拟身份的操演。因此,公共生活的戏剧学模式不仅仅意味着个体如演员一般扮演着其社会角色,它与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结合,更强调述行/操演与演员表演之间的不同。这意味着,个体在公共生活中并非只是“扮演”一个现成的角色,而是可以通过言语的施为操演新的身份。这种情况在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虚拟 /潜在
如果说社交媒体为个人的多重角色扮演提供了更丰富的条件,那么多人线上游戏则是让扮演-游戏(play)的本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虽然对于许多用户来说,线上自我仍是线下自我的延伸,但更多学者注意到虚拟世界带来的差异。例如在游戏世界中,玩家能够自由地通过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化身构建虚拟的生活世界。与热衷于构建自身元叙事的社交网站用户不同,游戏用户的兴趣在于适应或创造完全虚拟的身份,这也为新型的亲密关系创造了可能。媒介研究者沙卡·麦格罗顿(Shaka McGlotten)在其讨论虚拟亲密关系的著作中,就将游戏《魔兽世界》中呈现的亲密关系图景描述为“多元宇宙”。他指出,虽然《魔兽世界》中主导的两种关系类型“团队游戏”和“单人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都是玩家为了达到某个游戏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但因为这个游戏世界由多重虚拟世界构成,成千上万的游戏玩家又将个体的多样性(multiplicities)带入其中,这让《魔兽世界》成为新型亲密关系的发生场域,也使这些关系得以转变为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
在他看来,《魔兽世界》中主导的工具性关系主要由这类游戏的限制性因素造成,包括限制性的身份、空间、时间与归属。首先,《魔兽世界》的玩家需要在进入游戏之前创建自身的角色。这些角色的设定由不同的人通过电脑、卡牌游戏、漫画、小说以及电影等不同媒介共同想象和构建。如同线下世界一样,《魔兽世界》的身份由这个世界的“历史”给定,玩家通过选择一个身份继承其叙事、阶级、性别、种族和特定的亲密关系星丛。另外,在游戏过程中,玩家有时会遇到无法前进的情况,其化身如同被一堵隐形的“空气墙”阻挡而止步不前。这揭示了《魔兽世界》的限制性空间,以及虚拟世界作为封闭系统(closed system)的存在。而比空间更具限制性的则是时间。因为玩家与所有人一样,一天都只拥有24 个小时。时间以空间所没有的方式抵制着虚拟化,因此它成了游戏的一个核心限制。身份、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性最终限制了《魔兽世界》中的关系类型。这带来的结果是,《魔兽世界》中主导的亲密关系仍再现了线下世界的亲密关系脚本,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联系仍受到规范性愿望和理性的约束。
当然,其中也存在例外。例如,许多玩家采用与自身不同的性别角色参与游戏,并在游戏过程中维持着这样的性别扮演。又如游戏中公会创造的共同生存体验。麦格罗顿就提到他曾参与过的“卡林姆多的亚马逊女战士”(The Amazons of Kalimdor)公会,此公会虽然不限制游戏玩家的身份,但是只允许玩家以女性化身的方式参与,这催生了一种以性别角色为纽带的游戏情谊。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魔兽世界》中看到因游戏相遇发展出的网络恋情故事,通过游戏文本交流情感,或是在游戏的虚拟环境中约会旅行等诸多案例。这些现象都是玩家实践虚构身份可能性的结果。但通常人们对于这些虚拟角色或亲密关系不以为然,并认为这些情况不可能带来任何规范性的承诺。虽然它们可能衍生出关系的新形式,但它们并不真正重要,“它们是梦幻的或模拟的、想象的、无形体的、不真实的”。然而,麦格罗顿认为,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潜在/虚拟”(the virtual)概念将为我们理解这些现象打开全新的视角,并阐明虚拟与真实并不对立,虚拟的身份与情感关系是实现(actualization)的过程之一。
在德勒兹的生成本体论中,“虚拟”是一个需要结合“现实”(the actual)理解的概念。二者虽互相排斥,但又共同充分表征着真实(the real)。在他看来,生成性的真实不是一个现实向另一个现实发展的线性过程,而是从一个事态(state of affairs)的实现开始,经由虚拟/真实趋向的动态场域,运动至这一场域在一个新事态中的实现。虚拟在这里有着引发实现的潜能,但它始终与这种实现保持着差异。因此“虚拟并不是缺乏真实的东西,而是它被平面赋予特定真实之后参与实现过程的东西”。虚拟是一种理念而非抽象(因而是具体的)、真实又非现实(因此尚待实现)的本质。换言之,虚拟是一种尚待实现的潜能,它早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就潜藏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社会学家罗伯·希尔兹(Rob Shields)在其专著《虚拟》()中跟随这个线索指出,虚拟正是未实现的真实。借此他考察了传统仪式中的“虚拟”空间,如基督教的圣餐仪式(Eucharist)或不同文化中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这些仪式通过虚拟将其发生的场所转变为一个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即人在生命历程转换过程中经历的独特时空。作为两个界域之间的中介地带,它流串交会着不同空间的特质,个体在其中体验着身份过渡的复杂经历。
从这个角度而言,游戏的虚拟世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阈限空间,虚拟身份以具体且真实的方式运作于其中,并引发新型亲密关系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验并操演着不同身份,试图借此跨越社会和具身存在的分类界限。虚拟与真实、线上与线下的对立不再可行,也失去了意义。如果我们接受德勒兹的肯定态度,那么网络应该被视为一个生成性空间,为每个个体提供改变生存状态的契机,实现新的身体规范、具身体验与物种身份。
三、虚拟身份与外族世界:生成
综上,我们已经说明虚拟社区的互动让传统社会角色与关系不再稳定。游戏世界的用户更乐于为自己创造另类的、有着不同性别和能力的角色,并通过这些角色与其他用户形成亲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角色与亲密关系的扮演-游戏不仅止于游戏世界,而是渗透在整个生活世界。伊娃·泽卡尼(Eva Zekany)就以外族亚文化为例,为我们详述了人们何以通过虚拟社区生成物理世界中的新身份与新型亲密关系。外族,指的是认为自己的灵魂、精神或心理部分或完全非人类的群体,也包括那些认为自己的肉身并非其真实样貌的人。动漫文化中有着类似外族的概念,即“人外”(日文:じんがい)。在古日语中,“人外”原指动物、妖怪等非人的存在。随着文学和动漫文化的发展,“人外”也指亚人或是机器人。很多外族认为自己是电子游戏、动漫、小说或影视剧中的人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着特定的生活风格(如 cosplay 文化),并主要通过网络进行社交。泽卡尼试图通过媒介本体论的视角,分析外族通过媒介技术构建其身份和社区的方式,借由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进化论,阐明人类与技术的共生演化,并指出“人的本体论核心其实是非人类的”。
通过对德勒兹“虚拟/潜在”概念的再阐释,我们重审了虚拟与真实的关系,并不再将线上的种种角色扮演与亲密关系从真实生活中剥离。基于此,外族作为一种虚拟身份也可以被视为虚拟的实现,或者说是具身化的结果。它不仅代表着一种潜在身份,也呈现了不同媒介的范式和亲密关系模型(特别是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泽卡尼将虚拟身份与亲密关系的生成和情动理论关联在一起,因为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在其情动理论的奠基性文本中曾指出,情动就是虚拟,“情动是虚拟的通感视角,锚定在现实存在的、具身体现它们的特定事物之中。情动的自治就是情动在虚拟中的参与。它的自治就是它的敞开”。作为前主体、前个人、非意识体验的力,情动总是同时参与着虚拟中的现实与现实中的虚拟,正如德勒兹描述的生成运动,一方从另一方中出现,又回到另一方中。换言之,情动时刻暗涌在虚拟/潜在的联系和媒介化的亲密关系之中。情动不仅发生于(in)亲密关系中,也通过(through)亲密关系发生。基于此,泽卡尼分析了外族身份在不同情动层面上的操演:其一,通过技术媒介本身的流动和强度;其二,通过基于亲缘关系(affinity-based)构建的虚拟社区;其三,通过用户与机器之间的亲密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与技术的持续相互构建成为后人类。
这种理解之所以是可能的,离不开斯蒂格勒对技术进化论的论证。在《技术与时间》中,他提出人本质上是历史性的。技术在人的进化过程中是一个特异的动物性现实,且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技术并非由人发明,而是相反,人在发明技术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因此,“技术史同时也是人类史”。他提出“后种系生成”(epiphylogenesis)的概念以否定一种瞬间形成继而固化的人论。在他看来,物种的一切特性并不是在胚胎中就已经先验地确定,而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中逐渐生成。生命进化实际上是沿着生命以外的方式继续。在这里,技术被理解为一种使“人”这一范畴出现的构成性动力,它与人有着共同原始性(co-originary)。鉴于此,泽卡尼提出,当我们在考察外族亚文化时,不应将外族赖以维系的媒介仅仅视为单纯的平台,或是像外族的反对者们那样,认为外族的身份认同只是个体为了满足自身成为“异类”的愿望。我们应该将外族身份看作后种系生成的一部分。它们在媒介内部或是与媒介共同涌现的具身形式与亲密关系,都将为我们提供不同的本体样貌。
另外,因为一些外族社群的成员将“外族”解读为“与他者为亲”(kin to the Other),杰伊·约翰斯顿(Jay Johnston)也论述了外族亚文化与他者之间特殊的亲缘关系。他指出“他者性”曾一度被概念化为极端的差异,是主体需要面对并与之争斗的威胁性存在,但近来许多学者意识到他者也能带来生产性,并且破坏主体固化的本体论基础。正如桑内特所说,我们需要与他者相遇。外族身份正是人类面对作为他者的动物时,得到的生产性成果。它消解了人与动物的两个本体论范畴,也为我们提供了跨物种身份的可能性。并且,正如上文所述,网络的虚拟世界为这种身份过渡提供了空间,外族的虚拟/潜在身份在其中被具体且真实地操演。再者,斯蒂格勒对“人类”和“技术”两个本体论范畴的消解也在外族身份中充分显现。这正呼应了真实与虚拟、有机物与无机物、智人与动物之区隔逐渐消解的后人类处境。在这里,外族并非一个不正常的“例外”,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成范式,强调了虚拟技术与人类之间持续相互生成的动态关系。
结 语
就此,我们勾勒了一个网络技术改变个体身份与亲密关系的线索。社交媒体的出现,彻底消解了传统的公私领域划分,并强化了个体在网络中的扮演本质。这种扮演不仅是一种主动性的操演,也有着随时转换角色的可能。多人角色扮演游戏则让虚拟世界变成了身份转化的阈限空间,使虚拟的身份与亲密关系得以实现。肯定这些虚拟身份与关系,不仅能够让我们重审人的本体论地位,也为自我与他者的亲缘性提供了可能的范式。正如约翰斯顿所提醒的,外族文化与其说是病态的,毋宁说是政治的,因为外族提供了一种肯定物种差异并重构本体论的手段。或许外族可以成为赛博格(cyborg)那样的政治神话,为我们的身份操演提供契机,以创造新的伦理和政治可能性。与其简单地否定这些虚拟世界产生的亚文化,不如慎重考虑这些文化,以重新校准主体性概念,并习得与他异性相处的方式。虚拟身份及其衍生出的亲密关系类型,通过具体真实地参与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激进且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实验。借此,我们得以重新想象后人类主义的主体形象,以及相关的规范性亲缘关系。
但不应忽略的是,虚拟身份在否定人类主体所依赖的身份边界时,也让自身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就外族身份而言,一方面,外族的差异性建立在它试图抹消的本体论差异之上,如果动物与人的区分不存在,那么外族的他异性也就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外族身份始终处于陌异的状态,其身份的合法性也将持续受到质疑。更重要的是,就像情动理论给人带来的担忧一样,肯定性的生成力量也将遇到问题:它是否是一劳永逸的?还是说,毫无章法的生成反而让我们最终陷入虚无主义?虚拟现实的身份与亲密关系是否无可指摘?甚至,我们有评判这些身份与关系的依据吗?当人类中心论被否定以后,原有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崩坏,我们又应如何重建伦理的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