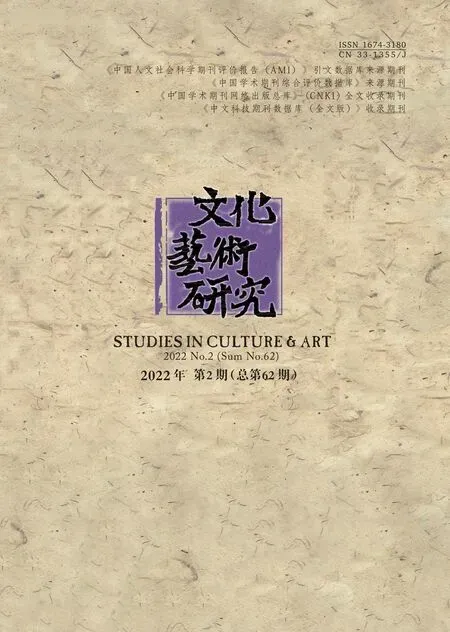数字亲密:爱还是痛?*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批判性反思
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062)
一、数字亲密的三重面向和三种研究进路
数字亲密(digital intimacy),是一个晚近以来愈发火热的学术话题。它指的是“晚期现代性”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趋势,即社交媒体在建构人际关系的过程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深广的作用。初看起来,这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并没有多少值得深挖的哲学内涵抑或政治意味。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实际上,在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去洞察和揭示令人困惑、焦虑乃至忧惧的难题和谜题,往往正是哲思的深意所在。数字亲密亦正是如此,它不仅标志着微观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勾连,而且由此深刻展现出人类生存在数字时代所发生的种种引人关注的鲜明变化。
首先,亲密关系远非晚近产生的现象,它几乎是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主题。也正因此,要清楚界定它的内涵并非易事,因为它既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同时又不断地在发展和变化。但在复杂多变的表象之下,亲密关系总还是展现出一些基本的、稳定的特征,比如它总是局限于小范围内(尤其是家庭和友谊)的密切人际关系,展现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清晰边界。又比如,它往往与更为高阶的认知能力没有太多关系,却总是牵涉到情感、感受、体验等更有具身性乃至肉身性的基础维度。虽然亲密关系看似总是私人的、感性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无力成为个人生存之中的关键和核心维度。正相反,它总是在看似幽微平淡之处将生存的基本面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进而凝聚成生活的节奏,谱写出人生的篇章。不妨借用劳伦·贝伦特(Lauren Berlant)的精辟概括:“亲密关系构筑着世界;它创造出种种空间,并由此僭越了别种关系所设定的位置。”
此种交织尤其体现于哲学、伦理和政治的三重面向。首先,亲密关系根本上是一种“切己”的关系,它虽然展现为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的种种交际与行为,但最终指向的恰恰是每个人与其自身的最内在、最私密,也最不可言喻的关系。亲密关系处理得当,会赋予个体生存关键的积极能量;但反过来说,一旦迷失在亲情、友情、爱情的网络之中,那么最终就很可能导致自我的迷失、人生的困境。因此,亲密关系所关涉的第一个问题,正是“我是谁”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对于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来说,这或许理应是一个有待思辨和论证的难题。但对于沉浮于人间世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来说,它首先是、始终是在亲密关系的纽带和网络之中实现的切身体悟。只有在与身边最亲密的家人、友人、爱人的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之中,我们才真正开始体验到自我,发现了自我,进而追问自我,塑造自我,甚至反省、质疑自我。
由此就涉及亲密关系的第二个面向,那正是伦理,也即“我和你”“我和他”之间的关联。亲密关系,正是在人与人的切近关系之中发现和建构的,但是,他人在亲密关系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多样而复杂的。他可以是镜像,反映出主体自身的欲望与意志;他也可以是力量,对主体的自我塑造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或负面的阻碍,乃至破坏作用;他更可以是命令,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主体的行为施加调节,予以引导乃至规范(normalization)。也正因此,亲密关系并非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人的地位也并非只能是从属、辅助和边缘。或许正相反,亲密关系始终意味着多元力量的交织,多重中心的互映。其中的每一个自我都在进行着持续的反思、协商、建构,却似乎没有哪个自我最终足以占据中心和主导的优势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亲密关系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主体间”的关系。
但伦理关系亦并非亲密关系的全部。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要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场域之中实现和展开,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它要与经济、政治、技术等其他社会子系统发生密切的互动,另一方面,它也必然会受到普遍性的社会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乃至控制。正是在这里,触及了政治这第三个面向。亲密关系总是私密的、微观的、不稳定,甚至不确定的,而这往往使它在与宏观的社会秩序进行周旋乃至对峙的过程之中处于弱势和下风。确实,历史上不乏从亲密关系领域首先酝酿和发动的极端而激烈的变革,比如吉登斯在名作《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所重点提及的“浪漫之爱”和“性解放”。但实情是,社会制度反过来利用和操控亲密关系才更是普遍的趋势、常见的现象。由此我们意识到,个体与群体、微观与宏观、私人与公共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早已不足以成为反思亲密关系的真正前提。换言之,亲密关系早已不是温暖的港湾和安全的堡垒,在各种力量和权力的渗透之下,它已然危若累卵,四面楚歌。如何在权力的操控之下捍卫亲密关系的“纯粹”和自足,如何在社会性的亲密“制度(institute)”之下不断摆脱沦为“顺从主体(compliant subject)”的命运,这些不仅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迫切的政治议题,更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困境和焦虑。
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这些焦虑看似有所缓解,却并未真正化解,反倒以种种更为尖锐和敏感的方式刺痛着每个人的肉身与灵魂。是的,今天的手机和互联网让我们越来越轻而易举地找到朋友,建立和发展关系。亲密关系的领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善用社交媒介来安排、拓展,乃至经营品类繁多而又花样翻新的亲密关系,堪称数字化生活的一大鲜明特征。但这些明显的变化乃至变革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促进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我们的朋友圈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但为何每个人还是那么的孤独?我们每天花上大把的时间来更新状态、点赞和回复,但为何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还是如此的空虚?我们被社交软件和互动媒介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想要找人倾诉之时,总会陷入举目无亲、四顾无友的窘境甚至绝境之中?以数字化为媒介和纽带的亲密关系,真的让我们找到自我,直面他人了吗?身陷、深陷于数字网络中的我们,到底是消极被动地顺从主体,还是足以有能力和资格将自己称作积极主动的“人生的主人”?这些追问绝非杞人忧天,因为晚近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字亲密研究者开始从实证转向批判,质疑数字媒介是否真的能够建立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本真的(genuine)纽带”,担心它最终所起到的作用几乎只能是负面和消极的,也即一步步蚕食着稳固的关系,破坏着安全的庇护,甚至最终将整个社会推向“去人化(dehumanise)”的境地。
由此,清晰地展现出数字亲密研究的两个鲜明趋向,一正一反,一褒一贬。对此,彼得森(Michael Nebeling Petersen)等学者在重要文集《媒介化亲密》()中给出了极为准确的概括。从正面来看,数字亲密带来的无疑是进步。肯定数字技术产生的积极的推进和变革作用,理应是分析的起点。如果一上来就对技术持一种偏激的、悲观和批判的立场的话,势必会让理论的话语游离于技术的发展之外,难以深入其细节,进而也难以真正揭示问题,摆脱困境。而说到数字亲密的积极作用,吉登斯在三十年前给出的判断至今仍颇为适用:“亲密关系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提到民主,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自然是“平等”“自由”“开放”这样的字眼。确实,数字化的技术和媒介极好地在亲密关系之中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沟通、自由选择、开放网络等今胜于昔的变革。但说到底,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与每个个体的生存本身息息相关,因为其核心原则正是“自治性”,它“意味着个人自我反思和自我确定的能力”。民主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但前提是每个人自身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能够认识到自我之所是、自身之所欲。民主保障每个人自由公正地行使他的权利,但前提是有切实的程序和手段。从这两个重要的方面来看,数字化技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亲密,堪称名副其实的“自治性”关系。
但也正是在这里,暴露出数字亲密的负面效应,不妨用“控制”来概括。很明显,数字技术在给个体提供自治性的手段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乃至剥夺了其“自我反思”的能力和“自我确定”的权利。很多持此种激进批判立场的学者都指出,数字亲密看似以每个个体为前提和中心,但实际上,它更意在将个体作为施加规范化作用的对象,进而通过种种奖惩的手段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控。简言之,技术绝非中性而透明的手段,绝非只是为人所用的工具,正相反,它在运作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在对人进行着深刻的影响乃至改造。在数字亲密的关系之中,你“觉得”自己是主人和主宰,但实际上,你只是在规则限定的范围之内来行使自由,你只能在规范允许的条件之下来进行自我的塑造。在数字的交际网络之中,没有人真的是他自己,也没有人真的能成为他自己,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成为那个理想中的社交达人,以期获得更多的点赞、更大的流量。如此看来,数字亲密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主体的自治,它所实现的最终只能是技术的控制。
进步还是控制?自治还是傀儡?数字亲密的研究似乎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之中,举步维艰。由此,另一派理论家提供了第三种选择,因为其鲜明的德勒兹主义的背景,不妨将其概括为“生成”。生成,更强调一种在时间性的流变过程中所展开的差异要素的张力和交织。“这样,亲密就变成了一种理解人的主体性与技术之间关联的方式;亲密发生于身体和技术的交织之处,在其中主体进行生成和塑形(becomes and takes form)。”但此种生成的立场又何以超越进步和控制的两难呢?我们已经发现,这个两难的症结在于对主体性的截然相对的理解。从进步的立场看,数字亲密无疑巩固了主体性的基础和前提,为主体性的实现和维系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但若从控制的立场来看,则正相反,数字亲密从根本上否定了主体性的可能,因为所谓的主体无非是技术塑造的产物,只是规范调控的对象,根本谈不上是主体,充其量只能说是阿甘本所谓的“被生产”出来的傀儡式主体。而生成的理论则显然在这针锋相对的两极之间实现了一种斡旋,达到了一种平衡。一方面,它肯定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主体性是结果而非起点。在这一点上,它与控制这一派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并不认为技术对人所施加的仅仅是单向度的规范和调控,而是将人与技术、身体与媒介皆纳入一个开放流变的生成网络之中。在生成的运动之中,没有哪一方最终能够成为主导和中心,它们都仅仅是不断变换位置、转换功能的“动元(actant)”而已。主体性并非幻象,但也绝非指向一个内在的核心、封闭的堡垒;正相反,它的边界是流动的,它的形态是变动的,一句话,它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所着力阐释的那个“游牧的主体(nomad subject)”。
生成虽然颇为巧妙而机智地化解了进步与控制之间的张力,但是似乎导向了另外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说到底,生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任何一种对亲密关系的界定,这就既令其面目全非,又让它的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如果亲密关系不再局限于人和人之间的“狭隘”范围,而是拓展到人与技术,甚至人与非人(non-human)的庞杂的网络,那么它在何种意义上还是一种亲密关系呢?没错,它确实是一种“密(close)”的关系,但“亲”之体验和情感又从何谈起呢?更为致命的是,虽然生成性理论极力倡导人与技术之间共生与共变(co-becoming),但说到底,人在这场生成性运动之中注定只是一个参与者甚至旁观者,因为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和维系机制最终不还是技术?人,只是被动地陷入了与技术的亲密关系之中,而当人越来越亲近技术之时,也就越来越疏远了自己。当人越来越疏远自己之时,又何以亲近他人呢?当你对着屏幕呼朋唤友之时,心间涌起的还是真情实感、真心实意的亲密体验吗?毕竟,你所面对的只能是,始终是文本、图像与声音,那么你那些所谓的情感和体验又在何种意义上不是模拟的效应、人工的产物?生成性亲密,难道不是一个更大的幻象、更深的危机?
二、重读吉登斯:数字亲密到底是进步还是控制?
既然进步、控制和生成这三重进路的争锋之焦点就在于主体性,那不妨再度回归《亲密关系的变革》这部奠基性的经典,来进一步探索其中未竟的深意。
主体性向来是吉登斯的理论要点,将反思性的自我认同作为晚期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也是他不断重申的主旨。既然如此,如何将自我这微观一极与社会那宏观一极真正切实地关联在一起,就成为他必须澄清的要点。而本来就贯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亲密关系,也就很自然地为吉登斯提供了这样一个必要的关联环节。因此,他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的开篇就明确指出,“在地方性和全球性互动之间的一极代表着我所谓的‘亲密关系的转型’”。当然,在这本书中,吉登斯已经展现了自我认同的诸多基本面向,比如身体、语言、时间性、叙事等;但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之中,他对自我认同的论述却展现出更为深刻的哲学意味。这首先体现于第二章中对福柯《性经验史》集中的批判性反思。在他看来,《性经验史》中的疏漏主要有三。第一点就直接触及福柯的理论要害,正是主体性这个棘手的问题:“在福柯的理论中,活跃的力量只是权力、话语和身体。权力在福柯的著作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活动,而作为人类主体所积极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却罕见存在。”简言之,福柯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了权力对主体的压抑和生产的各种单向度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人难道仅仅是任由权力摆布的棋子和傀儡吗?人何以在各种权力机制之中展现出自身的主动力量和主体性的地位?
但细究《性经验史》的文本,我们便会发现吉登斯的这个批判实在有失偏颇。比如,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第四章之中,福柯在全面批判压抑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的权力分析进路,虽然洞见卓然,但主体性的问题仍然是有待回应的根本难题。变换的只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主体被操控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变化。因此,在第二卷的开篇,福柯直面主体性这个主题,并明确指出,他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阐释“个体如何把自己塑造成道德主体的历史,即如何确立与发展各种与自我的关系,反思自我,通过自我认识、考察、分析自我从而改变自我的历史”。后文大量关于快感、养生、性爱的论述可以说都是对此种“自我的关系”的生动描绘,而且确实都颇具亲密关系的特征,尤其是第三卷,转向了“自我的关切”这个核心主题。
虽然吉登斯对《性经验史》中的主体性理论的批驳有些断章取义,但他随后的两点批判却显然更为有力,即便算不上对福柯的修正,但至少足以作为两个重要的补充。一是,《性经验史》的文本中虽然充满了对性与爱的各种描述和论述,但确实没有关注“浪漫之爱”这个位于亲密关系的近现代转型处的关键要点。二是,福柯还是太过倚重对话语和文本的阐释,而忽略了各种技术因素对亲密关系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所谓的“自我技术”其实并非真正的技术,而仅仅是用来比拟、描摹各种精妙复杂的自我关系而已。相比之下,吉登斯的研究就更为实证,他对各种避孕技术、心理治疗技术的关注皆为明证。那就让我们聚焦于浪漫之爱和亲密技术这两个福柯明显忽视的要点展开主体性的论述。
要想真正理解浪漫之爱的真谛,势必要在爱的历史之中对其进行清晰定位。吉登斯将这个转变过程凝练概括为从“贞洁”到“激情”再到“浪漫”这三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贞洁和激情是相关又相对的两极,因而“在婚姻的‘贞洁’性关系与婚外关系的放纵激情之间作出的清楚区分”理应是审视爱的近现代转变的起点。婚姻的契约对两性关系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和制约,由此与僭越而迷狂的激情之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浪漫之爱又不能简单等同或还原为激情之爱。这不单是基于历史发展的事实,更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本质上的差异。激情之爱是骤发的、偶然的、不稳定的,尤其会对卷入其中的个体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将个体从生活世界连根拔起”。而浪漫之爱则截然不同,它绝非激情的自我失控,反倒导向极为清楚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掌控。若说激情的本性是“迷狂”,那么浪漫的旨归恰恰是“自由”。在激情之中,人是不可能成为主人和主体的,最终只会沦为激情的奴隶和傀儡。唯有在浪漫之爱中,彼此相爱的人才能在精妙而复杂的自我反思、自我关切,甚至自我改变的践行之中实现主体性的自由。
其次,从时间性的角度看,浪漫亦与激情截然相对。激情总是偶发的,不期而至的激烈事件打断了日常生活的连续步调,中断了自我反思的连贯轨迹。身陷激情的人,总是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抛到了生活之外,卷进了无法自控的旋涡。但浪漫则显然不同:“它成为一种控制未来的潜在捷径,对于那些为浪漫之爱所支配了生活的人们而言,它还是一种(从根本上)保障心理安全的形式。”也就是说,浪漫之爱的时间肯定不能等同于平淡而重复的日常生活,但它所展现出的各种情感的强度并未真正中断,反而以一种朝向未来的筹划贯穿起内在的时间线索。浪漫之爱,就是自由地成为自己的主人,就是以爱为纽带重塑主体性的形态。既然如此,它显然要求卷入其中的主体对自己的言与行进行清醒地反思,清晰地规划,清楚地控制,尽可能地排除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正是因此,“海枯石烂”“天长地久”,是浪漫的宣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浪漫的写照。
由此就涉及浪漫之爱的第三个特征,那正是“超验性……的特殊信念和理想”:“因为它假设了一种心灵的交流,一种在性格上修复着灵魂的交会。”这种理想当然并非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浪漫之爱与肉体和性之间有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但浪漫不同于激情之处确实在于,它并不满足于在骤发的男欢女爱之中获得虽极致,但毕竟昙花一现的片刻快感,而且最终试图以精神的交流和融汇来实现和维系那种更为持久而稳固的情感纽带。借用全书第四章的标题来概括,浪漫之爱是“纯粹的”,因为它尽可能地摆脱了一切世俗的利益和束缚;浪漫之爱又确是一种“承诺(commitment)”,它是灵魂之间的超越时空的牢固纽带,既是对自我的承诺,又是对爱人的承诺。自我的反思、未来的筹划、灵魂的融汇,这三个本质特征联手将浪漫之爱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与高潮。
读到这里,用心的读者可能会反躬自问,甚至反唇相讥:即便吉登斯的论证言之凿凿,但反观今天的爱与亲密,哪里还有一星半点浪漫的影子?吉登斯当然也意识到了浪漫之爱在晚近以来的蜕变乃至衰落,并颇为敏锐地给出了两个诊断:一是浪漫之爱转变为“合流之爱(confluent love)”,二是自治转变成上瘾。这里,吉登斯虽然自己仍然坚持“进步”这个基本立场,但显然已经极具启示性地打开了“控制”这个批判性反思的方向。合流之爱,听起来颇有几分近似作为浪漫之极致的灵魂融汇,但实则截然相反,因为它全然违背了浪漫之爱的上述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合流之爱的宗旨绝不导向自我反思,而恰恰是“日渐增长的制度反射性的产物”。浪漫之爱的起点是个体探寻自我的欲求,终点则是不同灵魂之间的激荡和融汇。但合流之爱则相反,它的起点是制度所施加的各种规范,而终点则是由此所产生的一个个,甚至一批批合乎规范的自我。“合流”这个词用来形容此种趋势就很生动,一个个自我就好似一个个微小的水滴和支脉,最终都合并入主流之中。浪漫背后的推力始终是自我的反思,而合流背后的推力向来是制度的需求。
其次,合流之爱的时间性亦体现出与浪漫之爱的明显差异,它是“积极主动但又偶然飘忽的爱”。正因为它背后的动力是制度而非自我,这也就会导致一个明显的恶果,即当一个个“被合流”的自我在主流之中不断被裹挟着向前之时,虽然也明确展现出朝向未来的趋势,但从根本上来看与未来毫无关联。这个未来只是制度引导的结果,并不是自我筹划出来的,他(她)只是被卷进其中而已。而在规范的一遍遍引导之下,自我也就慢慢地丧失了自我反思的动力、自我控制的能力,渐渐看不到别样的可能,进而“反射性”地将合流的未来当成自己的未来。浪漫之爱中的自我,虽然也往往对未来充满着不安和焦虑,但在那一次次情感的冒险之中,还是有力量将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合流之爱中的自我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她)被推向一个与己无关的未来,在这个难以根除的被动性的前提之下,他(她)总是“变得十分脆弱”。他(她)的自我被掏空,无法掌控和反思自己,而只能是无所遮蔽、无所庇护地暴露在强大的规范化力量面前,因此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甚至自怨自艾,都是合流之爱的典型的自我体验。“我真的在爱吗?”“这是我想要的爱吗?”“爱到底是什么?”…… 被合流的自我时刻陷入无可化解、无从挣脱的困惑和彷徨之中。
由此也就能够理解,合流之爱显然会更倾向于肉体的激情而非灵魂的融汇。这也是它不同于浪漫之爱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既然合流绝非自我的欲求,亦非灵魂的渴望,那么,也许在肉体之中寻求昙花一现,却强烈鲜明的满足就成为唯一的安慰。但这种安慰也同样是虚幻而脆弱的,它既没有稳定的基础,也没有持久的可能,一切都只是徒劳的努力、绝望的挣扎。而且更致命的是,制度性的规范力量甚至早已渗透到肉欲的深处,不仅令不同的自我合流,而且将一具具被欲望煎熬的肉身也都愈发“亲密”地合流,“通过大量的性知识、性建议与性训练而被反射性地组构起来”。可以说,在合流的时代,性技术空前发达,这正是为了在肉体的最细微的深处操控自我,令其在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之处都尽心尽力地达到规范的标准,达到那个“理想形象”的自我。
正是因此,合流之中的自我确乎可以被描述为十足的“为爱上瘾”的状态。吉登斯随后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合流之爱与上瘾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足见他确实是将其视作晚期现代性的爱之衰变的终极症状。上瘾是合流的结果,但又将合流的负面效应推向无以复加的境地。合流的自我还有可能被浪漫所拯救,但上瘾的自我则几乎无疗治之可能,最终只能自暴自弃:“上瘾是对自我的放弃……丧失自我感后来被羞愧感和悔恨感所代替。”由此,上瘾之爱就几乎构成了浪漫之爱的截然对立面。浪漫之爱是自治,上瘾之爱是自弃;浪漫之爱是朝向未来的筹划,上瘾之爱是深陷当下的循环(“瘾是不能进入未来的”);浪漫之爱最终追求灵魂的融汇,而上瘾之爱甚至连肉体的激情都快体验不到,而唯有一遍遍重复着空虚、空洞、空茫的行为。从浪漫蜕变为合流,再从合流衰变为上瘾,现代性的自我到底还有何种可能用爱来拯救自己?还有何种资格来谈论爱这个永恒的话题?
三、为数字亲密辩护:关系性自我与人际关系的网络
吉登斯的这部经典至今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其中的每一个要点几乎都深深地刺痛我们的灵魂。这不仅是因为他鲜明地启示了从进步到控制的理论视角的转换,还因为他所指出的合流和上瘾这两大症状,亦足以用来深刻剖析当下数字亲密的爱与痛。
但在展开批判之前,不妨让我们先审视一番与吉登斯截然不同的积极肯定的立场,对照之下方能彰显对立双方各自的优点和弱势,而这个对照的核心焦点仍然在自我和主体性。很多对数字媒介和数字亲密持相对乐观立场的学者也大都从此处入手展开辩证与辩护。道理很明显,吉登斯之所以对合流之爱忧心忡忡,正是因为他在其中清醒地看出了自我失去自治的厄运。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也同样可以且理应向他发问:为何自我一定要自治?自我真的能自治吗?为何自我一定要牢牢以自己为中心展开生活的场域,而不能一开始就将自己当成庞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一个微小而变动的结点?为何自我一定要心心念念地将自己抓在手中,而不是一开始就抱着一种向世界敞开胸怀的态度,随大大小小的潮流而动,不断地逾越边界,重塑自己?或许,数字亲密中的自我,远非吉登斯所口诛笔伐的那般不堪。他认为合流的自我是衰退的形式,是否意味着他早已默认、预设了一种“本真的”自我形态?说到底,浪漫之爱不也同样是一种值得质疑乃至批判的意识形态吗?它难道不也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而诞生的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吗?
一句话,浪漫之爱的自我或许并不构成对合流之爱的自我的有力批判,正相反,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我们恰恰应该用另一种全新的自我形态来取而代之。那不妨就用肯尼思·格根(Kenneth J.Gergen)的那个重要概念来概括,即“关系性的自我”。在其近作《社会建构的邀请》第四章之中,他通过对传统的三种自我理论的辨析突显出自我的关系性内涵。虽然格根有些令人意外地全然未提及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的理论,但后者恰好可以在他的理论框架之中被定位于“拟剧论”和“文化心理学”之间。拟剧论的代表人物是戈夫曼,而他显然是吉登斯的重要理论来源。由此,拟剧论的内在症结也同样体现于吉登斯的论述之中:“接受这一观点意味着对他人和自我的深刻怀疑,这是对爱、对感恩或亲情产生的普遍不信任和怀疑。”自我总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场域和时空情境中面对他人表演自己,甚至可以说,你表演到什么样的程度,也就将自我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可厚非。但拟剧论挥之不去的迷执恰恰在于,它总是偏执地认定在那一张张变动不居的表演面具之下,还潜藏着一个个所谓真实的自我。于是,显现与遮蔽、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关系就成为拟剧论的理论预设。正是因此,表演中的自我无论怎样自信和自然,总会落入难以根除的自我怀疑的困境之中:“这真的是我自己吗?”“我怎样才能表演出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到,这恰好也是吉登斯所着力阐释的从浪漫之爱向合流之爱蜕变的隐藏线索。浪漫之爱是不同的自我向着彼此的敞开,是自我向着他人的表达,但即便这种表达如何真实而自然,仍然不可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表达出来的自我和进行表达的自我彼此抵牾乃至对立。自我表达的前提是自治,但自治性自我总会怀疑表达出来的自我是否与真实的自我相一致。由是观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并非仅仅是合流式自我的产物,正相反,在浪漫之爱的自治性自我的内部,其实早已深深地撕出自我怀疑这个裂痕。浪漫之爱,本就是自治和自弃之间的矛盾合体。
面对这样一个矛盾,本就存在着两种选择,要么是坚持捍卫自治的立场,坚执自我有一个不能完全被外化的内在核心;要么是彻底选择自弃的道路,将自我“合流”进庞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吉登斯当然意在坚持前一种立场,他虽然不会像笛卡尔那样将自我视为“我思”式的实体,但完整性、连续性和概念性这三个自我认同的基本特征皆鲜明体现出他对自我的中心性、基础性和内在性的偏执。而令人颇为疑惑的是,他用来建构自我认同的关键手段却恰恰是“叙事”这个自我最难掌控的要素。没错,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持续地吸纳发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把它们纳入到关涉自我的、正在进行的‘故事’之中”。但问题恰恰在于,自我既然是故事的主角,那么又究竟有何种能力乃至底气将自己始终确立为故事的“作者”?再进一步追问,即便自我真的是作者,那又何以有能力成为合格的、权威的“解释者”呢?文化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布鲁纳(Jerome Bruner)就明确指出:“事实上,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在我们脑海中被反复修改着的自传草稿——只有通过我们文化系统的说明或解释才能被自己和他人理解。”说得直白一些,你并非你人生自传的作者,至多只能是具有参与性的“修改者”或“编撰者”。更有甚者,你连解释权也无法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你是谁,你的人生到底有何意义,都有待你所置身的社会系统来给出“权威性”的“说明”或“解释”。
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索性全然放弃自治性自我的迷执,而全身心地拥抱关系性自我的当下和未来。按照格根的提示,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放弃“核心自我(core self)”这个颇具“误导性”的迷执,将自我化为复数(“我们”),进而将复数的自我化为社会系统和人际网络之中变动不居的“‘我地位’(I positions)”。格根这一番论述固然深刻入理,也足以向吉登斯对合流式自我的批判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但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憾,那正是对数字媒介的忽视。遍览他的几部论述关系性自我的代表作,鲜有涉及数字媒介和亲密关系之处。这实在令人不解。在当今的世界,真正主导着自我建构和叙事的难道不恰恰是数字媒介?铺展开无数的复数而多元的自我位置的社交网络难道不恰恰是数字亲密的网络?
如此关注关系性自我的格根当然不会错失这样一个要点。实际上,虽然数字亲密从未成为其论著的主题,但在研究数字媒介和亲密关系的早期重要合集《永久联系》(Perpetual Contact)之中,格根亦贡献了一篇专文,深入探讨了数字网络对自我和人际关系建构的深刻影响。遗憾的是,他所揭示的种种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消极的,这或许也间接说明了,他为何不愿在代表作中对数字亲密进行集中处理。这篇论文的标题《不在场之在场的挑战》()本身就蕴含深意。“不在场之在场”,这多少是在嘲弄拟剧论所迷执的那种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性。从关系性自我的角度看,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即便仍然展现为外与内、显与隐的关系,但这两极之间却并不存在主与从、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关系,也不存在可清晰厘定的边界。正相反,真正的关系性自我始终都游戏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在两极的渗透、交织、转化的过程之中不断编织、重塑自我。“我”的肉身坐在电脑前面,但“我”的精神却游荡于不在场的虚拟网络之中,甚至分裂为众多化身(avatars),穿行于不同的虚拟空间。“我”迷失了吗?“我”异化了吗?“我”真的四分五裂、难以自主了吗?似乎并没有,似乎从来没有。不妨戏拟休谟的那句名言:自我,无非就是一束关系,甚至一束束的关系。在关系的背后,没有核心;在面具的背后,还是面具。
看似格根准备对数字媒介进行一番欢呼和赞颂,但实情却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自我确实是关系性的,但并非所有的关系都是积极的,都是建构性的。数字关系或许恰恰就是一种本质上负面的、破坏性的关系。说到底,数字关系不仅破坏了自我的建构,更进一步破坏了自我之间的亲密。因此,格根随即笔锋一转,开始历数不在场之在场的数字网络的“罪行”。这主要集中体现于两点。
第一,关系有两种,垂直(vertical)和水平(horizontal),数字网络恰好是水平关系的极致体现。我们发现,这个区分又恰好与吉登斯在浪漫之爱和合流之爱间的区分形成了完美呼应,甚至连表述方式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格根指出,垂直关系“要求的是投入与专注,努力,承诺(commitment)与牺牲”,这显然正是浪漫之爱的典型特征。而水平关系则相反,它不向高处超越,也不往深处沉潜,而只是在各种数字媒介所编织的“无尽迷宫”之中进行着不知所向亦不知所终的游荡。格根还进一步将数字媒介的水平关系的罪证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破坏了“面对面的共同体”,瓦解了“自我的连贯和中心化的意义”,消解了“深度的关系”和“道德的担当”,将人生的意义“从实在的环境之中连根拔起”。
单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数字关系几乎已经堪称“罪孽深重”了,而格根还意犹未尽,进一步点出了其第二个更为致命的缺陷。垂直和水平,主要描摹的是关系的静态,那么还应从动态的角度对关系再进行区分,即“内生(endogenous)”和“外入(exogenous)”。内生以既有的关系为起点和中心,然后向外拓展,在这个过程之中,原有的关系并未得到破坏,反而得到了增强。外入则正相反,它无视既有关系本身的特性,而只是强行从外部施加条件限制和规范,甚至深入原有关系的内部,对其进行全面的替换和改造。不妨将电话和手机这两种看似类别相似、实则截然相悖的媒介形态进行对比:电话显然是内生的,因为它是既有的“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的拓展;而手机则正相反,首先以水平的网络取代了垂直的高度和深度,进而用一整套数字化的规则和规范来对原有的自我关系和人际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外入”式改造。固然,手机在建构关系性自我、编织在场和不在场的互动网络之中亦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看,它的此种功用绝对是弊大于利。
或许是为了形成主题上的承接,同一文集中,紧随格根之后还收录了鲁尔(James B. Rule)的立场极为接近的论文,进一步深化了对数字亲密的批判性反思。首先,鲁尔借用埃吕勒(Jacques Ellul)的理论,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补充阐释了“内生”与“外入”的基本区分。他指出,传统技术与人的关系最终是积极的、正向的,亦即技术最终满足的是人的需求,实现的是人的欲望。虽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它们也往往会激发出人身上的新欲望,但新欲望仍然是基于人自身所既有、固有的力量。但晚近兴起的数字技术和媒介则正相反,它们对人的欲望所施加的根本上是转化性、替代性、改造性的影响和作用。不妨用一个生动的形象来比拟这新、旧两种技术形态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技术面前,人是“提问者”,而技术则致力于回答人所提出的各种难题。但如今,数字技术却摇身一变而成了“提问者”,而且还环环相扣地不断向人抛出无穷无尽的有待回答的难题。在技术面前,人如今蜕变成一个殚精竭虑、死命追赶的“回答者”。他根本无从理解问题的意义,甚至都无从把握问题背后的演进逻辑,但在数字技术的规范化作用之下,却“反射性”地将所有这些承担为自己的问题,自己真正关切的问题。这亦是整部文集的标题“永久联系”深刻又尖锐的含义:人被绑定于技术的永久联系(contact)之中,或许正恰似一种单方面的、不容撕毁的永恒契约(contract),人永远只能屈居为契约的参与者和履行者,而根本无力成为平等的合作者,更遑论对契约本身进行质疑、修正乃至解除。
四、探索第三条进路:数字亲密的“潜在(virtual)”之力
我们的本意是想借用格根的关系性自我的理论来为数字亲密关系进行辩护,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无讽刺的是,大力倡导对核心自我进行消解的格根,在对数字亲密进行批判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连贯和中心化的自我”这样很有吉登斯意味的概念。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关系性自我或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捍卫或至少值得深思的立场,但其前提显然是需要我们对数字媒介有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单纯从传统媒介和技术的角度对当下进行批判,显然不够。诚如本文开篇所示,更应该深入数字亲密之中,展现其中的错综复杂的力量纠葛。
那就先从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的经典之作《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入手。该书从批判开始,但随后逐渐深入揭示了数字媒介对人际关系的积极建构,这就颇为符合本小节的目的。此外,它特别以自我的建构为一个论述的中心,这也颇为契合“主体性”这个我们迄今为止所围绕的核心。从批判的精度、广度和力度来看,拜厄姆完全不逊于之前的任何一位代表性学者,而且要点皆颇为趋同。比如,她开篇就深刻提出了数字化人际关系的三个关键的难题,甚至困境。第一个当然是自我:“我们何以既在场又不在场?如果自我不在身体之中,它将是什么样子?”这明显呼应着格根所提出的关系性自我的那种“不在场之在场”的鲜明特征。自我的困惑进一步引申出第二个难题——政治的难题,那正是控制与自由。看似数字媒介让每个自我越来越获得对自身的自主控制(autonomy),但悖论在于,其前提恰恰是主体不能自控地与媒介技术所签订的单方面的“永久联系/契约”。这也就导致第三个难题,那正是私人和公共之边界的模糊乃至瓦解。技术不断渗透到私人领域之中,施加着转化和改造之影响,到了最后,甚至连自我最私密和内在的孤独都蜕变为技术所操控的产物和效应。
这几重批判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拜厄姆并未止步于此。相反,她随即列出了数字化人际关系的七个核心概念,试图通过深入而细致的实证性描述来揭示、激活其中尚且存在的积极的潜能。全书第五章聚焦于自我和数字亲密,颇有启示。她开宗明义地指出,之前的种种对于数字化人际关系的指摘皆存在一个共同的偏见,那就是仅将其视作所谓“本真的关系(authentic connection)”的蜕变、扭曲乃至遮蔽,而没有看到它所塑造的是新的自我、新的关系、新的未来。那么,它到底“新”在哪里呢?到底在哪些方面展现出传统的人际关系所无法实现的优势和长处?拜厄姆随后列举出的几个要点皆颇有说明力和说服力,尤其能展现出数字亲密的进步性变革。
首先,她敏锐地指出,作为不在场之在场,网络中的人际交往虽然看似抽离了肉身和实在的根基,甚至游离于“真实的”肉身和自我之外,但并非虚无缥缈的数字仙境。正相反,它通过虚拟的不在场的网络空间,恰恰意在回避、缓和、化解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的种种尴尬、焦虑乃至危险。屏幕隔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但这并不一定是疏远,也会给卷入关系之中的不同个体留出更宽的缓冲空间,更多的选择可能,更游刃有余的即兴创造。在现实生活中,当你直面一个活生生的他者之时,此种切近和迫近的关系总会多少让你心生某种难以摆脱的压力乃至紧张。萨特对他人目光的论述,阿布拉莫维奇的著名行为艺术作品《艺术家在场》()皆为明证。但数字化的关系就很好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
其次,数字化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面对面交往之中的盲目和偶然。在数字交际的平台之上,看似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着大量随时涌现的未知的际遇,但其实这些都只是背景噪声。庞大的基数往往并不会造成迷惘和错乱,正相反,它为我们寻找同道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维系良好的亲密关系的有效手段。你在网上一天邂逅的好友,可能比你在线下一年见到的加起来还要多。大数量保证了高成功率,同样,迅捷实时的数字连接也加固了亲密关系的“亲密性”。在以往的年代,朋友的离别总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件,但是,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般美好的愿景,在今天的数字网络之中却是唾手可得的现实。反过来说,如若你想真正、彻底地斩断一段数字亲密的关系,反倒变成了难上加难的事情。你即便屏蔽、拉黑了好友,但还是会主动或被动地,在有意无意间,在包围着你的信息海洋中发现他/她的明显踪迹。恋爱容易分手难,这或许恰是数字亲密时代的一个令人玩味的特征。
再次,数字化关系并未削弱人际表达的丰富性,反倒极大拓展了它的几乎不可穷尽的可能性。之前很多研究者指摘数字媒介的一个根本症结,就在于它主要还是以文字和图像为主导,由此就失去了面对面的交往之中的更为丰富的要素,比如表情、姿态,甚至触感和气味,等等。但实情或许恰恰相反。不妨追根究底地问一句:人际交往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交往的真正内容到底是什么?答案似乎并不复杂,那正是意义的交流、情感的共鸣,乃至思想的碰撞。诸多身体性的特征当然也是重要的,但那至多只是基础和手段,我们彼此之间面对面地注视,最终是为了理解对面那个鲜活的心灵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情感和思想。由此看来,那些身体性、物理性的特征反倒往往构成了人际交往的限制乃至束缚。比如,你根本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形象。再比如,有多少时候,你发现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表情和姿态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情感。所有这些限制在数字化空间中皆荡然无存。数字化的手段,正是以“不在场”的自由极大地突破了“在场”的重重束缚,让亲密关系变得更为深入、丰富而回味无穷。不妨想想你可以在微信上用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来说出“我爱你”这句话。
如此看来,数字亲密更为自由、更为丰富,也更加宽容。它最大限度地挣脱了世俗的利益,以及现实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隔膜乃至鸿沟(年龄、性别、地位,甚至单纯的“颜值”)。它并没有让人与人彼此疏远,反倒是愈发亲密。由此,拜厄姆甚至总结说,数字亲密才能真正实现浪漫之爱所憧憬的那种“纯粹关系”。但果真如此吗?数字亲密真的那么“纯粹”吗?或许不尽然。这尤其体现于“诚实性(honesty)”这个每每被用来批判数字化关系的关键要点。是的,你可以在网上随心所欲、无所束缚,甚至无所忌惮地捏脸、换装乃至变性,但在这些不断变换的化身之下是否还有一个“真我”呢?或者至少,在这些看似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化身之间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连贯性,得以被归于一个“我”呢?还是说,这些化身都是我,又都不是我,这本来就无所谓。因为更重要的本来就并非我“曾经是”“已经是”的样子,而更是“我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对于数字化自我来说,下一个我,另一个我,不同的我,才是主体性之真意。
但即便不对这个主体性的要点发起质疑,至少在无尽变换的数字自我之中存在着一个根本的难点,足以挑战拜厄姆所辩护的数字亲密的“纯粹性”。确实,数字亲密可以如浪漫之爱那般实现精神的高度、体验的深度,甚至关系的持久度,但它唯一无法真正实现的似乎正是“承诺”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当你和爱人面对面,彼此注视,甚至深情相拥之时,你不会怀疑他/她的真诚,你更不会怀疑你自己给出的承诺。但在数字空间之中,那可就是两回事了。当你们两人手指飞舞、妙语连珠、图文并茂地对话之时,想必每个人心中都始终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狐疑:“他/她说的是真的吗?”“她/他真的爱我吗?” 而且更为棘手的难题还在于,你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检验”和“测试”对方的真诚呢(testing out honest self-disclosure)? 似乎别无他法,唯有发更多的文字,抛出更多的表情包。一句话,你只能用数字来验证数字,只能用信息来核查信息。这既无奈,又颇有几分凄凉。面对这个难题和困境,拜厄姆自己显然也是束手无策,也只能是反复抛出“真我”来对质化身,用线下的在场来对线上的不在场进行纠偏。也正是诚实性这个难题让一众数字亲密的拥趸往往只能不无沮丧地承认,所谓的线上的亲密,实际上绝大多数还是来自“已经预先存在的线下关系(pre-existing offlinerelationships)”。
但拜厄姆在有意无意间带出的一个启示却打开了不同的方向,尤其是引向了生成这第三条道路。在第五章的最后,她对数字自我的真诚性给出了两个虽非相悖,却方向相反的解释。一方面,她指出,数字自我并非随心所欲的“虚构”,在种种化身和面具的背后,总是表现出“真实自我”的那种对自身进行“理想化”提升的倾向。现实中的“我”总是不完美的,有着各种各样难以克服和修正的缺陷,但在网络上的化身之中,“我”却完全有可能,有理由将自身塑造成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形象。这个方向显然仍然趋向于浪漫之爱的精神理想。但另一方面,拜厄姆又指出,虚构的化身并非毫无根据的捏造,而恰恰是“善用”技术手段来对自身进行“微小的策略化处理(minor strategic manipulations)”。这些处理可以趋向更高的精神理想,但也可以相反,深入自我背后的种种“潜在的”深处。“minor”这个词提醒我们拜厄姆所暗示的极有可能是后一个方向。我之所以要在网上变换各种化身,如果不是出于无聊、谨慎乃至欺诈,如果这背后真的有什么严肃的原因的话,那么,它可能并非只是朝向一种理想化的形象,而同样有可能意在敞开现实的自我中尚且潜藏着的,有待实现、敞开和释放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微观力量。现实的(actual)自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心和明确的基础,正相反,它总是各种潜在的(virtual)力量所生成的宏观效应和结果,也注定将伴随着潜在力量的格局变化与不同强度的结域-解域的运动而一次次进入生成。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现实的“我”和潜在的“我”之间彼此渗透、交织、转化的关系,恰好可以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潜在性”的理论进行完美恰切的解释,由此亦开启了超越进步和控制的二元对立的第三条研究进路。
当然,拜厄姆在文中充其量只是暗示了这个线索,虽然她多次使用了“潜能(potential)”这个词,但是既没有明确援引德勒兹的相关理论,更没有花费笔墨在这个方向进行推进。真正明确从潜在性的方向推进数字亲密研究的,是麦格洛滕(Shaka McGlotten)。在研究数字亲密的专著之中,他甚至在标题中就将“数字亲密”直接转换成了“潜在亲密(virtual intimacies)”。此举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提醒我们,亲密关系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基本人际关系,其实向来已经蕴含着实在和潜在、可见与不可见,甚至在场与不在场这些双重交织的维度;另一方面,他明确将亲密关系的潜在性与晚近数字媒介的发展关联在一起。与拜厄姆的论证策略一致,麦格洛滕在导言之中也是以批判性的悲观语调开篇,但随即用德勒兹的潜在性概念来指明更为积极乐观的方向。这其实也恰恰呼应着“virtual”这个词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即“虚拟”和“潜在”。从虚拟的角度看,它更多地与数字亲密的技术本性结合在一起,尤其展现出值得质疑和批判的面向。针对“虚拟的亲密”,麦格洛滕的指责堪称不留情面,认为它只是“失败了的亲密关系,由此中断了良善生活之流”,最终它无非是“真实生活的苍白模拟甚或丑陋的衰败(ugly corruptions)”。
但他随即转向了“潜在”这另一个更为积极而乐观的方面。他坦承,在德勒兹的潜在性理论的启示之下,他至少发现了病入膏肓的虚拟亲密的两种积极变革的可能性。一是,“潜在性并非与真实相对立,潜在性指向着内在性(immanence)、能力与潜能(potentiality);二是,我之所以强调亲密关系已然是潜在的,正是因为它经由情感体验(affective experience)而显现出来”。显然,内在性和情感体验是两个要点。
先说内在性。上面援引的拜厄姆的那段话恰好提示我们,亲密关系具有超越性和内在性两个面向,既可以是朝向灵魂融汇的精神理想,也可以回归关系内部的多元和差异的力量博弈。麦格洛滕所谓的内在性显然明确指涉这后一个方向。而具体落实于数字亲密的领域,内在性又展现出两个相关的面向,一是僭越(transgression),二是流变(variation)。僭越对抗的恰恰是数字技术所施加的规范化操作,但此种对抗并非采取外部的视角,而是试图从技术形态自身内部去释放出解域和逃逸的潜能。之前的学者们之所以总是陷入进步和控制的两难之中难以自拔,正是因为错误判断了数字技术的作用,将其仅仅作为外在施加的限制和控制,进而与“本真的”“纯粹的”亲密关系的领域(比如浪漫之爱)对立起来,分隔开来。此种“异化”理论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直白甚至浅白:在数字技术以前,亲密关系虽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根本上还是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和自足;当数字技术侵入之后,一切都变质了,一切都衰败了,本真的关系变成了虚情假意的游戏,精神的理想变成了肉欲横流的享乐,未来的筹划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但若从麦格洛滕着力阐释的内在性的角度来看,此种立场显然是错误的。技术的作用并非只是影响、操控乃至侵犯,正相反,唯有凭借数字技术的手段,原来潜藏在亲密关系之中的种种“内在性”的力量才得以被激活,被展开,被创造。数字技术并非只是强大而邪恶的捕获装置,其实更是一个“内在性的平面”,在其上,亲密关系才真正得以释放并实现自身的种种源源不竭、不可遏制的差异性潜能。那么,究竟该如何解释合流之爱、上瘾之爱这些欲盖弥彰的时代乱象呢?道理亦很简单,那不是因为技术犯了错,而只是因为原来具有创造性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僵化和固化,无法再起到激活潜能的作用。要解决这个困境,恰恰不能从技术之外去祈求超越性的拯救力量,而只能一次次回到技术本身,将其带入生成和流变。技术本就是一个差异力量的聚合体,一个异质性要素离合聚散的内在性平面,那么,不断突破自己既有的边界和僵化的结构,再度进入解域和生成,这本来就是它的固有趋势。借用麦格洛滕的精准概括,“修复(recuperate)潜在性之中所固有的拓展性可能(expansive possibilities)”,这就是内在性的真意。在更为晚近的研究文集《数字亲密:公众与社会媒介》之中,显然是“生成”这第三条途径占据了主导,“越轨与僭越(excesses and transgression)”明确成为数字亲密的变革性政治(transformative politics)的核心词汇。
结语:亲密关系,爱还是痛?
但僭越与流变并不是以麦格洛滕为代表的生成性亲密关系的全部。实际上,他的这部著作本就兼容理论与实践,理论方面自然以德勒兹的潜在概念为本,但实践方面则深入而生动地描绘了从性到电子游戏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的亲密状况,尤其突出了“情感体验”这第二个重要维度。如果说生成是技术的解域之力,是技术不断突破自身的束缚而不断释放潜能的过程,那么情感体验则更为鲜明地涉及了“主体性”这个本文的要点。
之所以要在数字亲密的研究中细致刻画个人的体验,既是因为亲密关系的独特属性,又因为这多少展现出超脱于德勒兹主义的可能性。生成性的游牧主体固然得以克服关系性主体的种种弊病,用生生不息地从潜在到实在的流变运动来回应真诚性这个难题,但它同样有着明显的症结:创造性的、内在性的生命,确实理应成为主体性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但自古希腊以来所强调的自我反思、自我控制,甚至自我改变的“自治”仍然不失为另一个关键特征。仅仅沉迷于流变而没有自控,仅仅醉心于创造而从不反思,似乎都不能成为主体的完整、完善的形态。因此,在全文的最后,我们似乎又有必要重提主体之自治这个吉登斯的原初理念。即便我们不再认同浪漫之爱的空洞的意识形态,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同时放弃自治这个主体性的立场。
那么,如何在数字的网络和数据的云端中重新探寻自治之根基呢?情感体验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入口,但不再是被技术所规范、市场所引导、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种种所谓积极的、“肯定的(affirmative)”的情感,而是恰恰转向其反面,在否定性的体验之中敞开对抗与逃逸的可能性。这一要点,很多学者都提到过,但明确将“苦痛(suffering)”这种极致性的否定体验作为核心来重思、重申亲密关系的,似乎无人能出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之右。她的三本代表作几乎就是从不确定性到脆弱性再到苦痛性的逐步加剧的情感体验的历程。在2007年问世的《冷亲密》(Cold Intimacies)一书中,她虽然也大量涉及了情感话题,但是对数字亲密的论述主要还是集中于批判。她所列举出的数字亲密的四大症结之中,后三点(知识先行、意识形态、市场导向)与吉登斯和贝伦特等人的批判性立场并无二致,而第一点则鲜明突出了主体性这个维度,亦即数字亲密堪称前所未有地“锐化了(sharpen)自我的独一无二的体验(one's sense of uniqueness)”。正是“sharpen”这个词带给了读者深刻的触动。确实,数字亲密改变着自我的形态和人际的关系,用拜厄姆的话来说,它不断塑造着“新的自我,新的关系”,但数字自我到底“新”在哪里呢?体验或许正是一个要点。数字媒介带给每一个人前所未有的自我体验,那早已不再是浪漫之理想,亦非激情之欲望,更非合流之瘾性,而是一种自我与自身的否定性的体验。这不是自我确证,但也不能等同于自我怀疑乃至否弃。正相反,此种否定性体验的起点是主体的极端被动性的感受: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力量正在渗透“我”,支配“我”,把“我”推离自己的位置,将“我”卷入主流的旋涡,令“我”越来越失去对自身的控制和自治。因此,自我否定不同于自我怀疑,后者见证的是主体的瘫痪和无力,并从根本上瓦解了进一步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但前者则正相反,虽然深陷被动性的困境,却对自身有着强烈而鲜明的体验,更为明确地确证了自身的存在,进而得以激发出更为坚定有力的行动。“我不知道我是谁”,这是自我怀疑者的口头禅;“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自我否定者的宣言。
由此在后续的《拯救现代人的灵魂》(Saving Modern Soul)一书中,她再度明确强调了“反思性的强烈形式”,更是将“脆弱性的感受(sense of vulnerability)”界定为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的根本维度之一。然而,脆弱性仍然不足以成为描绘否定性的亲密体验的恰切语汇,因为其中仍然弥漫着浓重的自我怀疑的气息。或许正是因此,在名作《爱,为什么痛》(Why Love Hurts)之中,她明确地转向“苦痛”这个核心的否定性体验,甚至将其视为爱之体验的近现代转化的核心枢纽。与前现代的三种爱的形态(贵族、基督教、浪漫)相比,现代爱情和亲密关系所缺失的最为重要的维度恰恰是“爱之苦痛(love sufferings)”。她不无尖锐地指出,伴随着“医学话语”而兴起的现代性的自我文化几乎是有史以来唯一一种对苦痛之体验进行无视和否定的传统。在往昔,爱总是与痛相伴相随,甚至可以说,痛才是爱的极致和巅峰的体验;但如今,痛不仅与爱鲜明对立,更是成为一种有待被治疗的“病”,必须被根除的“恶”。“活着不是为了痛苦。”这显然是现代爱情的至理名言。既然如此,那么重新激活否定性的体验,再度回归爱之苦痛的传统,是否能够成为拯救数字化主体的可行途径?面对吉登斯在三十年前向我们提出的自治性主体这个难题,或许伊洛斯对于爱之苦痛的深刻论述切实展现出了一条可行的回应之道,一条有别于进步、控制、生成这三种经典立场的前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