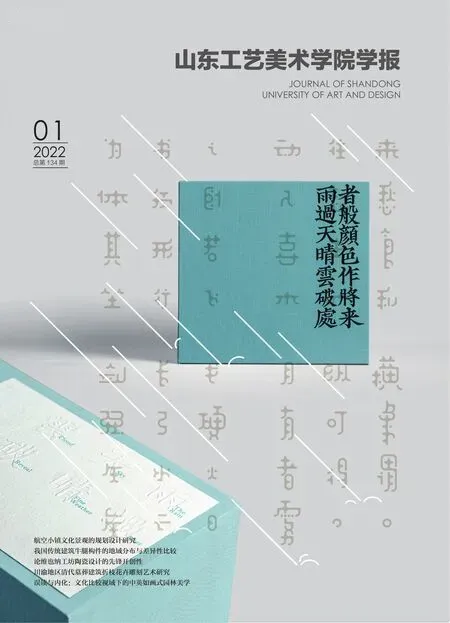工匠与学者的互动:先秦士匠造物机心与诸子批评
刘华年
先秦存在着亦士亦匠的“士匠”群体,若墨子、公输班之流,文献对此类工匠发明的记述非常广泛,小到锁具大到攻城守城器械,都有涉及,他们是先秦最具工匠精神的群体。其工匠精神核心的“机心”是推动造物进步的重要动力。“机心”始于“制器尚象”设计思维,发展于能工巧匠之“巧思”,并形成朴素的事理设计经验。但“机心”终究未能发展为系统的设计科学,其根源在先秦已经埋下。诸子一方面褒奖个人高超身体性技能的“匠巧”,同时又对工匠探索造物科学的“机心”大为防范,从道德伦理上对其进行有意贬低和防范,故工匠之智竞用于个人精湛技艺的追求,而于发明创造少有建树。
士匠;机心;创物精神
引言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反过来即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对此奥地利学者齐尔赛尔的回答是“欧洲在16世纪由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兴起,知识分子——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高级工匠三阶层的社会壁垒被瓦解,他们的智识才能转化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独特事业,称之为科学。”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知识分子和高级工匠之间身份壁垒消隐的时代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在先秦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士群体的成分比较复杂,亦工亦士的人大量存在,本文称之为“士匠”群体。他们或以匠技闻达于诸侯,或以匠事安身立命,如庄子曾为漆园吏,墨子出身木匠,诸子也常以匠事喻理。那个时代涌现了如鲁班、墨子这样的技术巨匠,创造了大量的器械,是中国历史上技术大爆炸的时代,也是思想大爆炸的时代。
1.先秦士匠群体产生的社会基础
“士”在中国长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但通过文献查阅,却发现“士”的所指是不断变化的,正如余英时所说:“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游士则说明了当时的士群体是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是可以“择木而栖”的,和君王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亦可不与君王交。在西周,士的群体相对固定,为贵族子弟,他们习“六艺”之术,往往只有士的后代方能为士,亦即管仲所谓“士之子恒为士”。但至春秋战国时代,亦即孔子所谓“礼崩乐坏”之时,之前西周的各种宗法门阀规制被打破,“士”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诸侯不拘一格用人才,大养门客,凡怀治国安邦之策、之技能者皆可称之士。既有落魄贵族如孔丘、韩非之流,商人如子贡、陶朱之辈,亦有孔武之士如子路者,更有怀一技之长之士如墨翟、公输班者。正如《商君书·算地》云:“技艺之士,资在于手”,身怀绝技者亦可为士。当时怀有绝技的名士除了墨翟、公输班还有善治兵器的欧冶子、干将,善于工程营建的李冰、郑国、史禄等;另外还有一些以工匠之业谋生的名士,如《吕氏春秋·季冬纪》载:“齐有北郭骚者,结罘罔,捆蒲苇,织葩屦。”《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名士陈仲子“彼身织屦,妻辟卢”。北郭骚、陈仲子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名士。其实华夏民族的始祖都是一些最初的能工巧匠,如发明车的黄帝、建造房屋的有巢氏、捏制泥人的女娲、制陶的唐尧等,故士人作工匠之事亦是正常不过。鉴于当时的状况,亦士亦匠的“士匠”群体是大量存在的。因这个群体的存在,先秦时期士和工匠之间的壁垒并不分明;也因他们的存在,先秦的技术爆炸和创造精神才得以产生。
士匠群体而非普通工匠群体成为技术创造发明主体,是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个人身份分不开的。其一,时代需要具有技术创造能力的士匠。周王朝王权旁落,诸侯争霸,欲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装备技术成为必要条件,故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手工业,手工业发达的诸侯国也是经济、军事发达的地方,如当时齐国就拥有非常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手工制造业的发达依赖于大量工匠,而想提高生产水平,则依赖于更为先进的机械,故具有创造能力的士匠就格外受到诸侯的礼遇,如公输班就得到楚王的聘请,充分发挥其技术创造的才能。其二,士匠群体不同于一般“食官”的工匠,他们往往是新技术发明的构思者,不一定需要亲自动手制作,更不需要“工勒其名”。士匠群体可以受聘于官,亦可特立独行。即使受聘于官亦非唯诸侯之命是从,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甚至可以对诸侯不合理的要求加以反对,即所谓可以“执艺事以谏”,著名的士匠。至于独行于野的士匠群体则是完全自由的,既可为“逐于利”而发明,亦可为“逐于义”而创造,前者如公输班、《列子》所载制造跳舞小人的偃师,后者如墨子等。正是这样的时代土壤和士匠群体的存在,先秦创物精神的社会基础才得以产生。
2.士匠群体的机心解读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士匠群体为当世之智者,是先秦发明创造的主要群体,和当时如《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巧者”百工相比,其最大的差别就是拥有创造精神和造物思维能力,亦即所谓的“机心”。机心一词出之《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清朝郭庆藩《庄子集释》对“机”的注解:“机,关也。”何谓“关”?《后汉书·张衡列传》:“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施关发机”中“关”即机关,汉阴老翁所言“机”就是机关之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机关:“机械设备中承担启动和制动功能的关键性组件,对机械设备起着整体控制的作用。”《庄子集释》又言“夫有机关之器者,必有机动之务;有机动之务者,必有机变之心。”故“机事”即“机动之务”,即制造机械或使用机械的情况。机心即“机变之心”。何谓“机变”?《墨子·公输》:“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拒之。”此处“机变”意为变换和改进机械。故“机心”即具有熟悉机器内部机关构造和灵活改变机关的能力,并具有制造和不断改造升级机器机关的欲望。先秦机械多为木制,熟悉内部机关构造并能加以改造升级,或利用机关创造新的器械不是“述之守之”的一般工匠所能胜任,一般的工匠往往只具备“巧心”而不具备“机心”,故“机心”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动机和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造物思维能力。
2.1 作为动机的士匠机心
从当时的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士匠群体创物的动机有三:第一,用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心理诉求。比如公输班,在面临季康子葬母难题时想到是用“机封”技术解决问题;在面对宋国的高大城墙想到设计云梯攻之,面对越国优势水军设计“钩强”破之。而墨子面对公输班的云梯,首先想到的也是用技术破解,才有“九设机变以破之”,在技术较量的反复过程中,技术的发展也就越来越快。第二,士匠群体对技术原理的探究欲望。他们会在反复的技术实践中发现技术原理和初步的科学规律,并运用于新的创造之中,如墨子就在技术实践中发现了八条光学规律,特别是折射、小孔成像原理、日影原理,为后世的发明提供了科学依据,公输班发明的木鹊、鲁班锁亦是在初步掌握动力学原理的情况下发明的。第三,士匠之间互相竞争的技术进取精神。墨子先发明能飞一日的木鸢,公输班便发明能飞三日不下的木鹊,公输班发明云梯,墨子便设机变以破之,表面目的是证明自己技术的高明,本质目的是以此获得诸侯的另眼相看和重用。
2.2 作为造物思维能力的士匠机心
守其旧制者往往只能充之百工,供人役使,具备创物思维能力者方能闻达于诸侯,如公输班与墨子的第一身份并非工匠,而是拥有创物能力的士人。关于公输班的发明,《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典籍中记载了其很多发明,如锯子、伞、石磨、墨斗等;《墨子》中则记录了公输班发明的钩强、云梯,记录了墨子发明的连弩、转射机等器械。《易经·系辞传》言:“是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即言先秦造物思维的总论是“尚象”,即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悟得物理的规律,并创造器物为人所用,如滚木原理发明车,浮木原理发明舟等。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先秦士匠掌握的技术原理往往是在观察中形成的物理经验,观察的方法就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在观察自然中发现了植物反弹力、绳索扭绞反弹力、空气浮力、风力、水力、杠杆等原理;在近观人体自身中发现了气囊、曲臂连杆、绳索连动等原理,并由这些原理发明了滑轮、风箱、抛石机、弓箭等物,可能局限于冶金水平,先秦但始终未能发明弹簧、螺丝螺母。先秦士匠们就是利用观察总结到的这些技术原理进行创物实践的,墨子、公输班就是掌握这些经验原理的士匠。但通过观象获得的原理往往是停留在经验层面的,即使是解释原理也往往是通过现象进行,如《易经·系辞传》解释造船造车原理:“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涣卦、随卦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现象解释,以经验去解释经验,自然离科学还有很大距离。
3.诸子对待机心的态度
再次回到李约瑟难题,因何技术没有在中国古代发展成科学,除了上文提及的用经验解释经验的直接原因之外,当时知识分子主体的诸子对待技术的态度、参与技术实践的程度亦是重要原因。先秦主流的四大学术流派为儒、墨、道、法四家,梁启超先生称四家为“一期思想之主干”,四家对待“机心”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就决定了技术发展成为科学的可能程度。
3.1 墨家与机心
四家中直接参与技术实践的只有墨家,即使是墨家也用“义利”的伦理观看待技术,这在《墨子》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若翟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谓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公输班是纯粹的技术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技术开创精神,而墨子却是技术实用主义者,在墨子眼里技术有善恶之分,有利于民生的为善,而仅仅以机巧为执念者是不值得提倡的,亦即后世所谓之“奇技淫巧”。事实有另一版本,《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通过比较发现,墨子制作的木鸢只能飞一日,而公输班制作的竹木鹊能飞三日还不落下,在技术上墨子是逊色于公输子的,墨家学派所著《墨子》为抬高墨子,而借用儒家的技术伦理观贬低公输而已。民间尊公输班为木匠祖师,为妇孺皆知,也足以证明其机关术的高超。公输班和墨翟皆为游士,都是“资于在手”的技艺之士。两者不同的是,前者完全专注于技术本身,完全靠机关之术获得诸侯的封赏,不太注意技术的伦理问题,也不干预政治问题;后者以技术干预政治,有自己的技术伦理主张,形成自己的学派。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学派并未向公输班那样将发明创造作为终生事业来追求,其终究目的还是试图建立等同于儒家思想体系并用于治理国家,技术发明恰恰充当了他们闻达于诸侯的手段,成为被举贤的资本,如《墨子·尚贤上》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提出举贤不分出处,技艺高超者亦可为贤的观点客观上促进了出身低微的士匠靠技术进身的积极性,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3.2 儒家与机心
儒家一方面对技术发明于生产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荀子也对发明创造对生活产生的便利持肯定态度,并指出君子应该积极利用技术发明为自己服务、为生产服务,正如《荀子·劝学》所言:“假舆马者,非立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揖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之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另一方面又不主张知识分子从事发明创造活动,“君子不器”。从上述所知,儒家是鼓励技术发明的,并强调技术为民生服务,但又反对士人直接从事发明创造。这直接造成后世的文人对技术知识的了解等于零,儒士不可能成为发明创造的主力军。但荀子认识到了人要战胜自然,必须要借助技术创造方能实现,只有“善治”技术方能富国,其在《荀子·富国》云:“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此“善治”即指农耕技术的发达。再有儒家以是否符合礼教看待技术,《礼记·檀弓》就记载公输班设计“机封”下葬季康子之母,被儒者认为于礼不合,“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母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这段文字就记载公输班请求在葬礼中用机关被斥责之事,反映了公输班并未意识到技术是否符合礼制、是否符合儒家道德的问题。
3.3 道家与机心
道家对发明创造的“机心”无疑是持批判态度的,其批判的着眼点是担心技术异化会导致国家混乱、民风不朴,担心人用技术害人。《老子》云:“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言:“道家作为合作性社会的代表,对于强权专制社会可以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那些技术持有一种矛盾心理的态度,这是情有可原的。他们看来,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庄子同样对技术于自然的破坏持担忧态度,《庄子·肤筐》云:“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罘罝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庄子·马蹄》中亦有大段论述,认为伯乐治马、陶匠制陶、木匠制木都是不应该的,甚至极端地认为:“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但道家一方面反对作为发明创造动机的“机心”,另一方面却对熟能生巧的个人技能大加赞赏,甚而认为“技近乎道”,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津人操舟、丈夫游水、梓庆为鐻、东野驾车、工捶旋矩、丈人钓鱼、无人施射、匠人捶钩、匠石斫垩等。李约瑟也意识到道家强调手工的技艺,却歧视技术与发明,李约瑟先生将之解释为“这种技术活动中各因素的充分和谐,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事物各种有机联系的和谐理念,因而可以充分避免不和谐的技术实践带来的异化现象。”由此可知,道家反对借助于工具与技术,而主张以人自身的身体机巧达到人和万物的和谐。道家的技术观念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但在今天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3.4 法家与机心
法家对技术发明并不反对,但要求工匠职业化。如韩非则主张专业的事情由专人做,主张工匠的职业化,《韩非子·定法》“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且虞庆诎匠也而屋坏,范且穷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诚者,非归饷也不可。”由此可见,法家亦不主张知识分子参与技术发明。另外法家主张技术为农耕和作战服务,而将刻绘、刺绣之类的手工技艺作为不重要的末业看待,“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法家的主张既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又限制了技术的发展,限制的原因是其将知识分子与工匠阶层割裂开来。
上述可知,先秦诸家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鼓励发明创造,一方面又担心技术的过分发展导致民心不古而影响其统治,去限制其发展。除了道家之外,三家都是积极的技术实用主义者,积极维护“士农工商”的阶层秩序,采取抑制商业的策略,主张技术为“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体系服务,凡有益于此的就支持。同时反对以钻营利益的发明和工艺,认为钻营利益者往往以“奇技淫巧”蛊惑人心,使国君不安于治国,民众不安于稼穑。再有士人群体不主张直接参与技术实践,就让知识和技术分离开来,缺少了将经验理性上升为科学知识的智力基础。唯一有可能发现科学的墨家也因秦的一统而消逝了。
4.结语
再来看齐尔赛尔对科学产生的回答,他认为大知识分子和高级工匠之间的壁垒消除是科学得以产生的智力基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促进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工匠融合的社会动因是什么呢?先秦时的墨子兼有这两种身份,甚至发现了一些力学和光学的规律,但终究也未能提出如“阿基米德定律”那样的科学定理,还始终停留在技术经验的层面,其根本的原因是“以农立国”的根本国策,这是和西欧“文艺复兴”以“工商立国”的国策是根本的差别。农业国家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统治阶层只希望农民安于农业生产,整个社会机制在“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下稳定运行即可,相比于技术发明,知识分子从事读书治经获得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更多更高。故在先秦尽管有墨家学派对技术的重视,但整个社会并未觉得技术发明有利可图,这是技术发明缺少更多知识分子参与的主要原因。尽管先秦有“执艺事以谏”的工官制度,墨家成员可以用技术作为进身士阶层的资本,但相对于儒、法二家从事官僚事业的庞大队伍而言,人数还是太少了,直接从统治阶层那样获得的利益也是太少了,至于后世科举制度的确立,则基本断送了技术从仕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再理会技术发明了。相反西方自“文艺复兴”,人们的技术竞赛就没终止,不停地发明新机器以打败商业竞争对手,人们从技术发明中获得的商业利益太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人人愿意从事技术发明,即使是达・芬奇这样的大艺术家,也都积极从事技术发明就可见一斑。
绝大部分人是趋利的,大部分人能从中获取利益的事业自然人们趋之若鹜,反之则避之不及,科学技术的问题终究还是社会的问题。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术成为唯一显学,儒学有以注经著称于世,知识分子唯有通过经史学习方可达成人生理想,故而对技术之事漠不关心,这是古代中国技术没有发展为科学的主要社会原因。当代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下,提出了培育大国工匠的时代诉求,给予技术知识分以充分的地位和经济回报,相信中国人会为世界的科技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注释:
[1]戴维·史密斯:《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2]WKrohn,DRaven.The Zilsel The sis in the Context of Edgar Zilsel’s Research Programm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0,30(6):925-933.
[3]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页。
[4]左丘明:《国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5]商鞅等:《商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页。
[6]吕不韦:《吕氏春秋》,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16页。
[7]孟轲:《孟子》,何晓明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8]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9]庄周:《庄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1]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82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72页。
[13]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4]墨翟:《墨子》,苏凤捷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姬昌:《易经》,于春海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16]姬昌:《易经》,于春海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1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78页。
[18]墨翟:《墨子》,苏凤捷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林志鹏:《战国诸子评述辑证:以〈庄子·天下〉为主要线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8页。
[20]墨翟:《墨子》,苏凤捷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21]荀况:《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
[22]荀况:《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
[23]戴圣:《礼记》,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24]上海辞书出版社专科辞典编纂出版中心:《老庄名篇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2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
[2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
[29]韩非:《韩非子》,赵沛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0]韩非:《韩非子》,赵沛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1]韩非:《韩非子》,赵沛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2022年1月14日上午,第五届“国际公共艺术奖” 中国-青岛西海岸新区公共艺术方案国际征集活动颁奖典礼暨国际公共艺术论坛系列活动开幕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出席活动并作主旨演讲。党委副书记苗登宇参加活动。
潘鲁生以《中国方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公共艺术策略》为题,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艺术发展现状”“公共艺术发展策略”三个方面作了主旨演讲。
潘鲁生结合近年来的调研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现状。他认为,中国公共艺术在形成聚集效应、构建日常生活美学、带动属地资源盘活、促进历史街区改造、带动人口回流乡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发挥艺术“公共性”,有助于推动艺术与自然、城市、乡村、社区、公众之间互动融合。公共艺术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正是公共艺术设计、建设者、管理者需要不懈努力的主要动因。
潘鲁生把我校公共艺术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与各地调研案例相结合,提出公共艺术系统化发展的七个基础。认为公共艺术发展的要将公共艺术纳入城乡总体规划,持续系统规范发挥文化艺术的建设与提升作用;要夯实政策基础,强化制度保障,进一步强化公共艺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要加强公共艺术的人才培养、教育引领、学术研究、普及推广;要培养良好公共艺术生态,推动艺术服务社会、赋能经济、繁荣文化权责明晰、保障有力的公共艺术发展财政保障机制;要构建公众全面、系统、多元参与及广泛共享的公共艺术发展机制;要营造以创新谋发展的良好氛围,鼓励公共艺术发展融合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结构技术。
此次论坛由国际公共艺术协会(IPA)、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会、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上海大学国际公共艺术研究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共同主办,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研究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产教融合青岛基地承办,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活动邀请到了国内公共艺术领域的杰出研究者和常驻中国的海外公共艺术研究者,分享最新的公共艺术案例研究及研究成果。本活动致力形成公共艺术最新的创作成果,汇聚城市发展新动能和创新活力。旨在聚焦青岛西海岸文化特色与发展诉求,汇聚城市发展新动能和创新活力,研究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和文化内涵,为世界各地区正在开发中的城市提供公共艺术建设范例。
——时尚的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