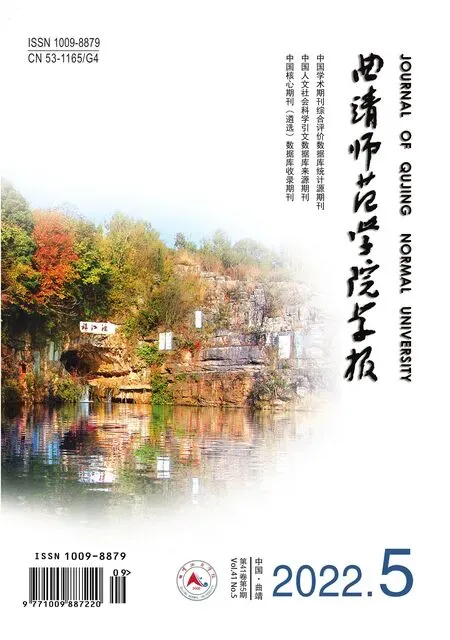杨慎在滇时期的石刻创作及文学特点
李 丹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石刻乃纸质文献之外一种特殊文献,因其载体为岩石,故而保存时间久远,可于之中观得古人之墨迹与文学创作。杨慎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状元及第,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三十余年,逝于戍地。在其在滇时期,遍访西南边疆山川风物,所及之处操觚留题,留下许多石刻。王巍详细整理杨慎于川、贵、滇有石刻89处。[1]杨慎在滇期间的石刻至今流传于世,向世人展示其流寓滇南的行迹与心路历程。
一、杨慎在滇时期的石刻创作
明代入滇有三条路,“自四川马湖府以至云南府属之嵩明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属之会川卫以至云南武定府,是为北路;自广西之田州府至云南之广南府,由广南之广西府,是为南路;其自湖广常德府入贵州镇远府以达云南之曲靖府,是为中路,则今日通行之道也。”[2]杨慎走的是“中路”,一路上皆有记录各地景物与民风之作,自贵州入滇,“经过交水(在今曲靖市)、马龙、杨林、板桥,于嘉靖四年正月底抵达昆明。”[3]在滇期间,杨慎曾至大理、安宁、建水、玉溪等地,于各地留下石刻印记。现据云南各地石刻文献记载,统计得出杨慎在云南的石刻如表1所示。
从杨慎行迹来看,他于嘉靖四年(1525)到达昆明,“二月至永昌,在三月就移寓安宁。”[4]杨慎因年少就颇负盛名,其文章早就传至滇中,虽为谪戍,但受到大多数地方官及文人志士的优待,因而行动相对自由。“丙戌(1526)九月,闻石斋公(杨慎之父)寝疾,疋马间道,十九日至家,石斋公悦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戌所。”[5]杨慎于安宁停留一年余便赴新都探望父亲,因是戴罪之身,虽不舍但无法长留,于1526年7月回到戍所。在次年8月18日,升庵前往弥渡拜访同为蜀人而寓居弥渡的曹太狂,留下《访太狂草堂诗》。“戊子(1528)春,疫殍大作,乃徙居珥海。城疫息,仍居云峰……”[6]在徙居洱海期间,再度拜访曹太狂,先后于1528年10月4日第二次访曹太狂、1528年10月26日第三次访曹太狂,升庵与曹太狂等好友交往之雅事在《杨升庵墨迹碑》中记录下来,三次活动分别为一首诗与两篇跋,清人陈希祖、吴鸿恩、吴郁生、俞陛云、吴鲁敬、赵鹤龄、李锦江等八人跋语,后将这些文字共刻为《杨升庵墨迹碑》,流传至今。升庵在滇期间结识了众多好友,最著名的便是有“杨门六学士”或“杨门七子”之称的张含、王廷表、杨士云、李元阳、胡廷禄、吴懋、唐琦等人,围绕在升庵周围的一批文士游山玩水、互相唱和,对滇云文学及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嘉靖戊子(1528),约同中溪李公为点苍山之游。”[7]同年升庵受李元阳之邀同游点苍山,二人皆留下笔墨,《点苍山记》《瑞鹤观记》也应为这时期之作品。“己丑(1529)八月,寓赵州,闻石斋公讣,奔告巡抚欧阳公子重,疏上,得归襄事。十一月,还滇。”(1)按:丰家骅《杨慎评传》第82页载“嘉靖五年(1529)六月,杨慎知道他父亲杨廷和回新都后生了病,在云南当局的默许下,他单人匹马从小路赶回新都探视父亲……”应为误。经历短暂归蜀奔丧后,嘉靖九年(1530),升庵受中溪之邀重游大理,二人同游至剑川,升庵于沙溪乡兴教寺感慨身世,写下《咏兴教寺海棠诗》,中溪亦和诗一首安慰好友,后人将二诗于1550年刻作《杨升庵李中溪咏兴教寺海棠诗碑》,1855年又重刻。壬辰(1531)正月,云南布政使高公韶邀升庵前往昆明修《云南通志》,升庵前往,但因修纂《通志》避祸于安宁,主要居于遥岑楼,为安宁知州王白庵供升庵居住和讲学而建,今遗址位于安宁市官厢街北边的螳螂川畔,可惜已毁。安宁亦是吏部尚书太子太师杨一清故里,升庵早年向其求教,杨一清与升庵父子有着深厚友谊,在“议大礼”事件中始终站在升庵父子一边,并为升庵在朝中暗施援手,后因此受排挤,终于嘉靖八年(1529)愤懑而逝。升庵于1530年来到安宁,写下《太极山道院记》,1531年来到一清故居,感慨良多,于遥岑楼题《明大学士杨文襄公故里碑》,并题石联“相业四朝称第一,人文六诏羡无双”追思师友,1533年在安宁还留下石刻《重修曹溪寺记》。“癸巳(1533),西游大理诸处,会禺山张公含于霁虹桥,刻诗崖崿以志别。”[8]升庵与保山张含为总角之交,1533年西游大理时与张含相会于距大理不甚远之保山兰津渡,写下《兰津渡诗》,张含亦和诗一首,皆镌刻于霁虹桥边崖壁之上。“甲午(1534),阿迷州(今开远)佥事王公廷表迎,往馆之。”[9]在前往阿迷州期间,据阿迷州不到一百公里的临安府(今建水)当时颇负盛名,升庵于这一年在临安府留下《临安府四乡贤碑记》。而后又返回安宁,安宁学者张素时任湖广兵备道,从长沙岳麓书院摹得禹碑拓片。相传禹碑原碑在湖南衡山(岣嵝山),因而又名岣嵝碑。升庵于1534年见此拓片惊喜不已。因禹碑文字为“蝌蚪文”,多无人知晓,升庵凭借自身才学将其译出,将碑文与译文同刻于安宁法华寺旁岩石上,现今所见安宁温泉摩崖石刻群之《禹碑》乃20世纪30年代重刻。后升庵于“丙申(1536),至(大理)喜洲访给事杨弘山士云,复寓点苍山感通寺之写韵楼”[10]。又于1537年在大理弘圣寺等处留下《禹碑歌》《禹王碑(一)》《禹王碑残石(二)》石刻,可见他对禹碑之喜爱程度,为此,他还专门写过《行书禹碑考证卷》,对研究禹碑和升庵之书法有重要价值。此后,升庵再度还蜀,于1541年返滇,1543年冬于安宁作《宝华阁记》,1543年又领戎役于蜀,1544年四月还戍所,再居大理。“丙午(1546)冬,公与简绍芳游易门……”[11]在玉溪期间,留下《州守赵公遗爱碑记》。“戊申(1548)春,至晋宁,与侍御池南唐公琦游海宝、蟠龙、生佛诸山。”[12]留下《题关将军庙诗碑》,后又至昆明,“庚戌(1550)四月,疏海口。云南台司顾箬溪诸公请公记其事于石。”[13]这便是记录修浚滇池西岸海口之《修浚海口碑记》,自1553年后一直居泸州、新都,1559年返滇,直至1560年去世。除以上提及的石刻之外,杨升庵之其它石刻作品如“不可不饮”摩崖石刻、《杨升庵题石屏歌碑》、杨升庵题“文献名邦”、《关王庙观画壁歌》具体刻立时间已不可考,皆为作者寓居安宁、大理之作。
总之,杨慎在云南操觚留题,歌咏碑竭,留下许多题刻,有的现在已不存,如“金蝉关碑,杨慎书,王褒移金马碧鸡文并题赞十六字,在昆明县西山罗汉壁龙王庙;《碧峣精舍记》碑,杨慎撰,嘉靖二十五年(1526),在昆明西山高峣;‘幽谷’二大字石刻,杨慎书,在昆明县圆通寺。”[14]除昆明外,杨慎在大理、保山、建水、楚雄、玉溪多地都有题刻,还有许多深埋在泥土之中的宝贵石刻,留待后人去发掘。杨慎在云南广受欢迎,至今云南人都亲切的称之为“杨状元”,存世的这些石刻,也向世人展示着杨慎在云南的生活印记,其中不乏诗词、游记,通过这些可考云南明代自然与人文发展状况,对云南地方文化研究大有裨益。

表1 杨慎在云南的石刻统计表(2)按:此统计表根据云南各地之石刻文献统计而得,其中《瑞鹤观记》《关王庙观画壁歌》《点苍山记》《太极山道院记》无准确之碑刻信息,因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录》将四篇文章归入,故而此处也视为石刻作品。
二、杨慎在滇石刻创作内容
杨慎在滇期间内心情感非常复杂,在石刻中也有所体现。作为流寓边疆的文人,升庵在滇时期免不了与大多数流寓文人一样,对前途充满未知与迷惘,但心中仍存对朝廷之希望,因而内心十分矛盾,滇云大地的美景暂时让升庵内心的情感有所寄托,欣赏美景之余更多的是追慕先贤,在对前人历史功绩的追慕中也坚定自身报效国家实现个人价值之志。同时,升庵在滇期间结交不少文士,有的还成为挚友,在与他们的交游酬唱中,升庵内心对于风云涌动的朝政及未来命运的担忧与恐惧也得到淡化,也抚平了内心的创伤。虽身处异乡,但升庵仍秉持儒家之思想,对边疆民生十分关心,重视边疆之教化,为云南的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一)寄情山水,以史明志
作为流寓边疆的文人,杨升庵自一开始便充满了辛酸与无奈,这在他最初流寓滇云大地的诗歌《恩遣戍滇纪行》中写道:“商秋凉风发,吹我出京华。赭衣裹病体,红尘蔽行车。弱姪当门啼,怪我不过家……”[15]诗人在秋风萧瑟中裹着病体出发,门口小儿的啼哭声使诗人更添悲凉离别之感。升庵在南下路途中因见沿途之奇异景物与风俗人情,稀释了内心的痛苦,入滇之后见大理美景便立刻爱上了这片土地,他在石刻《点苍山记》中直抒对大理的喜爱:“余自为翏人,所历道途万有余里,齐鲁楚越之间,号称名山水者无不游,已乃泛洞庭,逾衡庐,出夜郎,道碧鸡而西也,其于山水盖饫闻而厌见矣。及至叶榆之境,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16]从游记中可知,升庵与李元阳在1528年游览了大理的点苍山、龙尾关、宝林寺、鹤顶寺、金相寺、感通寺、玉局寺、帝释寺、无为寺、遗爱寺、金榜寺等地,赞颂所游历之美景,让作者暂时忘却了内心的烦忧。再如其于大理所作之石刻《瑞鹤观记》,游记中除记载瑞鹤观之景外,也记载李元阳修瑞鹤观之缘由,写到(李元阳)曰:“某之修崇塔庙,非为求福也。吾郡山水如此,若非寺观,则远游立览之徒,无从托跡,骚人墨客,安所寓怀?”[17]升庵十分赞同此说,操笔而叹曰:“夫有形胜而无塔庙,则登览之兴不成;有亭榭而无湖山,则绵远之观易索。況祝釐保境,必奠百灵,利物化人,莫先幽赞。……古之君子,思欲倏然远游,却立垢氛之外,常托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见其志。”[18]李元阳认为瑞鹤观景色虽好,自己修建瑞鹤观的初衷在于使登临游览之人于美景有所寄托寓怀,升庵进一步说到塔庙在登览之中对于“兴”的重要性,最终所游之景是为见“志”,这便是托物言志。实际上,升庵的游记作品除了有对滇云风光发自肺腑之喜爱,更借山水风光抚慰自己因政治失意带来的伤痛,亦是借山水明志。
同时,升庵也擅长在写景中借古咏今,常常怀念先贤,以此展现自身内心仍望报效国家之志向。如他在晋宁关将军庙留下《杨升庵旧题关将军庙诗碑》写到:“关锁危岭在何处?猿梯鸟道凌青霞。千年庙貌犹生气,三国英雄此世家。同捷西来武露布,天威南向阵云赊。行客下马一酎酒,候旗风偃寒吹笳。”[19]这首七律写景抒情,以夸张手法描绘关岭之险要,进而写到关将军庙历经千年仍存生气,想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之功绩,转而写到自身作为行旅此处之过客,唯有下马饮酒追溯南征蜀将之功勋。可见,升庵在写景之余,更多的是借景物排遣内心之忧愤,自在滇始,他的心中一直对明王朝、对世宗仍抱有希望与幻想,认为自己终有一日会被召回重新起用,升庵内心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想法一直没有消歇,即使在山水中徜徉,总免不了内心情绪的流露。
(二)交游酬唱,抚慰心灵
杨慎在流寓云南时期结交了不少好友,通过与好友共游山水、交游酬唱,慢慢抚慰了升庵内心之创伤。在升庵的好友中,不可不提及的便是保山张含。张含年长杨慎八岁,二人之间的交往缘于父辈,天启《滇志》载:“公(张志淳)与新都杨文忠公素厚善,……因询公,亦有一子,但日引来见。次日,与俱来,两人年相若,且臭味同也。是为文忠公长子慎、公之子含,终身为金石之交。”[20]二人可谓从总角之交到白首唱和,升庵在滇期间,多次与张含同游唱和,如二人于1533年相约在保山兰津渡各作《兰津渡》诗一首,刻于霁虹桥边崖壁上。升庵作《兰津桥》诗:“织铁悬梯飞步惊,独立缥缈青霄平。腾蛇游雾瘴氛恶,孔雀饮江烟濑清。兰津南渡哀牢固,蒲塞西连诸葛营。中原回首逾万里,怀古思归何限情。”[21]作者于诗句极言兰津渡环境之险峻,再次提及诸葛亮南征之伟绩,明确写道“中原回首”“怀古思归”之情,语句中对中原充满无限留恋与无奈之感。见好友有如此之感,张含亦和《兰津渡诗》:“山形环抱哀牢国,千崖万壑生松风。石路真从汉诸葛,铁柱或传唐鄂公。桥通赤霄俯碧马,江含紫烟浮白龙。渔梁鹊架得有此,绝顶咫尺樊桐宫。”[22]诗句开篇从山势地形描绘兰津渡之险要,历数此地之历史,以夸张手法歌颂此桥之重要功用,有了此桥,即使远在绝顶之樊桐宫也如近在咫尺一般。诗句中看似赞扬兰津渡上霁虹桥之功,实际上也在安慰好友杨升庵虽身处边疆,有朝一日若得类似霁虹桥之桥梁相助,那么实现理想也近在眼前。杨慎在滇期间丝毫不吝惜笔墨赞颂大理地区美景,这与大理名士李元阳有重要关系。作为大理本土人,李元阳十分钦慕升庵的文才,上门拜访年长自己九岁的杨慎,二人之间的情谊也慢慢形成。李元阳十分清楚如何游玩大理及周边景色为最佳,便邀升庵几次同游,到达剑川沙溪镇兴教寺时留下《杨升庵李中溪咏兴教寺海棠诗碑》。升庵作诗:“两树繁华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23]仁甫作诗:“意浓姿淡浣新红,山馆相逢二月中。区别要君重着眼,野桃篱杏烂成丛。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比去年芳。莫言空谷知音少,也有题诗玉署郎。”[24]升庵以花自比,多情却无人珍惜,本应该在京华大放异彩,却流落到这空山路尘之中。仁甫安慰升庵虽为国色名花流落路旁,但却也格外芬芳,莫愁前路无知己,自己愿做升庵的知己。两首诗皆巧妙地借物喻人,为后人留下知音同游之雅趣。
除与云南文人交往外,升庵还与居于云南之同乡亦有交游,如《杨升庵墨迹碑》中升庵墨迹为五言诗一首及两篇跋,诗名为《访太狂草堂诗》:“结宇依仙藉,成桥断俗踪。御风看列子,避雨对茅容。鹤绕三株树,龙蟠五粒松。蜀山归有约,策杖会相逢。”[25]此诗作于1527年8月18日,为杨升庵第一次访曹太狂所写。曹太狂,名学,字行之,号太狂,明代四川眉山人。“嘉靖初,客游滇西,寓点苍之中和山。性豪放,能诗,善草书,尤精于画。随性泼墨,皆有神韵。喜饮,懒于下山,日系钱与壶于驴背,遣入城市沽酒,人识之为曹之驴也。取钱贮酒,复遣而归。尝雪夜坠驴,驴以身覆之不得死。后同杨慎寓蒙化,数年卒。他日驴经其墓,踯躅哀鸣,撞死于侧。”[26]可见曹太狂乃至情至性、旷达随性之人,诗句中亦可见曹太狂之飘逸脱俗,二人也结下再相逢之约。果然,不久以后,升庵于1528年10月4日第二次访曹太狂,诗后之跋写到“去年中秋后三日,与苏子升、李公路、公台、杨齐物访太狂草堂于迷渡,酒边书此。匆匆别来,又复一年。阻兵滞疾,不面之阔久矣,兹徂洱海居,而太狂慧然来枉。余因诵前诗,感岁月之益驶,叹归此之雨阻,为之悁邑相对。是日,五云陈子亦同来,且相期与杨其楹、时尧旬及前四子再往赏梅,太狂效乡先生东坡公,性好栽插,诸经手植,一一茂异,且有竹格重荣之瑞。吾二人者归期当有说乎。归不归且付之无何有之乡,而狂醉放歌则准矣。先书此以识。嘉靖戊子十月四日,升庵书。”[27]此跋记录第一次升庵等五人同访曹太狂之情景,时隔一年再度访太狂,见太狂性好栽插,翠竹茂盛,颇得东坡先生雅趣,与诸友狂醉放歌。嘉靖七年(1528)六月,《明伦大典》完成并颁行天下,“议大礼”基本定性,升庵之父杨廷和被削为平民,次年即逝。升庵深感世宗心意已决,自己回朝已无望,加之世宗频频询问升庵在滇之境况,更担心自身再受迫害,内心惶恐不已,只能通过饮酒作乐、放荡不羁来展示自己已无心朝政,也是对内心深处失落痛苦的掩盖。此后在1528年10月26日,升庵又再度访太狂,碑文记录作者与好友就阅“新淦张震注唐音”所生发之对地名的讨论。可见,升庵在滇期间内心情感是十分复杂的,有痛苦、惧怕、思乡、忧愤等诸多交杂之感,但好在有好友相约陪伴、交友酬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升庵内心的痛苦,抚平了内心的创伤。
(三)关心民生,重视教化

同时,升庵在滇期间,对云南的教育事业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升庵在滇期间广交好友,围绕他产生了一大批滇中文人,促进了云南文学与文化发展,这与升庵对边疆文人的提携与教化密不可分。如其石刻《题梁生霄正苍山奇石屏歌》诗题中的“梁霄正”为人名,“木公曾支派梁霄正携木公的诗集和《木氏宦谱》,请杨升庵批点和编选诗集。”[29]梁霄正应为木公所派之使者。木公虽为边疆少数民族土官,但素仰慕汉族文化,且自身文化修养较高,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他曾与当时云南名士永昌张志淳父子三人、大理李元阳等交往密切,并虚心向他们求教。木公虽未与杨慎谋面,但十分仰慕其才学,二人具体开始交往时间不可考,据现存资料,“在公元一五四三年之前,也就是木公四十七岁,杨升庵五十五岁之前,两人已有较深的来往。”[30]二人之间以诗、文、画为交往媒介,互通才学。可见,升庵对云南少数民族文人并无轻视,而是提携与教化。同样,在石刻中也可见升庵对“教化”之强调,如作于建水的《临安府四乡贤碑记》主要记载选临安府四乡贤之经过与缘由。碑文记载嘉靖十三年(1534),朝廷昭告天下,严格筛选各地乡贤,临安府最终选出四人:“杭州府知府张公隆,南阳府知府邢公干,两淮运司经历、封南溪知县张公文宗,文昌县知县田公荣。”[31]碑文还列举四人之品性、成绩:张隆居丧守礼、治水利民、政绩显赫;刑干赡养族属、为官清廉、人民爱戴;张文宗孝友睦亲、敦行化俗、造福百姓;田荣不媚权贵、救济贫弱、为官正直。并且在最后申明此举的意义:“君子谓是举也,昭则戒违,彰往勖来,是之谓名教,名教之谓政首,政首之谓人纲、人纪。人纪弗纪,曷昭,曷戒,曷勖哉!”[32]升庵认为彰显榜样的力量有助于革除错误之举,表彰往者的目的在于勉励来者,这便是教化的作用,教化为治理政治之首,乃关乎于做人的纲领和立身处世之道。总之,杨慎在滇期间石刻中,明显有着关心民生疾苦一面,同时,他也注重对边疆文人的提携、对边疆人民的教化,可以说,明代云南文学在整个明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与升庵的贡献密不可分,同时,他对边疆民生的关心也使人民至今仍怀念他,云南多地都有为升庵所立之祠便是最好的证明。
三、杨慎石刻的文学特点
杨慎在滇期间的石刻创作反映着他的心路历程,作为流寓边疆的文人,升庵对边疆的影响从石刻中也能窥见一斑。升庵的石刻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展现出其过人之才,且因为他有专门的书论著作,在石刻之中也得见其书法的特点及成就。升庵及其石刻作品于云南而言,已成为一种兼容并蓄之文化符号,象征着中原与边疆和谐发展之美好愿望。
杨慎广为人知的便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从作品中可见升庵之文才与胸怀。升庵石刻作品也可见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特点,升庵擅长游记作品,《点苍山记》《太极山道院记》《瑞鹤观记》《重修曹溪寺记》《宝华阁记》等作品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构思精妙,辞藻华丽丰富,展示出作者石刻作品的独特文学价值。
如升庵于安宁所作之《重修曹溪寺记》:“连然金方,堂川宝地,蔚何名蓝?实曰曹溪。衡六祖之云席,分一勺之法流,邈乎远矣。原斯地也,有异境焉。伏流吐泉,潮信日三,洊至科盈,尘刹罔二。爰有金蟾,号日泉神,卜其出潜,定为潮候。”[33]作者开篇阐明曹溪寺之由来,点名此地有两大特点:一为佛教圣地,历史悠久;一为景致奇异,相传一只金蟾出现时水流而出,隐没时水流低落,故而号称“神泉”。碑文一开始即点名描写对象,加入神化传说,引人入胜。接下来的描写即围绕两个特点展开,如描写景致的句子:“林木翳荟,人境顿隔。旁列洞穴,石宇窅。禅栖影息,时翔岁集,松籁鸟哢。旦衍鱼山之音;风柯月渚,夕湛龙湖之境。禅沐斜埃,陶铸尘憩。赏洽既并,缠疴用弭。”[34]作者认为曹溪寺之景致仿佛仙境一般,树木繁茂、洞穴排列、石屋窅然,宛若世外桃源,每年都有来此禅修打坐、净化身心之客。清晨时,松风与鸟语伴着梵呗歌声隐隐传来;傍晚时,曹溪寺前之水在月色下更显清净澄澈。此地使人沉浸学禅之中,仿佛沐浴沉浸于山林间之薄雾,使人自觉摒弃俗念。将这样的景致赏于目、观于心,俗尘之念断绝,即使一切病痛皆会全消。进而写到曹溪寺之辉煌过往:“相传此宇,在昔盛时,楼殿撑天,梵呗沸地,福田连阡,岁入千钟,香积食指,无虑近万。”[35]昔日曹溪寺殿宇轩昂、佛子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对比眼前所见之残破景象:“而以烽销其记莂,苔露蚀其贞绀,并使日月湮于往劫,名氏坠于初日。惜也!”[36]今日之见确是佛殿因战祸而消、佛寺为风雨剥蚀,不复往日之显赫,实在令人可惜!鉴于此,才有重修曹溪寺之举,升庵于碑文中也简略记载重修之经过,最后说明“升庵子流戍滇阴,遗情系表。斯地斯徒,盖数晨夕,因其恳请,而著兹记,垂后观。俾勿坏。”[37]作者流寓云南,心中对云南充满感情,常到寺里与僧侣徒众相聚,受其之托,故作此文,垂之后世。全文开篇点题,阐明描写对象,描绘景色时加入自身之情感,自然生动,毫无造作之嫌,末尾说明写作缘由,简洁明了。统观全文,作者对此地之喜爱之情始终贯穿其中,加之对景物描绘优美凝练,将曹溪寺之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有机融合,呈现在读者面前。此碑由杨慎撰文,出自状元之手;内容书写的是南疆之名胜;由朱提(昭通)山人肖杶集唐代书法家北海刺史李邕之字镌刻,故称“三绝碑”。
总之,从杨慎在滇期间的石刻创作来看,既有充满情感流动之作,又有辞藻华丽的铺陈之作,显示出升庵石刻文学的多样性。结合升庵的其它石刻来看,升庵石刻中的文学价值就在于升庵作为流寓云南的中原文人,对云南始终充满“他乡即故乡”的亲切之感,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升庵对于云南这片土地包含深情。与同时期李元阳等人的石刻游记作品相比,升庵之石刻作品更显得饱含深情。这与他流寓云南的经历有关,曹溪寺可以让他暂时忘却烦恼,以更纯粹的情感体会山川大地带给他身心的愉悦与平静,因而笔下的文字就更显示作者内心之情感深沉,也使云南山水在升庵笔下呈现别样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