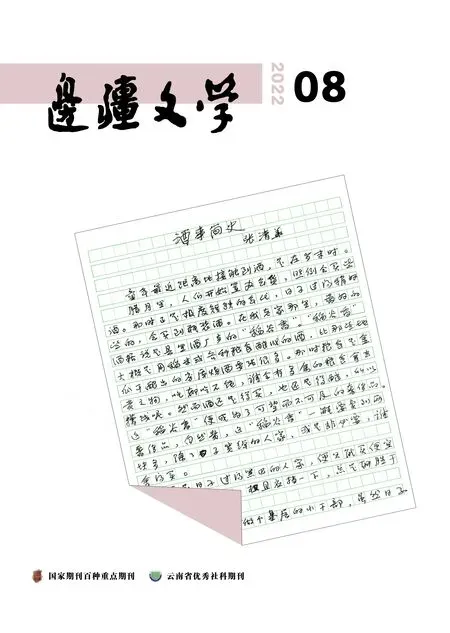永远的月光
漠 月
我的主观感觉是无论古今中外,人世间流行的神话或者传说,至少有一半是阴柔的凄恻的,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在月光下产生的。譬如最著名的中国古代神话嫦娥奔月,鲁迅先生就根据这个神话专意写了小说《奔月》,嫦娥飞进月亮里之后,外出回来的丈夫羿很生气, 一气之下,向着月亮连射三箭,“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 —— 但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损伤”。读到这里,我们放心了。庆幸月亮没有掉下来,依然我行我素地运行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甚至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幸亏月亮没有掉下来,否则,天空多么寂寞,只有星子在闪烁;大地没有月光,漫漫长夜,黑咕隆咚,想想都让我们心惊胆寒;至于吴刚伐桂、玉兔捣药这样与月亮直接相关的神话,更不会产生了。我们知道,在茫茫宇宙中,月亮是一颗死寂的星球,它本身是不会发光的,反射的是太阳的光。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们,却要给予月亮太多关注和青睐,终于形成博大丰盈、长盛不衰的“月亮文化”,大概与“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现象有关,因为它恰好对应了“人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现实,所谓天上人间。
毫无疑问,大诗人大作家都是写月亮写月光的高手。且看唐诗宋词,李白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杜甫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白居易有“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王维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孟浩然有“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张九龄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欧阳修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陆游有“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辛弃疾有“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王安石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鲁迅先生的名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我读到这首诗词的时候,在上世纪70年代,是作为课文被收入中学教材的。既然是课文,要求学生必须背会。我不仅背会了,而且铭记不忘,尤其随着自己年龄的渐长以及思考的深入,这首诗词愈加入脑入心,常常令我感慨不已: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全诗以漫漫长夜为背景,以人们的爱憎为线索,将诸多事件编织在一起,像展开一幅人生晦暗曲折的画卷。诗词的最后一句是,月光如水照缁衣,留给我印象曾经最深刻,也最惊心动魄:清冷如水的月光,悄无声息地照着避难者身上的一袭黑袍。该诗句极具画面感,同时也像一个深刻的梦魇,既凄凉又恐惧,很容易令人产生诸多不堪的联想。有时候,我夜间回家很晚,走在月光下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就会忍不住地想起这句诗来,然后开始胡思乱想,以至头皮发麻,身后凉飕飕的,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都变得不那么真实了。从小我就听大人们讲过,月亮是有魂魄的,每逢夜深人静,月亮的魂魄就在大地上走来走去。月亮的魂魄,也许就是月光吧,我曾经这样想。所谓百鬼夜行,据说经常早出晚归走夜路的人,迟早要遇上鬼。我承认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完全扭曲了鲁迅先生的原意,风马牛不相及,不仅很庸俗,也很浅薄,客观上消解了这首诗词深刻的思想性和尖锐的批判性,实不可取。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越是克制自己不去想,越是克制不住地要想。这和我们小时候坐在大人身边听鬼故事一样,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是相同的道理。
作为一个牧人之子,我有过多年在草原和大漠生活的经历。草原和大漠的月光,永远是那么坦荡,那么清洁,那么宁静,如果真的是一层铺满大地的银子,它的纯净度都能够达到百分之百。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在那么多年的牧人生涯里,我居然对草原和大漠的月光熟视无睹,即便是后来的文学创作,我也没有给予它应有的关注和更多描述。这似乎是一种背叛,不可饶恕。好在,我毫不犹豫地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漠月,也算是一种补偿和安慰吧。
后来,我读到了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对这样一部描写北方草原的作品,我是认认真真地读过好几遍的,间隔的时间也比较长。我甚至刻意地坐在月光下读过《黑骏马》,是在一个叫马儿庄的乡村学校支教的时候。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边缘的这个乡村,农牧交集,村人既是农民又是牧人,既种庄稼又放羊,他们居住相对分散,特点是地广人稀。每逢夜深人静,羊不咩、鸡不鸣,狗不吠,似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停止思考、进入了梦乡,村庄便笼罩在一片大神秘中。一个周末的夜晚,学生和老师都走光了,校园里更是安静异常。于是,我坐在供我暂时栖居的宿舍屋檐下的台阶上,在亮如白昼却没有一丝热度的月光下,捧读《黑骏马》。我的眼前再一次展开这样经久不息的画面:偏僻的遥远的乌珠穆沁草地深处,月光下的伯勒根河在默默流淌,诺盖淖尔湖平静如镜;一匹名叫钢嘎哈拉的马驹,从茂密的草丛里拔地而起,它黑缎子一样的毛色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后来,它终于长大了,像风一样在草原上驰骋,却始终陪伴着白发苍苍的慈祥的老奶奶和美丽单纯的草原姑娘索米娅;后来,白音宝力格出现了,他和索米娅在苍凉凄婉的《钢嘎哈拉》古歌中,情不自禁地演绎了一场悲欢离合、刻骨铭心的人间之爱。“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那山梁;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这又注定是一个悲剧的结尾,老奶奶去世了,索米娅成为别人的妻子;白音宝力格无奈地告别索米娅,满怀怅然失落的心情和无尽的思念,开始走向新的人生。
阿来《月光下的银匠》,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小说。首先,这部小说的名字就非常诗意,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银子反射着月光,冷清而魔幻:在故乡河谷,每当满月升起,人们就在说,听,银匠又在工作了。满月满满地升上天空,朦胧的光芒使河谷更加空旷,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而又遥远。这时,你就听吧,月光里,或是月亮上就传来了银匠锻打银子的声音……
多年前,我读过鲍尔吉·原野的《月光手帕》,很短的一篇散文,不到一千字,同样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释怀。我称它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小姑娘行走间突然蹲下身去,要拣一样东西,却落空了;这是从窗户投到楼梯上的一小片月光,被小姑娘误以为是一方奶白色的手帕,结果是她的手指只触到冰凉的水泥地,而不是手帕。小姑娘的举动里充满生机,心里盛着美,不然不会把月光误作手帕。作家因此感慨不已:“多么喜欢她把这块手帕捡起来,抖一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替月光遗憾,它辜负了小姑娘轻巧的半蹲拣手帕的样子。”读罢这篇散文,我似乎还看见小姑娘那害羞的模样,然后匆匆离开,生怕被别人看见她的举动而难为情。我心想:怎么可能呢?可爱的小姑娘,正因为你的纯净和善良,月光才与你开了一个小小的善意的玩笑。原野的另一篇散文《在碗白的月光下把手都伸出来》,涉及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虽然写得冷静而理性,我却觉得月光下总有丝丝血光在闪烁,让人心情有些沉重。
笔者在文学期刊做编辑二十余年,阅读和经手发表的作品难以计数,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散文随笔,其中描写月光的作品很多,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月光与村庄紧密联系起来,借此表达对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怀念,诗意而坦诚地呈现乡愁和家园意识,留给读者的印象也较为深刻。譬如:“月光在世界上是最美的,苹果树在村子里是最美的,月光照在苹果树上,就是美与美的相遇,就是极致与无限的碰撞,就是世界上大美之物的诞生。甚至也可以说,如果月光是雌性,苹果树当然就是雄性的,那月光下的苹果园,就是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家,像一个优秀的男人和一个漂亮的女人走在一起,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叶梓《月光下的苹果树》)“娘突然忍不住地哭了。在银色的月光下,在空阔的院子里,娘的哭声是那么细小,那么微弱。秋风乍起,淹没了娘的哭声。恰在此时,我闻到了一股玉米的味儿,朴素,清爽,香甜。再看洒遍院子的月光,似乎也被玉米的味道浸润了。玉米味的月光,真好!”(胡静《玉米味的月光》)……
张贤亮的《习惯死亡》,最早出版于1989年1月,首印十万册,很快告罄,多次再版,可见其影响之大。这是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所有文学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将一个心灵遭受重创的知识分子孤独、苦闷和无望的精神世界,叙写得细微而生动。作家一反惯用的传统表现手法,在艺术上刻意求新,使本书颇具特色,诗一样的语言,比比皆是的格言和警句;当然,还有大量对月亮和月光的描写,照例不乏深邃,甚至惊心动魄。小说开篇不久,就写到了月亮和月光:
一瞬间,月亮便跃到小树林上面。橙色的月亮好大好大。许多年后他都能一直看见那轮月亮。那样的月亮和那样的月光,宇宙间只能出现一次。后来他看到的所有的月亮,都不过是那轮圆月的复制品。
作品的中间部分,又多次出现对月光的描写:
这夜月光非常亮,和枪毙人那天的阳光一样。原来这间房里还睡着许多人,月光一个个地照亮他们的面孔。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泥地上。他们睡着了但却不闭眼睛,不过显然他们没有看见我。他们睡觉的样子既别扭又安详。
我想这一切大概都是因为月光太亮。明亮的月光下死人和活人都凝结在地上。
我想动动手拂去盖在身上的月光,但还是怎么也抬不起胳膊。这时我的半边脸颊贴到了冰凉的土地,我看见月光和我徐徐地穿进泥土的孔隙。
而将近二十万字的小说,则直接用月光结尾:
一支、两支、三支,我依次吹灭蜡烛,高山上的月光顿时从窗外泻进来。
月光,又见到月光。
我盘腿坐在炕上,闭起眼睛。我陡然看见她在月光下非常美丽和年轻。
……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关于月光的文字,不胜枚举。如果有谁对此感兴趣,将这样的文字段落摘录下来,完全能够编著一部非常厚重的《月光描写大全》。但是,至今我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书籍出现,也许是有的,只是我孤陋寡闻,没有发现罢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有了,反受其累。当下的人们早已经淡忘了月光,月亮不再成为人们寄思予情之物。尤其在繁华的都市,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红尘滚滚,人们都在忙碌着,出门后脚步匆匆,哪里还顾得上抬头仰望天空,即便是有月亮的夜晚。那么,忙忙碌碌、脚步匆匆的人们,到底去了哪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确认,在当下扮演着社会主体角色的资本面前,曾经高尚的劳动者成为弱势群体,人们都变成了被资本奴役的追随者和攀附者,物质利益正在取代精神价值,“月亮”也好,“月光”也罢,只能黯然退场。我不明白这是月亮的悲哀,还是人类的悲哀。
接下来,再讲一个艺术方面的传说,同样与月光有关的传说。
因为这个传说与贝多芬密切相关,被不少人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因为这篇文章的需要,我也要将它写进去。请允许我根据他人的文章,把这个传说再复述一遍:这是一个温暖的春夜,贝多芬突然听见有人弹奏钢琴曲,而且是他的作品,遗憾的是,总有一个音阶被弹错了。贝多芬循着钢琴声而去,走进一间小屋,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正在神情专注地弹琴,并没有发现他。后来,贝多芬还是忍不住地打断了琴声,开始耐心地给她指导,纠正被她弹错的音阶。这时,他才发现这个弹钢琴的少女竟然是个盲人。银色的月光,如水的月光,静悄悄地从窗里流淌进房间,洒在少女身上,把少女的模样勾勒得如诗如画。贝多芬非常感动,于是在钢琴上即兴弹奏了一支曲子,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著名钢琴曲《月光》。也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且具有浪漫的色彩。我却觉得它更应该是一个凄恻的传说,浪漫似乎无从谈起。因为这个少女是一个盲人,她永远看不见自己有多么美丽、月光有多么宁静。只有音乐对这个少女具备真正的实际的意义,因为她有和正常人一样的听力,她更应该而且能够在音乐的旋律里想象月光之宁静,以及自身之美丽。正因为它是一个凄恻的传说,我便牢牢地记住了,至今难以忘怀。
还有一种说法,把《月光》这首奏鸣曲与贝多芬的失恋联系在起来,此曲是献给他的恋人的。贝多芬曾经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的恋人,说“她爱我,我也爱她”;后来,他的恋人却移情别恋,并且和别人结婚。《月光》的第一乐章,表达的是“沉痛的悲哀”;作家罗曼·罗兰说,“幻想维持得不久,奏鸣曲里的痛苦和悲愤已经多于爱情了”。也有人反驳,说《月光》写失恋的痛苦,与事实不符。究竟哪种说法正确,似乎没有定论。但是,不管怎样,音乐温暖了我们,我们爱上了音乐,却是真的,确凿无疑,无论它是热情的,还是凄恻的;是柔曼的,还是激烈的;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贝多芬的《月光》,无疑能够唤起我们许多的渴望和热情,乃至丰富的想象。倾听贝多芬的音乐,有如我们渊面黑暗之时,神的魂灵运行在水面上……
无论什么样的传说,或美丽,或凄恻,但毕竟只是传说,它的真实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质疑。但当我们知道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的民间叙述文体时,对它的质疑便显得毫无意义。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然后保持沉默。后来,我也通过翻阅相关的资料才知道,贝多芬的这首G小调钢琴奏鸣曲最初并没有名字,为其取名为《月光》的是一位叫雷尔斯达布的诗人。诗人在日内瓦湖月夜泛舟,看到湖面上月光如银,分外美妙,联系起贝多芬的这首G小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觉得乐曲和月光一起在湖面上轻轻荡漾,是那样的协调,便用了《月光》这个曲名。那么,那个贝多芬为盲女即兴弹琴的传说真的不存在,是子虚乌有,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有时候,不真实的幻影,比真实的存在更具有动人的魅力,更具有长久的价值。在我心中,贝多芬在盲女的陪伴下,即兴弹奏钢琴曲的传说,要比诗人雷尔斯达布在日内瓦湖上泛舟而灵感一动想到曲名,而美妙得多,也长久得多,尽管都是在月光下发生的。我相信,尽管后者是真实的,前者是一个传说,而人们宁愿相信前者。多少年来,知道后者的人们并不多。大多数人明明知道前者是通过想象诞生的传说,却依然相信着。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仅仅是真实的,并不见得就是艺术。
最后,还是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海子的《月光》吧:
今夜美丽的月光,你看多好!
照着月光
饮水和盐的马
和声音
今夜美丽的月光 你看多美丽
羊群中 生命和死亡宁静的声音
我在倾听!
这是一支大地和水的歌谣,月光!
不要说 你是灯中之灯,月光!
不要说心中有一个地方
那是我一直不敢梦见的地方
不要问 桃子对桃花的珍藏
不要问 打麦大地 处女 桂花和村镇
今夜美丽的月光 你看多好!
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
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
月光照着月光 月光在普照
今夜美丽的月光合在一起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