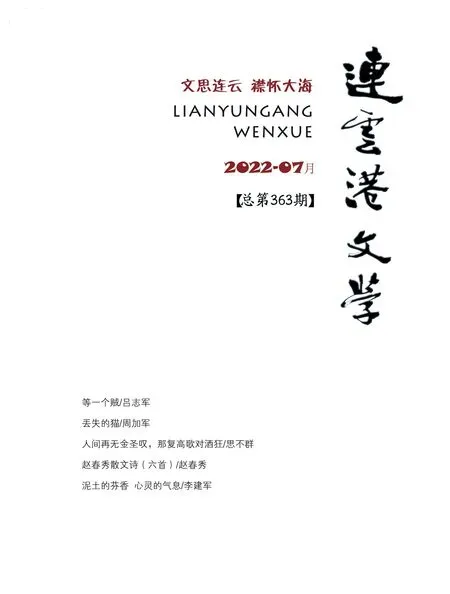隼眦看无物
方挺
如同疫情的伤痛,心灵的余震远比地震本身更久远、可怕和致命。好在人心没有平复不了的创伤。当我们看到永无止息地在空中翱翔的隼,双翅静止,却一个俯冲扑来让人躲闪不及。终是人类赋予它的品性:勇猛、刚毅……
一
我至今无法分清“鹰”和“隼”的区别。以前,当他一次次以“专家”的身份从相机里找出他拍的各种各样隼的照片,开始不厌其烦地试图再给我进行重复了N 次的科普时,我不耐烦了。和大多数女生一样,“随便问问干吗认真?分不分清有关系呢?”这时,他刚刚还因兴味十足而不断开合的嘴唇突然静止如隼的翅膀,两唇之间留下一条窄窄的缝隙。只是停留几秒,旋即细缝也消失了,代之嘴角迅速上扬,右手如隼的俯冲迅疾地放下相机,顺势揽我入怀。而我,却莫名地置气地推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推开他?我,一名年轻护士,总是将最好的耐心给了陌生的病人,反而在爱人面前毫无耐心,这是一种习惯使然,还是我真正的本性暴露?
我当时无法弄明白这些,就像我那时永远弄不清鹰和隼的区别。但是我分明看到了它。在灰白的天幕,先是出现一个小小的墨点,渐渐上下左右移动,越来越大,转眼间已经填满瞳孔。这时,我高昂的头颅被它牵引着不停转动,同时不由自主跟着移动的还有身子和双脚。它在黑色戈壁和白色雪峰之间滑行,翅膀平展,竟然纹丝不动,却能像黑色闪电快速对黑白世界进行着切割,天空像乳液般被划开旋即弥合。有时,它黑色的身子被同样黑色的山石所隐没,再出现时,它已经在白雪背景中凸显,而这个位置,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方位和另外一种距离。这只我无法分清是鹰是隼的鸟,总是永无止息地在空中翱翔。我忽然担心,鸟像人一样,也总有累的时候啊!那么多个夜里,我始终凝望着它,却从没见它落在哪块石头哪根树枝上作片刻休息。难道,它是神话里的“无足鸟”?
鸟类会不会咳嗽?这是个新问题,我同样无法知晓。我之前从没有问过他,之后也再不会了。但我分明听到了咳嗽,也幸亏那样猛烈的咳嗽,一下子将我从无法醒来的飞翔的梦魇中挣脱,就像濒临淹死时恰有一双手拉住你,我捡回一条命似的在黑暗中笑了,也学着他嘴角上场的样子。
其实咳嗽未必猛烈,只是在疫情时代,在我们这些白衣大褂面前,连接着咳嗽的听觉神经异常敏锐。不需要培训,我已能从任何咳嗽所引发的气流冲击喉咙的声音里分辨出原因及程度,室友不过是感冒了。但这也足以让周围的人退避三舍。我翻过扣在床头的手机,凌晨五点十分。几声咳嗽之后,我听到隔壁她趿着拖鞋下床走路的声音、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紧接着是卫生间水龙头哗哗的水流声,甚至能清晰听到她小便的声音、撕厕纸的声音、回到床上盖被子的声音。我对声音太过于敏感,然而奇怪的是,这么多天以来,那一整夜一整夜的梦却从来没有任何声音,寒冷裹挟住我整个身体,隼的翅膀无数次划过空气,它们始终像无声的黑白电影。
睡是睡不着了,但又懒得起来,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原来在嘴角上扬的过程中,脸上已是一片冰冷的水渍。
早晨七点,我起床,只是脚掌着地那一秒钟的突然决定,我拿起手机给领导发信息请了十天的假。我要远行,到他去过的藏区,看他看过的“隼”。
二
经由成都进藏,到他拍照的地方,得经过北川。租好车,出发。
我不了解成都男人,是不是都那么啰唆。刚一上车,这个小个子成都男人就开始介绍风景名胜、风味小吃,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最后还表现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姑娘,你要去的那个山口风大得很,气温可不比咱这儿,我看你没带多少行李,到时怕是吃不消啊!”“亏你遇上了我哟,跑车的没几个人愿意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路不好走不说,回来还得放空。那里又不是景区,本就没人去,要有就是喜欢登山的,也是成群结队地去,我从没见过女孩子独自一个人去呢。要说好玩的地方多着呢,要不你好好想想?”
大概等了一两分钟没听到我的回答,小个子将头从驾驶室座椅中间扭向后排,却迎上了一双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以前他对我说过,隼与鹰最大的区别之一是眼睛,隼科鸟类的眼睛虹膜颜色较深,几乎分不清虹膜和瞳孔,也有眶上嵴突出的,看上去非常凶。我想,我当时就是这样一双眼睛,不然的话,小个子也不会立刻收回他的视线,迅速点火,脚上已轰的一声踩上油门,上了马路。
车上只两个人,我们谁也没说话。过了几分钟,大概他觉得这样一言不发有点尴尬,或者不符合成都人热情的待客之道,开始找我说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的就是咱四川。姑娘,看你是学生吧?你听李白怎么说的,‘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等到上了真正的盘山路,你可得抓好坐稳了。”我拍了拍他的座椅后背,这回他没有扭过头来看我,而是往车内后视镜瞅了瞅,大概又看到了我那双隼眼,便闭口不说话了。除了发动机的声音,车内又恢复了我要的安静,这样,我就可以将头靠在椅背上,眼睛茫然地看着窗外。窗外,有树木、村庄、山峦、河流,而这一切并不与我相关,我也并没有看见它们,我的眼中空洞无物,此刻,我需要并享受着这样的茫然。
“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是喜是悲,尘缘注定,不折磨自己……”突然,音乐声严重骚扰到我。我开始拍打驾驶室座椅后背,他的眼睛瞟向车内的后视镜,似乎不甘地说,“海来阿木的《点歌的人》,知道他哪里人吗?咱四川凉山州的,最近可火了。”他还要说,我加重拍打座椅,他只得关掉了音乐,将眼睛收回到方向盘,不再看后视镜。在后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果然再没有说一句话。我将脸颊倚在车窗玻璃上,一动不动。已是春天,但山区还是透出一股寒意,我贴着玻璃的脸颊冷冰冰的,其实,冰冷有什么不好?最起码从医学上讲,冰冷可以镇痛,我要的正是这些啊。
车子很干净,这是我看了一眼就决定租下的原因,它将伴我未来几天,做医生的是不是多少都有些精神洁癖?最起码我觉得他是这样的。我怎么突然又冒出了他?没有声音,我可以忽略车内还有人,不打开车窗,便是小小的密闭空间。突然一阵风从前方将我的头发吹起,紧接着看到他夹香烟的左手搭在摇开的车窗上。我使劲拍打着车门,他猛吸了一口,“姑娘,我得抽根烟提提神,对我好,对你也好,你说是不是?”我懒得说话,继续拍打着车门。他又猛吸了一口,将大半截香烟扔了出去,摇上了车窗。
山路果然不好走,车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动不动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再也没办法放松地将脸紧贴在车窗上了。这是一段盘山路,我坐在后面,看不清前面的路,只是透过车后玻璃看到山涧隐隐,已经看不到山脚,车子爬坡已经不低了。好不容易到了一段平坦的路,速度刚上来,突然一个刹车,我的脑袋差点撞到椅背。这时我看到路旁站着一个中年男子朝着我们的车招手,马路边还坐着一男一女,他们肩上都是大大的旅行包,手上各有一根旅行手杖。小个子回过头,“喏,他们几个想必是登山的,顺路,载他们一程,少收你一半车费,怎么样?”我没好气地猛烈拍打着他的座椅,他的眼睛躲开我的隼眼,旋即打开车窗向外不耐烦地摆着手臂。
三
这次司机不得不刹车,因为又有一个人站在马路中间,拿着小旗子的双手由两侧到头顶来回挥动。这已是我们已经翻过几座大山之后的事了,时间已经傍晚。怕又是要搭车的,小个子已充分领略了我的隼眼,也不停车,边按喇叭边将左手伸出窗外摆手。哪知对方是个不怕死的家伙,居然趴上了车头。
“喂喂,停!停!赶紧悬崖勒马,要是越雷池半步,那是险象环生十万火急危如累卵啦。就在刚才,霎那就让人明白什么叫旦夕祸福不测风云,好在那人身手敏捷,突如其来的飞沙走石天崩地裂,他在那生死攸关千钧一发之际跳了车,总算履险蹈危死里逃生。照理说,车子开到那里恰恰山体塌方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吧,我带的旅游车跟那台私家车紧随其后间不容发啊,那么我们一车人也算大难不死,只是到现在还泥船渡河心有余悸。这后面说不准还有滚石教人防不胜防,依我说回吧,回吧!”透过车窗,那人手上三角旗分明写着“大凉山旅游”,再看看他身后不远处就是迤逦的村寨,这不明摆着拉客吗?司机正欲问什么,我死命拍打座椅。小个子已经习惯了这种沟通方式,于是拼命按响喇叭。在“小旗子”刚一让开便一脚油门窜出去,他的声音赶在车窗关严之前飘了进来,“唉,这年头!你非要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看是不撞南墙心不死啊!”
果然行不多时,我们就看到响着警报器的拖车拖着砸扁的轿车迎面驶过。俄而有警察正在指挥车辆掉头。透过车窗,能看到远处那片赭黄色,像一大瓶颜料不小心泼洒在一幅清丽的油画中,将缠绕在青山上的飘带弄污好几块。司机终于开口了,估计憋坏了,这次也不看我,只管骂娘,骂得忿忿然。我也想骂,但要骂绝不像他那样,我要骂一定得骂得歇斯底里。我一阵拳头擂在椅背上,结果山路太窄,一边峭壁一边深涧,正掉头间,突然“哐”的一声,司机下车检查,果然,底盘卡上了一块石头,那时天色已经暗了。好不容易移走,幸好能开。“你看,得先把今天的车费给我结了,修车的钱你看咋办?”
折回村寨,天已黑透,小个子只管寻找修理厂。好容易一棵大树上亮出汽车修理的指示牌,闪着鬼火似的红光。跟着道路指示,很快循进寨的岔路找到大铁门,按了半天喇叭没反应,借着灯光看到门上留有电话。十几分钟后,“红马夹”骑着电瓶车来了,一看到是我们他呵呵笑了。我张大眼睛,这不是那个谁吗?导游闪变修理工,打开院门,我并没有下车,任由小个子与他交涉。红马夹蹲下身又站起来,小个子打开车门,他的声音便飘了进来。“你可算找对了人,这就叫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给我一天,保准让你的爱车起死回生完璧归赵,你只管高枕无忧吧。”我心想,简直是信口雌黄鬼话连篇。正要下车,小个子又把车门关上与红马夹说着什么。我从旁边下车,红马夹倒也灵活,立马跑到车后打开后备厢提起我的行李。“姑娘,我先带你住店,保准环境清幽一尘不染百里挑一啊,我就不带你去灯红酒绿花柳繁华之地了。”他的脸上现出讨好般的殷勤,回头对小个子,“我自有安排。稍等片刻少安勿躁啊!”。他的话总是不着调,但事故的事他没骗我,再说我也更不想在这里等着修车,那时候又不知会多出多少口舌,而我此行本不必说一句话,更不想说。我还是跟着他。
“姑娘啊,依我说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听说过世间之事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吧,你不能说话,但……”那时一轮明月照着他的身影,他就像每次回家时爸爸拖着我的行李箱背着我的旅行包走在前面。还没等他说完,我抢白道:“谁说我不能说话了?”我几个大步抢到他前面头也不回。“王燕,燕儿。”离院子还有几百步,他就大声嚷嚷起来。旋即,一个三十多岁穿着彝族服饰的女人跑着迎了下来,热情地要拿我手上的小包。我没给,她尴尬地笑笑。他进院放下行李便走,一面招呼老板给客人做点吃的,一面回头告诉我老板人挺好的。在城里也是,出租车跟酒店合起来做生意,我多个心眼就是。
女人将我送上二楼。门廊上亮着几盏黄色的灯,因与灰黑色的建筑不甚协调而显得突出,然而却能在清冷中显出温暖,见到这样的光,我的身体不由松垮下来。进门,墙壁、地面和房顶都是木料装饰,同样的黄色灯光,刹那间疲惫如千军万马向我袭来,“姑娘,楼上就你一个人住,我住楼下,有事打电话。”在女人摆好行李箱轻轻关门的那一刻,我立马将身子往后一倒,将身体在白色被子上摆出一个“大”字。真舒服啊,我太需要一张床了。还未躺稳,木门上响起笃笃的敲门声。坐起,迎接到一张友善的笑脸,她将背包从身下卸下,“你的包。”我刚躺下,她又进来了,打开衣柜,从里面拿出一套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桌子上铺展开又叠好。“我做的,记得明天穿上,拍几张美美的照片。”她还向我做了个表情。而我只是站在门口,不耐烦地冷冷说声谢谢,估计她是感受到了,不无讨好又不无卑微地笑了笑为我关上门,我重将门锁锁上。我刚洗完澡躺进被窝,又听到敲门声,我懒得起床,不耐烦地说睡了,门外传出女人的声音说别饿着,让我尝尝她做的彝族美食连渣菜,我说不吃了,一声谢谢之后许久,我才听到鞋子触着楼梯的声音。
这一夜,竟然是我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没有梦到隼。
四
真是美美的一觉。早晨,我被窗外不知名的鸟儿吵醒,睁眼,太阳已经在蓝绿相间的窗帘上打出一片亮色。开门,一张纸条从门缝翩然落下。“姑娘,身体要紧,出门在外也要好好吃饭,就当这里是家,每顿咱们一起吃。”字不漂亮,但却认真。这时,我才得以认真地打量起这个院子,昨晚原本太黑又太累。这是普通的两层覆着灰瓦的二层小楼,上下各三间,由民宅改成的民宿。前面一方小小的院子,正中一棵大树倒也蓊郁,枝叶在我眼前发出青翠的绿来。远处,山峦层层叠叠由绿而黛。树下,仍旧是那个女人,面前石桌上摆满红红绿绿的布料。她这时已经看到我了,招手呼我下楼。等到我下来,石桌上的布料已经推在一旁的石凳上,几只碗碟摆上石桌。我照旧没说话,心想赶紧到修理厂找到小个子出发。王燕热情地招呼着我,问我是要到哪去,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怕她问太多,我只象征性地吃几口。临走,“饭钱挂我账上。”她一下子收住笑脸,“姑娘,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是也要吃饭吗?”我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溜烟跑出门。
修理厂大门紧闭,透过铁门,车子已经不在了,赶紧打电话。拨通,原来车子已经连夜修好,小个子在车上躺了一夜,天刚亮就回去了。我顿时火冒三丈,让他马上回来。“小姑娘莫生气噻,怒火中烧七窍生烟咬牙切齿,你说哪一个不是在伤自己身体?再说了,我这里也事关重大燃眉之急刻不容缓,等我塌方抢险完了,那时路也通天彻地畅通无阻,再帮你找台车还不容易,保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包在我身上,你安心住两天,你看看春和景明惠风和畅绿肥红瘦也不错,何不心旷神怡一下呢?还是那句,塞翁……”我啪地挂了电话。我没说话,是因为已经落下泪来,突然间,我无比想他,而这个“无比”无人能晓,包括他。我抬头,蓝天白云在群山簇拥下,没有鹰,更没有隼。
一整天我像没头的苍蝇四处瞎逛,期间给他打过两个电话,他在现场没法回来,再说回来也不济事。等到晚上,我实在等不及了,他说让我到寨子中心广场找他。那个地方白天我去过,是连通寨子四周的一块平整场地,在旅游季节起到集散中心的作用,因此,四周便是鳞次栉比的卖特产的商铺,只是绝少游客。很容易便找到他。他已经换了一身彝族男子的行头,面前一堆山货,正借着店面铺展出来的灯光叫卖呢,周围三三两两围着些同样是彝族装扮的人。他那也不是在叫卖,而是在弹着月琴,也不对着人群,而是对着面前三脚架上的手机。等我走近,他已经弹完了,口中振振有词,“欣赏完咱彝族的月琴,现在是粉丝福利时间。这是大凉山正宗的崖鹰鸡,身形高大,形象崖鹰,生长于海拔1800-2800 米高寒多变气候环境,听说过鹰拿燕雀鹰击长空吧,肉质上乘味道鲜美,尝试过后保准让人垂涎三尺爱不释手。还有这是美姑山羊,听听这名字,两种山羊杂交,凡经杂交那就改头换面截然不同了……”我看不下去,说心里话,我对他这种钻营钻到钱眼里的人打心眼里鄙视,这大山里少数民族多么纯朴的最后一片净土,迟早会让他这种人给糟蹋了。被拉客不说,私自放走司机,若不是他,我也不至于陷在这地方动弹不得。还有,先不说他直播带货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夸大其词,光他公然在商店门口抢人家生意这一点就不地道,我竟生出一种凛然的大义来。他显然没有注意到我已走到手机旁,那时他正一手提着黑苦荞一手提着红辣椒,而我已经去取手机。他慌了,“亲爱的铁粉们,不好意思出了点状况,咱们明天继续,记得关注加红心哟。”一边仍不忘把货物举在摄像头前,而手机与他像连着一根线,我牵着他来回转,让我觉得有点好笑。匆匆与网友打完招呼,他一把夺回手机关掉直播。“搞撒子噻,好不容易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积铢累寸,几万个粉丝……”我哪里会听他哆嗦,“会不会正常说话,你是成语词典吗?赶紧地,我要车。”我心中除了隼,还有冥冥中引领我来看隼的他,再稀罕的山水景致和风土人情我都看不到,我的眼中纯粹到装不下任何多余的东西。“多了一个字,我姓陈,都叫我陈词典。要车,那也要等路通了噻。”
正在掰扯中,突然一个彝族男子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不容分说拉着就走,“陈词典,可找到你了,家里的羊嗷嗷乱叫,这会儿一只羊已经倒在圈里口吐白沫了,赶快赶快,一家几口就止着它呢!”杨词典抽身返回来,居然在货堆里面捞出一只药箱。“你看,这一摊东西,”那人噘噘嘴,他便看向我,“姑娘,有劳你了,我马上回来。”他又塞给我一件外套,“山里不比城里,穿上,别冻着。回头让你尝尝美姑山羊。”我才不穿呢,宁愿冻着。心里愤愤不平,这算哪门子事?我找他解决我的问题,反倒替他解决问题,成了看货的。不过话说回来,他就这么放心?在我扔下衣服时,那只醒目的红色袖套露出来,上面是白色的三个字“志愿者”。
五
“姑娘,我知道你有心事?跟姐姐说说噻。”第二天,王燕非要拉着我到广场去跳篝火晚会。我知道她是一副热心肠,可我哪来的心情?正当大家手拉着手载歌载舞时,我一个人走到僻静处坐下,只当一个纯粹的局外人远远地看着,热闹与我无关。她发现我不见了,很快找到我。“问那么多干吗?烦不烦啊?能不能让我静静?”我居然朝她发起火来,简直是哆嗦,是暴跳如雷,好像要把积攒我胸中一个多月的悲哀都要通过这一声给吼出来。她显然被我吓着了,好在篝火晚会那边仍然在欢声笑语。我立刻就后悔起来,脸上洒着泪水,深深地弯下腰说了声对不起,然后飞奔着逃走了。
回到客栈,院子里突然热闹起来。客栈远离村寨中心,除了我再无其他客人,显得格外安静。果然,大树下石桌边坐着几个人,他们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立刻将这个偏远的院子装点成家的感觉,我油然想起另一个农村宅子里的温暖。他们二男一女,看得出来比我年龄要大得多,都是三四十岁的模样。而我大学毕业才两年,本来正是追逐自己的理想,散发青春生命力的时候,因为还没有经历过太多风霜雨雪的淬炼。但是就在上个月,我不是完成了人生的转变了吗?我知道,哪怕就一个月前,我和他一起,也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而现在,眼前的几个人倒显得比我年轻了。
“姑娘,今天刚下来的新茶,来一杯?他们几个是去登山的,听说也要经过你说的那个什么山口,要不要一起结个伴?”王燕端着几只茶杯,显然并没有把傍晚的事情放在心中。“啊——那个——”我张着嘴巴不知如何回答。以前我是多么害怕一个人呀,可是现在……“王燕,我那杯不要茶叶,喝了夜里睡不着。”那边有人向王燕招手,她端起茶杯,总算为我解了围。在我经过他们时,我听到一个男的在说,“这个茶叶好呀,碧油油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大地震那年,比现在迟上一两个月,茶叶全下来了。那时我从成都带车队拉救灾物资,连续拉了好几天。茶叶也不用泡,困的时候嚼上一把,比什么都提神。”还没等王燕回答,另一个男的也说,“巧了,那年我俩也在。那时我正在办退伍,你说我一个当兵的跑来抗震救灾那是应该的,她一名精神科医生,也跑来救什么灾?没想到我俩就那么认识了,后来还结了婚。你说,世上的事谁想得到呢?哎,说不准那时我们也见过呢!”“我精神科医生怎么了?除了治病救人,当人们突然面临那样的灾难,你觉得我不重要吗?十几年了,活着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也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到汶川走的就是这条路,那时时不时还有余震,你说怎么着?运输物资的车队刚过去,我就听到身后传来隐隐的雷声,塌方。从后视镜一眼就能看到后面升起一阵烟雾,离车队大概也就一两里地。你们说悬不悬?不说车队经过那里正好塌方,哪怕我们迟上几分钟,肯定就被拦在那里,再清理好过去最起码得半天。与死神赛跑的时候,几小时意味着什么啊!”“听说前面的塌方还有两天才能好,王燕是不是啊?”后面的话便听不太清了,因为我已经上楼了。楼上另两间房的灯也亮着,他们将是我今晚的新邻居。透过照向院子的那片光亮,我还是认出了他们就是昨天白天在路上拦车的那三个人。我的心脏竟突突跳将起来,赶紧锁了门熄了灯。
这一夜,我又梦到了隼,依然是那么一只,滑行、俯冲,永无止息。不同的是,梦里的黑白电影不再是无声的,而是有隐约的雷声,紧跟着画面因震颤而模糊,我知道地壳下面的岩石正在撕裂、摩擦发出巨大的能量,但它丝毫影响不了空气,那只鸟还在兀自飞翔。但是,它却戴着白色口罩,阻隔着某些东西的吸入,可它还是发出几声轻微的咳嗽,难道隼真的能咳嗽?尽管隔壁很小心,我还是听到轻轻关门和下楼的声音。等到起床,王燕告诉我他们三个天刚亮就出发了,塌方拦不倒他们,他们走小路。
我不再拒绝王燕的热情,决定穿上那身彝族衣服。还甭说,这一换装还真有点时空转换的错觉,虽然心里明白我还是我。我主动问王燕今天干啥?她说今天才是真正的开茶,我眼尖手快拿起竹篓背上,她笑了,如茶,那样纯粹。
茶园就在寨子后面的山坡上。茶树一坝子摞着一坝子,起起伏伏蜿蜿蜒蜒,整座山看起来就像围了一条又一条的围脖。在满眼的青翠中间,已经有几十个人在采茶了。像一个盛大的节目,她们无论老少,都与我一样,穿着自己民族的衣服,让人一时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一幅画,又像是一首诗,或者一首曲子。只是,中间怎么就跳出了不和谐音,“今天是我们彝族最重要的开茶节。你们看到了吧,这里就是百亩茶园,山川秀美景色宜人,绝对是让人修身养性心旷神怡的好地方。这是正宗的高山茶啊,日月钟秀天地精华,看我手上,这茶和采茶的老妹小妹一样,土生土长自然天成不假雕饰,绝对秀外慧中,碧绿清澈碧玉光泽。现在是明前茶,精华中的精华,别以为不出味,可比山下的茶味浓,喝上几汤仍能涩后生津齿颊留香回味无穷。抬抬你们的小手指,现在就可以预订哟,今天买茶优惠力度最大……”不是那个陈词典吗?怎么哪里都有他?他正手举着杆子用手机直播呢,他并没看到我,只管在茶树和采茶人之间穿来穿去。
本来我以为,我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除了隼。然而我错了,就在这时我却突然看到了别的,不是茶,而是她们。她们中的许多与我不一样,终于我第一次拿出他的相机,紧接着一次次按下快门。
六
他们三个走后,客栈没有增加新的客人。晚上,陈词典却来了,另外还有三四个人,王燕说今天开茶节,活动结束后他们要来喝点小酒。他们都是寨子里的当地人,围在石桌边喝的也是自酿的米酒。
“都说这茶叶杀菌解毒,怎么就对付不了新冠呢?青春才几年?疫情已三年。如今的高危职业啊,依我说,一是当官的,二就是穿白大褂的。”他们中有人抽烟,烟雾在灯光月光交辉中袅袅升起。“看新闻病毒又变异了,什么塔又什么戎,可不能再封城了。这两年旅游算是完了,山货又卖不出去,后面的日子恐怕更难了。”原来他们谈的并不是茶,疫情,多么沉重而可怕的话题啊。我不想听,一时想换个话题。扫一眼周围的人,个个身体健壮肢体完整,我才拿出相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残疾人?”那是我在采茶时偷偷拍的,有一只手的、拄着拐的。陈词典先将相机接了过去,“忘了这是哪里?北川,她们都是经历过大地震的人啊。咦?怎么这么多老鹰噻,还都形单影只,来个比翼双飞噻。”他已经翻到了前面的照片,我一把夺回相机。
“我说,你呀就是掉进成语词典里去了,你怎么不比个冀噻。”几天来,我看到他总是一个人,问过王燕他老婆呢?她没回答。这时旁边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姑娘,你说得对,他就是掉词典里了,不然怎么叫词典呢?”看他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要了碗米酒,居然甜丝丝的,一点不辣。“他不但叫词典,还真有一本词典呢。那我说了?”那人接过话茬儿,并没有征求的意思,已经哗啦啦一通说了下去。“我是信了,人啊,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零八年大地震,寨子全毁了。房子倒的倒塌的塌,学校新盖的楼房也躲不过,几秒钟就一头栽到地上,老师学生哪里来不及跑出来,结果被压在里面,有十几个没扒出来。”陈词典伸出手,“我来说,当时的情况,那是山河破碎惨不忍暏啊,活着的都哭着喊着到处救人,大家徒手在钢筋水泥里搬呀扒呀,能救回来几个?活着的几个也只是杯水车薪望洋兴叹啊。我找到一个,可几个小时,就是救不出来啊,我跪在地上,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迫不得已啊,到最后只扒出来一本成语词典,男孩到死还一直握在手里。”他的脸颊下居然泛出一层月光。“他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孩子,当时都在里面。知道他怎么叫陈词典了吧?”有人端起酒碗,“日子过着过着就攒成了月,又成了年,你看现在不挺好嘛。词典你倒是说说,今天生意怎样?”词典用袖子抹了一下脸,破涕为笑。“一般一般,茶叶不够,亏了杨大那几百斤竹笋救急,真是时雨春风啊,不然我也黔驴技穷,没法子向粉丝交代噻。”词典倒上一碗酒碰上。“他现在可是咱寨子里的首富哟。”王燕给我倒上一碗酒,又有人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词典已笑得咧开了嘴,像迸裂的石榴。“姑娘跟你讲,他这个首富是假的,赚了钱除了家用,都给了男孩的家人了。”“词典可是个好人啊,成天帮我们直播带货,要不是他,我们的店子怕是早关门啦,还有乡亲的茶叶羊羔谁去卖去?疫情根本没有游客,生意没法子做。”
“陈词典,我敬你!”我端起刚倒上的酒碰到他的碗沿,他也端起来,摆出一副正式和认真的样子,让我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我也敬你,再过一天路就要通了,大哥祝你旅行愉快、一路顺风!”刹那间,我哽咽了,“其实,我不是去旅行的,”我发现大家都看着我,于是我借着酒劲,“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再走一走他走过的路,看一看他看过的风景。”我已经忍不住趴在桌上呜呜哭了起来。这已经不知道是我多少次哭泣了,只不过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打开相机,这时他们把头伸过来,“那不是鹰,是隼。知道鹰和隼的区别吗?鹰的翅膀较宽,适合留空,喜欢在盘旋中发现目标,而隼的翅膀尖长,适合冲刺,总是闪电般快速飞行。隼的眼睛大,头顶较平,脸上有黑色的斑纹,鹰就没有这些。还有,隼上喙左右两侧有齿突,那是更好地撕咬猎物,鹰也没有。那些隼都是他——他——拍的。”我俨然变成了他。“他是动物专家?你和男朋友分手了?”有人小心地问。“不是,他是医生,我是护士,我们一起在抗疫,他被感染了,隔离,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层玻璃,但是我摸不到他,直到他——他——他死了——”我已经泣不成声……
七
第二天一早,词典没去当志愿者,也没有做直播,而是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与我们一起的,还有王燕。昨晚我喝多了,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
“这轮疫情赶上清明,就咱山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也不让祭扫,更何况你们城里?”词典停下,在一座墓碑前放了两束鲜花。而在另一座墓碑,王燕也在献花。“我老婆是那所学校的老师,大地震那年儿子读五年级。”我的心猛烈地震动一下,好像也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地震。他的脸又转向旁边,“那里埋的是她的丈夫。”我惊愕了,僵在那里。“灾难来了,总得有人牺牲。”他已一手揽住客栈的王燕,“你们?”“地震,让我的家没了,她的家也没了,之后我俩一起过,又是一个新家。死了的人肯定都愿意看到我们活着的人现在的样子,你说呢?”他居然不再说成语了。我张大了嘴巴,“你俩?”看着他俩相视的一笑,“他忙。”随即我的嘴角和王燕一样变成上扬,溢出像他还在时的一抹笑。
墓园出来,“词典,给我找车,我现在就走!”他俩显然很意外,“明天路通,你带我俩也去看看你相机里的隼噻。”“我不去了,其实我要走的看的,不是藏区的隼,而是他一直战斗的地方!”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同时口中小声地说出一句,“我是要回去呢。我会感激你们的。”也许他们根本没听见,因为他们已经相携着走出了一小段距离。
载我的还是小个子,巧得很,他正好送上来一趟人,他不再提修车的事。车上还是我俩,这次变成他不说话了,也许是怕了我这样难缠的女乘客。我反而成了话痨,不仅让他打开音乐,还有一茬没一茬地找他说着话,“你喜欢海来阿木呀?”“你喜欢李白吗?”“你喜欢谁更多一点?”车内的紧张气氛立刻消除了,他又恢复了喋喋不休常态。
“停停停,倒回去,倒,倒——”当我喊停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到几个人前头一两百米。小个子回头,眼神里满是狐疑,“赶快倒车,我的车费一分钱不少给,免费搭他们啊。”小个子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好勒!”
还是那三个人,我在已经是第三次相遇了,但他们不认识我。“怎么,这是登完山了?”小个子招呼上了。“这不是疫情嘛,突然爆发,还遍地开花,我老婆是医生,她跟医院报了名,要抗疫。她去,我一个人在家多无聊啊,我也去,我到社区,多少能帮上点忙吧。”挤在车后座中间的男子两手分别搭在前排的靠椅上,听他说的语气,他们回去要做的似乎倒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是护士,我也是回去抗疫的。你在哪家医院?”我不失时机地搭上话,车内顿时热闹起来,超过了那晚的小院子。“你们经常去藏区吗?爬的哪座山?下次去也带上我。”“等疫情结束约你啊。”小个子却来了句,“把口罩戴好!”
“那是什么?从天上掉下去了。”透过车窗,只有我知道,那是一只隼,我敢确定那就是一只隼。我的眼中并不再空无一物,我看到了它,我看到了它,就在刚刚,冲过山峦,冲过河流,冲进了另一片有声的彩色梦境……